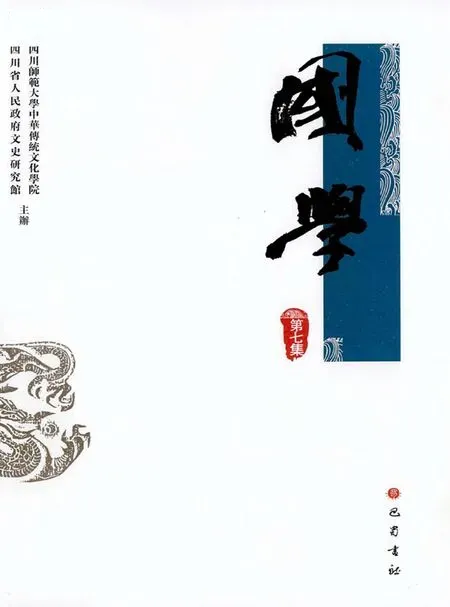轉型期的同光體詩派
胡迎建
一、同光體詩派的形成與發展
“同光體”因清同治、光緒年號而得名,此一説法始於鄭孝胥與陳衍。陳衍《沈乙庵詩序》中説:“吾於癸未、丙戌間,聞可莊、蘇戡誦君(沈曾植) 詩,相與嘆賞,以為同光體之魁傑也。同光體者,蘇戡與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①錢仲聯:《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2 頁。又《冬述四首視子培》云:“往余在京華,鄭君過我邸。告言子沈子,詩亦同光體。”在其詩話中也有類似説法:“丙戌在都門,蘇戡告余,有嘉興沈子培者,能為同光體。同光體者,余與蘇戡戲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②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民國詩話叢編》第1 册,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第18 頁。
作為這一詩體的特徵是,既尊唐也宗宋,尊唐不僅尊盛唐,還要尊中晚唐,重在以宋詩為門徑進入。上繼宋詩運動以來至同治、光緒間的傳統,同光體由體到派有一發展過程。後來陳三立、鄭孝胥成為光緒詩壇的領軍人物,有了大量的跟隨者與崇拜者,“同光體”便成了這一派的標籤。這一説法在當時已流行於詩壇。沈曾植為沈瑜慶所作《濤園詩集序》中説:“近人言同光派閩才獨盛,假有張為圖者,太夷為清奇僻苦主,君(沈瑜慶) 為博解宏拔主乎? 入室誰,及門幾人?”①轉引自錢仲聯主編:《歷代别集序跋綜録·清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49 頁。“同光派”的説法,標明同光體已被目為詩派而非僅詩體。
道光、咸豐時期國力漸衰,士大夫有以天下為己任之志,扭轉世運,其詩亦力求新闢途徑。其時大學士祁雋藻與侍郎程恩澤宣導學杜韓,身為重臣的曾國藩更號召學黄山谷,以糾詩壇甜熟淺滑之弊。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等紛紛響應,蔚然成風,一時稱為宋詩運動。
同光體之興稍晚於宋詩運動,大抵五十年後。陳衍將道光以來的詩學依照詩風的不同,分為二大派:“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捩,略别兩派。”其“清蒼幽峭”一派,特徵是“洗練而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以陳沆為標志、魏源為羽翼,此派“近日以鄭海藏為魁壘”;其“生澀奧衍”一派,力求“語必驚人,字忌習見”,以鄭珍為“弁冕”,以莫友芝為“羽翼”,“近日沈乙庵、陳散原實其流派”②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則四,《民國詩話叢編》第1 册,第47—48 頁。將同光體作家從鄭孝胥追溯到陳沆、魏源,將陳三立、沈曾植一派追溯到宋詩運動的代表人物鄭珍、莫友芝。後來黄曾樾整理陳衍的説法,作為其説的補充:
同光而還,鄭海藏、陳聽水(陳寶琛)、陳木庵(陳書) 三先生出,以宛陵、半山、東坡、放翁、誠齋諸大家為宗;同時江右陳散原先生力祖山谷,於是數百年來之為詩者,始一變其窠臼,大抵以清新真摯為主,海内推為同光派③陳衍:《陳石遺先生談藝録序》,《民國詩話叢編》第1 册,第700 頁。。
曾克耑詩云:“晚清詩壇述流别,變風變雅聲鏗鏘。”(《答懺庵次元韻》) 光緒、宣統詩壇活躍,開始形成各種流派,詩派之多,為詩史所少見,其局面恰如黄遵憲詩云:“世變群龍見首時”(《酬曾重伯編修》)。錢仲聯認為這一時期的成就“達到了唐宋、清初以來的一個新的高度,成為中國古典詩歌在它發展後期矗起的又一座高峰”④錢仲聯:《近代詩壇鳥瞰》,載《社會科學戰綫》1988年第1 期,第276 頁。。同光體詩派在衆多流派中脱穎而出,影響最大。
同光體詩派人物主要活動於武昌、江寧。張之洞幕府是促成同光體形成的契機。光緒十五年(1889) 十一月,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次年創辦兩湖書院,招邀四方人才廣集武昌。陳三立曾記述當時盛況:
當是時,張文襄方督湖廣,競興學建兩湖書院,選録南北高才數百人,設科造士,海内名儒名哲就所專長,延為列科都講,特置提調員,拔君重院事,余以都講式闕,謬承乏備其一人焉。院中前後鑿大池,長廊環之,穹樓複閣臨其上,歲時佳日,輒倚君要遮群彦,聯文酒之會,考道評藝,續以歌吟。文襄亦常率賓僚臨宴雜坐,至午夜乃罷,最稱一時之盛①陳三立:《余堯衢詩集序》,《散原精舍詩文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56 頁。。
光緒二十年(1894),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在江甯宣導風雅:“光緒乙未……時南皮張文襄公總制兩江,崇尚風雅,以詩相鳴。”②李宣龔:《濤園詩集跋》,《李宣龔詩文集》“碩果亭文集”,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9年,第331—332 頁。其時鄭孝胥在張之洞幕府,沈瑜慶主持籌防局事。
次年底,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聘陳衍、沈曾植在兩湖書院主持教席,邀鄭孝胥前來辦理蘆漢鐵路新政。陳、鄭、沈是促成同光體詩派形成的重要人物,三人均有詩學卓識,有共同愛好與旨趣,在武昌的機緣湊合,激發詩興,切磋詩藝,熱烈探討,明確認識,共同提出同光體的詩學觀。然此年初陳三立往長沙,侍其父陳寶箴推行新法,與此三人未同時居武昌。
同光體詩派的形成與張之洞有莫大關係。曾克耑説:“散原、海藏、石遺三先生則是張孝達的幕客,憑着他們的政治後臺關係,所以也就等於卿相的居高一呼,便開出—種新風氣,成了一種新派系了。他們不衹呼了一下便了事,他們有論詩的宗旨,對於古人的詩有新發現和新評價,而他們的作品又能够實踐所言。各人有各人的面目,各人有各人的意態,同歸殊途,總結一句,是要用最好方法做出最好的詩歌,所以他們便佔了清代詩壇最重要的位置了。”③曾克耑:《論同光體》,載《頌橘廬叢稿》第四册,香港:新華印刷公司,1961年。
同光體領軍人物為陳三立、鄭孝胥。楊聲昭説:“光宣詩壇,首稱陳、鄭。海藏嚮稱簡淡勁峭,自是高手。若論奧博精深,偉大結實,要以散原為最也。”④楊聲昭:《讀散原詩漫記》,《散原精舍詩文集》附録(中),第1237 頁。李漁叔認為:“自散原出,與海藏雁行,乃各攜爐韝,成一代之作矣。”⑤李漁叔:《魚千里齋隨筆》,《散原精舍詩文集》附録(中),第1247 頁。
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人,中進士後棄吏部主事職,在長沙依其父參與推行新法。戊戌政變後退居江寧,鋭意為詩。有《散原精舍詩集》。鄭孝胥,字太夷,别號海藏,閩侯人。曾到日本作神户、大阪總領事,後為京漢鐵路南段總辦,曾為龍州邊防督辦;參與維新與立憲活動。“九一八事變”後,挾溥儀出關,在偽滿洲國任國務總理,成為大漢奸,後去職而病死。有《海藏樓詩集》。
同光體重要人物還有:陳衍,字叔伊,號石遺,侯官人。光緒八年九月中舉。後任學部主事。清亡後任無錫國學專修館教授。著有《石遺室詩話》《石遺室詩話續編》,編《近代詩鈔》。大詩論家、大選家。有三大功勞:一是與鄭孝胥共同舉旗,提出同光體概念與内涵,對同光體進行初步分派;二是編詩鈔,著詩話,保存一代文獻,記載近代詩壇諸多交遊活動;三是選評詩標準主要看他是否“有感於詩與時世相關切”①錢仲聯:《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並指出其人詩學淵源。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號乙庵,嘉興人。光緒間進士,任刑部主事時,贊助康有為等維新變法,後歷任江西、安徽按察使。清亡後居上海。著有《海日樓詩集》。
陳寶琛(1848—1935),字伯潛,號弢庵,福建閩縣人。光緒元年(1868) 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為江西主考官,擢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被革職,歸故里二十年。宣統元年復原職。清帝遜位後,他侍奉溥儀為師。
沈瑜慶(1858—1918),字志雨,號愛蒼,别號濤園,侯官人。曾在江寧委辦水師學堂,後歷任山西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官至貴州巡撫。
陳曾壽(1878—1949),字仁先,湖北蘄水人。清末進士,官廣東道監察御史。民國初,隱居不出,後往偽滿洲國任文書吏。
范當世 (1854—1904),字肯堂,號伯子,江蘇通州 (今南通) 人。光緒十一年(1885) 任武邑信都觀津書院山長。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號觚庵,浙江紹興人。光緒十六年(1890) 進士,授刑部主事,後任江南陸師學堂兼附設礦務鐵路學堂總辦。
民國初年,流寓上海的遺民、遺老,禊集賦詩,結超社、逸社,切磋詩藝,唱和編刊,期待着詩運的中興。其中大多為同光體詩人,再次迸發創作高潮。他們的傳統文化素養較高,有充裕時間從事詩歌創作與研究活動,能將詩藝提高到新的水準。但其詩或惋惜或哀嘆,懷舊氣息相當濃重,也有不少是檢討清末政治的腐敗。同光體詩派繼續發揮領袖舊體詩壇的巨大作用,其他派别則影響式微,有的改宗宋詩,受同光體影響,或者可以説,同光體猶如一塊磁石,吸引其他派的詩人改變了詩學門徑。所以林庚白從反的方面也説出了同光體詩派在當時的廣泛影響:“民國詩濫觴所謂同光體,變本加厲。”②林庚白:《今詩選自序》,《今詩選》1940年出版,轉引自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2 册,第1403 頁。
民國以來,在南京創辦的南京高師、東南大學、金陵大學等高校,重視傳統文化的繼承,網羅不少江南名彦以及海外歸來學有所成者。一批同光體詩派後學如王瀣、胡小石、胡翔冬、胡先驌、邵潭秋、汪辟疆等進入高校或文化界,他們中的不少人,會通中西文化,並創作舊體詩,培養學生,潛承同光體之傳統,出現學者詩人群體。大約在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前夕,詩派之畛域漸歸泯滅,同光體詩派也走完其歷程。
二、同光體詩為變風變雅
汪辟疆認為:“有清一代詩學,至道(光) 咸(豐) 始極其變,至同(治) 光(緒)乃極其盛。”①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5 頁。“詩至道咸而遽變,其變也與時代為因緣。然同光之初,海宇初平,而西陲之功未竟,大局粗定,而外侮之患方殷,文士詩人,痛定思痛,播諸聲詩,非惟難返乾嘉,抑且逾於道咸……在此五十年中,士之懷才遇與不遇者,發諸歌詠,憫時念亂,旨遠辭文。”②同上,第283—284 頁。同光體接續道、咸時期宋詩運動之後再放異彩,詩歌與時代共嚮發展。龔鵬程認為,同光以前詩作多為“一己之哀感”,至同光時代則發生改變,“詩非一己之哀戚,乃時代之寫照。國家不幸,賦到滄桑,亦非某氏之窮通,抒懷感憤,實有理想與辦法指寓其間,更非空為大言者。詩至同光為一大變,猶時自唐代中葉至道咸,道咸以後亦為一大變也”③龔鵬程:《説晚清詩》,《近代思想散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202 頁。。這裏説的是整個同治光緒年間詩風,然用於同光體詩派最為恰當。此詩風之大變,乃為一時代風氣所釀成,故以同光體命名此詩體,有其相當之理由,或可代表一時期詩壇之主流,也説明同光體領軍人物有總攬一代詩風的雄心。
同光體的興起,與社會亟變、人心思變、思潮競起的晚清世運相關。此派與宋詩運動一脈相承,均産生於變風變雅時代,但外患更亟,國運更衰。變法失敗,更使詩人心靈蒙上了陰影,他們看到改良無望,清廷也難以維持,但害怕清廷垮臺,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但後來社會劇變發生,帝制被推翻,他們最擔心的是傳統文化也隨之斷絶,所以其詩作最能反映這一轉軌時期的現實與内心的痛苦。陳衍多次談到時代與詩創作的關係,在《祭陳後山先生文》中説:“惟言者心之聲,而聲音之道與政通,盛則為雅頌,衰則為變雅變風。”④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7 頁。在《山輿樓詩敘》中説到變雅特徵:“余生丁末造,論詩主變風變雅,以為詩者人心哀樂所由寫宣,有真性情者哀樂必過人,時而齎諮涕洟,若創巨痛深之在體也。時而忘憂忘食,履決踵,襟見肘,而歌聲出金石、動天地也。其在文字,無以名之,名之曰摯曰録,知此可與言今日之為詩。”⑤同上,第1089 頁。在《小草堂詩集敘》中更進而説到同光體詩風形成的原因與特徵:“詩至晚清同光以來,承道(光) 咸(豐) 諸老蘄嚮杜、韓,為變風變雅之後,益復變本加厲。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淩厲之筆,抒哀痛逼切之辭,甚且嬉笑怒駡,無所於恤。”①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4—1075 頁。在皇權統治發生危機時,詩不僅嬉笑怒駡,甚至敢於指斥時政,以“突兀淩厲”之筆法,抒“哀痛逼切”之情感,這就是陳衍對同光體詩風總的認識,並認為這與道光、咸豐以前模山範水、吟風弄月的詩風大不相同。這正是《詩大序》中所説:“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同光體詩人對詩之變雅變風可説是達成了共識。石銘吾詩云:“諸公丁世亂,雅廢詩將亡。所以命辭意,迥異沈(德潛) 與王(士禎)。”②石銘吾著,曾楚楠編校:《慵石室詩鈔》,潮州市饒宗頤學術館,1997年。(《讀石遺室詩集呈石遺老人八十八韻》) 鄭孝胥對清朝廷的腐敗無能有所不滿,認為這是一個衰世,“世衰士益放”(《答沈子培比部見訪夜談之作》)。同光體詩人大都經歷過戊戌變法時的變故,他們看到專制王朝難以為繼的總趨勢,卻對現實無可奈何,故詩作往往哀婉過人,真摯沉痛。陳三立詩云:“國憂家難正迷茫,激蕩騷雅思荒淫”;“陸沉共有神州痛,休問柴桑漉酒巾”(《次韻黄知縣苦雨二首》);“滔天禍水誰能遏,繞夢冰山各自傾”(《建昌兵備道蔡伯浩重來白下》)。似已預感到天翻地覆的劇變,所以潘若海説陳三立“掩淚題詩續變風”(《贈伯嚴吏部》)。沈曾植詩云:“長嘯宇宙間,斯懷吾誰與”(《長嘯》);“浩劫微生聚散看,空江老眼對辛酸”(《答石遺》)。痛定思痛,詩風哀婉淒切,不難看出清末行將崩潰的社會在同光體詩人身上留下的陰影。慘佛議論鄭孝胥詩,也覺察到了時代與詩的關係:“鄭詩境界尤狹,無復雄博氣象,則亦時代為之乎!”③慘佛:《醉餘隨筆》,轉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光宣朝卷》第18 册,第12937 頁。
民國初年政局不穩,更成亂世。清遺老、遺民紛紛僑寓上海、天津、青島等地,或退歸故里,衹有極少數人轉入民國政權中任職。政治制度大轉軌給他們帶來不安與焦慮,空前的文化震盪與急劇轉變更使他們精神極為痛苦。陳三立詩云:“滿意魂翻變徵聲,彌天哀憤坐中傾”(《訪楊子琴同年不遇》);“復傾肝膈疊吟詠,寄痛略依變雅説”(《次答蒿叟疊用東坡聚星堂詠雪韻寄懷》);“醉魂併入淩雲氣,世患收為變徵歌”(《和答閑止翁見贈同屙韻》);“爬抉物象寫離亂,自然變徵音酸楚”(《八月廿八日為漁洋山人生辰補松主社集樊園分韻得魯字》)。多首詩中寫到“變徵”“變雅”,正是“亡國之音哀以思”。
清遺老們的傳統文化素養較高,又有充裕時間從事詩歌創作與研究活動,能將詩藝提高到新的水準。但他們的詩或惋惜或哀嘆,懷舊氣息相當濃重,也有不少是檢討清末政治的腐敗。他們結社禊集,切磋詩藝,唱和編刊,期待着詩運的中興。此期間,無論是同光體還是湖湘派還是詩界革命派諸子,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對清王朝的懷念和對袁世凱政權的抵觸,曾有的政治隔閡不再是溝通的障礙,他們會聚到一起抒寫着荆棘銅馬的異代之悲。康有為於民國二年(1913) 回國後與陳三立、俞明震、沈曾植詩歌交往密切。梁啓超此時在他主辦的《庸言報》上刊登陳衍的《石遺室詩話》,傳播了同光體詩派在民初的聲望。王闓運赴滬,與沈曾植、陳三立、樊增祥等交遊,促成了超社的成立。一種情緒的融通再塑了民國的詩壇。
民國時期,同光體繼續發揮領袖舊體詩壇的巨大作用。其他派别則影響式微,有的改宗宋詩,受同光體影響,或者可以説,同光體猶如一塊磁石,吸引其他派的詩人改變了詩學門徑。
三、同光體詩派學古求變以創新
在詩派衆多之時,“同光體”衹有翻新求變,找到自己的出路,纔能獨具風貌。宋詩刻意精深的内容與講求句法的特質,為“同光體”學古而求變提供了通道與藉鑒。同光體諸大家識見高明,以學宋詩為途徑,這與他們認同當時乃為變風變雅時期有關。他們偏重於悲壯美、瘦峭風格,與詩多苦語相應的是,詩多硬語。無論“生澀”還是“幽峭”,其詩句都傾嚮於拗峭而不平直,勁健而不疲軟。這些内質都與宋詩靠近,然而並非局限於宋,而是力求走出宋詩光環,上溯唐詩,超唐軼宋。
就詩家個人而言,大多同光體詩人都經歷過學古途徑的多次選擇。他們在變古創新的道路上作過多種嘗試,纔確定以何者為主,何者為輔。如陳衍標榜他“於詩不主張專學某家”①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三,《民國詩話叢編》第1 册,第579 頁。,應取法多人,如果“但專學一家之詩,利在易肖,弊在太肖。不肖不成,太肖無以自成也”②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四則六,《民國詩話叢編》,第200 頁。。其詩先後學過白居易、梅堯臣、楊萬里、陸游諸家,“新穎清切,晚近頗喜用俗語俚字攙入”③由雲龍:《定庵詩話》卷下,《民國詩話叢編》第5 册,第585 頁。,則為學白居易所致。這也就是王鎮遠之所以要從閩派中析出元白派的原因。
陳三立早年學漢魏南朝詩,中年以後學韓昌黎、黄山谷,“辛亥亂後,詩體一變,參錯于杜、梅、黄、陳間矣”④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四則十,《民國詩話叢編》第204 頁。。沈曾植初喜張籍、李商隱、黄庭堅,繼學梅堯臣、王令,晚出入杜、韓、梅、王、蘇、黄間⑤見陳衍:《沈乙庵詩序》,《沈曾植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2 頁。。也更提出過三關,效法至劉宋元嘉間,然“不取一法,不壞一法”。鄭孝胥“三十以前,專攻五古,規杬大謝,浸淫柳州,又洗練於東野。沉摯之思、廉悍之筆,一時殆無與抗手。三十以後,乃肆力於七言,自謂為吴融、韓偓、唐彦謙、梅聖俞、王荆公,而多與荆公相近,亦懷抱使然”⑥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則五,《民國詩話叢編》,第21 頁。。同光體詩人從個體到群體幾乎都存在前後詩風不一的現象。他們在幾十年的創作道路上,努力尋求新的最能表現自己的道路,其創作道路有變化的軌迹可尋,這也正是同光體與宋詩運動諸大家不同之處。
同光體詩人既固守傳統樣式,同時在藝術上乃至用語措辭方面力求創新。如梁啓超説陳三立“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①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轉引自《散原精舍詩文集》附録(中),第1225 頁。。此説未必對,與詩界革命派相似,陳三立也採用新異之語,吸收白話、新詞彙入詩。這類詞多半是隨着社會發展而出現的詞彙,但與詩界革命派連篇滿紙的羅列不同,衹是選擇適當,務求妥帖融化。如:“家庭教育談何善,頓喜萌芽到女權”(《題寄南昌二女士·周衍巽》);“安得神州興女學,文明世紀汝先聲”(《視女嬰入塾戲為二絶句》);“要知天機燦宇宙,海底星辰搜一網”“希臘竺乾應和多”“世健者知誰何”(《次韻答王義門内翰枉贈一首》);“主義侈帝國,人權擬天賦”(《次韻答黄小魯見贈三首》);“人權公例可灌輸”(《雪晴放舟題寄樂群學舍諸子》);“憲法頓輸灌,合彼海裔轍”(《除日祭詩和劍丞》);“地方自治營前模”(《除夕被酒奮筆書所感》);“莫從報紙話兵戈”(《曉暾、公約相過》);“等為玩具誇留存”“飛車潛艇難勝原”(《和東坡詠雪浪石》);“救亡苦語雪燈前”(《挽嚴幾道》) 等。這些詩句中的詞語,為古代所無,令人感到親切,表明陳三立對新思潮、新觀念、法制以及科技新産品的瞭解。當然,僅用若干口語、新名詞,並不足以言新,要開拓詩境,還是要着力於煉字,善於取象,推陳出新。如梁啓超評陳三立詩所云:“每翻陳語逾清新。”(《廣詩中八賢歌》) 務求新奇,融注主觀情感,擴大並豐富了詞彙量與表現力,有的形成了奇詭意象,但詩中確實有過於艱澀處。李漁叔論陳三立:“惟其姿禀英邁,又以讀書之博,導其思力,回入篇章,乃或過矜,貪於字句精新,惟饒奇致。”②李漁叔:《魚千里齋隨筆》,轉引自《散原精舍詩文集》附録(中),第1247 頁。“貪”字包含有陳三立致力於創新出奇的努力,又有因此而造成的過於艱澀之意。
就陳三立所代表的同光體來説,如同唐代元和體,是新變之體,其成就啓後人以無數法門。就二千年詩史來説,它總結屈原以至鄭珍之經驗,為古典詩之殿軍,同時又為舊體詩的嬗變開了先聲。即便對“五四”以後新詩而言,它為之作了先導,提供了參照系,李金發的“朗月卧江底”與陳三立詩“一痕山卧煙”,聞一多的“好容易孕了一個苞子”與他的“千山孕緑待啼鵑”(《次韻季祠齋居即事》) 等詩句頗為相似。
如何看待陳三立,究竟是古典詩歌的最後結束者,還是開風氣者,有待重新認識。二十年前,有人將陳三立稱為“古典詩歌的末路英雄”③馬衛中等:《中國古典詩歌的末路英雄——陳三立詩壇地位重新評價》,《社會科學戰綫》1989年第1 期。,十多年前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也認為他是“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中最後一位重要的詩人……他的創作也表明在一定範圍内古典詩歌形式仍有活力”①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下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90 頁。。
之所以持此説,乃是有見於古典詩歌在詩壇上讓位於白話新詩,既然古典的、傳統的詩被打倒了,没落了,退出歷史舞臺,那麽“同光體詩”也就失去了價值,陳三立也就理所當然成了最後一位重要詩人,“末路英雄”,推論大抵如此。甚至有人認為陳三立衹不過是“為古典詩歌作了一個悲酸而又不失體面的收束”,即使對前人有所超越,“也很容易被熟爛的形式所銷熔,被豐厚的前人遺産所淹没”②劉納:《陳三立:最後的古典詩人》,《文學遺産》1999年第6 期,第84—92 頁。。其立論基礎是,古典詩早已形成完整嚴密的詩歌系統,音節與情感韻律已經定型,詞語方式與意義的穩固契合造成意型的老化、硬化,語言的衰象、形式的熟爛,使得詩的創意無比艱難,所以古典詩不過是迴光返照。這一論斷否定了舊形式的可繼承性、可利用性、可改造性。形式有相對穩定性,但其情感、詞義相對而言是活躍的、可變的,而韻律衹是一種通用規則,按照規則仍可如魔方般千變萬化。可惜持論者仍沿襲五四時期“一班新人物”以形式主義看事物的眼光。
近十年來,一些年輕學者的觀點與前者已有很大不同,他們看到陳三立與同光體詩人及其後學努力創新的一面,認為其詩作顯現出舊體詩的活力。他們將其詩的求新求變看作是“現代轉型”。如楊劍鋒對劉納等人的觀點作出針鋒相對的評判:“陳三立對舊體詩歌的現代轉型所做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應被視為用舊體詩歌創作的現代詩人”③楊劍鋒:《從散原詩歌的意象變革看舊體詩的現代轉型》,《近代文學學會第十四届年會論文集》下册。。筆者基本同意此説。
作為同光體詩派的領軍人物,陳三立“用詩古文辭主東南壇坫者幾三十年”④袁思亮:《跋義甯師手寫詩册》,轉引自《散原精舍詩文集》附録(中),第1219 頁。。沈其光説:“自散原老人提倡江西詩派,海内宗之。”⑤沈其光:《瓶粟齋詩話》第4 編上卷,見《民國詩話叢編》第6 册,第706 頁。羅敷庵詩云:“散原品節匡山峻,老主詩盟一世雄。”(《呈伯嚴丈》) 以他和以他代表的同光體詩,成為同時代或後學一大批詩人的典範。受同光體影響,民國詩壇,多宗宋詩。吴宓説:“近世中國舊詩人多為宋詩,宗唐者寡。”⑥吴宓:《空軒詩話》22 則,《民國詩話叢編》第6 册,第43 頁。“多為宋詩”並非某一人有此能力,這也是由於時代、社會變化諸種因素所形成局面,但與陳三立為代表的同光體成就與影響是分不開的。
然而同光體詩以及舊體詩還有拓展之前途。著名學者胡先驌指出,詩應富孕理致。胡先驌(1894—1968) 字步曾,號懺庵,江西新建人。早年留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獲林學碩士歸國。先後任南京高師、東南大學教授。在北平創辦静生生物研究所。他是舊體詩的守望者,針對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之論而作《中國文學改良論》(載《南京高等師範日刊》,1919年《東方雜志》轉載),認為文學革命之説偏激,是將中國文學不惜盡情推翻。但他又從時代的發展、中西對比的角度來看待舊體詩的前途。他在《評嘗試集》一文中説:“清末之鄭子尹、陳伯嚴、鄭蘇堪不得不謂為詩中射雕手也,然以曾受西方教育、深知西方文化之内容者觀之,終覺其詩理致不足,此時代使然,初非此數詩人思力薄弱也。”①張大為等編:《胡先驌文存》,南昌:江西高教出版社,1995年,第58—59 頁。可見他對近代以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舊體詩應如何發展有更高的視野,認為詩應表現理致。錢鍾書有《胡丈步曾遠函論詩卻寄》詩云:“汲古斟今妙寡雙,袖攜西海激西江。中州無外皆同壤,舊命維新豈陋邦。”論其所作貫通古今中外,傳承創新。這也印證了早些時候范罕所説:“比歸,語故弟彦矧曰:‘胡君新詩人也。’ 予弟曰:‘然亦舊詩人,今之同學輩殆無與匹者。”②范罕:《懺庵詩稿序》,臺灣中正大學校友會編:《胡先驌先生詩集》,1992年臺北刊本,第2 頁。新在新思理、新境界,舊在仍用舊詩形式。
四、同光體詩人作品的傳播
與當時文化界主流重在革新,倡新詩、白話文不同,他們重在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維繫,通過《東方雜志》《庸言》《學衡》等現代媒介,繼續傳播他們的詩作,傾訴心聲,施展影響。所以林庚白從反的方面也説出了同光體詩派在民國時的廣泛影響:“民國詩濫觴所謂同光體,變本加厲。”③林庚白:《今詩選自序》,《今詩選》1940年出版,轉引自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2 册,第1403 頁。
楊萌芽博士認為:“1912年後,陳衍在梁啓超主編的《庸言》雜志上發表《石遺室詩話》,是近代宋詩運動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的標志。1915—1920年宋詩派以《東方雜志》為陣地,發表了大量作品,同光體成為席捲民國時期古典詩壇的一種文學思潮。在《東方雜志》詩文欄内發表的1700 首詩中,其中百分之七十屬於宋詩派詩人的創作。學衡派是一個精神淵源上和宋詩派很相似的團體,人事上也有諸多糾葛。通過宋詩派與這些文學群體的研究,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凝聚力很强、對民初其他文學力量有較大影響的團體。清末民初宋詩派是一個介於傳統文學流派到現代文學社團之間的過渡性文人群體,體現了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過渡的複雜性。”④楊萌芽:《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研究——以1895—1921年為中心》,復旦大學博士論文。這是同光體在民國時期影響極大的實證,但楊氏及一些學者每以宋詩派作同光體之代稱,似不妥當,宗宋詩人極多,但不能簡單説成是宋詩派。此之前還有翁同龢,瓣香蘇、黄,力倡宋調;嚴復心儀王荆公,多有和作;張蔭桓接武蘇東坡,歌行尤肖。但這些人通常也不能看作同光體或宋詩派。
20年代,吴宓、梅光迪、胡先驌創辦《學衡》刊物。胡先驌負責詩選,後交由邵潭秋負責,發表了不少同光體詩派詩作。沈衛威説:
由於胡先驌的關係,《學衡》雜志上大量刊登江西人的詩,且作者大都宗法宋詩(江西詩派),使得《學衡》雜志的“文苑”成了“江西詩派”之絶響,南社社員之餘音……同時宗法“宋詩”,崇尚“江西詩派”的同光體的許多詩人成為《學衡》的作者,也有非《學衡》作者的黄侃、胡小石等,和非江西籍的《學衡》作者汪東、王伯沆(瀣)、胡翔冬等宗法“宋詩”。而胡小石、胡翔冬本是李瑞清門人。20世紀30年代,在中央大學、金陵大學,這批宗法“宋詩”的詩人,還結為“上巳社”和禊社,同時吸引了文學新人如沈祖棻、程千帆等隨他們學習舊體詩詞①見《作為文化保守主義批評家的胡先驌》,載《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3 期。。
自1927年起,由曹纕衡接辦舊體詩園地《采風録》,附載於天津的《國聞周報》中。至1937年停刊為止,共出刊近五百期。“自同光諸老、並世名宿以至南北學校青年學子之作,惟善是求,無不登載。”(王仲鏞《借槐廬詩集後記》) 同光體詩人是其中的主要作者。當時遠在貴州的李獨清,在《潔園剩稿》自敘中就説道:“晚清之際,詩風丕變。讀《采風録》,時有伯嚴、乙庵、肯堂諸老之作,心竊好之,復沉潛於《散原精舍詩》《海日樓集》《石遺室詩話》諸書,更知有所謂同光體者。”②李獨清:《潔園剩稿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 頁。藉助現代傳媒而瞭解名人詩作。在南京還有《國風》半月刊刊登舊體詩。1935年《民族詩壇》創刊於漢口,盧前主編。其宗旨是建設民族詩歌,主張詩在内容上寫民族精神、愛國之志,形式上溝通新舊詩體。
1940年中正大學在泰和縣成立,校長胡先驌、文史系主任王易都好吟詩,由此調動校内教授的吟興,創辦的《文史季刊》,以刊登贛派詩人作品為主。同時江西省參議會創辦《江西文物》,開闢“贛風録”欄目、“紀念陳三立”專欄。這一類報紙雜志,前後相繼興起,不僅維持詩學傳統於不墜,且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也發揮了極大的影響。
五、同光體贛派、閩派、浙派
同光體詩派由於隊伍龐大,學古途徑、創作手法各異,早有人進行再分支派的研究。陳衍在《石遺室詩話》中,將道光以來至同光間的詩,按詩學淵源、風格分為清蒼幽峭、生澀奧衍二派。兩派即汪辟疆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一文中所説“閩贛派”。細分則為贛派與閩派,分别以陳三立、鄭孝胥為領軍人物。龍榆生説:“晚清詩壇,鮮不受陳、鄭影響,儼然江西、福建二派;江西主山谷、宛陵,福建主後山、簡齋、放翁諸家。”③龍榆生:《中國韻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 頁。錢仲聯承汪辟疆“閩贛派”之説:“百年以來,禹域吟壇大都不越閩、贛二宗之樊,力蘄咳唾,與之相肖。金陵一隅,尤為贛派詩流所萃。”①錢仲聯:《唐音閣吟稿序》,霍松林:《唐音閣吟稿》,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 頁。
贛 派
贛派詩人的活動地域主要在南京與南昌兩地。陳三立長期居南京,推崇者衆,不少前輩詩人、在位或退隱的詩人交遊。新生代學者詩人,也奉其為一代宗師。還有皖、粵、浙、閩等地,均有宗宋詩人受其影響。誠如吕貞白詩云:“縱録大海掣長鯨,詩陣宏開擁主盟。高座記曾親謦欬,得沾餘溉到鯫生。”(《追憶陳散原丈》)
從詩歌淵源來看,贛派可定名為韓黄派,即師法韓愈、黄庭堅,近代則效法陳三立。贛派與宋代江西派相比,並非冥搜枯索,刻畫雕琢,而是熔情采於理趣之中,去枯澀而存奧瑩,去生硬而取嫵媚,學古而不泥於古。詩人各就性之所近,趣味之所投,既有緊隨陳三立學詩者,也有出入江西派而能自張一軍者。
贛派由四部分人組成:(一) 江西籍贛派詩人,他們近步陳三立,遠宗宋詩,以黄山谷、陳後山為主,上窺杜、韓,如程學恂、華焯、胡梓方等。胡先驌説:“自陳散原先生出,始重振西江緒餘,夏吷庵、華瀾石、黄百我、楊昀谷諸前輩亦能各樹一幟。”②以上見《胡先驌文存》,第313 頁。夏敬觀主要學梅堯臣,與鄭孝胥相近。錢仲聯説:“近代江西詩家,陳散原後最負盛名者推夏劍丞。其詩並不學山谷,而為宛陵之清苦。”③錢仲聯:《夢苕庵詩話》則四十,《民國詩話叢編》第6 册,第178 頁。
後起之秀有王浩、吴天聲等。陳三立説:“過南昌,所遭鄉里英俊少年六七輩,類多偏嗜山谷,效其體,竭其才思,角出新穎,竊退而稱異,殆西江派中興復振之時乎?”④陳三立:《培風樓詩存序》,《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6 頁.又説:“吾鄉英異少年則多依山谷,懸其鵠而争自立。王君簡庵、然甫兄弟才俊而學勤,號尤能窺藩籬而振墜緒者也。”⑤陳三立:《思齋詩序》王浩《思齋詩》,1924年王易刊本,第2 頁。他滿腔熱忱推許王氏兄弟、胡詩廬等年輕江西詩人,寄托重振江西詩風的希望。
抗戰期間,贛北淪陷,贛省政治、文化重心移至泰和縣。詩人輾轉流離,至此稍得安定,遂多憂憤之作。當時以舊省府職員為主成立“澄江詩社”。抗戰勝利後,在南昌成立“宛社”。儘管時世亂離,生活維艱,仍能活躍詩壇,正如涂世恩詩句云:“西江宗派今當盛”(《送四弟之浦城》),維繫了江西半個世紀以來的舊體詩傳統。
(二) 贛派學者詩人,能在傳承中蜕變,風格由生澀奧峭轉為崛健。部分為江西籍人,如辛際周,萬載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歷任《民報》主筆,廈門大學教授,江西省志館總纂。發揚贛派傳統,有詩云:“詩派衍吾鄉,千載資溉灌。屹屹義甯叟(陳三立),殿砥波流濫。繼明仗後起,西江燈未暗。”有《灰木詩存》。其詩採山谷之瘦峭,融後山之深婉,近法陳散原,其莽蒼沉雄自成一格。
汪辟疆,彭澤縣人。京師大學堂畢業後,歷任心遠大學、中央大學教授。他期待詩的理想境界是:“能於旖旎存風骨,且學婀娜見雪肌。”(《學詩一首示浚南》) 遠受韓昌黎、黄山谷、陳後山等人影響,近受陳三立影響,是贛派後學中既能創作又擅長研究的中堅。
王易(1889—1956),字曉湘,號簡庵。京師大學堂畢業後,歷任中央大學、中正大學教授。詩有黄山谷之錯綜句法,陳後山之堅蒼骨力。弟子涂世恩,豐城人。中正大學副教授。著《彊學齋詩存》。自言“及事簡庵(王易),導以李杜蘇黄之途,旁及後山、簡齋二家。”(《與懺庵論詩書》)
邵祖平(1898—1969),字潭秋,南昌人。在東南大學任教時結識陳三立。爾後到之江大學任教時,又與適來杭州寓居的陳三立切磋詩文。著有《培風樓詩存》《續存》。陳三立序其詩集云:“冥搜孤造,艱崛奧衍,意斂而力録,雖取途不盡依山谷,而句法所出頗本之,即謂之仍張西江派之幟可也。”陳衍在詩話中舉其《自祖堂登牛首》等五首之後説:“以上古近數篇,皆酷似散原者,‘峰尖’ 一聯尤神似…… 《後湖三絶句》亦神似散原。”①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三則七十二,《民國詩話叢編》第1 册,第579—580 頁。
還有涂公遂(1904—1991),修水人。曾在開封河南師院任院,後往香港任珠海書院中文系主任,其詩效法陳三立,形神俱肖,風格蒼秀。有《浮海集》。
還有部分是在南京高校中任教的贛派詩人,但並非江西籍。如中央大學教授王瀣,字伯沆,江蘇溧水人。金陵大學教授胡翔冬,安徽和州人。苦心吟詩,避俗避熟,力求新怪。還有胡光煒,字小石,嘉興人。歷任東南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教授。兩人壯年均從陳三立遊。
(三) 陳三立五子,衡恪、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均能詩。陳衍説:“散原諸子多能文辭,余贈陳師曾詩,所謂‘詩是吾家事,因君父子吟’ 者也。”②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二十一則五,《民國詩話叢編》第1 册,第285 頁。
(四) 其他贛派詩人,如詩風逼肖陳三立的有貴池人劉詒慎。金天羽在《龍慧堂詩集序》中論其詩:“堅蒼藴藉,中涵禪理,句法時學散原。”③轉引自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81 頁。合肥人李彌庵,煉字造法學陳三立,龍澗老人論其詩云:“幽深瘦勁,其秀在骨,精光外溢,直繼散原、海藏,了無愧色。”當塗人奚侗,民國初年官江浦縣知事。陳衍説他“詩語奇崛,余嘗敘其詩,以為近於散原一派者”①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二十九則十七,《民國詩話叢編》第1 册,第395 頁。。
羅惇曧,羅敷庵兄弟,廣東順德人。其詩力追黄山谷、陳後山,刻意求新,風格簡遠。錢基博認為:“其在散原,亦猶蘇門之有晁張也。”②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編“古文學”,上海:上海書店,2004年,第191 頁。
香港傅子餘説:“辛亥而後,革命党詩人之最著名者為胡漢民。胡氏寢饋於荆公之詩甚深,加以記憶力最强,有過目不忘之譽。其詩喜用人名為對,用事準確不移,又無一首不與家國有關。故言民國之詩,莫不首推漢民,陳融翼而助之。……顧陳氏致力後山,與其高弟熊英沆瀣一氣,若其門下諸子,則多趨嚮於兼葭樓詩。此外,與胡陳同輩而聲氣相孚者,又有廖仲愷、朱執信、陳樹人及胡氏之弟毅生。但胡、陳二氏及其同輩,仍步同光後塵,未能自闢一途,以津逮來者。”③傅子餘:《二十世紀名家詩選序》,毛谷風編:《二十世紀名家詩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4—5 頁。將胡、陳兩人歸於同光體後學。還有陳寂(1900—1976),廣州人,陳永正認為其詩“大體上都是清末同光體詩人學宋一路”④陳永正:《枕秋閣詩詞略論》,《當代詩詞》2011年第1 期,第103 頁。。
閩 派
以鄭孝胥為首的閩派,以陳衍為理論家。在香港傅子餘説:“此派以鄭孝胥為主,而鼓吹之力,則出自陳衍石遺,其《近代詩鈔》及《石遺室詩話》早已風行全國,影響至六七十年代。當日閩中詩壇,名位最高者為陳寶琛,次為沈瑜慶,而何振岱、周達、林旭、李宣龔為其羽翼。”⑤傅子餘:《二十世紀名家詩選序》,毛谷風編:《二十世紀名家詩選》,第4 頁。閩派宗宋詩,又有宗嚮宋某家或幾家傾嚮的不同,謂之支派亦可,與贛派陳三立獨居尊座的情況不同。不過,閩派群雄並起,而後學既尊其師,又受其他名師的影響,兼取他派之所長。既有門户,又不拘門户之約束,這其實是詩壇分化衍派的興盛表現。
繼鄭孝胥而起者李宣龔,字拔可,號墨巢,閩縣人,為近代一大作手。章士釗《論近代詩家絶句》中云:“閩嶠詩家鄭與陳,君來應是第三人。”肯定他在閩派中的地位為鄭孝胥、陳寶琛之後第三人。楊鍾羲説:“余謂閩人詩,滄趣典遠,其緒密;海藏清剛,其氣爽;拔可出稍後,深粹堅栗,境界日辟,亦不以千里畏人者。”⑥楊鍾羲:《碩果亭詩序》,《海藏樓詩集》“附録三”,第548 頁。
閩派中的陳書、陳衍一支,詩宗白居易、陸少游。陳書,號木庵,是陳衍伯兄,近代學者並未將他看作同光體的重要人物,但他詩風清新,變革了閩詩的宗唐風氣。陳衍詩弟子,著名的有黄浚、黄曾樾,後者師從陳衍時,記其説詩語而有《陳石遺先生談藝録》。還有梁鴻志,錢基博説他“足以張西江之壁壘,而殿同光之後勁者也”①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編“古文學”,第192 頁。。
閩派中還有何振岱、王允皙、林旭、郭曾炘、郭則壽等人,初受鄭孝胥影響,宗法韋應物、柳宗元,又受陳寶琛影響,以王安石、黄庭堅、陳師道為門徑,上溯韓愈。
還有曾克耑,閩侯人,為同光體之後勁。錢仲聯説他:“其祈嚮所在,似不外肯堂、散原二家。古體全學肯堂,差能具體,近體則以范、陳樹骨,參以異派之長,與近代閩派詩人取徑絶異。”②錢仲聯:《夢苕庵詩話》複九,《民國詩話叢編》第6 册,第350 頁。胡先驌評其詩云:“健筆雄篇,上逼杜韓,高格超出閩詩範圍甚遠,洵一代之大手筆,五十年來所稀見也。”③見胡宗剛編:《胡先驌先生資料長編》,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643 頁。
浙 派
錢仲聯在《論同光體》④錢仲聯:《論同光體》,載《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第115—118 頁。一文中,從贛派中析出浙派,乃因沈曾植同時有袁昶,後有金兆蕃宗法相同,還因沈曾植主張過三關,將陳衍三元説(開元、元和、元祐) 通到元嘉(劉宋年號),廣泛吸收自南朝以來的詩歌之長,詩學觀與贛派稍有異。
袁昶,字爽秋,號浙西村人,浙江桐廬人。官太常寺卿時,八國聯軍進犯大沽,他反對圍攻使館與對外宣戰,被清廷處死。由雲龍説:“漸西村人袁爽秋,亦學宋體者而好用僻典,與嘉興沈乙庵有同調焉。”⑤由雲龍:《定庵詩話》,《民國詩話叢編》第五册,第583 頁。其詩清健近黄山谷。
沈曾植的傳人金蓉鏡(1856—1930),字甸丞,號香嚴,浙江秀水人。清末官兵部主事,民國後歸故里。從沈曾植學詩,改變詩風。還有王蘧常,嘉興人,任教於無錫國專。陳衍説:“嘉興王瑗仲蘧常,沈乙庵高足也,與常熟錢仲聯萼孫為文字骨肉,刊有《江南二仲詩》,大略瑗仲祈嚮乙庵,喜鍛煉字句。然乙庵詩雖多佶屈聱牙,而俊爽邁往處正復不少。”⑥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一則二十五,《民國詩話叢編》第1 册,第488 頁。
同光體詩派陣營中,浙派人數最少,影響也小,曲高和寡,是此派影響小的重要原因。但這一派具有學人之詩的特徵,從傳統詩的發展來看,詩言理趣,也許是未來最有價值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