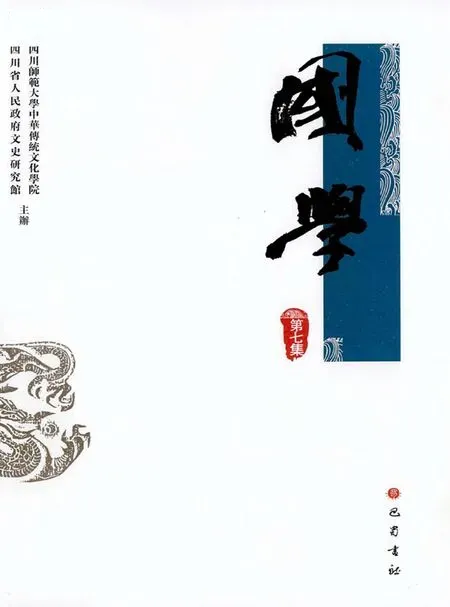國學“運動”主流意義的闡釋
——謝桃坊國學史研究述評
郭一丹
自20世紀90年代初國學熱潮再度興起以來,關於國學的理解可謂言人人殊,例如以為它是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或將它等同於中國學術,或認為它以研究儒學為主,將琴棋書畫等技藝也作為國學研究的内容,等等。面臨此種紛繁複雜,實有必要認真考察國學運動的歷史經驗,進行正本清源的工作,回歸一份純粹與精深。謝桃坊先生少年時代曾從劉杲新先生學習傳統文化,20世紀50年代在西南師範學院中國語文系學習時,自學中國思想史,泛觀博覽中國古代典籍,廣泛涉略,從《周易》到《宋元學案》、從《四書》到《諸子集成》、從《廣韻》到《新訂六驛館叢書》,以及地方志與筆記雜書等國學基本典籍。他在多年從事古代文學的研究工作中,接觸了更多歷史文獻,也從來没有停止過對國學相關問題的思考。先生自1981年以來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工作,以詞學研究為主,尤其在當代詞學理論建設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先生自2006年因詞學研究可以告一段落,遂轉入國學研究,他以理論的、歷史的方法,認真考察了20世紀初年以來國學“運動”的歷史,對重要國學家的學術理論進行總結,對國學研究的性質、對象與方法等有了自己的論斷。先生經過多年的黽勉努力與艱苦探索,近十餘年來已出版《國學論集》《國學史研究》和《四川國學小史》等專著,發表了系列國學研究論文,近年還負責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與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館所主辦《國學》集刊的審定工作。先生對國學性質的理解,或尚難獲一致認可,但亦有學者充分肯定,先生的主要貢獻在於對國學運動主流意義的闡釋。拜讀先生有關論述,我對國學運動衆多學術意見有了一定瞭解,理解純學術的治學原則,也理解他們明知可能“淺表或褊狹”而仍然堅持己見、卓爾自立的初心不改。國學研究者對於真理王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的追求和純粹獨立、找尋真知的沉潛精神,令人肅然起敬,故不揣冒昧,對先生國學相關論著,謹作述評。
一、什麽是國學
長期以來,學界談論國學,各執一詞,令人困惑,國學的普及以及通俗化,又引發一些新的争議。謝桃坊以國學“運動”為考察物件,從中梳理對國學認識的發展過程,發現“國學”的共性在於對傳統文化中許多狹小的學術問題或者文史批評公案的考證,認為我們之所以對“國學”言人人殊,難以確定内涵,原因在於學科觀念的缺失,在無形中習慣於將學術研究、研究基礎和國學普及工作混為一談。謝桃坊旗幟鮮明地為國學正名,為國學研究物件界定一定的研究區間,對國學的性質、研究物件、研究方法、研究意義作了必要厘清與説明。
國學的性質是什麽? 謝桃坊認真考察了始於20世紀初中國學術界的國學“運動”,仔細檢討這段學術思想的歷史過程,總結出國學“運動”中的幾種學術意見:一、國學即儒學。“以儒術為主,取讀經而會隸之”,以“四經”(《孝經》《大學》《儒行》《喪服》) 為“統宗”。謝桃坊指出,這種意見並不是從學術觀念出發來理解國學,而是藉由它來推行儒家倫理道德,畢竟時過境遷,以儒家價值觀念强加今之國人是緣木求魚,煎水作冰。這樣的定位超出了國學應該承擔的學術責任,他認為國學的研究物件遠比儒學更為廣博。二、國學是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中國過去的文化史。謝桃坊認為,這種看法擴大了國學的研究物件,關涉諸多學科,如果“以國學統一中國學術,其發展的結果是對國學的消解”①謝桃坊:《國學辯證》,《學術界》2007年第6 期。,他强調,國學衹能專精於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值得探究的學術問題,而非不加鑒别,照單全收。三、國學為史料學。謝桃坊認為,儘管國學研究特别重視材料和證據,必須在佔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研究某一學術問題,但史料學僅僅是研究的基礎或前期準備,它不是國學本身。四、國學為中國學術思想史。謝桃坊認為,學術思想等“流轉變遷之大勢”是哲學的研究物件,國學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學術思想本身,更專注於文史考證。五、國學即“中國學術”。總之,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經世之學,無所不包,無所不能。在謝桃坊看來,“中國學術”是不具學科意義的,如果包羅萬象、過於龐雜,就意味着無法開展具體的、專業的研究工作,國學應當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他説:“我們考察國學運動期間發表的重要論著的傾嚮,便可見到它們具有一種共同的學術性質……這些論著所探討的是中國學術的頗為細小的問題,它們涉及中國的經部、史部、子部和集部的典籍,採用傳統的考據方法以作極深入的專門問題的研究。”①謝桃坊:《國學辯證》,《學術界》2007年第6 期。在謝桃坊看來,國學是中國學術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學術需要有“以考據見長的國學家”“涉及文獻與歷史的狹小學術問題”的考證。國學作為一門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學問,具有綜合性的特點,而國學新傾嚮最能體現國學“運動”的本質特徵,我們認識國學的性質應當以國學新傾嚮為依據。儘管他也意識到,這難免會被質疑褊狹或者淺表,但他仍然堅持這纔是最接近國學本質的。在謝桃坊看來,國學的特徵是“以科學考證方法研究中國文獻與歷史上存在的狹小而困難的學術問題”②謝桃坊:《關於國學的特質與價值的認識——回顧對國學運動新傾嚮的批評》,徐鼎一主編:《藝衡》第七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2年。謝桃坊:《國學辯證》,《學術界》2007年第6 期。。因此,國學其實是近世新興的一門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綜合性邊緣學科。而作為一門學科,它“從國學思潮的産生,整理國故的進行,文史研究的開展,考據方法的提倡,到近年國學熱潮的再度出現,經歷百年的努力,國學作為學科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了”③謝桃坊:《國學辯證》,《學術界》2007年第6 期。。在謝桃坊眼中,國學作為一門專業學科的條件已經具備。
國學研究的主要物件是什麽? 謝桃坊認為,一方面,國學研究物件涉及廣泛學術領域,學術結構層次複雜;另一方面,國學研究的物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問題,以及中國文獻與歷史中狹小的學術問題,其本體是關於中國古代文獻與歷史上存在的問題,或中國學術史上存在的狹小問題,例如典籍真偽、版本源流、文本校勘、文字考釋,等等。還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的許多重大的學術問題和文史批評公案,如中國上古史的斷代、中華民族的起源、儒家學説與政治的關係、天人合一説的本義與演變、新儒學的學術特徵,等等。國學也將中國古代實用技術作為研究物件之一,但切入點是它們在歷史文獻與歷史上存在的狹小的學術問題,如《詩經》農事詩考釋、茶引的起源、《黄帝内經》的作者,等等。這些複雜而困難的學術問題,都屬於國學的研究物件。謝桃坊强調國學研究物件是狹小的、特定的,認為涉及宏觀的、理論的研究是應歸屬其他各學科來解決的。一言以蔽之,謝桃坊眼中的國學即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文史研究”,具有較强的綜合性、邊緣性、學術層次的複雜性。
二、國學“運動”的兩種基本傾嚮
謝桃坊總結國學“運動”的兩種基本傾嚮的特徵,着力探討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粹派,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潮派的學術思想,對其濫觴、發展、主要特徵、學術價值,一一考察,總結國學思潮的經驗或教訓,説明我們認識國學的主要性質。
在20世紀初,崇尚中國傳統文化的學人對西學東漸的飆發電舉、沉醉西風而憂心忡忡,擔憂在言必稱希臘、滿腦子歐風美雨中潛藏着中華文明或將失落的風險。他們堅決反對凡是言治興學皆取法西方,擔憂如此這般終將喪失中國的民族文化傳統,最後招致“化附於人”。他們堅信,衹有古典經籍纔是立國的根基與道德的源泉。他們宣導保存國粹,樹立文化自信。他們成立國學保存會、國故社,創辦國粹學報,刊行《國粹學報》《國故月刊》,極力弘揚傳統經典,這“是由一些民族主義的學者們為保存中華傳統文化而湧現的學術思潮”①謝桃坊:《胡適開啓國學研究的新方嚮》,《國學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主要學人有鄧實、吴之英、劉師培、黄侃、陳漢章、唐文治等,章太炎是“國粹”陣營的代表人物。
謝桃坊對章太炎的國學思想詳加考察,對其治學成就予以充分肯定,也對他脱離學術軌道的治學之路進行歷史反思。章太炎在國學“運動”之始,適應了文化思潮之需,他講經學、史學、玄學、文學,對顧頡剛等後輩學人的學術素養與追求均有積極啓發與帶動;章太炎對《春秋》見解深刻,對揚雄“善惡混”人性學説、對於《莊子·齊物論》的主旨,對法家與政治之關係等的見解,堪稱精湛卓識,獨具隻眼;他系統講述國學基本知識,涉及國學概論、派别、國學本體的認識,如“經史非神話”“經典諸子非宗教”“歷史非小説傳奇”,均眼光獨到,見地深刻。謝桃坊在肯定章太炎學術成就時也指出他的不足之處:缺乏對經史與神話、諸子與宗教、歷史與小説關係的嚴格界定、區分,顯得混沌無序;精治小學,旨在解釋經典,通過文字進入古人的思想,指責新學“以今文疑群經,以贗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許書,以臆説誣諸子”;既忽略古代經典或者文本背後的具體歷史場景,又罔顧新的時代語境。而之所以存在這些不足,皆因章太炎胸懷“修己治人”理想,欲脱離純粹學術軌道,去試圖承擔重大的社會使命,這就註定他的學術研究衹能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國”而已。儘管“章太炎對每種學問的源流概括而深刻,但‘國學’ 是晚清時期的一個新的學術概念,特指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之專門學問,而中國傳統學術本身卻非‘國學’”②謝桃坊:《章太炎與國學普及工作》,《古典文學知識》2012年第3 期。。在謝桃坊看來,章太炎贊同章學誠“六經皆史”説,視“六經”為史,這與以董仲舒、何休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家視“六經”為孔子政治學一樣,都並不符合“六經”性質,衹能算是兩種不同的學術價值觀念。章太炎精研儒家經學,經世致用觀念根深蒂固,他治學總是在“求是”“致用”之間猶豫不決,摇擺不定,最終混合成了“今日切要之學”,意圖藉此樹立儒家的政治理想,實現“讀書保國”的政治理想(鄧實,1904)。謝桃坊認為,這種治學其實“遠離了清代乾嘉學派的治學旨趣,也遠離了真正的學術,在某種意義上是以文化保守主義的態度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抵制……國學如果按照章太炎的‘統宗’ 發展下去必然會走到國粹主義的絶路的。”①謝桃坊:《評章太炎的學術思想與方法》,《國學論集》。他意在説明,這種治學實為國粹派的根本病竈所在。總之,誠如傅斯年1935年《大公報》發表的《論學校讀經》一文中所指出的“皇帝的新裝”一樣,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朝代都不是靠經術而得天下、造國家的,經學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畢竟有些力不能勝,迂腐不堪了。
在治學方法上,章太炎通過辨書籍真偽,通小學、明地理,知古今人情之變,辨文學之應用。章太炎所講國學並非國學研究意義上的國學,例如《國學概論》中國學的派别,“將國學分為經學、哲學和文學三大派别,它們實為儒學演變的歷史、諸子之學和宋明理學、古文和韻的知識”②謝桃坊:《章太炎與國學普及工作》,《古典文學知識》2012年第3 期。。章太炎衹相信經史記載,而總是懷疑、否定新材料、新方法,他好奇惡新,最終走入困境。謝桃坊認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學和文學等構成一個系統整體,是治國學者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章太炎對國學的理解從國粹主義觀念出發,已經不合時宜,“國學運動若按照保存國粹、志於復古的方嚮發展下去必然是中國學術的倒退,從而阻礙中國學術現代化的進程”③謝桃坊:《胡適開啓國學運動新方嚮》,《國學論集》。。總之,在謝桃坊看來,廖平代表今文經學派的尾聲,章太炎代表古文經學派的終結,今後“國學運動的新發展不再重複他們的道路了”④謝桃坊:《雲夢學刊》2009年第1 期。。謝桃坊意在告訴我們,傳統治學固然有積極意義,但是我們絶不能泥古拘方,而應該具有足够的學術理性,應合理利用傳統優秀思想資源,在新時代條件下去作適當的變通與創新。他啓發我們,學術發展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繼替的過程,學術研究就是一個在繼承中創新,在替换中繼承,逐漸完成現代化轉型,並且始終行走“在路上”的過程。
國學新傾嚮的出現是國學“運動”發展的轉捩點,謝桃坊對它的形成與發展,新的學術特徵,學術價值進行考察。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粹派可謂一時大張旗鼓,轟轟烈烈,這引起宣導新文化的學人們警醒與反思,他們也在苦苦思索傳統文化的賡續利用與民族學術的應時發展問題。1922年,蔡元培主導成立了以胡適為主任的北大季刊國學組,他們致力於“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擺脱“儒術一尊”的桎梏,警惕培養出過猶不及的“復古的種子”(周啓明)。他們對中國學術的新方嚮心嚮往之,上下求索。隨後,《國學季刊》刊出,國學“運動”中新思潮嶄露頭角。胡適首先引入實用主義方法,繼而,傅斯年引入德國歷史語言學派,他們皆以中西結合的方法研究中國文獻與歷史上狹小的、困難的學術問題。他們重事實、重證據,取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與中國傳統考據方法相結合,成為國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河南安陽殷商甲骨文、甘肅敦煌藏經洞敦煌文書、清代内閣大庫檔案等發現與研究不斷開闢學術領域,刷新學術視野,二十餘年間,實可謂俊才輩出,成果豐厚。
胡適是為中國學術謀求解放的先行者,他從新文學轉入國學研究,從學理上批評並否定國粹觀念,提出新的國學理論,促進國學“運動”走嚮新的發展道路。他主張“輸入學理”“再造文化”,提倡以批判態度、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在1923年《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他説:“國學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過去的中國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在具體研究中,胡適採用中國傳統考據學,貫通“四部”,並運用中西結合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屬於純學術性質,是在更高的學術境界中探尋真知,為許多學科提供基礎的、事實的判斷依據。胡適以小説考證樹立了國學研究的新典範。他以新文化批判態度看待傳統文化,希望在研究“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中去辨析“國粹”與“國渣”,掙脱儒家經學的束縛,將國學作為純學術加以研究。胡適提出“整理國故”的治學路徑,就是條理系統地整理出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頭緒,尋求每一種學術思想源流與路徑綫索,用科學方法對有關文獻作盡可能的精確考證,盡力去洞悉奧義。他提出索引式整理、結賬式整理、專史式整理,讀本式整理等幾種方法。胡適認定整理國故的重點是在中國的學術思想方面,治國學要從文本的解讀,歷史的考察,辨偽存真,做出實事求是的學術評價,這樣便兼顧到了經典文本與具體的時代語境。這種治學路徑運用科學的程式,運用反思批判的眼光,具有現代學術研究的特點。在胡適看來,治國學的原則,就是尋求“無數細小問題的細密解答”,“文化史的寫定終自依靠這一點一滴的努力”。他形象地比喻説,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在“爛紙堆”裏“打鬼”、“捉妖”,以圖“解放人心”;國學研究的價值在於“為真理而求真理”,因為尋求真知本身就是人類的一種天性。學術研究不應該先存狹義的功利觀念,治國學就應有精神的自由,應持堅定的學術信念。謝桃坊也指出,胡適的“整理國故”其實衹是整個國學研究系統的一個部分,如果將整理國故與國學研究等同起來,這便混淆了兩個不同的學術層面。此外,國學研究還具有與西方學界進行學術競争的意義。西學東漸以及西學擴張,正是國學應時而起的歷史背景,西方漢學成果衆多,成績斐然。國學研究的真諦,正如一位外國漢學家所感慨的,中國的學術問題還得由中國人自己論定,“非異邦人所能為”。的確,國學研究正如郭沫若所説,是“鼓睛暴眼的文字實在比穿山甲、比蝟毛還要難於接近的逆鱗”,很多問題衹有中國學人纔能更為貼切地去接近,通過傳統、科學、細密的考證去探尋其古奧冷僻的歷史的“真影”。國學承繼了自宋代以來,特别是近三百年形成的傳統考據學的深厚淵源,“實係地道的國貨”(胡適)。上千年的學術與思想傳承,衹有中國學人纔能堪當此任。當然,胡適也面臨過諸多質疑,胡適回應説,“應時勢之需”、古人“通經而致治平”的夢想這些狹義的觀念是治學者應當與之保持距離的。謝桃坊評論説,在這次針對胡適的批評中,主要問題在於國粹派“將儒家政治倫理所代表的傳統文化精神與對這種文化的學術研究混為一談,因而從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的視角而否定學術研究的意義。國學研究是不關心傳統文化價值的,它通過對傳統文化中若干狹小的學術問題進行考證而作出的結論,可能成為新的事實依據,創造了新知,由此可以掃除歷史上存在的謬妄或迷信,求得一種真知”①謝桃坊:《關於國學的特質與價值的認識——回顧對國學運動新傾嚮的批評》,《國學史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38 頁。。當然,胡適對國學的理解也有偏頗,謝桃坊説:“儘管他主張輸入新的學理,並將整理國故作為再造文明的一個條件,而實際上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國學研究的意義在認識上仍是不够清楚的。”②謝桃坊:《為中國學術謀解放— —胡適開啓國學研究的新方嚮》,《天府新論》2008年第6 期。然而,瑕不掩瑜,大醇小疵,胡適的貢獻在於導引國學從社會政治、倫理道德和儒學相分離,使中國學術走嚮現代學術的道路;胡適的“疑古”精神對國學“運動”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重大指導作用,直接影響到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傅斯年為代表的歷史語言學派,這兩個學派勃然興起,鬱鬱蔥蔥地發展壯大,成為國學“運動”中的兩大主流學術派别。
三、國學“運動”新傾嚮的兩大流派
謝桃坊總結國學新傾嚮的兩大流派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傅斯年為代表的歷史語言學派。1926年起,《古史辨》的刊行標志着古史辨派的誕生,1928年起,《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刊行標志着歷史語言學派的興起,它們都是在新的國學觀念下採用科學考證方法研究國學的先進典範。
顧頡剛早年聽過章太炎的國學講座,開闊了學術視野。1921年,他請胡適搜集資料,助其完成《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他從胡適那裏讀到晚清崔述的《東壁遺書》,深受震撼,深得啓發。他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沈兼士、馬裕藻的助教,從事整理國故工作,編輯《國學季刊》,《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等,接觸到羅振玉、王國維的相關著作,立志“要使古書僅為古書而不為現代的知識,要使古史僅為古史而不為現代的政治與倫理,要使古人僅為古人而不為現代思想的權威者”,堅決不讓“舊思想再在新時代裏延續下去”。1927年,他任教於廈門大學,又編《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成長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1921年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册,顧頡剛、羅根澤、吕思勉、童書業分别擔任各册主編,作者有胡適、顧頡剛、錢玄同、吕思勉、傅斯年、郭沫若、楊嚮奎、蒙文通……在他們當中,有史學家、有考古學家、有經學家、有文學家、有哲學家、有文獻學家以及文字學家,他們大都是以疑經、疑古的精神來探討中國古史的,這就是人才輩出、疑古辨偽的古史辨派。
一直以來,中國學術界將古史辨一派納入史學範疇,謝桃坊並不認同這種看法,認為其研究成果多為關於先秦古籍辯偽、諸子考辨,以及秦漢學術史問題,並非盡屬史學的研究範疇。他們的治學方法基本上屬於中國傳統的考據方法,因此從學科歸屬劃分,應將古史辨學派歸入國學,而不應歸於史學。謝桃坊的判斷並不是為了標新立異所做的任意妄斷,而是將這種判斷建立在對學術成果全面分析的基礎之上的。他認為,古史辨派對三皇五帝考鏡源流,固然要採用史學方法,但此外仍需要訓詁考證等方法。例如,《説文解字》中關於“禹”“堯”“舜”“夏”“姬”“姜”等字本義的訓釋,與“古帝”的關係等,更需要大量古籍辯偽工作纔能開展研究;而討論古史所依典籍是否可信,則需要用文獻學的而非史學的方法去解決;此外,還需要用社會學的方法對傳説、歷史進行理解與解釋。《詩經》是文學研究的物件,而古史辨派通過考據,證實孔子並未删述六經,未曾删訂《詩經》,進而否定了漢代經師的“美刺”説,他們辯證《詩序》的附會,揭示《詩序》附會史事的錯誤。古史辨派考證《商頌》年代,重新考釋《國風》若干詩篇,等等,這些探索與討論,採用的是研究古書的方法,但都不屬於純粹的史學研究。針對學術界“所用的材料不是古史的材料,所用的方法不是研究古史的方法”的質疑,顧頡剛回應説:“我誠然是專研究古書,誠然是衹打倒偽史而不是建設真史。但是,我豈不知道古書之外的種類正多着,範圍正大着,又豈不知道建設真史的事比打倒偽史為重要。我何嘗不想研究人類學、社會學、唯物史觀等等,走在建設的路上……我不但自己衹能束身在一個小範圍裏做深入的工作,而且希望許多人也都能束身在一個小範圍裏做深入的工作。”①顧頡剛:《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三册《自序》,第6 頁。這一回應,正説明他們就是以考據方法研究中國文獻與歷史上細小的學術問題,承認相關研究並非盡為史學研究,而是屬於國學研究。顧頡剛在《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發刊詞》中説國學“是中國的歷史,是歷史科學中的中國的一部分。研究國學,就是研究歷史科學中中國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學方法去研究中國歷史的材料”。謝桃坊認為這種説法使國學概念的界定趨於確切,這裏所理解的國學,就是用科學的考證方法研究中國的歷史文獻。
顧頡剛理解的國學研究物件是“中國歷史的材料”,即歷史文獻,研究方法是科學的方法。胡適認為清代考據學是與西方的科學實證方法的精神一致,但國學研究方法是在以西方實證主義為方法論,以中國傳統考據學為具體方法的,它比傳統考據學更為進步。在顧頡剛眼中,清代學者辛苦集聚很多材料,為後輩學者們“取精用宏”創造了基礎條件;清代學者大都是信古的,卻給了後輩學者“做疑古之用”;清代考據學“校勘訓詁是第一級”,古史辨派“考證事實是第二級”。國學不等於簡單的名物訓詁與校勘,而是對文獻與歷史事實進行細密的、科學的考證,它超越了清代考據學,但也繼承了清代樸學“凡立一義必憑證據”“孤證不為定説”,表述樸實簡潔的學術品格。謝桃坊在肯定古史辨派高潔獨立的學術品格之時,也指出顧頡剛對於國學的論述存在一定缺陷。他對國學理解過於狹隘,考據學儘管是一種符合科學精神的中國傳統治學方法,但在具體應用中,是需要研究者的沉潛精神與嚴謹態度的,否則容易造成失誤,造成以訛傳訛。他説:“綜觀古史討論和國學研究中的許多學術問題,它們仍處在争論之中,而這些研究仍需不斷地進行,因為舊的‘因襲和謬妄’ 被掃除了,又滋生了新的‘因襲和謬妄’。國學研究的意義就在於以細密的考證方式澄清中國學術史上諸多‘因襲和謬妄’ 的事實。”①謝桃坊:《古史辨派在國學運動中的意義》,《學術界》2009年第4 期。但無論如何,國學新傾嚮和國學研究的新方法在古史辨派的研究成果中得到集中體現,他們既藉鑒西方近代實證主義方法論,又繼承了中國傳統考據學,研究中國歷史與文獻上的狹小學術問題,始終堅持純學術的道路。古史辨派的基本特徵與歷史語言學派可謂不約而和,不期而遇。
中國歷史語言學派的創始人是民國時期“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這位十一歲時就已經讀完《十三經》的才子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在1918年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發表《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一文,歷陳“東方思想界病中根本”。他説:“中國學人,不認時間之存在,不察形勢之轉移。每立一説,必謂行於百世,通於古今。持論不同,望空而談,思想不宜放之無涯之域。欲言之有當,思之由軌,理宜深察四周之情形,詳審時代之關係。”他又説:“中國學人,好談致用,其結果乃至一無所用,學術之用,非必施於有政,然後謂之用,凡所以博物廣聞,利用成器,啓迪智慧,熔陶德性,學術之真用存焉。”總之,中國學人大都喜歡“大言炎炎,憑空發抒”,然則其實往往以龐大之詞,空發議論,真正的切時之論則乏善可陳,或者是“真理或為往古所囿”……這些病痾、基本誤謬、不良之特質是應該掃而除之,除之後快的,是應該在學習西方先進學術思想之前就需要克服的。傅斯年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長達二十三年,周圍凝聚了大批學術菁英群體,如岑仲勉、王明、楊志玖、芮逸夫、董同龢等等,刊行專書七十多種,相關研究論文發表五百多篇,為中國的學術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至今他們所創辦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在臺灣地區仍在刊行。
歷史語言學派也主張用自然科學實證方法,認為這種方法與中國傳統考據學精神有異曲相通之妙,他們這一派衹是在組織機構、擴充材料、擴充工具、研究範圍、治學精神等方面與古史辨派略有差異。受德國蘭克學派影響,傅斯年對蘭克學派“史學即史料學”的治學途徑極力闡釋與推崇。他將“歷史與語言”熔鑄一體,賦予特定内容,創立“中國歷史語言之學”。歷史語言學派既具有國際學術視野,又主張“不以空論為學問”“不以史觀為急圖”“就史料以探史實”,不妄自臆測,或者比附成式了事。記録語言的是文字,文字用以記載史事,“歷史”即中國傳統文化,是廣義的歷史概念;“語言的材料”即文獻資料,屬於史料。謝桃坊理解“歷史語言學”就是“歷史文獻學”。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歷史語言學派的宣言,它追溯中國歷史語言學淵源,探尋奧義,用科學方法整理史料。謝桃坊認為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史學,也非傳統意義上的語言學,而是同其他學科甚至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有了一定的可通約性,它仍是屬於國學研究。
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都是歷史語言學的“幾個不陳的工具”。歷史語言學派歷史組主要搜集史料、進行文籍考訂;語言組主要作方言調查,語言學研究,考證文字、語音、語義等問題;考古組主要作考古發掘工作;人類學組搜集人類學資料,考辨少數民族族源。這足以證明,歷史語言學派的研究已經形成一個新的綜合性學科。他們的部分理論方法來自西方,但面對西方漢學家的學術成就與競争壓力,他們不盲從自卑,具有應有的文化自信。他們認為,西方學者畢竟“讀中國書不能親切,認中國事實不能嚴辨”,尤其文字審定、文籍考訂、史事辨别等工作,往往還是本土學者最可勝任。因此,中國歷史語言學趕超西方漢學,致力於與之争勝,這種勇氣、鋭氣與底氣值得敬重。他們致力於改變陳陳相因的傳統研究範式,提倡採用西方近代的地質學、地理學、考古學、生物學、氣象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的方法為工具來整理史料,重視資料搜集、考察、實驗,並按合理科學的程式進行。因為,歷史上的某問題、某事件,當在比較各種性質的文獻記載之後,纔有可能發現矛盾、疑難、真偽,再加以科學考證,纔有可能去尋得歷史的真實。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就是通過細緻考辨,而不是通過哲學或思想史方法進行研究的。他針對清代阮元《性命古訓》進行考辨,得出不同結論,證實宋明理學有關“性命”之説在學理上成立,並使用新的甲骨文和金文資料,也採用西方語言學音素分析等新方法。謝桃坊認為,這種研究並不屬於哲學研究,它們衹是為哲學提出新的事實依據的基礎性研究,是屬於國學研究的。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説》採用歷史地理學方法,對亳、殷、商、帝丘、窮石、東夏、華夏、塗山、戎夏等古地名進行考證,引用大量先秦史料及域外金石文獻資料,提出中華民族起源的新見解。這裏所探討的是中國古代某個具體問題,採用自然科學與考據學結合的方法,力圖去解決一個狹小的學術問題,為古史研究提供事實依據。此外,陳寅恪、徐中舒、朱希祖、李濟等一大批學者的研究成果無不體現了這種鑽研精神和科學方法的結合。國學與歷史語言學都採用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方法,但在具體研究中國歷史與文獻存在的若干狹小問題時,還得回到傳統考據學上去,以圖整合,再次出發,衹有“雙流匯合”,方成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考證①謝桃坊:《致中國歷史語言之學於自然科學之境界中——論傅斯年與歷史語言學派在國學運動中的意義》,《社會科學戰綫》2014年第9 期。。
歷史語言學派的成果主要發佈平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是具有國際學術影響的大型學術集刊,集中體現歷史語言研究學派的宗旨和學術特色。論文多是考證性的,以新資料、新工具、新問題見長,以自然科學與中國考據學相結合的科學考證方法,對中國歷史與文獻狹小的學術問題做一些窄而深的研究。在謝桃坊看來,它們實即國學研究論文。衆多繁豐、細密的考證成果,如涓涓細流匯成湯湯流水,引領人們去深入探勘歷史長河的真實面目,亦如無數細小視窗的次第開啓,拼接成真切觀察中國歷史文化的落地窗扇。
專崇尚科學考證的國學,包括古史辨派和歷史語言學派,在中國現代學術系統中是應有合理地位的,但它們的學術價值和作用又的確是有限的。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他們都從未刻意放大這種研究的意義,説他們的研究衹不過是“專崇技術工作”,“不見得即是什麽經國大業不朽之盛事”,甚至或許衹是“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罷了。這種專業、精深、清醒與自謙的認識,其實也遮蔽不了中華民族求真求實、追求真理的光華。
四、國學研究的科學方法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嚮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就純學術而言特别看重西方的科學方法,介紹西方科學方法遂成為一種學術風尚。科學方法本是西方近代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當其被介紹入中國後,廣為社會科學研究所採用,尤其為國學家們所採用,這亦源自西方近代的實證主義哲學思潮。近代實證主義者將觀察、實驗、比較、歸納等自然科學方法引入社會科學,强調對客觀現象的研究,認為自然科學方法是社會科學新的研究方法。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國學新潮學者所提倡的科學方法主要來源於美國的實用主義,以及德國的歷史語言考證學派。這裏需要説明的是,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認為,乾嘉時代的考據學方法的實證精神,與科學實證精神是有相通之處的。嚴復為中國學術界引進了西方邏輯的實測内籀之學,對國學研究同樣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梁啓超認為科學方法就是善懷疑,善尋問,不妄徇成説,不囿於一己之臆見,旨在極力求真;原始要終,縱説録説,盡其條理,備其佐證;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明者,啓其端緒,即使一時或有未盡,而能使後來者因其所啓者而競其業,等等。謝桃坊認為梁啓超的概括是較為全面深刻的,這種客觀求真態度正是科學精神的體現,專門的、系統的、重證的、比較的研究,就是科學的國學研究方法。
胡適提倡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清理國故的功夫,“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主張一分材料説一分話,三分材料説三分話,“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幾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作一番系統的整理。胡適在國學“運動”中提出的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和在國學研究中採用的科學方法,即是他將美國實用主義引入中國的方法。在他的國學研究中,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是中國古代白話小説考證,以新文化思想在學術界確立了新的國學觀念,以整理國故來切實開展國學研究。他關於中國古代長篇白話小説的系列考證,成為聯繫新文化運動和整理國故的紐帶,有助於白話文學語言的建設,為中國學術開拓新方嚮,打開新通路。顧頡剛等發起的古史討論是整理國故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古籍的辨偽與古史的考辨,沿用發展胡適提倡的科學方法,將衆多散亂零碎的材料用科學方法分析、分類、比較、試驗,尋求因果,歸納,假設,搜集證成假設的證據,發表新主張。儘管他們深知這不可能包打天下,解決全部古史問題,但至少能推翻自古將神話傳説作為信史的成説。謝桃坊指出,考證這些問題,不僅大量引用先秦兩漢典籍,辨析材料,考證相關注疏,考證清人研究成果。當然,這些問題並不一定是最終定論,但這種研究是必要的。傅斯年主張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文獻與歷史的學術問題,“致中國歷史語言研究之學於自然科學之境界中”是他的學術理想,認為這種學術工作註定不能好高騖遠,貪大求全。國學研究的物件涉及經學、史學、文學、哲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中的文獻與歷史上若干細小的學術問題,為各學科的建設提供新的事實依據,它所探討的問題卻又非經學、史學、文學、哲學等學科按自己的研究方法所能解決的。總之,“國學成為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文獻與歷史中存在的狹小學術問題的新的綜合性學科。國學研究的性質和物件決定了它不可能採用思辨的、演繹的、經學的、玄學的和神學的研究方法,而衹能採用實證的科學方法”①謝桃坊:《國學研究與科學方法》,《國學史研究》,第85—86 頁。。國學既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問題為研究對象,而且直接繼承和使用清代考據學方法,但在方法論上則吸收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方法——實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史學方法,成為國學研究的科學考證方法。西方近代實證科學方法與傳統考據學的結合,科學的、細密的、煩瑣的考證方法,這種科學方法在國學研究中具有方法論意義,也是20世紀初以來國學新傾嚮的顯著特徵。在對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等大批學者研究方法進行梳理總結之後,謝桃坊認為,國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國學“運動”新傾嚮的學者們所創造的科學考證方法,是在對中國傳統考據學的繼承超越的基礎之上,引入了西方近代的實證主義方法,使二者結合為一種新的方法,以西方實證主義為方法論,以中國傳統考據學為具體方法的。在面對中國文獻與歷史的具體問題時又須採用中國傳統考據學,需要貫通“四部”對經、史、子、集“不可劃疆而治”的傳統考據方法。因此,國學的研究方法比傳統考據學更加進步科學,國學研究客觀、冷静地看待歷史與文化,而且對歷史事實的論斷符合學理。他們研究某一問題,固然不可能真正做到“上窮碧落下黄泉”,但至少憑理性、直覺與專業視角去鑒别、選擇材料。國學研究採用實證的科學方法是與其研究物件適應的,但這種方法也具有專業性與局限性的。
五、國學研究的意義
國學研究的成果是為諸種學科提供新的事實證據,這在中國學術研究中是較為基本的研究。國學新潮學派將傳統考據學與西方近代科學方法結合,注重專門問題研究,致力於掃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因襲、謬妄或迷信,“可與史傳正其闕繆”,這樣方能體現出中國社會的文明進程,這便是國學研究的價值與意義所在。誠然,學術和科學一樣,都有基礎性研究和實用性研究。國家的學術結構中固然需要經世致用的應用研究,但從國家與民族長遠利益計,發展純學術同樣不可或缺,甚至更為根本。對純學術研究給予必要的重視與支持,纔能獲得國家和民族文化生命“相對獨立的意義”,以及“表示自己歷史的存在”。國學研究的物件和價值是有限的,它看似無用,實則無用乃大用。縱觀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哲學、新史學、新文學等學科的建立與發展,其理論大廈大都是建立在國學研究的基礎之上的。例如新史學,不再以“三皇”“五帝”為中國歷史的起點,新紅學不再走索隱派的老路。在謝桃坊看來,考證衹是一種方法,並不是最終的目的。他一再强調,國學是以中國文獻與歷史上存在的若干細小而困難的學術問題為研究物件,用傳統的考據學方法作細密的考證的基礎性研究。建立崇高宏大的學術信仰是治國學的重要前提,“未將所學的知識及所治的學問轉化為學術信仰,從而建立人生的信念,這樣的國學家缺乏思想之光,必然影響其學術成就,也不能去發現具有重大意義的學術課題”①謝桃坊:《回顧梁啓超與胡適在東南大學的國學講演》,《古典文學知識》2011年第3 期。。崇尚科學考證的國學,在中國現代學術譜系中是應有合理地位的,但它的學術價值和作用的確是有限的甚至“褊狹”的,或者是郭沫若所説的“殊屬微末”,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等學人,他們也從未刻意誇大其作用。誠如史學家蒙思明曾反思“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金字招牌之下,有如打了一劑强心劑,使垂滅的爝火,又將絶而復燃,竟成了學術界唯一的支配勢力。……評文章以考據文章為優,倡學風的以考證風氣為貴,斥理解為空談,尊考據謂實學”②蒙思明:《考據在史學上的地位》,《責善半月刊》第2 卷第18 期,1941年12月。。或者如葉青所批評的“是機械的物質論的,没有運用過優於科學的辯證法”①葉青:《從方法上評老子考》,顧頡剛:《古史辨》,第六册,第418 頁。,有牽强附會、割裂斷取之嫌;或者如有些學者所説的“整理國故”讓人失去幻想,徒留虚無,無涉“人情厚薄”的一些思考,因為,在“真”之外,還有“善”、“美”等價值。因此,我們對國學“運動”中的幾番辯論不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應吸收批評意見的合理因素,兼顧情感與理性。我們對國學研究的意義或作用不宜刻意放大,也不宜過度崇尚,而陷於另一種迷信。但無論如何,國學研究對我們民族“重證”“求是”的心習養成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此外,謝桃坊也力圖避開産生新的謬妄,提醒我們對同一課題的考證可能出現不同的結論,一時難有定論,如關於古帝的世系的討論、關於《老子》的討論等問題長久争論,這些都屬正常的學術現象,這也正反映了人們探尋真知的曲折過程。但他堅信,堅持國學研究的方法,終能“以科學實證的方法去無限逼近真理”的。
六、四川國學運動述評
四川國學運動是20世紀初年以來國學運動的一個縮影。謝桃坊介紹四川國學的歷史發展過程,揭示國學的性質,幫助我們進行歷史反思,探尋意義。他認真考察四川國學運動的發展過程,追溯四川國學運動在20世紀初年興起的情形,並提出個人創見。他在其《四川國學小史》一書中,對四川國學院、國學學校、國學會、國學研究會,各種國學雜志及刊物、代表人物的學術思想與國學觀念,抗戰爆發後四川國學界的盛況,從宋育仁、吴之英、謝无量、廖平、劉師培、劉沅、劉咸炘、侯外廬、郭沫若、傅斯年、岑仲勉、王明、楊志玖、陳寅恪、王伊同、金景芳、顧頡剛、錢穆、蒙思明、趙少咸、徐中舒、一直到蒙文通,他都進行了精到研究與精煉總結。例如對於經學大師廖平,謝桃坊表達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指出“廖平的治學方法卻擺脱不了今文經學家的局限,他在發掘微言大義時不重視事實的客觀性、隨意曲解或推測經典之義,並與神話、緯書、醫典、文學作品等聯繫,大肆穿鑿附會,構成種種荒誕的怪説。……這使他偏離了純正的學術軌道,嚴重有損四川國學的學術性”②謝桃坊:《四川國學小史》,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第26 頁。。對帶來“蜀學丕變”的、與廖平進行學術交鋒的劉師培,謝桃坊以為其“學術思想的成熟,展示了深邃的理性光輝”③同上,第31 頁。。認為蒙文通等弟子在師長們紛紜分歧、互有抵牾的學術思想中,雖左右為難、無所適從,但還是激發了他們在比較中去探尋真諦的精神。私立國學學校的代表人物劉咸炘,他所理解的“史”是廣義的,包含“六經”,即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學;他的“學”是歷史與文獻的結合,以探討事理為目的,不同於儒家以政治為目的之學。因着這樣的認識,他纔可以超然於今文經學、古文經學的偏見,“對四川今文經學思想的特盛作出客觀的評價”①謝桃坊:《四川國學小史》,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第49 頁。。
謝桃坊不僅梳理學術史,也間或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例如,他對今文經學作了反思與評價:“今文經學家所宣導的發明儒家聖人的微言大義,多屬穿鑿附會,還不如宋代理學家對儒學義理的闡釋。今文經學家所發明的屬於遠古荒誕的東西,他們的經世致用則流為粗俗的政論。這是廖平等今文經學家的根本痼疾。”②同上,第50 頁。總之,謝桃坊對蜀中學者或抗戰時期流寓巴蜀學者們的國學研究成果進行挖掘整理,總結出幾條歷史經驗:其一,四川學術是中華學術的一部分,在國粹主義思潮影響下首創國學院、研究者大都是經師,且以儒學為國粹的核心,以今文經學思想特甚,國粹觀念强固。其二,同全國國學運動的發展軌迹一樣,四川國學也經歷了從國粹到國學新思潮的發展,因抗戰時期高校和學術機構内遷最終匯入國學新思潮主流,民族學術工作不但没有停滯或沉寂,反而益愈得到發展。其三,從四川國學運動發展過程,梳理國學家對於國學認識的發展過程。如:廖平將國學等同於儒學;劉師培從學術的視角,將國學理解為學術流變史;劉咸炘提出國學是四部書相連,不可劃疆而治;葉楚愴認為文史研究的物件是文史的批評案;郭沫若將國學研究等同於考據,提倡科學的考證;蒙思明指出國學考據是一個時代的學術風尚;蒙文通則以哲學和史學的理論為指導進行考據。在相關論文中,謝桃坊對四川國學運動中代表人物的國學思想進行檢討與反思,贊成什麽,反對什麽,合理在哪,不合理在哪,他都態度鮮明,敢於論斷。他也絶無門户之見,無模棱兩可、含混不清,體現了老一輩學者的學術自信與純粹追求。
七、餘 論
自1905年《國粹學報》創刊,標志着國學“運動”興起,迄於1949年,國學“運動”存在共四十五年。當我們回顧國學“運動”的歷史時,明顯地見到胡適於1923年發表《〈國學季刊〉 發刊宣言》發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號召後,所得到的熱烈響應,遂在國學運動中形成一種新傾嚮,它取代了國粹派,逐漸發展為國學“運動”的主流。我們現在應對國學“運動”主流進行歷史經驗的總結,纔可能認識國學的性質、研究對象及方法。謝桃坊對國學史研究所作的貢獻,即在於以充實的歷史事實,闡明國學“運動”新傾嚮的意義。這可引起反思,啓發我們以學術理性審視近年再度興起的國學熱潮,推進當代國學研究。謝桃坊對國學的定義、研究物件、學術特徵、研究方法、不同流派的學説都進行認真梳理與總結,在開放姿態中有集中,勇於質疑、批判,敢於闡釋、論斷,為謀求學術的獨立與解放而殫精竭慮,焚膏繼晷。他冷静客觀地看待國學熱潮,强調要區分國學基礎與國學研究。他勇於學習、善於學習,絶不食洋不化,食古不化。他的寫作風格與國學研究一樣,不求宏大敘事,富麗堂皇,衹求專業精深、繁豐細密。他對國學“運動”的總結與闡釋,實則在學術信仰滋養下對真理、真知、真影、真相最真誠的追求。這種衹追求專業精深的學術信仰,謀求學術的獨立自由的精神,與當年國學家們“專崇技術工作”,與當代弘揚的執著專注、作風嚴謹、精益求精、敬業守信的精神可謂殊途同歸。經由他的梳理與闡釋,上個世紀國學“運動”的主流意義,對純學術風尚追求的意義,已然呈現於我們面前。
但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謝桃坊先生也提到文、史、哲貫通,不可劃疆而治。而且,國學“運動”主流之外還有幹流、支流,地下徑流,它們也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歷史文化長河的活水源頭。“國學”最初是由章太炎由日本“國粹運動”藉鑒而來,後來再到胡適提出“國故學”,是當時語境下對西方文化和價值體系、生産方式衝擊下的一種“權宜之計”,是民國初期學界用於對傳統“君學”的一種反撥。“民族國家”始終是建設“國家”之“學術”的一個邏輯起點。因此,“國學”終究是要承載着現代民族國家的精神和價值支撐的,通經致用、利用厚生同樣值得尊敬。我們的確需要“從武斷迷信裏面尋求出一個真價值來”(胡適,1919),但“真價值”並非唯一的價值追求,有時候美麗動人的神話傳説,文學、藝術、宗教等帶給人類情感與價值的意義,有時或許是比純粹、精深更讓人樂於接受的美好。總之,格物致知與崇善尚美都是我們的文化中所需要的價值。此外,從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到當代“四重證據法”的學術實踐,當代學者對過度求“真”、“為學術而學術”而過度解構、消解的一些反思,對當年國學家們對衹專崇技術工作或將走嚮狹窄與僵化的擔憂,這些同樣應該引起我們冷静與思考。總之,國學應該是一個更具開放性、包容性的概念。或許,我們重回梁啓超所説的“古典考釋學”,自宋代考證學、至清代樸學直至國學“運動”主流的這種追求純粹學術空間的合理訴求更易讓人接受,這種合理訴求自然是學術譜系中的重要一環。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當年“國學”運動的時代語境與當今時代語境不可同日而語,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資訊化深入發展的今天,“我們已然無法在習慣性的思維裏閉合‘國學’ 的研究,必須超越‘國故學’的研究模式,面嚮西學作開放式的、生長型的發展。與此同時,還得積極吸納西學,以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問題意識拓寬傳統學術的研究視野,以恢復學術的生命力和延展性。”①文韜:《“國故學”與“中國學術”的糾結——民國時期兩種“國學”概念的争執及其語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年第5 期。作者還想要囉嗦的是,在“國家”語義下的“國學”不應該衹是少數學者的專利,啓蒙派的學者認為,“中國的精神不在經典之中,而是存在於民衆的生活世界中”②幹春松:《“國學”:國家認同與學科反思》,《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 期。。“思想與學術,有時是一種少數精英知識分子操練的場地,它常常是懸浮在社會與生活的上面的,真正的思想,也許要説是真正在生活與社會支配人們對宇宙的解釋的那些知識與思想,它並不全在精英和經典中。”③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1—12 頁。國學是不可能真正“懸浮”於“斯土、斯民、斯邦”的人間煙火之外的,國學不應該僅僅衹屬於“學術共同體”。關於“學”與“術”的關係,梁啓超在1911年的《國風報》的《學與術》上已經講得很透徹了。因此,文化的選擇與理解終究是由不同的文化主體來判斷選擇的。對國學這一“文化共業”的討論還將繼續,没有“標準”答案,但正是紛繁複雜成就了中華文化的複異豐富,海納百川,這也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生機與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