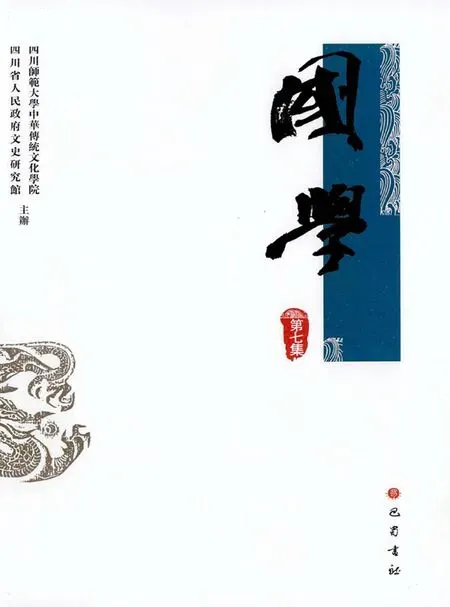韓偓與閩國王審知及其幕僚關係探賾
——從劉後邨、全祖望之説談起
吴在慶
關於韓偓和五代十國王審知閩國的關係,清人全祖望在其《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題跋·跋韓致光閩中詩》中説:
劉後邨曰:“唐史謂致光挈族入閩依王氏。按,王氏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後邨之言是也,而尚未盡。致光以丙寅至福唐主黄滔家,丁卯唐亡。戊辰尚寓福唐,己巳寓汀州之沙縣,庚午寓尤溪之桃林,辛未而後始至南安。則其在福唐亦三年,又二年而居南安耳。然致光之居南安,固不依王氏。即居福唐,亦非依王氏。何以知之? 王氏固附梁者也,致光避梁而出,豈肯依附梁之人。故其嘆郎官之使閩者曰:“不羞莽卓黄金印,翻笑羲皇白接籬。”《鵲》詩曰:“莫怪天涯棲不穩,托身須是萬年枝。”《驛步》詩曰:“物近劉輿招垢膩,風經庾亮污塵埃。”《喜涼》詩曰:“東南亦是中華分,蒸鬱相凌太不平。”《悽悽》詩曰:“嗜鹹凌魯濟,惡潔助涇泥。”《閑興》詩云:“他山冰雪解,此水波瀾生。”豈但於王氏無一毫之益,且危疑百端矣。讀詩論世,可以得其情狀也①[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題跋·跋韓致光閩中詩》,清嘉慶十六年刻本。。
劉克莊和全祖望論韓偓和閩國關係的這段話大體是可信的,但還有不够準確之處;且其尚未論及韓偓之所以屢次徙居各處之具體情況與原因,以及韓偓之所以離開福州,有意疏離王審知也與王審知幕僚之妒忌不無關係。這些闕失是可依據韓偓之詩文以及有關記載加以探賾補充的。
一
劉後邨所説的“唐史謂致光挈族入閩依王氏”之説,其所説乃指《新唐書·韓偓傳》。此傳云:“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 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①[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八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390 頁。後人所説多據此,如宋李綱《梁溪集·讀韓偓詩並記有感》云:“韓偓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頗與國論,為崔胤、朱全忠所不容,謫濮州司馬。其後復官,不敢入朝,挈其族依閩中王審知。”②[宋]李綱:《梁溪集》卷十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九《韓偓傳》云:“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③[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九。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43 頁。明陸時雍《唐詩鏡》謂:“貶濮州司馬。天祐中復召入,偓挈家南依王審知,卒”④[明]陸時雍:《唐詩鏡》卷五十四,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十國春秋·韓偓傳》謂:“昭宗被弒,哀帝復召為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來依太祖,僑居南安。”⑤[清]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371 頁。按,《新唐書》所説的韓偓“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所用的“依”字,檢之典籍也是有所依據的。考王審知的幕僚黄滔有《丈六金身碑》,中云:“我公之慶鍾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設二十萬人齋,號無遮以落之。是日也,彩雲纈天,甘露粒松。香花之氣撲地,經梵之聲入空。座客有右省常侍隴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誥兵部侍郎昌黎韓公偓、中書舍人琅琊王公滌、右補闕博陵崔徵君道融、大司農琅琊王公標、吏部郎中譙國夏侯公淑、司勳員外郎王公拯、刑部員外郎宏農楊公承休、宏文館直學士宏農楊公贊圖、宏文館直學士琅琊王公倜、集賢殿校理吴郡歸公傳懿,皆以文學之奧比偃商,侍從之聲齊褒嚮,甲乙升第,巌廊韞望。東浮荆襄,南遊吴楚,謂安莫安於閩越,誠莫誠於我公。依劉表,起襄漢,其地也,交轍及館。值斯佛之成,斯會之設,俱得放心猿於菩提樹上,歇意馬於清涼山中。我公乃顧幕下者滔,俾刻貞石以碑之。滔以甲科忝第,盛府蒙招。刊勒之職,不敢牢讓,謹推於厥旨。”⑥[清]董誥等輯:《全唐文》卷八二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55 頁。據上引文可知閩國此次佛會在天祐四年正月十八日,而參加此次佛會的李洵、韓偓、王滌、崔道融等原唐昭宗朝臣乃因時局動亂,“謂安莫安於閩越,誠莫誠於我公”而來“依劉表,起襄漢,其地也,交轍及館”。黄滔時為閩國王審知幕節度推官,故文中之“我公”,乃指王審知。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韓偓諸人“依劉表”之謂。所謂“依劉表”即用《三國志·魏志·王粲传》故事:“ (王粲)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黄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内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①[晉]陳壽:《三國志》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97—598 頁。韓偓亦因遭朱全忠所嫉恨,在朝中被貶濮州司馬,後流寓於湖南,並於唐昭宗被弒、朱全忠立唐哀帝後經江西入閩福州。故黄滔謂韓偓等人“依劉表”云云實在頗為貼切。《新唐書·韓偓傳》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其用“南依王審知”之“依”字當依黄滔此文而來。那麽“依劉”之“依”又何解? 據《漢語大詞典》,“依劉”乃謂“投靠有權勢者”②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第1353 頁。按,本文若干語詞之解釋以及其用例均據此詞典,文繁此下容不一一出注。。韓偓之“依王審知”,即投靠王審知。那麽這裏的“投靠”又做何解呢? 我以為從《王粲傳》和韓偓入閩當初的情況看,解釋為投奔依靠閩國王審知,以求避難安身是比較貼切的。因此這裏的“依”,雖然不排斥王審知禮遇接待韓偓之成分,但並無依附乃至入仕王審知幕府之意。因此,《新唐書·韓偓傳》所謂的“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如從其當初入閩之動機與實際情況看當大致不誤,此即如《十國春秋·黄滔傳》所言“梁時强藩多僭位稱帝,太祖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為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數十輩,悉主於滔”③[清]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十五,第1373 頁。。檢韓偓《手簡十一貼》第六貼云:“旬日前所諮啓,乞一書與建州,為右司李郎中經過,希稍延接。況承舍人亦與正郎舊知聞,必切於施分。今晚有的的人去,若可踐言,速乞封示。幸甚,幸甚。偓雖承建州八座眷私,自是旅客,難於托人,伏惟照察。偓狀。十月十五日偓狀。”④吴在慶:《韓偓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073—1074 頁。本文所引韓偓詩文均據此書,以下容不一一出注説明。又韓偓有《李太舍池上玩紅薇醉題》詩,中云:“花低池小水泙泙,花落池心片片輕。……乍為旅客顔常厚,每見同人眼暫明。”此詩作於開平元年(907) 春末⑤吴在慶:《韓偓論稿·韓偓生平詩文繫年彙纂》,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04—305 頁。按本文韓偓詩文作年除另注外,均據是書此文,下容不出注。,據鄧小軍先生《韓偓年譜》⑥鄧小軍:《詩史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91—292 頁。所考,上文乃作於梁開平元年十月,其時王審知已經稱臣於後梁朱全忠。文中“建州八座”即指王審知,而從“偓雖承建州八座眷私,自是旅客,難於托人”來看,韓偓確實是獲得王審知之“眷私”的,但他此時並没依附王審知,衹是“旅客”而已。這就説明韓偓入閩後其身份衹是“旅客”而已,也就是我們前分析《新唐書·韓偓傳》所記的韓偓“依王審知”,乃即投靠王審知。但這裏的“投靠”,“從韓偓入閩當初的情況看”應“解釋為投奔依靠閩國王審知,以求避難安身”是比較貼切的。從這一角度考慮,韓偓既然在貶官、棄官後入閩,那麽他初入閩時如何安頓自己以及家人,就成為必須依仗他人解決的急切問題。我們知道韓偓等人之入閩“悉主於(黄) 滔”,可見黄滔是提供過具體切實幫助的。但黄滔衹是王審知的節度推官,他要解決包括韓偓在内的諸位來閩避難的唐朝官員的安頓問題,應該會徵得王審知的同意,並取得安頓諸人的資源。據前所考韓偓確實獲得王審知之“眷私”,那麽在入閩安頓等問題上,韓偓得到王審知的“眷私”應該是可以確定的。從這一意義上講,《新唐書·韓偓傳》所記的韓偓“依王審知”,在韓偓初入閩時是恰當的,因此全祖望認為韓偓“以丙寅至福唐,主黄滔家”“即居福唐,亦非依王氏”這種説法是有違事實的。而他所謂“王氏固附梁者也,致光避梁而出,豈肯依附梁之人”之説也不無問題。蓋韓偓初入閩國依王審知時,王審知也尚未“附梁”,因其時李唐儘管風雨飄摇,但尚未被朱梁所取代。而劉克莊所言“王氏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的説法,雖然大致不錯,但也忽略了韓偓初至福唐(即福州) 那一段時光確曾獲得王審知“眷私”的“依”的事實,因此也多少存在以偏概全之弊。
當然《新唐書·韓偓傳》所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的説法也不無問題。我們懂得這樣的記敘確實是舊史常見的籠統記敘之筆,容易為講究精确的後人所詬病。因為這樣的表述將韓偓自入閩至卒的全過程均描述為“依王審知”,這未免過於籠統,同樣也存在以偏概全之弊,因為這樣描述也與事實有違。
事實到底如何呢? 通讀韓偓詩文與有關記載,我們還是可以梳理出韓偓與閩國王審知及其部分僚屬之親疏關係,乃至其演變的大致情況,其“依”或“非依王氏”,即可藉這一梳理分辨清楚。
檢韓偓《鵲》詩末云:“莫怪天涯棲不穩,托身須是萬年枝。”此詩乃詠於乾化二年(912),此時詩人經幾次徙居,已經隱居於閩南南安縣鄉村。從他這兩句藉詠鵲的自白,我們可以意會到他所以屢次遷居,原因在於没有遇到可以托身的“萬年枝”,而這“萬年枝”既不是朱梁王朝,也非閩王審知政權①關於《鵲》詩所包含的具體意藴,請參看拙著《韓偓論稿·韓偓〈失鶴〉 〈鵲〉 〈火蛾〉 三首詩發覆與解讀》一文。見此書第125—139 頁。。那麽詩人在閩中的幾次遷徙,我認為是和王審知及其幕僚與詩人的不同關係緊密相關的。以下我們即將此關係之具體情形分為:1.韓偓初抵福州至避到沙縣時;2.在沙縣寓居時;3.從沙縣遷至桃林場隱居時;4.離開桃林場徙居至南安縣鄉村隱居至其卒時四個階段進行梳理探賾。
二
如上所述,韓偓初至福州的那段時間確實可以説是依王審知的。其依王審知是建立在如黄滔所説的包括韓偓在内諸人“謂安莫安於閩越,誠莫誠於我公”之上的,也就是説諸人認為閩越(此處指閩福州) 可以作為南下的避難安身之地,而且相信王審知接納他們的誠心。當然天祐三年(906) 秋韓偓入閩時,王審知仍是李唐藩臣,這是韓偓決定入閩之首要因素。但是這段信任接近可稱為“依王審知”的時間,我以為充其量大致至韓偓從福州移居沙縣時,即約在後梁開平二年(908) 冬①吴在慶:《韓偓考論·韓偓生平詩文繫年彙纂》,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04—305 頁。本文所述韓偓形迹以及詩文作年如無特别説明均依此書。。這一離開福州,表明韓偓有意疏離王審知,其原因或許有多種,但主要原因在於王審知稱臣於朱全忠,接受後梁之封官。考《資治通鑒》後梁開平元年四月乙亥載:“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禀梁正朔,稱臣奉貢。”②[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六六,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8675 頁。據此可知,此時閩國王審知也已“稱臣奉貢”於梁。又《十國春秋》卷九十《閩一·司空世家》即記有以下諸事:
開平元年五月乙卯,梁加王兼侍中。冬十一月,梁封福州閩縣玷琦里古廟為昭福祠,從王請也。是歲,以九仙山萬歲寺請為梁主祝釐,表額曰壽山。
開平二年春正月,梁詔改福州福唐縣曰永昌③[清]吴任臣:《十國春秋》,第1309—1310 頁。。
誠如宋李綱《梁溪集》卷十一《讀韓偓詩並記有感》所云:“韓偓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頗與國論,為崔胤、朱全忠所不容,謫濮州司馬。”④[宋]李綱:《梁溪集》卷十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故韓偓對朱全忠以及其弒殺唐帝後所建立之梁政權是極為憎惡的,非但拒絶其復故官之招,而且入閩遠避之。而他選擇入閩,乃基於王審知其時仍是李唐臣子,且“安莫安於閩越,誠莫誠於我公”。因此開平元年四月當他知道王審知稱臣於朱全忠之後梁,他對此必然産生反感,並對王審知有所警惕戒備,其時出現疏離王審知之心也就可想而知了。隨着上引《十國春秋》所載閩國與朱梁王朝互動事件的陸續發生,韓偓對王審知的疏離之情必然逐漸增强,並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加深。
值得注意的是韓偓自從天祐三年秋入閩時就居於王審知幕府所在地福州,但約在開平二年(908) 冬他就“嘗道沙陽,寓居天王院者歲餘,與老僧藴明相善,以詩贈之”①見吴在慶:《韓偓論稿·韓偓生平詩文繫年彙纂》,第304—305 頁。。這一移居意味着什麽? 韓偓為何要離開福州而寓居到相對偏僻的沙縣天王院歲餘?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史籍文獻並没有記載,我們衹能依據詩人的政治立場、處境以及其個别詩文加以探賾。從如前所述韓偓疏離王審知之原因考察,詩人這一離開福州遠避至沙縣之舉,就意味着詩人有意避開王審知,更為疏離他了。如果説移居沙縣之前的那段寄居福州的日子,可説是“依王審知”的話,那麽從移居沙縣起,“依王審知”的成分就更為淡薄或可説已掙脱王审知了。
那麽除了這一政治立場的原因外,還有何因素催動他離開福州呢? 檢韓偓開平元年作有以下兩首詩:《息慮》云:“息慮狎群鷗,行藏合自由。春寒宜酒病,夜雨入鄉愁。道嚮危時見,官因亂世休。外人相待淺,獨説濟川舟。”又《味道》云:“如含瓦礫竟何功,癡黠相兼似得中。心繫是非徒悵望,事須光景旋虚空。升沉不定都如夢,毁譽無恒卻要聾。弋者甚多應扼腕,任他閑處指冥鴻。”這兩首詩中“外人相待淺,獨説濟川舟”“毁譽無恒卻要聾。弋者甚多應扼腕,任他閑處指冥鴻”等句較為難解,且是值得推敲細味、重點討論的句子。為此,我們得把兩首詩的大致意思先行解説,然後再探究這些詩句之意藴。
《息慮》詩之要旨乃“息慮”,即謂如今已止息入世求功名之雜慮,以獲得出處行止之自由。故首兩句即緊扣詩題,表明此主旨。中四句即以最簡略之情事述説入仕貶出以及棄官以來之事。末二句謂如今尚有人以輔佐國事相稱許,然而乃是不深知者之意,他哪裏知道我而今已是“息慮狎群鷗,行藏合自由”之人矣! 《味道》乃詩人歷經人生患難,流寓入閩後回顧人生,體味為人處世之道所作。首句謂人生如不悴不榮,無馨無臭,如含瓦礫般又有何意思呢! 第二句乃詩人所體味,亦即為人癡黠相兼最為相宜。第三句以為人若心繫是非太甚,則徒然招致悵望而已。第四句乃“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之意。第五句謂世事無常,皆如夢般變幻不定,有如《莊子·德充符》所謂“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②見《莊子注》卷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六句乃葛洪《抱朴子·自敘》所謂“毀譽皆置於不聞”也③[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四,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末兩句應看作詩人所面對之險惡處境與態度,意為可悲嘆者乃心存謀害捕殺的人實在太多了,然而衹要如冥鴻般隱逸高飛,他又能奈我何呢!
這兩首詩均作於韓偓入閩後次年,此時他已“依王審知”一段時間了,且此前之天祐二年九月、天祐四年正月,他已兩次拒絶朱全忠控制下的唐朝廷的復故官之招,並已多次賦詩言志云“宦途棄擲須甘分,迴避紅塵是所長”(《即目二首》之一)、“宦途巇嶮終難測,穩泊漁舟隱姓名”(《病中初聞復官二首》之二)。那麽開平元年在他已經避開中原朱梁王朝而“依王審知”的新環境裏,他為何還要賦詩感慨“外人相待淺,獨説濟川舟”,要慨嘆“毁譽無恒卻要聾。弋者甚多應扼腕,任他閑處指冥鴻”呢? 而這些詩句又何所指呢?
先解析“外人相待淺,獨説濟川舟”句。按,外人,即他人,别人。此指對自己瞭解不深之人。如《孟子·滕文公下》:“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①[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六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品藻》:“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 答曰:‘固嘗不同。’ 公曰:‘外人論殊不爾。’”②[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卷中之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94 頁。相待淺,《韓非子·六反》:“猶用計算之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此句意别人對自己瞭解不深。又“濟川”語出《書·説命上》:“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③[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注疏》卷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後多以“濟川”比喻輔佐帝王。如唐獨孤及《庚子歲避地至玉山酬韓司馬所贈》詩:“已無濟川分,甘作乘桴人。”④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二四六,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2763 頁。因此此處“濟川舟”意為輔佐帝王之人。此句連上句意為别人對自己瞭解不深,到如今還把我看作是心存輔佐帝王之人。那麽韓偓這裏的“外人”指何人? 他為何要講上述這些話? 我以為這裏的“外人”從當時他所處環境來看應指王審知和黄滔等人。蓋他們對曾是朝中重臣的韓偓以及其輔佐唐昭宗的才具品德是瞭解的,而且他們均是器重並“眷私”韓偓者。可以設想當韓偓來閩“依王審知”時,他們必定會想方設法説服並禮聘他入幕為閩國效力。然而這對於決計“穩泊漁舟隱姓名”的韓偓來説,不管王審知們對他寄予多大的厚望,他也是無心入仕閩國幕的,故以《息慮》為題,表明自己“息慮狎群鷗,行藏合自由”之志嚮。這裏我們還須進一步説明的是《息慮》詩作於唐天祐四年正月,此時唐尚存梁未立⑤據《資治通鑒》卷二六六,第8674 頁所載:天祐四年四月“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而閩國王審知稱臣於朱梁乃在賦此詩約四個月之後,這就説明此時以及此前韓偓不願意入閩國幕並不是因王審知稱臣於朱梁,而是另有其他考慮。我們設身處地細細斟酌,除了上文所説的他已有“宦途巇嶮終難測,穩泊漁舟隱姓名”之徹底退隱之想,以及下文再分析的“毁譽無恒卻要聾”原因外,我想應還有其忠於唐昭宗之李唐王朝,而決不他仕之效忠情結。這一情結劉克莊的《後村詩話》即言之:“及朱三篡弒,偓羈旅於閩,時王氏割據,偓詩文止稱唐朝官職,與淵明稱晉甲子異世同符。”⑥[清]鄭方坤:《五代詩話》卷六引《後村詩話》,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230 頁。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三《經籍》七十亦云:“石林葉氏曰:‘韓偓傳自貶濮州司馬後,載其事即不甚詳。其再召為學士,在天祐二年。吾家所藏偓詩雖不多,然自貶後,皆以甲子歷歷自記其所在,有乙丑年在袁州得人賀復除戎曹依舊承旨詩,即天祐二年也。昭宗前一年已弑,蓋哀帝之命也。末句云‘若為將朽質,猶擬杖於朝’,固不往矣! 其後又有丁卯年正月《聞再除戎曹依前充職詩》,末句云‘豈獨鴟夷觧歸去,五湖魚艇且餔糟’,天祐四年也。是嘗兩召皆辭,《唐史》止書其一。是歲四月,全忠簒,其召命自哀帝之世。自後復召,則癸酉年南安縣之作,即梁之乾化二年(慶按,癸酉年乃乾化三年,此謂乾化二年誤),時全忠亦已被弑,明年梁亡。其兩召不行,非特避禍,蓋終身不食梁禄,其大節與司空表聖略相等。惜乎,《唐史》不能少發明之也!’”①[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923—1924 頁。《十國春秋·韓偓傳》亦載:“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②[清]吴任臣:《十國春秋》,第1371 頁。韓偓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即在於忠於李唐,感恩唐昭宗對他的器重寵任。這一情結不僅如上所記,而且也流露於其詩中,如早在天復元年(901) 所作的《賜宴日作》詩中即有“臣心浄比漪漣水,聖澤深於瀲灎杯。纔有異恩頒稷契,已將優禮及鄒枚”之詠,故開平元年秋詩人在福州所賦《秋郊閑望有感》中云“心為感恩長慘慼,鬢緣經亂早蒼浪”。因此這一忠於李唐昭宗朝的感恩情結,也是他既不仕朱梁朝,也不願入閩國幕的原因之一③關於韓偓不仕朱梁,也不入王審知閩國幕問題,可參看拙作《韓偓〈露〉 〈六言三首〉 詩發覆與解讀》,見《韓偓論稿》,第140—146 頁。。
如上所述,王審知和黄滔也是有恩於韓偓,並有延攬他入幕之舉的,這還可以從詩人《味道》詩的“升沉不定都如夢,毁譽無恒卻要聾”等句品味出其“味道”。作者抒發這一感慨是在他到福州的翌年,即正在“依王審知”時,因此這裏的“毀譽”多半是就當時的遭際而發的。所謂的“譽”,應包括王審知、黄滔等人對他的“獨説濟川舟”,並想延攬他入幕之舉之類,以此也可反證王審知確實有想延攬他入幕之舉。此外,從“毀”的角度分析,我認為“毀”他的人就有王審知幕府中之人,而之所以要“毀”他,就在於知道王審知有延攬詩人之意,因妒賢嫉能而心生排斥,並進而讒毀他。這樣的判斷從詩人此後所詠的《此翁》詩“高閣群公莫忌儂,儂心不在宦名中”等句即可參悟(説詳下)。其實“高閣群公”擔心韓偓入閩國幕從而嫉妒讒毀他不僅在寫作此詩時,早在開平元年前後韓偓在福州時已經如此了,故他在《味道》詩中針對“弋者甚多應扼腕”處境,不僅存有“儂心不在宦名中”之志,而且以“毁譽無恒卻要聾”處之,一表“任他閑處指冥鴻”“息慮狎群鷗,行藏合自由”之心迹。
若細緻品讀韓偓詩,我們尚可品味出王審知想徵聘他入幕恐早在他天祐三年至福州後不久就開始了。這一年韓偓入閩後有《兩賢》和《再思》詩,前作云:“賣卜嚴將賣餅孫,兩賢高趣恐難倫。而今若有逃名者,應被品流呼差人。”《再思》後半云:“但保行藏天是證,莫矜纖巧鬼難欺。近來更得窮經力,好事臨行亦再思。”《韓偓年譜》曾指出:“此二詩顯係有為而作。前首之‘逃名’,後首之‘但保行藏’,及‘好事臨行亦再思’,殆即指復召仍不赴。不然,即指王審知欲用偓為官。朝命既一再不赴,審知倘有意用之,又安能從命耶?”①鄧小軍:《詩史釋證》,第286 頁。我則以為“近來”“好事”兩句均是對自己而言,那麽對於朱全忠所控制的唐哀帝朝廷之“復招”,詩人應不會認為是“好事”,衹有王審知之有意徵聘他,他纔會視為“好事”。如果此理解不誤的話,那麽這就可以表明,早在天祐三年詩人入閩後王審知就有徵聘他入幕之意了。這不僅可以進一步説明王審知等人對他有“眷私”之恩,同時也可以表明王審知之幕僚(即“高閣群公”) 對他的嫉妒讒毀也隨之而來。這也是詩人不願入王審知幕,並在後來避到沙縣,以此有意疏離王審知的原因之一。
三
如果説從韓偓離開福州遠避到沙縣寓居於天王院歲餘,標志着韓偓疏離王審知之第一階段的話,那麽從其離開沙縣擬至撫州、信州之行起則為其疏離王審知之第二階段之開始。
檢韓偓《己巳年正月十二日自沙縣抵邵武軍將謀撫信之行到纔一夕為閩相急脚相召卻請赴沙縣郊外泊船偶成一篇》云:“訪戴船迴郊外泊,故鄉何處望天涯。半明半暗山村日,自落自開江廟花。數醆緑醅桑落酒,一甌香沫火前茶。”按,據詩題知此詩乃作於己巳年正月,亦即後梁開平三年(909) 正月。詩題所謂“謀撫信之行”,指謀劃將經邵武到江西的撫州、信州。“閩相”,指王審知。其時王審知為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稱。“急脚”,唐時急速傳遞書信信息者。此詩詩題後吴汝綸評注云:“是時撫州刺史為危全諷,信州為危仔倡。是年淮南取撫、信地。閩相即王審知。”②見吴在慶《韓偓集繫年校注》第292 頁此詩“集評”下引。據上所析知開平三年正月韓偓離開沙縣擬往江西之撫州或信州,但行至邵武卻被王審知所派遣的信使召回沙縣郊外駐泊。誠如《韓偓簡譜》所云“玩此詩致堯頗有離閩之意”③孫克寬:《詩文述評·韓偓簡譜》,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第98 頁。。那麽詩人為何又要徹底離開福建往江西去呢? 此時到底又發生了什麽而使詩人下此決心?
檢韓偓有以下兩首詩:其《余寓汀州沙縣病中聞前鄭左丞璘隨外鎮舉薦赴洛兼云繼有急徵旋見脂轄因作七言四韻戲以贈之或冀其感悟也》,題下自注:“己巳年。”詩云:“莫恨當年入用遲,通材何處不逢知。桑田變後新舟楫,華表歸來舊路歧。公幹寂寥甘坐廢,子牟歡抃促行期。移都已改侯王第,惆悵沙堤别築基。”另一首《又一絶請為申達京洛親交知余病廢》云:“鬢惹新霜耳舊聾,眼昏腰曲四肢風。交親若要知形候,嵐嶂煙中折臂翁。”前一首詩的某些語詞、句子的清晰解讀,對於避免誤讀,準確理解此詩本身是很有必要的,而且還關涉韓偓在此後為何要離開沙縣擬往撫、信的問題,為此我們先作些解釋。
“前鄭左丞璘”,即原唐朝尚書左丞鄭璘,時亦在閩中。“外鎮舉薦赴洛”,指鄭璘為閩王審知之舉薦而將赴洛陽任梁朝官職(據《資治通鑒》卷二六七,梁遷都洛陽在開平三年己巳正月)。“兼云繼有急徵”,指韓偓聽説還有急徵之事。“旋見脂轄”之“脂轄”,乃指脂車,謂準備駕車遠行。如《左傳·哀公三年》:“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楊伯峻注:“轄為車軸兩頭之鍵,塗之以脂。古無機油,以動物脂肪代之,使車行滑利也。”《晉書·張軌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唐白居易《偶題十五韻聊戲二君》:“聞君每來去,矻矻事行李。脂轄復裹糧,心力頗勞止。”(以上“脂轄”之註釋以及所引例句均據《漢語大詞典》) 因此此處的“旋見脂轄”説的是很快見到鄭璘已經“脂轄”,準備動身了。韓偓見此很不以為然,故以“公幹寂寥甘坐廢,子牟歡抃促行期”之典規諷之。此處的“促行期”即針對旋見鄭璘的“脂轄”而言。以此可見當時韓偓是見到正“促行期”而“脂轄”的鄭璘的,故能賦此詩以“贈之”;並因鄭璘將赴京洛,故有《又一絶請為申達京洛親交知余病廢》之托付鄭璘之事。
明白了上述兩首詩之内涵,就更便以探明韓偓為何要離開沙縣之原因,以及邵武被追回“沙縣郊外泊船”之内在隱情過程了。原來當韓偓見到鄭璘為王審知所舉薦,即將赴洛陽仕於朱梁王朝,又聞知王審知還將有“急徵”之事時,他當然會引起警惕,擔心王審知也將會舉薦他赴洛陽,或請他就任福州幕府。因此他的《又一絶請為申達京洛親交知余病廢》詩之自訴“病廢”“折臂翁”等殘疾之病況,除讓交親知曉自己病情外,當還有以此為藉口,一表拒絶徵召之意。但詩人之擔心疑慮並未到此解除,故採取一走避之之行動。那麽韓偓此舉為何立即為王審知所知曉,並馬上派遣“急脚”追回他呢? 我以為鄭璘之被“急徵”赴洛,必定有王審知的使者至沙縣傳命“急徵”他。這樣此使者一旦知道韓偓離開沙縣,即會火速報告王審知,王審知也就立即命“急腳”緊追詩人。如果這一推測大致不誤的話,那麽這件事表明儘管韓偓此時已經更為疏離甚至可以説不願依王審知了,但後者至此時還是很器重關注,甚至可説是“眷私”韓偓的,否則他又何必如此作為呢?
四
韓偓於開平三年正月被王審知所派遣之“急腳”追回沙縣後,並没有擔任任何職務,也未見曾到福州之迹,這説明儘管王審知仍然器重關注他,但他仍然與王審知保持疏離的態度。此後更是有意避開王審知,遷居他方,離福州越來越遠。開平三年(909)年底,詩人離開沙縣赴尤溪。開平四年(910) 春抵尤溪後不久即寓居於南安縣桃林場,時有《桃林場客舍之前有池半畝木槿櫛比閼水遮山因命僕夫運斤梳沐豁然清朗復覩太虚因作五言八韻以記之》詩,中云:“插槿作藩籬,叢生覆小池。為能妨遠目,因遣去閑枝。鄰叟偷來賞,棲禽欲下疑。虚空無障處,蒙閉有開時……稍寛春水面,盡見晚山眉。岸穩人偷釣,階明日上基。”此詩以詩人“命僕夫運斤梳沐”“閼水遮山”之櫛比木槿,使得“客舍之前”“豁然清朗,復覩太虚”,而詩人也樂在其中。詩人之所以這麽做,乃表明他有意隱居於此,故有如此之舉。這一打算有作於同年春末的《卜隱》詩可證:“屏迹還應減是非,卻憂藍玉又光輝。桑梢出舍蠶初老,柳絮蓋溪魚正肥。世亂豈容長愜意,景清還覺易忘機。世間華美無心問,藜藿充腸苧作衣。”還有同年春所賦的《寄隱者》和《贈隱逸》詩體現此時詩人的隱居生活與安於隱逸的心態。兩詩如下:“煙郭雲扃路不遥,懷賢猶恨太迢迢。長松夜落釵千股,小港春添水半腰。已約病身抛印綬,不嫌門巷似漁樵。渭濱晦迹南陽卧,若比吾徒更寂寥。”“静景須教静者尋,清狂何必在山陰。蜂穿窗紙塵侵硯,鳥鬥庭花露滴琴。莫笑亂離方解印,猶勝顛蹶未抽簪。築金所得非名士,況是無人解築金。”
那麽為何詩人在王審知追回沙縣不到一年後要再離開沙縣,遠避於離福州更遠的福建南方的桃林場呢? 我想詩人之所以如此,這表明他想遷移到更能躲避王審知影響力的偏僻之處以安身隱居,可見他更有意疏離王審知了。這是其中原因之一。此外,起碼還有與王審知和其幕府諸幕僚關係之因素。
考韓偓《此翁》詩云:
高閣群公莫忌儂,儂心不在宦名中。嚴光一唾垂緌紫,何胤三遺大帶紅。金勁任從千口鑠,玉寒曾試幾爐烘。唯應鬼眼兼天眼,窺見行藏信此翁。
此詩題下有“此後在桃林場”小注,據此知詩作於後梁開平四年(910) 在桃林場時。岑仲勉《唐集質疑·韓偓南依記》謂“考偓初至福州,後乃之泉,觀《此翁》詩有‘高閣群公莫忌儂,儂心不在宦名中’ 等語,知審知左右忌之者甚衆”①岑仲勉:《唐人行第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79 頁。。孫克寬《韓偓簡譜》亦謂“《此翁》七律詩有‘高閣群公莫忌儂’ 句,殆王審知參佐有忌之者”②孫克寬:《詩文述評·韓偓簡譜》,第98—99 頁。。品味此詩首聯可知妒忌讒毀詩人的是“高閣群公”,也就是王審知幕府中一些頗有地位勢力的僚佐,而且其人數也不少,故詩中以“高閣群公”稱之。那麽這些人為何要“忌”詩人呢? 從韓偓“儂心不在宦名中”句以釋“群公”之“忌”揆之,當是王審知尚器重並有延攬詩人之意,甚至有所行動,故引起“高閣群公”之“忌”其入宦王審知閩國幕府之舉動。正因有“高閣群公”之“忌”,故詩人又以“嚴光一唾垂緌紫,何胤三遺大帶紅”,以決意隱居的嚴光和何胤自比以明心志①關於這兩句詩之寓意,請參讀《韓偓集繫年校注》此詩下之相關注釋。。很明顯,“高閣群公”之“忌”倒不是韓偓得罪了他們,而是他們出於自保地位而嫉賢妒能之所謂小人之心。試想韓偓曾是一位為唐昭宗所寵重,任過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的重臣,如今如肯為閩國所用,禮賢下士的王審知必定以高位禮聘之,加以尊崇重用。這對於那些自保地位而嫉賢妒能的“高閣群公”來説是難於接受而必然引起不安的,因此也就“忌”“毀”起詩人來。而“高閣群公”的“忌”“毀”,對於“儂心不在宦名中”的詩人來説,更會增强不入王審知幕府之心,並加速他遠離王審知之步伐。
此外從開平四年韓偓所作的《失鶴》詩,也能印證上述韓偓為何又遠避至桃林場之故。此詩云:“正憐標格出華亭,況是昂藏入相經。碧落順風初得志,故巢因雨卻聞腥。幾時翔集來華表,每日沉吟看畫屏。為報雞群虚嫉妬,紅塵嚮上有青冥。”品味此詩,乃詩人受閩王審知幕僚猜忌有感而作。詩用寓托之法,失鶴即自喻自謂,以離開故巢之華亭鶴,抒發自己被迫離開朝廷之處境與心志。首二句以華亭鶴表明自己原本出身不凡,氣宇軒昂,不同於一般群類。頷聯回首身世經歷,謂原本在唐昭宗朝亦曾仕途通達得志,不料卻因朱全忠之竊取朝政,屠戮排擠朝臣,以致自己不得不離開故都。頸聯則抒寫對昭宗朝之嚮往與懷念。“幾時”,表熱切之盼望也;“每日”,明無時不“看畫屏”,無時不為思念往昔而“沉吟”。尾聯則歸結至本詩原意,不無諷刺地告訴猜忌者:我本有超脱紅塵之高遠志嚮,汝等正不必空嫉妒也②關於《失鶴》詩所包含的具體意藴,請參看拙著《韓偓論稿·韓偓〈失鶴〉 〈鵲〉 〈火蛾〉 三首詩發覆與解讀》。。
此外,除了上文所示本年韓偓多有卜隱、隱居以及和隱者來往的詩作外,《卜隱》之“世間華美無心問,藜藿充腸苧作衣”,《寄隱者》之“已約病身抛印綬,不嫌門巷似漁樵”,以及《山院避暑》之“何人識幽抱,目送冥冥鴻”,《閑居》詩之“厭聞趨競喜閑居,自種蕪菁亦自鋤。……刀尺不虧繩墨在,莫疑張翰戀鱸魚”等詩句也頗值得體味。在這一年中詩人為何要這麽頻繁地表白自己“厭聞趨競”“已約病身抛印綬”,無心追求“世間華美”,樂於隱居生活之心志呢? 又為何要提出並嚮誰表明“何人識幽抱,目送冥冥鴻”“莫疑張翰戀鱸魚”呢? 考之於韓偓不斷遠離福州之前述緣由,除了以此不斷嚮王審知表明自己無心仕宦、決意隱逸而婉拒其入幕之請外,此次之“何人識幽抱”“莫疑張翰戀鱸魚”之句,就如《失鶴》詩,其指嚮更主要是針對忌毀他的“高閣群公”。
五
韓偓遠離福州的腳步並没有止於桃林場,他住桃林場約一年,即於開平五年(911,是年五月改元乾化) 春又徙居至南安縣。又據《十國春秋·韓偓傳》“龍德三年,卒於南安龍興寺,葬葵山之麓”①[清]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十五,第1371 頁。,知龍德三年(923),韓偓年八十二卒於南安。
韓偓在南安度過最後的十三年時光。這裏我們要提出兩個問題,首先是他又遷居南安是否還與避“高閣群公”之忌毀、進一步疏離王審知有關? 我以為回答是肯定的。考《資治通鑒》《十國春秋》等史籍,朱梁建國後,王審知不但“稱臣奉貢”,還時有互動(詳上文),就是在後梁開平四年左右“梁加王中書令、福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閩王”②此事《資治通鑒》卷二六七(第8708 頁) 和《十國春秋》卷九十(第1310 頁) 記在開平三年四月;《五代會要》和翁承贊《大唐故扶天匡國翊佐功臣威武軍節度觀察處置三司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福州大都督府長史食邑一萬五千户食實封一千户閩王墓志並序》記在開平四年。。據翁承贊《大唐故扶天匡國翊佐功臣威武軍節度觀察處置三司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福州大都督府長史食邑一萬五千户食實封一千户閩王墓志並序》,此次敕封儀式非常隆重:“翌歲,敕封閩王。天子御正殿親降簡册,自東上閣門宣車輅冠劍,太常鼓吹,詔名卿乘軺,直抵南閩。至止之日,自江館陳儀注,復展鹵簿,旌旗珂佩,文武導從,籠絡井邑,簫鼓相望二十里,抵登庸館展禮。王弁貂冠,被禮服劍履,受册命,乘輅車,坐公衙,以彰曠代之貴盛。雖郭尚父、渾令公之恩澤,無以加也。”③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449 頁。此文亦見《文史》第28 輯,第138 頁。試想韓偓知悉此“以彰曠代之貴盛”事又做何感想,豈不更反感而越加疏離王審知。此外“高閣群公”之忌毀也一直延續下來,即使在他移居南安後也如此,這使得他一直惴惴不安。這兩種狀況和情緒在他詠於乾化元、二年的諸多詩作,如《殘春旅舍》之“兩梁免被塵埃污,拂拭朝簪待眼明”,《喜涼》之“東南亦是中華分,蒸鬱相凌太不平”,《淒淒》之“嗜鹹凌魯濟,惡潔助涇泥”,《露》之“名因霈澤隨天睠,分與濃霜保歲寒。五色呈祥須得處,戛雲仙掌有金盤”,《鵲》之“莫怪天涯棲不穩,托身須是萬年枝”等詩句中均有所流露。
其次,韓偓到南安之後是否如史籍所謂“依”王審知,或者依王審知之弟、侄王審邽、王延彬? 檢《新唐書》卷一百九十《王審邽傳》:“審邽……為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④[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九〇,第5492—5493 頁。《十國春秋》卷九十四《閩五·王審邽傳》:“中原亂,公卿多來依閩,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禮之,振賦以財,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誥兵部侍郎韓偓、中書舍人王滌、右補闕崔道融、大司農王標、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勳員外郎王拯、刑部員外郎楊承休、弘文館直學士楊贊圖、王倜、集賢殿校理歸傳懿,及鄭璘、鄭戩等,皆賴以免禍。”①[清]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十四,第1363 頁。又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四《寓賢·杜襲禮傳》引《王氏家乘》:“杜襲禮,昭宗時為水部員外郎,朱全忠篡唐,避亂來泉依刺史王審邽,與常侍李洵、承旨韓偓諸公同賓禮於招賢院。”②鄧小軍:《詩史釋證·韓偓年譜》,第311—312 頁。按,《韓偓年譜》曾引以上典籍記載,經過細緻考訂認為其所記多有誤,云:“偓自本年辛未梁乾化元年(911) 起,至癸未梁龍德三年(923) 去世,寓居南安共十三年。偓寓居南安以後大部分時間,泉州刺史為王延彬。”“ 《新唐書》謂偓來依王審邽,實則辛未梁乾化元年(911) 偓來南安時,審邽早已卒於天祐二年(905)…… 《新唐書》此説誤。《八閩通志》《十國春秋》等亦沿其誤。”“《新唐書》《十國春秋》及乾隆《泉州府志》所引《王氏家乘》,謂唐朝官員李洵、韓偓等來泉居招賢院,實則偓並未入招賢院。諸家記載,蓋連類而及之誤。”“偓至南安後,先寓居旅舍,後在縣東龍興院(元代地名三都) 葵山下建成‘枳籬茅屋’ 之家園,率家人躬耕自養,並未入王延彬之招賢院。”③同上,第312 頁。此實況陳敦貞《唐韓學士偓年譜》後梁太祖乾化元年譜亦早有指出:“韓公在桃林場,似仍未能安心住下去,乃於今年夏間(慶按,此謂“夏間”恐稍晚,應是“春間”) 離桃林,取水路南下至南安縣治,即今豐州鎮,寄居九日山僧舍。山在鎮西里許,去泉州郡城不上十里。……韓公既不到這郡城去,也不住到距豐州鎮五里的潘山之招賢館。”④陳敦貞:《唐韓學士偓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62 頁。同譜乾化二年又謂:“韓公自去年至南安縣治,今年仍在南安縣,而自九日山移居於縣治東門外二里許偏處西北方之三都董埔鄉龍興寺。故老相傳,韓公在董埔鄉寺間,亦自居處。蓋公南來,除了家人,還有族人,有些族人留居閩中,其餘到南安縣來,就在韓公領導下,擇地龍興寺後的葵山,以墾荒耕種,名其地曰杏田,並以安置族人,隨成一小村落,至今猶稱杏田村。”⑤同上,第65 頁。今檢韓偓詩文以及有關記載,仍可見韓偓到安南後並未依閩國王氏諸人,而是過着村居之貧寒生活。如作於乾化二年(912) 之《余卧疾深村聞一二郎官今稱繼使閩越笑余迂古潛於異鄉聞之因成此篇》之“枕流方採北山薇,驛騎交迎市道兒”,《深村》詩“甘嚮深村固不材,猶勝摧折傍塵埃。清宵玩月唯紅葉,永日關門但緑苔。幽院菊荒同寂寞,野橋僧去獨裴回。隔籬農叟遥相賀,且喜今春膏雨來”,乾化三年(913) 之《南安寓止》云“此地三年偶寄家,枳籬茅廠共桑麻”,貞明二年(916) 之《幽獨》云“幽獨起侵晨,山鶯啼。更早。門巷掩蕭條,落花滿芳草。煙和魂共遠,春與人同老。默默又依依,淒然此懷抱”,從這些詩中不難窺見韓偓在移居南安後仍然過着清貧的鄉村生活。他在南安尚有嚮人借衣借米的兩封書信。《手簡·第十帖》云:“眷私借及女使衣服,不任悚荷。來早令入州人馬,必希踐言。泉州書謹封納書中,亦説皆諮托。必望周而述之,幸甚,謹狀。九日偓狀。”《手簡·第十一帖》云:“憂眷借及米貳碩,不任濟荷。鈍拙無謀,惟撓知與,不勝愧赧之至。即冀拜謁,它冀面述。謹狀。念二日偓狀。”可見詩人在泉州南安時之清貧,故其時即賦有《安貧》詩。韓偓在唐亡後多次拒絶朱梁復故官之招,也不從王審知之請入仕閩國幕府,因而晚景貧寒,使得後人頗為感傷。黄庭堅即云:“今觀十一帖,字字筆到。亂離中借衣、乞米,真復可憐。”①[明]汪砢玉:《珊瑚網》卷二《法書題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鄭文寳《南唐近事》卷二曾謂:“韓寅亮,渥(慶按,渥即韓偓,文獻中時有將韓偓寫作“韓渥”者) 之子也。嘗為予言渥捐館之日,温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玩,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為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内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宫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 余丱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説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即渥之妾云耳。”②《宋元筆記小説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5 頁。故史家清吴任臣《十國春秋·韓偓傳》云:偓“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殁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而已”③[清]吴任臣:《十國春秋》,第1371 頁。。
綜上所述可知:韓偓入閩之初尚可稱依王審知,然而因他忠於李唐王朝,厭惡篡奪唐政權之朱梁僞朝,故不久即不滿並疏離稱臣於朱梁之閩國王審知,離開福州,踏上不依王氏之路。儘管王審知一直敬重並有延請他入仕閩國之熱忱,但以上述原因以及王審知幕府群公不斷忌毀之故,他即先後遷徙到沙縣、桃林場、南安等地,過着清貧的隱居生活至卒,以表既不仕朱梁,也不依王氏之志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