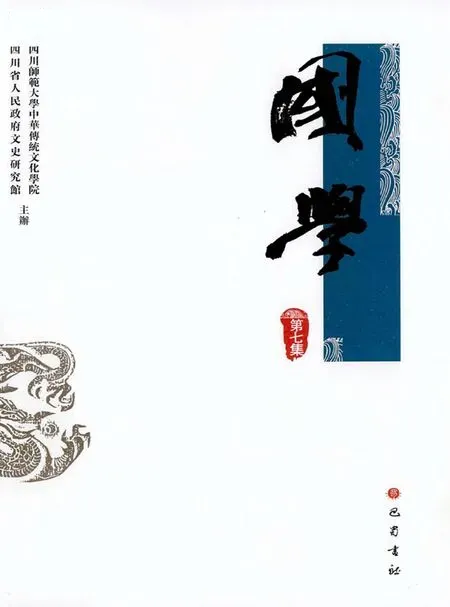清代考據學的理論與方法檢討
謝桃坊
中國在20世紀之初興起的國學運動以1905年《國粹學報》的創刊為標志,自1919年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胡適號召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得到學術界的響應,使國學運動出現新的傾嚮。此年傅斯年也認為“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1926年顧頡剛在回答某些學者對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質疑時説:“國學是科學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學的方法而做研究),而不是與科學對立的東西。”①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集》(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7—81 頁;傅斯年:《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 識語》,《傅斯年全集》(1),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2 頁;顧頡剛:《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發刊詞》,《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第169 頁。新文化思潮的學者們所提倡的科學方法是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研究的實證主義方法。實證主義注重在研究工作中採用一般的自然科學研究程式,特别是胡適引入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和傅斯年引入德國蘭克的實證主義史學對國學運動新傾嚮産生了重大的影響②謝桃坊:《國學研究與科學方法》,《國學史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69—88 頁。。然而西方近代科學重證求真的精神與中國清代乾嘉的考據學是有相通之處的,國學運動新傾嚮的代表人物即認為清代考據學是採用的科學方法。梁啓超談到清代考據學時説:
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方法。清代考證學,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惠(棟)、戴(震) 諸師,實闢出一種新途徑,俾人人共循,賢者識大,不賢識小,皆可勉焉③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第18 頁。。
中國的考據學興起於北宋,盛於清代乾嘉時期。胡適説:“這種考證方法,不用來自西洋,實係地道的國貨。三百年來的考據學,可以追溯至宋,説是西洋天主教耶穌會士的影響,不能相信。我的説法是由宋漸漸地演變進步,到了十六七世紀有了天才出現,學問發達,書籍便利,考據學就特别發達了。”①胡適:《考證方法之來歷》,《胡適文集》(12),第112 頁。考據學也稱為實學。傅斯年説:“近千年來之實學,一炎於兩宋,一炎於明清之際。兩宋且不論,明中世後焦竑、朱謀垏、方密之實開實學之風氣。開風氣者為博而不能精…… (清代) 亭林(顧炎武)、百詩(閻若璩) 謹嚴了許多。然此時問題仍是大問題,此時材料仍不分門户也,至乾嘉而大成。”②傅斯年:《致王獻唐》,《傅斯年全集》(7),第100—101 頁。顧頡剛則從先秦古籍的辨偽工作而肯定清代考據學的意義。他説:“清代辨偽的主流,無疑是要把從戰國到三國的許多古籍的真偽和它們的著作時代考辨清楚,還給它們一個本來面目。他們的優點是不受傳統的束縛,敢於能觸犯當時的‘離經叛道,非聖無法’ 的禁條,來打破封建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造成的歷史,所用的方法也是接近於科學的。”③顧頡剛:《崔東壁遺書序》,[清]崔述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0 頁。國學運動的新傾嚮逐漸在國學運動中居於主流的地位,這些學者們在國學研究中繼承和發展了清代的考據學,同時吸收了西方近代的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而形成科學考證方法,所以學術界往往將國學等同於考據學,將國學家等同於考據家。近二十餘年來,國學思潮再度在我國興起,我們在考察20世紀國學運動的歷史和近年的國學熱潮時,實有必要探討國學與西方科學方法及清代考據學的内在的學術淵源。兹謹對清代考據學的理論與方法試作檢討。
一
考據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種治學方法,它在對中國文獻與歷史上存在的若干狹小的學術問題進行考索研究時,以客觀的態度,注重證據,以求真知。自北宋以來興起了疑經疑古的思潮,開創了學術的求真時代;以後經明代的發展,至清代終於形成了一門學問——考據學。清代初年學者們在研究經學時採取考據的方法取得突出的成就,至乾隆和嘉慶時期考據學蔚然成風,由經學嚮史學、諸子學、小學、音韻學、地理學、金石學、圖譜學、天文、數學等學術發展。雖然在清代中期以後今文經學復興,但考據學仍然綿延,並為國學新傾嚮的學者們所承傳。清代著名的考據學家有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盧見曾、朱筠、萬斯年、惠棟、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王鳴盛、趙翼、俞正燮、翁方綱、畢沅、阮元、孫星衍、盧文弨、武億、洪亮吉、淩廷堪、孔廣森、焦循、陳澧、王昶、江藩、郝懿行、崔述、全祖望、孫貽讓、俞樾,等等。他們的努力使考據學成為清代諸種文化中最有成就和最富時代特色的學術。考據學在傳統學術中屬於義理之學、經濟之學、詞章之學後的新興之學。關於它與其他學術的關係,王鳴盛説:
夫天下有義理之學,有考據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詞章之學。譬諸木然,義理其根也,考據其幹也,經濟則其枝條,而詞章乃其葩葉也。譬諸水然,義理其原也,經濟則疏引灌溉,其利足以澤物,而詞章則波瀾淪漪,濚洄演漾,足以供人玩賞也。四者皆天下所不可少,而能兼之者則古今未之有也。……是故義理與考據,常兩相須也;若夫經濟者事為之末,詞章者潤色之資,此則學之緒餘焉已爾①[清]王鳴盛:《王戇思先生文集序》,《西莊始存稿》卷三十五,《續修四庫全書》第143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這合理地説明了考據學在諸種學術中的意義,並説明了它與諸種學術的關係。然而我們回顧清代學術史時,考據學的意義確是特别突出的。
考據學在清代有多種别稱,或稱之為“樸學”,因其以樸實學風見長,而與虚談義理者相區别。如翁方綱説:“今日經學昌明,學者皆知奉朱子為正路之導,其承姚江(王陽明)之説者固當化去門户之見,平心虚衷以適於經傳之訓義,而又有由荀(爽)、虞(翻)、馬(融)、鄭(玄) 博涉群言以為樸學:此則考證之學又往往與朱子異者。”②[清]翁方綱:《姚江學致良知論上》,《復初齋文集》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 册。考據學又名“實學”,以其重證求實之故。黄承吉説:“自漢晉以來,經學集成於本朝,而邃學者尤以徽、蘇兩郡為衆盛,即吾揚(州) 諸儒亦皆後出。徽(安徽) 自婺源江氏(永) 首倡,戴氏(震) 出於休寧繼之,歙金氏(榜)、歙程氏(瑶田) 等又繼之。蘇(江蘇) 則惠氏(周惕) 研溪猶出顧氏(炎武) 之後,而顧更遠出於徽衆氏之前,然則論實學者,莫或顧之先矣。”③[清]黄承吉:《字詁義府合按後序》,《字詁義府合按》附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考據學又在清代稱為“漢學”。梁啓超談到清代正統的考據派時説:“正統派則為考證而考證……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佚,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④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3—4 頁。此外考據學常等同於考證學,或考訂學,名稱雖異,其實相同,而通稱為考據學。
清代考據學繁榮興盛的社會文化原因梁啓超概括為:因明代學術極空疏之後,學者治學趨於沉實;清初以來社會比較安定,學者有餘裕自厲於學術;漢族學者在清代耻立乎其朝,專致於樸學;理學的權威被破壞,學者們自由研究的精神特盛①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17 頁。。近世學者對於清代考據學興盛的外部社會歷史條件,清代的文化政策,以及學術發展的内在原因均做了充分的論述②參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10—411 頁;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派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8 頁;林慶彰:《實證精神的尋求——明清考據學的發展》,《中國文化新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295—342 頁。。此外,乾嘉時期的學術風尚應當引起我們關注。梁啓超已經見到此種社會風尚:
乾嘉間之考證學,幾乎獨佔學界勢力,雖以素崇宋學之清室帝王,尚且從風而靡,其他更不必説了。所以稍為時望一點的闊官乃至富商大賈,都要附庸風雅,跟着這些大學者學幾句考據的内行話。這些學者得這種有力的外護,對於他們工作的進行,所得利便也不少。總而言之,乾嘉間考證學,可以説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合全國人的力量所構成③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第24 頁。。
清代諸帝王都是崇尚宋明理學的,理學成為統治思想,科舉考試沿襲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而考據學是一種純學術,它與統治思想無關,也與科舉考試無關,乃是無社會現實效益的學問。清代統治者們實際上並不支持,亦不反對,讓它自由發展。然而漢族學者卻不計現實的功名利禄而從事這種純學術的研究工作,固然由此可以遠離政治,亦可滿足真正的學術興趣。考據風尚得到漢族某些貴幸官員以及富商大賈的支持,他們贊助考據著作的刊行,這應是他們為保存中華傳統文化而作出的努力,衹要漢民族文化存在,漢民族便有復興的希望。漢代的經師、南宋後期至明代的理學家們受到朝廷的重視,在社會上有尊榮的地位,李慈銘將考據學與明代以來的理學相比較,以為“若我朝諸儒之為漢學也,則違忤時好,見棄衆議,學校不以是為講,科舉不以是為取”。這樣考據學既違背清王朝諸帝王之好尚,不為朝廷議論,不為學校講授,不為科舉考試所取,實為無社會實效的無用的東西。因此李慈銘考察了數十位考據學者在清代的社會命運後嘆息説:“諸君子之抱殘守闕,齗齗縑素,不為利疚,不為勢詘,是真先聖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夫豈操戈樹幟,挾策踞坐,號召門徒,鼓動聲色,呶呶陸王之異辭,津津程朱之棄唾者所不同年語哉!”④[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761 頁。考據學者們孜孜以求的學術不會給他們帶來財富利禄,不能通嚮科舉入仕之路,但他們憑着學術的使命所産生的信念,以畢生的精力致力於學術的事業。衆多的學者在師生、朋友、同僚、親戚、同年和同學之間,以學術互通聲氣,互相討論,互相支持,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例如朱筠的門人有陸錫熊、程晉芳、任大椿、戴震、汪中、孫星衍、洪亮吉、江藩。戴震師事江永,其同年及友人有程瑶田、金榜、惠棟、紀昀、王昶、錢大昕、姚鼐、秦蕙田、王鳴盛、盧文弨、是仲明、盧見曾、任大椿,其弟子則有王念孫、段玉裁、孔廣森、朱珪、孔繼涵、畢沅。錢大昕的交遊更廣,友人戴震、段玉裁、孫星衍、盧文弨、王鳴盛、朱筠、梁玉繩、洪亮吉等時常書信往來,討論學術問題,並為閻若璩、胡渭、萬斯同、陳祖范、惠士奇、王懋竑、惠棟、江永、戴震等作傅。這些學者之間破除師生界限、尊卑地位、年齡差異,没有門户之見,在學術面前平等,形成真正的學派:此應是清代考據學繁榮興盛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二
清代考據學涉及中國各種傳統學術,致力於對文獻與歷史上存在的若干狹小學術問題進行考證,其形式可概括為五類:
(一) 疏證,對古代典籍之字、音、義作細緻的考辨訓釋,例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洪亮吉《春秋左傳詁》、焦循《左傳補疏》、段玉裁《説文解字注》、桂馥《説文義證》、王念孫《廣雅疏證》、郝懿行《爾雅義疏》。
(二) 校訂,對典籍文字進行校勘訂正,例如戴望《管子校正》、俞樾《群經平議》、戴震《水經考次》、嚴可均《唐石經校文》。
(三) 史考,對史籍進行考訂,並對史事進行辨正,例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趙翼《廿二史劄記》。
(四) 筆記,作者讀書時對發現之各種細小學術問題進行考辨而寫下的學術心得,例如顧炎武《日知録》、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俞正燮《癸巳類稿》。
(五) 專題考證,對學術問題作專文考證,如戴震《河間獻王傳經考》《尚書今文古文考》《明堂考》《樂器考》,錢大昕《秦三十六郡考》《漢百三郡國考》《華嚴四十二字母考》《古嘉量考》《兩漢佚史别史考》,沈垚《後魏六鎮考》《蔥嶺南北河考》《漳北滱南諸水考》,等等。此外,清代學者許多專題的考證專著體現了考據學的最高的學術水準,例如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沈彤《周官禄田考》、張金吾《兩漢五經博士考》、徐松《兩京教坊考》、李光廷《漢西域圖考》、阮元《三江考》、沈濤《説文古本考》、紀容舒《唐韻考》、陳澧《切韻考》、淩廷堪《燕樂考原》、李超孫《詩氏族考》、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考》、崔述《洙泗考信録》,等等。
學者們在考據工作的實踐中總結出的考據學理論,是我們研究乾嘉學術應特别關注的。翁方綱生於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十七年(1752) 進士,卒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他歷主學政,時值考據學興盛,負海内清望數十年。他的《考訂論》乃是一篇總結考據學理論的長文,以為“考訂者,考證之訂,非斷定之定也。考訂者,考據、考證之謂,非斷定之謂”①[清]翁方綱:《考訂論》下之三,《復初齋文集》卷七。。考訂即是考據或考證,乃依證據以訂正文獻及史事,但通稱為考據學。考據的根本出發點在於“考”,而不在於“定”。翁方綱理解的“定”乃是製作,例如聖哲之製作禮制或樂制,而“考”則是比較經典所載之制的沿革與異同,以此證彼,求得一個正確的結論;當然這是判斷,它與自我立論製作有性質上的不同。如果從主觀的意見以某事或某制應當是怎樣的,誰又能相信此事或此制為真實呢? 此隱含的意義是可以通過考據而否定儒家某些經典的。為什麽學者必須進行考據呢? 翁方綱認為:
凡考訂之學,蓋出於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後考訂之,説有互難而後考訂之,義有隱僻而後考訂之;途有塞而後通之,人有病而後藥之也。乃名義之隱僻者,或實無可闡之原,或碎無可檢之來處,則虚以俟之可矣。事有兩歧,説之互出,而皆不得其根據,則待其後而已矣。此亦莊生所謂緣督為經也②緣督: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莊子·養生主》:“緣督以為經,可以全身,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但如未有窾郤,而何以批之導之哉! 若其立意以考訂見長者,則先自設心以逆之,而可言考訂乎! 若其事之兩歧,説之互出,義之險賾,苟間以私意出入,而軒輊焉者,其為考訂也,必偏執而愈增其擾矣,又奚以為考訂哉! 訂者懲棼絲而理之也,未有益之以棼絲者也③[清]翁方綱:《考訂論》下之一,《復初齋文集》卷七。。
當學者發現文獻記載中事實分歧,意見互異,義理深奧隱僻,這就需要進行考證,以求真實,達於真知。考據工作有如道路阻塞而使之通暢,人們患病而給以治療。學者對義理之探討不得其本原,未查尋到出處,於事實、意見之考察未獲得證據,這衹有闕疑。如果從以上三項中發現問題,獲得大量證據,設立假説,這樣便可從事考據工作。但若憑主觀並挾私意而輕率斷定,這樣的考據必然因偏執而使問題變得愈加複雜了。考據工作有如治絲,將紛亂之絲理順,而不是使之愈益紊亂。因而考據並非與義理無關,而是以義理為指導的,所以翁方綱主張“考訂之學以義理為主”。關於義理與考訂的關係,在古代的訓詁、辯難、校勘、鑒賞的學術中都存在考訂,但是古代學者立言主要是闡明義理,尚不知考據之學。考據之學是中國學術的發展到了求真的時代纔興起的新的學問。考據家治學的目的不是探求義理,卻必須具有高度的理性判斷,否則其考證是難以達到高度學術水準的。
梁啓超論及清代考據學派時認為:“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 ‘無徵不信’。”④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4 頁。這是就方法論而言的,但確切地説它們不是方法,而是考據學的原則,由此以指導具體的方法。我們可以把考據學家們崇尚的原則概括為“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和“條理精密”。《漢書》卷五十三《河間獻王劉德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注:“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這是指通過對實事的考察以求得符合事實真相的正確結論。淩廷堪解釋説:“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强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强辭而是之也,如六書(六種造字條例)、九數(九九演算法) 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説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别持以為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①[清]淩廷堪:《戴東原先生事略狀》,見[清]戴震撰,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第七册,合肥:黄山書社,1995年,第23 頁。考據學主張的實事求是乃探討事實的,故又稱為實學,它所認定的事實不可能强辭論辯而被否定,因正確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義理之學是以思辨的方式談虚理的,它所樹立的理,衹要持一種理論便可被否定、動摇或懷疑。因此考據與義理之學在治學原則和思維方式上均是相反的,所以淩廷堪認為戴震所治的是“實學”,而與義理之學有别。阮元從治經學的角度論及怎樣做到實事求是,他説:
余以為儒者之於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安國)、賈(逵) 義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説經者也,其説《考工》戈戟鍾磬等篇,率皆與鄭(玄) 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為不刊之説,未聞有違注見譏者。蓋株守傳注,曲為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為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②[清]阮元:《焦理堂群宫室圖序》,《研經室集》一集卷十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478 册。。
考據學在清代又稱為漢學,某些學者解經堅信漢代經古文學派之傳注,以為是絶對應守的,其所謂“是”即是合於漢人之傳注。阮元認為漢儒之傳注有是有非,若要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則既可依從漢儒之傳注,亦可否定,這纔是真正的實事求是。在某些考據學者迷信漢儒傳注時,學者們易於見到捨棄傳注憑臆空談之錯誤傾嚮,難以見到墨守漢儒傳注之弊,所以阮元為糾正考據學中的一種偏嚮而堅持主張實證精神。實事求是要求學者們服從真理,尋求真知,以此作為學術價值判斷的最高標準。萬斯同説:“事而真,即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真,即百十人亦可疑。此論真偽,不論衆寡也。”③[清]萬斯同:《石鼓文辨》,《石園文集》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415 册。堅持實事求是即堅持學術的真理。真理很可能在某些時期不為大多數人所理解,但它終會取得勝利的。這是考據學者的信念。考據學的第二個原則是無徵不信。孔子談到夏殷二代古禮説:“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 文,是有關典章制度的文字資料;獻,是指多聞且熟悉掌故的人;徵,即證據。孔子在春秋時對於夏殷的古禮已因文獻的不足而無法證實,由此可得出無徵不信的結論,這成為考據學家的重要原則。龔自珍對孔子之言解釋説:“聖人神悟,不恃文獻而知千載以上之事,此之謂聖不可知,此之謂先覺。但著作之體,必信而有徵,無徵不信。”①[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八輯語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他認為聖人是生而知之的,固有神悟;聖人之言無徵不信是先覺的智慧,它為學術著作必須遵奉的原則。段玉裁記述戴震十歲時於私塾“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 以下,問塾師:‘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師應曰:‘此朱文公所説。’ 即問:‘朱文公何時人?’ 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 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 曰:‘幾二千年矣。’ ‘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 師無以應。”②[清]段玉裁:《東原年譜》,《戴震全書》第六册附録。宋代理學家以為《禮記》中《大學》一篇乃孔子之遺書為曾子所記述,但並無證據。戴震幼時對此的質疑即表現了無徵不信,體現了考據學家的求實精神。按照無徵不信的原則,學者在進行考證時因而特别重視搜集證據。王鳴盛為友人秦惠田的《五禮通考》作序稱贊説:“公每豎一義,必檢數書為佐證,復與同志往復討論,然後筆之。故少辨析異同,鋪陳本來,文繁理富,繩貫絲聯,信可謂博極群書者矣。”③[清]王鳴盛:《五禮通考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十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34 册。盧文弨批評宋代理學家治學的空疏作風説:“其病皆由於譾譾拘拘,不能廣搜博考,以求其佐證,而且專以自用,不師古人。”④[清]盧文弨:《錢晦之後漢書補表序》,《抱經堂文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32 册。李慈銘讀趙新又的《左傳質疑》説:“其言皆實事求是,不務為攻擊辯駁之辭。每樹一義,必有堅據,每設難,必有數證。”⑤[清]李慈銘:《趙新又同年左傳質疑序》,《越縵堂文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559 册。考據學家們堅持無徵不信原則,不僅廣搜證據,還注重史料的辨偽,以求所用證據之堅實。崔述説:“是知偽證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凖是以推之,莫有能遁矣。然而世之學者往往惑焉,何也? 一則心粗氣浮,不知考其真偽;一則意在記賢,以為詩賦時文之用,不肯考其真偽;一則尊信太過,先有成見在心,即有可疑,亦必為之解,而斷不信其有偽也。”⑥[清]崔述:《考信録提要》卷下,[清]崔述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第15 頁。這已指出怎樣辨偽的方法。考據學的第三个原則是條理精密,這是要求考據著作應當有謹嚴的邏輯,而使條理清晰,並在實證推理時達於精密的程度。戴震自述治學經驗:“凡僕所以求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没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必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説而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尋根可以達梢,不手披枝肄之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①[清]戴震:《與姚孝廉姬傳書》,《戴震全書》第六册,第372 頁。他所謂十分之見,即是考據的成熟的結論,它是有條貫的,確鑿而不可能有異議的,它不是從傳聞、衆説、空言、孤證而得出的,而是有極精密的推理的。戴震治學力求專精,其弟子段玉裁説:“東原師之學,不務博而務精,故博覽非所事,其識斷審定,蓋國朝之學者未能或過之也。”②[清]段玉裁:《與胡孝廉世琦書》,《韻經樓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1435 册。在考據的專精方面,戴震確可為典範。陳澧的《切韻考》是極精密的考據著作,他批評自宋代興起的等韻學在分析聲韻方面尚“不能精密”,“至國朝嘉定錢氏(大昕)、休甯戴氏起而辨之,以為字母即雙聲,等字即疊韻,實齊梁以來之舊法也,二君之論既得之矣。澧謂切語之舊法,當求之陸氏(法言) 《切韻》,韻雖亡而存於《廣韻》。乃取《廣韻》切語上字繫聯之為雙聲四十類,又取切下字繫聯之,每韻或一類,或二類,或三類四類,是為陸氏舊法。隋以前之音異於唐季以後,又錢、戴二君所未及詳也。於是分别聲韻,編排為表,循其軌迹,順其條理,惟以考據為準,不以口耳為憑,必使信而有徵”③[清]陳灃:《切韻考序》,《切韻考》卷一,北京:中國書店影印,1984年。。陳澧在乾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切韻》音系的考證達於條理而精密的程度,其《切韻考》在方法上是很科學的。
考據學家們没有門户之見,對學術問題以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研究,形成良好的學風。考據學是實學,乃相對於空談義理之學而言的,但義理又與考據有關。翁方綱説:“考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為主,其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於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異、不嗜博、不嗜瑣而專力於考訂,斯可以言考訂矣。”④[清]翁方綱:《考訂論》上之一,《復初齋文集》卷七。考據者必須博學,證據必須充實,考證之專題每涉瑣細深奧,考據的結果應是創獲,這極易流於矜己、求異、炫博、繁瑣的弊病。翁方綱指出此類弊病應當避免纔可能是真正的學者態度。為此,他希望學者“多聞”“闕疑”“慎言”,以為“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於是矣”⑤[清]翁方綱:《考訂論》下之二,《復初齋文集》卷七。,這即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戴震則强調治學不苟且、不留遺憾,他説:“其得於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世之名,亦不期於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蔽二:非抨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漏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⑥[清]戴震:《答鄧丈用牧書》,《戴震全集》第六册。學者為求真知,應客觀地對待研究對象,克服主觀私意,不圖虚名,既不妄自攻擊前人,也不盲目依附成見,做到不自欺欺人。王鳴盛考史主張將事實考證清楚,不隨意評論褒貶。他説:“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横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自擇焉可矣。其事迹則有美惡,讀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迹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記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之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書生胸臆,每患迂愚,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不當,況考之未確者哉! 蓋學問之道,求於虚,不如求於實。”①[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北京:中國書店,1987年。考據僅提供史事真相,而不作評論,衹求實證。學者們若發現前人之錯誤,或與當代學者辯論,尤應有真正學術商榷的態度。錢大昕説:“愚以為學問乃千秋事,證偽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②[清]錢大昕:《答王西莊書》,《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36 頁。學者們因有平心静氣討論學術問題的態度,所以我們見到他們師友之間互相尖鋭地批評辯論,都互相敬重,十分友好。翁方綱曾指責清初閻若璩在其《古文尚書疏證》裏存在謾駡的情況,他認為“説經宜平心易氣,擇言而出之,和平審慎而道之”③[清]翁方綱:《古文尚書條辨序》,《復初齋文集》卷一。,如果謾駡,便不是“疏證”了。閻若璩的這種態度在乾嘉學者中已經罕見了,學術的風氣已經很不正常了。
三
清代考據學的方法,我們從學者們的著述中可歸納為辯證、訓詁、校勘、參驗、博證、探原、實測七種。兹舉例分述如下。
(一) 辯證 以充分的證據辨别文獻或歷史記載之是非真偽。清初的大學者錢謙益長期留心於明史,旁稽博詢,纂成一百卷的著述,惜乎毀於絳雲樓失火,但今存《太祖實録辯證》五卷應是清代考據學之第一名著。例如《太祖實録》記載:“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寜謀反,詞連李善長等。賜惟庸、寧死,善長勿問。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長大逆罪狀,廷訊得實,善長遂自經,賜陸亨等死。”錢謙益辯證此條記載用七千四百餘字,以明代《開國功臣録》、《昭示奸黨録》以及詔令和審訊供詞等第一手資料辨析記載之誤。他認為:“永樂初史局諸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誤,於記載若此。窺其大旨,不過欲以保全勳舊,揄揚高皇帝之深厚仁德,而不顧當時之事實,抑没顛倒,反貽千古不決之疑,豈不謬哉! 國初《昭示奸黨》凡三録,冠以手詔數千言,命刑部條例亂臣情辭,榜示天下,至今藏貯内閣,余得以次第考之,而厘正如左。”④[清]錢謙益:《太祖實録辯證》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390 册。關於李善長由明太祖撫慰遣歸,善長自殺,錢謙益證實李善長曾下獄:1.刑部備條亂臣情辭,首列李善長招供辭,若未下獄,何得招辭;2.營陽家人小馬招:二十三年閏四月聞知李善長被捕;3.據《皇明本紀》記載:太師李善長因叛逆伏誅,妻女子弟並家人七十餘口悉斬之。因此可證李善長並非在家自經。錢謙益的辯證極為鑿確,還原了歷史真相,所以李慈銘以為《太祖實録辯證》乃“奇作也”①[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720 頁。。清初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亦是考據學的極重要的專著,他辯證《古文尚書》之偽列義例數十條,例如:書有古人纔引,忽隔以它語豆,千載莫能知,而妄入古文中賡續者;傳注家有錯解之辭,要久而後錯始見,論始定;作偽書譬如説謊,雖極意彌縫信人之聽聞,然苟精心察之,亦未有不露出破綻處;事之真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贋者無往而不復多所抵牾②[清]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卷首,《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他根據所定之義例詳辨《古文尚書》之著録與流傳情況,各篇之訛誤,文字、曆法、山川、制度等記述之誤,宋以來各家辨偽的情況,由此證實《古文尚書》乃後人偽作,否定了唐代以來將它奉為儒家神聖經典的做法。
(二) 訓詁 考釋古代典籍的字義。戴震批評空談義理者與習時文者説:“夫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目故訓之字不足為。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意。”③[清]戴震:《爾雅注疏箋補序》,《戴震全書》第六册。其意在强調治學於典籍之文字意義應有切實的理解,方可通其語言及義理,這必須進行訓詁的工作。每個文字的形、音、義是有關聯的,清代考據學家們主張訓詁以聲為主,由聲及義。王念孫説:“以詁訓主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此之不悟,則有字别為音,音别為義,或望文虚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鮮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淩亂之譏,亦所不辭。”④[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序》,《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466 册。他在其訓詁名著《廣雅疏證》裏具體地貫徹了其主張。《廣雅》為三國魏人張揖著,乃增廣《爾雅》之未備。王念孫的疏證是就古音以求古義,整理疏解,凡原書錯亂者皆為補正考釋,如釋“聆聽自言仍從也循”云:“聆,古通作令,《吕氏春秋·為欲篇》‘古經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 令,謂聽從也。仍者,《楚辭·九章》‘觀炎氣之相仍兮’ 王逸注云:‘相仍者,相從也。’ 循者,《爾雅》‘循、從,自也’,《文選·陸雲答張士然詩》注引《廣雅》‘循,從也’,今本脱‘循’ 字。”⑤[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漢字存在一字多義的現象,它在某典籍中之具體意義,衹有通過訓詁纔能確解,而訓詁則意味着以證據進行考釋。李慈銘從學者治經的角度談訓詁的意義説:“經之須訓詁,其事甚嘖(争論、紛歧),其功甚勞,其效甚微,昔人亦何好焉,而必孜孜於拾遺掇墜,抱殘守闕,若甚於性命,身心不得已者,蓋章句不明,即經旨晦,文字不審,則聖學疏,節文度數形器之不詳,則禮樂兵刑食貨輿圖均不得其要。”①[清]李慈銘:《書沈光禄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録後》,《越縵堂文集》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559 册。訓詁不僅是研治儒家經典必需的工作,而且是研治中國古代典籍必需的工作。
(三) 校勘 是將典籍的各種版本和有關資料加以比較,審定原文的正誤真偽。戴震對《水經注》的校勘整理堪稱典範。段玉裁説:“然東原氏之功,細大互辨,據古本,搜群籍,審地望,尋文理;一字之奪必補之,一字之羨必删之,一字之誤必更之;東原氏之能事也。”②[清]段玉裁:《與畢耀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韻經樓集》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1435 册。《水經注》之經文常有錯簡,文字多訛誤,而且經文與注文時有混雜,因而它是校勘的難題,但卻引起幾位著名考據學家的興趣。戴震確定的校例是:“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凡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内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③[清]戴震:《校書提要·水經注》,《戴震全書》第六册。戴震的校本最精善,被收入《四庫全書》。晚清俞樾的《群經平議》與《諸子平議》實為校勘劄記,從典籍中發現訛誤之處,則從文字訓詁並參證有關資料以校正原文。《老子》第六十八章“是謂配天古之極”,俞樾校云:“按此文,王弼無注。河上公以‘是謂配天’ 四字為句,注云:‘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 三字為句,注云:‘是乃古之極要道也’。然此章每句有韻,前四句以‘武怒’ 與下為韻,後三句以‘德’ ‘力’ ‘極’ 為韻,若以‘是謂配天’ 為句,則不韻矣。疑‘古’ 字衍文也。‘是謂配天之極’ 六字為句,與上文‘是謂不争之德’ ‘是謂用人之力’ 文法一律。其衍‘古’ 字者,‘古’ 即天也。《周書·周祝篇》曰‘天為古’,《尚書·堯典篇》曰‘若稽古帝堯’,鄭注曰‘古,天也’,是‘古’ 與‘天’ 同義。此經‘配天之極’,它本或有‘配古之極’ 者,後人傳寫誤合之耳。”④俞樾:《諸子平議》,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59 頁。我們由此可見凡校一字之正訛是必須要進行繁瑣考證的。
(四) 參驗 即以文獻相互比較,參稽、驗證、考核,求得某一細小問題之正確的結論。錢大昕談到戴震治學經驗時説:“其學長於考辨,每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果不可易。”⑤[清]錢大昕:《戴先生震傳》,《潛研堂集》第712 頁。王引之承傳家學,在闡釋儒家經義時以參互驗證見長。錢熙祚總結王引之在《經傳釋詞》裏所用參互驗證之法計有六種:“有舉同文以互證者,如據隱六年《左傳》‘晉、鄭焉依’,《周語》作‘晉、鄭是依’ 證‘焉’ 之猶‘是’;據莊二十八年《左傳》‘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語》作‘乃可以威民而懼戎’,證‘乃’ 之猶‘則’。有舉兩文以比例者,如據《趙策》‘與秦城何如不與’ 以證《齊策》‘救趙孰與勿救’,‘孰與’ 之猶‘何如’。有因互文而知其同訓者,如據《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孟子》‘無不知愛其親者,無不知敬其兄也’,證‘也’ 之猶‘者’。有即别本以見例者,如《莊子》‘莫然有間’,《釋文》本亦作‘為間’,證‘為’ 之猶‘有’。有因古注以互推者,如據晉六年《公羊傳》何注‘焉者於也’,證《孟子》‘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 之‘焉’亦為訓‘於’;據《孟子》‘將為君子焉,將為小人焉’ 趙注‘為,有也’,據《左傳》‘何福之為’ ‘何臣之為’ ‘何國之為’ ‘何兔之為’,諸‘為’ 字皆當訓‘有’。有採後人所引以相證者,如據《莊子》引《老子》‘故貴以身於天下,則可以托天下,爰以身於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證‘於’ 猶‘為’;據颜師古引‘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引‘鄙夫不可以事君’,證《論語》‘與’ 之當訓‘以’。”①[清]錢熙祚:《經傳釋詞跋》,《經傳釋詞》,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43 頁。趙翼從事歷史的考證也採用參驗的方法,他自述撰著《廿二史劄記》的方法云:“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②[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小引》,見[清]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例如他在《宋史多國史原本》《宋史各傳回護處》《宋史各傳附會處》等條皆引用《宋史》之紀、表、傳、志之有關記載以相互參驗③[清]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二十三。。
(五) 博證 為證實某事、某義或某問題之是非正誤而搜集極為衆多的證據,以做到信而有徵。此方法為清初顧炎武所創,他研究音韻學即採用博證。他説:“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採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④[清]顧炎武:《音論》,《音學五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例如中古音之“四江”,“古通陽”,古雙切。顧炎武為證唐代開元、大曆時“江”讀為“工”,考證之文一千五百餘字,引用《楚辭》、《荀子》、《淮南子》、《白虎通》、《史記》、《易林》、《越絶書》、揚雄《蜀都賦》、黄香《九宫賦》、楊修《五湖賦》、曹植《九愁賦》、《晉書·五行志》、石崇《思婦嘆》、《山海經》、陶潛《停雲詩》、《後漢書》、張説《鄧國夫人墓銘》、柳宗元《湘沅二妃廟碑》等衆多文獻⑤[清]顧炎武:《唐韻正》卷一,《音學五書》。。郝懿行釋《爾雅》“冥,幼也”,計四百餘字,其義為:1.幼為窈之叚音,《説文》“深遠也”;《詩·關雎傳》“窈窕,幽閑也”。2.窈作窅,又通作杳,引《文選·西都賦》李善注,又《詩·斯干》釋文。3.幼、幽同聲為義,《説文》:“冥者,幽也。”4.冥、窈連文,引用《莊子·在宥》《史記·項籍傳》《文選·魏都賦》《文選·舞賦》《莊子·逍遥遊》《史記·司馬相如傳》《楚辭·湘君》。5.要眇即杳渺,意態深遠之貌。杳渺又即窈冥、冥窈,一聲之轉⑥[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上之二“釋言”,北京:中國書店,1982年。。這樣的博證是否會導致以繁瑣為病呢? 段玉裁以數十年的精力完成的《説文解字注》雖博證而似繁瑣,但盧文弨認為:“吾友金壇段若膺明府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别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年之精力專説《説文》。以鼎臣(徐鉉) 之本頗有更易,不若楚金(徐鍇) 之本為不失許氏(慎) 之舊,顧其中尚有為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第者,一一考而復之,悉有佐證,不同臆説,詳稽博辨,則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二書以繁為病,而若膺之書則不以繁為病也,何也? 一虚辭,一實證也。”①[清]盧文弨:《段若膺説文解字讀序》,《抱經堂文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432 册。《説文解字》博證而不以繁瑣有病,因其為實證,乃考辨之必要。
(六) 探原 是一種歷史研究方法,注重考察探究每一事實源流本末,而辨析其是非正誤。顧炎武的讀書筆記《日知録》採用探原竟委的方法,開啓了考據學良好風氣。《四庫全書》的編者認為“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抵牾者少”②《四庫全書日知録提要》,[清]黄汝成:《日知録集釋》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日知録》中例如“卜筮”“九族”“佔法之多”“三年之喪”“周室班爵禄”“州縣賦税”“輔郡”“漕程”等條皆是探原竟委之作。崔述的《考信録》以辨古史之偽著稱。他自述:“故今為《考信録》,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為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所注釋者悉信以為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别其事之虚實而去取之。”③[清]崔述:《考信録提要》卷上,[清]崔述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第8 頁。他的長文《古文尚書真偽源流通考》是探原竟委的集大成之作。他關於辨《古文尚書》之偽提出六證:1.孔安國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史記》《漢書》之文甚明,但於二十九篇之外,復得多十六篇,並無得此二十五篇之事。2.自東漢以後傳《古文尚書》者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諸儒,歷歷可指,皆此二十九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3.偽書所增二十五篇,較之馬、鄭舊傳三十一篇文體迥異,顯為後人所撰。4.二十九篇之文《史記》所引甚多,並無今書二十五篇之一語。5.十六篇之文《漢書·律曆志》嘗引之,與今書二十五篇不同。6.自東漢至於吴晉數百餘年,注書之儒未有一人見此二十五篇者④[清]崔述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第582—594 頁。。這以歷史考察的方法可足證《古文尚書》之偽了。
(七) 實測 自北宋以來學者們在研究金石學時已用地下所發掘的金石實物,參以文獻的二重考據方法,清代學者在天文、算學、金石、地理等的研究中還嘗試採用實地考察的方法。西方的自然科學在明代逐漸引入中國學術界,但很多學者盲目加以嘲諷與否定。淩廷堪肯定了西方實測之學的意義,他與孫星衍辯論云:
蓋西學淵微,不入其中則不知,故貴古賤今,不妨自成其學,然未有不信歲差者也。歲差自是古法,西法但以恒星東移,推明其故耳,不可以漢儒所未言遂並斥之也。再審來劄所云天文與演算法截然兩途,則似足下尚取西人之演算法者。夫西人演算法,與天文相為表裏,是則俱是,非則俱非,非若中學有佔驗推步之殊也。苟不信其地圓之説,則八綫弧三角,亦無由施其用矣。西人言天,皆得諸實測,猶之漢儒注經,本諸目驗。若棄實側而舉陳言以駁之,則去嚮壁虚造者幾希,何以關其口乎? 中西書俱在,願足下降心一尋繹之也①[清]淩廷堪:《復孫淵如觀察書》,《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80 册。。
學者們引入西方實測之方法應是清代考據學的一個重大進步。清初學者萬斯同的《崑崙河源考》因僅據古文獻所載地理情況,而未實地考察,以致得出的結論是錯誤的。李慈銘批評説:“荒外之功,聖人所不事,故荒外之地,聖人所不言。禹治水,江河致力最大,而導江僅於岷山,導河僅於積石,不欲窮徼外之原也。自《山海經》有河出崑崙一語,於是張騫鑿空,而漢武求之於蔥嶺矣。李靖遠征吐谷渾,而實以星宿川柏海矣。聖元世祖勤遠略,而都實(今作篤什) 迻之吐蕃朶幹思矣。道里不一,名號日歧,季野(萬斯同) 堅主崑崙,力申漢説,謂河必不出於星宿海,朶甘思之雪山必非崑崙。書闕難稽,事非目驗,終不得而詳也。”②[清]李慈銘:《越鏝堂讀書記》,第489 頁。黄河之源的問題,若衹憑古代文獻的記載,而不實地考察,是決不可能弄清楚的,所以萬斯同雖然博學,也不免作出錯誤的結論。古代關於三江説亦甚為紛歧,清代學者全祖望、汪中、王鳴盛、錢大昕、洪亮吉、孫星衍、段玉裁等皆主《水經注》引郭璞語,以為是岷江、松江、浙江,阮元經過實測目驗肯定此説是正確的,特著《三江考》以詳述,由此可見實測方法已為學者們所採用了。
以上清代考據學的方法在學者們的具體研究工作中根據對象而採用,亦不限於一二種方法。我們如果將這些方法加以綜合比較,則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與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歸納法相通。梁啓超論及清代考據學即以為:
清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種程式始能表現耶?第一步,必須留心觀察事物,覷出某點某點有應特别注意之價值;第二步,既注意於一事項,則凡與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係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第四步,根據此種意見,更從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證據,證據備則泐為定説,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凡今世一切科學成立,皆同此步驟,而清考據家之每立一説,亦必循此步驟也③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37 頁。。
此概括是很確切的,表明清代考據學方法與西方科學研究的歸納法的精神是一致的,但考據學的方法尤其有中國學術的特色。
四
漢代學者治經學在理解經學的意義和解釋經典的方法上存在兩派:一是經今文學派,盛行於西漢;一是經古文學派,盛行於東漢。清代考據學家們崇尚古文學派以客觀的態度治學,重視他們對經典字句的訓詁和名物制度的疏解,因而被稱為漢學;但考據學實不同於漢學,而有自己的理論與方法。學者們為認定考據學的性質而存在不同的意見,遂有關於漢學之争。清代最早提倡漢學的是乾隆初年甚有名望的盧見曾,他以為漢儒解經因其近古,故最可信:“竊謂通經當以近古者為信,譬如秦人談幽冀事,比吴越間稍稍得真。”①[清]盧見曾:《經義考序》,《雅雨堂文集》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423 册。他又説:“學《易》數十年,於唐宋元明四代之《易》,無不博綜玄覽,而求其得聖人之遺意者,惟漢為長,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猶存故也。”②[清]盧見曾:《刻李氏易傳序》,《雅雨堂文集》卷一。同時的惠棟治學深受盧氏的影響,著有《易説》六卷。他以為:“ 《六經》定於孔子,毀於秦,傳於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禮》、《公羊》猶存毛、鄭、何三家。《春秋》為杜氏(預) 所亂,《尚書》為偽孔氏(安國) 所亂,《易經》為王氏(弼) 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校同於賈(逵)、服(虔),偽孔氏則雜採馬(融)、王(朗) 之説,漢學雖亡而未盡也。惟王輔嗣(弼) 以假象説《易》,根本黄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以四子之學,上承於漢,存十一於千百,庶後之思漢學者猶之取證。”③[清]惠棟:《易漢學自序》,《松崖文鈔》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427 册。他治經專宗漢儒之義,堅持漢儒之訓詁不可改動,經師不可廢除。當時詩人袁枚即指出漢學之弊:“漢偏於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説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易》不通,《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弦矣;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者貴乎,德成者貴乎? 而況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説,顯悸聖人,箋注中尤難僂指。”④[清]袁枚:《答惠定宇書》,《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續修四庫全書》第1432 册。漢學在解經方面是很有成就的,但不可盲目遵從,有待認真檢討。嘉慶二十三年(1818) 江藩著《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敘述考據學在清代承傳的歷史,自此欲以漢學取代考據學。他認為:“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淡,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惠周惕、惠士奇、惠棟)之學盛於吴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⑤[清]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這裏以漢學為考據學,而且從治經的範圍而言,皆是片面而於義不確的,故立即遭到龔自珍的嚴厲指責。他在與江藩的書簡裏提出十條批評意見,例如:“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專”;“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瑣碎餖飣,不可謂非學,不得為漢學”;“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為漢學乎”;“若以漢與宋(學) 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①[清]龔自珍:《與江子屏箋》,《龔自珍全集》第五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這些指責切中要害,是江藩難於辯解的。桐城古文家方東樹研治義理之學,藉此撰著《漢學商兑》三卷以攻擊考據學,他説:“近世有為漢學考證者,著書以闢宋儒,攻朱子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海内名公鉅卿、高才碩學數十家遞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飛條,競欲咀嚼……如東吴惠氏(棟)、武進臧氏(琳),則為闇於是非。自是以來,漢學大盛,新編林立,聲氣扇和,專與宋儒為水火,而其人類皆以鴻名博學,為士林所重,馳騁簧舌,串穿百家,遂使數十年間,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為之大障。”②[清]方東樹:《漢學商兑序》,《考盤集文録》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97 册。方東樹指責的是古文家的習氣缺乏學理,故顯得無力,但開啓了漢學與宋學之争。淩廷堪從學術的發展變化來看待關於漢學與宋學之争,他説:“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一語遂可盡其源流,即如今所存《十三經注疏》亦不皆漢學也。蓋嘗論之,學術之在天下也,閲數百年而必變。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譁然而攻之。其既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之。夫譁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亦必有一二人矯其弊,毅然而持之。”③[清]淩廷堪:《與胡敬仲書》,《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480 册。清代考據學的遠源始於北宋由疑古思潮而興起的求真求實的學風,其近源則出自明代中期以後的實學。因此從學術史而言,清代的考據絶非出於漢學,亦絶非漢學所能體現其實質,因此將漢學以名考據學是極不恰當的。我們從漢學之争可見到當時考據學之盛,但如淩廷堪所預見,考據學在極盛之後是必然存在弊病的,故乾嘉之後義理之學——今文經學得以復興。
五
考據學在清代諸種學術中成就最大。當其在乾嘉時期成為學術主流風尚時,亦有辭章家對它批評指責,而考據學家們作了充分的辯護,由此突出考據學的意義。
(一) 關於袁枚的批評。袁枚是性靈派的詩人,看重詩文的價值,而否定考據學的意義。他曾比喻説:“考據家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現;極其所至,燎於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得者皆灰燼也。”①[清]袁枚:《答程蕺園書》,《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十,《續修四庫全書》第1432 册。他見到晚輩孫星衍之詩,嘆以為奇才,後來得知孫星衍專致於考據學,特以書簡責備説:“近日見足下之詩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歸咎於考據。蓋晝長則夜短,天且不能兼也,而況於人乎! 故敢陳其穴管。足下既不以為然,則語言而不知捨之可也,又何必費足下援儒入墨之心,必欲拉八十翁披膩颜帢、抱《左傳》逐康成車後哉! 今而後僕仍以二十年前之奇才視足下,足下亦以二十年前之知己待僕可也,如再有一字争考據者,請罰酒三升,飛遞於三千里之外,何如?”②此書簡不見袁枚文集,見存於孫星衍《問學堂集》卷四附録。孫星衍答書云:“來書惜侍以驚采絶豔之才為考據學,因言形而上謂之道,作者是也;形而下謂之器,考據是也……侍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達之學,閣下奈何分道與器為二也。來書又以聖作為考據,明述為著作,侍未以為然。古人重考據甚於重著作,又不分為二……是古人之著作即其考據,奈何閣下欲分而二之……考據之學,今人必當勝於古,而反以為列代考據如林,不必從而附益之,非通論矣。”③[清]孫星衍:《答袁簡齋前輩書》,《孫淵如先生全集·問學堂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77 册。袁枚將考據學視為形下之學,以考據為著作,在概念上並不確切,孫星衍的解説亦隨之而未將考據的意義闡述清楚,所以焦循致書以補充。他歷述考據學在清代的發展後説:“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考據混自於其間乎!……考據之稱或為此類而設,不得竊附於經學,亦不得誣經學為此,概以考據目之也。……又無端以著作歸諸抒寫性靈之空文,此不獨考據之稱有未明,即著作之名亦未深考也。袁氏之説不足辨,而考據之名不可除。”④[清]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雕菰集》卷十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489 册。焦循以為袁枚之説因概念混亂不足以辨,但他特别强調考據學是獨立之學,不是經學的附庸,而且不同於辭章之空文。
(二) 關於蔣士銓的嘲諷。著名詩人蔣士銓曾在《題焦山痤鶴銘》詩中云:“注疏流弊事考訂,鼷鼠入角成蹊徑。”此詩未見於其《忠雅堂文集》,可能因翁方綱的斥責而未收入。翁方綱記述詩人錢載與戴震在朝廷相遇,二人持議不同,但錢載不敢公開表示反對考據學,當時衹有蔣士銓作詩以諷。翁氏引述了此詩句後説:“考訂痤鶴銘特金石中一事耳,與注疏何涉? 而以考訂之為弊,歸咎於注疏,是特俗塾三家村中授蒙童者,第知有范翔《四書體注》,語以《十三經注疏》則茫然未嘗開卷者,蔣(士銓) 或即其人耶? 吾所識如諸城劉閣老墉之於金石碑板,及錢侍郎載之於詩文,皆不善於考訂,而不敢公然斥考訂為非。惟一蔣君出此言之違失若此者。蔣之詩近頗為人傳誦,此豈得阿私好而諱匿之。凡人各有所長,豈其人必考訂而後成家乎,要在平心而勿涉矜氣,考訂與不考訂皆無弊矣。”⑤[清]翁方綱:《考訂論》中之二,《復初齋文集》卷七。蔣士銓嘲諷考據家似老鼠鑽入牛角尖,翁方綱以為此不值一駁,因其如鄉村塾師見識之狹隘,學者應以自己治學所長而選擇研究對象,而考據僅是一種選擇而已。史論家章學誠不喜考據,但他説:“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冬寒,以之推代而成事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①[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内篇四,《續修四庫全書》第448 册。學者的治學對象與方法不同,應當互相尊重,以共同推動整個學術的發展。
(三) 關於王芑孫的攻擊。詩人王芑孫在《蓮花寺讀書圖記》裏斥責考據學説:“自近五百年,士用時文之術決科取名,無事讀書。比者考證之學興,學者多尊信鄭康成、許叔重,又旁獵漢人雜説,雖其不能讀書者,亦必撰述斷爛,東鈔西撮,以具攻宋儒之資,而不能無事於書矣。然其所讀書之意,則猶乎決科取名者也。”②[清]王芑孫:《惕甫未定稿》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481 册。他將考據學與時文相比,以為都是獵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且以為考據家僅是東鈔西撮並未認真讀書。這實屬不懂考據者之見解,因為時文為朝廷科舉考試之目,可以獵取功名,而考據學僅是學者一種純學術的追求,與利禄無關。翁方綱在與陳石士的書簡裏説:“昨見尊集有王芑孫紅字識語,因言義理斥考訂,遂比之邪説,此不特不知考訂,抑且不知義理。夫考訂之學何為而必欲考訂乎? 欲以明義理而已矣。其捨義理而泛言考訂者乃近名者耳,嗜異者耳。然若以其矜言博涉目為邪説,則言義理者獨無涉偏涉空者,亦得目之為邪説乎……甚有臆逞才筆者視考訂為畏途,如吾同年蔣心餘(士銓) 有詩筆者也,而亦有云‘注疏流弊事考奇’,此轉以考訂為流弊,且歸咎於讀注疏,適以自白其未嘗讀注疏而已。今見王芑孫之言,至於比考訂於邪説,則其害理傷道,視心餘為尤甚。”③[清]翁方綱:《與陳石士論考訂書》,《復初齋文集》卷十一。陳石士為王芑孫友人,他們俱是反對考據學的,翁方綱在書信中辨析邪説對考據學的攻擊,重申義理與考據的關係。王芑孫見到此書信回答説:“芑孫懵學,無所知曉。生平讀書,略取大意,頗不欲留連風月,為詞人以没世,並不欲屑屑為訓詁考訂家,言以幽窘於名物象數,斷爛無用之中。妄謂三代後士之所可就者,其事業不過如唐之姚(崇) 宋(璟)、宋之范(仲淹) 韓(琦),不幸而遇;其文章之可傳者,不過如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 苟能是亦足矣。捨此而高談,皆謂之自欺以欺人,其誤又不止於學術而已矣。”④[清]王芑孫:《答翁覃溪先生書》,《惕甫未定稿》卷八。他以為考據是無用的,更看重文章的意義,這是極其片面的看法。翁方綱似乎以為没有再辯論的必要,没有覆書了。
以上三位詩人對考據學的批評、嘲諷和攻擊,因他們並不願深入認識考據學,所指責皆無真正的學理依據,而且他們也不可能真正見到考據家的某些錯誤,僅流於門户之偏見而已。當考據學全盛之時,這些無足輕重的指責對考據學的發展並未产生什麽影響,許多考據學家亦不屑於同他們無理糾纏。
六
中國傳統學術有義理之學、經濟之學和辭章之學,自北宋以來興起的考據學經明代中期以後的發展,至清代乾嘉時期達於繁榮興盛,體現一個時代的最高學術成就和中國古代學術達到的高度水準,為傳統學術增添了一門新的學問。清代的考據由經學而嚮史學、諸子學、文字學、音韻學、天文、算數、地理、圖譜、金石等等廣泛發展,它所關注的是這些學問中的狹小的學術問題,實即中國文獻與歷史存在的狹小的學術問題,這些問題衹能用考據的方法纔可解決。考據家們崇尚的原則是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和條理精密。他們使用的方法有辯證、訓詁、校勘、參驗、博證、探原、實測,皆屬於歸納的實證的方法。因此考據學是具有獨特學術性質的,有特定對象,有理論原則,有細密的方法,在乾嘉時期已是有系統的獨立的成熟的一門學科了。如果將它僅視為一種方法,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它完全具備了作為一門學科的條件,有如西方近代的實證主義哲學一樣。
清王朝以儒家政治倫理學説為統治思想,特别大力提倡宋代的程朱理學,加强思想與文化的專制。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考據學看似是無關社會現實的無用的東西,但學者們巧妙地通過考據在動摇着儒學的理論基礎。他們證實自古相傳的三皇屬於神話傳説,並非真正的中華始祖;自唐代以來流行的儒家政治經典《古文尚書》乃出自後人的偽造;儒者堅信的古帝堯舜相傳授的統治經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它實為出自道家之語,而非出自儒家;宋儒以為《禮記》中《大學》一篇乃孔氏遺書,此論斷並無依據;理學創始人周敦頤所傳的太極圖並非出自儒家而是出自道家。他們還公開反對宋明理學的游談無根、空言義理的不良學風;他們通過辯證揭露了歷代正史的不實或歪曲的記載,還原歷史真相,尤其揭露許多帝王的殘暴行為;他們考察古代禮制與風俗,使漢族人民不忘漢民族的傳統;他們校勘、疏證、輯佚、整理中國古代典籍,以使中華文化傳統得以承傳……凡此,我們可見考據並非無用的東西,它的實證的力量是巨大而堅實的。考據家們重證求知的執著的學術精神,對真理的追求,對學術信念的堅持,最能體現中華民族優良的學風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因而他們留下的大量著作是我們民族珍貴的學術遺産,值得我們學習與承傳。
我們縱觀考據家們的治學,其中有的學者是存在某些錯誤觀念的,例如迷信漢人的注疏,不敢否定孔子删述六經之説,重視考證古音而忽視今音,不願接受聲韻的音素分析出自印度的事實,衹重視文獻的記載而忽視實地的驗證,特别注重儒家經典的箋注疏證而具拜經、詁經、韻經、抱經等觀念,把大量的精力投之於難以確考的古代禮制,許多的考證極其繁瑣而毫無學術意義,等等。這些直接影響他們成果的學術價值,留下了不少的遺憾。雖然如此,但清代考據學的主要成就仍是應予充分肯定的。梁啓超總結乾嘉考據學的意義説:
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輩嚮覺難讀難解之古籍,自此可以讀,可以解;二、許多偽書及書中竄亂荒穢者,吾輩可以知所别擇,不復虚靡精力;三、有久墜之哲學,或前人嚮不注意之學,自此得卓然成一專門學科,使吾輩學問之内容日益豐富。其間接之效果:一、諸大師之傳記及著述,見其“為學問而學問”,治一業終身以之,銖積寸累,先難後獲,無形中受一種人格的觀感,使吾輩奮興嚮學;二、用此種研究方法以治學,能使吾輩心細,讀書得間;能使吾輩忠實,不虚飾;能使吾輩獨立,不雷同;能使吾輩虚受,不敢執一自是①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29 頁。。
這是從我們承傳與接受乾嘉考據學的積極意義而言的,對我們現在治國學仍有啓發的作用。國學運動新傾嚮的代表者胡適、傅斯年和顧頡剛等非常重視乾嘉之學,以為考據家們的方法是合於西方近代的科學方法的。國學運動新傾嚮是國學運動的主流,新傾嚮的學者們直接繼承了清代的考據學並引入西方的科學方法,從而形成了科學考證方法,在治國學時取得空前的學術成就。我們若考察國學運動的歷史,顯然易見到國學運動主流與清代考據學之間的密切的内在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