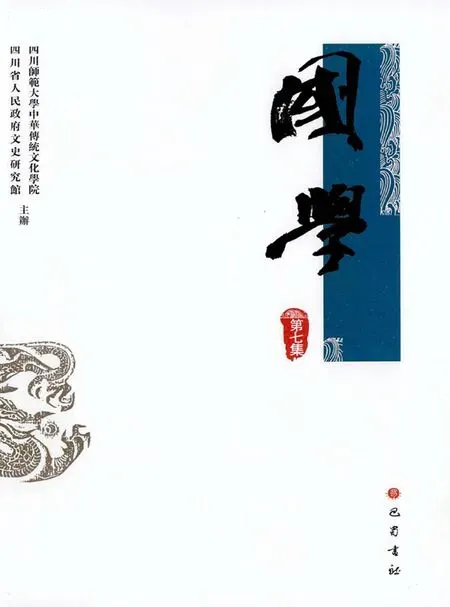堯舜神話譾論:以《山海經》為中心*
賈雯鶴
堯舜作為聖主明君的觀念在我國可謂家喻户曉,深入人心。20世紀20年代開始,“古史辨”派學者通過一系列的研究,證明這些所謂的人間帝王最初都是天神,關於他們的史實都源自神話。然而,近年來隨着“走出疑古時代”口號的提出,學者在實踐中又開始將這些被“古史辨”派學者判定為神話的資料當作歷史的資料,神話人物當作歷史人物,似乎又回到了信古的老路上去。而且,他們往往把神話資料和科學的考古資料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骨幹是科學的,外衣是神話的,更具有迷惑性。本文擬以我國最重要的神話著作《山海經》為中心,對堯舜神話作一詳細考察,或許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古史辨”派學者在古史研究中的貢獻。
一、從歷史到神話:顧頡剛關於堯舜的研究
司馬遷作《史記》,開篇就是《五帝本紀》,即以黄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和帝舜五人作為夏商周三代之前的五帝。當然,《史記》的五帝系統並不是司馬遷的發明,他依據的是《大戴禮記·五帝德》的記載。《五帝德》在五帝之外又加上了禹,實為六帝。它藉宰我提問,孔子作答,描述了六帝的種種事迹。其中關於堯舜的描述寫道: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黄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行不回,四海之内,舟輿所至,莫不説夷。”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陶家事親,寛裕温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為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厤,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闢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臯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顇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蒼梧之野。”
這些話真的是孔子説的嗎? 我們知道,古人著書,藉重名人以立説,是他們慣常的伎倆。根據《論語》的記載,孔子是知道堯舜禹的,但對黄帝、顓頊、帝嚳卻未置一言。《論語·泰伯》云:“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可見在孔子的心目中,堯舜禹是擁有天下的君王,是無可挑剔的聖主明君,故對其贊美可謂不吝其詞,推崇備至。然而除了空洞的贊美之詞外,没有任何具體的事迹。其實孔子還説過這樣的話:“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言之。”①《論語·八佾》。孔子慨嘆夏殷的文獻尚不足徵,遑論其前的堯舜了,可見這些話非孔子所能道,是不辯自明的。
有了儒家老祖宗孔子的贊美,有了史家典範司馬遷的歌頌,堯舜是上古時代聖主明君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關於其紀載則成為國人心目中的正史。
然而這種正統的上古史觀在進入現代學術時期,遭遇了極大的挑戰。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通過對上古文獻典籍的深入細緻的考察,創立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他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前記中説:
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説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説。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説明“時代愈後,傳説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裏説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黄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説明“時代愈後,傳説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衹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説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①原載《讀書雜志》(《努力周報》增刊) 第9 期,1923年5月6日;又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此據《顧頡剛全集·古史論文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81 頁。。
在信的正文,他進一步説道:“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商族認禹為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為最古的人王,可見他們對於禹的觀念,正與現在人對於盤古的觀念一樣。”“東周的初年衹有禹,是從《詩經》上可以推知的;東周的末年更有堯、舜,是從《論語》上可以看到的。”“在《論語》之後,堯、舜的事迹編造得完備了,於是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出現。有了這許多篇,於是堯與舜有翁婿的關係,舜與禹有君臣的關係了。”“從戰國到西漢,僞史充分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於是春秋初年號為最古的禹,到這時真是近之又近了。”②《顧頡剛全集·古史論文集》卷一,第182—185 頁。
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回應道:
先生所説“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意見,真是精當絶倫。舉堯、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傳説為證,我看了之後,惟有歡喜贊嘆,希望先生用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後來學子不致再被一切僞史所蒙。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衹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③原載《讀書雜志》第10 期,1923年6月10日;又載《古史辨》第一册。此據《顧頡剛全集·古史論文集》卷一,第187 頁。。
現在看來,顧頡剛關於堯舜是神非人、堯舜的事迹都是後人創造的僞史等看法不僅在當時即得到了錢玄同高度的認同,而且在當今的學術界尤其是神話學界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
1926年,顧頡剛在為《古史辨》第一册所作的《自序》中寫道:
我很想俟孟姜女故事考明之後,再着手考舜的故事。這一件故事是戰國時的最大的故事(戰國以前以禹的故事為最大,可惜材料很少,無從詳考),許多古史上的故事都以它為中心而聯結起來了。後世儒者把其中的神話部分删去,把人事部分保存,就成了極盛的唐虞之治。這件故事又是古代最有趣味的故事。……這件故事如果能研究明白,一方面必可對於故事的性質更得許多瞭解,一方面也可以對於僞古史作一個大體的整理①《顧頡剛全集·古史論文集》卷一,第61—62 頁。。
然而由於學術興趣廣泛,顧頡剛衹是在堯舜神話研究的道路上指示了門徑,在之後的時間裏並没有繼續深入下去,殊為可惜。倒是楊寬、童書業等“古史辨”派健將踵武顧先生的足迹,做出了十分精彩的研究。
二、神人之際:神話與歷史的糾紛
顧頡剛將堯舜禹從人帝的寶座上拉下來,從正史系統的典册中剔除出來,把他們打入一嚮被國人視為“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②《史記·五帝本紀》。的神話中去。不幸的是,國人對神話嚮來是不待見的。孔子的學生子貢曾經説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③《論語·公冶長》。一言以蔽之,“子不語怪、力、亂、神”④《論語·述而》。。孔子的教導對國人影響巨大,因此堯舜禹從聖主明君一下變成了虚無縹緲的神話人物,打亂了人們固有的知識譜系,在當時就引起了争論。
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第二章《禹》裏舉春秋時期秦國的銅器《秦公敦》⑤于省吾著録為“秦公”,見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203 頁。銘文“鼏宅禹”和齊國銅器《齊侯鎛鐘》⑥于省吾著録為“叔弓鎛”,見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86 頁。銘文“成唐……處禹之堵”,認為:
王國維以春秋時期的金文與略為同時的《詩經》互證,除了證明當時人“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外,實在不足以動摇顧頡剛的觀點。因此顧氏在將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收入自己所編《古史辨》第一册後,愉快地寫下了一段《附跋》,云:
頡剛案,讀此,知道春秋時秦齊二國的器銘中都説到禹,而所説的正與宋魯二國的頌詩中所舉的詞意相同。他們都看禹為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湯與后稷) 是承接着禹的。他們都不言堯舜,髣髴不知道有堯舜似的。可見春秋時人對於禹的觀念,對於古史的觀念,東自齊,西至秦,中經魯宋,大部分很是一致。我前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説:“那時(春秋) 並没有黄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衹有禹。”我很快樂,我這個假設又從王静安先生的著作裏得到了兩個有力的證據!②《顧頡剛全集·古史論文集》卷一,第331 頁。
當然,還有學者對顧頡剛的學術觀點予以全面否定,如金景芳、吕紹綱在《〈尚書·虞夏書〉 新解》中就説:
《堯典》所記堯舜禹的史迹基本上是可信的。説堯舜禹是神話人物,《堯典》是戰國秦漢人精心編造的,古代中國的歷史是層累地造成的,這一觀點我們認為是錯誤的。《堯典》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研究中國古代史捨《堯典》不用,是極大的失誤③金景芳、吕紹綱:《〈尚書·虞夏書〉 新解》,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 頁。。
金、吕二先生認為“堯舜禹的史迹基本上是可信的”,和傳統的正統史觀殊無二致,可惜他們並没有給予證明。
那麽,堯舜禹究竟是神話人物還是歷史人物,這實在是一個難以證明的問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神話與上古史中有文字記載之前的一段是重合的,神話學者和歷史學者基於各自的學術立場,得出不同的結論,勢必陷入誰也説服不了誰的境地。
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中説道:
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説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説無異,而傳説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區别。此世界各國之所同也。在中國古代已注意此事。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故於夏殷之禮曰:“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孟子於古事之可存疑者則曰“於傳有之”,於不足信者曰“好事者為之”。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取孔子所傳《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馴之百家言,於《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來皆有年數之《諜記》,其術至為謹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書》於今古文外,在漢有張霸之《百兩篇》,在魏晉有僞孔安國之書。《百兩》雖斥於漢,而僞孔書則六朝以降行用迄於今日。又汲塚所出《竹書紀年》,自夏以來皆有年數,亦《諜記》之流亞。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為五帝三王盡加年數。後人乃復取以補太史公書。此信古之過也。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僞,《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並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録,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①王國維:《古史新證》,第1—3 頁。。
王國維認為“傳説與史實混而不分”,原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不易區别”,須以“二重證據法”予以證明。王氏所論十分通達,已成為學界的共識。
因此,神話中包含有歷史,歷史中包含有神話,二者原本是密不可分的。不僅如此,神話人物和歷史人物還可以互相轉化。袁珂師將此稱為“神下地和人上天”,並且認為:中國神話的一個最突出的特徵,就是神話這條綫和歷史這條綫平行,而又往往糾纏在一起,攪混不清。神話可以轉化作歷史,即天上的諸神歷史化而為人間的聖主賢臣;歷史也可因人民世代的口耳相傳而轉化為神話,即人間的聖主賢臣神話化為天上的諸神②袁珂:《袁珂神話論集》,第154 頁。。
然而,讓人遺憾的是,拿神話作歷史的情況在學界比比皆是。因為我國的古史學者喜歡將地下的考古材料與神話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表面上看,這體現了運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方法。但實際上看,將神話記載與考古材料隨意牽附的現象屢見不鮮,導致隨處堯迹,遍地禹蹤,讓人無所適從。這不是王國維所提倡的“二重證據法”,而是神話與考古的簡單相加。
如有學者在關於炎黄二帝的研究中寫道:
一些學者把有關炎黄的文獻記載看作傳説、神話,很少有視作信史者。如果絶對地以這樣的觀點看問題,我國的歷史就會出現很長一段時間的空白。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有關炎黄的傳説都可以看作口述歷史,原本是世代口耳相傳,後來文字形成纔加以記録。世界上許多民族在使用文字以前都曾經經歷過口述歷史時期,炎黄的傳説也是如此①何崝:《炎黄新考》,收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主辦:《國學》第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 頁。。
作者以歷史會出現空白來作為神話可以視作信史的理由,實在有點勉强。而且傳説和口述歷史並不能畫等號,口述歷史其本質還是歷史,與神話傳説有着根本的區别。作者或許想表達的是炎黄的傳説在炎黄時代就已經産生,經過口耳相傳,直到被文字加以記録,因此可以算作炎黄時代的口述歷史。神話、傳説和民間故事在被文字記載之前,大都有一段口耳相傳的時期,這是没有問題的。但神話傳説再怎樣口耳相傳,終究還是神話傳説。如果前提是有關炎黄的傳説在炎黄時代就已經産生,能够多多少少反映炎黄時代的史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這個前提卻是永遠無法證實的。
其實,將神話視作歷史,並非我國學者獨有的愛好,在西方同樣是古已有之。朱狄的《原始文化研究》在論述“歷史派的神話理論”一節中説道:
古希臘哲學家歐赫麥洛斯(Euhemerus) 像寓意派一樣,認為神話的文字上的意義並不是它的真正意義,但是和寓意派不同,他認為必須把神話中的英雄看作是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英雄,把神話中的事件看作是歷史上真正發生過的事件。即使某些神話在我們看來十分費解,也僅僅是因為在神話的傳遞過程中被無意地進行了歪曲,或是因為遠古時代的人們把英雄人物奉為神明,對他的功績作了誇大的描述,因此帶有神奇的色彩。總之,在歐赫麥洛斯看來,神話不是一種秘傳的哲學(esoteric philosophy),而是一種篩選了的歷史(garbled history)。因此對神話的解釋首先要採用的是以歷史事實作為其根據,並從神話中抽引出歷史事件的核心成分。對歷史派的神話理論作完全否定和作完全肯定同樣困難,因為許多神話的確包含有真實的歷史成分,但同樣可以肯定,也有許多神話並不包含有真實的歷史成分。這兩方面都有明顯的實例可以作出説明①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第657—658 頁。。
如此看來,神話與歷史的糾紛還將持續下去。俗話説:“畫鬼容易,畫犬馬難。”如孔子的傳説,因為我們知道孔子的歷史,自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區分何為傳説,何為歷史。然而史前時期的堯舜,神話和歷史渾然一體,對它們的區分顯然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胡適在看了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以後,認為顧氏所闡發的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並説明用這個觀念來考辨古史傳説,其方法可以總括成下列公式:
(1) 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説,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 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麽樣子的傳説;
(3) 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 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
(4) 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②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第一册,第192—193 頁。。
我們認為,顧頡剛、胡適所指示的路徑仍然是研究神話的不二法門,下面我們將就堯舜的神話談談個人的看法。
三、《山海經》中的“帝”
《山海經》是我國保存神話最多的一部典籍③茅盾在《中國神話研究初探》中即説《山海經》“是一部包含神話最多的書”(茅盾:《神話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第144 頁);袁珂師在《山海經校注》的自序中亦稱《山海經》為“神話之淵府”(袁珂:《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1 頁)。,已成為大家的共識。雖然該書成書於戰國時期④賈雯鶴:《〈山海經〉 兩考》,《中華文化論壇》2006年第4 期。,時代較晚,但卻保留了較為原始的神話,或者説更多的神話原貌。因此,《山海經》關於堯舜的記載,相較於同時期其他典籍而言,可能更加接近堯舜神話産生之初的面貌。
堯舜在《山海經》中,多稱為“帝堯”和“帝舜”,這裏的“帝”是人帝還是天神呢?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看《山海經》中的“帝”。《西次三經》云: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
郭璞注:
天帝都邑之在下者也。《穆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黄帝之宫,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言增封于昆侖山之上。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云:
郭云“帝,天帝”,非也。帝者,黄帝。《竹書》《穆天子傳》〔卷二〕 云“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黄帝之宫”,《莊子〔·天地〕》云“黄帝遊于赤水之北,昆侖之丘”是也①[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 頁。。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云:
今本《穆天子傳》作“而豐□隆之葬”,闕誤不復可讀。或據《穆天子傳》“昆侖丘有黄帝之宫”,以此經所説即黄帝之下都,非也。《五臧山經》五篇内凡單言“帝”,即皆天皇五帝之神,竝無人帝之例。“帝之平圃”“帝之囿時”,經皆不謂黄帝,審矣②[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9年,第72 頁。。
《中次三經》云:“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郭璞注亦云:“天帝曲密之邑。”與此注同。我們認為郭璞以帝為天帝的理解是正確的,而畢氏以“帝”為黄帝則是,以為非天帝則非;郝氏以“帝”為天帝則是,以為非黄帝則非。黄帝在《山海經》中實為天神而非人帝,畢、郝蓋以黄帝為人帝,故云。
黄伯思《東觀餘論》卷上“論黄陵碑二女”條云:“ 《山海經》凡言‘帝’ 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 ‘帝之下都’ ‘帝之平圃’ 與‘帝之二女’ 皆謂天帝也。”③[宋]黄伯思:《東觀餘論》卷上,第六十葉。明毛氏汲古閣津逮秘書本。所言甚是。
《海外東經》云:“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夜于此野。”袁珂師《山海經校注》云:“帝,天帝。《山海經》中凡言帝,均指天帝。”①袁珂:《山海經校注》,第229 頁。
可見《山海經》中的“帝”都是指天神。“帝”既然是天神,那麽“帝某”順理成章地應該同樣是天神。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在注釋《堯典》“帝堯”時就説:
其實古代“帝”字指上帝。“帝某”總是指某一天神。……神話全書《山海經》中許多“帝某”,都是指各種天神或各種氏族神。因古代每一氏族都以為自己的族起源於一個神,所以“帝某”往往就是某氏族的宗族神。氏族部落多,這樣的帝某也就多。所以《山海經》記載了那麽多。“帝堯”已見於《山海經》中,帝舜和禹也見於此書中,但在該書的幾個顯赫的群神古帝世系中,没有帝堯,可見他地位並不高②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7 頁。。
我們認為顧、劉二氏的説法是對的。對這一問題,考古學家徐旭生也發表了看法,他説:
我們用帝顓頊、帝堯、帝嚳、帝舜、帝丹朱等名詞,固然因為古代人相沿着這樣稱呼他們,而最主要的,卻是因為當日處在原始公社時代的末期,專名前面加一“帝”字,很恰切地表明他們那半神半人的性質。帝就是神,單稱“帝”或加一字作“皇帝”,而下面不繫專名的,均指天神,並無真實的人格。如《尚書·吕刑篇》所説“皇帝請(清) 問下民”的“皇帝”,就是這樣。可是帝下帶着專名的卻是指的人神,他們雖説“神”氣十足,而人格卻並非子虚。必須兼這兩種性質來看,纔近真實③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年,第75—76 頁。。
徐氏認為“帝顓頊、帝堯、帝嚳、帝舜、帝丹朱等名詞”是古人相沿所稱。那麽這些稱呼真的就是原始公社時代末期就已經産生了嗎? 這是一個永遠難以證明的問題。如果這些稱呼遲到春秋甚至戰國時代纔産生,那麽他們還能反映多少原始公社時代末期的情況,同樣是一個無法證明的問題。徐氏又認為“帝”與“帝某”代表的是天神與人神的區别,徵之於《山海經》,難以成立。《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吴姖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上,名曰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處于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前面言“顓頊”,後面言“帝”,所指的是同一人。“重獻上天,黎邛下地”就是著名的“絶地天通”故事,而同樣的故事在《尚書·吕刑》中亦有記載,云:“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上言“上帝”,下言“皇帝”,所指的是同一人。兩相比較,《山海經》中的“顓頊”就是《吕刑》中的“上帝”,根本就没有天神與人神的分别。因此,徐氏之説難以成立。
四、《山海經》中的堯及其相關問題
《山海經》中有帝號的天神很多,關於帝堯的記載不多:
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視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久、視肉、虖交。(《海外南經》)
熟悉《山海經》體例者都知道,《海外四經》與《大荒四經》往往對同一個事件分别予以記載,因此内容大同小異。因此“岳山”,郭璞注云:“即狄山也。”
《海内北經》云:“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郭璞注:“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夷狄慕聖人恩德,輒共為築立臺觀,以標顯其遺迹也。一本云:所殺相柳,地腥臊,不可種五穀,以為衆帝之臺。”郭璞所謂一本云云,即《海外北經》所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為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衆帝之臺。在昆侖之北。”
《山海經》關於帝堯的寥寥幾條記載,幾無事迹可言,但從帝堯臺位於神話色彩濃厚的昆侖東北來看,多少透露出其天神的本色來。此外,在《山海經》中,帝堯、帝舜、帝丹朱都是獨立的神,除了他們的葬所(帝堯、帝舜) 和帝臺(帝堯、帝丹朱、帝舜) 在一地外,絲毫看不出他們還有任何關係。
後世典籍關於堯的記載中,他和羿發生了關聯。《淮南子·本經訓》云:
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
堯命羿為民除害,羿不負所望,取得了成功。堯憑藉此功勞,被萬民奉為天子。羿射十日,成功地解除了“堯之時,十日並出”的危險狀態,使自然重新恢復正常狀態。因此羿所除的民害中,自然以“十日”為最。
《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 烏焉解羽?”王逸注:“ 《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十日神話見於《山海經·海外東經》,云:
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郭璞注:
《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離騷》所謂“羿焉畢日,烏焉落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並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災,故羿禀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
可見古人對“羿射十日”的神話是十分熟悉的。然而在《論衡》一書中,“羿射十日”卻變成了“堯射十日”。對此,袁珂《山海經校注》解釋説:
郭引《淮南子》“羿射九日,日中烏盡死”云云,今本無之。而《論衡》各篇所引,尤與今本違異。《對作篇》云:“ 《淮南書》言: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十日。”《説日篇》云:“ 《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並一日出也。”《感虚篇》云:“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均以射十日者為堯而非羿。所謂“儒者傳書”,蓋亦《淮南書》也。尋繹今本《淮南子》文義,下文既云“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固《禮運》所謂“選賢與能”之意,則以射日除害事逕屬之堯似較屬之堯所使羿更近情理,或《論衡》作者所見乃真古本《淮南子》歟? 疑關於射日除害神話,初本有兩種民間傳説,一屬之堯,一屬之羿。屬之羿者更佔優勢,後人乃於古本《淮南子》“堯乃”下增“使羿”二字,以為今本狀態,於是堯射日之神話遂泯,羿射日之神話獨昌焉①袁珂:《山海經校注》,第310 頁。。
袁先生以“堯射十日”之説更為古老,而今本《淮南子》“堯乃使羿”之“使羿”二字為後人妄添,實在難以成立。且不説《論衡》成書晚於《淮南子》,其記載的可靠性並不比後者强,僅就《淮南子》本身來説,亦很難得出“使羿”二字為後人添加的結論。《淮南子·本經訓》云:“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又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本經訓》這兩段關於堯和舜的文字,明顯可以看出是對舉成文的。堯遭的是“十日並出”之害,是旱災,舜遭的是水災,故堯使羿射日,舜使禹治水,都是假手於人,無勞親自上陣。因此,《淮南子》“堯乃使羿”之“使羿”二字不可能是後人添加的。
然而在《山海經》中,使羿為民除害的不是堯,而是帝俊。《海内經》云:“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下地之百艱”可能就包括《本經訓》所説“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故郭璞注:“言射殺鑿齒、封豕之屬也。”《山海經》就記載了羿與鑿齒之戰,《海外南經》云:“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昆侖虚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前文我們已經指出,《山海經》保存的是更為古老的神話,因此帝俊命羿除害的神話可能更接近於真相。
屈原《天問》亦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夏民之“夏”,學者據王逸注,多以為指夏商之“夏”。實則“夏”與“下”通,《左傳·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公羊傳》《穀梁傳》俱作“下陽”。因此,“夏民”即“下民”,也就是“下地之民”。《詩·小雅·十月之交》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與此句式相近,亦可為證。可知“革孽夏民”就是《山海經》所謂“恤下地之百艱”。“帝降夷羿”之“帝”,王逸注:“帝,天帝也。”顯然就是《山海經》的“帝俊”。
帝俊在《山海經》中是最顯赫的天神,神迹十分豐富,為其他諸神所不及,無怪乎徐旭生感嘆道:“帝俊這個人物,在《山海經》裏面,可以説是第一煊赫的了。”②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第67 頁。然而,儘管《山海經》對帝俊的記載頗多,但衆多的記載反而讓人們對他身份的判定陷入了歧異不定之中。章太炎先生《檢論·尊史》云:“帝俊,一名也。帝俊生中容,則高陽也。帝俊生帝鴻,則少典也。帝俊生黑齒,姜姓,則神農也。帝俊妻娥皇,則虞舜也。帝俊生季釐、后稷,則高辛也。及言帝俊竹林與妃羲和、常羲者,其名實尚不可知。”③劉凌等編校:《章太炎學術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 頁。其身份的複雜亦為他神所不及。我們認為帝俊作為一位神迹豐富的天神,其神話事迹在傳播過程中,往往為其他部族所吸收。其他部族在吸收神話的同時,往往將主神改為自己的部族神。這種現象在神話傳播中是經常出現的,不足為怪。因此,《淮南子》所記載的堯使羿為民除害的神話實際上來源於《山海經》中的帝俊神話。
其他典籍關於堯的記載中,他還和丹朱發生了關聯,成了父子。《尚書·堯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僞孔傳云:“胤,國。子,爵。朱,名。”孔穎達疏云:“有胤國子爵之君,名曰朱。”不以“朱”為堯之子。然而“胤子朱啓明”一句,《史記·五帝本紀》作“嗣子丹朱開明”,張守節《正義》引鄭玄云:“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後世大都採納《史記》的意見,以“朱”即“丹朱”,為堯之子。《淮南子·泰族訓》云:“堯治天下……以為雖有法度而絑弗能統也。”高誘注云:“絑,堯子也。”陳直云:“ 《説文》:‘絑,《虞書》丹朱如此。’ 與本文同。”①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389 頁。亦稱堯子單名“絑”,與《堯典》合。
有《尚書》研究學者認為:“ ‘朱’,在神話中原是一種神鳥……又叫‘鴸’。”②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67 頁。“鴸”見於《山海經》,《南次二經》云:“《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
前文已經指出,帝堯與帝丹朱除了臺同處一地之外(《海内北經》云:“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没有其他聯繫。《海内南經》又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和帝堯更没有聯繫了。他們的父子關係似乎是在作《堯典》的時代纔確立的。至於《堯典》的作時,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把它置於《孟子》之後,《荀子》之前③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13 頁。,大概以其為戰國時的作品。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云:“由於《孟子·萬章上篇》所載四凶名字已經與現在《堯典》完全相同,它所載《帝典》中幾句話也同現在《堯典》的大致相同,就可以推斷當戰國前期,修正的《堯典》本已經同現行本相差不遠。它定型現在的樣子約在戰國後期。”④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第30 頁。裘錫圭亦認為“ 《山海經》的主要部分和《堯典》大概都是在戰國時代成書的”⑤裘錫圭:《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43 頁。。雖然《山海經》和《堯典》大致都成書於戰國時代,但從堯與丹朱的記載來看,《山海經》保存了更為原始的材料進一步得到了證明。
根據《山海經》的記載,我們知道帝堯、帝丹朱都是古代的天神,二者之間本無關係。在《堯典》中,二者已由神變為人,並成了父子。因此,“古史辨”學者認為:“ 《堯典》作者把這些來源不同混糅交錯在一起的不同時期不同行輩神話人物資料,除炎帝外,都扯到一起,成了並列於堯舜朝廷的歷史人物。”①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79 頁。但古史學者的看法卻完全相反,他們認為“ 《堯典》所載當是歷史的實録,它書所記是由史實衍生出來的神話”②金景芳、吕紹綱:《〈尚書·虞夏書〉 新解》,第72 頁。。後者顯然將神話與歷史發展的次序顛倒了,因此不能成立。
五、《山海經》中的舜及其相關問題
相較堯而言,無論是《山海經》還是其他典籍的記載,關於舜的故事都更加豐富,同時更為複雜。
學者經過研究,發現舜與《山海經》的第一天神帝俊實為一名之分化。《大荒東經》云:“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木實,使四鳥:豹、虎、熊、羆。”郭璞注:“ ‘俊’ 亦‘舜’ 字假借音也。”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云:
《初學記》九卷引《帝王世紀》云:“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疑夋即俊也,古字通用。郭云俊亦舜字,未審何據。《南荒經》云:“帝俊妻娥皇。”郭蓋本此為説。然《西荒經》又云:“帝俊生后稷。”《大戴禮·帝系篇》以后稷為帝嚳所産,是帝俊即帝嚳矣。但經内帝俊疊見,似非專指一人。此云帝俊生中容,據《左傳·文十八年》云,高陽氏才子八人,内有中容,然則此經帝俊又當為顓頊矣。經文踳駮,當在闕疑③[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第398 頁。。
袁珂《山海經校注》云:
郝説帝俊即帝嚳,是也;然謂“郭云俊亦舜字,未審何據”,則尚有説也。《大荒南經》“帝俊妻娥皇”同於舜妻娥皇,其據一也。《海内經》“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即舜子商均(《路史·後紀十一》:“女罃(女英) 生義均,義均封於商,是為商均。”説雖晚出,要當亦有所本),其據二也。《大荒北經》云:“ (衛) 丘方圓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而舜二妃亦有關於竹之神話傳説,其據三也。餘尚有數細節足證帝俊之即舜處,此不多贅。是郭所云實無可非議也①袁珂:《山海經校注》,第398 頁。。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於“舜”字下亦云:“舜者,俊之同音假借字。《山海經》作帝俊。”②[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34 頁。於“俊”字下則云:“《山海經》以俊為舜。”③同上,第366 頁。章太炎先生《文始》二云:“舜可讀如俊。”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 頁。實則俊、舜古韻並屬文部,故得通用。可知帝俊即舜。
舜與帝俊既為一名之分化,而帝俊從典籍記載來看,應該是光明神。《大荒南經》云:“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經》又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乙篇則有“帝夋乃為日月之行”的記載⑤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9 頁。。日、月既然都是帝俊的兒女,那麽帝俊是日月大神,亦即光明神,則毫無疑義了。因此,舜亦當是光明神。
明白了舜是光明神,舜的含義就好理解了。舜,我認為是取義於太陽的朝升暮落,這可從取義與此相似的一種植物“蕣”來推知。《説文·草部》:“蕣,木堇,朝華暮落者。《詩》曰:颜如蕣華。”桂馥《説文解字義證》云:“ ‘木堇朝華暮落’ 者,《廣雅》:‘日及,木槿也。’ 《玉篇》:‘槿,木槿,朝生夕隕,可食。’ 《月令》:‘仲春之月,木槿榮。’鄭云:‘木槿,王蒸也。’ 《秦策》:‘君危于累卵,而不壽于朝生。’ 高云:‘朝生,木堇也,朝榮夕落。’ 《吕氏春秋·仲夏紀》:‘木堇榮’,注云:‘木堇朝榮暮落。’”⑥[清]桂馥:《説文解字義證》,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第82 頁。蕣,今本《詩·鄭風·有女同車》則作“舜”。由此可見舜義,於太陽而言是朝升暮落,於草木而言是朝榮暮落。
舜又名重華或重明,其含義同樣與其東方太陽神格有關。重,在《邢侯作周公》中作从人从東之形,所以丁山先生認為“東、重古本一字”⑦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北京:龍門聯合書局,1961年,第51 頁。。《韓非子·説疑》“董不識”,《漢書·古今人表》則作“東不訾”,亦可證東、重古字相通。而華、明最通常的含義就是光明、光華之義,如《淮南子·地形訓》:“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注:“華猶光也。”因此,所謂重華、重明實際上就是東華、東明,也就是東方太陽神的意思。作為東方太陽神的舜,經過歷史化後,在《孟子·離婁下》中則成了“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
章太炎先生《文始》二云:“然虞舜曰重華……疑舜本蕣字。木堇朝華莫落曰蕣,《詩》言‘颜如舜華’,舜即蕣也。以華美故為衆華表。”⑧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七),第230 頁。認為重華之“華”為“花”,以與“蕣”字相符,可能並不正確。因為重華就是重明,如果重華是花,那麽重明又當作何解釋呢?
對於重華、重明,在典籍記載中,卻是另外一種解釋。《帝王世紀》云:“帝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①[晉]皇甫謐著,徐宗元輯:《帝王世紀輯存》,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40 頁。《淮南子·脩務訓》云:“舜二瞳子,是謂重明。”汪繼培《尸子輯本》卷下亦云:“昔者舜兩眸子,是謂重明。”②《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6 頁。我認為這完全是一種“語言疾病”造成的得名臆説。
茅盾先生《中國神話研究初探》云:“西洋解釋神話的一派名為文字學派者,説‘神話是語言有病的結果,猶之珍珠是蚌有病的結果’。什麽叫做‘語言有病’ 呢? 據文字學派的意見,原是古人一句平常的話語,但因口耳相傳,發音上有了一點小錯誤,後人不知真義,反而曲解,又添了一些注釋——藻飾,於是一句平常簡單的話竟變成一則故事了:這便叫做‘因了語言有病,反産生神話’。”③茅盾:《神話研究》,第162 頁。這一理論由德裔英國學者馬克斯·穆勒所提出,W·施密特《原始宗教與神話》云:“馬克斯·穆勒以為神話的起源,是由於‘語言的訛傳’ (disease of language),就是語言‘過多’ 的現象。”④(德) W·施密特著,蕭師毅、陳祥春譯:《原始宗教與神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51 頁。章太炎先生《檢論》卷五所附《正名雜義》云:“馬格斯牟拉以神話為言語之癭疣,是則然矣。”⑤劉凌等編校:《章太炎學術論著》,第137 頁。
實際上,重、童古字通用,《禮記·檀弓下》:“與其鄰重汪踦往。”鄭注:“重皆當為童。《春秋傳》曰‘童汪踦’。”《楚辭·九章·涉沙》:“固將重昏而終身”,聞一多謂重昏即童昏⑥聞一多:《九章解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 頁。。又董字,《説文·草部》作“蕫”,段注:“古童、重通用。”⑦[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第32 頁。其實,童从重省聲⑧[漢]許慎撰,[宋]徐炫校定:《説文解字》(大徐本),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58 頁。,重从東聲⑨同上,第169 頁。,三字故得通用。因此,重華、重明也可讀作童華、童明,而童、瞳為古今字,亦即眸子之義。這樣,由童華、童明就很容易敷衍出舜有“二瞳子”或“兩眸子”的傳説。
這種經過“曲解”所産生的傳説一旦固定化後,就自然對其本來含義産生了遮蔽作用。這樣,習非成是,所以《論語比考讖》就徑以“重瞳”來指稱舜了⑩[明]孫瑴:《古微書》第二十五卷,第1 頁b,見[清]錢熙祚輯:《守山閣叢書·經部》,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典籍解釋重華、重明得名的原因,是一種典型的誤讀。
此上,我們對重華、重明的原義應為東華、東明,亦即東方太陽神進行了抉發。雖然其正確含義已久不為後人所知曉,但《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的東夷人中的夫余國的始祖名叫“東明”,從他的神迹看,他應該是太陽神①蕭兵:《中國文化的精英——太陽英雄神話比較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94—113 頁。。令人驚奇的是,他竟然與東夷人的始祖神舜名遥相契合,可見重明為東方太陽神的觀念早已成為東夷人的集體無意識了,這也為我們前面的推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例證。
舜的神話中,舜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佔據着重要地位。《堯典》云:
帝曰:“咨! 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 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首次提到堯以二女妻舜,但没有出現二女的名字。《孟子·萬章上》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廪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屈原《天問》云:“舜閔在家,父何以鰥?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荀子·成相》云:“堯不德,舜不慈,妻以二女任以事。”同樣没有出現二女的名字。直到漢代劉嚮《列女傳》纔出現娥皇、女英的名字,《列女傳》卷一“有虞二妃”條云:“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
實際上,在《山海經》裏,娥皇就已經出現了,《大荒南經》云: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滎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有淵四方,四隅皆達,北屬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舜之所浴也。
娥皇雖然是帝俊之妻,但考慮到帝俊與舜的事迹重合之處甚多,且此文云三身國姚姓,與舜姓相合,下文亦云“舜之所浴”,似此處帝俊實際上就是舜。後人在傳述舜的事迹時,有意删落其不雅馴的成分,如生三身國之類即是。
《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尸子》云: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其致四方之士。堯聞其賢,〔徵之〕 草茅之中,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
又將“娥皇”一名析為“娥”與“皇”,作為二女的名字。《御覽》卷一三五引《尸子》又云:“堯妻舜以娥,媵之以皇。娥皇,衆之女英。”後一句似以娥皇為女中之英,女英一名可能就是由此衍化而來。
總之,娥皇一名見於《山海經》,來源甚古。女英一名,《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世本》作“女瑩”,《大戴禮記·帝系》作“女匽”,英、瑩、匽一聲之轉,其産生時代肯定晚於娥皇。
舜二妃之外,又有“三妃”之説。《禮記·檀弓上》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注:“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孔疏云:“云‘但三妃而已’ 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孔疏引《帝王世紀》作“癸比”,《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帝王世紀》作“登北”,即《山海經》的“登比”。《海内北經》云: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宵明、燭光又見於《淮南子》,《墬形訓》云:“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頗具神話色彩。相較娥皇、女英而言,舜妻登北氏在後來的典籍中很少被提及,或許就是因為其具有神話色彩的原因。
如同堯有不肖之子丹朱,舜亦有不肖之子商均。《孟子·萬章上》云:“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没有提及舜子之名。《國語·楚語上》云:“莊王使士亹傅大子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 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 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首次言及舜的不肖子名叫商均。
《山海經·大荒南經》云: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貝、離俞、久、鷹賈、委維、熊、羆、象、虎、豹、狼、視肉。
郭璞注:“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今在九疑之中。”王念孫《山海經》手校云:“ 《〔大荒〕 西經》云:‘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 則叔均非商均也。《海内經》云:‘稷之孫曰叔均。’”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云:“ 《海内南經》既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此又云‘舜與叔均之所葬’,將朱、均二人皆於此焉堋邪? 又郭云‘叔均,商均’,蓋以為舜之子也。然舜子名義鈞,封於商,見《竹書紀年》,不名叔均。而《大荒西經》有叔均,為稷弟台璽之子;《海内經》又有叔均,為稷之孫,準斯以言,此經叔均,蓋未審為何人也。”袁珂《山海經校注》云:“是王、郝俱不以郭注叔均即商均為然。然此叔均,實是商均,叔、商一聲之轉。能與舜同葬,非舜子商均不足當之。舜與商均同葬蒼梧,並無礙於《海内南經》所云‘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之不同傳説之流播。郝云‘將朱、均二人皆於此焉堋’,未免失之拘矣。至叔均又謂是稷弟台璽之子或謂是稷之孫者,尤見神話傳説之錯綜紛歧無定,是書非出自一手,蓋各記其所傳聞,不足異也。”①袁珂:《山海經校注》,第420—421 頁。
《山海經》還記載了兩個舜的後裔國: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戲,戲生摇民。(《大荒東經》)
有臷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百穀所聚。(《大荒南經》)
從描寫兩國的文字來看,具有一定的神話色彩,所以後來關於舜的故事中,與這兩國有關的内容再也没有出現。這或許是帝舜人君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儒家學者對這些怪力亂神的不經之談有意加以刊落的結果。
六、結 語
通過上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古史辨”派學者關於堯舜研究的結論是正確的、可信的。“古史辨”派學者對古史傳説的研究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示範意義,他們所提倡的研究方法是科學的。
最後,我們以常玉芝《讀顧頡剛〈黄帝〉 文談商周之“帝”》中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
“古史辨”派學者論證“三皇”“五帝”不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是由神話傳説演變來的,這是科學地研究歷史的態度,是對古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貢獻。但近二十年來,有學者卻極力抬高《五帝本紀》的歷史價值,認定五帝(甚至三皇) 都是實有的歷史人物,其提出的理由竟然是因為“各種古書都記有基本相合的傳説”①李學勤:《古史、考古學與炎黄二帝》,收入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8、44 頁。(原注),注意,這裏他也説五帝是“傳説”,既然是“傳説”,為何不加考證就認定其必是真實的信史呢? 顧頡剛先生説:“學術是非,不在乎異同而在真僞。”②見俞國林編:《顧頡剛舊藏簽名本圖録·編纂説明》,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 頁。(原注)是至理名言。崇信五帝為真實歷史人物者還告誡人們,不要懷疑古書的記載,號召大家“走出疑古時代”。這種對古書記載不加甄别、考證,盲目相信的做法,絶不是科學地研究歷史的態度③常玉芝:《讀顧頡剛〈黄帝〉 文談商周之“帝”》,載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6—37 頁。。
可見學界對時下過於盲目信古的傾嚮還是有嚴厲的批評。雖然批評的聲音還很微弱,但應該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