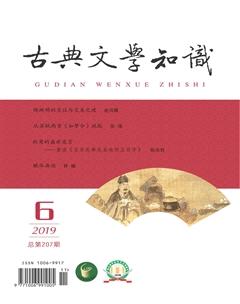物象离合
张波
《十离诗》是薛涛诗作中饱受争议的作品。谭正璧先生《中国女性文学史》认为此诗系于薛涛名下,是其蒙受的千载不白之冤,“以后如有人重编薛涛诗,当删去《十离诗》,以替她雪冤,才能有以对我们这位孤芳清拔的女诗人”(见刘天文《近百年薛涛研究述评》,《天府新论》2004年第3期)。可见《十离诗》中颇有些句子格调卑下,与历来对薛涛诗风的定评不符。笔者也觉得在诸多版本中尤以《犬离主》“毛香足净主人怜”一句难以卒读,确实不愿意承认这是薛涛所作。然而上世纪唐诗选本《又玄集》在日本的发现,使得人们不得不承认《十离诗》确实是薛涛的作品,所幸集中所载此诗此句为“为知人意得人怜”,读之似觉赧颜稍解。这之后愿意仔细去读《十离诗》的人多了起来,于是有人说这是落入社会底层的女性微弱的抗争,这是对两性不平等的残酷现实的呐喊,等等不一,试图为女诗人寻找回合理的尊严。
薛涛诗不作雌声,有格调,历来有定评。晚唐《诗人主客图》将薛涛列为“清奇雅正”之属。宋代《宣和书谱》称薛涛“诗思俊逸,有林下风致”。明代《唐音癸签》有“工绝句,无雌声”之评,《唐诗镜》称涛诗“气色清老”。明人稱其“士女行中独步”(杨慎《绿窗女史》),清人则云“非寻常裙屐所及”(《四库全书总目》)。从《又玄集》的选诗标准“清词丽句”来看,于薛涛诗仅选两首,《犬离主》占其一,说明选者认为此诗可以窥见薛涛诗风之一斑。那么,这位非同一般女流、历事十一镇节度使皆以诗受知的薛涛,在她所创作的颇为特别的《十离诗》中,究竟呈现了怎样的风貌?
《十离诗》的创作背景,历来有两种说法。据万历三十七年洗墨池刻本《薛涛诗》此题下记云:“元微之使蜀,严司空遣涛往侍,后因事获怨,远之。涛作《十离诗》以献,遂复善焉。”此说最早出自《唐摭言》:“元相公在浙东时,宾府有薛书记,饮酒醉后因争令掷注子击伤相公犹子,遂出幕。醒来乃作《十离诗》上献府主。”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选此诗即题作“十离诗上浙东元相公”,署名“薛书记”。而此中之薛书记显然不是薛涛。另一说法即《十离诗》是写给西川节度使韦皋,最早见载于后蜀何光远《鉴诫录》,但按其所言,薛涛所献为《五离诗》。而《五离诗》实则《十离诗》中的犬、鱼、鹦鹉、竹、珠五题。两说互有抵牾,因此《诗话总龟》《事文类聚》等书辑录时皆两存之。明代万历年间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综合两说,认为薛涛“初为连帅所喜,因事获罪,怒而远之,作《十离诗》以献”。
在最早选录此诗的《又玄集》中,《犬离主》前一诗题作“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今学者一般将《十离诗》与之一起讨论,认为作于同时。因《十离诗》中有两处提到“四五年”(“出入朱门四五年”、“戏跃莲池四五秋”),学者由此推断薛涛在韦皋幕中四、五年时获罪被罚。被罚时间,朱德慈先生《薛涛生年再考》认为“至多在贞元十三年(797)”,因贞元十二年(796)韦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能称“韦相公”。刘天文先生《薛涛生年考辨》则认为被罚时间在贞元十六年(800),因贞元十二年至贞元十七年(801)韦皋加中书令应称“韦令公”之前,恰是五年时间,符合诗中自述。不过以诗集版本而言,“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之题虽在《又玄集》《成都文类》《唐诗纪事》《唐诗镜》《诗女史》《艳异编》皆同,而《万首唐人绝句》题作“陈情上韦令公”,万历本《薛涛诗》题作“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这样看来,由诗题所涉称谓“韦相公”推测的时间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
一个显见的问题是,并无文献证据指明薛涛“因事获罪”导致“罚赴边有怀”,因此《十离诗》作于罚边期间只是一种推断。薛涛被罚赴边的原因,张篷舟先生据《鉴诫录》所载认为薛涛因颇得韦皋宠念,使车至蜀,每先赂涛,涛亦不顾嫌疑,是以获罪。而据《鉴诫录》载薛涛因献诗“情意感人,遂复宠召”。说明《十离诗》打动了韦皋,起到了实际的作用。那么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献诗促成了薛涛从边地被释回。
韦皋镇蜀长达二十一年,因抵抗吐蕃屡有边功。观《旧唐书》所载韦皋对边地历次用兵,薛涛献《十离诗》可能在贞元十七年(801)。此年韦皋对吐蕃全面用兵,多路兵马深入蕃界,其中有“都将高倜、王英俊兵二千趋故松州”,又有“雅州经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趋吐蕃租、松等城”,与薛涛罚边诗所述“烽烟直北愁”、“不敢向松州”地理方向一致。无论薛涛是因与闻幕府机要获罪,还是因某些史料所称的“营妓”身份,本就需要随军酬唱,只有跟随胜利之军才有可能再次回到成都。而此年的战事“自八月出军齐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万”、“转战千里,蕃军连败”。也正是这一年,韦皋以功加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薛涛在此时献诗陈情,才有可能使韦相公或韦令公的称呼皆具有流传的合理性。
薛涛很可能是在边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受到真实磨难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创作了《十离诗》。因此这一组诗既具有种种直白、显露的物象与结构,而细味其内在,又似乎有某种层次和逻辑。明代钟惺《名媛诗归》对这组作品有颇为中肯的评价:“《十离诗》有引躬自责者,有归咎他人者,有拟议情好者,有直陈过端者,有微寄讽刺者,皆情到至处,一往而就,非才人女人不能。盖女人善想,才人善达故也。此《长门赋》所以授情于洛阳年少也。”善想与善达确实是《十离诗》最令人称奇的特点。善想表现在诗中采用了物象纷呈的喻体传递作者心绪,善达则说明诗作达成了改变命运处境的效果。而要想解读作者如何想、如何达,我们需要将十首诗中包含的物象进行分拆重组。
《十离诗》的诗题结构是“某离某”,前者自喻,后者比喻韦皋,这似乎没有疑问,然而,诗作中运用了多种物象去比喻薛涛与韦皋之间关系,通过对这种关系的描述,传达作者的苦心孤诣。既往论者有认定《十离诗》“殊乏雅道,不足取也”(《历朝名媛诗词》),这种判断或许是基于十首诗对人的物化和矮化,但其实却忽视了物象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作者表述情感复杂性的重要手段。
《十离诗》的诗题中主语所包含的物象按照基本属性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动物,共有六题:犬离主、鹦鹉离笼、鱼离池、马离厩、燕离巢、鹰离鞲。其中,前三种是家中驯养之物,离开主人提供的环境无法生存;后三种虽亦从属主人,但是与外界有联系,离开主人提供的环境并不会有生命危险。对比这两类动物,实际上有格调高下的区别。作者究竟是乞怜犬、笼中鸟、池中物,还是追风马、筑巢燕、利爪鹰?这取决于不同的视角,也许以附庸关系来看,薛涛及笄不久,被节度使召入幕府侍宴,作为娱宾之妓,其身份是可悲的,但是后一组物象又体现了倾诉者内心对自己的定位和认同,她不是池中之物,而是有能力安身立命或远走高飞的不凡之物。
第二类是物品,共有三题:笔离手、珠离掌、镜离台。这组物象同样可以对照来看,在通常视角下,女性以色侍人,承欢受宠也不过“皎洁圆明内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宫”(《珠离掌》),被主人捧在手心。然而薛涛不同,史载她八九岁知声律,生平经历十一任西川节度使,皆以诗受知,“言谑之间,立有酬对”(《鉴诫录》),在蜀中有“女校书”的称号。此校书之称,或传韦皋曾欲奏请,或传武元衡镇蜀时奏授。然在唐代,校书郎是唐代士人中进士后出仕的最优职位,恐难授予女性,故宋人陈振孙说“恐无是理”(《直斋书录解题》)。但在蜀中“女校书”称呼的流传已经足以说明薛涛不让须眉的文才。从这个视角看《笔离手》中“越管宣毫”、“羲之手里”,所用之笔为何等身价,笔下所写为何等文字,便不难理解这是作者心中的自我。《镜离台》一首为全篇收束,这其实暗含夫妻的隐喻,由此上升到薛涛对此次被罚赴边的深刻领悟,其结局是“无限蒙尘”,不得再出入“华堂”“玉台”,意味着她和韦皋恩爱关系的结束。
第三类是植物,只有一题:竹离亭。如果说薛涛将自己的身世、经历和处境进行了物化的比喻,以三个层次分别对应三类关系的认知:对主从关系的认知、对夫妻关系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认知。那么在前两个层面都有外界和内在两个层面的对比,第三类则没有对比,只有自况。“常将劲節负秋霜”的竹就是薛涛的自况。现存薛涛诗集中还有一首《酬人雨后玩竹》,也特别写道“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不刻意彰显而是虚心涵养,直到万物凋零的晚岁方见竹之高标劲节。薛涛以竹自喻,被释后隐居浣花溪,得享终老岁月,其人生命运也映衬了其自喻、自况实乃真实心迹。
宾语位置的物象是韦皋的象征,这种象征性也可以通过归类看出层次关系。第一层级的三个诗题是:犬离主、笔离手、珠离掌。这三个诗题中处于宾语位置的是主、手、掌,象征着人对物的控制。第二层级的三个诗题是:马离厩、鹦鹉离笼、鹰离鞲。处于宾语位置的是厩、笼、鞲,分别是为马、鹦鹉、鹰量身打造的所在,象征着三者与主人之间特殊的依附关系。称霸一方的节度使韦皋,治下的一切人和物都依附于他,这是最本质的现实。《旧唐书·韦皋传》载“其从事累官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史,又或署在府幕,多不令还朝”。正反映了中唐士人的普遍境遇,选择到幕府就职,最现实的出路就是终身依赖幕主,仰仗幕主的提拔。另一方面,厩、笼、鞲也有束缚、羁绊的隐喻,因此这一层级的“离”也带有主语脱离束缚的指向。
第三层级的三个诗题是:燕离巢、鱼离池、镜离台。宾语巢、池、台都含有家园的象征,它们作为地点的深层含义是主语的归宿。而燕、鱼、镜在诗歌意象中经常指代夫妻关系,所以这一层级的“离”具有男女双方分离的意味,从情感层面上说又带有留恋不舍的意蕴。而位于最高一个层级的诗题仍是竹离亭。这首诗在最深层含义上暗示主宾分离的命运。细味《竹离亭》的主宾关系,竹生长于玉堂亭榭内自有一种风姿,然而玉堂并非竹的生长所必须依赖,二者之间本是互为映衬、相得益彰。竹子不在亭台之中润色风景,尚能在山林之中“虚心自持”得一隐逸名号,而因“春笋钻墙破”而不使竹再“垂阴覆玉堂”的亭台主人,失去了郁郁葱葱的茂竹,也即失去了眼前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
《十离诗》的诗句结构也具有某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每首诗的前两句都是在写物象的本来面貌或者承宠时的景象,后两句都是突然逆转的悲剧或曰失宠后的落魄。然而仔细分析,每首诗都在第三句揭示了“离”的内在原因,按诗句结构的相似性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的原因是“无端”的,“失宠”仿佛突然降临:
无端咬着亲情客(犬离主)
无端摆断芙蓉朵(鱼离池)
无端窜向青云外(鹰离鞲)
诗人借喻体在活动中无意识的错误来暗示命运急转直下的不可预测性,这或许是作者对“罚赴边”最直观、最本质的体验。在《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中作者称“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这种对苦难的直接体验触目惊心,迫使作者开始思索缘由。其中四首诗的“缘由”最多只能算是主客观都难以避免的微小过失:
都缘出语无方便(鹦鹉离笼)
都缘一点瑕相秽(珠离掌)
都缘用久锋头尽(笔离手)
为缘春笋钻墙破(竹离亭)
这些被作者思考出的原因仍可对照来看。主观层面,可能作者确实做错了一些事,类似前两题中鹦鹉说错话、珠宝有瑕疵这样的过失。客观层面,幕主厌旧的心性和强势的作风也造成了作者的“被弃”。
另外三首诗则在第三句揭示出明确的、较为显眼的过失:
为惊玉貌郎君坠(马离厩)
衔泥秽污珊瑚枕(燕离巢)
为遭无限尘蒙蔽(镜离台)
薛涛究竟为何被罚,史料语焉不详,似乎无法达成共识。根据离薛涛时代较近的笔记《鉴诫录》所载,薛涛“每承连帅宠念,或相唱和,出入车舆,诗达四方”。又说涛性“狂逸”,虽“遗金帛往往上纳”,而韦皋“既知且怒”。于是今学者多有推测,被罚原因应该是薛涛交接四方又无所避嫌,使得韦皋心怀不满。从“玉貌郎君坠”、“秽污珊瑚枕”的诗文来看,可能薛涛确实做了令韦皋觉得不妥的事情,不一定是金帛的收受,也可能是诗名太盛,与士子交接导致幕主不悦,使薛涛最终遭尘所蒙,镜与台分,与韦皋的关系终于破裂。
《十离诗》每一首诗的第四句都是以“不得”开头。无论何种层次的比喻,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得”。这十个“不得”,既像韦皋对薛涛的严加申斥,令其再不得如此,又像是薛涛无奈和无声的咏叹,悲己再不得如何。而十个“不得”的背后又蕴含着某种“欲得”的希望,即薛涛希望以这样的十篇诗作上达韦皋,改变自己深居边地的处境。
《十离诗》通俗流丽的语言、诗题结构的相似和诗句构造的相通,很容易使人想到乐府民歌。已有学者指出《十离诗》与隋朝丁六娘《十索曲》具有可比性(李涛:《〈十离诗〉: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性的十声叹息》)。后者为五言六句,皆以“从郎索某某”的语句结构结尾。索者为衣带、花烛、红粉、指环、锦帐、花枕之类女性意味明显的物品。其实,《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本有“古别离”之体,解题云:“楚辞曰:‘悲莫悲兮生别离。古诗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后苏武使匈奴,李陵与曰:‘良时不可再,离别在须臾。故后人拟之为‘古别离。文帝又为‘生别离,宋吴迈远有‘长别离,唐李白有‘远别离,亦皆类此。”而属于此体之下的作品有古别离(古离别)、生别离、长别离、远别离、久别离、新别离、今别离、暗别离、潜别离、别离曲,亦合“十离”之数。
薛涛《十离诗》作为个人创作的组诗,其艺术成就自不会囿于对民歌风调的继承,但由此视角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十离诗》的“诗眼”:离。乐府诗的创作者们所发挥的“别离”之体,意在申发人生中各不相同的分离境遇及感受。而薛涛诗的“十离”还有遭受、背离等意义,可以说这组诗既象征着她遭受的苦难,又体现了她对造成这一现状的反思,再以多重的组合物象层层渲染铺垫,将“离”的不同含义表达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此外,离亦是一个象征着火的卦象。朱熹《周易本义》曰:“离,丽也。阴丽于阳,其象为火,体阴而用阳也。物之所丽,贵乎得正。”由离假借丽而引申出的美丽、偶对、附着之意象征着薛涛侍宴承欢的过往经历,而此卦所隐含的“吉”象则需要通过涵养德性来实现,是为“贵乎得正”。如果说薛涛真的以《十离诗》改变了自己的不利处境,由被罚之地释还后“虚心自持”,获得了“晚岁君能赏”的安稳,或许也称得上命运的一种眷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