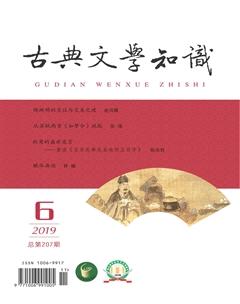言虽不经,义归于正
刘运好
陆士龙文集有“嘲”——《嘲褚常侍》《牛责季友文》两篇,乃西晉散文中的奇文。所谓“嘲”者,虽汉代有之,然体无所归,漫谓之“杂”。就其本质,近乎俳谐。“辞虽倾迥,意归义正”(《文心雕龙·谐隐》),用笔幽默诙谐,然讽喻弊政,讥讽时世,意在匡正世风,故言虽不经,却义归于正。陆云杂体,刻画了两位落魄文人的形象,笔墨近乎游戏,口吻诙谐调侃。名之为“嘲”为“责”,实乃为褒为奖。同情之心,油然生于言外;抑扬之中,辞锋直刺现实,藉此而阐释深刻道理,虽杂以嘲戏,而寓庄于谐,颇类后代之杂文。然而,学界将其弃之不顾,令人扼腕叹息。
《嘲褚常侍》以诙谐的笔墨,调侃的语调,勾画了褚常侍形象——怀才不遇,安贫乐道,却最终在君子的语言暴力下,不得不随俗浮沉。文章开篇即曰:“前临川府褚老常侍,君子谓吴如是乎能官人。”不作铺垫,峭然而起,树立了一位善于御民的官吏形象。用“如是乎”的君子惊诧语气,更突显其无与伦比的官人之才。然后按下其人不表,却专论御民之意义:
官人,国之所废兴也。古之兴王,唯贤是与。吕望渔钓,而周王枉驾。宁戚叩角,而齐王忘寐。委斯徒而靡好爵,释短褐而服龙章。姬姜之族,非无人也;亲昵之爱,非无怀也。取彼庸贱之徒,登之佐臣之列。故九贤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时,匡霸以济。夫唯能官人之所由也。
国之兴废,在于择官,故盛世之君,唯举贤才。吕望渔钓渭水,遇文王而得举;宁戚叩角而歌,遭桓公而为用。唯因贤才是举,上古有九贤治世,天命归之;齐桓有五子辅佐,终成霸业。作者还特别指出,周用吕望、齐用宁戚,并非族无贤才,国无昵亲,之所以用此地位卑贱之人,唯在御民以兴国。如若从国家的用人之道和人物的旷世之才两个方面推想,褚常侍必然际会风云,腾霄飞举。然而,现实却大跌眼镜:
褚氏,大夫之常佐,远邦之贱司。才则邵矣,官实陋矣。而拔出群萃,超升阶闼。虽文王登师,桓公取佐,亦何以加之?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官人得才也。褚常侍闻之喜曰:“君子之言,岂虚也哉?吾得此足矣。”君子谓褚常侍于是乎不谦。谦也者,致敬以存其位者也。谦之不存,德无柄矣。
现实中的褚常侍却沉沦下僚,才美官微。本是出类拔萃,超乎廷僚,有吕望、宁戚官人之大才,却无吕望、宁戚之际遇。然而,当他闻之官人得才、文王以宁之诗时,喜之不禁,心满意足,一是君子之言肯定了他的官人之才,窃喜;二是君子之言暗示了他的未来前程,期待。然而,这一点虚幻的心理安慰,也被现实打得粉碎——君子指责其毫不谦逊、不敬其位、道德无本。然后,文章又正襟危坐地进一步阐治乱之道,以及君子对褚常侍的严厉批评:
世之治也,君子自以为不足,故撙节以求役于礼,敬让以求安于仁。世之乱也,在位者自以为有余,故爵丰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复广。世之治乱,恒由此作。今褚侯蝉蜕槁木,鹄鸣玉堂,不庶几夙夜允集众誉,而意充于一善,心盈于自足。足则无求,盈则无戒。不求则善远之,无戒则恶来之,亦何以为君子哉?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慎之至也。
将官人者的道德与谦逊上升到国家治乱的高度,指出:治世,君子自谦道德不足,故遵循法度而规范于礼,恭敬谦让而安心于仁;乱世,在位者以为道德有余,故位高禄丰却贪欲不止。而褚常侍虽然翱翔华堂,却栖身枯木,安于现状,不求众誉,意满于一己之善,心足于既得之位。为此,又遭到君子无端指责:心足则无所追求,意满则缺少警戒,其结果是“善远之”“恶来之”,何能成为君子?诗之所云,君子必须至慎啊。按照文章本来的逻辑思路,褚常侍安于位、养其德、敛心自谦,正合乎国家治乱之道,然而却又出人意外地遭到君子的指责。如此现实,对褚常侍来说,欲进无路,欲退不能,真正进入进退维谷的人生窘境。可是文章的结尾却大出人所料:
褚常侍闻是言也惧,谓之昌言也而拜之。君子曰:“褚侯其几矣。闻善而喜,过又应之惧。嘉服义之贤,而拜谠言之辱。规同禹迹,义均罪己。君子哉!吴无君子,斯焉取斯!”
本是持守自我的褚常侍反而以无端指责为良言,终于“幡然醒悟”,这本是一幕丧失了自我的人生悲剧;可是,君子以为褚常侍能拜受直言之辱,如禹汤之能罪己,赞誉其是真正的君子,文章以含泪的喜剧收场。本来,褚常侍心如槁木,超越荣辱,意止于善,超越得失,结果却在君子的指责下,不得不走向与君子随俗浮沉的人生。褚常侍人生“被塑造”的过程,恰恰是一个人性“被异化”的过程。然而,人性异化后的褚常侍,却被君子赞叹“吴无君子,斯焉取斯”而推崇备至。这就深刻揭示所谓君子社会是怎样的颠倒是非,人性本真又是如何的被社会异化!
全文以褚常侍窘迫人生为切入点,深入论述举贤兴国之理,世道治乱之由,从具体人物的境遇抽象出普遍的治国用人之理;以褚常侍人生观的转变为收束,揭示了君子文化的虚伪及其对人性的异化。语言幽默,词锋通脱,而意蕴精警。文章虽短,却跌宕回环,出人意表。以正笔入题,以反承破题,再以调侃转折,以“喜剧”合题。运用两种不同的对比方法:第一,显性对比。褚常侍“如是乎能官人”与“大夫之常佐,远邦之贱司”才美官卑对比,揭示其有吕望、宁戚之才而无君识遇合的落魄;褚常侍栖身槁木,安贫乐道,与爵丰而求厚、位隆而欲广者对比,揭示其不遇于时、不得其君的窘迫。用笔似贬,实是褒之;明写人物,暗讽现实;诙谐幽默,义归于正。第二,隐性对比。褚常侍不“允集众誉”,“意充于一善,心盈于自足”与君子“不求”“无戒”的无端指责对比,揭示了挂着正人君子徽号背后的丑恶嘴脸;褚常侍闻“官人得才”“吾得此足矣”之喜与闻“不求”“无戒”却“谓之昌言也而拜之”的恐惧心态对比,揭示所谓君子文化对人性异化的巨大影响。笔触深入社会本质和君子文化的劣根性,在调笑抑扬、漫画夸张的灰色幽默中,浸透着冷峻的现实沉思。
《牛责季友文》与《嘲褚常侍》皆正言反说,意在讥刺,然立意用笔,却有不同。前文讽刺对象明确,后文讽刺对象隐晦。前文以说理为核心,亦正亦反;后文以人物为核心,反语正说。从表层看,主旨是劝其离隐仕进;从深层看,讽刺乃在其怀才不遇的现实。开篇以常理切入:“天造草昧,万物化淳。类族殊品,莫尚乎人。”虽自然造化万物,物有殊品,各以类聚,然人为万物之灵。突出人在宇宙造化中的特殊地位,乃为后文写人铺垫。然后即以夸饰之笔,描述季友之才异于常人,却高蹈山林,故切言劝之:
今子履方象以矩地,戴圆规以仪天。該芳灵之凝素,挺协气于皓玄。故神穷来契,思洞无闲。踊翰则愤凌洪波,吐辞则辨解连环。子何不绝渊而跃,照日之光,使颖秀旸谷,景溢扶桑。俯经见龙之辉,仰集天人之堂。
季友戴天履地,道法自然,钟天地之灵秀,得自然之和气,才思敏捷,洞悉幽微,挥笔则情如波涌,吐辞又妙语连珠。然而,如此俊彦,却韬光养晦,遁世隐居。故作者带着急促的语气劝之:子何不如龙跃于渊,日光之升,离隐出潜,辉耀天人!后文又以调侃笔调描述季友弃世遁隐的窘迫现状:
维子之服,既玄而素。今子之滞,年时云暮,而冕不易物,车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珥,华蝉右顾;令朝服青轩,夕驾轺辂;望紫微而风行,践兰途而安步?而崎岖陇坂,息驾郊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疾?何子崇道与德,而遗贵与富之甚哉!
他人纡青拖紫,子着隐士之服,沉沦落魄,岁月蹉跎,冠冕不改,车服依旧。何不戴玄貂、饰华蝉,乘华美之车,安步于芬芳之途,风驰于天子之宫!反而奔走于崎岖山路,息驾于郊外荒郊,乘病牛而含悲?何必推崇道德、敝屐富贵,如此之甚呢!所以,作者又以叹息的语调劝之曰:
日月逝矣,岁聿其暮。嗟呼季友,盛时可惜。迨良期于风柔,竞悲飚于叶落。陈谠言于洪范,图遗形于霄阁。使景绝而音流芬,身荐而荣赫奕。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时,予请迹于桃林之薄。
嗟乎,日月流逝,盛年难在,须趁青春年华,不必老大伤悲;为朝廷大法献言献策,在凌烟阁上图其遗像,即使身亡影绝,亦可青史留芳。最后,以决绝的语言告之曰:如若不及建功立业,就请你遁迹荒僻山林——不要在人世间晃眼啊。表面上,作者似乎是正说,批评其身怀奇才而不用于世,所以劝其离隐仕进。深层里,却名为责难,实为褒扬。其“何子崇道与德,而遗贵与富之甚哉”句,说明不仅季友才秀,而且德厚,所以弃世高蹈,处境落拓,实在有难以言说的现实原因,只是个中原因,留余言外而已。同样,两处“何不”的责难,亦是表面指责季友,深层批判现实。“纵我不往,子宁不来?”野有遗贤,或因贤才者乱邦不入,或为治政者昏聩不察。如果联系作者当时入洛仕晋的艰难处境,即可推想其中也蕴涵着作者理想之失落。此外,作者也借批评季友的口吻,间接描述了达官贵族生活的奢华、权势的追逐和气焰的煊赫,唯将批判的锋芒隐蔽到巧妙的叙述背后而已。从结构上看,文章虽短,却反复渲染,有扬有抑,结尾之调侃,更留有不尽之余味。表面上责季友潜隐不仕,而深层里痛惜其不遇于时。在杂以嘲戏之中,鼓荡着勃郁不平之气。
从文体意义上,士龙二文颇类俳谐。俳谐之体渊源久长,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为先导,汉代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踵其武,至魏晋则大放异彩。《文心雕龙·谐隐》曰:“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发嘲调,虽抃推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晳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其俳谐之文即有三国麋元《吊夷齐文》,西晋潘岳《丑妇》、束晳《饼赋》等等,然皆“辞浅会俗”,虽可以娱心,终止于“悦笑”而已,“曾是莠言,有亏德音”,缺少警动人心的意义。士龙之文皆以具体人物的怀才不遇为描写对象,而后上升到治政举贤之理,名为“嘲”人“责”人,实是“嘲”世“责”世。虽也调笑抑扬,涉笔成趣,但语带讥讽,警世醒心。特别是《嘲褚常侍》一文,在翻转腾挪中,浸透彻骨的悲凉,调笑之中浸透着眼泪,别有精警动心之处。
简要言之,陆云杂体,辞锋通脱,庄谐随体,涉笔成趣,舒卷自如,“文藻丽密,词旨深雅”,最见其性情的丰富与复杂,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亳州学院中文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