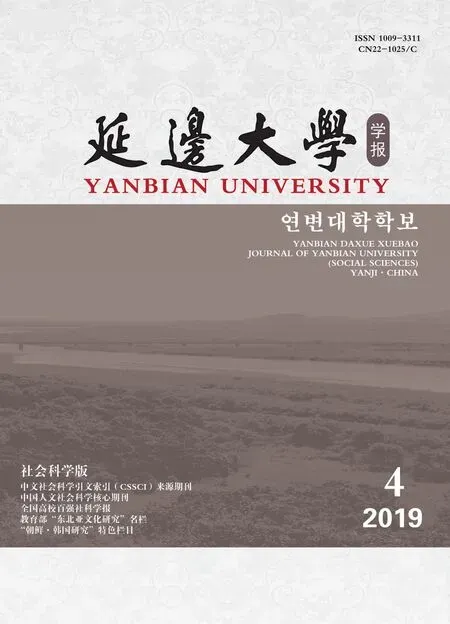论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的扬州形象
安桂颍 马金科
崔致远出身于一个奉儒之家,12岁远离故土入唐求学,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及第,881年任淮南节度使,28岁时担任国信使一职并荣归故国新罗。在韩国现存历史最悠久、内容最完备的汉文典籍中,《桂苑笔耕集》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并被尊为“东方文章之本初”和“东方艺苑之始祖”。对于《桂苑笔耕集》这部著作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在版本考证、史料价值等方面,[注]《桂苑笔耕集》目前主要代表性研究有:贾云的《宾贡进士崔致远和他的〈桂苑笔耕集〉》(1997);阎李明的《崔致远与九世纪后半期的唐罗关系》(2006);朴现圭的《中国所藏新罗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之实态调查》(2004);金允珍的《晚唐著名韩国诗人崔致远与〈桂苑笔耕集〉》(2012);刘伟的《〈桂苑笔耕集〉考述》(2004);李时人、詹绪左的《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的版本及校勘札记》(2010);田廷柱的《论〈桂苑笔耕集〉的史料价值——兼评高骈其人》(1996);姜昌求的《新罗人与唐代人的赠诗研究》(2008);陈蒲清的《韩国韩文文学的奠基作〈桂苑笔耕集〉》(2002);马家骏的《崔致远和他的诗》(1983)等。尚未有学者从形象学等角度对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开展相关研究。
一、崔致远与《桂苑笔耕集》
盛唐时代的中国,在商业方面与世界联系广泛,其中与新罗往来最为密切。两国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唐朝末年,他们彼此互遣使节,通过海上和陆路积极沟通。新罗王曾多次派遣本国使臣到长安进献,多携稀世珍宝,唐朝也以罕见珍品回赠新罗。同时,新罗留学生也是来唐求学的学生中最多的。在罗唐两国的往来进程中,作为当时唐朝重要口岸的重镇扬州,起到了桥梁性的纽带作用。而影响最为深远的留学生中便是在扬州工作、生活四载的崔致远,他被称为“中韩交往第一人”。崔致远,字孤云,新罗宪安王元年(857年)生于王京(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沙梁部,[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公元868年(唐懿宗当政9年),崔致远访唐求学。[注]韦旭升:《崔致远居唐宦途时期足迹考述》,《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66页。公元874年,唐朝为新罗、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专门组织了留学生考试。通过勤学苦读,崔致远参加了这次考试,并成功考取“宾科”进士,当时也仅是及冠之年。但是命运的天平却悄悄地倾斜,他及第后并没有适合他的官职,所以他只能默默地等待,这一等就是两年。在栖居东都洛阳的两年时光中,他酾酒赋诗交游士林。历史终是没有埋没这位才子的耀眼光芒,在公元876年(乾符三年),崔致远偶然结识了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裴瓒,因其才华横溢而备受裴瓒垂爱,终获裴瓒提拔担任江西道宣州溧水县尉一职。据载:“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淮南节度使高骈聘请崔致远任从事巡官,执掌军事文书。”[注]韦旭升:《崔致远居唐宦途时期足迹考述》,《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66页。此后,崔致远来到了唐朝君主统治下的扬州,这是国家粮仓、交通枢纽。“安史之乱”之后,长江以北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的治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凭借东南地区的支持来维持统治。这时,地处吴楚两国交界的扬州便迅速跻身发展要地行列,原本兴盛的城市经济更是瞬息万变、一日千里,以致今天我们翻开任何一本唐诗著作,目光所至皆是其繁俪华侈。若我们来不及亲自查阅,也会在与人交谈中对那个盛世有所耳闻。能下车至扬州,让多少士大夫趋之若鹜。崔致远勤勉治学、笔耕不辍,创作了不胜枚举的诗词作品。崔致远回到新罗后,公元886年,将其留唐16年所作的诗文编成了《桂苑笔耕集》。文集所载入的大量公文、信札以及诗作,皆是其在扬州任职期间书写和创作的。此文集收录了大量晚唐时期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重要史料。
《桂苑笔耕集》中记载了数不胜数的唐末历史事实及人物,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晚唐历史及文学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崔致远虽然未逃脱幕僚文人的束缚和条框,著作中表达了对黄巢起义军贬咒批判,于无形之中助推了当政者的统治,但就其才华的优胜及史学价值来说,仍是不可小觑的。此文集共20卷,前16卷公文由高骈代写,后4卷是崔致远自身的抒怀之作,包括表、状、别纸、书、檄文等10多种类别。[注]黄平:《朝鲜诗文集的开山鼻祖:〈桂苑笔耕集〉》,《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第90页。纵览其诗歌,可发现崔致远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了“桂苑”一词,如“岂如扬都粤壤,桂苑名区,四夷之宾易朝天,九牧之贡无虚月。”[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3页。(《请巡幸江淮表》)。其中“桂苑名区”一词就体现了当时的扬州的确名震四海。“九天降诏,万里宣恩,柳营之列将欢呼,桂苑之群寮感泣。”[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1页。(《谢郄公甫充监军手诏状》)。“捧嘉贶而增荣,窥雅言而窃忭,况对莲池之客,实逢桂苑之仙。”[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6页。(《宣歙裴虔余尚书》)。由此可见,“桂苑”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地名。南京毗邻扬州,属于淮南节度的辖区,由此可以推断,崔致远用“桂苑”一词代指淮南。而“贞观之治”时期,扬州属淮南道,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扬州改名为广陵郡。[注]李廷先:《唐代扬州城区的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第193页。所以,从地理的考证来看,崔致远笔下的“桂苑”“淮南”指的都是扬州。
崔致远之所以将此著作命名为《桂苑笔耕集》,一方面源于“桂苑”是古时淮南地区一个有代表性的象征地名;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广招门客,撰写了著名的《淮南子》,在他的幕僚中有8位知名人士,被称为“八公”。崔致远文章中的“指桂苑而访刘安”出自《桂苑笔耕集》中《迎楚州行李别纸》二首中:“伏审尚书远赴天庭,将遵水道,整兰桡而思郭泰,指桂苑而访刘安,睹神仙则楚俗皆惊,闻雅颂则鲁儒相贺。”[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6页。这里崔致远把高骈比作淮南王,把高骈幕下的文人包括自己比作八公。“桂树之山”是当年刘安招隐士之地,崔致远以“桂苑”寓淮南,隐含了他对淮南王刘安的向往及对高骈的期望之情。
二、崔致远笔下的扬州社会
《桂苑笔耕集》是崔致远在担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从事和都统循官期间进行创作的。唐朝淮南节度使将治所设在扬州,即淮南地区之中心。《桂苑笔耕集》中记录的扬州形象深入人心,尤其是在身份为异国人的崔致远笔下,更是别有一番特点。孟华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中写道:“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形象,他是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注]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页。在《桂苑笔耕集》中,我们也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这位新罗文人描写的各种形象背后所蕴藏的诗人的内心情感。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就“形象”的基本特征来说,首先应是异国形象间的比较,其次才反映本国对异国文化的认识,体现的是异国与本国的文化关系。也就是说,扬州形象在身为新罗诗人的崔致远的笔下是异国形象。崔致远汉诗中体现的扬州形象是当时罗唐文化关系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崔致远笔下的扬州形象既有以景物为中心的城市外观形象描绘,又有以人物情感为主线的变化升华,既是一种物化形态,也是一种人文情感的写照。作为一国文化的隐喻或“软实力”象征的“形象”,它成为一个国家在他国所包含某些形象的文学传播程度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中国汉文化在新罗的传播构建了诗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这对于了解当时中国形象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扬州社会——从极尽繁华到残殇衰落
丹麦学者拉森指出:“形象的属性是一个持续变化之过程的结果。”[注]乐黛云、张辉:《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而崔致远在扬州生活的4年,是扬州变化较大的4年。随着唐朝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崔致远诗歌创作中的扬州形象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透过崔致远对扬州景物的描绘,我们看到了扬州经历了从繁华到战乱的变化过程。
1.繁华景象
崔致远居住在扬州。历史上,扬州既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又是唐朝重要的财富之源,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桂苑笔耕集校注》十九卷《谢周繁秀才以小山集见示》一文中记载“集桂苑之名都,占莲池之雅望”。崔致远将“桂苑”称作名都,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桂苑——也就是扬州,是当时淮南地区的重镇。关于淮南的富庶繁华,又如《请巡幸江淮表》中两处所指,一为:“况江淮为富庶之乡,吴楚乃繁华之地。”[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5页。再为:“岂如杨都粤壤,桂苑名区,四夷之宾易朝天,九牧之贡无虚月。”再如,《萧遘相公》一文中:“淮南乃寰中裕富,阃外名高,喻以金瓯,永无衅缺;比于玉垒,实异繁华。”[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0页。由此可见,淮南当时是周围地区中最富裕的城市,名扬四方。崔致远对“金瓯”、“玉垒”这些景物形象的描绘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当时扬州的繁华程度,令人惊叹。十分精炼的语言,恰到好处的比拟,生动、形象地呈现出了当时淮南地区繁华的景物形象,而作者恰恰是通过对扬州繁华景物形象的描写,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十分华美的扬州图画。此时富庶、美丽的扬州形象也正是在新罗诗人眼中中国汉民族大国的光辉形象,扬州形象借助新罗诗人崇尚汉文化的影响而更加丰满。对扬州繁荣富庶的描绘,对唐朝美好形象的整体塑造,都折射出崔致远对中国形象寄予的理想之国的乌托邦色彩。
2.战乱烽火景象
《桂苑笔耕集》中的扬州形象并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美好形象,随着当时政局的变化也呈现出了差异的形态。扬州繁盛、富有,又是战略要地,所以自古以来它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历史的原因,它数次经受战乱的“洗礼”。《桂苑笔耕集》中描写这一时期备受战争摧残的扬州景象也有迹可循。如在《奉和座主尚书避难过维阳宠示绝句三首》一文中,崔致远如此描绘:“年年荆棘侵儒苑,处处烟尘满战场。岂料今朝进宣父,豁开凡眼睹文章。乱时无事不悲伤,鸾凤惊飞出帝乡。应念浴沂诸弟子,每逢春色耿离肠。”[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44页。诗中“烟尘满战场”“鸾凤惊飞”的景物形象十分生动地反映出了当时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的局面以及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此时的扬州与前文所述的繁华一景形成了强烈且鲜明的对比,也表现出了诗人对于眼前局势的无奈和无助。
又如《上都昊天观》一文中:“但以桂苑繁华,扬都壮丽,既见星坛月殿,处处荒摧;难期鹤驾霓旌,时时降会”,[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7页。就恰到好处地反映出了扬州形象由繁华走向了衰落,流露出了诗人的无奈和惋惜之情。这种异国形象的变化也体现了崔致远乌托邦理想的破灭。莫哈指出:“形象学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种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而这些都是主观向往相异性所特有的。”[注]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页。美好的扬州形象寄托着崔致远对理想社会的期盼,影射出了其改造自身的美好愿景;扬州在战乱中不仅仅是一所城市,也是一种意识、一种形态化的形象,也体现了其对唐朝政局同情关注的态度,由此体现出“自我”与“他者”形成的一种交流融合的状态。
三、崔致远笔下的扬州情怀
形象的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之间的关系是从自我与“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入手,崔致远作为新罗诗人与中国友人交往的背后就体现了这种“自我”与“他者”、“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因《桂苑笔耕集》不同于小说和杂话,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是直接地对人物言语、行为的描绘,而是一种“间接描绘”。这些人物是崔致远在“扬州形象”这一大的背景环境下结识的诸多友人。他们都是与崔致远本人有着深厚情谊的文人形象。这些形象受限于个人所处的政局之中,具有自身形象特色的同时,又寄寓着自身对他者形象的感激怀念之情。
(一)情深谊厚
1.裴瓒——休戚相关,患难与共
当年提拔崔致远的伯乐裴瓒(字公器),两人可谓是至交。《桂苑笔耕集》中裴瓒的形象也随着其与崔致远的交往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据《桂苑笔耕集校注》记载,乾符元年(874年)裴瓒主贡时,两人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也因此结下了深情厚谊。此时,裴瓒是提拔崔致远的恩人形象。其次,裴瓒的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深处乱世之中的裴瓒是不得志的官宦形象。据崔致远的《吏部裴瓒尚书二首》其一记载:裴瓒“情疏宦路,性悦道风”,然而济世之心并未泯灭。由此可见,裴瓒遭遇了人生巨大的打击,甚至没有栖身之处,只得流浪于江南。因此,这一时期裴瓒的形象特点是:身处乱世之中,虽心系国家但力不从心,前途未卜,忧心忡忡。崔致远得此消息后,便立即提笔撰写《与恩门裴秀才求事启》一文,送予高骈请求帮助,高骈当时已高居时任淮南节度使。唐军破土归来,在关中镇守,裴瓒因率军有功升迁为礼部尚书,走陆路劳顿且有危险,此时裴瓒接受了崔致远的帮助和支持。一方面诗中描绘出了裴瓒当时“郁郁不得志”的形象特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崔致远对这位落难挚友深处难境却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其次,据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卷十五“辑考五上·礼部尚书”条考,在崔致远的极力推举下,裴瓒转授礼部尚书,此时裴瓒是在友人帮助下东山再起的文人形象。崔致远为了表达对挚友终于重得重用的喜悦之情一连写下了《吏部裴瓒尚书二首》:“伏承荣膺宠命,伏惟感慰……用舍既归于重柄,古今皆托于长材,人望所谐,主恩斯在……”[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1页。诗中盛赞裴瓒为人贤能,性情淳朴,称其虽运途坎坷但贤德之人终得重任,实是众望所归。此时,裴瓒是蛰伏数载,重得重用,春风得意,苦尽甘来的光辉形象。
最后,在《贺除礼部尚书别纸》《上座主尚书别纸》(《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十九)及《与礼部裴尚书瓒状》(《孤云先生文集》卷一)等文中,崔致远接连恭贺裴瓒。裴瓒赴任途中,曾亲自前往淮南探望崔致远。[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86页。可见裴瓒对其关怀可谓是无微不至,对于身在异国的崔致远来说,裴瓒是其患难与共的挚友,也是给予其无尽关怀的恩人。
唐末之际,正值黄巢起义军攻入首都之时,裴、崔两人再次聚首于扬州,一人是逃难,一人是北上回国,逃难中的偶然相逢让内心慌乱瞬时间化为喜悦。裴瓒写诗给崔致远,崔致远还以《奉和座主尚书避难过维阳宠示绝句三首》回赠裴瓒。诗中将自己对恩师、挚友的依依惜别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离别情境之中表达了两位文人的离别愁苦。在扬州时裴瓒还创作了“七绝”三首赠予崔致远,皆因情到深处有感而发,崔致远也应和以表达对裴瓒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其一有“岂料今朝觐宣父,豁开凡眼睹文章”之句,[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44-745页。展现了崔致远心中裴瓒尊师如父的高大形象。
2.高骈——伯乐之顾,知遇深恩
高骈形象的塑造,是在崔致远与其交往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崔致远对这位提携自己的恩人形象的描绘也是从与之渐进的交往而发生变化的。唐广明元年(880年),崔致远任官溧水县尉一职,投靠高骈,成为淮南幕府的一名门客。为表达高骈对自己的提携之恩,他作诗一首《陈情》:“俗眼难窥冰雪姿,终朝共咏小山词。此身依托同鸡犬,他日升天莫弃遗。”[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07页。
崔致远引用一人得道举家升天的典故(为汉代淮南王刘安典故),向高骈暗示自己追随忠诚之心,寓示提携伯乐之情。因为这首诗使得高骈对其欣赏有加。此后,崔致远和高骈成为挚友。崔致远另外执笔续写《陈情上太尉诗》:“客路离愁江上雨,故国归梦日边春。济川幸遇恩波广,愿濯凡缨十载尘。”[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44页。此诗中,崔致远借诗词向高骈表明自己投靠幕府的意图是“求食禄”“为荣亲”,表达了对高骈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恩泽如海,可谓是“曾为大梁客,不忘信陵恩”。在《桂苑笔耕集·长启》一文中记载:[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25页。高骈在百万雄兵中给予重托,让崔致远深感身负重任,在崔致远的心中,高骈就是提携自己、重用自己,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恩人。投桃报李,崔致远不遗余力尽心竭力地为高骈代写一系列文书。尤其《檄黄巢书》闻名遐迩,也正是这篇《檄黄巢书》,让崔致远被高骈一眼选中,给予了他进一步的认可和赏识。高骈让崔致远给朝廷写一封毛遂自荐的状文,落自己的字。在中和二年(882年)夏初,崔致远最终因为这份宝贵的举荐状终获“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的奖赏,可谓如日中天。
3.顾云——志同道合,至诚至真
顾云字垂象,又字士龙,池州秋浦(今安徽省贵池县)人。顾云出身富贵之家,为大商人之子,好且擅长诗词文赋,唐末颇有名。崔致远与顾云二人来往频繁,在广明元年(880年)冬,崔致远进入高骈幕府之时,多亏了顾云的推举和引荐。崔致远入幕淮南后,与顾云相见恨晚,关系日进千里。可以说,顾云对崔致远有着知遇之恩。崔致远对顾云的才华可谓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读了顾云的《献诗启》(献给高骈),诗中这样写道:“某启:某窃览同年顾云校书献相公长启一首、短歌十篇,学派则鲸喷海涛,词锋则剑倚云汉,备为赞颂,永可流传”。[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83页。由此可以看出,崔致远对顾云的评价极高,其心目中顾云是才子,是才华横溢的文人形象,崔致远对其才学甚至达到了仰慕的程度,盛赞其“永可流传”。中和二年(882年)七月,顾云左迁观察支使,崔致远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当即撰写了《请转官从事状》,表达了他对好友的恭喜和祝贺之情,赞顾云为:“东筠孕美,南桂抽芳,曳谢朓之长裾,从卫青之军幕,五羖皮之为重,岂谓虚谭;百鸷鸟之不如,方知实事”。[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4页。又据《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十八《谢示延和阁记碑状》记载,中和三年(883年),高骈筑延和阁竣工,为了树碑立传,遂命顾云“谨撰碑词”,并遣观察衙推邵宗将此“《延和阁记》碑本一轴”赠与崔致远,崔致远盛赞顾云说:“今者支使侍御以好善心得稽占力,骋真才子之藻思,辱大丞相之笔迹”。[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38页。顾云在崔致远笔下是文学造诣极高的诗人的形象,崔致远对其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又据高丽李奎报《白云小说》称:“崔致远入唐登第,以文章名动海内,有诗一联曰:‘昆仑东走五山碧,星宿北流一水黄。’”[注]崔致远:《高丽名贤集》第一册,首尔: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1986年,第574页。可见这位来自异国的友人,其在汉赋方面的极高造诣也深得顾云的赏识。
4.女道士——芳卿可人,依依惜别
在扬州与崔致远交往的众多文人墨客之中,有一位女道士曾给独自在异乡漂泊的崔致远留下过很多情感上的慰藉与关怀。在《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崔致远特意为这位女道士作诗一首,临行前向她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真挚的情感:“每恨尘中厄宦塗,数年深喜识麻姑。临行为与真心说,海水何时得尽枯?”[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51页。“海水尽枯”,用典与抒情结合得巧妙无痕。崔致远多年来独在异乡为异客,在他乡世事艰难,常常因官场险恶而感到苦恼怨恨、筋疲力尽,女道士应该是崔致远在异乡路上的知音,甚至可以说是红颜知己,并给予了崔致远很多的温情与关怀。现在就要踏上回国的征程了,崔致远想讲几句知心话,但“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不了情,又如何说得尽呢?离别的酸甜苦辣,把诗人置于“无力挽狂澜”的波涛之中,将他百感交集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留别女道士》是崔致远献给女道士的诗篇,崔致远在和女道士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很深,表达了他的离愁别绪与想超脱尘世的深厚而切实的感情。
从人物形象分析的角度而言,《桂苑笔耕集》中无论是对其有着知遇之恩的裴瓒,还是令其爱恨交织的高骈,抑或是挚友顾云,有着爱慕之情的女道士,在对其形象的描绘中,既有诗人眼中的“他者”形象,同时也透过这些才子文人的形象,表现出了崔致远与友人的深情厚谊,更窥探出了他细致多情的内心世界。当形象的塑造者进入到被塑造者的文化之中,以一种平实的眼光去观察“他者”时,其塑造的形象就会融入对被看对象的同情、关切和理解。这种立场就是巴柔所言的第三种态度——友善。[注]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异国形象的关注不是绝对否定或绝对差异的体现,崔致远对扬州形象的关注恰恰就体现了这种友好关切的态度。
(二)托物言情
《桂苑笔耕集》中的景物形象有两个主要的特征:第一,这一时期崔致远虽身处内陆地区扬州,但是诗中的景物形象却往往是与内陆扬州不相及的“海”,也就是以“大海”这一景物形象为意象,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第二,在咏物诗中来说,《桂苑笔耕集》中对于景物形象的描写,大多寄托着诗人惆怅的思绪,抑或是思想的思绪,抑或是怀念友人的思绪,将自身复杂的情感寄于景物形象之中。研究其咏物诗中景物形象的塑造特点,能使我们十分清晰地了解他当时在扬州的境遇和心情。这种中国形象的描述也体现了形象背后崔致远的意识形态。在《山顶危石》中:“万古天成胜琢磨,高高顶上立青螺。永无飞溜侵凌得,唯有闲云拨触多。”[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62页。在《石上矮松》中:“自能盘石根长固,岂恨凌云路尚赊。莫讶低顏无所愧,栋樑堪入晏婴家。”[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63页。“山顶危石”和“石上矮松”这两个景物形象,所体现的是庄子“达人知命”的思想。崔致远因为他的外国人身份,念念不忘自己身份的卑微和低下,将自我内心的孤寂寄托于危石、矮松来表现其自身所处的环境,以物来表现自我形象。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中,孟华这样叙述道:“形象本身与形象建构也透露出作家和本国人的心态。他者形象是反观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注]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页。因此,在崔致远的咏物诗里面喻托的对象往往有一种生不逢时或者生非所属的自卑感,总想积极进取,过富贵人生,但却屡屡不得志。这首诗正是从景物中反映出诗人当时内心的痛苦与纠结,寓情于景地表达了其独在异乡为异客,在异国他乡没有归属感,想要回到祖国的心情。狄泽林克所言:“形象是塑造者在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支配下对他者的想象和构建”。[注]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正值唐末,扬州兵荒马乱,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一时期整个扬州的形象是落寞的、沉沦的,诗人一方面借“危石”“矮松”比喻自己的处境,同时也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扬州的荒凉局势。
《题海门兰若柳》
广陵城畔别蛾眉,岂料相逢在海涯。
只恐观音菩萨惜,临行不敢折纤枝。[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71页。
“柳”在中国古诗中大多寓意“留”。崔致远诗歌中借柳枝表现离情,诗中的“广陵城畔”即现在的扬州。“柳”这一景物形象被诗人寄托情感,表达依依惜别之情。此处的“临行不敢折纤枝”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诗人对扬州的深深眷恋。与其说崔致远眷恋友人,不如说他更眷恋这承载他太多政治理想的“广陵畔”。“峨眉”象征女子,此时的扬州是如同女子般温柔的、娴静的,是蕴含诗人无限不舍之情的形象。[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48页。在《酬杨赡秀才送别》一文中:“谷莺遥想高飞去,辽豕宁惭再献来。好把壮心谋后会,广陵风月待衔杯。”诗中“芜城”即别称扬州(是扬州的别称),这里借“大海”这一景物形象来烘托回家之路艰辛遥远,此处大海的意向表露出诗人的不舍之情。“谷莺遥想高飞去,辽豕宁惭再献来”表明诗人期待与友人的再次“扬州逢”,反映出了在诗人心中“广陵”为自己留下的是既美好又珍贵的回忆。崔致远期待与友人的再次重逢,更期待能够与友人在“广陵之畔”对酒当歌。
四、结语
孟华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中写道:“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形象,他是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注]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2页。在《桂苑笔耕集》中,我们也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这位新罗文人描写的各种形象背后蕴藏的诗人的内心情感。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也指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注]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就“形象”的基本特征而言,首先应是异国形象间的比较,其次要反映本国对异国文化的认识,体现的是异国与本国的文化关系。也就是说,扬州形象在身为新罗诗人崔致远的笔下是异国形象。崔致远汉诗中体现的扬州形象是当时罗唐文化关系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崔致远笔下的扬州形象既有景物为中心的城市外观形象描绘,又有人物情感为主线的变化升华,既是一种物化形态也是一种人文情感的写照。形象决定了一国文化的软实力水平,一个国家在他国所具有的形象成为了其在他国传播力量的主体影响因素,新罗诗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体现了中国汉文化在新罗的传播,这对于了解当时中国形象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