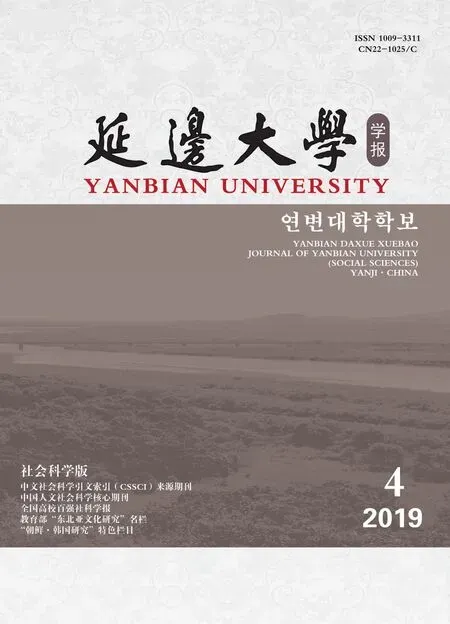试析马建忠与1882年的朝鲜
——以马建忠在朝笔谈为中心
李 晓 光
19世纪40年代,在西方坚船利炮冲击下,中国国门被打开,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接受来自西方各层面的影响。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降,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开始生成,他们也开始选择变革自身内部肌体。晚清开明士绅在思想认识上的转变,是“基于现实历史运动展开的,具体就表现为从帝国体系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政治大变迁”。[注]付春:《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第4页。到19世纪80年代末,“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以重塑其统治合法性,从而在事实上开始了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型”。[注]陆勇:《传统民族观念与清政府——以“中国观念”为视角》,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7年,第88页。清对朝鲜的属国政策也因此开始转变。有学者以朝鲜开港以前的部分《燕行录》为主要资料进行研究,从制度层面上揭示了中朝关系演变的内在动因和趋势,并认为这“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注]王元周:《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98页。总之,在内外因的交错影响下,中朝宗藩关系在近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并最终被迫走向解体。
19世纪80年代是中朝宗藩关系发展演变的关键时期。本文仅以1882年马建忠三次前往朝鲜与朝鲜官员笔谈的内容为中心,通过对笔谈内容的分析,阐释马建忠在理论上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进而了解在中国国家处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朝鲜问题上思想观念的些许变化,这既体现了处于由传统向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一部分受过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也展现了他们在“传统”与“近代”之间腾挪转圜乃至尴尬的窘态。
一、马建忠与1882年的朝鲜
马建忠生活在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他“少好学,通经史。愤外患日深,乃专究西学,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1册·卷446·列传23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82页。1880年春,马建忠结束在法国的留学生活,回到天津,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李鸿章向清廷推荐马建忠,称:“该员持躬谨慎,为外人所敬重,允称品学兼优,或备充出使人员,或备咨询例案,以与洋员辩论,均堪胜任等因。……华学既有根柢,西学又有心得,历试以事均能折衷剖晰,不激不随,凡过津各国公使领事无不同声引重,实堪胜专对之选”。[注]李鸿章:《奏保马建忠片》(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奖赏提拔马建忠,称其“足智多谋,熟悉公法,能持大体,历办朝鲜与美、英、德议约事宜及此次朝鲜善后各务,均为远人所敬服,实堪胜专对之选,拟请赏戴花翎,并恳特恩,以海关道存记擢用”。[注]李鸿章:《奏保丁汝昌马建忠片》(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10)奏议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从李鸿章的两次奏稿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建忠能力的认可及对马建忠处理朝鲜问题的肯定,中国学者陈三井和权赫秀、日本学者坂野正高都对马建忠有评价,坂野正高的评价甚至更高。[注]陈三井认为,“中国最早派遣学生留法,肄习国际公法与外交者,当首推马建忠”(陈三井:《略论马建忠的外交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期下册,第543页)。权赫秀进而认为,马建忠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学习近代外交及国家法理论和知识的专业人士”(权赫秀:《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6页)。坂野正高认为,马建忠是李鸿章幕下一名有力的辅佐。如果能够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政治社会这个语境中对他的整个思想、行为、挫折进行综合的跟踪研究,那么这个研究一定会对探明“传统主义式”的旧中国那充满苦涩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助一臂之力([日]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这样的评价说明了马建忠在近代中国外交中所展现的外交才能,并进而从侧面说明马建忠对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影响。
1882年,朝鲜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5月22日,美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简称《朝美条约》),这标志着朝鲜全面开国。6月6日,英国与朝鲜签订《通商友好条约》。7月1日,德国与朝鲜签订《通商友好条约》。7月23日,“壬午兵变”爆发。日本出兵朝鲜干涉兵变。清政府应朝鲜之请,派兵援助朝鲜平定兵变。“壬午兵变”是“对日本侵略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但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此为借口也扩大了对朝鲜的侵略”。[注]曹中屏:《朝鲜近代史1863-1919》,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83页。随着朝鲜形势有利于日本,朝鲜与日本最终于8月30日签订《济物浦条约》,[注]该条约由本约6款和续约2款组成。该条约严重侵犯了朝鲜的内政,并使日本在事实上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壬午兵变”的另一后果便是,马建忠、丁汝昌以煽动兵变罪诱捕了大院君李昰应,于9月24日护送大院君前往中国,后羁留于直隶省保定府。上述事件发生期间,马建忠奉命三次出使朝鲜,这是“他一生中从事过的重要外事活动”[注]谈群玉:《马建忠与朝鲜问题》,《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马建忠三次赴朝,主持朝鲜与美欧等国签订通商条约、帮助平定“壬午兵变”、诱捕大院君、促成朝鲜与日本订约等重要事件,尤其是处理朝鲜“壬午兵变”,是“建忠从事外交,初展长才所建的第一功”。[注]陈三井:《略论马建忠的外交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期下册,第547页。马建忠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策略,实际上也是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尤其是他对朝鲜通商伊始给予的各方面指导,虽说其中无法脱离宗主国对属国的一些做法,但对通商之初的朝鲜也是很有助益的,这在近代中朝关系史上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从理论上看马建忠对1882年朝鲜问题的指导
1882年,马建忠先后三次出使朝鲜。5月和6月赴朝主要是为主持朝鲜与美国、英国、德国签订通商条约。8月赴朝,参与平定“壬午兵变”并计擒兵变主谋大院君李昰应。马建忠三次赴朝,与朝鲜官员进行了多次笔谈,每次笔谈都从理论上对朝鲜的现存问题进行了论证指导,这对通商伊始的朝鲜在处理通商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影响,也可看出此时清政府在中朝关系上所处的地位。
(一)第一次在朝笔谈对朝通商事务的指导
1882年初,马建忠前往朝鲜斡旋朝美条约。经过三个阶段的谈判协商,朝美于1882年5月22日签订了《朝美条约》,条约共有14款。从条约的内容看,美国取得了经商不受限制和特别受保护的权利、领事裁判权、最惠国条款、派遣公使驻扎朝鲜首都、剥夺朝鲜关税自主权等权利,这实际上是政治侵略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一个极不平等的条约。
《朝美条约》使朝鲜与西方国家正式通商,朝鲜对通商事务的许多方面是懵懂无知的。因此,条约签订后,马建忠便与金宏集[注]即金弘集,初名宏集,后改为弘集。于5月22日当晚、25日和26日进行了三次深入交谈,以期与朝鲜方面深入沟通,并借此对初开通商事务的朝鲜予以指导。
第一次笔谈,金宏集主要就朝鲜通商后设立关卡规制、海关规则等方面的内容与马建忠进行交谈,马建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并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具体问题涉及通商条约的批准文式、格式、海关规则的运用、地租定界及罚款等。如金宏集提出:“1.海关规则敝邦从未设立,日使屡以为言,故敢请规则如何可得妥善?2.地租定界及罚款多少远近轻重之等当如何?方与日使议通商章程,而彼欺我不谙外规,专要从少从轻。定界又欲广占,故即此仰质。3.敝邦人全昧万国公例,一切通弊皆所不解。故所以来日人之要挟,否则何虑?”[注]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656-657页。马建忠的意见是:“1.可参酌中外海关规则用之,但此系创始,贵国须雇一熟谙此事者,以总司之,切不可雇用日人。2.罚款当以案情之轻重,由判官定拟。地租定界当握定主意,许以每口周围若干里,至通商章程在诸君与日使争执。若美国条约,则通商章程约内注明照万国公例酌办。3.吾国初开口岸,亦未深谙通商条例,大为吃亏,今则遣人至外洋察看考究,深知底蕴”。[注]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656-657页。从谈话内容上看,这次笔谈只涉及了设立关卡的一些层面上的内容,并未就具体的内容进行深入交谈。但这对通商之初的朝鲜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指导,既可促使朝鲜快速制定通商相关规章,又可避免在具体操作中走弯路。
第二次笔谈主要是就朝鲜正与日本交涉的通商税则问题展开。谈话中,马建忠指出了与日本人接触时朝鲜所应具有的态度,即“与之接谈须内刚外柔,若不协议,亦无碍事,公法以全权办事者未必节能定议耳”;[注]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658页。指出了朝鲜对日的通商税则,应谨遵“公共税则”及日本“抽七五”税则的底线,为了使日本能够执行这一税则,朝鲜要使用这样的计策,即“公等现用缓兵之计”,等到美国换约时,就将通商章程、公共税则在朝鲜各口岸公布,到时来朝鲜贸易的国家,如果签订的条约内没有共议税则,就按公共税则来征税。这时日本还没有将条约议妥,就必然会按公共税则来抽税。金宏集对马建忠的这一提法极度赞同,他说“此教节节切至,敬服,敬服”,[注]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657-658页。并将与日本通商章程的底稿交给马建忠,请他在闲暇时对此底稿再加点阅,逐条提出意见。
第三次笔谈内容主要是关于日本有意对朝借款及开采矿山问题。金宏集拿着国王的密谕向马建忠咨询“日本愿向朝鲜借款”一事,马建忠首先指出了“借贷之事,所系甚重”,然后指出了借贷的利害关系,并通过分析借贷,指出“向一国政府告贷,势必受其要挟”,[注]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659页。而日本政府愿意借款给朝鲜,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事。至于开采矿山,马建忠指出朝鲜的五金矿已被日本、俄罗斯垂涎很久,若是开采的话,必须对矿山进行实地踏勘,确定某处矿山产什么矿、矿苗怎么样。如果矿苗很好,则借款开采之事就非常容易了。
马建忠第一次赴朝与金宏集的三次笔谈,涉及朝鲜设立关卡、通商税则、借款、开采矿山等内容。每次谈话内容及其深度都各有侧重,为通商伊始的朝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且马建忠在每个问题上的建议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足见其对近代西方法律、法规理解程度之深。第一次赴朝是马建忠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观念转变的开始,不仅仅只是将朝鲜局限在维持属国关系上。马建忠在回国前让朝鲜大臣转告朝鲜国王:“刻以要务暂归,如他国续来,即告以朝鲜不谙外交,约事多由中国主持,今欲与朝鲜立约,可先赴津门商请北洋大臣派员莅盟,方可定议。”[注]马建忠:《东行初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36页。也就是说,朝鲜要与其他国家继续签约时,要先通知清政府。清政府派员赴朝后,才能议约。这也表明了作为清政府官员的马建忠在处理朝鲜问题时的立场和宗旨。由此可见,马建忠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也未完全摆脱传统对朝思想,仍旧在“传统”与“近代”之间转圜。
(二)第二次在朝笔谈对朝通商事务的指导
马建忠回国后不久,德国使臣巴兰德要前往朝鲜与之商议通商条约。1882年6月21日,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北洋通商大臣张树声再次派遣马建忠与丁汝昌前往朝鲜,帮助朝鲜与西方国家订立通商条约。这次出使,可以看作是第一次的延续。6月23日,马建忠一行抵达仁川,与德国使臣巴兰德会合。朝鲜方面与德议约的官员是大官赵宁夏、副官金宏集。因为有《朝美条约》为蓝本和与美订约的谈判经验,所以这次议约谈判进展非常顺利。7月1日,朝德两国在仁川签订《朝德通商条约》。7月2日,马建忠一行返回清朝。
朝德议约期间,朝鲜大官赵宁夏受国王高宗之托,于6月29日向马建忠密询内政、设关、开港、电线、探矿等通商事务。马建忠与赵宁夏就这些通商事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笔谈。马建忠首先指出赵宁夏代高宗国王密询的各件事“关系甚大,当密禀我傅相代为筹定”,但也对密询各事做了一个简略回答。他对朝鲜提出的“外交之际,内政为先”之策进行了深入分析,引用苏洵《审敌》中“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注]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7页。来强调内政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同时,他又指出了朝鲜的外忧和内忧所在,即“今贵国与欧西大各邦讲信修睦,不过欲杜强邻之觊觎,此为急标之举,忧在外者也。国民贫困,商务不兴,官冗职旷,此忧在内者也”。[注]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7页。
马建忠又对朝鲜贫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意者其不均之过欤”。这种不均的解决方法就是要物货流通,没有拥塞之患,“其法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在上者第为民除害,设法鼓舞,令民踊跃于农桑懋迁而不自知”。[注]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7-48页。后面又对朝鲜的教育、军事、开港设关、电线邮递、采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贵国王慨念局时,发奋为雄,思有以改弦更张,此乃吾东方之福”。[注]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8页。由此可以看出,马建忠对朝鲜的改革是赞同的,并对朝鲜的改革予以高度评价。因朝鲜立国已五百多年,“臣民安于故辙,若骤议革变,易启惊疑,当因势利导之,使民日趋于化而不觉”。[注]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8-49页。这是对朝鲜改革应遵从的原则而提出的指导意见,希望朝鲜能够顺利实现改革,以免朝鲜国内发生动乱而导致朝鲜国王的统治危机。在用人方面,“贵国不求富强则已,贵国而求富强,富参用西人,征收关税,讲论殖财之道”。[注]马建忠:《东行续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49页。人事在改革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税收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亦毋庸置疑。这两点的提出,足见马建忠对朝鲜改革是非常关注的。
赵宁夏此次密询马建忠有关通商事务诸细节,马建忠的回答使朝鲜君臣对通商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对他们了解近代知识以及开放通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马建忠主张帮助朝鲜实行内政改革,走近代化的自强之路。这种主观愿望虽好,却不能得到当时中朝两国政府的认可,但这也说明马建忠在对待属国朝鲜的观念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
(三)第三次在朝笔谈对朝政策指导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爆发后,清政府派马建忠与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舰于8月9日前往朝鲜,帮助朝鲜处理“壬午兵变”问题。8月27日午后,户曹尚书金炳始奉朝鲜国王的命令来馆驿,就日本公使花房义质提出的七款要求来征询马建忠的意见。马建忠对日使所开条款,用“即可许者、有决不可许者、有须变通者”分别进行批答,内容如下:[注]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869页;马建忠:《东行三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75-76页。因《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和《东行三录》记载的个别文字有出入,文中以《东行三录》记载为主,但在括号内标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的记载。
第一条,当许。惟以不限时日为妙。乱党不独伤及日人,亦且戕害贵国王妃大臣;若不严行查办,将国法之谓何?
第二条,可许。
第三条,可许。优恤金(《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写为“银”)五万圆,分给十三人家属,尚不为滥。
第四条,当力与争辩,若必不得已,可列入第三条优恤款内;于五万圆外,增添若干。因以前次舟内,与竹添进一笔谈示之。
第五条,旷(《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写为“扩”)地闲行,无碍于事;惟贵国民心不靖,宜限以数年后,再为举行。至咸兴、大邱开市,则为陆地通商,决不可为日人开端。杨花津虽属汉江埠头,惟以逼近王京,若许以通商,不识有无流弊?
第六条,公使领事游历内地,原属至(《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写为“公”)法。惟大乱初定,日后公使等若往内地游历,必先知会地方官方可。
第七条,京内长(《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写为“屯”)置大队,万不可许。至该公使为保身之计,随带若干(《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未有“若干”二字)兵弁,在馆内驻扎,尚无不可,惟不宜列入款内。至遣使至日廷慰问,似亦无所不可。惟宜与花房言明,日廷亦当有国书,由彼赍呈国王,以慰恤王妃相臣之难。如是,则彼此相慰,乃于国体无碍。盖朝鲜既无驻日使臣,特地派人慰问亦不为过。
批答之后,马建忠又对朝鲜与日本交涉时所应保有的立场给予说明,即朝鲜在“措辞之间,宜以直捷了当为妙。可许者,则立地许之;不可许者,则坚持不许;隐示以既有可恃,不足深畏之意;彼外屈于公义,内怯于我国,谅不至始终决裂也”。[注]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869页;马建忠:《东行三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76页。这是外交立场上必须坚持的原则,有利于“主权”观念的形成,也从一个侧面来鼓励朝鲜自强,维护自己国家的外交权力。
8月27日晚间,金宏集又以奉派议事副官的身份前往仁川,来馆面询各款,内容如下:[注]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870页;马建忠:《东行三录》,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主编:《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第76-77页。因《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和《东行三录》记载的个别文字有出入,括号内标注不同之处。
金曰:“日间所教,(亦既捧诵矣,而)间有未明(还赐指导)。恤银五万圆,而添以兵备之费宜若干。”(此处括号中文字《东行三录》中未记载)
忠曰:“日本兵舰原有常费,陆兵亦有定饷,调集(《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未有“调集”文字)来此,不过稍加运费。若与恤银统算在内,不过十万圆足矣。”
金曰:“诚如教矣,而有按限分偿之例乎?”(《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未有此句)
忠曰:“若贵国国帑可支,则宜一起交付,以免日后生息之累;若无力齐付,则可摊作几年(《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记载为“次”),仆想花房亦不至于以全付相强也。”
金曰:“杨花津开埠可许乎?”
忠曰:“若无大弊,何妨许之。仁川已开口岸,杨花津亦不过销仁川出入之货,其实非于仁川外另开一口也。况杨花津亦属水路通商,与已开口岸尚属一例,非若大邱、咸兴等地,复滋陆路通商之流弊也。惟议事之时,先可一概不许,必不得已则可许杨花津通市,而不给兵备之费,挹彼注兹,未始非计。”
金宏集对马建忠关于花房义质提出的七款要求批答不明之处,如“兵备之费”“杨花津开埠”等问题又请马建忠指导,马建忠对这些问题做了更为详实的解答。金宏集提出恤银“有按限分偿之例乎?”马建忠指出要根据朝鲜国库的储备情况来考虑这一问题,如果国库储备充裕可以一次性付齐,这样可以避免时间久了受偿还利息之累;如果国库储备不充裕,可以分作几次偿还。
“壬午兵变”后,马建忠第三次前往朝鲜,就朝鲜官员提出的问题给予逐条分析,并提出与日本谈判时所应遵循的原则。虽然如此,后来朝鲜与日本谈判的结果并未全部按照马建忠的建议进行。马建忠在完成此次赴朝的使命后,返回了中国。张佩纶就日本与朝鲜定约一事对马建忠进行弹劾,奏议称“再日本与朝鲜所定之约兵费五十万元及兵驻王城两条,一则竭其脂膏,一则据其心腹,所关甚大。……道员马建忠身在王都,去仁川不及百里。听两国私歃窃和事,先绝无闻见,事后复不争持,谓之形同聋瞽,坐失机宜,实亦百喙难辞”,“惟近日道路藉藉,谓朝鲜之约,马建忠不但预其谋并且主其事。……嗣该道恐李鸿章等察出,乃属朝鲜使臣弥缝其失笔谈中,谓‘此约并非建忠主谋’,正其欲盖弥彰之迹。……应请敕下张树声密询吴长庆,秉公覆奏,据实纠参,以为巧诈偾事者戒”。[注]《张佩纶奏日本与朝鲜秘密定约片》,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29b-30a页。由此可知,马建忠第三次前往朝鲜处理“壬午兵变”问题,他在这件事情中所展现的外交才能并未能被清朝某些大臣(如张佩纶等)认可,反而成为他被弹劾的藉口,也因此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奖赏提拔马建忠的建议未被批准。
三、结语
马建忠在1882年三次出使朝鲜,这是其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外交活动。马建忠与朝鲜的关系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即在实践中执行清政府加强宗藩关系的政策,在理论上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注]谈群玉:《马建忠与朝鲜问题》,《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本文中仅从理论上对他与朝鲜官员的“笔谈”内容进行了考察。
在朝期间,他与金宏集等人就朝鲜的通商、外交、内政、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这些重大问题今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策略,虽然这些理论构思在朝鲜并未能按预想执行,但是也对朝鲜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深深地影响了此后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壬午兵变”后,朝鲜国王因国势积弱,想要振兴国力,派全权大臣赵宁夏、副官金宏集、从事李祖渊等随同马建忠、丁汝昌于1882年9月7日抵达天津商量朝鲜的善后各事,马建忠在朝鲜的笔谈抄送至总理衙门备查。12日,赵宁夏等向李鸿章面呈朝鲜应办《善后事宜六条》,希望能得到清政府的训正。《善后事宜六条》内容包括“定民志、用人才、整军制、理财用、变律例、扩商务”[注]郭廷以、李毓树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910-912页。等六个方面,涵盖了马建忠与金宏集等人笔谈的内容。“《善后六条》原来被认为是“壬午兵变”善后的产物,而且似乎是朝鲜方面独有的、自发的提案,实际上是马建忠自薛斐尔条约缔结之后在朝鲜陆续部署的几步棋。换言之就是,他在中韩关系的重组过程中延续了自己“壬午兵变”之前的想法,并在此付诸实施。”[注][日]冈本隆司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54-155页。同时,这些理论构思也促成了他朝鲜观的转变。尽管存在矛盾,但却体现了处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一部分具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在中华帝国体系逐渐瓦解、“天下观”愈益崩溃时期对中朝宗属关系的策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