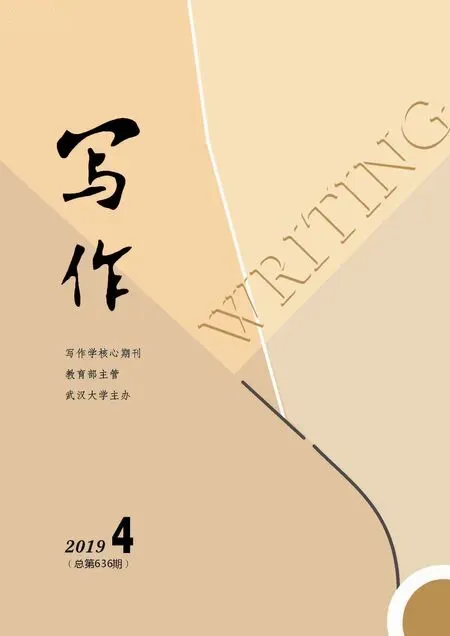写作的迭代资源和伦理传统
——从邱华栋的历史“转型”说起
陈若谷
一
“年轻的老作家”这个玩笑般的悖论,在短时期内可能都是邱华栋的独属标签。其中,“老作家”这个词颇可以用洋洋洒洒的一大篇文字来细陈其创作谱系。
粗梳一遍,最早期的《别了,十七岁》和《西北偏北》是典型的青春写作,一个在天山博格达峰下长大的少年,经历着和后来目所能及的青春叙事不一样的青春物语。大学毕业后,邱华栋又立马瞄准新的书写对象——城市和城市里的人。在这个时期,他创造了如青年吕安这样的都市“闯入者”形象,他们一方面痛苦地吞咽着自己精神的蜷缩感,另一方面却也丝毫不加掩饰地表达着对琳琅满目的经济社会的钦慕。当这些外来者终于缓步步入城市的内在肌理,疲惫地关闭四处打望的双眼,渐入迂阔之境时,邱华栋又将城市视为一个巨大的病灶,都市新富人和新美人们需要重新看待生活平静水面下的泥藻,这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时装人》《公关人》《社区人》《鼹鼠人》《环境戏剧人》等中短篇。
不过,这些以“XX人”命名的篇章有着理念先行的共同特点,作者在情节和描写中不断掺杂着现代性批判理论。虽然指向了人物怪诞性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但终究是稍嫌简化。短时间内,这些古怪变异的形象喷薄出现,为邱华栋在文坛的声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些作品也反噬了其创作尽快突破与转型的可能。因为批判视角和反抗主题,成为了邱华栋的文学评价体系里最顽固的一道屏障,即便在学位论文这样的专项研究中,论者依然容易忽略掉他的其他写作面相,而选取他对北京城的书写为研究对象,并且认定:“邱华栋的书写中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都是不存在的。”①郭彤:《邱华栋小说的北京书写与城市症候》,河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不过,这也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发现,他写作中那种信息流特质的东西,仿佛电影《黑客帝国》片头处的数码矩阵,刺目的荧光绿载着单调的数字和符号,但当它们集中迅即地顺流而下,展示的则是瞬时的激情美学。
这种情况在“北京时间”系列长篇小说出现后稍微有了缓解,在《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中,邱华栋的笔触显得更为贴近人物了。因为有了更为厚重的知识视野,他更是以新闻记者、私人老板、高校教授等精英群体为切入点,进一步写出了社会阶层和思想意识的分化状况。
“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就从这个形象序列显示出强大的生长性。尤其对于中国作家而言,层出不穷的现实状况和社会变化让他们不断向外拓展物理空间,又向里深掘心理空间。对于有完整教育背景和丰富媒体经历的邱华栋尤其如是,而他也在不断依靠一种“知识型”的经验结构来处理自己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在《十三种情态》《唯有大海不悲伤》这两个短篇和中篇小说集里,主人公们走向墨脱、走向边境,甚至攀爬冰峰、潜入大洋,此前在都市里患“扁平症”的人们,重新实现了“治愈”和自我丰满化。
出乎意料的是,在把城市逐渐吃透,并且形成了趋于成熟的写作风格之后,邱华栋这个都市猎鹰者,又走进了历史。小说集《十一种想象》涉及楼兰古国的繁华寂灭、玄奘归来后上殿面圣之状、两幅韩熙载《夜宴图》的神秘去向、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传奇文采和命运、全真教道长丘处机西行赴约、明清易代后文人李渔的异彩纷呈的文化生活……其中既能看到繁花簇锦的文化,又能体会到幽深浮动的禅机。另一方面,作者的眼光还打量到了现代舒适生活中难以消化的那部分内容,《一个西班牙水手在新西班牙的纪闻》和《色诺芬的动员演说》等文本提示的是:“除去被海藻覆盖的时代,人类一直被自己的血和眼泪喂养而成长着。人类的本性中到底隐藏着多少只野兽,谁都无法从任何一部历史典籍中完全测知。”②邱华栋:《十一种想象》,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邱华栋用一个个复杂的人性切片把正史那些混沌凝滞的边缘处搅动了,由此历史生成了新的涡旋。
如果说中短篇小说的灵活篇幅足以容纳一个聪明作家对历史的奇思妙想和灵感偶得,那么从创作意图上看,作者对于长篇小说的用力、修补和自我阐释,应更能体现他的关注方向。2016年《时间的囚徒》出版后,前后花费十多年的“中国屏风”历史小说系列集结完成。在《贾奈达之城》《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等几部小说中,邱华栋选取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1947年英俄角逐的新疆形势、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巴黎的红五月风暴等。邱华栋不满足于攀爬经纬线的格子,还以时间的坐标轴横插进来,开始吸收历史,触摸一种陌生的东西。但据此判断这就是邱华栋创作中的“转型”依然为时尚早,我们暂且搁置这个问题,先把它界定成一次写作历程中的时间扩容。
早年间,针对城市文学和那一代新生代作家的写作问题,批评家黄发有曾这样刺穿他的精神困境:“邱华栋的写作是历史意识消失的断裂式写作,他不是将融注着历史性的当下作为透视人生繁杂体验的瞬间,而是在割裂历史性的前提下全面介入当下。……邱华栋的城市讲述是一种非连续性的写作,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观念消散殆尽,只剩下空洞得让人恐惧的现在。”③黄发有:《迷茫的奔突——邱华栋及其同代人的精神困境》,《小说评论》2001年第1期。时隔二十年,我们可以公允地说,20世纪90年代城市写作中的“非个人化”和“非历史性”是新生代作家的普遍症候。但不久后,从文学现场又传来了这样观察的声音:“从《贾奈达之城》开始,从前那个天真无畏的青年,结束了自己一段内心飘摇的历史,更加深沉、淡定,自然而又超然地走向了人生以及创作的新阶段。”①徐坤:《〈贾奈达之城〉:转向清寂的历史》,《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25日。以题材上转入“清寂的历史”为判断依据,这段话捕捉到了其写作航向标的浮游和摆动,也十分恰切地贴合了作者自己的生命历程。两相对照,邱华栋从一种没有纵深感的感官平面上立起来了,从浮萍一般的个人精神里挖出了时间深处凝结的莲蓬。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视阈中认识,那就是说,他将自己创作的来路扩张,将古典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意识作为写作资源,达到更远的向上接续。
二
在写作任何题材的小说时,邱华栋都调动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首先,得益于多年来的文学浸润,他熟悉各种文学流派和艺术思潮,甚至对于外国文艺经典中的声音与肖像了如指掌。他也许不那么“精细”,只在乎那一刻想要冲出口的声音——这在从立意到标点和格式都慢慢打磨的古典气质作家那里是不可思议的。正因此他也曾遭遇诟病,他太聪明了,仅需从别人那里引来一支细弱的水流就能推动自己的叙事。比如《夜晚的诺言》中几个小标题都采用了米罗的一些画作译名,并以文字诠释那些画作的精义。如果西方文学经典是邱华栋的开蒙导师,那么谁都能看见,这个学生在课堂上不知疲倦地做着笔记、课间与老师亲密互动、课余还反复揣摩,甚至每周都提交学习心得和练笔之作。不得不承认,邱华栋可能才是那个最合格的毕业生。
作为传媒和文化圈人士,邱华栋面对社会的各个角落张大了自己的触角,那些言谈和行走中的所见所闻皆点亮了一簇簇灵感的火苗。如果说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是本雅明意义上的闭门造车的产物,那么奈保尔《印度三部曲》与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则指示着文学半径中观察和记录的素材要素。海明威《永别了,武器》则与其战地记者的经历不无相关。以知识结构为支撑的向内探索的能力,与向外行走的能力一道,构成了当代作家的写作资源。因此,在他的都市小说中,有许多人指认出了熟悉的公众面孔或者具有争议的社会事件,比如“合法”寻租或非法代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唯有大海不悲伤》的三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登山者的经历疑似取材于著名诗人兼商人黄怒波,海外华人遇害的故事可能来源于耸人听闻的“黑色大丽花”等等。
再次,邱华栋也是一个文化修养颇高的研究者和博物学家。比如在写作《花儿花》(后更名为《花儿与黎明》)时,他边推动叙事边阅读多本花卉学书籍;在写作新疆题材小说时,他甚至买了本字典认真学起了维吾尔语;想象利玛窦的故事时,他不仅仅参考了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还研读了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为了写好历史小说《长生》,他的案头读物则变成了“法国历史学家格拉塞的《草原帝国》《成吉思汗》,以及《多桑蒙古史》、方毫先生的《中西交通史》、许地山的《道教史》等著作”②邱华栋:《长生》,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后记。。而创作《楼兰五迭》等西域背景小说时,他又购置了大量古代地形图,细心体会时间深处的沙舞风啸。
由此清理一番,我们可以大致总结道,邱华栋的历史小说有两种处理历史的方式。一种是实有其人,但小说中的故事都是根据有限的史料进行传奇演绎。比如《贾奈达之城》中的戴安娜是英国驻喀什领事馆领事夫人,她在日记中见证了边疆动乱;《骑飞鱼的人》则源生于A.F.LindLey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这一历史文献;《长生》是根据蒙元史、成吉思汗史传和丘处机的诗文为基础。与二月河、唐浩明、熊召政、孙皓晖等人的历史小说不同,邱华栋完全放弃了帝王和庙堂视角,他进行的是逆向和他者的透视。另一种写作方式是《时间的囚徒》这样的,依托着八国联军的史实。但是,该小说中的三代菲利普家族则是虚构和假设。该小说用父亲的说书口吻讲述第一代菲利普作为一定士兵来华的经历;又用女儿的亡灵视角,再现父亲在中国的七年劳改生涯;儿子则亲历了巴黎街头的风暴。莫言的《檀香刑》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为历史背景。这二者的相似点都是,选取一段耳熟能详的历史,却要对其间的人和事展开充分的虚构。那么,作家在面对史实的时候,应如何处理那些漫长时光里的故事资源和认识定论?
鲁迅的《故事新编》、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集》、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埃科的《玫瑰的名字》等,无不用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重新编排了历史,他们重新探讨了道德、人性、文明和制度等问题。福柯认为:所谓的流逝和发展都是人为的设定,历史叙述仅仅是权力的傀儡。海登·怀特创立“元历史”理论,他的理论革命性地让历史与文学最终合而为一,把客观、真实与想象、虚构的界限模糊了,一切的历史文本都成为文学的文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童的《罂粟之家》、叶兆言的《追月楼》、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之类文本的出现也对传统历史小说创作和阐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客观说来,这个创作潮流由于各种内外原因后继乏力,在短时期内的喷涌,无意间窄化了新历史主义的认知动能。这既是因为认知惰性作祟,也受到当时文学冲决一切的盲目膨胀的影响。
在今日我们“后见之明”地回溯一番,可以发现,现代主义的传入似乎遗失了一个环节:它用人的生理性来解释文化,却无法用文化来解释人和人的命运。比如,鸠摩罗什的高僧大德形象本来在《高僧传》中十分明确,但是在施蛰存那里,我们看见了信仰背后爱欲的一面。现代主义文学在80年代的大量译介和重新生成,加深了对人性图景的片面刻板印象:“性”是革命的最大动能甚至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方向。这虽然极大暴露了曾经被遮蔽在褶皱里的一部分人性,但是当欲望成为唯一的“人”的表征,历史本可以敞开的可能性则收紧了。
在邱华栋这里,人欲的一面似乎并未得到淋漓尽致的挥洒。此前的城市小说里,人欲既是正当的,又是背负了全部不正当性的载体。因此可以说,他对欲望有着复杂的态度,有时候颇显暧昧。但是面对历史的时候呢?他几乎把欲望全部纯化了,而且面对古代人的理解时,他将自己那点顽皮老老实实藏到了门后。在长篇小说《长生》中,邱华栋自述自己没有吴承恩的本事,所以无法形成天马行空的作品:“最后,我却老老实实地写了一部基本写实的历史小说,我是桌子上摆放着十多种如《元史》《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籍,以及各类能够让我标示丘处机西行路线的历史地图集来写这部小说的。而且,丘处机的诗词引文也是原文。丘处机和成吉思汗见面的谈话,我是按照耶律楚材等人的记载来翻译的。所以,我对这部小说并不是特别满意。”①陈元喜、邱华栋:《关于历史的想象是可以无比丰富的》,《青年报》2016年7月10日。如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求新求变,正如20世纪80年代黄子平留下的名言:“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因此,每个作家都使出浑身解数去摆脱“影响的焦虑”。邱华栋在这里之所以对自己不满,其实主要是一种未能创新的不安。他自认为在思路方面受限于传统,因此没有足够的光合作用去妥帖地转化这部分写作资源。
事实上,邱华栋并非没有能力裁剪历史视角。在《时间的囚徒》中,第三代菲利普走出了中国的领土空间,来到法国。以“在场”的形式正面经历五月风暴革命。异国血统和异国历史,其实是揭示欧洲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史背后的个人视角,又与中国的命运和当今世界格局的整体连接起来。如此看来,邱华栋将自己的思想倾向也即历史观,巧妙地潜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了。那么为什么在面对某些传统的时候,邱华栋的现代叙事技巧会选择性地失忆呢?
三
日新月异的当代生活中,人工智能不仅可以代替人去做容易损耗的体能工作,还涉及了新闻报道、作诗、谱曲、写论文这一类本被视为精神劳作的领域。事实上,有怎样的输入就会产生怎样的输出。只需要建立的数据库,人工智能就可以从中排列出词汇的奥秘和句法。与文本细读相反的,莫雷蒂提出的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其实正是许多社会学科已经引入的研究方法。比如在探讨“想象的共同体”时,本尼迪克特就运用了文化类型学理论,对他者文化进行遥读和整合。所以,机器的文化(文字)生产,在数字意义上就是对于材料的排列,在它那里,几千年的文明化约为一种平面的数据,失去了历时性。材料就是材料,不是一种历经时代的资源。
但是人的文明是怎样的呢?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①顾颉刚:《自序》,见《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2页。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但汉以后却把起源上推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也正如“小说”这个概念,是因为现代小说出现,上古神话、唐五代传奇、宋元话本,才被收纳到“小说”概念里。这就是说,我们如今接受的全部信息,都是在现代装置里的资源迭代的认识,它不是从古到今的顺时累积,更不是断裂的新世界产物。齐泽克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是说,与历史共时空的体验和文字,反而是进入历史的最佳角度。正如菲利普、黛安娜和LindLey从他者眼光来看待中国一样。
也是从这个角度上理解,我们才可以得知,为什么一个以虚构见长的想象力蓬勃旺盛的当代作家,会苦恼地认为历史材料限制住了自己,旧历史意识打败了新世界的资源和知识。艾略特曾经说,传统是一个巨大的结构,它促使你不断与之对话,不断消灭自己的个性,“要做到消灭个性这一点,艺术才可以说达到科学的地步了。因此,我请你们(作为一种发人深省的比喻)注意:当一条白金丝放到一个贮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瓶里去的时候所发生的作用。”②[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罗经国、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邱华栋2018年以来完成了三篇武侠小说,他写的不是刀光剑影阴谋暗杀的江湖,而是作为被庞然大物一般的儒家正史压抑掉的那个侠客行的道义世界,是正史背后那些明灭难辨的部分,那些支撑着正史“之所以如此”的地带。那是另类的历史。《听功》写的是唐太宗换立太子时期发生在宫内宫外的事情;《剑笈》的背景是乾隆修《四库全书》。但奇特的是,这些人的故事其实没有发生历史叙述的位移。比如《击衣》写的是刺客豫让的剑术,但他延续了《史记》和《战国策》等典籍里“豫让刺赵襄子”对豫让的历史定位——一个为知己者死的义士。
也就是说,当《大唐西域记》《西游记》《长征记》《中国札记》等一系列历史中的记录、想象、演义如山一般堆叠在面前,在传统认知和纷杂的材料,甚至于心灵中的道德律令都翻涌而来时,作家选取的是那个在情理、道理、伦理上都更有说服力的一方。
把自己摆入文化谱系之中,看似仅仅是一种对于传统的臣服,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当代社会发展状况的回应。而邱华栋在写作历史小说中感受到的苦恼,其实正是一种无法脱离开历史所植根于我们内心中的伦理传统的失败感。一方面,他们在迭代资源的滋养之中感受到无穷的丰富性,但对于整体性视野的本能运用,又让他们主动掐灭了旁支斜逸乃至故作惊人语的可能性畅想。几千年来,我们的文学中不断继承《史记》笔法和古典的伦理对位,不能说是历史有多么伟大,或者《史记》“无韵之离骚”的魅力起了决定作用。而是因为作为一种制度发明的现代文学,不断为自己制造一种对于传统的需求,且承担着处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危机的职能。
因此可以看出,每一种新生成的写作既增加了这一传统,实际上因为写作正在变成传统的内在物质,也就能够形成对于传统的微弱变形。希望通过回到所谓的源头去指认传统,则很可能仅获得一把生锈的铁锁,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因此,艾略特所说的、甚至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原则和美学原则之组合,才是真正重要的。
另一方面,在重新找到自己的语言这个过程中,许多中国作家都有着独树一帜的进展。比如李锐坚持方块字的风格,莫言“大跨步地后退”,金宇澄在《繁花》中形成了一种可以书面呈现的沪语。他们寻求资源挪用突破的努力,其实正源自于所谓的传统丧失的焦虑。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是被西方的字母语言强行地赋予的,句子里面复杂的逻辑关系逐渐形塑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也就是说,从最早将域外文学翻译到中国来的翻译家们那里,中国作家同时获得了最为层次丰富的写作资源,在快速传播的过程里,漫长悠久的知识、视野被压成密实厚重的资源层。当迭代的资源扑面而来时,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受惠尤多。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邱华栋的语言风格是如此硬朗结实,历史人物出场之时,他们并没有像许多仿古小说里那样操着古言古语,反而有着大量、内向的心灵独白。甚至都不是古代人口语中的白话,邱华栋让他们坚持着一种语法更工整的现代汉语。这样,语言的问题最终指向了伦理传统。比如在《击衣》中,豫让不愿意在别人如厕时动手,这一情节的描述正是整篇小说里的精华。因为这样的风骨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最为悲壮和有价值的一部分。正如刘大先评论的,虽然这导致提前终结了他个体的生命,但在生死存亡的场合坚守某种不合时宜的尊严,却是不可放弃的在文化传统中积淀成型的伦理传统。他们强大的精神漫过了衰亡的肉身,成为现实缺憾的一种替代性补偿。
在城市小说里,邱华栋描画的是社区群像和商业逻辑,但是在历史小说里,他更加注重于创造个人修辞,置身于一种他这代人成熟之后的、与传统对话的关系之内。他的叙事焦点其实并不需要区分是城市、还是历史,抑或是国境内外。因为他始终关注的是在现代背景下,自己那不断做着精神加减法的人格精神。历史小说是无所谓今日之新人和历史之旧人的区别的。因为他一直都是在迭代的资源和伦理传统中做着思考和取舍,都投射了现实指向和理想寄托。从这个角度来看,邱华栋的历史题材与都市题材小说实际上形成了对话关系,他的历史写作里其实与当下生活有很多摩擦。如果说,欲望式的简单阐释并没有冤枉了他20年前的文学风貌,他在当时那些呼啦啦腾漫开来的写作是虚伪的个人主义表达,那如今的这个深入历史的所谓“转型”写作,其实并不全是在表达对历史的想象,同时也是一份对于现代生活的建议和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