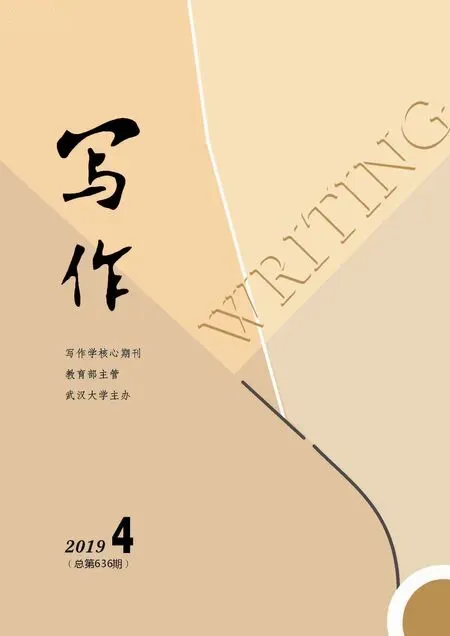对焦虑的克服:孙文波诗歌写作的意义
洪文豪
简略回顾一下中国现代汉诗的发生史,从第一部新诗集即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到不足十年后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对胡适的诘难,从新月派诸君对新诗的诗行诗形的探索,到后来普遍开始重新审视古典诗歌传统的再思考,乃至到后来民谣对新诗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汉诗的诞生与发展是伴随着强大的“歧义”与焦虑的。“歧义”在于新文体的塑造是历史进行时的,不可能是一言堂,诗人与现代汉诗研究者都面临着文体草创之初的自我抉择(诗歌实践与诗学等意义上)。这种不同的选择正是现代汉诗发生史蕴含着巨大张力的原因所在,其中自然又涌动着文学与话语/权力之间颇为复杂的互动。而焦虑则是更为整体性的,可以说,现代汉诗的历史就是一部诗歌的焦虑史。哈罗德·布鲁姆分析西方诗歌史时,把诗人与传统的关系主要看作是后来者对前辈诗人的影响的焦虑。而面对短暂的现代汉语诗歌史,一个显著的不同是,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焦虑并不凸显,或者说现代汉语诗歌自身并没有形成足够坚实的诗歌传统使得诗人与之暗暗较劲。现代汉诗的焦虑则是更深层次的,连接着文体本身的焦虑,其中又包含着诸多与之相关的诗学命题,比如现代汉诗的语言资源与对诗歌本体的反思、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态度等等。这些一直缠绕着汉语诗歌的问题,像守门者考验着每一个进入现代汉诗之门的诗人。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理解汉语诗歌、对现代汉诗的焦虑有深刻洞察的诗人,其诗作里必然隐约存在着某种焦虑的影子,更进一步,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诗人力图摆脱焦虑的方式。
孙文波在当代诗坛中很早就享有诗人盛名,但不得不承认对他的诗歌的研究却一直处于隐而不发的层面,或者只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获得讨论。而这明显与诗人的外在声名不相匹配。纵观孙文波的诗歌写作,我们可以发现,孙文波正是这样一位深刻介入当代诗歌焦虑感中的诗人,孙文波的焦虑嵌在被研究者认为“像树那样稳稳站立”①敬文东:《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的诗行内部。这种焦虑的层次感、丰富度绝少有诗人能望其项背。首先,孙文波对语言/叙述与真实、真切的生命体验之间的反思就可以放入诗歌焦虑释放的层面考察;其次,我们大致还可辨认出诗人鲜明的“创造传统”的诗学意识,诗歌创作的美学价值、思想价值与介入现实之间的“内在争吵”等等。正如诗人在访谈中自陈的那样:“我所有诗的完成,如果硬要说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下完成的’,我所能说的是,它们均是在对语言与认识方面的焦虑的克服状态下完成的。”②孙文波:《还有多少真相需要说出——孙文波访谈录》,张伟栋:《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6页。这给他的诗歌带来了某种口语色彩的哲思化,某种叙事性的繁复化。从他最新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体之杂合体》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诗人一以贯之的诗学态度与自我驳难式的焦虑感。这首现代汉语诗歌中罕见的长篇系列诗作几乎囊括了诗人所关心的一切诗学命题,以其繁复与醇熟成为诗人创作生涯的高峰,也是诗人迄今为止最具抱负与“野心”的作品。
一、语言的自审:如何进入真实
孙文波从80年代中期起一直笔耕不辍,被许多诗评家认为是越写越好。也许比对其具体诗歌评价更为重要的是,从同一位诗人跨越几十年的创作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变与不变?正如诗人张枣所说:“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关键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也就是在诗歌的程序中让语言的物质实体获得具体的空间感并将其本身作为富于诗意的质量来确立。”③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孙文波诗歌正是在 “语言本体的沉浸”中逐渐锻造出个体的诗艺。对语言的自审无疑是其诗歌作品重要的品质,在经历了写作的阶段变化之后(1997年),这种诗歌意识愈发鲜明,成为他诗歌写作一以贯之的书写意识与策略。
在孙文波写于1988年的诗歌《口腔医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
我由此想到了一些以说话为业的人:
政客、演员、教师和诗人。他们
中的一些牙齿并非有病,还能称作整齐,
一开口吐字清晰圆润。但他们却使
国家和时代患了病。使文字变得软弱和肮脏,远离了美……
诗人由去口腔医院的经历联想到时代的“口腔病”。这是一次颇为精彩但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联想与比喻。由个人推及时代,这是很能代表80年代的诗歌整体风貌。可以认为,梁小斌写作于80年代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开启了一种由具体物象出发指向大话语的诗歌写作策略,随后整整一个时代共享着相同思路的隐喻。这让人联想到雅各布森关于失语症的思考,他认为失语症有两个类型,一个是隐喻失序,一个是转喻失序。如果说90年代以后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界都为某种失语症而焦虑,那么,80年代一定不属于失语的年代,而恰恰与隐喻失序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隐喻的畅通无阻。正如雅各布森所说,这是一种深刻嵌入人类共同意识的想象模型,无对错好坏之分。但在文学审美和文学史意义上,我们可以探究这种流行模式为何流行,为何被某个时代的审美标准所推崇,以及这种联想背后的事物链接关系是由怎样的链条、怎样连接起来的。笔者认为,这种诗歌联想的前提是某种价值观的确定性,包括诗人对自身无论是审美抑或道德上的价值确认的确定性。诗人没有过多思考这种联想之间的关系(可能真实也可能虚幻)便不假思索地运用在一切事物上。到了90年代,诗歌开始进入到怀疑的领域,无论是所谓的个体诗学、日常审美,都是切断了这种不假思索的联系。
难能可贵的是,在同一首诗中,孙文波以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丰富了这种联想:
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又有谁是他们的
医生?我不知道。有人说是时间,
有人说是历史。但时间和历史怎能让发生了
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我于是不得
不笑那些这样说的人:他们不是医生。
他们的手中缺少器具。历史和时间
他们身在其中,已经是受害者。
在这里,诗人已经开始表达出对历史的抵制。可以说,孙文波的诗人气质在这里并不主要体现在那个口腔比喻中,而是体现在一种能一定程度超离当下,从自我体验切入更深刻的人类处境中去的品质。当然,如前所述,诗人还没有对诗歌想象策略本身展开更深刻的解剖与怀疑。
从收录诗人90年代诗作的最重要的诗集《孙文波的诗》中,我们需要特地把1997年提取出来作为孙文波诗歌风格变化的关键之年。这也是符合诗人访谈中对自我写作的体认①孙文波:《上苑札记:一份与诗歌有关的问题提纲》,《诗探索》2001第3期。。但我们也不得不坦认,这些诗作对于诗人的写作生涯虽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大多称不上诗人的杰作。在这本诗集中,诗人写于1997年的诗作被收录最多。我们稍做辨析便不难发现,这一年孙文波的诸多诗作都涉及了相似的主题。诗人在这一年对语言能否反映真实的问题尤其感兴趣,并且用诗作深刻检讨了之前的创作(《改一首旧诗》)。问题与方法是相互生成的,孙文波对真实问题的关注决定了他对诗歌的重新审视,以及由此推演出的诗人的诗歌方法论,这似乎又重新回到诗歌创作最初的问题,即诗人该如何创作?这也许是一个诗人写诗之前就已思考过的问题,又或者诗人之前并没有自觉的思考。那么,孙文波在这里把一个本应是写作之前的问题重新放置到写作当中,又意味着什么?
1997年的孙文波开始进入到对语言的自我审视之中。正因如此,一系列诗作如《他削尖了脑袋……》《慌里慌张》《阅读》《关于一部旧小说》等,都不免染上元诗的色彩。在这些诗作里,我们能看到后来被诗人本人认可的“虚无”的影子。诗人由一个词开始思索语言与真实的关系,或者从阅读经验中钩沉语言与记忆/自我之间的相互缠绕、消弭。《母语》中,诗人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运用产生警惕:
譬如现在,我准备写一篇讥讽练习
于是,“某X哪,他的皮鞋比他的
文章好。”“她修饰过的脸,让人想到
被拔光了毛的鸡”。我写下这些
完全不用担心别人不懂,我甚至
可以更“邪乎”地写下:“他的眼镜
是我们时代的陷阱”。“他是
一头革命的公牛,正处于发情期”。
……
写下它们,写下它们,在写的过程中
我体会到了快乐。我知道,母语
它不会把我当做它的敌人,使我
尴尬。“噢,这个丫挺的霜雾弥漫
的早晨;噢,这个锤子和镰刀的早晨”。
这不禁让人想到那个维特根斯坦式的疑问:是我们在说语言还是语言在说我们?诗人警惕的是这些语言“不过是傲慢的修辞术和技艺的工匠气”(《改一首旧诗》)。它们无法满足诗人想要竭力贴近事物真相的要求,只会满足写作者的虚荣心。它们就会变成罗兰巴特所言的“我们几乎不能再谈论一种诗的写作……语言自足体的暴力,它摧毁了一切伦理意义。”①[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诗人在这里毫不讳言得向我们展示了他新的方法论:
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
像“摇晃的公共汽车。”或者“大雪天
冷得人要死。”它们似乎十分平淡,
但只要安排妥当,就会产生惊人
的力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联想到同样写于1997年的诗歌 《成都》,诗人最后向自己抛出的那个疑问:“我还能在哪里找到/我需要的,进入……一座城市的……途径?”②孙文波:《孙文波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在这里袒露了自己思考如何进入真实的焦虑。而其实,这更是在语言的意义上,诗人对如何用语言开始这趟真实之旅的焦虑。对语言可能滑入看似耀眼实则空洞的警惕,对某种日常的、叙事性语言的主动敞开是一种基于语言表达的解困。
讨论到这里,我们已经能更为准确地理解诗人以后诸多作品的诗歌策略。以《与……有/无关》为题的作品,诗人作了20余首;《临时的诗歌观》有10余篇,还有一系列《从……一词开始的诗》等等,诗人立意要用一种顽强的“方法论”来代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偶然灵感。从某一个词进入,从语言的自足与不确定性中进入诗歌冥想,诗人的探索为我们刨开了作为表象的世界(叔本华意义上),在这里,语言与生命体验之间有着重重纠缠的关系。诗人首先必须突破语言的迷雾,尽管就连这可能也仅仅是一个幻想,但从认知迷雾的方向开始进入真实是孙文波始终坚持的诗歌立场。孙文波的元诗热情,既是在抵制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语言,也是一场个人诗学的自我清洗。在对语言本体的反思中,我们看到了孙文波的许多诗歌是在对语言本体焦虑的克服中写作出来的。
二、创造传统:一份诗学宣言与实践
艾略特说过:“诗歌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表达感情和感受。与思想不同,感情和感受是个人的,而思想对于所有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用外语思考比用外语来感受要容易些。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③转引自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对于现代汉诗更是如此,这不仅仅是艾略特所言诗歌与民族传统的紧密联系使然,更因为传统是新诗不断探索的历史过程中必须要借鉴的文化资源。任何一个诗歌态度纯正的当代诗人都必须面对如何与传统对话的问题。对于诗人孙文波而言,思索传统与当下诗歌写作的关系既是一份诗学宣言又是切实的诗歌实践。
在他最新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之八》中,有这样一段诗句:
就像国家找不到自己的魂——
发展经济,房屋建了拆拆了建,事物的保存,
在经济增长的计划中面目全非。以至于一座城市
除了名字还是旧的,早已经成为另外的一座城市。
家国也是另一个了。如果我们还假装
自己是古老民族的后人,身体内还携带着很多
过去;它的骄傲,它的优雅。已经成为
死亡的文字——书写,不过是与痛哭一样的行为。
诗人哀悼城市的面目全非、民族传统血液的流逝,最后又回到书写的问题。“书写,不过是与痛哭一样的行为”,诗人在此直露出他的悲观与虚无。但事实上果真如此吗?没那么简单。孙文波的无是一种无中生有。正如加缪表述过类似的观念,认识这个世界是荒诞的,这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孙文波写作长诗的努力就可以首先视为“反抗虚无”的行为。诗人无法直接改变社会,但可以从语言的砥砺中抵达一个民族的深处。
基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孙文波在多篇诗论文章中谈到传统与现代诗的关系。他对回归传统的坚定态度和定义传统的开放性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不管是“中国性”也好,传统也罢,孙文波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绝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方面,从古典诗歌谨严的格律到新诗相对自由的诗歌形式,古典诗歌传统似乎成为某种回不去的乡愁。但另一方面,无论古今,形式皆有通变,诗歌始终想要传达出个体隐秘的精神空间,而从这种隐秘中又能窥探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基调。总的来说,诗歌的形式与内容从来都不是分裂的,而是在整体上融汇成一种圆融的诗歌精神。因此,无论是微观层面上现代汉语诗歌对古典诗歌字、词、典故的借鉴,还是思想方式与古典精神空间的反顾,孙文波想竭力打开的,或许正是这条现代汉语诗歌与古典诗歌之间需要被不断创造出的通道。
孙文波说:“传统不是历史事件的总和,不是已存的人类历史典籍,传统是一种精神。”①孙文波:《在相对性中写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正是这样,孙文波才展现出作为一位严肃的现代诗人对现代诗面对“传统”的焦虑上既清醒而豁达的认知。他认为传统的价值在于对我们当今能有所借鉴。传统不是像一块僵硬的石头,我们只需要把传统搬过来就行了。“没有‘此时’的需要,或者不能为‘此时’需要,传统的意义何在,它能够存在吗?我们难道不可以说传统是被需要创造出来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对继承传统这样的看法不以为然。我宁愿认为传统是被‘此时’创造出来的。”②孙文波:《上苑札记:一份与诗歌有关的问题提纲》,《诗探索》2001年第3-4辑。前面也提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包括诗人都感知到某种“失语症”的文化症候,继而一些人又提出“中国话语”“中国学派”的命题。暂且抛开个中争议,孙文波以一个诗人的视角为我们描述了这个问题被人们忽视的一个侧面:“如果真要强调 ‘中国性’,我宁愿将对‘中国性’的强调看做是对‘中国问题’的追寻,即在什么情况,什么意义上,文学解决的问题是迫切的,对一个民族而言是需要的。”①孙文波:《在相对性中写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这也就脱离了把继承传统视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一分为二的庸俗理论怪圈。孙文波以这种变通的态度对传统作出一份宣言的同时,他的诗也成为将古典传统创造性融入此在的诗歌实践,毫无疑问对现代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探索性。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的副标题为“感怀、咏物、山水体之杂合体”。感怀、咏物、山水诗是古典诗歌最常见的题材。“情往似赠,兴来如答”②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古典诗人常常需要面对自然才能打通自己的生命体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③陈子昂:《陈子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2页。,在咏物、山水的背后是诗人面对浩瀚宇宙时的恍然与悲慨,一种无法言说的失语状态。也许有人说这样的诗其实在古典诗歌中并不常见,咏物、山水诗更多是一种单纯描摹外部世界的感怀之作。但联系到孙文波对传统的真知灼见,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传统不是单一的,而且是需要被我们反复激活的。孙文波的这组长诗,如果说在诗歌形式上并无多少继承传统,那我们应该注意到,诗人看到古典诗歌中那种从人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中感物体物的精神。因而,副标题看上去像是对古典诗歌的一种戏仿,实则饱含诗人“创造传统”的良苦用心。
这是普遍发生的事。正是这样,入目所见
无论是琼楼玉宇、卧虎坐狮、舞伎乐工
还是黄金面具、玛瑙凤冠、经文碑刻,都是
权力的隐喻。我不得不想到,权力代替着美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之三》)
所以那些托孤,断桥之吼;那些割袍绝义,
我只能当戏剧观看。八百壮士,百万雄师,
也没有换来一个更加干净的世界。
这种事,就是再问一万次天,仍然得不到答案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之八》)
诗人在诗中“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④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把关于历史与现实、个人与民族的思考融汇在变幻莫测的笔记体诗歌中。就如同长途汽车上的蜿蜒颠簸,整组诗歌都显现出一种绵延、繁复的哲思化风格。诗人在行旅之间不断叩问历史/时代的大命题,也在不断地叩问着自身:
也是暗示;暗示我已经很难设计自己的未来
我不想模仿晚年的杜甫。但我很可能
必须像他一样,不停地从一地漂泊到另一地
不得不接受“青山处处埋钟骨”的宿命之命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补遗》)
现代诗人郑敏曾在多篇文章中表达了新诗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摒弃与盲视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断裂。面对这种断裂的焦虑,孙文波的诗学态度无疑是充满智性与豁达的。即使郑敏也认同:“德里达将一切广义语言归结为‘心灵的书写’,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的源泉,有谁能以命令来喝令它改变呢,然而它在历史中会依照自己的意愿不断地变化。”⑤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在孙文波的诗歌中,语言与形式的传承在更大意义上被置换为历史性与当下性的双手互搏。这种看似身段轻巧地一跃却使诗人获得了另一份沉甸甸的力量。在书写的“痛哭”之后,诗人始终在思接古今中锻造一种历史的想象力。
三、慢与问:诗歌与时代的“内心争吵”
贫乏时代,诗人何为?荷尔德林似乎抛给了诗人们一个永恒的疑问。诗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孙文波思索的诗学命题。叶芝说过:“我们从与他人的争吵中造出辨术,而从与自己的争吵中造出诗歌。”①转引自张桃洲:《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叶芝启示我们,这种思索绝不是诗人站在诗歌外部进行议论,而是诗歌原初的书写焦虑,是一种诗歌的“内在争吵”。当然,不要忘记,在我们进入“诗人何为”的思索之前,荷尔德林以自己敏锐的心灵发现了时代的贫乏、诸神的黄昏。孙文波无疑具有相同的气质,在同样是写于1997年的《南樱园纪事》中,诗人这样写道:
“告诉你吧,我虽然离这个国家的中心
近了一些,却感到它更加陌生。”
“使我不能想象的是,为什么,即使
出入于文化人中间,感到的仍是
知识的贫乏”
这是贫乏在诗歌中的显影,但是更多时候,对贫乏的感知犹如一块影幕是诗歌的整体氛围。贫乏有时候转化为一种无力感,诗人把握事物的无力感在诗中成为另一种焦虑。
诗我当然还是在写。只是越写越怀疑
在这边政治的国土上,我的笔到底
能指向多么远?而历史的重负,又有多少
应是诗必须承担的?了解到它有多少官邸
多少错综复杂的机关,我更加觉得
倘若写诗是我注定的命运,那么,
这样的命运一遇上高大的官墙就会碰壁
(《给小蓓的骊歌》)
一直到现在,这仍是诗人诗歌中最明显处理的主题之一:
我们是在修辞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人
祭坛上,放不进国家、阴谋、人生变更。
甚至也放不进股票、石油,和房价。
激情澎湃,拳头打棉花,才是现象之秘密。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之一》)
那么诗人真的只能在语言的狂欢中随意沉浮吗?至少孙文波是不满意的,“而今天,中国的诗人却成为了自己国家的政治、文化领域里的边缘人物,我们几乎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去,更没有发挥出哪怕一点能够影响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进程的作用。想起来,这不能不是悲哀的。”②孙文波:《孙文波访谈录(答韦白22问)》,新浪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cc3b70102er1d.html,发表日期2014年3月18日。诗人该如何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或许我们从孙文波诗歌中的两种姿态可以管窥一二。
慢,孙文波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自己的慢,这种慢不是生活节奏上的,而更多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慢恰好给了诗人稍稍脱离时代的观察视角。当然,完全脱离是不可能,也是诗人不赞成的(这一点,诗人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诗中孙文波这样描述自己的慢:
而我仍是埋头苦读,从莱布尼茨的
《中国近事》直到九七年新版地图。
但就是这样,还是赶不上流行的速度,
这里的人早已成为福柯和德里达的信徒,
(《给小蓓的骊歌》)
——我,一个慢人,喜欢悠闲生活;
就像上百年的树,生长的变化不易察觉。
(《在成都宽巷子喝茶》)
诗人的慢,是沉入心灵思索的必要准备,也是诗人不随波逐流的支点。这给诗人的作品带来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冥思性,包括诗人在诗中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严肃思考。我们可能很难找到诗人与外部变动的联系(不能否定没有),但不难发现诗人自我诗歌的生长逻辑;二是私密性,诗人竭力在诗歌中重新唤醒自我的生命体验。所以我们看到诗人描述自己的时代时,恰恰不是用最易于理解的公共话语资源,而是从自我最隐秘而真实的生命体验中攫取。这正是诗人《六十年代的自行车》系列诗作中具有的优秀诗歌的品质。也是慢赋予诗人的气质,我们可以称为慢的辩证法。
问,笼统地说,现代诗人不可能像古典时代那样写诗,是因为现代诗人心灵中的确定性早已被打破,诗人的疑惑无时无刻不在咬噬诗人自身。现代诗人笔下的山水再也无法与谢灵运、王维媲美,诗人的笔也难以满意地划下一个个的句号(虽然古典时代也有诸如屈原的《天问》、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作品,但与浩如云烟的古典诗歌相比,比例少得可怜。)。但我们注意到,遍布孙文波诗中的问句已然成为一个具有精神分析色彩的现象。一方面,这当然来自他谨慎、谦和的诗人气质,不愿草率地书写。更重要的是,他是有意识通过疑问来达到诗歌体认事物的纵深,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看到正是疑问推动了诗歌的“叙述”。
他是一只喜鹊。这样一句,
是不是诗?如果他可以在天上飞,
或者,看见他筑巢细细的树梢上
这是不是诗?
(《夜读韩愈》)
如此一来所谓的思乡、怀友、吟咏河山,
需要另外的解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真的淘尽了么?民族的潜意识,到底
存在着什么?作为问题,是不是由这样的东西灌注?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之八》)
孙文波的诗,可以从焦虑说起,但又奇妙地丝毫没有陷入焦虑的沉滞感中。作为诗人,孙文波身上有某种当代诗人少见的沉着与执拗的气质,这不仅体现在他对诗歌创作的坚持上,更体现在他执着于不断探究诗歌与外部关系的诗学追求上。这两点都和他敬佩的诗人杜甫颇为接近。由此,诗人与他那位年代相隔遥远的半个同乡之间获得了某种精神联系。当然,我并非认为这两者之间真是因为什么同乡的精神传承,这是诗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另一位深深影响孙文波的诗人是波兰诗人米沃什。并不意外的是,这位伟大的波兰诗人曾经也对自己提出过“诗歌是什么?”的疑问。但我们应该看到,米沃什诗歌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把展现心灵与记忆的诗歌艺术与迫切的现实互相敲击,展开内心的驳难。这种剧烈的摩擦才能迸发真实的诗艺,因而也才能成为“诗的见证”,而不是别的什么。诗人希尼评价米沃什的诗歌时说道:“他的诗歌承认主体的不稳定,并一再揭示人类的意识,指出它是互相争夺的话语的场所,然而他不会允许用这些承认来否定绝不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退缩这一古老训令。”①[爱尔兰]谢默斯·希尼:《希尼三十年文选》,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46页。如今这个不稳定的主体搭乘孙文波的“长途汽车”再次出发。
纵观孙文波的诗歌实践,似乎他经历了一次诗歌的“正反合”过程。诗人经过对语言的反思,最终并没有走向一种虚无主义,而是让一种元诗意识更为深刻地扎根在诗歌的根茎之处,对现实与个人经验的书写始终成为其诗歌显在的主题。这是诗人在价值多元的后现代境遇与波谲云诡的中国场域中对诗歌缪斯的持续追寻。孙文波的诗,在主动介入焦虑的过程中,展现了现代汉语诗人卓越的诗意突围能力。也许,诗人永远无法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终极答案,他的诗歌仍然会继续抛出一个个疑惑。同时,这些疑问也迫使读者随着诗人的脚步“慢”下来,并不断给予我们更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