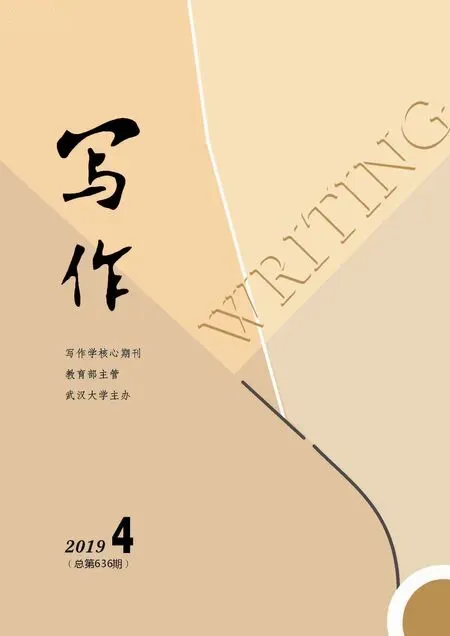“新浪潮”的“旧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的冷战书写
陈 韬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等科幻作家逐渐活跃,中国科幻写作开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并在这次被称为“新浪潮”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被称为中国“新浪潮”(new wave)科幻,是宋明炜借用英美“新浪潮运动”的概念,以指称这一时期打破传统文类成规、具有先锋文学精神的科幻写作。详见宋明炜:《弹星者与面壁者 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宋明炜、樊佳琪:《科幻研究的新大陆》,《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3期。本文认同这一界定,并将“中国新浪潮科幻”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视为同一概念。的繁荣中孕育出了既迥异于以往的中国科幻传统、也区别于同时期中国文学主流的写作特质。对于这种写作特质,已有不少学者进行分析,如宋明炜认为新浪潮科幻明显有别于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初期的科幻,而后者“几乎等同于面对儿童写作的科普文学”②宋明炜:《弹星者与面壁者 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任一江则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科幻具有“人类文学”“科技文学”“观念文学”“推演文学”四副面孔③任一江:《文学新境与审美路标:论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的四副面孔》,《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这是其与传统文学不同的特征。这些分析各自揭示了中国新浪潮科幻的部分特质,使该领域的研究有所推进;不过,上述研究还远未穷尽这一时期中国科幻写作的不同侧面,其更多面貌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在笔者看来,冷战话语在科幻文本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这是中国新浪潮科幻写作的一个重要特质,尤其是其异于同时期中国文学主流的特质。从社会主流文化背景来看,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与美、日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打破对立局面,70年代末又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苏东剧变,国内启动市场经济建设,可以说在中国科幻开始产生新变的时间节点上,主流文化已经彻底走出了冷战时代的话语场。从国内主流文学氛围来看,“文革”结束以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已经开始了对冷战时代的批判,其后的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将文学话语的演进由“反冷战”阶段推进到了“非冷战”阶段,主流文学写作对冷战话语的抛弃甚至还要早于主流文化环境。在这样的主流文化背景和主流文学氛围下,新浪潮科幻对冷战时代“旧话语”的大量书写便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反常”现象。基于此,本文将梳理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写作中具有典型冷战色彩的作品,勾勒其作为冷战话语载体的大致面貌,并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冷战话语”这一术语并非成熟的文学或文化学概念,以往涉及到冷战话语的讨论往往限于政治学范畴,因此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内涵上的界定。在笔者看来,所谓“冷战话语”,是指冷战时代(二战后至苏联解体前)特有的文学话语,它在旨趣上与后冷战时代的话语相对立。换言之,凡是那些能够让读者暂时脱离后冷战话语环境、重新进入冷战时代话语场的话语,都可以被称为“冷战话语”。在中国新浪潮科幻中,冷战话语大量存在,其书写方式主要有两种:冷战的全景书写和冷战的意象书写。
一、冷战话语在新浪潮科幻中的两种书写方式
(一)冷战的全景书写
全景书写是冷战话语书写最为直白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设定在各种幻想环境中的“冷战”成为科幻作品书写的主要对象。在这些作品中,“冷战”往往表现为两个世界的对抗,对抗导致了世界的隔绝和相伴而来的人性嬗变,而这些都是冷战话语的经典表达。如陈楸帆的《过时的人》描写了三百年前的“旧时代”与三百年后的“新时代”之间的对立,借助主人公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异化的世界;台湾作家黄海的《地月脐带》表现了地球社会与月球社会的对抗,地月脐带的碎裂、战争的爆发和宇宙中其它文明的作壁上观,无疑是“亚细亚的孤儿”在冷战中的写照;韩松的《冷战与信使》则不再满足于隐喻,而是对“冷战”进行了直接的、宏观的呈现,其与历史真实的“冷战”唯一的不同只是发生于浩瀚星际。
在全景展现冷战时代方面,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显然更具篇幅优势。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降临派、拯救派与幸存派,面壁者与破壁人……一组组对立关系勾勒了中短篇小说难以呈现的“冷战”面貌。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开篇便设定在“文革”年代,主要人物叶文洁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转而投向三体人的怀抱,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三体》系列故事,这为刘慈欣笔下的“冷战”注入了色彩浓厚的中国元素,使《三体》的冷战话语书写更加丰富多义。
在新浪潮科幻对冷战的全景书写中,还出现了一些较为特殊的作品,它们的冷战话语书写也是全景式的,却不直接表现冷战,而是从冷战的反面切入。比如赤色风铃的《精英酒吧》,虽然没有明写两种世界形态的对抗,只虚构了一种单一的社会形态,但文中描绘的娱乐至死的社会氛围和“人类代表”陈一在弱肉强食的“精英酒吧”里不堪一击的表现,恰恰构成了对“美丽新世界”的绝妙讽刺(尽管《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三部曲”均诞生于二战前,但考虑到它们在冷战时代的深远影响,完全可以被视为冷战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陈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典型的后冷战社会,而作者在对这个后冷战社会的否定中凸显了冷战的话语威力。
相对于《精英酒吧》,星河的《非理性时代》在书写冷战话语方面似乎更为高明。从叙事的表层来看,这篇小说照见了“动保”“植保”等环保主义异化形态的现实与未来,关注的是后冷战时代的社会话题①关于环保主义异化的现象,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曾有著作论及。克劳斯援引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特内德斯的观点,指出“在1990年和2007年之间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即环保主义发生了异化,详见[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力》前言,宋凤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14页。尽管环保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寂静的春天》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但环保主义的异化主要发生在后冷战时代。而具体到动物保护(尤其是伴侣动物保护)这一特定的环保主义异化形态,其产生、传入国内并具备社会影响更是在21世纪以后。因此笔者将环保主义异化视为后冷战时代意象。。但在它的深层叙事结构中,“动保”与“植保”之间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显然是对“五四”与“文革”的隐喻,整篇文章几乎是对20世纪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再现。高呼口号的青年运动,气氛狂热的批斗大会,“给花下跪”的荒诞戏码,乃至“老动”“老植”等暗示着阵营与资格的称谓,都令读者对冷战与“文革”的时代产生了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在这篇小说中,星河将后冷战时代披上了冷战话语的外衣,在揭示后冷战时代的脆弱与虚妄的同时,也进行了“冷战并未远去”的沉思。
(二)冷战的意象书写
相比全景透视,中国新浪潮科幻在表达冷战话语时更多的是借助冷战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某个文学意象来书写。笔者认为,种族、阶级、战争和拓荒是新浪潮科幻写作中四种典型的冷战文学意象。这四种意象的产生与冷战时代特殊的社会现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写作对这四种意象都有所涉及。
首先,冷战时代涌动着第三世界国家独立与解放的浪潮,也涌动着欧美社会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浪潮,殖民主义的阴魂与新殖民主义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冷战时代;而在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已经基本完成,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正确”在欧美社会内部也得到了承认,种族话语在全球范围内被淡化。因此种族意象应当被视为冷战意象的一个典型。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写作中,陈楸帆的《仰光在燃烧》《巴鳞》,陈茜的《最高价猎物》,阿缺的《与机器人同居》都是运用这一意象的成功范例。
在所有运用了种族意象的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韩松的《红色海洋》。如果说刘慈欣及其《三体》分别是中国硬科幻作家和长篇硬科幻小说的代表,那么韩松及其《红色海洋》就是中国软科幻作家和长篇软科幻小说的代表②从韩松的科幻文学评论中也能看出,他是以软科幻捍卫者自居的,故而会有《危险的硬科幻》《坚守软科幻的最后防线》等评论文章,参见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诚然,以《红色海洋》的篇幅和它所描绘的宏大叙事,“种族意象”远不能从理论上覆盖这部小说,但这并不妨碍种族意象成为这部小说中举足轻重的构成元素。在小说的开头,刚出生的海星便目睹了母亲与来自另一种族的“银色男人”交媾的场景,后来他又经历了“银色皮肤的孩子与红色皮肤的孩子”的争斗,掠食族对白水族的围猎、对女丑族的偷袭、与反抗联盟的战争,在难以计数的海洋异化人种间周旋,可以说种族意象支撑起了小说的第一部分。后三个部分中,种族意象虽不再如此密集,但也贯穿始终,比如机器人与水栖人的对立,日本制造水栖人时的“大和种”执念,怀特人与地球原住民的矛盾等等。除了以叙事方式呈现外,韩松还以他的独特风格,对种族意象进行了更直白的揭示:
“我是人,却又不像人。”
“为什么?”
“因为我离开我的族群了。……”
“……我们也是扎堆儿生活在一起的,但不是一个族群。这也是人。但我们也不像人了。”
在这里,“人”的概念是与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是因族群而得以成立的。这段对话表明,《红色海洋》不仅制造出了丰富的种族意象,并且在运用种族意象方面是具有自觉意识的。
其次,在以意识形态对立为首要标志的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话语较量贯穿始终;而在后冷战时代,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中产阶层”概念在国际上扩展开来,阶级话语也逐渐淡化。因此,阶级意象也不可避免地与冷战时代捆绑在一起。刘慈欣的《中国太阳》可以说是使用这一意象的典型作品。王瑶(夏笳)对这篇小说的解读值得关注,她认为刘慈欣通过强调身体与“技艺”,表达的是类似“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阶级话语,是对后革命时代“阶层”话语(精英管理者——底层劳动者)的挑战和颠覆;水娃最终的选择也是对当下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的挑战与超越,是“一种在后革命时代受到压抑的乌托邦冲动”①王瑶:《从“小太阳”到“中国太阳”——当代中国科幻中的乌托邦时空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4期。。这种解读与宋明炜对刘慈欣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反,后者认为“刘慈欣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严肃的精英意识”②宋明炜:《弹星者与面壁者 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应该说,宋明炜的分析是对刘慈欣的一种误读,他将思想性等同于精英性,却忽视了刘慈欣小说中带有反精英色彩的阶级意识。
除《中国太阳》外,刘慈欣的《赡养人类》,赵海虹的《南岛的星空》,陈茜的《火星人临死前说了什么》,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韩松的《乘客与创造者》等也都在文本中充分运用了阶级意象。
再次,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冷战时代全球局势呈现出总体冷战、局部热战的特点;而在后冷战时代,尽管局部热战仍时有发生,但随着全球局势的整体趋缓,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占据了上风。因此,凸显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对立与冲突的战争意象也是冷战意象的重要分支。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写作中,星河的《你不曾沉没》,韩松的《世界清除员》,陈茜的《探梦人》,杨贵福的《我的外骨骼,诺基》等都是典型的战争意象作品。其中《世界清除员》最具代表性,它在表面上采用了荒诞不经的后现代叙事风格,实际上却处处显露出冷战时代经典的战争话语:“泡沫世界”与“非泡世界”的对立,世界的“真实和正确”,“打黑”行动,男主角在结尾说出的“打游击”和“荒郊反攻家庭”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战争意象都可以算作是冷战意象的分支,有些科幻作品中的战争意象完全是后冷战的。比如在刘慈欣的《光荣与梦想》中,战争不再具有两个世界对抗的背景,而是抽象为一个难以消除的恶的符号,整篇小说对战争意象背后的深刻内涵缺乏解析,沦为了后冷战时代反战情绪的注脚。但《光荣与梦想》这样的作品终究是少数,作为冷战书写的战争意象在新浪潮科幻中占据着主流地位。
最后,作为人类开发陌生空间的活动,拓荒在冷战时代达到了一个高潮,美苏的太空竞赛、苏联对西伯利亚的开发、中国的三线建设和上山下乡运动都是拓荒意象的时代注脚;而在冷战结束后,这几种拓荒活动都已放缓节奏乃至停滞下来。因此,拓荒也应当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冷战意象。在这方面,苏学军的《火星尘暴》和《火星三日》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讲述了火星考察站因“火星蘑菇”的意外发现而陷入缺水危机的故事,表面上看更接近灾难叙事,但结尾地下水源的发现和“他仿佛看到一座人类的火星城市正从那里崛起”显示了小说的拓荒主题,秦林等人的牺牲也是拓荒题材中的常见桥段;后者则描写了火星基地里那些被地球人遗忘的蛮荒、艰苦与集体主义,这不仅是对逝去的红色年代的象征,也是对这些在新时期被淡化的记忆所作的缅怀。
拓荒意象也从距离冷战不远的90年代和世纪初一直延续到了2010年代,阿缺的《我讲我爷爷的故事》近乎精确地表现出了拓荒年代的短缺与失序,以及这种短缺与失序之下的人性,整篇文章历史色彩浓厚,农田改造、生产队、饥荒和“知识青年下乡扎根”……集合了这些要素的故事发生地“芜星”几乎就是冷战时代拓荒农场的翻版。
二、冷战书写在新浪潮科幻中大量存在的原因
以上的梳理很难说展现了本文研究对象的全貌,但至少足以说明,冷战书写的确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中大规模地存在着,不仅有冷战时代的全景书写,也有种族、阶级、战争、拓荒等诸多冷战意象的书写。尽管略显沉重的冷战书写并非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写作的唯一特征,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也涌现出许多像《关妖精的瓶子》这样轻俊灵巧的作品,但新浪潮科幻对冷战这一旧话语的大规模接纳却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而这在同一时期的文学类型中是独树一帜的。那么,为何科幻文学领域产生了如此特殊的现象?
以往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但往往是聚焦于某些作家个体。比如王洪喆指出,冷战与“文革”是“二十世纪内部尚未被打开的时空褶皱”,而刘慈欣恰恰从“二十世纪的动荡、匮乏与超越性”中开掘出科幻道路,展露了它们的复杂面貌,堪称“冷战与‘文革’的孩子”①王洪喆:《冷战的孩子——刘慈欣的战略文学密码》,《读书》2016年第7期。。就以作家个体为对象的考察而言,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亲身经历过冷战时代的作家,刘慈欣对冷战话语无疑较为熟稔,而娘子关电厂较为封闭的工作环境又使其冷战记忆得以“保鲜”。然而,一旦观察对象扩大到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写作者群体,这种阐释视角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了。它无法观照“更新代科幻作者”②董仁威、高彪泷将清末以来的中国科幻作家群体划分为原生代、中兴代、新生代、更新代和全新代,详见董仁威、高彪泷:《中国科幻作家群体断代初探》,《科普研究》2017年第2期。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篇文章的划分方法,这里为了论述方便借用了“更新代”的称呼。那些充斥着冷战意象的作品,比如陈楸帆、郝景芳这些未曾经历冷战时代的“80后”的作品;也无从解释为何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稀释了刘慈欣个人因素后仍表现出了浓重的冷战时代的风格③从创作者方面来看,根据电影官方海报,《流浪地球》有8位编剧且多为“80后”,而“60后”刘慈欣位列最末;从内容上看,电影对同名原著的吸收主要在于故事背景,具体剧情基本属于原创。另外,在中影指数对该片编剧严旭东的专访中,严旭东称原著作者刘慈欣 “一直以来对我们剧本创作都给了极大的自由和创作空间”“所以他没有过多地干涉我们的创作”,详见《对话〈流浪地球〉编剧:改编之路困难重重》,搜狐娱乐,网址:https://www.sohu.com/a/294683443_810093,发表日期2019年2月14日;新浪网文章《关于〈流浪地球〉,你需要知道的50件幕后故事》也称刘慈欣未去过《流浪地球》片场,详见新浪娱乐,网址:http://ent.sina.com.cn/m/c/2019-02-08/doc-ihqfskcp3748358.shtml,发表日期 2019 年 2 月 8 日。 可以说,一方面,作为电影文本的《流浪地球》弱化了刘慈欣的个人色彩,该电影文本的写作基本上是由一群“80后”主导;另一方面,电影文本中的集体主义叙事和苏式工业画风又显示出鲜明的冷战风格。。
对作家的个体观察无法揭示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的整体面貌,而一些看似较为全面的探讨有时也未免偏颇。科幻写作的话语体系——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话语体系整体“落后”于时代,为主流文学所排斥,这似乎印证了吴岩关于科幻小说的论述:“科幻小说其实是科技变革的时代里,受到各类社会压制的边缘人通过作品对社会主流思想、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所进行的权力解构”④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但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它一方面忽视了科幻作为一种写作类型的整体面貌(即科幻写作并非只是边缘话语的注脚,即便其中的冷战意象也并非只具有边缘性),另一方面又模糊了科幻与其他非中心化的写作方式之间的边界(其他文学类型,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对“边缘”的关注并不逊于科幻作品)。换言之,吴岩的观点只是对文学“边缘性”的笼统总结,科幻之为科幻、科幻之区别于其他写作方式的独特性,并没有在这种论述中体现出来,中国新浪潮科幻对冷战书写的情有独钟也就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写作之所以大规模书写冷战,是因为科幻这一文类本身就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冷战性”。中外学者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分析早已揭示了这一点,如达尼埃尔·鲁瓦约所说,科幻电影根本就是一个冷战类型,“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搬到了集体的想象之中”①[法]达尼埃尔·鲁瓦约:《好莱坞》,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1页。;有学者甚至认为,后冷战时代的科幻电影也与冷战时代一样具有意识形态功能②王垚:《邓肯·琼斯:后冷战时代的独立制片科幻电影》,《当代电影》2013年第1期。。由于书写内容的相似,“冷战性”不仅存在于电影工业之中,也存在于其他科幻写作文本之中。因此,冷战书写并非是简单的个体经验的投射,也并非是某种边缘话语的言说,而是基于科幻写作特性的书写。换言之,正是科幻写作以其类型特性为冷战话语提供了叙事出口。从这个角度看,冷战话语在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写作中的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科幻写作是如何与“冷战”这一明显带有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因素联系起来的呢?在人们的印象中,以科学原理为圭臬的科幻写作在文化和价值领域本应是“中立”的,甚至本应比其他写作类型更中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上述学者虽然揭示了科幻写作与冷战紧密相连的现象,但并未深入挖掘其内在原因。在笔者看来,要解释这一问题,需要追溯到科幻这一文类的源头;这种追溯触及了科幻写作的类型特性,也反映出当下中国科幻的发展方向,即回归世界科幻写作主流。
三、科幻写作的“冷战性”与新浪潮科幻的价值
亚当·罗伯茨(Roberts A.)在《科幻小说史》中对科幻小说进行历史考察,指出科幻小说在17世纪的“复兴”与新教改革存在内在联系,并且“作为一个文学类型整体,科幻小说仍然具有孕生该文类自身的文化危机的烙印,而这一文化危机恰好是欧洲的宗教危机”③[英]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科幻小说在17世纪之所以是“复兴”,是因为作者将古希腊幻想旅行作品视为科幻小说的源头,并且认为在古希腊时代和17世纪之间存在千余年的断裂,这是他将科幻小说与新教改革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亚当提供了一种考察科幻写作特性的视角,即回到这种文类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分析特性发生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认同他对科幻小说起点的界定,而是接受更为主流的划分(即布莱恩·阿尔迪斯所说的科幻小说始于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认为,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整体上应当带有作为其起点的19世纪欧洲社会的典型特征。而考虑到科幻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④与大众阅读者的一般认识不同,科幻并非脱离现实的,而是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中外理论家如鲁迅、莫考克等人都有所阐述。详见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5、42、45页。,科幻写作理所当然会刻上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在这种追溯视角下,笔者认为可以用“不充分的冷战性”来概括19世纪欧洲的社会特性。尽管“冷战”是一个后出的概念,但19世纪欧洲的很多元素的确是“冷战式”的:阶级对立与革命风潮,殖民扩张带来的种族冲突与地理拓荒,频繁的战争以及战争间隙中作为“冷战”雏形的不同阵营的对抗(从反对法国革命的反法同盟、神圣同盟,到相互对抗的法比关税同盟和德意志关税同盟,从制衡英法的三皇同盟,到后来催生了一战的德奥意三国同盟,19世纪欧洲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各国结盟对抗的历史)。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可以被视为冷战时代的预演。
相应地,在19世纪的欧洲科幻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大量具有“冷战性”特征的元素。在“凡尔纳三部曲”中,英格兰政府与苏格兰人之间的种族对立,贫困、失业和剥削所揭示的阶级冲突,潜水船长尼摩的革命者形象,凸显了19世纪的种种“冷战式”矛盾,也为后世的科幻作家提供了无尽的启发。而在威尔斯笔下,《星际战争》的火星人无疑是英国殖民者的外星翻版,《时间机器》中爱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分化也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对立,《当睡者醒来时》甚至直接开启了“反乌托邦”小说的先河。可以说,以凡尔纳和威尔斯两大巨匠为代表的19世纪科幻作品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表现出了浓厚的“冷战性”,成为科幻古典主义的先声。
到了真正的冷战时代,“冷战性”在社会历史中更加充沛之后,科幻写作便进入了它的辉煌阶段:首先是科幻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中扩散,成为一种全球写作方式;其次,在文学文本之外,科幻拓展出了电影、漫画、电视剧、电视广告等新的写作领域;最后,以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莱因、齐奥尔科夫斯基、阿·托尔斯泰、别利亚耶夫等科幻大师的涌现为标志,科幻写作获得了空前的文化地位,甚至影响了人类科技史的进程。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伏笔于19世纪的“冷战性”因其切合时代特征而集中迸发出来,推动了科幻写作的发展。
而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写作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对这种“冷战性”的继承。宋明炜曾指出,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经过数次中断,每次重启时科幻作家都不得不重新发明自己的传统和话语①[加]维罗妮卡·霍林格:《“长城星球”:中国科幻小说的陌生化》,陈广兴译,《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这种断裂导致新生代科幻作家(指以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为代表的作家群)在90年代开始活跃时,很难从国内前辈那里汲取营养,只能转而学习那些在冷战时期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外同行,因此一些学者会认为新生代科幻作家 “受世界科幻大师的影响大于受中国科幻前辈的影响,具有国际化的视野”②董仁威、高彪泷:《中国科幻作家群体断代初探》,《科普研究》2017年第2期。。吴岩等人则在《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中更进一步指出,刘慈欣小说与科幻小说本身的经典价值一脉相承;而经典,主要指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和前苏联时代的科幻小说(作者称之为古典主义科幻),这两者又都渊源于凡尔纳③吴岩、方晓庆:《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其实不仅是刘慈欣,其他科幻写作者也大多符合这一结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这篇文章中,吴岩等人在肯定了刘慈欣对古典主义科幻的接续和发扬之后,又对这种古典道路作出了相当悲观的判断。科幻写作在当下的发展表明,吴岩等人所担心的“未来已来”没有崩解“真善美”等宏大叙事,中国科幻反而逐渐追赶上了世界的步伐,许多年轻作家也开始重回古典道路,刘慈欣并非独行于穷途。尽管这篇文章十多年前的判断已经被推翻,但它却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问题。吴岩等人认为科幻作品的真正内涵在于其启蒙性与现代性,并且指出这也是美国和前苏联科幻共同构成经典的原因所在;而启蒙与现代话语的衰落,又必将导致古典道路的终结。笔者认为,启蒙性与现代性恰恰不是科幻作品的真正内涵,它们在科幻诞生的19世纪就已经显露出崩解的迹象;具有非理性和后现代特征的“冷战性”才是科幻作品的真正内涵,这是吴岩等人预判失误的原因所在。也正因如此,在全球化退潮、“新冷战”阴云密布的今天,科幻的古典道路非但没有越走越窄,反而指向了更多的可能性,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电影在2019年的集中爆发正是回应了这些可能性。
总而言之,通过新生代及之后的科幻作家的努力,中国科幻写作经历了近百年的艰难曲折,终于在90年代以后接续上了世界科幻传统,回归了世界科幻写作的主流,这是中国新浪潮科幻的价值所在。而在这一回归的过程中,由于科幻写作本身的“冷战性”,大量的冷战话语如同开冻的冰凌随江河而下,使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写作呈现出有别于国内文化话语和文学话语主流的异彩,这是其对冷战书写大规模接纳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