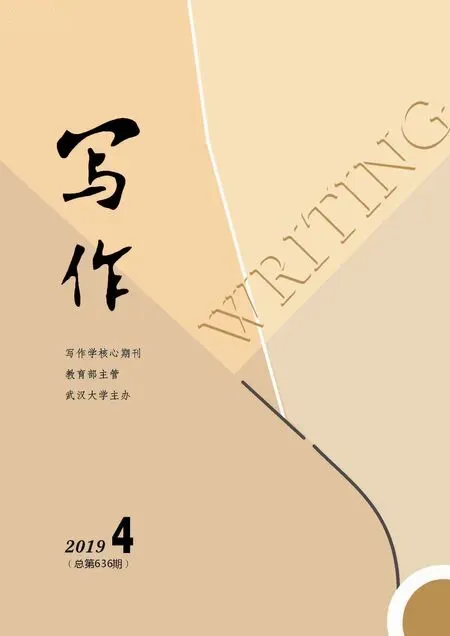自塑与他塑的互文性建构
——论朱自清散文对“扬州”形象的重构
罗小凤
朱自清祖籍浙江绍兴,却自称扬州人,将扬州定为自己的“故乡”,并写下一系列关于扬州的散文①《我是扬州人》《说扬州》《扬州的夏日》《看花》《择偶记》《给亡妇》《儿女》《笑的历史》等都是关于扬州的书写。,不仅抒发其对扬州的情感,介绍其与扬州的深刻关联,更探寻扬州的历史文化与诗意美景,在自塑与他塑的多重视角中对扬州进行再发现与重构,体现了对扬州文化身份的一种追寻与再认,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与文学价值。
一、朱自清的“扬州”认同
朱自清虽然祖籍为浙江绍兴,但实际上他只去过绍兴两回,每回只住过一天。其出生地为江苏连云港东海县,4岁时跟随其父亲到扬州市江都县的邵伯镇(现为扬州市江都区),6岁时搬至扬州,19岁时北上读大学。读书期间回扬州与武钟谦完婚,大学毕业后曾回扬州中学任教过一段时间。如此经历显然表明朱自清是在扬州度过其童年、少年时期和部分青年时期的,毋庸置疑乃确确实实的扬州人,《我是扬州人》这篇散文便可作为各种教材、选本上对其籍贯莫衷一是的各种说法的一个澄清与正名。正如他在文中所明确宣告的:“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算是扬州人的。”②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4卷散文篇》,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页。正由于此,朱自清有一系列散文直接以扬州为题进行书写,这种“扬州书写”其实是对“扬州”的一种认同与重新发现。
众所周知,扬州在历史上一直是富甲天下、风物繁华、人文荟萃的形象,是素为大家心驰神往的“人间天堂”,古代曾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佳句,如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风流薄幸名”(《遣怀》)、“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送孟浩然之广陵》)、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等被广为流传的经典诗句,都塑造出一个令人神往的诗意扬州。然而,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现实中的扬州却迅速没落,其繁盛地位被上海替代,从此退居一隅。这是因为扬州的繁盛主要在于盐商的繁荣和水运交通便利,而随着盐商的没落,扬州的繁盛景象便一去不复返。面对这种境况,许多作家如叶灵凤、郁达夫、曹聚仁、易君左等都对扬州持批判和嘲讽态度,叶灵凤认为“一代繁华,仅余柳烟,社会经济的凋敝,已经使得扬州到处流露了破落户的光景”①叶灵凤:《烟花三月下扬州》,洪迅编选:《叶灵凤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郁达夫则感慨“所见的风景,都平坦萧杀”,“扬州好梦,已经醒了一半了”②郁达夫:《郁达夫散文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易君左更是由于在其《闲话扬州》一书中对扬州的批判而在当时引来一场轰动文坛的风案③20世纪30年代初,易君左的游记《闲话扬州》准备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局中的两位扬州人对作者在书中辱骂扬州的言语不满而交给青帮头子阮五太爷,此人准备“办掉”易君左,易君左请其顶头上司教育厅长周佛海出面方化险为夷,却引发官司并销毁书籍。。朱自清虽然亦曾在文中感叹过扬州的“破落”,并进行过一些批判,但更多是表达他对扬州的感情,如他在《我是扬州人》中说:“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并且说“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他甚至将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当作“地方气”,认为绝不止扬州人如此,显露出其对扬州的至深情感。在其眼中,无论扬州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扬州永远是唐诗宋词中那个美丽诗意的扬州。因此,在面对众多作家批判与嘲讽扬州的“虚有其名”之时,朱自清以一系列文章予以回应,《说扬州》一文便是回应曹聚仁的《闲话扬州》一文。而曹聚仁的《闲话扬州》是根据“扬州究易团”揭发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一书的材料而写的,朱自清认为易君左的《闲话扬州》“将扬州说得太坏”,而“曹先生又未免说得太好”,因而提笔写下自己作为“扬州人”的亲身体验与感受。《说扬州》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先对扬州一些不好的“地方气”进行揭露,但随后笔锋一转,对扬州饮食文化、旅游文化、历史文化进行热情介绍与呈现,既未避其短,同时亦能扬其长,呈现出一个客观、真实的扬州。在当时扬州所处的境况下,此文无疑是对“扬州”的重新发现与对扬州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而且,当朱自清在异乡内心彷徨抑郁时,他便常想起故乡,如他在《荷塘月色》中想起江南的采莲场景从而产生怀乡情愫:“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里的“江南”其实是故乡的借代,饱含他对故乡的怀念,与鲁迅禁不住“思乡的蛊惑”而“屡次回忆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④鲁迅:《鲁迅文集小说·散文卷》,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叶圣陶“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⑤叶圣陶:《藕与莼菜》,《荷花》,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等心境如出一辙,而故乡对于朱自清而言即为扬州,正如他所言:“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⑥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页。;他还指出:“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⑦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页。可见朱自清对于扬州的内心认同,正是他对扬州的深刻情感促使他用笔建构出一个他眼中的“扬州”形象,形成他对扬州的再发现与重构。
二、朱自清对“扬州”的重构
不少人对于扬州的印象大都源于“想象”,其基石建立于古代诗词之上。而朱自清的扬州书写既不同于古典诗词将扬州预设于“人间天堂”的至高位置,亦不将其贬损为一无是处徒有虚名,而是深怀他作为扬州“本土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自觉,客观地还原了一个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扬州形象,建构出一个富有诗情画意、文化深厚,同时又不无土腔土调的朴实的扬州,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扬州”的重构。
(一)诗情画意的美丽扬州
扬州的诗情画意,俯拾即是。朱自清在《看花》《扬州的夏日》《说扬州》《我是扬州人》等散文中抒写着他对扬州各大美景的褒扬之情。他突出呈现了扬州的水上游玩之乐,尤其是坐游船游瘦西湖的乐趣。如《扬州的夏日》中他指出:“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而这好处主要集中于瘦西湖,因为它“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可见小金山、五亭桥、法海寺、白塔、栖灵塔、大明寺、欧阳修的平山堂等美不胜收的风景,其中小金山可望水或赏月,五亭桥可看亭台楼阁与红桥画舫,湖上则可撑船或乘坐“小划子”游玩,突出呈现了水上的“闲寂”“幽静”“悠然”之美与妙。
而且,扬州是一个花园般的园林城市,三步一景,五步一园,处处可见花草树木,朱自清在其文中对“花”亦进行了近距离聚焦。《看花》中呈现了他对栀子花的酷爱,由于他对栀子花的爱而竟然对桃花毫无兴致,从而错过对桃花之美的欣赏。尤其文中写到的巷中“卖栀子花来”的声音,笔者认为可与戴望舒《雨巷》中丁香般的姑娘媲美,令人回味无穷,成为现代散文中的一个独特创造。“荷”意象亦是朱自清构筑的一个独特意象,扬州人喜欢种荷,处处可见荷,尤其瘦西湖里便一半种红莲一半种白莲,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朱自清即使身在离故乡遥远的北京却依然对荷倾心,因而他才会对住处附近的荷塘挂心,在惶惑苦闷中便去荷塘边走走,并由异乡的荷塘联想起江南故乡的荷塘,一句“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将异乡的荷塘化为作者心之所惦记的“江南”缩影,因此,他所塑造的荷塘月色美妙绝伦,因为它不仅仅是清华大学那片荷塘,而是处处闪现着江南尤其是扬州的影子,凸显出扬州的诗情画意与美妙。
(二)文化深厚的人文扬州
朱自清笔下的“扬州”首先是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扬州是个历史文化名都,拥有2400多年的历史,乃人文荟萃之地,各种历史古迹遍布古城区。据统计,古城区拥有147处文物保护单位和30多处私家园林①吴周文:《朱自清与扬州名城文化》,《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浸润在这种历史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朱自清,禁不住探访历史遗迹追寻历史记忆,正如朱自清在《说扬州》中指出:“城里城外古迹很多”“邀上两三个人去寻幽访古倒有意思”。这种“寻幽访古”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追忆”。“追忆”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阐释与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时捕捉到的一个关键词,他认为“追忆”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主要旋律,不少诗词中以“追忆”的方式展开,在对往事进行再现的过程抒发情感,具体而言,追忆主要在场景和典籍的基点上展开:“场景和典籍是回忆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它们是有一定疆界的空间,人的历史充仞其间,人性在其中错综交织,构成一个复杂的混合体”②[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4页。。朱自清对扬州的书写亦是在他离开扬州多年后对扬州的一种“追忆”,他凭借一些蕴藉着历史文化的“场景和典籍”进行追忆,并在自己的记忆和视点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想象和重新建构,如《扬州的夏日》中一开篇他便追溯扬州被诗人文士称道的源自隋炀帝时期的历史,并介绍了小金山、平山堂、法海寺、白塔等地的历史渊源和传说。这种对历史文化的追寻无疑是对叶灵凤、郁达夫、易君左等人嘲讽扬州“徒有虚名”的一种回应,是对扬州文化身份的一次确认和再发现。
其次,朱自清呈现了扬州饮食文化的丰富多样。朱自清在《说扬州》中写道:“扬州是吃得好的地方。这个保你没错儿。”①朱自清:《你我·标准与尺度》,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78、79页。众所周知,扬州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淮扬菜的发祥地,在这里“吃”作为一种文化受到推崇,积淀了丰富深厚的饮食文化,如扬州点心曾在康熙、乾隆时代被定尊为“贡品”,狮子头、扬州炒饭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名美食。朱自清将扬州菜与其他菜做了比较,认为扬州菜具有“色香味”俱全的特点,颜色上“清新夺目”,口感上颇为鲜美,而且“滋润,利落,决不腻嘴腻舌”。朱自清对扬州面亦有独到体验,认为其妙处在于“汤”的味道“醇美”,扬州面所用之汤根据食料的不同而做成不同味道,有用“鸡鸭鱼肉等熬成”的“白汤”,有用单纯鸡肉熬成的“鸡汤”,这些汤经过“大煮”之后“更能入味道”。此外,朱自清还对扬州美食中最负盛名的富春百年老店点心进行了介绍,如各种馅儿的小笼点心、烫干丝等,朱自清在文中对小笼点心的介绍可谓津津有味:“肉馅儿的,蟹肉馅儿的,笋肉馅儿的且不用说,最可口的上菜包子与菜烧卖,还有干菜包子。菜选那最嫩的,剁成泥,加一点儿糖一点儿油,蒸得白生生的,热腾腾的,到口轻松地化去;干菜也是切碎……可以嚼出一点橄榄般的回味来”②朱自清:《你我·标准与尺度》,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78、79页。,显示出朱自清对扬州点心的内行。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朱自清对“烫干丝”制作过程的介绍,他在文中极其详细地介绍了如何切丝、烫熟、调料等过程及其与外地“煮干丝”的区别。由此可见出扬州饮食文化的精细与丰富。
此外,朱自清先生在其散文中还呈现了诸多扬州的各种本土风俗,如早晚喝茶的习惯以及瘦西湖的船娘、水上的“小划子”、乡下姑娘走街串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等等,从风俗文化方面呈现出扬州深厚的人文底蕴。
(三)美女文化盛行的柔美扬州
“扬州出美女”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般的审美共识,朱自清对此亦曾指出:“提起扬州这地名,许多人想到的是出女人的地方”③朱自清:《你我·标准与尺度》,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78、79页。。朱自清喜欢用美女意象,与其自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显然不无关联。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的两个哥哥早夭后,母亲遵循“男孩女养”的迷信风俗让朱自清从小耳朵上戴着一副金耳环,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内心深处潜在地存在一种女性心理认同感,甚至有一种女性化性格,为其以女性形容各种物象提供了审美心理基础。朱自清曾在其散文《女人》中假借“白水”形象而传达了自己“欢喜女人”的意识,他假借“白水”的口吻透露出他内心不敢言明的真实想法:“老实说,我是个欢喜女人的人……我到无论什么地方,第一总是用我的眼睛去寻找女人。”当然,朱自清的“欢喜女人”是审美角度的“欢喜”,他是将女人当作艺术审美对象,正如文中所道明的:“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这是艺术的女人。”④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选》,上海: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30页。正由于朱自清对“艺术的女人”的欢喜与审美,她笔下常用女人意象作比喻,或对事物进行女性化描写,如《荷塘月色》中他将“田田”“袅娜”“亭亭”“羞涩”等形容女人情状形态的语汇描写荷叶、荷花,在他眼中,荷叶荷花都是“舞女”“刚出浴的美女”之化身;而《绿》中,朱自清将梅雨潭的绿比拟为女人“她”,将游人对梅雨潭之绿的欣赏描述成恋人之间的追逐与爱慕,如“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并用“少妇”“处女”“最嫩的皮肤”“舞女”“盲妹”“小姑娘”等词语形容或衬托梅雨潭之绿的魅力。此外,《一封信》中写紫藤花“临风婀娜”,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和“凝妆的少妇”⑤朱自清:《一封信》,《清华周刊·清华文艺副刊》1927年第2期。,《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将“垂柳树”写成“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和“月儿披着的发”⑥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东方杂志》1924年1月25日。,《阿河》中将“水”写成“像少女们皱她们的眉头,过一会儿就好了”⑦朱自清:《朱自清散文精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朱自清都是用女性意象、女性词汇、女性情态进行比拟。在他笔下,几乎一切都可用女性意象做比喻,吴周文认为这是一种“对女性的崇拜”①吴周文:《朱自清与扬州名城文化》,《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事实上,这是扬州美女文化在朱自清笔下的文字投射,由此呈现出扬州的“柔美”。
(四)土腔土调的朴实扬州
在古代诗人笔下,扬州是一个风华绝代、粉妆玉琢的形象,但在朱自清笔下也呈现出扬州土腔土调的朴实一面。朱自清操一口扬州口音,对扬州本土方言俚语都颇为熟稔,正如他在《我是扬州人》中所承认的:“我也是江北佬,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②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4卷·散文篇》,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他总是有意识地在其文章中夹杂扬州方言进行创作,甚至还尝试使用土腔土调的扬州大白话和方言俚语,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扬盘”“侉子”“呆瓜”“甩子”“咬嚼”等扬州口语和“不死要剥层皮”“烧成灰都认得”“烂面糊盆”“乖子望一眼,呆子望到晚”等扬州方言俚语。他的经典名篇《背影》中运用了“念书”“白托”“拣定”“膀子”等不少扬州方言,呈现出现实生活中扬州土腔土调、朴实平易的形象。此外,朱自清在一篇评论文章《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中,还使用扬州口语营造出一种“说话”氛围,如“寻常谈话一般读了亲切有味”,形成散文的“谈话风”,与周作人等作家的“闲话风”散文一道开创了散文的一种新言说方式与风格,在当时的文坛上盛行一时。
由此可见,与叶灵凤、郁达夫、曹聚仁、易君左等人相比,朱自清对扬州更为熟悉。而从朱自清对扬州的书写看,如果他对扬州没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是不可能用那么多笔墨去呈现扬州的方方面面的。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表达:“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朱自清先生亦是如此,为什么他用那么多笔墨书写扬州,因为他对扬州爱得深沉。
三、“自塑”与“他塑”的互文性建构
需要注意的是,朱自清散文中重构的“扬州”并非古典诗词中传说的“人间天堂”,而是多维、丰富而客观的,这与他本身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朱自清是扬州人,却是一个“特殊”的扬州人,因而带有“他者”视域下的眼光与心态;但他与作为游客身份审视扬州的叶灵凤、郁达夫、易君左、曹聚仁等又不同,朱自清曾在扬州度过其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期,因此他又属于扬州人,对扬州熟悉并对扬州深有感情。此外,朱自清后来并未定居扬州,而只在扬州短时间工作,多数时间漂泊异地,后来任教清华大学后定居北京。可见其身份是复杂多重的,因而他观看扬州的视角亦颇为复杂多重,其扬州书写既有其作为扬州人的“自塑”,亦有移民作家的“他塑”,二者交织于一体形成一种互文性建构,如此建构出的“扬州”更是一个真实、客观的多维扬州。在扬州多年的成长与生活经验让朱自清对扬州极为熟悉,但非本土扬州人的身份又让他在心理上与扬州本土人不无疏离感。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说扬州》中指出其文化身份的特殊,他明白自己“家里是客籍”,因而“与当地贤豪长者并无来往……他们的雅事,如访胜,吟诗,赌酒,书画名家,烹调佳味,我那时全没有份,也全不在行”③朱自清:《你我·标准与尺度》,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79页。,并未真正融入当地扬州人的生活中去,正是这种疏离感给朱自清客观“观看”扬州提供了机会。后来他又离开扬州到北京求学,在扬州短暂工作一段后离开扬州,辗转一些地方后定居北京。因此对于扬州而言,朱自清其实一直是个“游子”,当他携带着外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扬州时,他自身所浸染的扬州文化底蕴与所裹挟的外来文化一直处在激烈的纠葛与冲撞之中,朱自清将自己在这种文化冲撞的见闻、感受、体验与情绪进行呈现与书写,从而完成“他塑”与“自塑”的交锋。外来者采取的是“选择性聚焦”,现实的扬州与他们想象中的扬州不符时他们便进行批判。“选择性聚焦”是新加坡学者南治国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是挪用电影或摄影中的术语“聚焦”,对中国作家笔下的“南洋”图像进行分析解读,他认为中国作家们在写作中将异域文化纳入写作视野时对异域文化的“观看”与“审视”是具有选择性的“聚焦”,作家们根据个人志趣、喜好、阅历、经验和感受而进行选择,因而“聚焦”主体不可能是“聚焦”对象的全方位,被摄取的信息由作家的文化背景、个人阅历和“聚焦”角度等决定,因此,作家们所摄取的信息不过是异域文化的某些部分、片段,他们根据这些信息在文中所塑造的“形象”亦只是异域的“部分”与“片断”而非全部。叶灵凤等作家所游历的只是扬州部分地段的部分风景与名胜,因而他们眼中的扬州只是“选择性聚焦”的扬州。他们在古代诗词的基础上对扬州的想象与构造是古典的,而现实中的扬州不可能不带上现代化痕迹,甚至呈现衰落后的残败之相,因而他们选择性聚焦扬州那些古典风景却找不到想象中的效果或古诗中的诗意景象,由此失望并进行批判。而朱自清作为一个移民而来、长于斯却又离开斯的特殊审美主体,其审美视角、心态颇为复杂,既有生于斯的本土情感,亦有外来移民的他者视域,并有移民外地后的他者眼光,三者身份交织交融。作为一个具有复杂身份的扬州人,朱自清对于扬州的态度比较客观,既不避其短,同时亦扬其长,更能呈现一个客观、真实的扬州形象。因此,朱自清对于扬州的塑造是他塑与自塑的结合,“移民”身份让他既不像本土扬州人对本土的山水、文化已熟视无睹或怀抱“夜郎自大”的自负,亦不像纯粹的外省作家一般专为扬州的古典印象与想象而来,朱自清拥有扬州与异地的双重文化背景与经验,这种视角打破原生的惯有模式,焕发出多重魅力,由于多重经验的汇聚而获得写作的超越,建构出一个独特的“扬州”。
外省作家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其实主要基于想象基础之上,叶灵凤、郁达夫、易君左等作家对于扬州的想象是建立在唐诗宋词基础上的浪漫、古典想象,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衰落后的扬州便无法接受,想象与现实的距离导致强烈的落差感,从而造成他们对扬州的难判、嘲讽。而曹聚仁从未去过扬州,其文字表述完全根据历代诗词与口耳相传的关于扬州的传说进行文化想象。朱自清与此两类观点均不同,他对扬州秉持“维护性批判”,这种批判其实是基于“我是扬州人的一种文化焦虑”①景秀明:《江南城市:文化记忆与审美想象——中国现代散文中的江南都市意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这种“维护性批判”在吴周文看来,是朱自清对扬州人“国民性”的深刻解剖与批判②吴周文:《朱自清与扬州名城文化》,《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亦是他作为扬州自我与他者双重身份持有者的客观与自觉。
朱自清以自身的扬州经验为基点,在他塑与自塑的多重视角下多维度对“扬州”进行重构,是对“扬州”的一次再发现,更是其作为扬州人的一种文化焦虑与文化追寻和再认的体现,对于重新认识“扬州”不仅具有文学意义,亦不乏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