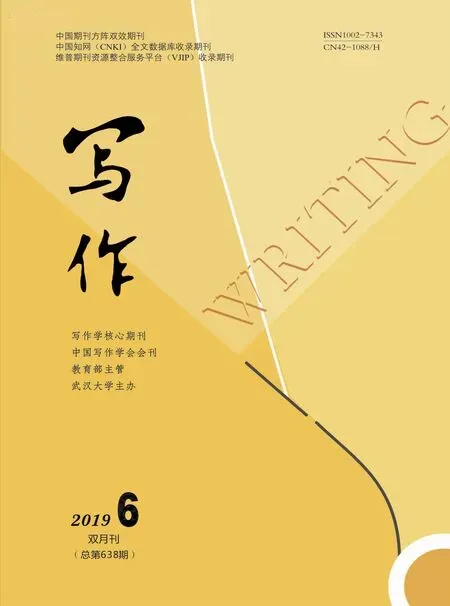先锋文学精神与今日生活
李修文
毋庸讳言,我们这一代写作者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以为,无论是作为方法还是精神,先锋文学都极大地改造了许多后来者的质地和肌理,它强烈而清晰地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样貌,给中国文学注入了现代性。在我狭隘的认识里,如此强有力的注射,单就文体的革新而言,无论有意或无意,它都回应了鲁迅先生改造中国旧小说、将白话文小说送上顶峰之时的一己之力。
但是,自我开始写作,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惑,即我们的写作,似乎总是无法与我们置身的时代、我们所遭逢的人事和际遇互相印证;我们的叙事里,也似乎总是无法有效地获得一个时代内部的人格力量;我们看似在通往现代性的历程中一路狂奔,但是,出自历史的负担,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现代性尤其暧昧、丰富和复杂,在缺乏了总体视野的情形之下,我们所秉持的写作方式是否反而助长了文本与现实的割裂?或者说,我们所受的文学训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它们是否反而模糊了真正的生活和心智,进而对我们作品中的人物造成了一种美学上的强制和阉割呢?
由此,我一度非常迷恋中国古典文学和戏曲资源中的说书人传统,但是很快,我也感受到了不满足:古典文本的魅力之所以绵长,绝非是艳情轶事所致,也绝非是一点闲情和雅趣所致,而是因为它们见证了古典时代的离乱兴衰。今日里被我们所供奉的至宝,多半都是从当时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代表着冒犯与重新确立的产物——当林冲夜奔,一颗被碾压过的心在弥天大雪里狂跳;当西门庆去打仗一般占领和攫取女性,女性背后所躲藏的宗法和制度顿时化作了难以逾越的沟壑与高山,烈火烹油之气与破败无力之身双双扑面而来;又或在京剧《天女散花》中,梦境与现实互相交织,此身非身,彼心即是我心。这时候,无论我们与它们诞生的时代相隔有多么遥远,我们也能够确信,它们所传达的气息与处境与我们是相同的,风雪山神庙和那座不得其门而入的城堡其实就是一回事。我以为,这就是现代性,而在这些文本诞生之前,古典传统里,其实并没有多少作品去冒犯“有诗为证”的惯性,如此真切地将人之为人的处境送达到我们的眼前。很显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先锋,唯有先锋精神,才能令传统起死回生,才能使中国文章的浩大势能在今日生活里重新被激活。
这些年,我无数次地重新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除去获得了一种“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和我有关”的强大心理暗示,最令我触目难忘的,就是那些清晰印证我们自身面目的小说人物。有一度,我迫使自己泥牛入海,去找工厂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去找房产公司里的“刘关张”。我以为,找到他们,自己就回到了某种古老的源流和怀抱之中,那些独属于中国式的词汇,譬如恩德,譬如情义,譬如树倒猢狲散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它们就能被我重新发现和验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避风港在等待着你去靠近。从某种程度上说,经由自己的总体视野,鲁迅先生通过精确的描述,已经将传统的中国人送上了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上,尽管这个历程何其艰难,但是,在我们通向现代性的历程中,鲁迅先生的作品成为了我们出发的源头。所以,在各种穷途末路上,要遇见“梁山伯祝英台”和“刘关张”,更不要忘了,举目之处,皆是“闰土”和“孔乙己”,皆是“涓生”“子君”和“魏连殳”。越过了这些人,我们就容易被那些闲情雅致所蛊惑,我们就容易与活生生的离乱兴衰失之交臂——这些文学谱系中新的出处和来历,不是由别人,恰恰是由真正的文学先锋鲁迅先生带来的。
鲁迅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愈至今日,愈加成为问题。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真正具备先锋精神的人,会受到时代生活的胁迫和迷惑;我们更应该相信,写一个创始人也好,写一个董事长也罢,他们除了活在现在,还活在中国人通向现代性的艰难历程中,在他们的身上,依然折射出了我们行进至此的国民性。今时今日,我们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碎片化与同质化,这个观点已经成为几近陈词滥调的共识。然而与此同时,一座座新的神殿也在拔地而起,且越来越无法沟通:我们一边看到,在一种普遍被劳动、个人价值、成功学神话所异化的处境中,人人只好画地为牢,任由神圣、崇高、自豪一类的词汇既囚禁了自己,又远离了自己;另一边又看到,因为关于整个世界的信息都唾手可得,我们在文学中强调了无数个年代的个人价值其实正在变得无足轻重,一个人,一个地方,都在空前地取消线性,转而要求自身和世界的横向链接。因此,向内的“个人”坍塌了,我们跟随着幽默感、瑜伽、国学等等新的神殿仓促奔跑,尽力奔向彼此,最终却成了一个苍白的集体。在今天,如何重新将这些早已破碎的处境凝聚起来?也许,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先锋精神,这种精神敢于将自身的感受作为感知今日生活的最敏感神经,也敢于将自身体验当作一种文体本身来建立,一如阿烈谢克耶维奇所说:“当我行走在大街上,就意味着多少长篇小说消失在风中。”
以散文写作为例,一个不足一百年的文体概念,在几千年的文学传统面前,就真的那么确定无疑吗?当时代的境遇无比突出,压迫了散文的所谓“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已经左支右绌之时,我们是否还要紧紧怀抱“真实性”的神话去强词夺理?如果我们将美学的真实视作叙事范畴里唯一的真实,那么,新闻意义的真实是否还能在美学呈现中具备某种天然的优越感呢?尤瑟纳尔说:如果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同样,我们无法证明,在《天问》中,在《山鬼》中,屈原写下的哪一部分是事实,哪一部分是谎言,我们只好说,所谓假的,就是真的。在我看来,因为各种文体的负担,今天,散文成了一件大事。在从前,我们通常认为,矗立在各种文体之间的那个地带构成了散文的主体性,在今天是否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刻,散文的主体性恰恰在于抢夺和侵占,抢夺小说,侵占戏剧,抢夺诗歌,侵占电影,才有可能真正构成今日散文的主体性?
也因此,我深深地怀念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写作,以及其后受到影响的各个饱满充沛的文本。它们横空出世,不分青红皂白,跟读者建立了最珍贵的美学信任。而且,它们不庸俗,在今天,当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和庸俗作战之时,我们应当有勇气告诉自己:我们的忤逆之心,永远年轻,且并不新鲜;我们的前辈,既是叛逆的幼子,也是承担了文章道统的长子,这颗长子与幼子之心所证明的,是我们从来就在传统的庇佑中,又必须代表传统变成一个新生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