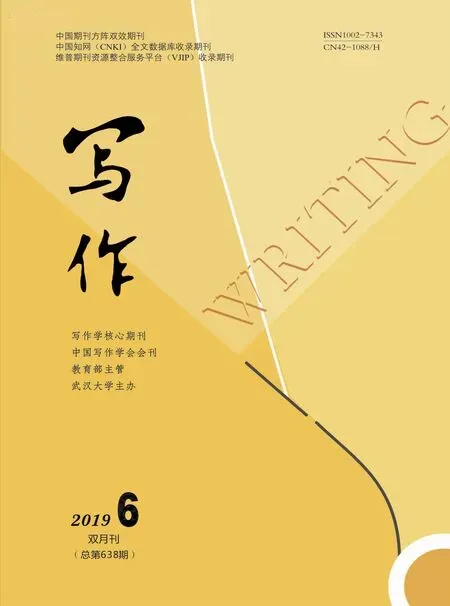“英雄主义”与时代个体的救赎之路
——评麦家新作《人生海海》
陈佳冀 陈心澈
麦家的新作《人生海海》将大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熔铸其中,借由“上校”荡气回肠百转波折的一生,对中国的乡土与城市的革新进行审视与批判。时隔八年,麦家再次捧起说书人的饭碗,将目光聚焦于“双家村”这江南一隅,把时代、人生与人性剖开来,幻化成故乡记忆与童年往事,将一个崭新的故事娓娓道来。有趣的是,麦家还是将英雄作为主人公,将跌宕起伏的命运存于往事之中,其叙事的方式还是力求满足人们的“窥探欲”,结局的处理仍旧暗含人道主义精神,怀揣善意,温情常在。然而八年时间的重新积淀同样为麦家的创作带来新变,作品的主题由波诡云谲的谍战风云变成潮起潮落的人生救赎,其意义也伴随着对隐秘人性的挖掘而渐为深刻,作品的价值也在跟随“我”对故乡的和解态度中再次升华。
《人生海海》讲述的是“我”的童年记忆与归来转变,借用“我”的一双眼睛去看“双家村”阴暗与私密的角落,借用“我”的一双耳朵去听来自这个封闭村庄的人性薄凉的声音。故事中让人又敬又畏、充满传奇色彩的“上校”,与“上校”关系最好的重情重义的父亲,最好面子的“读书人”爷爷,风流成性却智勇双全的老保长,可怜又可恨的小瞎子,充斥在这个人丁兴旺的村庄中,故事脉络交织在一起,一同向我们展示复杂又脆弱的人性的善恶美丑,以及生死选择的人生信条,不断挑动着读者的神经。小说中“上校”的一生颠沛流离,在暴力中度过艰难岁月,他本以为最安稳的余生将在双家村度过,不曾想这个村子成为他噩梦的开始。观文至此,人们才会发觉,暴力从来不止于身体,众人施加在他者心里的暴力才是被忽略掉的最残忍的施暴方式。这位不曾被历史铭记的英雄的命运令人动容,他的一生是个传奇也是个悲剧,命运对他的不公与他对命运的抗争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人的缩影,所谓人生、所谓命运,不过如此。百年来的苦难练就了这千千万人如今的刚强,如作者写在作品腰封的话:“人生海海,潮落之后是潮起,你说那是消磨、笑柄、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①参见麦家写于《人生海海》腰封的文字。作者将英雄主义的含义变得更加宽广,正如对待世事沧桑、人生沉浮的态度,经历过艰辛、抉择,最终找到自己与人生相处的方式。生而为人,逃不开,躲不掉,不如去爱上命运,珍惜生命中散发出的人性微弱的光芒与勇气。
一、被时代所遗忘“英雄主义”书写
英雄主义具有崇高的精神,不仅仅局限在社会价值层面,与人生涵养与精神人格也是息息相关的。“‘英雄’本身是一个固定的文化概念,他以鲜明的个人形象、悲情的气质往往在那些危险的关键时刻凸显某一稳定的伦理文化中最为光辉的部分。”②李一:《赤子之心与英雄叙事——评麦家〈人生海海〉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愁声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而书中主人公“上校”正是如此。他当过兵,打过仗,经历枪林弹雨;当过军医,救死扶伤无数;做过特务,深入敌营无所畏惧;回归故里,重拾“救人”本行。巴金曾说:“一部优秀作品的标志,总是能够给读者留下一两个叫人掩卷不忘的人物形象。古今中外的名作,所以能流传久远,就在于它的人物形象,以及它对当时生活的深刻描写,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倘若作家只是将这位英雄的光辉事迹讲述给众人听,便不会有如今揪心又痛彻的心境,作家脱离传统叙事对英雄歌颂式的书写,将其生活化平凡化,满足人们对英雄如何在世俗生活的想象,在生活与命运的磨砺下,“上校”的形象树立得更为真实立体。然而,“上校”光辉的行为在时代的浪潮下虽存在过短暂的值得铭记的价值,却从来无力支撑垮掉的人生。一个人再坚毅勇敢却仍旧冲不破时代对人的枷锁,至此,命运也随之转弯,变得曲折而离奇。肚子上的一排字仿佛才是为他人生定性的关键,将过往种种掩埋时间的尘土之下,忘记了他曾经的辉煌与贡献,他被“被成为”了一个汉奸,最终如一粒细沙沉入大海,无踪无迹。而所谓传奇经历,于“上校”自己只是磨难的一生,于众位看客而言徒增内心悲凉。
小说到“我”去上海找林阿姨为止都是一个悲剧,人们把记忆停留在广场上要对他公开处刑的一幕,对这个骄傲又孤独的“上校”而言,公开处刑乃至死刑都无所畏惧,直到台下有人高声喊道:“把他的裤子扒下让我们看一看!”③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56页。这句话才成为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刻在身上的文字隐喻了他黑暗的无从辩解亦无从考证的过去,短短几个字消弭了他荣耀的过往,身体在此处是卑微的存在。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曾说:“我的躯体只在通常的两种形式下才存在于我自身:偏头痛和色欲。”④[法]巴特:《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导致他陷入此番境地的恰好是“性”的问题带来的后果,这份卑微使“上校”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背叛者”,这是他小心翼翼掩藏的根源所在。文字的作用是双面性的,那比他命更重要的字是他的污点,是他试图抹去的真实过往,这隐秘的隐藏行为是支撑他能体面活着的力量,众人这一番“看”的举动,无异于将“被看”的他的尊严践踏,于是,他疯了。看客们用所谓正义与真相“编造”出了虚伪与谎言,可笑又可悲,英雄一样的体面人物却无法被铭记,反而被绑在耻辱架上供人观赏,更甚至要将耻辱架刻在“上校”心里,不间断地告诉他,他从来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有污点的人。造成此般结果的绝不仅仅是命运与人性,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时代。
全篇在描述“上校”时都带有历史虚无感,无论“上校”或是“太监”都只是一个符号的代称,所指的正是这个姓名已被遗忘的主人公。纵使他回归故里,却保持着孤独与神秘,故乡带给他的并非人情和温暖,冰冷与陌生加剧了他内心的疏离,强大至此的他失去了归属感与安全感,实则则是被时代所遗忘。何为虚无,虚无是人在时代不可逆的前提下失去了所谓的存在感,是一位神坛中的英雄消弭于历史长河中,时代抛弃的不止是落后与愚昧,还有千万万的人,无论品性纯良与否,人作为个体不过是那沧海一粟罢了。在普世的认知中,英雄应当被铭记,英雄的精神应当被发扬,所赋予的英雄主义的内涵应当被学习,可是如果这些都属虚无,那么又何来铭记,何来发扬,何来学习呢?在时代的浪潮中,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会变,但是生命涵养与人格质素不会轻易改变,然而英雄作为个体的存在却会随波消散,这便导致其个体的精神内涵亦不复存在,剩下的仅是需要留下与传承的意识形态,真正属于英雄的意志在时代中化为虚无。如今倡导学习英雄的精神却无人关心真实作为“人”的英雄,其实原来也没有世间传颂的那么完美。人之渺小和薄弱,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人能够抗拒命运,更无谓对抗时代,在一个人命如草菅的时代里,大家都逃不过生活的羁绊,英雄亦如此。私以为时代是造成“上校”悲剧的根源所在,是他生命的长度延伸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历经战争与革命,看过乡村与城市变迁,对人生早早看透,将生死置之度外,却不料看不穿时代的狠厉,早已将人折磨得不再为“人”。
麦家曾言:“上校的命运也说明,这一百年来中国个人的声音、个人的活力是相当微弱的,他总是国家的一分子,总是大历史中的一枚小螺丝钉,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国家主义的生存状态。”①季进、麦家:《聊聊〈人生海海〉》,《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英雄主义也不过是印着国家主义的意志在不断传承,“上校”的真实就在于日常化的叙事,而非英雄事迹的描绘。在悲壮中书写崇高所能带来的审美体验更具震撼心灵的效果,相较于大团圆式的结局,悲惨与抗争过后获得的温暖方能更具力量。作者讲述英雄的故事,书写他们的人格与生命,令悲剧主体以坚韧、顽强的精神与崇高的信仰抵抗生活的苦楚与命运的造化,使读者感受幕后英雄的意志与力量,这是麦家作品的深层次意蕴。在虚无的过往中,英雄虽无名,理应被铭记,他们的选择与成功为人们搭起了坚实的堡垒,道一句辛苦,说一句缅怀,是作者的情怀,亦是作品的价值传达。纵然时代遗忘多数人,总要有人为他们送行。
二、理想化英雄叙事的人性旨归
《人生海海》中的人物性格鲜明,行事特异,在“双家村”这个两山包围的封闭村落里满是奇人与异事。“上校”的身世、父亲与“上校”的关系、爷爷对“上校”又爱又恨的态度,老保长与“上校”扑朔迷离的关系都令人称奇。麦家擅于书写身处黑暗隐蔽空间里的个人传奇,他的小说主人公们往往被他置身于一个“封闭空间”里来进行深层地描摹与刻画,以此来充分展现人物的心理、推进故事的发展,以及深化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人性的弱点在这个密闭的空间中便会被不断放大,微小的举动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看客们喊着要扒掉“上校”的裤子导致他的疯癫,比如“林阿姨”一次冲动举报反而害了“上校”的后半生。身处“双家村”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面体,可怜可悲可恨可叹,不同人的不同选择却仿若一个连环扣一般,一环一环将选择的恶果扣在“上校”的身上,让他承担人性善恶的抉择带来的后果,在滑稽与荒诞中真实刻画了生活的多样性与人性的不可测性。
“双家村”对比于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容纳着一个社群,是一个时代乡土社会的缩影。密闭的空间充斥着紧张、焦虑和对抗,所有的感知都会放大,人会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人性也会在封闭的状态下被无限放大。爷爷与老保长,爷爷与“上校”都是在矛盾中不断转换态度与作风,当双方处在对立面时,冲突不可避免,行事出现偏颇与诡谲的现象是人在极具压抑感的密闭空间中自然行为反应。这时,道德危机便会在乡土社会中显现,非黑非白的“中间人”不断涌现,作者融入其具有时代感的批评态度,试图撬动尘封千年的道德秩序,将人性之恶展览出来不断鞭挞。人性在光明与暗黑中交织显现,阐释有关道德有关伦理的矛盾,人性的丑陋、罪恶、阴暗也在神性的光辉之下被接连披露。
作品中的爷爷与老保长是一对相爱相杀的老顽童,爷爷是读过书有知识的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颇有威望;老保长则是吃汉奸饭却不做汉奸事的老油条,说起话来粗且脏,三句不离女人。作品有趣之处在于,读者自然而然认为“我”的爷爷是品性纯良道德高尚之人,实则不然。倘若不是“上校”之事牵连其儿,爷爷的黑暗面也许将永远暗藏于道貌岸然的表象中。爷爷的跟踪与告发竟是导致“上校”被抓的直接因素,而不时造谣与咒骂“上校”的老保长却实打实地从内心敬畏这位英雄,甚至跟他出生入死过,并始终如一承诺死守秘密不与任何人言说。所谓人性的幽暗与脆弱,在这吊诡的故事发展中缓缓展开。老实本分的爷爷因为自家人的面子出卖了“上校”,他的清白一生只因这一个举动从此蒙上污点,后代也跟着遭殃。这其中除却他自己的一时糊涂,也有周围人用闲言碎语作恶,谣言一传十十传百,谣言成为了“真相”,人们的造谣生事势必要为爷爷的一时糊涂承担责任。“乡村制造谣言的土地特别肥沃,而人们对谣言的识别能力又特别差,谣言的杀伤力也就特别大。以前对乡土的批判和揭露,往往限于饥饿、贫穷这些表面的东西,更可怕更深层的是,由于长期暴力革命所导致的人心不古、人心向恶,时时处处都会莫名其妙地伤害他人。”①季进、麦家:《聊聊〈人生海海〉》,《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道德的约束力在当时的乡土社会中不具备普适性,爷爷夹在其中饱受苦楚,这时潜藏于心中的恶便悄然而现。
爷爷及其一家都是可怜的,无事生非的闲言碎语给这家人带来了伤害;然而爷爷又是可恨的,“上校”如若被抓便意味着凶多吉少,爷爷心中一清二楚,可自私自利的习性使然,爷爷在抉择的分岔口站到了善的对立面,一念向恶招致祸事不得不自食恶果。反观老保长,在老伙计与道德面前坚守正义,他知道了告密者是爷爷后便找上门来打他并放话说:“我反正以后再也不会踏进你家一步,他也别让我在外头看见,看见我就要骂,就要打,打死他我就去坐牢……”②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29页。老保长这种吃喝嫖赌所有恶习都沾个遍的俗人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含糊,两人的选择仿佛被置换,令人不得不叹其可笑又怒其可恨。人性之复杂往往显现于关乎自身利益的关键一二事件之中,一丝自我安慰过后的邪念,往往要导致他人付出惨痛代价,终将反噬自身。
如果说“双家村”的众人展现了人性美丑与善恶,那么“上校”就是一个理想化的英雄人物,象征着纯粹与高尚。作家将疯掉的“上校”描写成一个孩童,便是令一切故事回归原点,孩子的心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最纯净的容器,“上校”心智如孩童的隐喻代表了这个人物形象的纯粹,代表了其具备高尚内涵的品性。麦家将人性之美贯穿于“上校”波澜横生的命运中,“上校”当兵期间看不惯将重症伤员抛弃的行为,便自己在一旁学习摸索,成为“金一刀”后更是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这是对于家国的大爱,彰显出人性中神性的一面。“人类本身是具有神性的,这是神性本源的第三重意味:人类的神性在于能够感受到世界和万物之灵,并且在这种感受的浸染下思考物我关系,一个事件或者物体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定位,甚或一个词语的历史定位。”①陈柏彤:《于坚:在创作中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写作》2018年第3期。“上校”在村庄生活的日子里,他看到麻烦也会帮上一把;哪怕在监狱中,他也从来不曾放弃信仰,不屈服亦不认输。这是麦家心中理想化的英雄主义,借助给人深刻回响的尘封记忆,把人心赤裸裸血淋淋的剖开,通过对比“上校”的行为与“双家村”其他人的行为,解开人性的面纱,不带遮掩地告诉读者,人性之恶能够将一位英雄埋没尘土,而善却是导向胜利的真途。
《人生海海》中丝丝入扣的情节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为小说人物拓展打开了空间。无论是有关“上校”那不可描述的下半身的秘密,还是“上校”与“我”父亲之间的关系,抑或是“上校”参军过程中的辉煌与回乡之后的人生落差轨迹,都是山穷水尽局面后的柳暗花明之喜,在情节的陡转之间完成了文学审美的阅读体验。倘若要追寻人生波折之因,怕是还要归结于人性,人性的善触碰到人性的恶而产生的摩擦与毁灭,偶然与必然间的关联本就奇妙,这也构成了悲剧命运哲学的思考。麦家对悲剧命运的思考不是抱怨,而是用崇高的语言来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说明作者寄希望于美好大于丑恶,命运的不可逆需要坦然接受,但是后世的评判自在人心。
三、时代个体的自我救赎之路探寻
麦家以往的小说创作多是宏大的叙事格局,在思想上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家国意念在发挥作用,倘若之前仍有对麦家作品中对人性挖掘不够的质疑,《人生海海》问世便不攻自破。作者将对命运的思考融入作品中,弱化生死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消解隐藏支撑主人公一生信念的“英雄主义”,被消解后的英雄主义不再拘泥于家国之争,而是将人放置到生活的环境中,实现从被救赎再到自我救赎的升华,最终将生活的冷峻转变为内心的平和与宽恕。
作品浓缩了“上校”的一生,也是在书写每个人的一生;借由上校最终对人生的凝视与参透,与自己和解的态度规劝世人,英雄尚且如此,平凡人的磨砺从来都是生活的附属,保有人性的真善美,不被世俗所玷污内心应有的名为希望的光亮。作者从命运入手,将人与命运间的冲击与对抗展现得较为强烈,在矛盾交织中突出人物特性与主旨内涵;同时命运与磨难作为主题也贯穿了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在被命运捉弄的无奈中与英雄落幕的荒凉感下,重新找到人生出口,那就是看清生活,仍旧热爱。如果一个人经历苦难,并从苦难中懂得生活的真正含义,那么这个人必不会辜负自己,也不会辜负生活。这其实需要强大而独立的人格做支撑,不溺于洋洋自得,不畏惧失意落魄,以从容不迫的心态应对世间的万千变换,面对人生窘迫,甚至生离死别。“上校”曾是这样的人,长大后的“我”也是,后来救赎“上校”的林阿姨亦是。而作品中英雄主义的价值与内涵被消解了,不再局限于高尚和奉献的社会价值,其精神更像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外化,强调对人生美好的心向往之与心灵之音的回响,作品的群体面向于世上之千万人,其价值不拘泥于英雄主义的崇高追求,更是对于自我的一次内心救赎。纵然知道前路荆棘,也要勇敢前行,对自由、尊严、高贵的人生价值心存向往。
都说小说离不开故事,故事离不开人物,人物离不开命运,命运以其无穷尽的变数诱惑着人心。《人生海海》是一部描写了命运悲剧的小说,而命运悲剧的作品起源于古希腊时期,不同于中国神话小说的“大团圆式”结局,西方神话故事中大多存在着悲剧色彩与造化弄人的无奈情节,主人公无论付出如何的努力都摆脱不了命运的羁绊。麦家的创作思维受西方的影响较多,自然关注命运的伦理与价值。诚然,命运从来都具有琢磨不定又逃离不开的魅力。小说中爷爷、父亲乃至“上校”的命运都近乎以悲剧收场,前文曾叙述过“上校”生命历程中无常的命运轨迹,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早已看透了生活的无奈,却不断包容、宽恕、接纳,最终认同并仍旧热爱着生命。“我”的前妻也是如此,于“我”而言,前妻象征着真善美,是绝望时光中的一根稻草,将我从“垃圾”中扶起来,成为一个站立的人。然而从年少到生命的终结,前妻的一生十分凄苦,但就是怀抱着罗曼·罗兰式英雄主义的力量便拥有了积极面对生活的勇气,这是罗曼·罗兰的精神追求:“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①[法]罗曼·罗兰:《巨人三传》,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这个日常化平民化的英雄主义在发展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消解崇高的同时加注了更悠远而广阔的力量,那便是选择活着的力量与热爱生活的力量。
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生脉络笼罩在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家长里短中,他们的命运仿若海边翻涌的浪花,层层递进地拍打着并依偎着彼此,在名为时代的浪潮中自顾不暇,只能依靠本能的宣泄相互羁绊,而普通心灵的爱恨也同样在翻滚中不断升华,令读者仍能在冰冷中感受到背后的温情,心有戚戚,情有所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②唐宝民:《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学习博览》2013年第10期。苦难也有意义,尽管它从不被人羡慕。《人生海海》中每个人物的经历就像书名一样“人生海海”,每个人都经历苦难。作家的解读又将英雄主义熔铸其中:人之渺小之于时代不过一粟,英雄亦如是,在时代的浪潮中一切都变得虚无;然而造成英雄被吞噬之由不仅是时代的枷锁,还有人性恶的一面加持,在自我利益受到影响时毫不犹豫抛弃原则的行为被作者指责,而这更凸显了理想化的英雄主义所代表的人性美好与神性光辉;最后在生活的重压下,在命运的失控中对生活的态度也表明了他的英雄主义情怀:既然每个人都跑不掉逃不开,那不如去爱上生活。“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③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10页。愿真实生活里勇渡“人生海海”的英雄们也都能有此善终,清澈明朗,心怀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