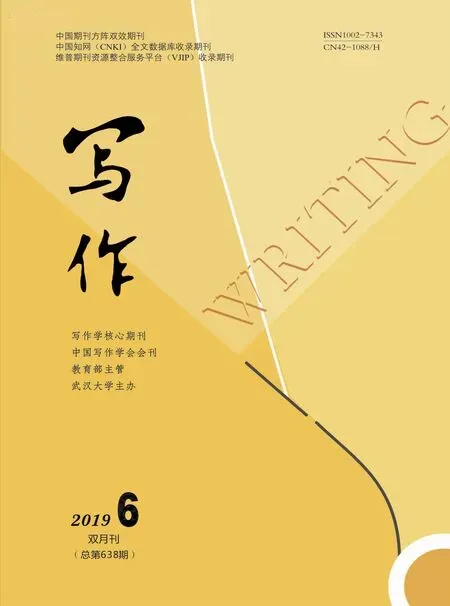从《致江东父老》论李修文创作的变与不变
萧 映 李冰璇
李修文是一位勇于挑战自我、给读者持续带来意外惊喜的作家。从短篇小说集《心都碎了》的先锋写作到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的古典唯美,到电视连续剧《十送红军》的宏大主题,再到散文集《山河袈裟》的生命悲悯,跨界写作的勇气与硕果令人钦佩。继《山河袈裟》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之后,2019年9月出版的《致江东父老》是李修文推出的第二部散文集。如果说《山河袈裟》是李修文初步明确“写什么”的转型之作,那么《致江东父老》便是其在进一步明确“写什么”的前提下探索“怎么写”的进阶之作。在《致江东父老》中,李修文回归中国式散文的本土姿态愈发坚定、确立美学真实散文观的文体意识愈发自觉、延续“人民”与“美”的写作审美愈发明晰,彰显出作家对当代书写的理性探索。
一、文体自觉:回归中国式散文
从《山河袈裟》到《致江东父老》,评论家们大都认为李修文的散文创作开拓了散文的文体边界。在我们看来,与其说他开拓了散文的文体边界,不如说是一种复古回归。正如李修文所说:“如果说在文体上存在着一丝自觉,我必须承认,我想写出某种‘中国式’的散文,我说的这个中国式散文,与《春秋》、《左传》和《史记》有关,与唐宋八大家有关,与明清小品有关,它承接的应当是这样一种传统,而非是现代文学以来被西方语境塑造过的散文。”①刘川鄂、李修文、钱刚:《从“人民”与“美”重新出发——关于〈山河袈裟〉的对话》,《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外延很广,除韵文、骈文以外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畴。小说、戏剧等是文体进一步细分的产物,究其本源还是散文。与其说李修文的作品具有散文小说化的倾向,不如说他重拾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叙事传统。这一点在他界定“中国式散文”的概念提及《春秋》《左传》《史记》三部作品时得到印证。《春秋》是记事的源头,开启中国古代散文的叙事传统,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左传》《史记》则各有侧重地影响了后世的叙事文学,这一点,章学诚“记事出于左氏,记人原于史迁”①章学诚:《湖北通志凡例》,武汉:武昌官书处1882年版,第8页。的评价颇为中肯。如果说李修文从《春秋》《左传》《史记》中汲取的是传记散文的叙事传统,那么他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中吸收的便是叙事对象与叙事手法。其中,韩柳的散文对《致江东父老》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无论是韩愈的《毛颖传》《圬者王承福传》,还是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童区寄传》,叙事对象由“大人物”转向“小人物”,叙事手法借鉴了当时的流行文体“传奇”,生动形象地描写市井细民和劳动群众的人生际遇。李修文试图通过《致江东父老》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其实便是为普通人立传,直接承接了唐宋散文为下层人物作传、吸收传奇叙事的写作倾向。中国古代散文讲求“形散神不散”,明清小品带给李修文的滋养更多地体现在“神”这一方面。明清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美学追求,既带给他不拘文体的自由不羁,又带给他抒发自我的酣畅淋漓。《致江东父老》写的是父老乡亲踽踽独行的困顿悲苦,更是李修文对生命的悲悯与对世界的思索。
跨文体写作在《山河袈裟》中初露端倪,在《致江东父老》中更加显露出一种文体自觉。以散文篇幅为例,《山河袈裟》除《自序》外共收录33篇散文,平均篇幅4000余字,篇幅最短的《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仅1000余字,篇幅最长的《义结金兰记》不足万字,基本符合篇幅短小的现代散文特征。《致江东父老》除《自序》外共收录18篇散文,平均篇幅1万字左右,篇幅最短的《长夜花事》4500字左右,篇幅最长的《何似在人间》1.6万字左右,扩充的篇幅使得跨文体写作的可操作性变强。相较《山河袈裟》因篇幅所限而显得有些中规中矩的散文而言,《致江东父老》扩充的篇幅使得散文的形式结构的多重探索成为可能,更显露出李修文创作时的文体自觉。
《猿与鹤》和《大好时光》是中国式散文痕迹较重的两篇作品,分别置于散文集《致江东父老》的首尾两处,别具意味的设置方式彰显出李修文的文体自觉与审美追求。李修文的《猿与鹤》与柳宗元的《三戒》有异曲同工之妙。《三戒》结构严谨,开篇用短序串联起三则故事,且《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故事各有标题,独立成文。《猿与鹤》由《猿》《鹤》《猿》《猿与鹤》《鹤》五篇散文组合而成,起到串联作用的是中部的《猿与鹤》。可见,《猿与鹤》的小标题不是散文小说化的体现,而是汲取古代散文营养的创作尝试。同为动物寓言,《三戒》借麋、驴、鼠三种动物,讽刺现实社会中恃宠而骄、不学无术、作威作福的行为;《猿与鹤》借失去自由而一心求死的猿和身处鸡群却不甘平庸的鹤,反思现实社会中扮演小丑的庸众。不同于柳宗元辛辣的讽刺笔调,李修文在批判的同时更多了一丝悲悯。《大好时光》沿用中国古代书信体散文的形式,由李修文假托艳梅大姐之口的《一封来信》和第一人称口吻的《一封回信》组成。事实上,《一封来信》只是引出《一封回信》的楔子,形式意味远大于实际意味,《大好时光》的重点是李修文自己所表达的大好时光。从这点来看,《大好时光》实际上继承的是“自序与自嘲”的中国散文传统。自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始,从唐代刘知几的《自叙》、明代张岱《自为墓志铭》、清代汪中的《自序》到近现代梁启超的《三十自述》和林语堂的《八十自叙》,后世中国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这一传统。陈平原认为“一般所说的‘自嘲’,除了显而易见的自我批评,往往还隐含着另外两种旨趣:一是讽世,一是述志”②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89页。。《大好时光》笔触并不辛辣讽刺,李修文的写作目的不是讽世而是述志,悲苦中有光亮和温暖,流露出一种抚慰人心的脉脉温情。“艳梅大姐,再见了。以上,就是我一定要写给你看的大好时光”①李修文:《致江东父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57页。,这既是《大好时光》的结尾,也是《致江东父老》的结尾,与开篇的《自序》首尾呼应,进一步印证了“自序与自嘲”的中国散文传统。
二、散文观念:美学意义的真实
百年以来,散文的文体边界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由小变大的过程。古代散文并不是一种文体,而是一种外延极广的文类。“五四”以后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现代散文的外延变小,成为与小说、诗歌、戏剧并驾齐驱的四种文体之一。新时期以来,散文家们意识到现代散文的种种限制,试图拓展当代散文的版图,文体间的跨界成为常态。因此,当代散文的概念仍在不断建构。
2014年3月17日到9月29日,古耜、何平、熊育群、朱鸿、陈剑晖、南帆、张炜、孙绍振等评论家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先后发表文章,就“散文的边界”这一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试图厘清当代散文的文体边界。其中,何平、南帆、张炜等都提及散文中真实与虚构的问题,但由于对“真实”与“虚构”的理解不一,呈现出姿态各异的解读。关于这一问题,李修文也有自己的思考与感悟,他在创作谈中曾经有过多次表述。2017年,李修文在与学者刘川鄂、钱刚的对话中指出:“所谓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在散文里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它只能说明,我们已经被文体的囚笼束缚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②刘川鄂、李修文、钱刚:《从“人民”与“美”重新出发——关于〈山河袈裟〉的对话》,《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2018年,李修文自认为有些武断地指出:“如果我的写作有一个归宿,那么,这个归宿不应当是所谓的‘真实’,而应当是疯癫和甜蜜构成的美。”③李修文:《在我的人间》,《文艺报》2018年8月24日,第2版。2019年初,李修文在与学者刘楚的对话中指出:“所有的文体其实都是一个作家的美学建构的载体,而不是像讨论一篇新闻一样,不断地辨析你写出来的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如果每个人的写作都有一个归宿,那么我的写作绝对不归于真实,而归于美学。”④刘楚、李修文:《从生活中获取热情和力量——李修文访谈》,《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在2019年9月21日的新书签售会上,李修文更加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散文观:“不在乎新闻意义上的真实,而在于美学意义上的真实。”⑤赵颖慧:《李修文:为了配得上你们,我要变得更加清白》,《潇湘晨报》2019年9月28日,第8版。
事实上,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中国古代散文也包括适当的想象性描写。如《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原本寥寥几笔便可以说清楚的史实,作者却从郑武公娶姜氏说起,加入姜氏因难产而不喜庄公的小细节,结尾又增加庄公与母亲黄泉相见的大团圆情节,从而达成历史之真与文学之美的高度融合。这里要明确想象与虚构的区别:想象是“有中补无”式的有限补充,虚构是“无中生有”的无限创造。散文中的想象性描写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并佐证真实,而不是虚构或重塑真实。李修文对待“真实与虚构”的态度看似与中国古代散文一致,其实并不相同。古代散文是在求真的前提下求美,真大于美。李修文的散文观是在求美的前提下求真,美大于真。
米勒的“错格”理论或许可以帮助读者理解“美学意义上的真实”:叙事线条“不是一根连贯的线条,而是用谎言的力量粘合起来的一连串并列的碎片”⑥[美]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作家的记忆往往是碎片化的,他只会记住印象深刻的几个记忆片段,事后的文字书写都是一种再建构,不可避免地需要用谎言的力量将真实的记忆碎片串联起来。比如《鱼》,池塘里一条条鱼高高跃出水面的奇迹般场景,震惊了母子两人,将试图寻死的母亲拉回了尘世。这一幕场景看似是非真实的,但联系“下雨前鱼因为缺氧会跃出水面换气”的生活常识,以及结尾处雪花打湿了母子俩头发的细节,这一幕是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据李修文自述,鱼跃出水面的确是其亲身经历,并且这一幕“在许多年里不断被回忆起来,它们一次次被想象、认知和建构,最终,它们呈现出了一个写作者意义的真实”①赵颖慧:《李修文:为了配得上你们,我要变得更加清白》,《潇湘晨报》2019年9月28日,第8版。。一连串的记忆碎片也许是真实的,但将记忆碎片串联起来的表述必定借助了谎言的力量。哪怕是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其诉诸笔下的真实性都是值得存疑的,更何况他人转述的亲身经历。因此,即使李修文采用非虚构的创作方法搜集“真实”的写作材料,材料的真实性仍然值得怀疑,不可能存在新闻意义上的真实。
作家要想自圆其说,就必须将分散四处的记忆碎片虚构组合成连贯叙事,哪怕在叙述过程中作家本人察觉到谎言的存在,也难以看清真实本身。比如《白杨树下》,每当李修文意识到自己见到的是故去的表姐和姑妈的鬼魂时,频频感到自己“深陷在某种深重的错乱”“产生了错觉”“罪犯般的慌乱”②李修文:《致江东父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27-231页。。而李修文出生在钟祥、成长在荆门,这一带恰恰是楚文化发祥地,巫楚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美学追求上,李修文期待荆楚风格的复活,相信绮丽妖艳而富有生命力的楚文化,希望靠近一种近似于《天问》和《山鬼》的美学传统。因此,深受巫楚文化影响的李修文相信自己真的能够见到表姐和姑妈的鬼魂,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讲述这类场景时所产生的一种迷乱之感,哪怕是想象占据主导所产生的一种想象,但我认为,这就是我心中的真相。”哪怕文字的蛛丝马迹暗示李修文本人也意识到叙述本身的“不真实”,但为了自圆其说、为了维护心中的“真实”,他还是极端强调自己主观感受的真实。在李修文看来,“在文学的范围之内,从自身出发的判断是最值得信任的判断”③李修文:《写作和我:几个关键词——自述》,《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哪怕作家眼中的“真实”可能是常人眼中的“不真实”,但是判断真实与否的决定权掌握在作家自己手中,这可能就是李修文所说的“美学意义上的真实”。
三、“人民”与“美”:写作审美的延续
无论是早期小说创作,还是散文集《山河袈裟》,亦或是新近出版的《致江东父老》,“人民”与“美”是李修文一以贯之的写作主题,并且伴随其写作的成熟,“人民”与“美”的内涵始终处于动态成长过程之中。
李修文笔下的“人民”经历了从个体到群像的变迁,其不同时期刻画人民的叙事姿态更是变动极大。在早期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中,他关注的是被生活和命运逼到角落的底层边缘人,通过零度叙事呈现出一种冷漠、残酷乃至看客般的姿态。在散文集《山河袈裟》中,他试图融入饱受穷愁病苦的平凡生命之中,呈现出一种众生皆苦的悲悯姿态。而在新书《致江东父老》中,他倾向于刻画具有群体性表征的人民形象,文风更加朴素、沉潜,呈现出一种仰望生命的谦卑姿态。“插画+文字”是一种跨媒介的艺术表现形式,有插画的散文像有声小说一样,是当代文艺作品的特有景观。插画师蔡皋用景泰墨创作了一群看不清眉眼轮廓、只看得清身体姿态的形象,她对《致江东父老》的理解与李修文是不谋而合的:人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普遍性群体,体现在插画上即为一群没有面目的人。
写完《山河袈裟》后,李修文希望接下来的散文创作能够“从一种有名字的写作变作无名无姓的写作”④刘川鄂、李修文、钱刚:《从“人民”与“美”重新出发——关于〈山河袈裟〉的对话》,《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山河袈裟》中反复提及的写作困境与不停暗示的作家身份,处处皆有“李修文”的写作痕迹,而《致江东父老》在淡化“李修文”乃至达到无名无姓的写作预期方面,无疑是有所突破的,但我们认为李修文仅是部分达到了这一写作预期。《致江东父老》中提及的人物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我”“他”“她”这类人称代词,二是“小蓉”“改改妹子”这类有名无姓的人,三是“老秦”“马家三兄弟”这类有姓无名的人,四是“和尚”“瞎子”“那瘸腿的中年男人”这类无名无姓的人。仅在《我亦逢场作戏人》《大好时光》两篇散文中,以“修文兄弟”“修文老弟”的形式正面出现了作家本人的名字。如果说《大好时光》为了继承“自序与自嘲”的散文传统,明确出现作家名字尚可理解,那么《我亦逢场作戏人》全篇共计出现17次“修文兄弟”就显得有些出戏。或许,李修文想要通过名字的复现进一步佐证其叙述的真实性,但这一处理方式不如《何似在人间》的“这位仁兄”“兄弟”或者《不辞而别传》的“穷作家”。如果李修文想要彻底达到无名无姓的写作预期,最好在文本中尽可能淡化“李修文”的痕迹。
在李修文的文学创作中,“美”的内涵不断成长。表面看来,大到主题标题,小到语句意象,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始终贯穿于李修文的文学创作。从短篇小说集《心都碎了》的《大闹天宫》《金风玉露一相逢》到散文集《山河袈裟》的《长安陌上无穷树》《义结金兰记》,再到散文集《致江东父老》的《万里江山如是》《何似在人间》《我亦逢场作戏人》,仅从标题就能看出古典文学对李修文创作的浸润滋养。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与冒辟疆《影梅庵忆语》中的“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被分别置于长篇小说《滴泪痣》与《捆绑上天堂》的卷首,奠定了古典唯美的小说主题基调。相较《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充满古典韵味的语言意象始终如一,文字却愈发内敛,少了一些张扬、浮华,多了一些朴素、沉潜。以古典文学的引用为例,《山河袈裟》更多的是直接引用古典文学中的只言片语,有一些略显刻意的炫技式张扬。伴随着作家心境日臻成熟,创作要素开始做减法,《致江东父老》鲜少有直接引用,文风更加朴实无华,能够感受到古典文学的气韵已内化于他的文字之中,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深层看来,“美”承袭了“爱与死亡”的小说主题,呈现出一种悲剧乃至悲壮之美。“爱”在李修文早期小说创作中更多的是男女之情的“小爱”,在后期散文创作中则转向更为广义的“大爱”:超脱于爱情之外的亲情、友情、家国之爱。“死亡”是李修文作品中的宏大背景和共同主题,从反抗死亡的恐惧本能到面对命运的无能为力,再到坦然接受的了然释怀,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近乎悲壮的人性之美。不同时期不同文体的作品具体呈现的“美”各有不同。在李修文早期小说创作中,“美”的最终落脚点是“爱”,是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绝望之爱,字里行间流露出感伤迷离的唯美与凄美。而在后期散文创作中,“美”的外延更广,包含走向死亡过程中的一切爱意、失败、苦难乃至死亡本身,多了几分厚重与悲壮的美感。
相较李修文之前的作品,《致江东父老》中既有对“人民”和“美”的继承与延续,细节处更彰显出他愈发明晰的写作审美:追求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美学感受。李修文认为自己的写作非常简单纯粹,不过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那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罢了。无论是作为一动不动的土地爷悄无声息记录下理当记下的一切,还是作为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全知全能地窥尽人间秘密,李修文想要抓住身边流淌行进的中国人的最初模样,想要与当代中国的心跳脉搏同频共振,创作出热情、准确、记录当下的属于当代中国人的文学作品。李修文在《重新发现与继续担当》一文中强调作家身为时代亲历者、见证者的责任:“亲历意味着亲身丈量,亲自擦亮,以此发现新的时代和新的自我;见证意味着暂时地遣散自我,使作品让位于他发现的世界,即回到新文学的初心:到人民中去,发出平民的、大众的、有血气的声音。”①李修文:《重新发现与继续担当》,《文艺报》2019年7月17日,第3版。《致江东父老》为中国大地上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刻碑立传,这一讲述中国故事的自觉写作,蕴含了李修文创作观中的美学自觉与文化自觉。
四、结语
伟大的作家往往都是杰出的文体家。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俱佳,汪曾祺、韩少功、史铁生创作出了游离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优秀作品。从小说家到编剧,再到散文家,李修文一直在尝试探索文学创作中的多种可能性。他曾多次在访谈中提到,自己从不拘泥于文体,而更加看重真诚的表达,这恰恰与“表达的内容永远比方式重要,更靠近表达本身”①林贤治:《中国散文五十年》,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的散文不谋而合。某种意义上说,散文富有包容性和延展性的自由特性,更适合李修文的文体实验,更契合他的写作审美。李修文在《致江东父老》中对“当下散文的可能性”的创作探索,既体现其进行文体实验的自觉意识,又彰显其讲述中国故事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