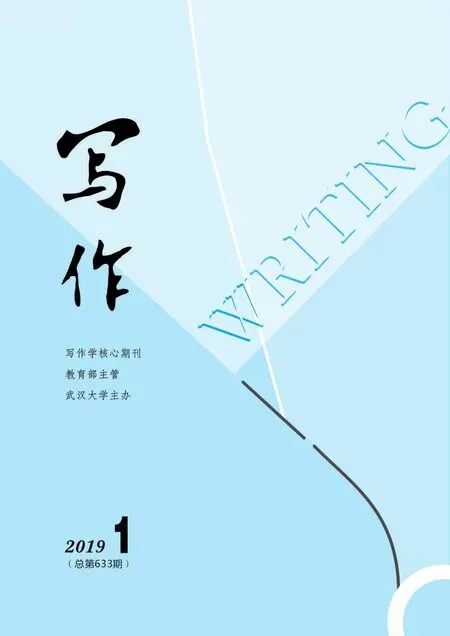严歌苓小说中的戏曲叙事策略*
俞春玲
在传统中国社会,戏曲在国人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提供着公共交流的空间,同时也是老百姓获得历史文化知识,树立道德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而人们对于戏曲或者对于伶人的不同态度,反之又体现了时代、地域、性别等背景差异。正是源于戏曲可以言说的丰富内涵与广阔外延,包括华文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坛出现了不少含有戏曲元素的小说,其中白先勇、李碧华、施叔青的相关创作已经受到了较多的关注,相对而言,严歌苓运用戏曲元素进行创作的独特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事实上,严歌苓是一位极富创作个性的作家:“她的创作不仅在海外华文文坛树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也注进了簇新的因子。”①[美]陈瑞琳:《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持质》,《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其大量小说由戏曲入手,借以展现现代人、异域人对于包括戏曲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观感,辨析戏曲文化在历史进程以及当下的复杂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到作者关于人性、人生的独特体悟。戏曲元素的运用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意蕴,赋予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
一、戏曲文化的多元映照
与许多戏曲题材作品着力于对戏曲演员形象的塑造不同,严歌苓的小说固然描写了有自己特点的“戏子”形象,但更多的却将笔墨放在“戏子”周围的人身上。通过对这些人物生活、情感的书写,体现了戏曲艺术的魅力,同时也展现了戏曲文化的复杂性,审视着孕育了多元文化的土壤。
戏曲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章诒和指出,如果要找出一种娱乐方式,既能为贵族文人所欣赏,又能为平民百姓所领悟,恐怕当属“看戏”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就曾经说过:“戏剧之于中国人,好比运动之于英国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①转引自章诒和:《中国戏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戏迷比比皆是。《角儿朱依锦》描写了观众对名角朱依锦的迷恋,展现了民众对戏曲艺术的热爱。“我爸和我都驾了云雾,给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样,认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么舞着水袖走远了,一双脚大大的,走起来倒完全像没有脚,乘船一样。下一个春节晚会我又见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撒花’的衣裳在台上东倒西歪地唱《贵妃醉酒》。那一段戏文我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②严歌苓:《穗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55、3-4页。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懵懂无知的孩童,都被戏曲艺术所吸引,这正体现了戏曲雅俗共赏的特质。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固然惊艳,下了台、卸了妆的他(她)们仍然成为受人瞩目的焦点。“她手里夹着香烟,跟我想象的名演员一模一样。她笑的时候露出长长的两排牙齿,每颗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从来不洗的茶缸子里面的颜色。”③严歌苓:《穗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55、3-4页。在这段描写中,主人公并没有闭花羞月之貌,也无法让读者感受到其魅惑之处,应该说,其魅力来自于舞台形象的迁移,人们对于名角的感情源自关于戏曲文化的移情。
大众被戏曲艺术所濡染,戏曲的影响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人们在生活中有意无意、时时处处关联到戏曲。形容一个人模样俊俏,有吸引力,人们会借用戏台上的人来比拟。如穗子第一次看到腊姐,“叫腊姐的十五岁丫头有些要迷住她的意思。穗子眼里她是戏台上一个人……”“她只认为腊姐大致是个下凡的戏中人。”④严歌苓:《穗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55、3-4页。人们会借用唱词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好恶,会联系剧中角色来比拟他们的现实处境,戏曲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融入国人的血液中。
戏曲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它是大众化的,它没有多高的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喜欢它,都可以找到接近它的方式。《柳腊姐》中的保姆柳腊姐虽然不识字,但学曲调跟偷一样快,就是利用干活时听着收音机里有一句没一句得唱,到穗子家的第三个月她便学会了朱依锦的四个唱段。《角儿朱依锦》写到了一个少年韦志远,虽然只是一个门房,却痴迷于戏曲文化。他默默钻研戏文,因为经常在腿上划板眼,灯芯绒裤子有块地方都被他划秃了;他大清早偷偷躲在厕所唱戏,自己唱男腔,女腔他就用胡琴伴奏;尽管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他还努力自己写剧本,克服羞怯向剧作家请教,一再被拒绝仍坚持不懈;即便在文革中名角儿受批判,每次被拖出去时,韦志远都会从板凳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站在一边……在这个内向的少年身上,潜藏着对于戏曲文化巨大的热情。正是这种热情可以使得人们在艰难的生存境遇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乃至力量,克服各种困难甚至包括心理上的弱势。也正是源于这种强大的群众基础,戏曲文化才能蓬勃兴旺、绵延至今。
戏曲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戏曲的传播往往联系着族群交流、地域变迁,戏曲传播史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在中外交流中,戏曲文化成为外国人观照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折射出的变形的戏曲表演,正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东方被认知又被误读的真实写照。“《魔旦》聚焦于漂泊美国的两代男旦,‘男人扮女人’所代表的特殊‘中国性’,成为‘东方奇观’的一部分。”⑤陈丹丹:《“戏剧化”的“中国”——从张爱玲到严歌苓》,《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魔旦》中的奥古斯特来看阿玫唱戏,是为了让自己看透阿玫,然后对舞台上幻化成无数个美丽女子的阿玫,奥古斯特却一直被困在意外中。在外国人眼中,戏曲舞台上的形象是变幻莫测的,这种东方奇观映射的是中国文化亦即中国形象在异域的隔膜与神秘。正是因为这种陌生化的视角,中国成为“扮装”后戏剧化的呈现。正如陈丹丹在《“戏剧化”的“中国”——从张爱玲到严歌苓》中所指出的,“戏”“舞台”“戏子”与“看戏的人”是张爱玲与严歌苓笔下不断出现的主题,但“张爱玲的笔触是向内的,严歌苓的视角是向外的”。随着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挖掘,包括施叔青、钟晓阳等港台作家在内的中国作家愈发意识到戏曲的重要意义。由于戏曲在华人文化积淀、民族凝聚中的重要作用,华人所到之处常常伴随着戏曲的传播。这一点已经在一些华文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如施叔青的小说《行过洛津》,即借七子戏从福建传播到海峡对岸的过程,书写了台湾洛津的历史变迁、人情风俗。严歌苓正是在戏曲海外传播史与中国移民史的关系这样一个重要命题上,早于施叔青等其他华人作家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
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戏曲。在这股创作大潮中,不管是大陆作家毕飞宇的《青衣》、贾平凹的《秦腔》、叶广芩的《状元媒》、常小琥的《琴腔》,还是港台作家陈若曦的《最后夜戏》、七等生的《沙河悲歌》、洪醒夫的《散戏》《清溪阿伯和布袋戏》、微知的《“天声木偶戏班”的传奇》、宋泽莱的《大头崁仔的布袋戏》、凌烟的《失声画眉》等中长篇小说,均唱出了在经济飞速发展、娱乐形式多样化的冲击下,戏曲艺术爱好者对戏曲文化衰落的无奈挽歌。值得注意的是,严歌苓对戏曲文化的书写,没有仅仅停留于对戏曲艺术魅力的渲染,或是对戏曲文化遭遇波折的歌哭,而是突破了狭隘的一己视角,关注面从底层到精英,从向内转移到向外,展现了被华彩流章所遮蔽的戏曲文化的复杂性,更加客观地写出了戏曲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以及不同文化交流碰撞中的重要意义。
二、“戏子”折射出的复杂人性
戏曲并不是一个独立体,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是由众多个体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其传播过程及效果与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严歌苓的小说艺术由戏延展到人,将戏与人放置于特定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下,通过描写人在不同状态、不同场合下对戏曲从业者的态度,展现了普通人身上丰富而深刻的人性。
严歌苓的作品中,人物用“戏子”来指称从事戏曲表演的这类人。据现有可查资料,“戏子”作为对戏曲演员的称呼约始于明清时期①闫辉:《“戏子”一词的文化考释》,《四川戏剧》2013年第6期。,明末冯梦龙的《醒世恒言》、清曹雪芹的《红楼梦》中都出现了“戏子”一词,而“戏子”的地位是非常低贱的。“戏子”这一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大众对从事舞台表演这类人的最普及的指称,同时也为行内人所接受。它既代表着魅惑、荣耀,也预示着地位低下、经历坎坷,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概念。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表演者的地位已经大为提高,成就卓著者被称为表演艺术家,但对于这一行业的偏见仍然普遍存在着。当听说柳腊姐要去学戏的时候,《穗子》中的外婆阴冷地说:“做戏子比做正经人家的媳妇好到哪里去?”朱依锦挨斗时要挂破鞋,因为大家认为“不做破鞋怎么做女演员啊”。成为“戏子”往往是一个人在走投无路时才会做出的选择,从事这一行当的人被认为是薄情寡义的,这一概念背后所含的轻薄意味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从文化濡染的角度看,“戏子”在中国地位的低贱与传统儒家文化对于戏曲的贬低有关,“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正统文人大多以诗文为‘正宗’,以戏曲为‘邪宗’。诗歌、散文都曾被封建文人用作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唯独戏曲一直被目为有伤风化、君子不为的‘末技’。”②郑传寅:《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古典戏曲的影响》,《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人们对“戏子”的态度却足以体现复杂的人性。戏曲文化作为国人的一项传统娱乐活动,为他们提供了获得历史知识、人生哲理的一种途径,涵养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国人常常以戏中得来的经验作为一种行为准则,羡慕戏台上人们的爱情、忠贞,也为名角儿的表演艺术和人格魅力而着迷。可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心底里瞧不起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哪怕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也可以以自己的身份高于“戏子”、自己的品格不同于“戏子”而沾沾自喜,甚至不惜以侮辱、损害他人以证明自己的高尚。就心理学而言,这其实是国人在外界种种压力之下的一种应激反应,是一种自欺欺人和自我麻醉,也是自我弱化、自我精神控制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提倡对传统戏曲的改革和对戏曲文化的弘扬,戏曲演员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新文化的冲击并未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长久以来人们对“戏子”的鄙视态度,再加上“文革”时期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包括传统戏曲演员的地位再一次跌到谷底。蒋子龙的《蛇神》、李碧华的《霸王别姬》、严歌苓的《角儿朱依锦》等小说均描写了“文革”时期戏曲演员所受到的猛烈冲击。这类小说在描写戏曲演员受批判的场景中,更加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周围人的“看戏”态度,将中国人的“看客文化”体现到极致。
由于人物戏曲演员的特定身份,周围的人习惯了用看表演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因此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周围的人,都常常将表演/观看表演的空间由真正的舞台拓展到日常生活舞台。李碧华的中篇小说《霸王别姬》,描写了段小楼和程蝶衣从起初的假意互批,到在环境逼迫、情绪失控的状态下,程蝶衣转而肆意揭发的过程。“红卫兵见戏唱得热闹,叫好。”而程蝶衣“为了稳定自己的立场,趁势表现,保护自己,斗得声泪俱下,苦大仇深”①李碧华:《霸王别姬》,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191页。。演员的痛苦、挣扎,在周围的人看来,这也宛如一场表演。即使演员不再有主动性的动作了,周围的人仍然抹不掉对其的好奇,由自我的窥视欲出发剥夺他人的尊严。严歌苓的《角儿朱依锦》中,朱依锦不堪批斗受辱吃药自杀了,抢救中的她被剥得一丝不挂躺在床上供人围观,甚至有几个人夹着双拐,艰难地爬到六层来瞻仰她。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借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名角最后的日子,孩子的善良与其他人的自私、恶毒形成鲜明的对比。
借由人们对戏曲文化包括戏曲演员的态度,严歌苓写出了自己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人们可以随时处于表演或观看表演中,它是以实现自我的满足为中心的,其中也包含着对周围的妥协。对此,严歌苓在对人性有深刻认知与理解包容的基础上,也有着批判与警醒。
三、对“戏梦人生”的反观
戏曲之所以吸引严歌苓,除了戏曲的艺术魅力之外,恐怕更在于来自她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不是演员的人物也常常需要“演戏”,展现了一种“戏梦人生”的人生观。这种意识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也从侧面体现出了作家潜在的心理特质。
人生在世是艰难的,“演戏”可以是对无奈人生的一种逃避,任何人都可能对此有一种本能的认知。穗子自幼被父母丢给外祖父母照顾,巨大的失落感使得穗子时时想要引起别人的关注;腊姐不管做童养媳还是给人当保姆都是寄人篱下,她发现穗子的孤独、可怜之后,发自内心愿意理解包容她。于是,穗子与腊姐“这样日子就过成戏了,好就好在她俩都是戏迷,都不想做自己,都想做戏里的人。”②严歌苓:《穗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08-309页。戏曲里的不同行当或不同扮相,正是现实生活中不同角色、不同人格类型的集中反映。“其实曾经做名角的母亲永远在一家人里唱红脸、白脸、三花脸,当继父的面,她得把继父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转脸又总是个凄美的含辛茹苦的母亲”。③严歌苓:《穗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08-309页。人们在生活中常常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戴着面具生活。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原型说,“人格面具”是其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证了人能够与他人,甚至与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帮助人们实现其个人目的。从积极意义上说,就人的生存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人格面具的。它是一种妥协和退让,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基础,这也正是“演戏”的意义之一。
通过“演戏”,人们还可以获得在惯常的人生中所不可能有的体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感受愉悦和满足,“演戏”正是对残缺人生的一种有效心理补偿。《少女小渔》中小渔为了得到绿卡买通一个老人假结婚,而穷困潦倒的老人在结婚典礼上却表现得非常庄重。“他活这么大岁数只能在这种丑剧中扮个新郎,而没指望真去做回新郎。这辈子他都不会有这个指望了,所以他才把这角色演得那么真,在戏中过现实的瘾。”①严歌苓:《少女小渔》,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亚当是一个男性同性恋,为了完成生命的延续,他找了一个中国女子与其一起生一个孩子。二人相处时,“像正常的男女一样。亚当的戏不错。”②严歌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白蛇》,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扮演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所不可能实现的角色,可谓幻化了人格与人生的完整。歌德曾经说过,“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③[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将理想的幻梦演化为现实,正是“演戏”的价值。
看戏或演戏给艰难的人生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方式的可能,给了人们活下去的希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梦人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除了“戏”,还有“梦”,意味着人生的转机。《梨花疫》中,由戏台上的过场,作者联系到了人生,通过人物之口写出了对于人世变幻的感悟。“幕布虽是静止的,却总让穗子觉得它后面有人在忙活。这就让穗子觉得戏剧最大的转折,就是在一张空无一物的幕布后面完成的。幕布后面那些看不见的人物,以看不见的动作,使阴谋得逞,危机成熟,报应实现。”“‘过场’时常有‘过门’,就是那么几件乐器,奏一个悬而未决的调门。”④严歌苓:《穗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141页。这种“过场”“过门”正与人生中的过渡阶段相似,可能暗含着巨大的转折。人生的魅力也正在于这种对未来的不可预知,以及角色的变换、事件的发生。严歌苓的小说中,人物常常存在着对未来的惶惑,但他们大多是沉默着的。作品中少有外向型人格,人物往往没有撕心裂肺的挣扎,而是以沉默坚韧的姿态面对人生中突如其来的种种变化。这种人物形象类型的塑造,恐怕与严歌苓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密切相关,而这种体悟与中国传统戏剧不无关系。
与西方古典戏剧舞台的写实性原则不同,中国传统戏剧舞台讲究的是虚拟性。“在西方人们走进剧场,自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戏剧家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可能的舞台手段,去制造现实生活的幻觉,让观众忘记自己在看戏,而是像身临其境一般沉浸在舞台上创造出来的生活环境与气氛之中。为此,西方的戏剧家将舞台当作相对固定的空间。绘画性和造型性的布景,创造出戏剧需要的规定情景。人物间的一切纠葛都放到这个特定场景中来表现、发展和解决。在同一场景里,情节的延续时间和观众感到的实际演出时间亦大体一致。”⑤章诒和:《中国戏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而在中国古代以及大量现当代的戏曲舞台上,场景和时间的变化是通过演员的唱词与道白,以及通过表演示意给观众的,时空可以随意变换。中国传统戏剧是在有限的时空内表现无限的时空,用虚拟的手法处理舞台时空与现实生活时空之间的关系。这种差异也造成了人物对中国传统戏剧的不同观感与体验。中国戏曲舞台上讲究的就是真真假假,受众感受到的就是虚虚实实的“逢场作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人生的认知。
作家的创作观念往往与其生活经历、个人体验关系密切。严歌苓的生活和创作一直与戏剧关联在一起,他的父亲萧马先生是一位剧作家,母亲则是一位话剧演员,其童年大量记忆与戏剧相关。在《魔旦》这篇小说中,有大段叙述者的回忆,记述了自己童年时看到老演员们如何化妆、排练的场景。无论是那描画出的一点点樱桃小嘴,还是飘卷的肮脏水袖,抑或是勾完脸后的演员顶着一张戏中人的脸,端着搪瓷大饭缸吃着普通人的饭,都给了严歌苓极大的刺激。也许正是这样梦幻与现实的冲突、交融,以及目睹身边人在现实与舞台之间的辗转,使她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悟,从而将这种“戏梦人生”的观念渗透到了小说创作中。
结 语
异于大量戏曲题材作品中的美化笔法和挽歌情调,在严歌苓含有戏曲元素的小说中,人物以及叙述者的姿态固然常常在追寻、在回忆,但其小说写出了戏曲文化的丰富与驳杂。显然作家是有着责任意识的,作家认为,“对传统的质疑精神实质上是文学创作者优秀的品质”①张琼:《此身·彼岸——严歌苓复旦讲座侧记》,《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多种文化体验,给了她艺术的滋养和创作的源泉,也给了她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加理性的心态,从而帮助读者借由戏曲去理解人性与人生,去体味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历史、文化的不同看法,这也正是戏曲在给人以美的享受之外,所应有的丰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