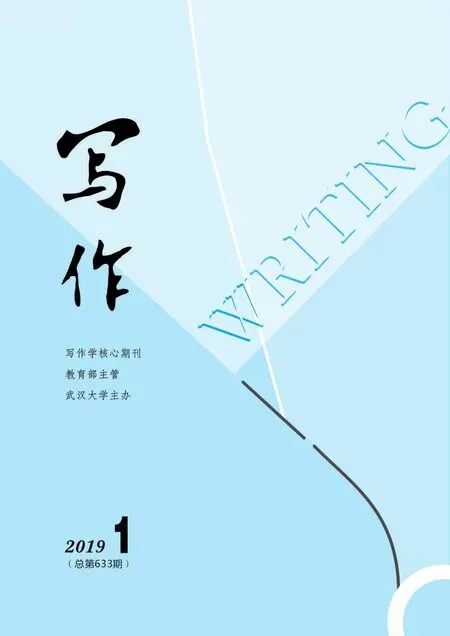一个“怀疑者”的离去
——《在医院中》呈现的唯意志论与怀疑主义的冲突
王芷晨
引言:从“多余的人”到“不快乐只是生活的耻辱”
瞿秋白是丁玲较早接触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之一,他牺牲前的遗书《多余的话》(1935年)真诚剖白自己更像是一位只会空谈的“多余人”,以此作为革命生涯的总结。瞿秋白面对的实践和空谈的矛盾症结在于自身内在人格的分裂性,即作为革命者理应扮演的角色和本来面目的自我之间的矛盾——作为革命者,他需要采取隐藏自己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追求的方式,将自己塑造为一位坚定、忘我的革命者,但同时他也常身处为一个异己者的矛盾之中。最终他在《多余的话》中忏悔了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革命身份的扮演性,这实际上是否认自我改造的有效性,从而维护了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多余的只是自己,而不是革命事业①参见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丁玲创作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即以瞿秋白为原型的《韦护》(1929—1930年),她敏锐觉察到了瞿秋白想要掩盖的这种分裂性。革命者韦护虽身着粗布衣服,但其精致的语言和精致的小窝却暴露了他私下的真实状态。和瞿秋白不同的是,叙述者最终安排韦护放弃了个人的爱情欲望,一并抛掷的还有他知识分子的趣味、私生活空间以及抽屉深处的诗稿(古典的感伤的文学趣味)。如果说《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捕捉的是现代自我理智与情感的对立,那么这部长篇小说通过“革命+恋爱”的公式想要触及的是革命工作、阶级立场的信念与知识分子个体的趣味、情绪之间的矛盾。20世纪40年代初期,丁玲创作了《在医院中》这篇新时期方才“翻案”的争议作品,主人公陆萍同样经历了异己性自我对主体的规训。与上述两篇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在医院中》试图处理的是“革命制度和革命理想的矛盾”②参见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贺桂梅语),换句话说,是思想的现实化过程和思想者本身的矛盾。
《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和韦护/瞿秋白最大的区别在于,尽管他们都能够意识到自我改造过程中的扮演性,但是瞿秋白最终是通过《多余的话》来忏悔并否认了这种通过“欺”和“瞒”来缝合自我裂隙的方式,陆萍则是逐渐认可这种方式是改造自己必由的中间环节。例如文中点明她认为有意修改的说话语调和为环境解释的习惯是十分必要的,最有症候性的表现是她曾引用“伊里奇”①笔者一开始认为这句话可能出自瞿秋白所翻译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 《伊里奇之死》,小说情节有微妙的吻合:例如伊里奇总是试图让自己体面地快乐起来等等。但是经过考证,原文中并无此句,所以不能贸然认定这句话的出处。根据老师和同学的讨论意见,伊里奇还是应该指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我们熟悉的列宁,但《列宁文集》卷帙庞大,笔者尚未详查,故录此备忘。的一句话来安慰自己:“伊里奇不是说过吗?‘不快乐只是生活的耻辱’。”②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这句话的问题在于其逻辑并不顺理成章,但口吻却言之凿凿。细究之,不快乐为什么不值得同情、安慰或者是寻找背后的原因以解决问题,却反而变成了需要避讳的“耻辱”了呢?陆萍不假思索地内化了这种思维方式,于是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③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问题就在于这始终被打扫的心情和始终愉快的基调上。小说的情节也照应了这句话的逻辑,即个人私领域的困扰是不正当的,无脚人不是就不在意自己的荣枯了吗?后文对这一逻辑的支撑是:不快乐意味着信仰不那么“单纯”坚定(“老练”),个人情绪的净化意味着革命方向以外的复杂性需要被统一,这显然有利于在艰苦环境中提高执行力。
这种被压抑而不是被消除的不快乐和复杂性,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文本阐释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启发:即阅读时需要我们调动“社会学上的想象力”(米尔斯)——“个人即政治的”④转引自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部分。,仿照丁玲的话⑤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原文是《“三八”节有感》中“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女子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于此借鉴,稍有改动。说,即把这些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
一、矛盾的叙述动力
在关于主体异化的理论中,拉康将得到认可且具有调节作用的“自我”定义为一个想象出来的他者,“自我”对主体有着召唤的作用,甚至很多实在的主体会被粉碎在自我想象中,从而保证对自身的认可、维持意志与行动的统一。⑥参见英霍默:《导读拉康》,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但是,《在医院中》中的陆萍只完成了这个理论的前半阶段,即她想象了一个自我,而后半段的召唤和代替最终都失败了。换言之,她的主体并没有被自我想象彻底地净化。
与之相对应的即是《在医院中》所采取的双重叙事视点策略:医院的环境和同事们的样子是由陆萍的内视点刻画出来的,同时又有一个更高的全知叙述者在审视着陆萍。
在陆萍的内视点中,医院的环境只有萧索混乱的一面,甚至连同事们的眼神都在微妙地传达着对自己的戒备和不满⑦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黄子平分析说,“这些颇具有杂文气息的对同事的第一印象”,反而暴露出了陆萍自己“一种对环境的‘过度反应’与‘自我防御’机制”。⑧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版。因而可以发现,小说通过将叙述视点集中在她自己一个人身上的方式来呈现陆萍和世界的紧张关系:不合理都是她内视点的关注重点。这种叙述技巧想要传达的究竟是外在世界的不合理还是革命工作者自身的问题呢?贺桂梅通过和同样与外在环境对立的个人主义者莎菲的对比,指出:“有理想而自愿带上紧箍咒的陆萍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不可解脱,她必须时时刻刻意识到外力的存在,并在对旧我的脆弱的指责中振作起精神来磨砺自己。”①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实质上,这表明置身于乡村民众之中的陆萍并未能自发地感受到作为革命主体的民众的革命性,相反,她所受的知识教育和感受世界的情感结构使她可以轻易地看出民众和粗糙的革命组织本身的问题,从而下意识地进行着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叙述者通过陆萍的内视点将知识分子和乡村民众的距离清晰地呈现出来,可以说是巧妙通过描述而不是下定义的方式勾勒出了一个需要接受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形象。
同时,小说还有一个更高的全知叙述者在审视着陆萍,他用大量笔墨展现了陆萍作为一个革命工作者建构自我形象的努力,似乎这位“上帝”想要引导读者去关注需要被改造的陆萍是如何成长的,这也符合丁玲创造这篇小说的初衷:“我想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我要写一个肯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是坚强的,是战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②新气象新开拓选编小组编:《新气象新开拓 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陆萍一出场“穿着男子的衣服,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地探照荒凉的四周”③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5、235、253页。。而回忆过去在学校的经历时:“她总是拿出这末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④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5、235、253页。叙述者这样总结她的性格:“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地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退让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得替他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末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⑤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5、235、253页。面对寒冷狭小的窑洞和不友善的室友,她采取的措施是“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可见,陆萍一直在试图表演出一个革命的自我形象,她采取否定本来自我的方式来改造自己以继续革命工作——而这个过程一面是“鼓励自己”带来的自我英雄化,另一面是“骂自己”这样原罪式自我改造论述的开始。
小说结尾甚至安排了一位无脚人来鼓励陆萍继续进行自我改造,从而使她能够在和现实遭遇落差之后依然为革命理想奋斗。同时这位无脚人还提供了一个对民众的新视点:“谁都清楚的,你去问问伙夫吧。谁告诉我这些话的呢?谁把你的事告诉我的呢?这些人都明白的,你应该多同他们谈谈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⑥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5、235、253页。读者这时候才发现,除了同事的冷漠,还存在着伙夫们的友善,而后者是陆萍没有看见的。这个新视点的引入就从外部瓦解了陆萍内视点的可信度,从而建构出对陆萍的反讽叙述。在多重视点的对话中,我们看见了陆萍身上被暴露出来的“主体”的确具有很多个人主义的东西,结尾给出的那些改造方式不完全是没有道理或者“机械降神”式的和解方式。所以丁玲对陆萍的一些负面评价一直是真诚的⑦参见《关于〈在医院中〉草稿》,新气象新开拓选编小组编:《新气象新开拓 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不是为了应对那些指责和批评而强行把陆萍说成一个需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习气的知识分子。
上述叙述技巧或许能够解释《在医院中》遭遇的争议,关注内视点的人会认为这篇小说满腹牢骚,而关注全知叙述视点的人则会同情陆萍的自我牺牲,但引入双重视点的概念之后,作者其实试图建立的首先是一种反讽的叙事格局,但随着叙述动力的偏移,以及读者认可主人公的情感惯性,导致小说被接受的样态也偏离了原本的设想。这种双重视角实质上和丁玲早期创作的一系列描摹“室内硬写”作家的元小说①在1928-1931年间的《仍然是烦恼着》(此篇是散文)《野草》《从夜晚到天亮》《年前的一天》《自杀日记》《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天》等都涉及了这一题材。“室内硬写”这一概念参见姜涛:《室内“硬写”的改造:丁玲〈一天〉读后》,《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一样都是在尝试用更高的叙述者来反讽人物(尽管主人公自己已然觉得自己进步了很多)。但《在医院中》为什么争议更大呢?相较旧时代的口诛笔伐,新时代的读者似乎更愿意将陆萍视作一个勇士②参见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钟山》1981年第1期。,正如本文也偏向将陆萍视作一位必要的怀疑主义者。
笔者认为,相比20世纪20—30年代“室内硬写”的青年作家们,作为革命工作者的陆萍遭遇的问题不仅仅是革命者自身的问题(例如理智与情感、精英立场和革命理论等),革命秩序本身也是作者所关注的。在这两种叙述动力的驱动之下,尽管全知叙述者暴露了陆萍作为一个革命工作者身上的分裂性和其党性的不彻底,但这种主体的扮演性和分裂性反而容易指向革命秩序本身的不合理,它导致医院新里来的年轻人的建议不被采纳,而这个敢于牺牲自我的怀疑者自身也被排挤了出去。
二、情绪的净化:针对思想者的彻底改造
从开头的 “不快乐只是生活的耻辱”到结尾无脚人对陆萍的亲切与不在意自己荣枯的生存态度,展现了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即是一种情绪净化装置的运作,它针对的就是实践环节中的思想者。借鉴存在主义的观点,焦虑与恐惧这些负面情绪具有提醒主体反抗异化、争取存在的积极作用,一旦人为排斥和压抑这种不快乐的情绪,就是人主动接受规训与异化的开始。主人公陆萍经历了一个从快乐到不快乐的成长过程,同时她的境遇也从主动融入到最终自我放逐、也被环境驱逐,这是否也是隐含作者遭遇的困境,即对于思想者而言,如果不能被净化,那么等待他的只有一个暧昧的离开/驱逐结局。
陆萍的身份很特别:她是一个经由组织被下放到基层的专家(不是像何其芳等诗人那样猛然经历了“天真遭遇现实”的困境),在下放之前,她就已经接受了一场——于自我价值期待与国家出于功利主义现实需要的安排二者之间的——磨合和自我改造。陆萍需要放下她不合时宜的投枪和对医疗伦理、制度的部分现代化要求,用身体的耐受力去适应这个低配版的现代医院。海涅的“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者的灭亡”在这里得到了具象的体现——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显得太不平凡。”③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这些思想者正如黄子平定义的那样,对“已成为惯例的”革命秩序而言是“外来的‘不洁之物’。尽管他们的意见往往在事后被‘组织’改头换面地采用,但通常是在‘组织’运用合法清洁手段‘处理’过他们个人之后”。④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问题在于,思想者的困扰真的只是类似于个人意志坚韧与否的问题吗?是小说里被流言转化为作风问题而被消解了正当性的私人事务吗?⑤这些不起眼的细节例如女同志总因为离婚问题被诟病,看似只是小说中的流言,但也透露出隐含作者对革命环境的观察与批判。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因为彼时革命的逻辑是三段论式的,如果你不能对革命理想抱有期待,那么你就必须遵从所有的革命秩序,包括接受它唯意志主义的自我超克方式。海涅对共产主义有一种类似“魔力”的表述:“一种可怕的三段论法把我捆住了,如果我不能反驳‘人人都有吃饭的权利’这个命题,那就得遵从从这个命题引出的一切结论。”①海涅:《〈卢苔齐亚〉法文版前言》,转引自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213页。这种单项因素的进化论确立了党的意义高于一切的信念——陆萍爱谈论未来,未来就是这个进化论的顶端,她是怀抱着对于那个最终命题的期待加入革命的,所以她也必须遵从这个三段论所得出的结论。而革命者的合法性建立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种三段论论述的存在——叙述者一开始就通过指导员的经历告诉我们:其他错误不要紧,“只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它什么嫌疑的”②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40、252页。——换言之,陆萍这样单枪匹马对群众有不耐烦情绪的革命骑士一定是没有“党性”的,其他人据此很轻易就可以否定她对于改良医院条件的种种建议。
丁玲刚来陕北时说:“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③《陕北风光校后记》,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9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这样的思路同样体现在文艺座谈会后的丁玲身上:“在克服一切不愉快的情感中,在群众的斗争中,人会不觉地转变的。转变到情感与理论一致,转变到愉快、单纯、转变到平凡,然而却是多么亲切地理解一切。”④《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这种对单纯的追求实际上是放弃个人主义之后又放弃了怀疑主义的表现。小说中的陆萍曾用一句奇怪的话来安慰自己:“伊里奇说过:‘不快乐是生活的罪恶’。”⑤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40、252页。这反映出陆萍一直在催眠自己认可的是:不快乐不仅不值得同情、疏导,反而成为一种需要被清扫的罪恶。个人的困扰直接的表现就是“不快乐”,可是这种情绪需要被净化,因为无论是女性还是知识分子的困扰都属于私领域而不具有合法性,因而陆萍也缺乏合法的有效的语言来表述这种压力和困惑,这种改造不仅仅针对理性的大脑,还针对了感性的情绪,单纯而圆满的状态才能够让革命队伍得到最大的整合,民族国家也才能够被建构在情感认同的坚实基础上。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是宣泄式的,换言之是疏导而非压抑和消除,这种情绪的净化只能引起知识分子要么脱胎换骨地告别思想者的身份,要么和革命队伍产生更大的距离。
小说篇末的无脚人是承担让陆萍获得启悟的重要人物,但这启悟过程看似顺理成章,实则掩盖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陆萍对无脚人情绪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她对革命秩序的认同。对陆萍而言,无脚人亲切的原因在于:首先,他遭遇了和自己一样而结果更严重的不公待遇;其次,他对自己像“家里人的亲切”“象同一个小弟妹”⑥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40、252页。的态度弥补了陆萍在医院感受到的冷漠。因而,他的存在和陆萍梦见回到故乡一样是一种现实补偿机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自我欺瞒色彩。正如学者黄子平指出的那样,谈话之前,无脚人就已经让陆萍感受到了精神的满足。⑦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因而,这里陆萍的认可革命秩序的逻辑是“爱屋及乌”式的,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早期普罗小说里著名的“革命+恋爱”的公式(如主人公因为爱上革命者而参与革命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直接处理转向经历,而是采取了一个“悬置+替代”的方式,最后陆萍的离去也说明作者不得不悬置了边区医院的一系列问题(如管理落后、卫生糟糕、资金短缺等),而让本来怀疑制度的陆萍转而去反思自己的觉悟是否不够。这种结尾看似消解了革命理想和革命制度的矛盾,但实际上是悬置了思想,驱逐了思想者,用苦行主义的耐受力去代替解决客观问题的行动力。
三、唯意志论对怀疑主义的暴行
结合彼时延安的历史语境,历时两年的长征(1934年秋—1935年10月)对红军而言,不仅具有保存革命火种的政治意义,还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美国学者莫里斯将长征带来的心理意义概括为“唯意志主义”,他指出,当毛泽东像先知一样将红军带出了非人的荒原以后,这段牺牲巨大的苦难经历“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这就是,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够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造历史现实”。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6页。这和陆萍获得的启悟何其相似:“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②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251页。然而让陆萍等看护险些丧命的煤炉事件已经说明“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肯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③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251页。的行为是可憎可恨的,即便假设陆萍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不消溶”,光靠意志的她仍无法避免身体极限被突破而导致的昏厥。陆萍和丁玲都没有经历过长征,因而她们不属于幸存的无脚人行列——在这样的差距下,她们必须进行自我超克。丁玲自己曾被国民党囚禁于南京,经历了“魍魉世界”,获救后向冯雪峰哭诉,却被制止了,因为在经历了长征的冯雪峰看来,只有以特殊的义务感和革命到底的觉悟,才能够不愧于长征的巨大牺牲。④丁玲回忆冯雪峰:“他是经过长征的人,受过见过多少苦难,他的心变硬了,他想到的是整个革命,而我只想到自己。于是我心胸立刻开阔起来了,坚强起来了,我更感到惭愧,觉得他的严厉是对的。”《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录》,选自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在这种唯意志主义的革命伦理下,陆萍和丁玲小我的荣枯自然算不得什么。正是在内化了这样的逻辑之后,丁玲为同样未曾经历过长征历练的读者们创作了《在医院中》这篇小说。
依靠唯意志主义建立的反讽叙事超越了现实的可行性,因而呈现出来的观感和文字背后隐忍的矛盾都和最初的写作目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震撼读者的不仅仅是结尾的格言和无脚人不在意个人荣枯的伟大精神,还有革命秩序对于革命精神的禁锢和驱逐。如何才能够避免思想者和思想的悖论悲剧,或许我们不仅要吸取长征精神,同时也要避免唯意志论对怀疑主义的暴行。
尾声:“怀疑者”离开医院之后
正如瞿秋白对丁玲的评价一样,丁玲的写作姿态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从莎菲式个人化的封闭写作挣脱出来后,她凭借新的叙述动力,创作了《杨妈的日记》《田家冲》《水》等“新的小说”,同时又在《年前的一天》《一天》等小说中通过反讽叙述清算了室内作家的感伤姿态和不切实际的革命浪漫主义思维。丁玲的选择一直是鼓励革命者进行无止境的自我超克,但在《在医院中》这篇小说里,不仅革命者的意志力被前所未有地发扬了,革命秩序的问题也深刻地暴露出来,尖锐的矛盾冲突之后,丁玲最终安排了无脚人的驱邪仪式,并让陆萍离开了医院——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写作主体悬置了革命秩序的问题,继续选择自我超克以至于自我被驱逐,成为一个遵从革命三段论逻辑的信徒。这影响了她后来的创作姿态,对比40年代的《我在霞村的日子》和50年代的《粮秣主任》这两篇通过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来讲述故事的小说,前者中的“我”尽管只是故事的见证者,但仍然有自己立体饱满的形象和质疑现实的能力,但后者中的“我”最常见的状态是“我不知道”⑤例如小说的结尾:“什么时候回到了我的住处,我不知道。”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因为这里的“我”只是一个跟随粮秣主任身影的传声筒。通过《在医院中》的驱邪仪式,丁玲作为写作主体最终进化为“无脚人”,完成了彻底不在意“个人荣枯”的改造方式。
丁玲回忆延安岁月时曾写道:“从一些感想性到稍稍有了理论,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①《陕北风光校后记》,选自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9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很像何其芳在投奔延安、经历自我改造后提出的一个“对于思想,对于人,都是适用的公式:‘单纯—复杂—单纯’……由原始的单纯,通过应该有的复杂,达到新的圆满的单纯”。②《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纂:《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中国青年》第3卷,第1-5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页。但他们似乎忘却了鲁迅的警告:“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③鲁迅:《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鲁迅选集·杂文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笔者想要追问的是,半现代化的边区医院这样一个被隐喻为解放区的场域,当质疑者离开后会发生什么呢?今天我们作为历史幸存者可以回答,我们的医院早就没有苍蝇了,陆萍的建议和想法都实现了,可是正像黄子平指出的,新来的年轻人已经被作为异物打扫出去。每一个思想的实现如果都需要这么多净化打扫,岂不是太不公平。于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光荣革命,并不等同于妥协和无计划地节约资本,还需要宽容的智慧和雅量,唯有如此,才会有更多鲁迅先生所说的敢于“直面现实的勇士”,更多使社会向上发展的“不满的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