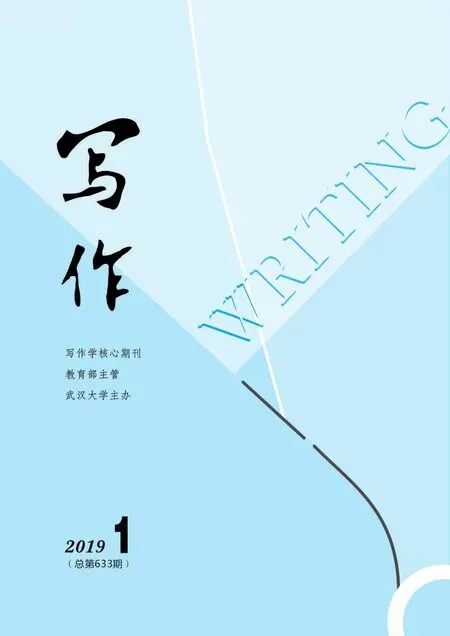“有难度的写作”:王家新的诗歌美学与伦理
魏天无
1992年寒冬,华中师范大学,武汉高校“一二·九”诗歌大赛现场。颁奖前的间隙,诗人、电台主持人余笑忠播放了他的同事、我的学弟肖新宇朗读的《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的录音带。当诗的声音穿越寒风呼啸、雪花翻卷的背景音乐而来,挤进了上千人的大礼堂鸦雀无声,以至能听见诗人的笔尖划过纸面的窸窸窣窣:
蜡烛在燃烧
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
整个俄罗斯疲倦了
又一场暴风雪
止息于他的笔尖下
……
如今,那座饱经风霜,有着一条条、一排排被磨得发亮的,从低到高的木质高脚椅的大礼堂早已被拆除;甚至没有废墟。但是,朗读者再现的诗的喑哑、沉痛却又愤懑、挣扎的声音,长久留在一颗颗热爱诗歌也热爱生命的年轻人的内心;只有这内心是不可褫夺的,如同诗歌:“蜡烛在燃烧/我们怎能写作?/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那一声凄厉的哀鸣/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来自我们的内心……”
将近三十年后,王家新在《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译序(2016)中引用曼氏诗句:“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看进你的眼瞳/并用他自己的血,黏合/两个世纪的脊骨?”并问道:“是的,从曼德尔施塔姆,到我们这个世纪,我们谁不曾感到了历史这头‘野兽’的力量?”①王家新:《译序》,[俄]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也是在这一年,诗人写下《在大堰河的故乡》,其结尾是:
我忽然觉悟到一个诗人最好的位置
也许就是那个带铁栏的窗口
在一个落雪的变暗的下午
在不同的时代,手中仅有一支笔的诗人的位置在哪里?又如何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如果世纪如一头“野兽”,诗歌如何获得能与之相匹配,乃至相抗衡的语言力量?这或许可以看作诗人王家新在持续四十年的写作中未曾忘怀、未曾中断的诗学路径,一条“向海之路”(《从石头开始》,1983)。它朝向的是一个无边的、未知的广阔世界,也是词语的危险地带。在那里,诗人写下的每一行句子,每一个词,或许会被个人无法左右的无名力量所删削、涂抹、篡改,但它们终将在黎明时分裸露出坚硬的、熠熠生辉的内核。
王家新是当代中国诗歌的一位标志性诗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写作从朦胧诗时期一直活跃到当下,也不仅是因为他兼具诗人、翻译家、随笔作家、批评家、学者等多重身份,以及他的写作与译介、与研究、与批评之间存在相互“激活”的关系,而且是因为,他是一位在所谓的“多元”时代,在反智主义与犬儒盛行的时代,持守诗人的职责与使命、诗歌的伦理诉求的诗人。他甚至是一位相当“自我”的诗人——“自我”到某些自以为是的写作者感到不习惯、不舒服——也是一位要让这“绝对自我”的声音,穿过历史重重雾霾,并因此裹挟着微小到肉眼无法看到的雾霾颗粒的诗人。或者说,他是一位他曾论述的阿甘本所言“不合时宜”的诗人,与他所敬仰并译介、研究的众多诗人处于“同时代”的诗人;也正是在这些诗人身上,他持续地发出他的“诗歌之问”也是某种“世纪之问”:“也许,这就是从曼德尔施塔姆,到后来的中国诗人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必须把自己的凝视紧紧锁定在其世纪野兽的双眼之上’。可是,他能做到吗?”①王家新:《诗人与他的时代——读阿甘本、策兰、曼德尔施塔姆……》,《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阿甘本认为:“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有才智的人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他同时也知道,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②[意]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不仅王家新所倾心推介的域外诗人和中国诗人杜甫、冯至、穆旦、昌耀等属于这样的诗人,而且这也是身为诗人的他在“向海之路”上艰难跋涉所祈望的“真实”境界:“真实有时是一种让人目盲的东西,甚至,是一种被卷到巨轮下才能体验到的东西。纵然如此,一个诗人又必须走向前去。是的,必须。”③王家新:《诗人与他的时代——读阿甘本、策兰、曼德尔施塔姆……》,《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这种“真实”,建立在诗人与其时代之间,也建立在他与词语之间,最终建立在他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中。这也是诗人朵渔为什么说,王家新“孤立地坚守在他的理想主义晚期,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庄重和持守,对抗一切时尚话语的冲击”;他“是要坦诚地面对世界,进入世界,从而创建一个敞开的世界,因而他的诗是‘走心’的。惟其‘走心’,才会诚心正己,不自欺,才能坦然地将心比心,不修饰邀宠,坦诚地与读者对话”。④朵渔:《从歌哭中寻找拯救的力量——王家新诗歌印象》,《草堂》诗刊2017年第11期。当然,他是在与那些同样“不合时宜”、同样坦诚的读者对话。一位“诚心正己”的诗人必然是挑剔的,这种挑剔首先针对自己笔下的每一个词语,然后是对待诗的严正态度:它会让阅读者不由自主地挺直日常中呈弯曲状的脊椎。“严正”,同样是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诗学词汇之一。
王家新是一位罕见的、一以贯之的抒情诗人,至今未有改弦易辙的迹象。这是他“不合时宜”的另一种表现。在“反抒情”成为写作时尚——对,时尚——的时代,“抒情诗人”几乎被打入另册,被当作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无关的“非诗”写作。但那是他们的“时尚”,他们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王家新曾在《“喉头爆破音”——对策兰的翻译》①王家新:《“喉头爆破音”——对策兰的翻译》,《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279页。中谈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反抒情”时代,王家新的写作——不限于诗——仍然具有确证自我、启迪人心、揭示现实的巨大力量。他就是那个“奔行呼喊在这个世界和我自己的黑暗里”(《晚来的送货人》,2018)的人,不会被轻易撼动,却依然会被眼前那些细小卑微的事物所触动。抒情这种看似古老的诗歌传统通过一位诗人的再生要告诉我们的是:“你已无处可去。你注定要在这临海之地承担起人类的孤独。”(《临海孤独的房子》,1992)“我也只能从我的歌哭中找到/我的拯救。”(《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录》,2016)
学者吴晓东将“在词中跋涉”的王家新称为“寻找词根”的诗人。他以“雪”和“黑暗”为例,阐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人在对“词根”的执着寻找中,给诗歌带来的“隐喻的深度,思想的深度,生命的深度与历史的深度”②吴晓东:《王家新论》,《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学者洪子诚也从诗人此一时期的写作中,提取出“北方、寒冷、雪”,“精神血脉”,“轰响泥泞”,“另外的空气”,“姿势”,“瞬间”等关键词。③洪子诚:《读作品记:〈塔可夫斯基的树〉》,《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5日。而诗人对“词根”或“关键词”或他自称“基本词汇”的寻找与反复打磨、擦亮,目的是“自我辨认”④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页。。他谈及翻译时也强调,那“只是出自爱,出自生命的自我辨认”⑤王家新:《回答雅典“周日论坛报”的书面采访》,诗生活网站“诗观点文库”,网址: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libshow&id=4140。。“自我辨认”也就是辨认语言与现实、历史与当下、美学与伦理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这一切,当然首先建立在对词语——诗人拥有的最微小又最稀有的矿石——的辨认上。
诗人自述,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词”的问题,这种关注“不仅和一种语言意识的觉醒有关,还和对存在的进入,对黑暗和沉默的进入有关。这使一个诗人对写作问题的探讨,有了更深刻的本体论的意义”。但这种关注会被现实中断,此时诗人更清醒地意识到,“‘词’不再是抽象的了,它本身就包含了与现实和时代的血肉关系”⑥王家新:《“走到词/望到家乡的时候”》,《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228页。。1979至1989年的诗作被诗人视为“练习曲”,与《瓦雷金诺叙事曲》同时作于1989年的《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被诗人看作“转变”期的开始⑦王家新诗集《重写一首旧诗》共分三辑,其中第一辑为“练习曲(1979—1989)”,第二辑为“转变(1989—1999)”。《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位于第二辑开篇。王家新:《重写一首旧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
比一阵虚弱的阳光
更能给冬天带来生气
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
双手有力,准确
他进入事物,令我震动、惊悚
而严冬将至
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比他肩胛上的冬天
更沉着,也更
专注
——斧头下来的一瞬,比一场革命
更能中止
我的写作
我抬起头来,看他在院子里起身
走动,转身离去
心想:他不仅仅能度过冬天
如同“雪”,“严冬”也是王家新的“基本词汇”之一,是其诗歌在词语的延展中得以站立起来的冷峻、严酷的背景。它既来自北方地理气候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同诗人在“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的“呼应”①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页。,也源于他所敬仰的俄苏诗人以此召唤强有力的生活信念和精神信仰的影响。在这一既是写实也是象征的景观中,“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更像是一位以词语为木材、为火焰而取暖的诗人的写照;他不是木匠或手工艺人,但同样需要“双手有力,准确”,需要“更沉着,也更/专注”。“中止”一词预示诗人意识到原有写作的“失效”,他将像劈木材者那样,以“有力,准确”的词语楔入现实。
“对词的关注”不仅是出于对“何为诗歌”这一诗学本体论的思考,同时隐含着诗人对这个世纪诗歌命运和诗人使命的探索。这种探索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渗透在诗人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包括为人称道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等,也包括长诗和“札记”体诗。这种思考和探索终将导向每一位诗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写作”。在长诗《乌鸦》(1995)第六节,诗人不间断使用32个“为”字句,试图予以回答。这一问题对彼时的诗人如此紧迫,如一把利刃高悬头顶,散发出冷冷寒气。长短间用、虚实叠合、时空交错的语句,呈现着诗人陷入精神的迷狂状态。他手中的笔在颤抖,写下词语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思想的游弋。他苦闷、窒息已久,终于在一个欲雪的夜晚,思绪喷薄而出。从农业文明时代(“燕子”)到工业文明时代(“汽笛”)再到后工业文明时代(“时装女郎、广告女郎”),诗歌已成为“被毁灭的天使”,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孜孜以求,为之献身?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杰出诗人(但丁、T·S·艾略特)对此或许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但对于诗人,答案只有一个:“为命运再次对我说话。”而命运注定诗人倾心于“对困难事物的爱好”,注定诗人的一生与恐惧、痉挛相伴,只能在死后获得自由呼吸(“为涌上我喉咙的一阵大雪,/为了在死后呼吸”)。命运注定诗人以“自虐”者的形象现身,因为在诗歌遭受虐待的时代和国度,诗人对完美理想、崇高精神、纯洁心灵的坚执,无疑会被视为疯癫的。命运注定诗人是被驱逐的人,被流放到沼泽地的人,那里是为人类灵魂洞察者所设立的“集中营”。命运注定诗人要说出真理,要以诗救赎人类的良知和正义。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和过于悲壮的理想。诗中的词语,在风雪裹挟而来的压抑、紧张和黑暗中发出光亮,在寒冷的生活中聚拢诗人仅存的体温。诗人浩叹:“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已被写下,/我在等着那惟一的事物的到来。”“惟一的事物”即写作所追求的终极事物,为词语所映射,如同史蒂文斯所说,“一个诗人的词语是属于没有这些词语就不存在的事物”①[美]华莱士·史蒂文斯:《高贵的骑手与词语的声音》,陈东东、张枣编:《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陈东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诗人是不可见事物的传道士”②[美]华莱士·史蒂文斯:《徐缓篇》,陈东东、张枣编:《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张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等着”——王家新的另一个“基本词汇”——是隐忍与磨炼,是相信付出终有回报;是让“我”消失,让词语开口替“我”说话,或者如策兰那样,“等待语言向我说话”。
王家新曾说:“在我们的这种历史境遇中,承担本身即是自由。”诗人必须把自己“置于历史和时代生活的全部压力下”来写作。③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诗人的写作当然也折射出这种压力。“承担”而不是回避或解构压力,是他认同的诗人在这个时代的职责和使命,这使他的写作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多了一份厚重的历史意识,一股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气息。库切认为:“我们的历史存在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部分,而我们现在的这一部分就是属于历史的那一部分。而我们所无法完全理解的恰恰就是这一部分,因为,想要理解这一部分,我们就得在理解自己时,不仅将自己看作是历史种种作用的对象和客体,而且将自己看作是历史的自我理解的主体。”④[南非]J.M.库切:《何为经典?——一场演讲》,《异乡人的国度》,汪洪章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理解自己”实际上意味着王家新所言的“自我辨认”:辨认“历史”与“现在”的关系,辨认自我在写作中的位置和处境,辨认词语在“全部压力下”所能迸发的全部能量——这是词语的极限,也是写作的极限,为诗人所迷恋和触碰。
“我仍在梦想着一种词语与精神相互吸收、相互锤炼,最终达到结晶的诗歌语言”。⑤王家新:《“走到词/望到家乡的时候”》,《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对词的关注”,对“结晶的诗歌语言”的梦想,似乎必然地把诗人导向另一个“不合时宜”的诗歌信念:“有难度的写作”或曰“写作的难度”。王家新认为杜诗的价值在于其难度,既是“语言的难度”也是“心灵的难度”,是两者之间的相互砥砺、磨炼,也是相互的映射。“有难度的写作”必然涉及现代诗歌在阅读接受中屡遭公众诟病的“读不懂”“晦涩”等问题。许多诗人为此展开过论辩。王家新认为,诗歌“自身的艰难”就是诗本身,“它的深度与高度、伟大和光荣,也只存在于这种艰难之中”⑥王家新:《“你的笔要仅仅追随口授者”》,《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页。。他在《答荷兰诗人Pfeijffer“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中写道:
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
比如说杜甫晚年的诗,比如策兰的一些诗,
……
它们是诗中的诗,石头中的石头;
它们是水中的火焰,
但也是火焰中不化的冰;
这样的诗就需要慢慢读,反复读,
(最好是在洗衣机的嗡嗡声中读)
因为在这样的诗中,甚至在它的某一行中,
你会走过你的一生。
比如我写到“去年一个冬天我都在吃着橘子”,
我吃的只是橘子,不是隐喻;
我剥出的橘子皮如今堆放在窗台上。
……
这首诗的重心与其说在前半截对“令人费解”的辩解,不如说在后半截将读诗行为与读者“走过你的一生”绾结在一起,甚至不如说,是在诗人“不经意”的插入句“最好是在洗衣机的嗡嗡声中读”:这样的诗既无限接近于日常生活的嘈杂,又竭力让人的心灵和精神超拔到梵音的境界中——诗人和读者皆须具备从市声中精确“辨认”梵音的才具。至于结尾的“橘子”是否为隐喻,吴晓东有精当的分析①参见吴晓东《王家新论》,《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不过我以为,“比如”之后的语言重心不在“橘子”而在堆放在窗台的“橘子皮”。这一日常而又非常的意象,对应着诗人在阐述“有难度的写作”时所提出的“意义的空壳”:“写到今天,一个诗人就不得不与时间和公众的接受展开斗争。我要让它 ‘掰不开’,掰开了就完了,就成了意义的空壳了——如同我们的生活本身。”②王家新:《“你的笔要仅仅追随口授者”》,《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易言之,诗人恪守“有难度的写作”,不是出于艺术技巧上的考虑,更非有意为难公众,而是出于超越生活的空洞,直抵为此空洞所忽略的残酷的现实真相。这就是阿甘本在论述“同时代”时所强调的:“同时代的人是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以感知时代的光芒及其黑暗(更多的是黑暗而非光芒)的人。”③[意]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王家新或许同意如下说法,诗歌只能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那些与诗人一样,或者在诗歌的引导下,去艰难地“自我辨认”的人。他的写作给人留下朝向经典写作的印象,不足为奇。库切曾引波兰诗人赫伯特的话说,历经时间检验、野蛮浩劫而留存下来的东西被称为“经典”,并非因为所谓的“内在品质”,相反,“是因为世世代代的人民不愿舍弃它,是因为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所谓经典仅此而已”。④[南非]J.M.库切:《何为经典?——一场演讲》,《异乡人的国度》,汪洪章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而在王家新所译介的诗人诗作中,我们会深刻体会“何为经典”的真实含义。
具体而论,“有难度的写作”在王家新那里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对写作的“绝对意义”的追问。王家新在谈论凯尔泰斯·伊姆莱的作品时说,后者写作中对人类灾难、创伤的“绝对意义上的追问”,那种“具有不朽的灵魂质地的文字”,“照亮的正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长久以来所盲目忍受的一切”;而“离开了这种绝对意义上的自我追问,我们怎能思考文学和灵魂的奥义?又怎会有‘另一个人’的诞生?”⑤王家新:《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223页。诗人对那些饱受风雪、历经劫难,而始终不放下手中轻若鸿毛又坚如磐石的笔的诗人诗作的评介,他自己对苦难、压抑乃至“喘不过气来”的生活的揭橥,以及近期写作中对卑微渺小的人与事的敬重与悲悯,正是为了一次次逼问自己“为什么写作”,而答案如前所述,“为命运再次对我说话”。为此必须“等待”,必须“在词中跋涉”,保持一种“艰难地贴近事物的姿态”。①王家新:《“走到词/望到家乡的时候”》,《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
其次是对“绝对性语言”的追求。何谓“绝对性语言”?它是否会导致另一种“纯诗”,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远离现实的诗”?或者,它恰恰指向的是“纯诗”,一种剔除了语言杂质、具有奇妙的音乐性、呼应着生命律动的诗?王家新将“绝对性的诗人”的称号赋予勒内·夏尔,因为他的语言中燃烧着“极端的碳火”,“但他又总是把不同的元素和相互矛盾的东西奇妙地结合为一体——为了那‘纯粹的矛盾’即生命本身……”。②王家新:《语言激流对我们的冲刷——勒内·夏尔诗歌》,《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诗人的使命,正在于将属于生命本体的这种“纯粹的矛盾”,在词语中达成平衡与和谐,却并不抹去而是凸显生命中紧张对峙的境况。这也正是王家新在40年写作中,交替试验不同体式的写作——抒情短诗、“札记体”诗和长诗,包括不分行的诗——的缘由:这是何其艰难的“在词中跋涉”。且以《田园诗》(2004)为例: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
你会经常遇见羊群
它们在田野中散开,像不化的雪
像膨胀的绽开的花朵
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被吆喝着
滚下尘土飞扬的沟渠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
在一个飘雪的下午
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良,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
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着它们
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
诗人阐释过这首诗对传统“田园诗”的反讽。它并没有他在20世纪90年代诗中常有的不可遏制的抒情性,反而有某种平静的叙说,暗相呼应着羊群眼神的“温良”“安静”;恰恰是这种无辜的“温良”“安静”,与生俱来的“好奇”,让诗人感受到“撕开了我们良知的创伤”,并追问“这种注视是谁为我们这些人类准备的”?③王家新:《在诗歌的目睹下》,《天涯》2007年第6期。无论诗人的自我阐释是否存在“意图谬误”,所谓“绝对性语言”并非古典诗学中的“以少胜多”“以一当十”,也并非现代诗歌意欲通过对词语的“高度提纯”来达到光滑、流畅、悦耳的艺术效果。“不化的雪”隐喻着观看者与被看者的相似命运。实际上,观看者与被看者、主体与客体、人与物……随着结尾的“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而一同“消失”:正是在这里,诗人返身古典诗歌永不“消失”的抒情传统,那种主客不分、物我混融、天地一心的抒情传统;它其实一直在那里,在诗人的词语中,成为“不化的雪”。在此意义上,王家新所言“绝对性语言”可称为“极限语言”,也就是他在称赞曼德尔施塔姆流放沃罗涅日时所写的诗时所说,“意象的奇特、语言的精确和艺术的灼伤力都达到了一个极限”①王家新:《一份迟来的致敬》,《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页。。“极限语言”无疑是“有难度的写作”,而最终可能指向不可能实现的另一种“纯诗”,一种“极限写作”。
第三是对“经验的幽暗部分”的追索。将笔尖深入人类精神层面,在那里显现出不同时代的创伤性经验,是王家新90年代以来诗歌的显著特征。如果按照阿甘本的论述,在感知时代的光芒及其黑暗上,诗人更多的是感知黑暗,因此,王家新与他所译介的诗人能够成为“同时代人”:“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②[意]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王家新自述,新世纪之后的写作确实更倾向于这种“蘸取当下的晦暗”,他也很赞赏学者、批评家陈超的说法:“经验的幽暗部分。”③吴投文:《“当一种伟大的荒凉展现在我们面前”——五〇后诗人访谈之王家新》,《芳草》2016年第2期。他曾举茨维塔耶娃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笔记中所写到的,怎样以词语来表现呻吟“nnh,nnh,nnh”为例,认为“这是发自体内的最真实的呻吟。这是生命的呻吟,也是死亡的呻吟。这是呻吟,但也是呼唤。这是语言的黑暗起源和永恒回归”④王家新:《“新鲜黑暗的接骨木树枝”》,《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这里不仅涉及如何以词语呼应生命或死亡的召唤,涉及应生命或死亡之召唤而降临的词语,以及词语对文本之外的读者所发出的召唤,而且触及前述“绝对性语言”或“极限语言”的来历和归宿。
“有难度的写作”归根结底是用生命写作。诗人与他推崇的那些诗人一样,将生命与写作视为一体,无法分割;它们相互依存也相互激发,相互赐予也相互索求。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一种近乎古典的文学观念,却是当下现实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当下生活的“盲目”性、“空壳”状而凸显出它与我们的“同时代性”。诗人要理解的正是历史与现实相互叠合的那一部分,诗人要用词语映射的,正是卡尔维诺所言的“必要而又困难的部分”⑤卡尔维诺:《狮子的骨髓》,《文学机器》,魏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或者说,只有通过这样的“极限写作”,我们才能探察人类生存的诸种可能性。王家新不止一次提及茨维塔耶娃的诗句:“……用我的血来检验/所有我用墨水写下的诗行。”他也曾转述阿赫玛托娃回忆录中的一个细节:莫斯科的一个街口,曼德尔施塔姆非常镇定地对女诗人说,“我已做好了去死的准备”。王家新由此感慨:“没有这种思想的勇气,生命的勇气,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⑥王家新访谈:《曼德尔施塔姆:语言比国家更重要》,搜狐文化,网址:http://www.sohu.com/a/109592469_458191。希尼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说:“……我相信诗歌,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和在所有的时代,它都因为它在真正的意义上忠实于生命而值得相信。”⑦[爱尔兰]谢默斯·希尼:《相信诗歌:诺贝尔演讲(1995)》,《开垦地:诗选 1966—1996》,黄灿然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55页。当然,希尼相信的只是他自己和他所认同的“忠实于生命”的诗歌,那些倾听生命的召唤并在词语中予以回应的诗歌。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王家新的诗歌呈现出回归“日常”、介入“当下”的特质,似乎与新世纪诗歌的整体趋势有着某种合拍。在谈及近几年的写作时,他说:“它们更多地回到了 ‘日常’,进入了记忆,更关注于细节、生命的质感和‘当下’的感受。”①王家新:《“你的笔要仅仅追随口授者”》,《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当然,这种回归与介入,依然延续着他对诗歌美学与伦理的思考。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历史的“强行进入”造成的写作的断裂、中止,使王家新“转向”建构一种“承担的诗学”。最近几年,王家新的写作则更多地“转向”对个人与他者日常生活状态的内省,其中渗入反讽意识,可称“内省的诗学”或“反讽的诗学”。他在谈及叶芝这位“激情的、痛苦而高贵的抒情诗人”时说:“叶芝的诗之所以能对我产生真实的激励,就因为他在坚持‘溯流而上’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复杂的自我反省意识。”②王家新:《叶芝:“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以王家新的近作为例,他在《黎明时分的诗》(2012)中描摹了一只机敏、忙碌的小野兔,数年后在《来自张家口》(2018)中,他再次写到野兔,“两只剥了皮的野兔”:
有人从张家口给我托运来了
一箱蘑菇罐头
两只剥了皮的野兔
和一大袋土豆。
野兔送给了亲戚,
土豆留下。但每次给土豆削皮时,
我都想起了那两只赤裸裸的
被吊起来的野兔……
我也只能遥想一下坝上的茂密草原,
获得一点所谓的安慰。
当两首诗里的野兔交错闪过,我们可能仍会将此具有“绝对的写实”风格的形象,与命运、痛苦、啮心、创伤等诗人的“基本词汇”相连;甚至“那两只赤裸裸的/被吊起来的野兔”,令人不由得不想到诗人当年透过车窗所看到的,有着“温良”“安静”眼神的羊群。诗歌的抒情有着明显的节制,但他沉郁、忧伤、悲悯的基调没有改变。结尾处经“遥想”而获得的“所谓的安慰”,看似平淡实则有着锐利的反讽:反讽之矛的尖,正对着自己的心。
吴晓东认为,王家新晚近诗歌构建的是一种“生活的伦理”,体现在“与大千世界的共感之中,这种与石头、树木、老马、羊群、过冬的牲畜之间的共感,是一种健全的社会伦理学的基础,一种健全的伦理学和健全的社会生活只能以这种内在的悲悯的情怀作为自己的底蕴”③吴晓东:《王家新论》,《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不过,如果我们认同诗人长达四十年的写作构成一部相对完整的“生命诗学”,与其说“生活的伦理”的建构显示出诗人“对90年代初期回归内心叙事的某种超越”,毋宁说,诗人在秉持“内在的悲悯的情怀”的同时,从另一个向度回归了90年代初期他曾辨析过的“个人写作”。1993年,他在谈论冯至时,就将莫衷一是的“个人写作”锚定在“知识分子精神”上:“一个知识分子诗人只能通过内省来达到对现实更深刻‘介入’——他并非逍遥于时代之外,但他却是坚持从‘个人’的写作角度来观看这个世界的。”①王家新:《冯至与我们这一代人》,《读书》1993年第6期。。冯至与“我们这一代人”,无疑是“同时代人”。其后他在谈论“当代诗学”时说,“个人写作”这一命题的最终指向,是“达到能以个人的方式来承担人类的命运和文学本身的要求”②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关于当代诗学》,《诗探索》1996年第1期。。始终以“个人”方式介入历史和现实,以“个人”的语言创造力去发现生命奥义,这不只是诗歌的美学要求,同样是伦理要求。这一点,在王家新那里从未改变。
不妨说,诗人王家新一直“跋涉”在寻找那棵也许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单的树”的路途中,不一定是为了致敬,是为了让它再次“生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泪水的播种期”(《塔可夫斯基的树》,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