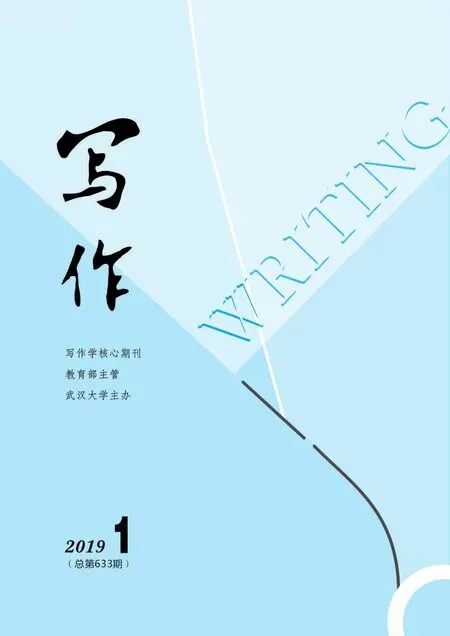“摩登”与“魔道”
——《凶宅》的多重空间建构与叙事生成
鄢予晨
《凶宅》这篇小说收录在施蛰存1933年出版的《梅雨之夕》中。这个集子中的作品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多被归为“心理分析小说”一类,主流解读亦多以弗洛伊德主义话语为切入点。仅从主要内容和叙事氛围来看,《凶宅》又可被归入以《魔道》《夜叉》等为代表,以暴力、色情、魔幻、凶杀等元素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的“魔道”系列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凶宅》在叙事组织方面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它是作者施蛰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先锋”理念的折射,也是他所融合的国内外文学资源的一个横切。本文将从小说多重空间视野,即文本空间、心理空间、文化空间三个方面的营建,来对《凶宅》的叙事组织方式加以观照。
一、文本空间:杂糅的文体图景与叙事美学
从技术层面来讲,《凶宅》对于文本内部空间的充分利用和挖掘,是小说叙事的完整性和逻辑框架搭建的重要因素。在《凶宅》中,多种文体形式的混合运用以及精心设计的伏笔与情节反转,在形式和逻辑两方面支撑起这样一个非线性、跨时空的小说叙事。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所要关注的是,文体空间在小说的叙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并最终以什么样的机制参与了叙事的有机生成。
(一)文体形式:纸媒、日记和供述
文体形式的杂糅可以说是《凶宅》给读者呈现出的最直观特征之一,作者将多种文体嵌套在情节开展的过程之中,形成了多重文本空间。这些文体既包括常见于“五四”之后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日记、报纸新闻,还包括相对并不常见的证人回忆、口供陈词等。不同形态的文本在线性的叙事中,作为不同时间、不同视角的叙事载体,造成了文本中时间倒错、空间分离的效果,更进一步制造了紧张、悬疑的氛围,于是《凶宅》中三起女人自缢事件的真相就更加显得扑朔迷离。
陈平原在谈到小说中插入其他文体形式时曾总结说,作家会“在小说叙述中大量引入书信、日记、笔记,借以补充固定视角产生的视域的限制”①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93页。。《凶宅》中无论是日记还是状词,的确都呈现出这样一种“装匣式”的特征。因此,小说中的事件真相在这些文本空间的配合中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的过程:詹姆士连环杀人犯的身份,弗拉进司基妻子事发前已经身染重病,弗拉进司基、莫哈里尼和玛莎林②作者按:人物名字均使用小说中首次出现时的名字,即人物的假名。三人在几个月时间内的爱恨纠葛……这些极具私密性的事实以及非当事者不可知的细节,在日记和状词中终于有了合适的安放位置,同时为真相被藏匿数年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当它们被并置于小说空间中时,就用“相当内在化的形式来表现一种相当外在化的行动”③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93页。。通过让读者走入不同文本空间、站在不同的限制视角上一步步自觉拼凑出事件的全貌,作者引导着读者重构人物的情感、行动轨迹和其中复杂的相互关系,形成一个实际的“上帝视角”。这样的方式一方面提供了更纷繁复杂的人物情感、形象和人物关系图景,另一方面又能够做到严格将故事的边界锁定在几个主要人物的关系中间——不求助于大量外部经验的引入,而是诉诸既有叙事的“破”和“立”。所以,它才能既参与对“凶宅”鬼魅表象由内而外的有力拆解,又维护了情节组织的可信度和逻辑性。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写道:“现代审美的习惯是,偏好那些不声不响却能‘告密’的细节。”④[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小说中珠宝商的日记和提琴师的讲述都提及的“三等舱旅费”,如果没有细节上的对接互证,便很难有人会想到它其实无意中成为玛莎林痛苦自杀的导火索。这种对接也被詹姆士在谋杀行动中付诸实践:“我心中想到了李却所说的话,走上楼就留心考察这房间,我想佛拉进司基实在傍晚时候看见他妻子背后的墙上有绳索影子的。”⑤施蛰存:《凶宅》,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一卷·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作案完成后,詹姆士故意遗留绳索和粘贴薄纸的半身人影的举动颇有深意,简直可以算是对人类思维因细节的弥合生成的自为整体的假象开了一次巨大的玩笑。
作为另一种在叙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文本,报纸文章的流传、译介在《凶宅》中已经“并不是再现的客体,而恰恰是小说生产的条件”⑥郭诗咏:《论施蛰存小说中的文学地景——一个文化地理学的阅读》,《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3期。。不同国家的纸媒在客观上提供了国际视野,扩大了小说的想象空间,人物获得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复杂体认。报业媒体在实现知识分享、信息流通的时候,本身在阅读期待层面上获得了权威地位,这使得《凶宅》中的报业媒体成为一个可操作的空间。报纸既已被潜在认定为客观性和知识性的代表,媒介语言对读者的有力引导性也由此生成。我们可以注意到,开头处《英文沪报》的文章已经先在奠定了“凶宅”的基本论调,也成为聚合大众经验的基本途径。国际范围内流通的报纸在一次次的文字译介、转述、确证中抽丝剥茧,连接成了一个跨境故事。在时间和空间都存在着巨大区隔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报纸不断被阅读和转译一直维系着小说叙事的链条——报纸将因当年的事件分散的人物重新集合起来,并为嵌套在内部的日记和状词连接情节、揭晓真相提供了最终的可能。
(二)“缺席”/“在场”的张力结构——反转的生成
如果说前一部分对文体的探讨是叙事展开的形式基础,那么如何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些文体的力量,让它们有效参与叙事的设计才是真正体现作者用心的地方。刚开始看上去三桩彼此独立的事件,实际上被作者设计成“2+1”的结构:前两起事件生成于巧合/误会,是事件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最后一起生成于人为的阴谋。伴随着真相一起展开的,是一系列由作者安排的人物“缺席—在场”的对比关系对读者的认知的不断反转,从而达到重新建构事件真相的效果。
若延续1919年《英文沪报》的思路,我们大概会对“凶宅”事件生成如下几个判断,作为接下来进入故事的假定前提:三起事件彼此独立;妻子一方确系自杀;自杀原因不得而知。如果这些假定被读者接受为默认事实,那么珠宝商弗拉进司基在第二起事件中的实际“在场者”身份便可以很好地得到遮蔽——既然读者根本无法想到他会在第二起死亡事件中扮演角色,那么也自然难以触及三角关系、情感纠葛等事件分支。在现实层面上,玛莎林的死亡让弗拉进司基和莫哈里尼两人保持在只掌握有部分真相的状态。他们两人对“凶宅”事件的讲述被分隔在两个时空、两种文本之内进行,“婚外恋”事件本身的隐蔽性、日记形式的私密性以及弗拉进司基的死亡,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人对话的可能。他们也无法先于读者察觉、揭露对方的“在场性”。而在第三个故事中,丈夫詹姆士身份在结尾处的反转,可以说是对前文呈现的一切带有好奇的猜测,赚人眼球的戏剧化的夸张形成了巨大的反讽。由于公众并不知晓前两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就更没有人去单独怀疑第三起案件在“凶宅”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这时,似乎唯有神秘力量作祟,才能够在短短时间内使得三个背景相似的女子呈现惊人相似的死因和死状——“凶宅”之“凶”至此才真正形成。
如果说存在于弗拉进斯基与莫哈里尼身上的“在场”与“缺席”是无意为之,那么詹姆士对于“在场”和“缺席”假象的构造,再利用细节的弥合,不停地在熟人和大众认知中制造一个个的烟幕弹、生成对于超自然力量的认定后,便更不会有人去过多追查。对大众心理的把握成就了这“技术最巧妙的一件”①施蛰存:《凶宅》,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一卷·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谋杀案。施蛰存真正充分利用了文本空间,完成了这样一场精心设计、逻辑通顺的思维游戏。
二、心理空间灰色地带:“现实”和“鬼魅”之间
曾有研究者指出,《凶宅》虽然带有“鬼故事”的色彩,但由于最终以真相大白的结局消解了“鬼魅”设定,所以将这篇小说的主题系于理性精神的体现。然而无论是从作品本身,还是从施蛰存这一时期的写作理念考虑,这样的判断未免过于草率。如果说所谓的“理性”的落脚点,仅在于证明所谓的凶宅中并无凶物的“鬼魅”叙事的消解,而仅把“鬼魅”看作在人类在自我思维经验所不及之物面前的反应机制,《凶宅》文本中的一些表述,却实际呈现出了超越这种限定的特征。
按照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那些在小说中有机会“发声”的男性角色,在面临情感现实与内心的矛盾时,必然会通过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来压抑冲动,维持现有的平衡状态。幻象的生成,正是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替代、妄想现实的外在形式②[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弗洛伊德主义话语内部的这一性别叙事框架,在施蛰存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得到了保留:女性、疾病、死亡、情欲、暴力这一能指的连锁在《凶宅》中可以从符号层面分别找到对应,甚至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人们对这一类作品的阅读期待。正如刘禾所说“在这些小说中,女人成了幻觉、诱惑、神秘与死亡现象中的永恒人物”、“怪诞之笔出现为以大写的‘女’字形成的女性,对于男性叙述者来说,它代表着某种不可知之物的极限”①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86-196、192页。。可以说,魔幻、鬼魅的超现实表征和人物心理中的非理性、非现实的一面“形成了彼此相互穿透的态势”②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86-196、192页。。幻觉、鬼影通过这种机制转化为死亡、毁灭的早期症候。人物的精神压抑与内心矛盾,带来的是真实与幻觉边界的一次次模糊和打破,便也出现了种种非理性状态的迷狂表达。
虽然上述框架在形式上不失有效性,但《凶宅》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原本都是神志清醒、具备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精神障碍者。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弗拉进司基和詹姆士两人的表述中找到非理性幻想对现实进行扭曲、重构的痕迹。按照精神分析理论,喀特玲的重病已经促使弗拉进司基潜意识中生成死亡意象,那么他看到上吊的女人的影子正是这种潜意识的外露。但是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弗拉进司基表现出的是一方面有意识验证潜在想法;一方面又竭力逃避现实的矛盾心理状态:“魔鬼已经来袭我们了,我怕”、“她的话全像遗嘱”、“噩兆的话!她不懂我内心的恐怖”③施蛰存:《凶宅》,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一卷·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213、219页。,以至于后来他看到妻子的微笑,也将之视作“可怖的微笑”。在和玛莎林的恋情中,珠宝商的日记主要呈现了他内心的徘徊和挣扎:与玛莎林相处中,他说“我不由的要想起喀特玲来”④施蛰存:《凶宅》,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一卷·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213、219页。,情感的发展中一次次请求妻子的原谅,最后竟也写出“我要疯了”这样的话。即便是冷酷无情的杀人惯犯詹姆士,也在供词中对非理性状态有所交代:“从玛丽的天真的睡姿中看到了以前的两个妇人的凶像,于是,一个斗牛士的血在我每一个脉管中迸激着了”,甚至还表达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悔过之情:“当我第二次觉醒的时候,我完全是很后悔了。玛丽是真心地恋爱着我……”⑤施蛰存:《凶宅》,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一卷·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213、219页。从这些片段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本身的复杂,在现实的挤压中产生的矛盾、挣扎心态最终促成了幻象的产生。而日记、供词等作为落实于纸面的表达空间,真实呈现了心理现实对于物理现实的变形反映与重新阐释,即“一种冒险地突入内心的不可知并从中带回了曾与它依稀照面的让人惊讶的消息”⑥[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在这一点上,作者并没有否认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却提供了特定心理状态下看待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与形成的现实效果——“鬼魅”超越了本体论的“现实”,而成为人们感知和认识世界的另一种装置。作者虽然依旧将真实的揭露、鬼魅的祛除作为小说的结尾,但是这些超现实的魔幻因素恰恰是以“现实”的组成部分,而非“现实”之出离的形态出现在文本中。
一个值得注意的前提是,小说情节展开的过程中,读者已然被作者放置在了一个类上帝的全知视角上。反过来讲,这种安排和设计恰恰是对人物的心理真实与他者观感所及的表象认知之间所存在的裂隙的暗示。心理空间中意识的瞬时性、无组织性都无疑阻隔着真相的感知,并进一步促使人的生存困境、情感困境在互通性断绝的情况下生成。然而,读者和人物所面对的共同困境在于,两者均无法仅仅从时间简单的结果倒推出其背后情感的复杂迷离和人性的挣扎。在这种似乎不可避免的裂隙下,我们更应当考虑给“心理现实”在现实物理世界中找到一个合法的位置,因为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讲:“现实主义——生活性是一切之源,是它令魔幻现实主义、歇斯底里现实主义,幻想小说、科幻小说,甚至惊悚小说的存在成为可能。”⑦[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179页。
三、文化空间:知识、经验与“魔道”
(一)“建筑之诡异”:从一次误读讲起
在“魔道”写作系列中,《凶宅》是唯一一篇将所有主人公均设定为外籍身份的作品,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半殖民地中国时期有着“冒险家的乐园”之称的上海。《凶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故事,都市空间似乎成为我们探讨这篇小说不可忽略的维度。
或许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著名汉学家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中对《凶宅》这篇小说作了如下解读:“心里装着爱伦·坡小说的施蛰存很可以通过《凶宅》来写一部都市哥特罗曼史的中国变奏,这种哥特罗曼史就是都会之‘非家园’感的想象性建构。”①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李欧梵当时套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理论家安东尼·维特勒的著作《建筑之诡异》(The Architecture Uncanny)中的观点。于是,李欧梵对这篇小说的关注点滑向了都市带给人的疏离感、寂寞感。在他看来,魔幻与恐怖正是这种都市情绪的折射,也是都市的“非家园感”对现实的扭曲与变形。然而时隔良久,李欧梵2014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推翻了自己当年写在书中的结论:“我这次重读文本的时候,发现自己几乎全错了,我受那个理论影响太大……这次再看的时候,我发现里面讲的和The Architecture Uncanny完全不是一回事……”②李欧梵:《“怪诞”与“鬼魅”:重探施蛰存的小说世界》,《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3期。反过来看文本中三对主人公人物关系、情感关系都是在异国已经生成,即便是珠宝商和玛莎林的婚外恋情,也是发生在宅子内部空间的事件,而不是具有统摄性的“都市感知”“都市体验”的折射。
以上一例虽已被李欧梵本人判定为一次“误读”事件,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误读”产生的原因,就产生了独特的启示意义。李欧梵提到的“哥特罗曼史”,指的即是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一种小说类别而存在的“哥特小说”。“哥特”一词来源于建筑学,指是一种盛行于17—18世纪的古典建筑,一般以华丽夸张的造型和尖顶为代表。这样的奇特造型一般和恐怖、神秘、厄运、诅咒等元素结合在一起,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凶宅》故事的发生地,就巧妙地被设定为一座远离闹市区的“荷兰风的小别墅”——从直觉意义上讲,这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灵异事件发生地。
(二)国际性文化场域和“知识性幻觉”:符号和经验对接
虽然李欧梵的误读和对人物关系的分析已经证实了我们不能将都市体验相关的话语简单地直接套用在对《凶宅》的解读上,但实际上我们可以选取另一个角度,在文化图景的考察中来完成对小说中“都会”意义的重新探寻。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自然是我们要回到李欧梵“误读”发生的原点,即与“半殖民地”“都会”等概念相系的国际文化背景。
基于对上述原点的有效性承认,再进一步联系我们提到过的主要人物多为异邦身份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上海在《凶宅》这篇小说中,很大程度上作为跨文化、跨国别的经验对接和视野融合的场所而存在。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在于,文本中作者在处理人物异邦身份与中国传统经验关系时,所采用的“知识性”方式。一方面,外国人身份标签是对于中国传统风水、鬼神等知识的屏蔽和回绝;但另一方面,异域人本文化身份所联结的超现实“鬼魅”知识,以及叠印在之上的西方对东方的神秘主义想象,又以此为窗口得以释放,形成情感、认知效果的相似表征。更进一步,当两种知识谱系形成对话关系,并在对方领域得到印证时,同向的知识和经验便会形成合力,促成那种世界性普遍经验和本体存在论想象。因此,小说中安排了几处这样的连结点:《英文沪报》开篇即引“柯南道尔勋爵有鬼论”来指认位于上海的“凶宅”,这是在开篇处的一个障眼法;詹姆士的同事们在其妻缢死后“没有一个人怀疑这是杜撰出来的,甚至有人说中国这个地方是充满了鬼怪和各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③施蛰存:《凶宅》,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一卷·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而詹姆士家的女仆也因为深信中国传统的替死鬼说而无意中帮助詹姆士达成了其目的。“三”这个数字也对中国“三人成虎”的传统文化心理形成了隐喻性结构,凶宅也就借助这些机制完成了从疑虑到实存的转变。
(三)文本试验:“志怪”与“先锋”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巨变的前夕,施蛰存的这些作品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仅仅是因为它将在近代消失良久的、中国小说传统中的那一套不登大雅之堂的“怪力乱神”重新带回了人们的视野,更是它和当时中国文坛力量正在不断强大的左翼话语在手法、创作理念、终极关怀方面的巨大差异。从结果来看,后者甚至有可能正是施蛰存选择终止超现实主义写作,并最终退出小说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凶宅》这篇小说的诞生,施蛰存有如下一小段自述:“其实,写到《四喜子的生意》,我实在可以休矣。但我没有肯承认,我还想利用一段老旧的新闻写出一点新的刺激的东西来,这就是《凶宅》。读者或许也会看出我从《魔道》写到《凶宅》,实在是已经写到魔道里去了。”①转引自施蛰存《梅雨之夕·跋》,上海:新中国书局1933年版,第2页。执着于超现实“魔道”题材,反映出的是施蛰存和当时文坛主流在写作实践、文坛未来走向上的意见分歧。然而按照李欧梵的说法,施蛰存对于“左翼”概念就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说30年代艺术上的avant-garde(先锋)才是真正的左翼”,而谈到他对出自自己之手的作品进行特点概括时,“施先生不赞成用这么多主义,所以我就问他,你怎么界定你自己的作品呢?他后来跟我讲了三个词,全部是英文,非常有名了,第一个是grotesque,就是怪诞;第二个是erotic,就是色情;第三个词是fantastic,就是幻想”②李欧梵:《“怪诞”与“鬼魅”:重探施蛰存的小说世界》,《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3期。。秉持这样的创作观念,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才呈现出不受制于现实主义题材和方法的特征,更大胆采用了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坛之外的新思路。他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吸收,对于安德烈·布勒东、施尼茨勒等西方作家的创作借鉴,都可以看成是为他的新形态小说实验提供了新的话语资源和理论基础。正如刘禾所说:“施蛰存的重要革新之处在于他引进了超现实主义的怪诞与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之间的象征性的通约,使得他把古代的志怪小说转化成汉语形态的超现实主义小说。”③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87页。以此来看,他的小说实验颇有连接现代与古典,现实和心理,甚至是重新组织文学叙事之中“魔幻与真实关系”的重要意义。这理应成为我们解读施蛰存这一时期“魔道”系列作品所必须把握的一个前提。
四、结语
施蛰存在《凶宅》这篇小说的创作中充分利用了文体形式、世界认知和文化图景三个不同层面的空间,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节跌宕、构思精巧的故事。在这三个空间中,《凶宅》表现出马赛克式的混合杂糅风格,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效果的突破,真正实践了“先锋”的理念。从这一点上来讲,《凶宅》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施蛰存30年代的创作理念,和30年代小说的面貌,提供了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