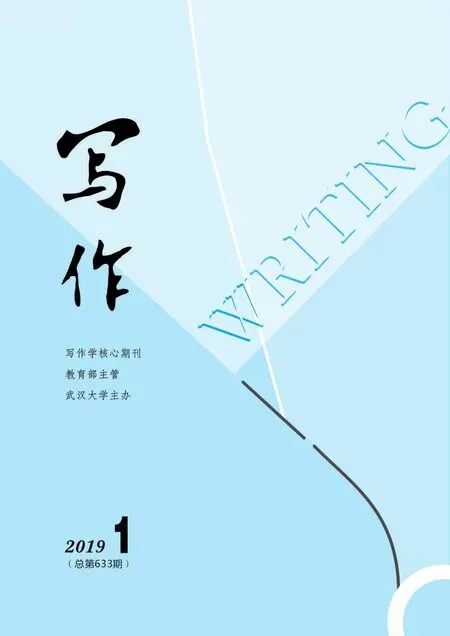戏谑的述者
——论沈从文《灯》的嵌套叙事
肖钰可
一、嵌套手法:“灯”与“我”
叙述分层是小说叙述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具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法国文论家热奈特将文本层次分为“第一叙事”“第二叙事(元故事)”①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161页。等,曾引起热烈的讨论。不过其理论体系比较复杂,表述上也有些难解。个人以为,学者赵毅衡对此问题的阐释比较简洁明晰,可供参考。他认为:“高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低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也就是说,高叙述层次中的人物是低层次的叙述者。一部作品可以有一到几个叙述层次,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那么,向这个主叙述层次提供叙述者的,可以称为超叙述层次,由主叙述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②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63页。
就小说《灯》而言,它的叙述结构并不复杂,但十分别致。文中存在两条基本的叙事序列:一是文本叙述者叙述青衣女子和屋主人的故事,二是屋主人“我”叙述老兵的故事。两条序列在小说中存在清晰的分野,互不交叉,但并不割裂。作者似乎有意在其中设计交织的伏笔,却又在小说结尾部分彻底消解了这种可能。从结构上看,青衣女子和屋主人的故事像一个大体的框架,为下层叙事提供叙述者,属于超叙述层;老兵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被嵌套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属于主叙述层。两层叙事巧妙结合,构成结构上的互动张力,使小说最终达成了真假难辨、亦真亦幻的叙述效果。具体来说,作者主要依凭“灯”与“我”两个媒介完成了嵌套结构的构建,下面将分别论述。
小说完成这种嵌套所借助的第一个媒介是象征性的事物“灯”。作为小说的标题,“灯”在一开始就被点出:因为青衣女子在屋主人的住处看见一盏油灯,感到疑惑并询问屋主人灯的来历,屋主人于是向她讲述关于“灯”的故事。由“灯”引出主叙述,不仅切题而且顺理成章。两层叙述之间构成隐秘的“因果”关系:因为没有这盏灯,就不会有青衣女子的询问,进而也就不会有老兵故事的展开。在主叙述层的开头,率先登场的是一盏经常熄灭的电灯,这个特性是造成后文换灯风波的起因。小说第二次出现“油灯”是在交代完“军官厨子”这句话的来历之后:
于是这老兵,不知从什么地方又买来了一个旧灯,擦得罩子非常清洁,把灯头剪成圆形,放到我桌子上来了。①沈从文:《灯》,凌宇主编:《沈从文小说选》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下文引用原文部分若无说明皆出自此版本。
这句话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即这盏灯是老兵买来的,也正因如此,“我”才会在被问起“灯”的来历时自然想起老兵。在“我”的记忆里,这盏灯和老兵始终联系在一起,当“我”在它昏暗不定的光线下望到老兵的脸时,总会不自然地牵引出许多思绪。后文具体阐述“我”和老兵交往的经历时,这盏灯暂时作为一种隐形的见证者而存在。称之为“隐形”,是因为“灯”未在主叙述层中被作为重要的叙事线索提及;称之为“见证者”则是因为尽管主叙述层的叙述者“我”没有刻意提这盏灯,但因为小说开头超叙述层的铺垫,读者似乎也可以透过叙述想见“我”在灯光下面对着青衣女子讲故事的情景。
在主叙述层的尾声,叙述者以一句“这就是我桌上有这样一盏灯的来由了。我欢喜这灯,经常还使用它”自然收束,仿佛一下子把读者又拉回到超叙述层的空间里。而在之后的叙述中,“灯”再度作为重要的线索登场。屋主人和青衣女子的两次交流都紧紧围绕这盏灯展开,这盏灯仿佛从叙述者“我”构建的那个老兵的年代里穿越过来,进入青衣女子的年代。“灯”正是作为重要的媒介打通了这两个时空,搭建起参与嵌套的两层叙事序列相关联的桥梁。至于在小说结尾,作者又通过改写灯的来历彻底切断了这座桥梁,从而建立起一层新的嵌套关系,这一点将在下文“另当别论”。
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曾说:“人是在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②[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3页。在《灯》这部作品中,无论是超叙述层的屋主人、青衣女子,还是主叙述层的“我”、老兵与蓝衣女孩,都是被叙述者建构起来的主体,这些主体借助人称转换在两级叙述层中自由穿梭。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所有的主体都没有名字,是被指示出来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超叙述层里的人物成了主叙述层的叙述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超叙述层就是单层次的。事实上,绝对的单层次结构几乎不存在,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叙述的产物,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叙述者的影响。因此,这种分层也只是相对而言。正如赵毅衡所言:“任何叙述行为,实际上都隐指了一个高叙述层次的存在,因为叙述者只能从这个超越的层次执行他的各种功能。”③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80页。就《灯》这部作品而言,小说一开始就无声地引入第三人称叙述屋主人和青衣女子的故事,这个叙述者未见得一定就是小说作者。而这种叙述模式和传统说书颇为类似,唯一的区别在于,《灯》里的叙述者更像一个目击者,他和被叙述的人物之间不存在时间差,除了表明正在进行叙述这一事实外,别无其他任何个性化特质。
在交代了叙述的起因后,第三人称叙事者自然隐退,小说随即进入主叙述层,即重点展开老兵的故事。“两年前我就住在这里”,小说第二段立即切换成第一人称,但并不会使读者产生误解,这里的“我”就是前文被叙述的那个屋主人。这样安排的一个好处是有助于叙述人引入自身视角刻画人物。虽然主叙述层的主角是老兵,但这部分的叙述是以“我”为中心展开的,是“我”感受到的老兵。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写道:“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①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一方面屋主人是在向青衣女子回忆自己和老兵交往的经历,具有追忆性质,难免会让人产生时空上的隔膜。在写到老兵和蓝衣女人谈话时,“我”没有直接写自己即时的感受,而是说“从后来他的神气上,我知道他在和女人谈话时节,一定是用了一个对主人的恭敬而又亲切的态度应答着的”,这明显是回忆性的语气。另一方面,借助于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者“我”又无时无刻不把自身置于当时当地的情境中,试图还原当时的心理,并推测老兵的所思所想。小说中有一段非常典型的“我”的自我剖白和对老兵心理的推想:
可是我将怎样来同这老兵安安静静生活下去?我做的事太同我这老家人的梦远离了,我简直怕见他了。我只告他现在做点文章教点书,社会上对我如何好;在他那方面,又总是常常看到体面的有身分朋友同我来往,还有那更体面的精致如酥如奶作成的年青女人到我住处来,他知道许多关于我表面的生活,这些情形就坚固了他的好梦。他极力在那里忍耐,保持着他做仆人的身份。但越节制到自己,也就越容易对于我的孤单感到同情。
这段描写突出了被嵌套的主叙述层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优越性。它有利于表达“我”当时当地的感受,使读者产生很强的代入感。老兵将他自己的梦投注在“我”的生活上,“我”对此既感动又困扰,甚至产生了一种想刻意疏远他的冲动,这种心理其实是很微妙、很矛盾的。同时,“我”也站在“我”的视角上推想老兵当时的心理,用诸如“他知道”这样的字眼将这种心理呈现给读者,这是一种在场、即时性的叙述眼光。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将这两种眼光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我”和“老兵”的形象同时被鲜明地凸显了出来。如果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也可以表达同样的内容,但在高度客观的要求下,又难免会有损表达的感染力。
在主叙述层行将结束的时候,故事中的“我”满含深情地对“自我”心理进行了剖析,并描绘出“我”眼中老兵清晰的形象:“我欢喜这灯……我在灯光下总仿佛见到那老兵的红脸,还有那一身军服,一个古典的人,十八世纪的老管家——更使我不会忘记的,是从他小小眼睛里滚出的一切无声音的言语,对我的希望和抗议”。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老兵曾经给“我”的生活带来一定困扰,但“我”还是敬重他、怀念他。“我”只能依赖这灯光追忆老兵的形象,这种深切的情感再度借助第一人称得以完满地表达。而当故事说完时,小说复又切换成第三人称,主叙述层叙述者“我”回归屋主人的肉身,第三人称叙述者登场。伴随着青衣女子走过桌子摩挲那盏小灯,读者似乎也从老兵的故事里被拉回叙述的现场。在主叙述层中,“我”的心理已得到了较为细腻的展现,因而在超叙述层中,叙述者除了描述两人间的对话外,把更多的叙述重心放在了对青衣女人的心理描绘上,例如:“女人稍稍吃惊了,怎么两年来还有油?”“女人对于主人所说的那老兵,是完全中意了”等,叙述者尽管没有和故事中的人物发生交集,但他努力地在揣想青衣女子当时的心理,以便于揭示更为丰富的面向。相比较而言,对于屋主人心理的描绘则显得薄弱了许多,仅有一句“主人懂得这是为凑成那故事而来的,非常欢迎这种拜访”。青衣女子特意穿了一件蓝色衣服来到屋主人家,其用意实际是显而易见的,她真的相信老兵与蓝衣女子的存在,因而存了满心的希望要为这个故事“辩护”。而屋主人明知这灯原本就不是老兵买的却并未点明,其面对青衣女子“一厢情愿”时的心理很耐人寻味,正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给了叙述者在此留白的可能,使得后文主人说漏嘴从而彻底暴露主叙述层的虚假性这一设计变得顺理成章。从主叙述层回归超叙述层,从“我”到“他”,人称的转换不仅切换了叙述的情境与视角,更为小说的最终走向开辟出更多可能,为情节的翻转预留了空间。
二、嵌套效果:被解构又重构的“真实”
和一般的倒叙写法不同,在《灯》的嵌套结构中,小说结尾的情节翻转非常耐人寻味,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来自于那盏贯通时空的“灯”。屋主人和青衣女子再次谈起灯的事情,主人想到要下楼去取灯,女子问他这灯的位置,主人的回答暴露了那个最大的秘密——这灯压根就不是什么老兵买来的,而是向楼下房东家的娘姨借的。这么一来,主叙述层中有关老兵和灯的记述的真实性陡然降低,不只是故事中的青衣女子,连带着读者也感到被大大戏弄了一把。小说这部分的描写非常克制且微妙,主人仿佛是故意露出了马脚:
“那是因为前晚上灯泡坏了,不好做事,借他们楼下房东家娘姨的。我再去拿来就是了。”
“难道是娘姨的灯吗?”
“不,我好像说过,是老兵买的灯!”男子赶忙分辩,还说:“你知这灯是老兵买的!”
“但那是你说的谎话!”
短短几句话,却几乎完全颠覆了主叙述层叙事成立的合法性,既然连灯都是临时借来的,那么很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老兵这个人,主人慌张之下辩驳的几句说辞并不能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那么是否就能确定老兵是由屋主人虚构出来的人物呢?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再次玩弄了一把叙述的游戏。尽管青衣女子揭穿了主人的“谎言”,但他俩似乎都很愿意继续为这个谎言辩护,小说没有以两人的不欢而散结尾,反而是两人相约一起去苏州、去南京。而这旅行的目的,正是为了探听那个“老司务长”的下落。如果说前文的对话颠覆了主叙述层成立的合法性,那么此处的叙述则是为整部小说打开了一个延伸的出口,把嵌套结构从封闭的空间“解救”出来。虽然这灯不是老兵买来的,但老兵这个人未必就一定不存在,甚至连屋主人和青衣女子都不相信他真的死了,因此才决定要继续追寻他的下落。沈从文后来写作《边城》的时候似乎也沿用了这种叙事风格:“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①沈从文:《边城》,凌宇主编:《沈从文小说选》第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页。也是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结尾,小说人物的命运仿佛是连作者也不能掌控的,与其说是叙述者向读者开的一个玩笑,不如说是小说人物向所有人开的一个玩笑,他们的命运最终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至于这判断是什么,作家不写,读者永远都不会确知。不过对于这样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结尾,也有评论者提出批评的看法,为避免断章取义,现将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从结构上说,后面的那几节也应该是删去的,只须用几句话照应篇首便够了。添加了它们上去,反把正文的重要性减少,而且对于表现的东西也减轻了效力。此外,正文的调子也不和它们相同:一个是庄严而稍带感伤,一个是轻率而稍带快意。总之,《灯》这篇作品在内容方面的确不错,在形式方面,那是要经过一番改造的。明白地说来,从第一百一十四面第二节起②参见沈从文:《沈从文子集》,北京: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14页。,一直到篇末止这一段蛇足可以断去,而掉以几句足以照应篇首的便很好了。③贺玉波:《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下)》,刘洪涛、杨瑞仁主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这种观点似乎认为,因为小说最后的部分和主叙述层的叙述风格不太匹配,使得整部作品产生了一种割裂感,因此主张把结尾部分删去。若真如此处理的话,整部小说成了以倒叙结构组织起来的回忆性作品。这么一来,这个小说就变成了“我”笔下的老兵的人物传记,和一般写人记事的回忆文字没有太大不同,还会大大弱化小说的戏剧效果。因为在《灯》这个小说中,所谓的戏剧冲突不仅产生在“我”和老兵之间,也同时存在于屋主人和青衣女子之间,那句“年青人在一种小小惶恐情形中抱着接了吻”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它表明“我”和女子也是一对有情人,女子后来追问灯的故事甚至特意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要“凑成”这故事是有她的“私心”的,老兵并不是整部小说唯一的主角。小说结尾两人决定结伴追寻老兵的下落看似突兀,但实际上前文并非完全没有铺垫,作者在处理人物关系时有意留下了使结尾情节翻转的空间,这也是他构思的一大匠心所在。
回到上文论及的叙事理论,在沈从文的《灯》中,超叙述层和主叙述层之间并非简单的拼贴,而是作者有意识的组织。从大的脉络看,超叙述层为主叙述层提供了叙述的前提和基础,是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并非是因果式的正面补充,而是一种颠覆性的“反解释”。超叙述层颠覆了主叙述层叙事成立的合法性,把读者带入了虚实难辨的叙述圈套,但这种“颠覆”并不是绝对的,作者又以开放性的结尾把这种追问和探寻延伸到文本之外,营造出意犹未尽的叙述张力。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灯》具有明显的叙述意识,文学创作不再是单纯的对生活的外在进行书写,而是变成了创作者自我审美意识的建构与解构活动,突破了将文学仅仅当作叙述经验的真实,突出了叙述行为本身的自我价值,从而将作者当作是生活的记录者进行了解构。”①吴正锋:《沈从文创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23页。
虽然沈从文的小说有不少是从生活中取材,有一些甚至能在他的经历中找到原型,但是他本人并不很纠结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学艺术没有真不真的问题,只有美不美的问题”②沈从文:《水云》,刘洪涛、杨瑞仁主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102页。,当有人问起他:“××,你写的可是真事情?”答曰:“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③沈从文:《水云》,刘洪涛、杨瑞仁主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102页。比起“真”,“美”似乎是沈从文小说中更执着的追求。这种感情和他本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④沈从文:《〈边城〉题记·新题记》,刘洪涛、杨瑞仁主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正因如此,他在写老兵的时候,即便怀揣着一种“奴性的鉴赏”⑤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笔下也总是蘸满了深情。在《灯》这部作品中,老兵是跟随“我”的父亲一同出征过的老司务长,人生阅历异常丰富。他对“我”怀了一种父亲对儿子一般的殷切之情,把他的梦寄托在我的婚姻与生活上,在得知自己理想破灭的时候甚至不禁落泪。虽然他的过分关切对“我”造成了一定困扰,让“我”有一种“怕见他”的冲动,但是在“我”心里,他仍旧是那样一个“纯厚”“正直”“古典”的人,即使“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我”也不愿意相信他真的就这样死了。这个被叙述者人为建构出来的主体形象竟是那样丰满,就算他真的是作者和叙述者一同虚构出来的人物,这种深切真挚的情感却是真真切切表现在作品中的,因此,作者在消解“存在”真实的同时实际是又强化了这种“情感”的真实。
三、结语:独特的嵌套
作为一位讲故事的大师,沈从文的叙事功力无疑是很高超的,嵌套结构正是他在“讲故事小说”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王瑶先生曾评价“他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⑥王瑶:《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国新文学史稿节选〉》,刘洪涛、杨瑞仁主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与故事的内容相比,叙述这个行为本身也具有同等的意义。无论是1926—1927年间创作的《猎野猪的故事》《入伍后》《松子君》《老实人》,还是他在1930年代成熟期创作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说故事人的故事》等小说,都采用了和《灯》类似的“故事里的人讲故事”这样的嵌套叙述模式,只是采用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在人称和叙述对象的选取上也各有差异,但是这些故事最终的目的仍旧是为了要说服读者相信这个“故事”。比如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尾,作者写道:“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①沈从文:《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凌宇主编:《沈从文小说选》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正如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当沈从文强调自己在写故事的时候,他所强调的并不是小说的真实性,而恰恰是借以征服都市读者的虚构性和传奇性。”②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灯》这个小说的独特性则在于,它的嵌套结构不是可有可无的,其本身就是小说意旨的一个部分。作者借助叙述者之口主动消解了主叙述层叙述的真实性,将小说引入真假难辨的无穷远处。由此,有关小说真实性与虚构性如何辩证共生的问题再度引发论者思考,这也体现了作品自身的叙述魅力。
帕慕克曾借用席勒的说法将读者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绝对天真的读者,他们总是把文本当作自传或乔装的生活体验编年史来看,无论你曾多少次提醒他们所阅读的是一部小说”③[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另一类则是“绝对感伤—反思性的读者,他们认为一切文本都是构造和虚构,无论你曾多少次提醒他们所阅读的是你最坦诚的自传”④[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帕慕克认为这两种人“根本体会不到阅读小说的乐趣”⑤[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阅读小说不是在做索隐游戏,所谓的“真实”与否在小说的语境里需要被重新定义,人物能否在现实中找到原型有时并不那么要紧,重要的是在叙述与被叙述的当下,他真实地在作者、叙述者与读者的心中活过,他也就有了被解读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在《灯》里搭建起的这个叙述圈套其实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次“真实”与“虚构”的“狭路相逢”,在这场一切小说都难以回避的相遇里,是戏谑的述者把玩的一出最真诚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