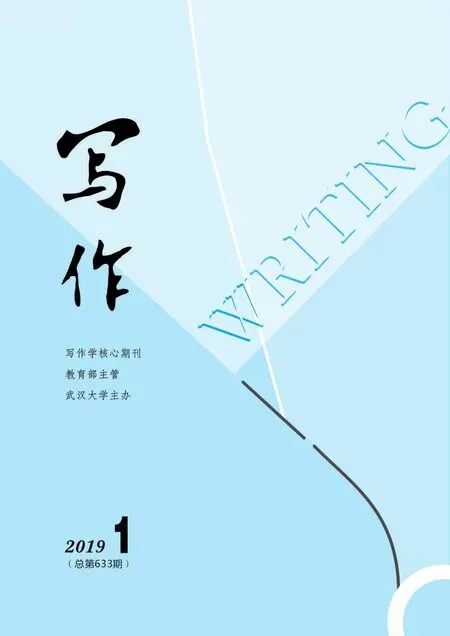论严歌苓《芳华》的写作缺憾
刘云 郝敬
引言
《芳华》是严歌苓对20世纪70年代某部队文工团的书写,以主人公刘峰的“触摸”事件为中心,讲述了一群文艺兵横跨四十年的命运流转。作者以回忆性叙事展开对那个特殊时代及特定人群的描写,讲述了主人公——好人刘峰的悲剧命运。严歌苓对这种横跨几十年的史诗般叙述本身是比较擅长的,这点从她以往的多部著作中都能看出来。拥有这样的基础,《芳华》原本应该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有厚重历史感和深刻批判与反思精神的小说。然而读完作品之后,却难掩深深的失望。这部小说无论从叙事上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显得诚意不足,缺少严歌苓文字原本应有的力道。
一、叙事层面
(一)叙事视角的模糊
严歌苓说:“写这个故事,我用了不同于过去我常用的叙事手法和架构,书中有一个人讲述过去的事……我用这样的手法来写,其实是想探索新的叙事手法和小说结构。在美国读艺术硕士的时候,我学过各种不同的小说形式,认为形式美和形式的独特,已经能让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所以我采用了这样一个新的形式。第三人称这种写法,我已经有点疲惫了。”①严歌苓:《我为什么写〈芳华〉》,http://www.sohu.com/a/210525896_173615。基于对小说形式美的追求,严歌苓采用了“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①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以现在的“我”——萧穗子(小说家)为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回忆刘峰、何小曼、林丁丁、郝淑雯及“我”(少女萧穗子)几个人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一共设置了三个叙事层:一、叙述行为,作为写作者的严歌苓的写作;二、话语层,现在的“我”,作为故事讲述者的作家萧穗子的叙述;三、故事层,回忆中的人物及故事,以“我”——以少女萧穗子的经历、眼光及其周围人物为中心。作者放弃全知视角的写作,转而使用这种主人公回忆往事的视角,向读者讲述当年曾经发生在他们几个人之间的故事。②关于叙事层的论述参见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按照严歌苓的写作逻辑,故事层中的少女萧穗子、话语层中的“我”(作家萧穗子)与写作者严歌苓本应该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有各自不同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点。但是在严歌苓的写作中,作为故事层中的主人公“少女萧穗子”的观察视角几乎完全被作家萧穗子代替,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作者都是以作家萧穗子的眼光和口吻来替代少女萧穗子去讲述事件、评论人物。而极少站在故事层里,在过去的时间里从当事人的角度描写当时正在发生的事,第一人称限知视角总是不自觉地被类似于全知视角的后视角取代,即多年以后的萧穗子在回忆的过程中不断地感受体悟改写过的人与事。刘峰从北京参加完全军学雷锋的标兵大会时,严歌苓写道:“我是唯一没上去握手致敬的。”原因之一是“我对刘峰这个严重缺乏弱点的人有点焦虑。我好像在焦虑地等待一个证明:刘峰是真人的证明。太好的人,我产生不了当下所说的认同感。人得有点儿人性;之所以为人,总得有点人的臭德性……他的好让我变得心理阴暗,想看他犯点错,漏点马脚什么的。虽然我当时只有十六岁,偶尔也会有心理不光明的时候。”③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3页。十六岁的萧穗子在文工团里是相对年幼的,更何况她的父亲托刘峰给她带食物时,还给刘峰送礼物,她明白这是父亲想拉拢刘峰,让刘峰的政治光环罩着她一点儿。但是严歌苓的那段话分明不是十六岁的萧穗子的感受。作者把自己成长后对人性的反思与焦虑强加在了十六岁的萧穗子身上,以外视角的叙述替代主人公当时当地的思想认识,导致叙述口吻及叙事层的模糊。再如,刘峰在寝室做甜食时,“我”的整个心理描写,从认为刘峰喜欢“我”,到“我看清了局面,三个同屋,蹭吃的是我。”④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3页。及发现刘峰看到郝淑雯、林丁丁走进来时带有“荤腥”的眼神,这整个的心理描写,实际上也是把她自己当下的价值判断,加在了当时的主人公萧穗子身上。使得叙述者和当事人发生了错乱,不自觉地把成年萧穗子回忆时的想象当成了少女萧穗子的心理认知。
这种模糊还出现在小说安插的叙事内容上,尤其是描写何小曼入伍前生活的那部分内容,几乎独立成篇,既不能被成年萧穗子的回忆性视角涵盖,更不在少年萧穗子的经历中。这就打破了小说情节和结构的自然流动,读来颇为生硬。虽然从故事层面来说,作者在这部分确实讲述了一个好故事,而且其中涉及的每一个人,形象都很突出,不管是何小曼的生父、继父,还是她那被刻意压抑了天性之后卑微讨生活的母亲,乃至何小曼自己,都让人印象深刻,对何小曼的心理发展和性格养成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但这部分内容的过于完整、独立,恰恰显露出与整部作品融合度上的欠缺,让人感觉作者在把这部分内容融入小说时略显草率,没有体现出一个写作者处理情节结构的严谨性。
(二)过度消解的“真实性”
作者通过“我”——作家萧穗子的回忆结构整部小说。这种第一人称叙事极容易营造出一种真实感,如同作者所宣讲的那样:“这个故事非常接近我的人生经历,从十二岁到二十五岁,我的青春芳华都给了军队。”①《严歌苓:“我就自信地认为,世界就缺我这一份表达。”》,严歌苓读书会(公众号ID:geling-yan),2017年8月14日发布。萧穗子的作家身份与经历都与作者本人高度重合。但作者在写作中,又时不时跳出来刻意打破这种真实感。她让处于话语层的“我”(作家萧穗子)不停地向读者坦白:“我”的想象可能改变了回忆,故事添加了虚构的成分。这种坦白贯穿小说始终,比较明显的有下面几次:
一是在刘峰转交父亲给“我”买的零食时,话语层的“我”写道:“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转述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或部分编造的话放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座,跟我抗议……”②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18、82-83、107、165、206页。二是在写何小曼的故事时:“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曼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曼……”③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18、82-83、107、165、206页。三是写到小曼加入文工团的时候:“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先是给了他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好得大致能实现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几十年后来看,那么写小曼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给她那么个结局,就把我们曾经欺负她作践她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十几年后我又写了小曼的故事,虽然没有用笔给她扯皮条,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现在我试试看,再让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④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18、82-83、107、165、206页。四是写到刘峰下放,小曼送他时的情景,叙述者补充道:“那时很多人对我解密,或许因为我成了个小说写手,而小说即便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也是加了许多虚构编撰泄露的,即便他们偶然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他们的秘密,也被编撰得连他们自己也都难以辨认了。”⑤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18、82-83、107、165、206页。五是“我”在郝淑雯家住下时:“……我写下的有关她的故事,只能凭想象,只能靠我天生爱编撰故事的习性;我有个对事实不老实记忆的脑子,要我怎么办?”其他,比如在描述刘峰在海南的生活时:“不管游到哪里,我不知怎么总想到,此地是刘峰和他的小惠姑娘过过小日子的地方,于是我的想象力起飞了”⑥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18、82-83、107、165、206页。;写刘峰晚年与何小曼的生活时:“刘峰和小曼的故事,大半是我想象的。我更喜欢我想象的经过和结局。”⑦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18、82-83、107、165、206页。这种坦言故事是“我”想象的表述有很多处。
可以说,严歌苓通过这种叙事话语的设置,不停地游移在对真实性的营构与消解之间。她一方面企图唤醒人们对于特殊年代中悲情主人公的关注,引发人们对于历史谬误及人性复杂的反思,以彰显现实主义的深度,如她在采访中一再强调的:“《芳华》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也有原型,有很多我对那个时代的自责、反思。”⑧《你所不知道的〈芳华〉:作者严歌苓答记者问》,网址:http://cul.qq.com/a/20170817/019148.htm。但是另一方面,她又通过叙事话语,不断设置和揭秘自己的叙事圈套,坦白故事的虚构性,刻意拉开叙事主体与故事之间的距离。这种写作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新鲜的阅读感受,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叙事内容的轻浮化、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削弱了文本反映现实的深度。从阅读感受上来说,文字似乎已经成为小说作者的一种语言游戏,读者在故事进展过程中,不断被人为打断,再重新进入故事,又不断被提醒小说的虚构性,于是,文本的现实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削减,作者对于历史的反思,也就只是浅尝辄止罢了。实际上,叙事形式应该是为文本内容服务的,过分重视形式容易走向反面。当年先锋作家们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恣意跳跃的写作态度成为他们后来被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严歌苓在此时拿来使用,并未见出任何新意。也许对于严歌苓这样成功的作家而言,每一部作品出来,似乎无论如何都会被追捧,有好故事有好文字,有熟稔的技巧,上下便一片叫好之声。但相较于她早期和中期的作品,《芳华》却已然流露出某种懈怠,对历史的反思深度与批判力量都匮乏而无力,缺乏厚重的质感,不免让人感觉遗憾。
二、人物塑造
虽然作者刻意设置了复杂的叙述层次,又运用了各种叙事顺序来讲述故事,比如小说以刘峰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叙事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在文工团时期一直讲述到2015年刘峰去世,采用倒叙、插叙与顺叙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40年间刘峰及其他人物的命运流转。整个小说结构不可谓不复杂。但是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刘峰,作者的塑造是相当不成功的。
刘峰是一个朴实善良热心肠的普通人,他帮着修补红楼,帮括弧提水,救靶场受惊的大娘,帮我们捎带零食,给马班长做沙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物资车辆先引到工兵营,临终前还帮小曼把浴室的地砖砌平,把冰箱修好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表明了他的朴实和无功利的善良。而特殊时代的我们却将他解读成“雷又锋”,一边利用着他的良善,享受着他的劳动成果,一边又恣意嘲笑他的奉献。我们无视他的内心,只把他当作一个像雷锋一样的政治色彩浓厚的人,一个口号式的人物,不允许他展现出一点作为普通人的情感。这是作者要批判的。作者想要诉说一个内心丰富的年轻人如何被一个政治符号抹杀了个性,成为大家眼中的“雷又锋”,又如何被战友们及历史无情地碾压,最终充满悲剧性地走完一生。但是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刘峰却是十分扁平的。作者极力表现刘峰的善良品质,但因为叙事视角的限制,读者很难全面了解刘峰真实的心理状态、喜怒哀乐。作者对刘峰的语言描写大多采用叙述者转述这种间接引语的方式表现。小说中关于“我”与刘峰的直接对话描写有如下几次:靶场上批评“我”、吃他做的甜食时,谈到“我”的父亲、修沙发时与“我”的对话、在四川街头碰见时的对话及在北京“我”去看望生病的他的对话,其余关于刘峰的语言和心理描写几乎都是叙述者的转述。而叙述者讲述的全是由她记忆的点滴拼凑起来的的刘峰,而不是由人物行为与内在心理驱动自然展现的刘峰,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降低了刘峰人物形象的真实感和丰富性。虽然刘峰的行为和心理受制于写作视角的限制,无法像全知视角那样全部呈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无法对刘峰的性格进行细致表现。尤其是刘峰作为一个默默做甜品给心爱的人吃,只看到她吃得高兴、便心生欢喜的人;一个默默顾全跳舞时卫生巾忽然漏出的女同事的心理自尊的人;一个在大家都不愿意去与有汗臭的女舞伴跳舞时他挺身而出的人;这样一个如此体贴与照顾他人的人,会在什么样的情感与心理状态下才会突破思想束缚,大胆触摸心爱的女子?这些复杂的情绪在小说中都被作者处理得比较粗糙。这使得刘峰后面对丁丁的触摸行为显得十分突兀,不符合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作者经常粗暴随意地代替人物对其进行心理分析。例如:
根据丁丁后来对我们的描述,我想象力都跟不上了:那该是多滑稽的场面!刘峰一只手紧搂着丁丁,生怕她跑了,另一只手那么眉毛胡子一把抓地给他心爱的小林抹泪。一边抹,一边暗自惊叹到底是上海女子,这手感,细嫩得呀,就像刚剥出壳的煮鸭蛋,蛋白还没完全煮结实……脸蛋就这样好了,其他部位还了得?①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以这样被想象的心理状态做基础,刘峰的手从丁丁的脸移到了后脖颈,又移到了后背,这样不可控制的状态之所以发生,那就似乎理所应当了。但这样的描写不仅粗陋,更是把刘峰的形象粗俗化,与之前那个细腻的刘峰大相径庭。
这之后作者又写道:
现在让我试着推理一下——如果雷锋具有一种弗洛伊德推论的“超我人格”那么刘峰人格向此进化的每一步,就是脱离了一点正常人格——即弗洛伊德推论的掺兑这“本能的自我”。反过来说,一个人距离完美人格——“超我”越近,就距离“自我”和“本能”越远,同时可以认为,这个完美人格越是完美,所具有的藏污纳垢的人性就越少。……①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4、163、183页。
在这里,作者不仅完全以个人的推论代替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显得苍白贫乏,缺少心理基础,而且有意引导读者将刘峰看成是一个有完美人格、缺少普通人性的人,因此当他展现情欲,众人的背叛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为大家背叛刘峰的行为寻找解脱的借口。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对刘峰好人形象的塑造,而且造成小说主题的模糊、情节转折的生硬。②在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中,导演对这一段情节进行了删减与细化。删去了刘峰抚摸林丁丁身体的行为,只是拥抱了一下,又增添了接触前二者共同收听邓丽君歌曲的情节,情歌激起了刘峰心底的柔情,情愫蔓延涌动至情不自禁,刘峰的拥抱行为变得可以理解和接受。这弥补了小说的不足。
再者,小说对于作为叙述者及小说主人公的“我”,即萧穗子的人物塑造更为苍白。整部小说基本没有对萧穗子的单独描写,关于萧穗子的心理描写只有在刘峰为林丁丁、郝淑雯和我做甜食时,有所刻画,从误以为刘峰为“我”做的甜食到发现三人之中蹭吃的是“我”。除此之外,小说中看不到任何关于“我”自己的心理描写。作者回避了对故事中“萧穗子”的人物刻画,基本只能看到叙述者对他人的回忆。她在文工团这么些年发生的事,我们只知道她看守靶场、给少俊写情书,而后者也是一笔带过。至于她后来怎么来到北京成为作家,以及这四十余年的命运流转,我们无法知道,更无从判断萧穗子的性格、品质。并且,在整个讲述中她似乎都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冷静地观察刘峰、林丁丁、郝淑雯几个人的命运变迁,对他们几个人的讲述,也全依靠几次偶然的“碰见”来触发,作者让叙述者代替了故事人物萧穗子,让她始终作为一个观察者和他人经历的转述者出现。叙述者用自己的故事外的视角,用她作为叙述者的情感改变了回忆本身,她用冷静的叙述口吻代替了作为当事人的萧穗子的声音,忽视了对故事层中主人公“我”的描写,造成了萧穗子人物形象的不完整。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角色的时候,巧妙地通过人物叙事功能和叙事视角的设置,回避了对自身人生经历的回忆与描写,使得所谓的个人自传色彩仅成为一个影子,几笔带过。抽离了对于这个小说人物的性格塑造,萧穗子的形象就被模糊成为一个故事讲述者,缺乏作为历史与事件参与者的那种思想与情感厚度,失去了真实感与打动人心的力量。
从本质上来说,刘峰与萧穗子一样,都只是作为写作者的严歌苓透视人性之恶的工具。刘峰是引诱和展示特定历史环境下众人之恶的靶子,一个符号性人物;而通过萧穗子的眼光,我们能够看到严歌苓对其他众人的嘲讽与鄙视。另外,她明确地告诉读者,萧穗子是与刘峰一样的无辜者与受难者。比如,小说中萧穗子两次否认参与了对刘峰的批斗:“当时我没有参与迫害,是因为我心不在焉。…我的恋爱视野,早就越过红楼老远老远……”;③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4、163、183页。“我不一样,我也是被所有人批判过的人。批判刘峰我的资格不够。我借戏言说真理。”④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4、163、183页。这也从另一方面削弱了萧穗子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历史与生活的复杂性就在于每一个参与者都难以独善其身。当严歌苓通过萧穗子充当一个具有话语权的道德观察者角色的时候,她的写作立场就呈现出对自我自觉或不自觉地偏袒,这使得作品对历史与人性的反思力量被严重抵消,她的文字对读者就失去了征服人心的力量。
结 语
联系严歌苓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在原成都军区当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经历,这个时期的部队文工团生活是她所熟悉的,严歌苓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严歌苓对这熟悉的生活却缺少深入描写。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的写作立场、叙事方式及人物塑造方面都着力不足。她尽力淡化对当时时代环境的描摹,把造成刘峰悲剧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其他人的背叛,仅仅用性恶论避开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例如:“谁不会有自我嫌恶的时候?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们的卑琐自私,都是与生俱来,都被共同的人性框定,我们恨,我们无奈,但我们又不得不跟自己和解,放过自己,我们无法惩罚自己,也没有宗教背景和境界想到‘原罪’。而我们的丑恶一旦发生在刘峰身上……我们所有的自我嫌恶都不必忍受了,刘峰就是我们想臭骂抽打的自我,我们无法打自己,但我们可以打他……”①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页。这里,作者将“我们”被时代胁迫不得不说人坏话,相互揭露,归结为“我们”人性的卑琐自私,将批判的焦点放在性恶上。又任由自己的情感好恶左右自己的叙事,把价值判断预先加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导致主题先行,人物符号化,反而没有凸显出那个特殊历史时代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带上了“我”的想象:刘峰是脱离普遍人性的“超我”,而少女萧穗子又是一个冷静清醒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这些都使得故事仿佛成为写作者的文字游戏,她笔下的历史与人物相比之前的作品,少了太多批判的力度。她只是打着自述的旗号,讲了一个尚算曲折但却单薄无力的故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