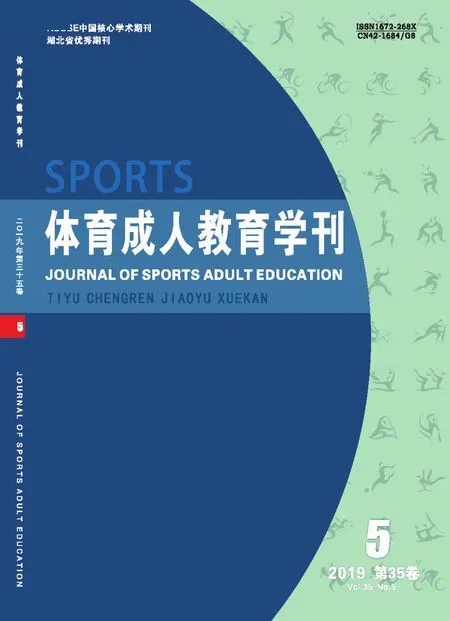回归语境:客家民俗体育研究的学理反思
张自永,刘俊涛
(1.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0,2. 深圳市新华中学 广东,深圳 518110)
客家作为汉族的民系之一,保留了丰富而古朴的体育文化事项,为民俗体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活的标本。熊晓正先生曾指出,学界关于客家民俗体育研究虽然“为深入研究赣南地区客家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但不无遗憾的是,目前关于客家民俗体育的研究总体上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未能完全真实、全面地展现客家传统体育活动与它所积淀的文化传统以及在客家社会生活演进中的意义。究其根源,便是“现代体育”的标签化所导致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失语”,以及研究过程中对其语境的不自觉缺失。这需要从客家民俗体育研究的学术史、客家民俗体育的分类和特征、民俗语境下的客家体育及客家民俗体育的语境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1 客家体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客家体育研究在21世纪初始为高校体育院系少数学者关注。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学理探讨。对客家体育的学理探讨包括对其概念、特征、内容、发展现状等进行整理和概括,如《客家体育的特征与功能》(吴玉华等,2005),《客家传统体育及其文化特征》(邓小勇,2004),《论客家民间体育文化的蕴含》(秦德平,2008),《梅州客家地区传统体育文化特征的研究》(田维舟,2005),《客家节庆民俗体育及其文化特征分析》(罗天怀,2012),《赣南闽西客家体育文化初探》(张允蚌、张齐斌,2007),《客家民间体育文化研究现状与分析》(焦峪平,2013)等。这一类的研究较少取得共识性结论,目前仍存在概念界定不明确,特征归纳不具体,内容分散和发展现状受限制的境况。就客家民俗体育的特征而言,其主要存在于节庆活动、宗教活动、祭祀活动中,而现有研究基本沿用其他民系体育文化的共性,少有客家体育自身的个性特点。
第二类是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客家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个案研究是有选择性地收集单个客家传统体育项目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展示某些项目的精华部分。吴玉华在个案研究上建树颇丰,先后对客家“打龙灯舞狮子”(2006)、竹篙火龙节(2010)、曾坊村“桥帮灯”(2010)、白鹭“抢打轿”(第二作者,2012)、南安“罗汉舞”(2012)、南康“鲤鱼灯”(2013)和宁都“中村傩戏”(2017)进行了研究。此外的个案研究还关注了营前镇“九狮拜象”(谭东辉、刘志民,2010),五华下坝迎灯(张俊华、曾桓辉,2011),姑田游大龙(温艳蓉,2013)和“抢打轿”(谭东辉,2010;刘涛,2013)等。
这类个案研究对客家体育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描述,为理解客家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精彩案例。但是这种案例的提供并没有达到立足宏观分析微观,通过微观反观宏观,并在实践中处处凸现理论功能的意图。如对“抢打轿”的个案研究,谭东辉、张玉菊和刘涛的切入点看似不同,实质上并没有摆脱“白鹭古村介绍-仪式过程-文化价值”的叙述桎梏。诚然,基于个案的研究方法不是统计性的扩大化推理(从样本推论到总体),而是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从个案上升到理论)(Robert K. Yin) 的逻辑基础,类型学的研究范式、个案中的概括、分析性概括以及扩展个案方法等是超越个案研究出路所在,关键是将民俗体育回归放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突出理论在介入、过程、结构化、重构的实现等原则中的位置。
第三类是应用研究。对客家体育的应用研究是受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影响,具体可以分为对学校体育、农村体育、体育旅游、资料库建设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对客家体育在学校体育中的应用的研究在于客家体育课程开发可行性研究、模式、作用和意义,主要有张允蚌(2009)、邱伯聪(2009)、廖金琳(2009)、吴玉华(2010)、赖建敏(2011,2012)、谭东辉(2011)、刘圣富(2013)等。刘霞对客家体育促进农村体育发展的研究较为深入,分别从发展对策研究(2006)、农村幼儿健康教育(2006)、农村社区体育建设研究(2007)进行了论述,其他学者也有与之相类似的研究(沈黄胜,2006;廖金琳,2009;李伟,2013)。对赣南、闽西和粤东北体育旅游关注的分别是赵金岭等(2007)、林丽芳等(2010)和龚建林(2012),谭东辉则从宏观上进行了论述,发表《客家民俗体育与旅游研究》(2011)。此外,谭东辉还对客家体育的资料库建设有所探讨。
综上,从研究队伍来看,客家体育的研究呈现出窄群体特征。以CNKI“客家”和“体育”为主题词进行联合检索,并类型筛选出的105篇论文中,赣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吴玉华教授便占17篇,比例达16.2%;江西理工大学的谭东辉9篇,比例达到8.6%。在研究方法上,客家体育的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在区域上,目前对于客家传统体育活动的收集整理及研究主要还局限于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和对客家文化研究相对较热的省市,客家族群聚居地域分布广泛,客家传统体育活动大多散见于全国各地,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在学科界定上,并没有实质性地与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互通,只是在研究形式上有所借鉴,研究思路相对狭窄,难以引起各界广泛共鸣与关注。
总而言之,以个案研究为主要生存策略的客家体育研究在总体上停留在表面形式的描述,而对其赖以生存的意义系统和符号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文化语境缺乏深入的讨论,更缺少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层面的社会环境加以考查和诠释,而这正是客家民俗体育研究的语境之殇。
2 客家民俗体育研究的基本问题反思:概念、分类及特征
2.1 “概念”的使用相对杂糅
关于“体育(Physical Education/Sport)”和“民俗(Folk-Lore)”的概念,相关学界虽未能达成完全一致的科学认知,但也取得一定的学科共识,具体而言,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发展的文化活动”[2],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3]。
《体育科学词典》将“民俗体育”界定为“在民间民俗文化以及民间生活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 是顺应和满足人们多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4];张鲁雅认为民俗体育是“民俗活动中的体育”[5];余万予认为民俗体育是“在民俗活动中产生, 依赖民俗节日发展, 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流传的与健身、娱乐、竞技、表演有关的活动形式”[6],台湾地区的蔡宗信将民俗体育定义为“是一个民族在其居住的地方慢慢共同创造形成传统而延续下来的一种身体运动文化习惯”[7]。
涂传飞博士首先于2007年对民俗体育的概念及其与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族体育的关系进行辨析,他认为民俗体育(folk sports),是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的一种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化、仪式化的传统体育文化,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体,也是一种生活文化[8]。将民俗体育阐释为一种“生活文化”具有较强的理论洞察力,与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相吻合,是从民俗学角度切入体育事项研究的必然路径。但这一观点随即引发学界的讨论。陈红新、刘小平认为民俗体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广大民众在其日常生活和文化空间中所创造并为广大民众所传承的一种集体的、模式化的传统体育活动[9]。王俊奇则认为,民俗体育是指那些与民间风俗习惯关系密切,主要存在于民间节庆活动、宗教活动、祭祀活动中,是一种世代传承和延续的体育文化形态,具有集体性、传承性和模式性特点[10]。
从以上诸关系辨析中,“客家民间体育”、“客家传统体育”、“客家民俗体育”及“客家民族体育”均可以被视为成立的,也正在被不同学科知识背景的研究者不同频次地使用。但这种机械的概念结合,却与“客家”本身背道而驰。
客家(HAKKA)是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中原汉民渐次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区,与当地土著和畲瑶等民族长期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独特客家方言系统,独特文化民俗的汉族支系。客家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融中原文化与南方土著文化于一体的多元文化”[11]。因此,考虑到客家民系独特的历史形成背景、地理分布、播衍路径、文化特质,以及内在的血缘认同、地缘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逻辑,综合考虑其内涵和外延,“客家民俗体育”的概念较为贴切。
客家民俗体育活动是客家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凝聚着族群认同,承载着地方性知识,记述了客家历史文化传统,是传承、发展客家人“历史记忆”的重要形式。还需要说明的是,客家民俗体育与节庆有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客家民俗体育必然附着于节庆之上,或者因民俗体育而产生成为区域内的节庆。在这个意义上,“客家节庆民俗体育”与“客家民俗体育”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相似,两者可相互替代。
2.2 “分类”的标准缺乏层级
吴玉华分别在2007年、2011年、2014年根据不同分类方法将客家民俗体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类别划分,将客家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分为跑跳类(7项)、投射类(4项)、水上类(3项)、舞蹈类(5项)、武艺角力类(6项)、室外游戏类(12项)、室内游戏类(11项);依据目的和形式不同,将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文化项目分为节庆祭祀仪式类(51项)和节庆娱乐舞蹈表演类(25项);依据目的、内容和形式不同,将客家节庆民俗体育分为舞龙类(5项)、舞狮类(3项)、灯彩类(10项)、舞蹈表演类(7项)和游艺竞技类(5项)。
不难发现,吴玉华在使用概念上没有完全一致,也因分类对象不确定,分类标准不统一,导致分类方法没有做到“不重复、不遗漏、分层次、不越级讨论”,并不能从整体上反映出客家民俗体育的面貌。
我们认为,从性质表现和形态划分,除了以嬉戏、消遣为主的民间游戏娱乐(如跳绳、踢毽子、滚铁环等)外,客家民俗体育可分为力量型(龙舟竞渡、舞狮舞龙等)、技巧型(高跷、上刀山等)、技艺型(灯彩等)三类。按照参与对象所属范围划分,客家民俗体育可分为个体、宗族/房派、跨宗族/区域三类,并多以宗族为单位。
2.3 “特征”的概括指向不明
关于客家民俗体育的特征,学人时有论述,如谭东辉(2010)以“抢打轿”为切入,将客家传统体育文化特征概括为儒学性、历史性、农耕性、传承性、娱乐性;王俊奇(2010)认为典型的汉民俗特色和风格和受土著文化的渗透是客家体育项目的文化特点;吴玉华(2011、2014)将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文化特征概括为五点,即多元共存与兼容并蓄性、山区农耕性、节庆与宗教祭祀性、宗族性、鲜明的地域性、竞争性;张俊华(2015)以兴宁赏灯为例,对客家民俗节日活动的体育文化特征概括为传统性、教育性、健身娱乐性、宗教民俗性;黄何平(2016)将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特征概括为独立性和移民性、地域性和共融性、娱乐性与竞技性。
如上所述,在对客家民俗体育特征的诸多论述中,往往是在其母题“客家文化”特质——如林晓平教授所述的“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质”[12]——基础之上的增删或阐述,缺少“体育”这一概念的核心指向,导致其在特征概括时出现文化元素缺失的现状。
特征是基于功能或价值的判断,客家民俗体育往往并不以自然质功能为旨归,而是侧重结构质功能和系统质功能,具体表现为调节功能、教化功能、维系功能和规范功能。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经验,认为客家民俗体育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寓于宗族生活,紧密民间信仰,兼顾强身健体。
3 民俗语境观照下的客家体育
用“现代体育”的标准理解、认知、衡量和研究客家体育是缺失民俗语境观照的典型特征。正如熊晓正先生所指出的,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整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中,我们应当避免用“现代体育”的文化取向去审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力图克服用“现代体育”标准的认知模式去解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思维定式,依据文化传承者的立场,从总体上去把握、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我国乡土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与功能,并争取契合到新时期的社会建设和民众生活之中去。
而所谓“现代体育”标准,即是以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为标志的,以“身体运动哲学”为建构基础的,以个体对抗性竞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西方体育形态,强调的是身体的运动极限和对抗。这种标准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在衡量尺度存在显著差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主要表现为大众化的生活表演(Performance),如气功、武术等修身养性形式,是建构在“生命运动哲学”基础上的体育形态,追求的是身心统一,个体与社会、自然相融合的境界。
因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应跳出基本的现代西方体育“竞技”理论的桎梏,将民俗体育重新归置于“生活世界”,注重民俗体育背后文化的建构、宗族的消长、时空的交融,从而客观描述静态的民俗事项,理解其产生,解释其传承,并把握民俗与民俗主体和发生情境所构成的活动整体,深入地认知渗透在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换言之,任何将体育与社会割裂开来所做的体育研究都是不完整的。
客家民俗体育归根结底是客家人改造地方社会的一种文化手段,是文化和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将民俗体育事象从多重语境中分割开来,尤其是使民俗体育与其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痛苦的剥离,这样只能勾勒出泛化的民俗景象,也将导致客家民俗文化的“失色”。
4 客家民俗体育的语境研究
语境(contest)进入民俗学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理论方法。美国民俗学家、表演理论代表性人物鲍曼(Richard Bauman)认为民俗存在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个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会赋予民俗以形态,并把语境划分为两个大层面,即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st,理解文化需要理解的信息,主要指意义系统和符号性的相互关系)和社会语境(social contest,主要指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层面)。为了充分理解民俗事件,共时研究应当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应当把表演者(人)、表演(活动)和处境(政治、经济、自然等方面的条件)的历史背景考虑进来。刘晓春认为从具体的民俗事象来看,时间、空间、传承人、受众、表演情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共同构成了民俗传承的语境[13]。
萨姆纳在《民俗》(Folkways:AStudyoftheSociologicalImportanceofUsages,Manners,Customs,Mores,andMorals)一书中,提出系列概念并将它们的生成关系联结为一体:习惯(habits)发展成风俗(customs),再发展为仪式(ritual)、德范(mores),进而派生出制度和意识形态。基于萨姆纳这一关于民俗的基本理论,我们认为客家民俗体育的研究,一般应着眼于宗族,地域社会,活动的发生、演变、仪式过程、传承发展,其文化价值和意义以及与社会意识诸形态的关系(如民间信仰)等。
以“客家摇篮”赣南杨村民俗体育“池塘龙舟赛”为例。现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如《池塘龙舟赛 传承五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报告》(赖观扬,2010),《客家池塘龙舟赛的仪式展演与集体记忆》(张自永、李雯,2013),《杨村龙舟赛的展演、价值与特征》(赖观扬,2014),《客家“池塘龙舟赛”集体记忆的建构》(吕秀菊、张自永,2015),《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活动的调查研究》(王美芝,2014),《民间体育组织中的精英治理——以赣南客家“池塘龙舟赛”为例》(郑国华、张自永、祖庆芳,2016)等。不难发现,既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仪式本身”(如起源、演变、仪式过程、传承发展)的或简或繁的白描,稍有涉及与之相关的宗族、地域社会,而相对于主体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与社会意识诸形态的关系(民间信仰等)则鲜有关切。
因此,学人在对类似于“池塘龙舟赛”等民俗体育进行研究过程中,对文献或田野资料缺乏辨析的能力,止步于现象。笔者曾专门撰文讨论“池塘龙舟赛”的集体记忆的形成,认为其起源历史的集体记忆形成初期并非一定基于全部的历史事实,而是社区精英展开了一场带有自救性质的文化经营,运用民族-国家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并由此获得来自经济或政治上的现实回馈。但遗憾的是,这也仅仅是基于一个田野点研究的一个视角而言,并不能对客家民俗体育“见木见林”。
总之,在客家民俗体育的语境研究中,除了“仪式本身”,要对“文化语境”(生活功能、相对于主体的价值)和“社会语境”(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与社会意识诸形态的关系)进行研究。换言之,要开展上述的关于民俗“语境”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历时性上的对充分史料的全面梳理,而且要强调能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的共时性考察,兼顾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的统一,从而追求整体性的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主张用单纯的定量的方式研究客家民俗体育,而应加强以“案例研究方法”为代表的定性研究,开展充分的田野调查,并基于理论反思进而“深刻揭示材料背后所潜在的深层次的社会的真正结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