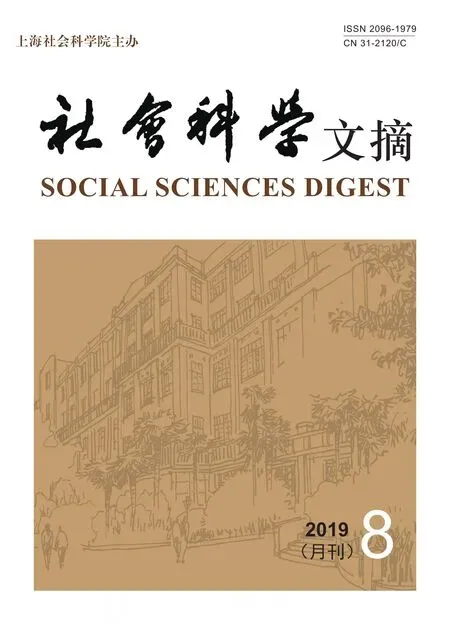全球化的再认知与价值重估
——作为全球化的现象学与全球化断层问题
文/田海平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期望在一种学科意识层面和学理深度上对该问题进行哲学总结和交代的时候了。首先,是“一种作为现象学的全球化”,它需要我们以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精神和眼光,思考全球化之“现象事情”本身。其次,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学”,它需要我们把全球化问题不只是单纯地看作是某个学科领域的问题,而是将它看作是一个哲学问题,即,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居优先地位的全局性的、总体性问题。我们需要从一种哲学意识的高度上进入我们所说的“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学”。
全球化的围城:全球化的“潮”和“逆”
什么是“全球化围城”现象?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有一个关于“围城”的比喻,原本是用来隐喻或描述人类婚姻现象的复杂性。它非常经典,广为流传。我借用它来隐喻或描述全球的“潮”和“逆”的复杂性。
“全球化”在今天确实已经呈现出一种日益明显的“围城效应”——一方面“在里面的已经想出来”了,另一方面“在外面的还想着要进去”。以美国为首的居于全球化之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出现了一种“里面的想出来”的“退群”之“逆流”,从而导致了今天所谓的“全球秩序的崩塌”;而广大的作为全球化外围的或非中心的发展中国家,则处在一种“外面的想着要进去”的全球化的“潮”中。因此,有学者说,2018年在世界历史上或将会留下特殊印记,或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年,美国发动“贸易战”(或者“贸易摩擦”)、奉行单边主义,实质性地刻画出了这种“潮”与“逆”的针锋相对的角力方向。它前所未有地激发人们重新审视和思考全球化的未来及其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全球化的再认知”问题,其实就是旨在呼吁人们正确看待并理性地应对全球化的“潮”与“逆”之相互对峙的现象。
谈到全球化的“逆”流,绕不开这个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从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特别是从一种“作为现象学的全球化”的意义上,围绕这个大人物所展开的世界现象,称之为“特朗普现象”。
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开始,这位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就以他特立独行的推特治国方式推行“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政策。特朗普的一大绝招,要么威胁“退群”或对现有的全球化规则采取质疑态度,要么就直接“退群”。这包括他让美国从诸多国际组织退出,以及对现有贸易组织和安全联盟的质疑和不满,也包括他主导的全球贸易壁垒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持有的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民族主义理念,它迎合了日益滋长起来的“民粹主义逆流”,是美国近些年内外政策的价值基础,也是其发动此轮“贸易战”的价值基础。因此,“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表面上看,似乎是美国人民选择了一位既“特不靠谱”又“特别靠谱”的总统——说其“特不靠谱”,是从全球主义者视角看,特朗普的某些欺诈性话语暴力、利益至上价值观和政治短视,在全球主义者或世界主义者看来,无疑是一些“特不靠谱”的言行;说其“特靠谱”,是从民族主义者的视角看,特朗普的言行相对于坚持“政治正确”的主流价值观而言,仿佛多了几分“真诚”和“可爱”,因此在民族主义者的眼中,其言行又是“特靠谱”的。但是,如一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特朗普现象”往深里看,反映了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种普遍性“撕裂”,是这种社会撕裂的表征——即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民粹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之间的撕裂,也可以看作是坚持“向右转”的人们与坚持“向左转”的人们之间的分裂。特朗普曾经公开地批评美国社会中的全球主义者的主张。他把他的几位前任称为全球主义者,他批评说,这些全球主义者只关心“世界如何”,而不关心“美国如何”,他们应该为美国的衰败负责,而坚持“美国优先”或“美国再次伟大”,就要做一名公开的甚至是标签化的民族主义者(这种自我定位离民粹主义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而不是一名全球主义者。
毫无疑问,“特朗普现象”是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它公开颠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世界关于全球化的神话,即全球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而美国在过去百年历程中拥有对全球秩序之现代自由规划的无可争辩的领导权或领导地位。然而,吊诡的是,这个全球时代的领跑者,现在却带头跑偏了,出离了它所预定的轨道,出现了对全球化或全球主义的“逆动”甚至“反动”。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时代神话,而现在这个神话无可挽回地幻灭了呢?或者,进一步,意味着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潮”了呢?
我认为,现在谈论“全球化的幻灭”,的确是为时尚早。不过,“特朗普现象”是可以用来分析“作为现象学的全球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对这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全球化之再认知”的一些基本要素。特别说来,是有助于我们认识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类型的“潮”与“逆”之互为他者、相反相成的形态特质的。
有关“全球性事物”的各种概念是我们用来描述和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工具,“特朗普现象”所表征的那种针对全球主义的“逆”或“反”,其本身就是这种“全球性事物”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
仅从语义学层面看,我们用来指称全球化的相关语汇,包括了“全球(global)”、“全球性(globality)”、“全球主义(globalism)”、“全球时代(globalage)”和“全球化(globalize)”,等等——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术语和词汇。这些语汇在一种语词现象学的诠释意向和空间中,是循着“从全球性的事物开始进而达到全球化”的那个系列。“全球性事物(giogal things)”总是在一种历史地理序列中已然使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超越了国家、民族或特定社群及社会的界划和疆域,从麦当劳、宜家、沃尔玛,到移动通信、iphone、推特、微信、GPS导航和人工智能,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高铁、孔子学院,等等,这些所谓的“全球性事物”所具有的“全球性”,使得“全球的”一词在现象形态上获得了一种空间性定位。它的本义是指地球或大地在空间位置上的集聚和展现。因此,当我们论说一物是“全球的”,这时,我们通常是指它在生产和消费的时间维度产生了一种空间化效应或空间化的结果,即它产生自一种对相互依存的地球生存的具体完整性的日益紧迫的吁求。这些“全球性事物”既产生自,同时又推进了那种使人类结合起来而非分离开来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的”和“全球性”在语义上表达了“人类之商品化”,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人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之后果的客观化”。当这一进程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全球化就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一种大“潮”。
“全球主义”是对全球化的一种积极的价值回应,它主张从全球视野和全球性事物之深远政治意义的价值立场看待国家、民族和个人,其所持的理念是将全球化的空间位置定义为必须予以坚持的一种价值立场。而民族主义则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消极的价值回应,它看到了全球化在改变人类行动准则的背后隐蔽着的国家间、民族间、文化间或社群间之争胜意志或权力意志的角力,其所持的理念是将全球化的空间位置定义为必须予以抵制的一种价值立场。从这个意义上看,“特朗普现象”所反映的正是全球时代之“潮”与“逆”两种运动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互为表里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客观地将“全球性”或“全球性事物”视为人类之商业化的种种算计活动的一个现实方面,那么“特朗普现象”所表征的民族主义的“精明”与中国当代社会中时常冒头的抵制日货或韩货之类的“群众运动”的“义愤”之间,实际上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它们都属于全球化博弈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其中的一种自然性的或者本能化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愚笨的)形式。
总而言之,在当今这个日益高速运转起来的全球时代,全球化的“潮”与“逆”,反映了异质性全球化的深层焦虑和撕裂,尤其是在面对全球性市场之竞争、全球化规制之主导和全球主义话语之争胜的现实博弈时,“全球性事物”所具有的全球性一再地面临着人口、资本、权力和话语的非连续性断裂的困扰。“潮”与“逆”的辩证法,出现在全球化的断裂层。在这个意义上,语义层面的现象学诠释只是瞄准了最显著地反映那种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一些标识性的“符号”或标签性的“现象”。除了语义层面的现象学诠释外,我们实际上还需要有更重要的价值观的、知识学的、意识或精神分析的,以及理性权衡等诸多层面的透视,才可能获得一种立体化的整体性观感。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现象”所表征的“逆”全球化,实际上可以归类为全球化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对全球化之“巫术”的抵抗运动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要言之,其所凸显的,乃是在全球化之连续性表象下(且为之所遮蔽)的一种始终存在的非连续性,亦即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的断层”。
“特朗普现象”的典型特征是运用“全球化的力量”(技术、经贸、政治、话语和军事)或最显著的“全球性事物”(他使用“推特”这样一种“全球性事物”)表达对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逆”动。这是一种全球化悖论的体现,因而不可避免地处在了“全球化围城”的焦虑中心。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应对“全球化的围城”现象,需要透过全球化的“潮-逆”之辩证的表象,真实地面对“全球化的断层”或“断裂”。
全球化的突围:全球化断层上的“势”和“能”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断层”问题?或者说,如何站在“全球化断层”上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需要考虑那种在全球化的连续性体系中赫然呈现的非连续性,它往往意味着某种异质性要素的出现带来了一种愈来愈具体的“全球化断层”问题。当人们站在“全球化断层”上时,问题之关键是要面对与“全球”照面的那个自身“方位”,或者说那个自己的“地方”。这需要建立在“对全球化的价值重估”的前提或基础之上。中国的全球化之突围,不能避开“全球化断层”上由“全球/地方”的空间感知及其本质直观所展开的两个价值重估:一是关于“势”的重估,二是关于“能”的重估。
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地方”对全球化及其断层的价值重估,重点即是要明乎不断变化着的全球博弈之“势”。而对于走向和平崛起和文明复兴的中国来说,在全球化断层上争取上升之“势”,是我们必须全力争取的“大趋势”。因此,必须在价值重估的意义上回答“我们究竟需要何种全球化”的问题。关于“能”的理念根源于对我们如何行动或怎么办的一种价值定位和价值评估,其意向性既指引向一种“积极之作为”,也指引向一种“消极之作为”。在“势”之权衡上,我们倾向于主张一种积极性的价值尺度——否则,我们很难把握“全球化断层”带来的新的战略机遇;而在“能”的价值评估上,我们需要优先思考一些消极性的有“止阀器”功能的价值尺度,即从一种“不能的能”出发进行价值重估或价值勘定,以避免落入“全球化断层”可能带来的各种陷阱。
具体来说,在2018年“特朗普现象”所展现的新一轮“全球化断层”上,对当代中国方位上的全球化突围而言,全球化的价值重估需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能”,以划出我们“能做”的边界:第一,我们不能掉进“文明冲突论”的陷阱,这些论调是美国学者站在美国方位上对全球化断层做出的一种价值重估,它预置了美国版的普世价值论的陷阱;第二,我们不能掉进“虚无的全球化”的陷阱,它是在美国方位上搞出来的一种“全球本地化”,是美国价值观的全球化,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资本主义、麦当劳化和美国化”的表征。
全球化的出路:面对全球化的战略机遇,中国何为?
全球化的关键动力,来自于增长的方位和源头。一国或一地区如果不能成为推动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方位和地方,全球化的战略机遇就很难或者很有限地被捕捉到,也很难或很有限地向该国或该地区开放。因此,我们今天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几代中国人的使命,它决定了我们要从追随全球化的大潮,转向做新一轮全球化的领跑者。有人说,中国有14亿人口这样一个巨无霸式的社会在“全面进入小康”,有14亿消费者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和美国打“贸易战”,我们无所畏惧——我们有底气!这话确实有它的道理,但基于消费的全球化仍然还只是一种“虚无的全球化”,它本质上是“虚的”,是“不实的”,是“无底气的”。我们只有基于一种生产的、工业制造的、产业领先的全球化,才能在中国方位上找到一种“实在的全球化”的进路。《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性体现在这一点上。
在今天的全球时代,“全球化断层”已经呈现。那么,出路在哪里?中国如何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潮中有所作为?
全球化始终与“去管制”、“去壁垒”、“去零和游戏”紧密相关。这意味着,它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最大挑战恰恰就在于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即“壁垒的产生”、“管制的人为设定”和“零和游戏的发生”。因此,在全球化的“潮”与“逆”中,围城现象(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会始终存在。在当前的“全球博弈”中,全球化的突围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新一轮全球化提供给我们的战略机遇,以及我们所做出的审慎抉择和明智决断。由此,我们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由于新时代来临,全球化仍然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潮”,它没有过时,没有过气,而且是历三百多年的世界文明的“大潮”之所系。虽然,今天世界上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甚至某些“反”全球化的现象,但并不足以改变全球化作为“潮”的文明特质。当然,我们必须正确理性地应对这种“反动”,即需要对这种“逆”“反”进行有效的回应。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关键在于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有效地反击各种形式的“文明冲突论”。
第二,由于全球化的“断层”赫然凸显,全球化呈现为一种新的“势”,以当今世界秩序而论,它正在成为“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大势”。我们要从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学的总体性视阈或哲学视界上,思考全球化之为一种新的大趋势,且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方案”,进而进一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即思考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旨归。
全球化的再认知与价值重估,需要立足于“新一轮”的全球化或新时代的全球化——全球化仍然是一种“潮”,内含一种“势”,它可能带来陷阱或者布满了陷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其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希望和机遇。尤其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技术等助力全球化的新时代,全球化蕴含有不可估量的“大潮大势”、“大能大力”,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