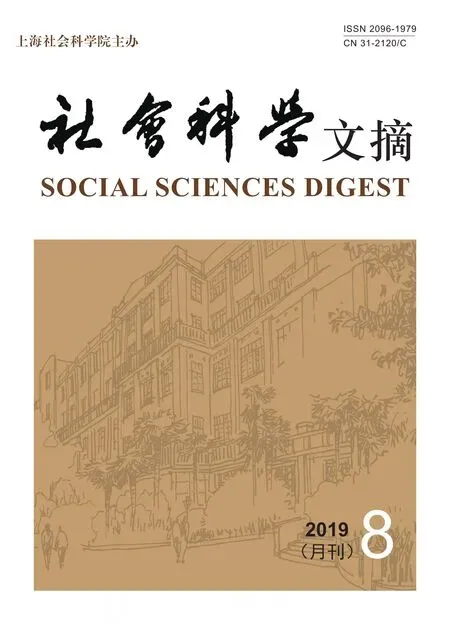从北美“中国研究”发展历程看智库研究范式之转变
文/袁曦临 吴琼
智库研究方法层面的发展态势
随着现代社会问题复杂性的增强,智库研究已经不再可能仅仅通过资料的收集整理、描述阐释得以完成,虽然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发掘和整理极其重要,但这仅仅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步,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从资料和数据中发现、归纳并提炼出对于当下或未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有价值的规律和普遍经验。现代决策理论越来越强调基于证据循证的科学决策,多学科合作交融已经成为智库研究的主流。
1.量化的实证研究趋向
欧洲自19世纪末开始,就已经注重将数据的统计学方式引入史学研究。通过收集并统计某地区一定时期内社会各阶层的人数及其收入状况,可以计算出该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即平均数),以及中产阶级的收入(即中数),发现该地区各阶层人口的收入集中趋势;再通过标准差计算,推演出个人收入与人均收入的差异,即离中趋势;而后将中数和平均数进行比较,得出该地区经济收入是否呈偏态分布及偏态的正负。在此基础上政府出台各类型政策等,调整政府决策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联系。著名经济史学家Robert William Fogel所著《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的出版即标志着“历史计量学”的诞生。采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对研究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以事实和数据为论据支撑,能够有效避免基于个人认知和社会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导致的研究结论的偏差。
现阶段我国智库研究主要围绕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展开,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一带一路、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政治经济制度建设、社会转型等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资政经验,因此对于实证研究方法有着深度需求和广泛呼唤。
2.整体与区域并举的研究趋向
整体主义研究范式是从整体性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渐成趋势。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58年发表了重要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认为历史时间有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之分:短时段主要是突发的历史现象、事件,如革命、战争、地震等;中时段是指具有一定周期和结构的局势或社会时间,如人口消长、生产增减;长时段属于历史的深层结构和基础,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等,而长时段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性作用。智库研究面向的是国际国内的政策制定和决策支持,如果没有宏观的视野,从整体予以考虑,而仅仅从一个学科的知识来分析,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过于细致的研究容易扭曲问题本身,带来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对于现实问题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政策建议。因此,整体研究符合智库研究的要求特点。
与此同时,智库研究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学科内部问题,故智库研究同样也需要具体而微的国别研究、区域研究和专题研究。2012年南海中心获批为首批国家协同创新中心,下设若干协同创新平台,包括南海环境资源研究平台、南海法律研究平台、国际关系研究平台、南海史地与文化研究平台、南海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平台、南海动态监测与形势推演平台、南海地区航行自由与安全合作研究平台、南海舆情监测与国际交流对话平台、南海问题政策与战略决策支持平台等,以期通过问题导向和任务驱动,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基础信息与决策支持服务。
北美“中国研究”范式转变的路径分析
“中国研究”是美国“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成立“国际与区域性研究委员会”伊始,有关中国文化演变、社会流动、经济体制、税收政策、政治制度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的课题越来越多。“中国研究”有着相当明显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
1.“中国研究”问题的多元化
北美“中国研究”至少历经过3次研究问题域的转变和调整。
最初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及其同辈研究者为主,主要考察19世纪末东亚世界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角色和意向,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和全球秩序之间的关联等。如费正清早期的研究《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芮玛丽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1862—1874》、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史华慈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和认识切入点发生变化,早期费正清等研究者多从“冲击—回应”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而孔飞力等的研究则转向保罗·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从中国人自身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近代发展变迁,作为对“冲击一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孔飞力于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即是“中国中心论”的突出代表,该书集中考察了华南与华中地区的社会基层组织团练在遭遇现代化的过程中自身所发生的变化。相关研究还有:楼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到1913年间的广东省》、凯普的《四川与共和中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1911—1938》、舍登的《地方军阀与共和中国:云南军1905—1925年》和周锡瑞的《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这些研究都是从中国的地方省份出发,观察和分析传统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路径。
与此同时,研究主题日益从政治生活层面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马若孟所著《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是关于晚清和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对新中国前的华北农村进行了深入考察,探讨了传统农业步入近代化的问题;而包德威的《中国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则关注了相同时期城市的社会发展问题。
第二次转变,主要关涉“二战”结束后冷战背景下东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态、利益与社会关系的探讨。该领域的研究涉及领域十分宽广,著名的研究有斐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该书力图以城市生活的变动来诠释中国的革命运动,揭示近代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诚如斐宜理自述的那样,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到《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她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
第三次转变,瞄准的是20世纪末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转型阶段。西方特别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成为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对世界的意义何在?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有什么区别?未来中国会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会发展出一个具有何种示范意义的文明?此范畴内研究内容丰富而广阔。诸如黄宗智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1990年出版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陈佩华的《陈村:革命到全球化》,通过跟踪一个村庄从最初的毛泽东时代如何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最后面对全球化的过程及其内部调整;顾林的《中国经济革命:20世纪乡村企业》,则通过对湖北地区自民国初年一直到1978年以后的农村纺织业的对照研究,探索市场经济与乡村社会变动的联系。
近年来,中国研究领域由宏观到具体,研究的主题愈加宽广。论文集《中国亲属关系:当代人类学视角》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和《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和社会网络》都是从人类学实地考察出发,展示中国社会的变迁。在法律建设方面,陆思礼1996年的成名作《中国司法改革》、1999年的《笼中之鸟:后毛泽东时代的司法改革》、2005年的《法律在中国的应用:国家、社会和实现正义的可能性》等侧重关注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
2.“中国研究”方法的实证化
费正清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之初,即奠定了开放多元的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的风格,强调对于中国的研究需要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图景的复原,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特质。担任过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的邵东方曾经开过一门汉学研究方法课程,在研究方法和证据使用方面提出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三原则,即识别古今之异、寻找发现证据和探究历史因果。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所做的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研究就充分体现了上述三原则。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中国城市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之一。施坚雅认为,把中国的乡村理解为自然村落,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社会结构,周期性的庙会集市才是农村的基层市场社区。由此,施坚雅计算出19世纪90年代全广东省的村庄数与市场数之比,提出形成中国乡村市场区域的正六边形模式。而后,他使用这一模型分析了四川、浙江等地的农村社会,发现“十八村庄一市场”的结构模式,从而形成了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施坚雅模式”。施坚雅模式的突出贡献在于将地理空间概念引入经济历史学研究中,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野。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对此理论模式有诸多非议,但从方法层面看,施坚雅模式是非常成功的。
3.“中国研究”资源的系统化
对于智库研究而言,研究资料和研究数据的获取、收集和组织、整理,不仅仅是工具准备,甚至就是研究本身。北美的中国研究非常重视实地调查报告和访问记录,重视统计资料、地方志、地方档案、报刊杂志、案件记录、回忆录、私人信件、宣传品、照片等资料的收集。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收集的《杰德·斯诺·王私人档案》包括了大量20世纪70年度初期访问广东基层社会的笔记,以英文记录了当时的广东农村的教育、经济、文化状态,是难得的基层社会报告。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馆收藏的《谭良所藏康有为保皇会资料》,主要是300多封20世纪北美保皇会成员之间及与中国国内的往来信件,对于研究华裔社团、广东一带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胡佛研究所则侧重中国档案文献的收藏,涵盖20世纪以来大量珍贵历史和政治史料,包括蒋氏父子日记在内的特殊人物的回忆录和个人收藏。2005年,该所还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黄宗智及其妻子多年收集的中国历史档案资料,其中包括2500件法律案件,时间跨度自晚清、民国政府到新中国时期。这些历史档案成为胡佛研究所进行智库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伴随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研究资料的收集和组织愈加注重分析资料背后的逻辑联系,倡导将量化数据库应用于历史研究。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曾任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中清,已建立了18世纪至今的中国历史数据资料库。
我国智库研究范式的转型思考
一个世纪以来的北美“中国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时空范畴和研究视野,也带来了方法论的创新。北美的中国研究无疑为我国智库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1.在研究思维层面强调全球化的研究视角
需要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放到国际和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从而完成中国地方性知识和历史经验转化成具有全球意义话题的转变。例如黄宗智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明清商品化的研究,通过对“过密化”理论的引入和修正,提出明清时期的商品化之所以无法近代化,根本原因在于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由此,过密化理论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认识视角和研究方法层面都对我国社会经济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2.在方法层面强调定量化的实证研究
对于智库研究而言,方法论和历史观其实是统一的。不存在孤立的方法论,方法和工具就决定了观察世界的立场和眼界。实证研究强调研究是建立在事实数据基础之上的,尤其重视一手资料的发掘、整理,强调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对于智库研究而言,这将避免研究预设的偏颇以及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长久以来,对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巨大成就,如何从理论和模式层面进行解释一直是学界也是全世界瞩目的问题,但仅仅阐述观点、描述过程和个案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合乎规范的数据和论证范式,才能减少模糊不清的争论,为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之间的讨论和交流提供事实基础,为科学决策提供扎实的事实依据。
3.在研究合作层面更多倡导跨学科协同研究
注重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围绕现实问题展开多维度研究。一般理解中,研究模式似乎只关乎研究路径的具体展开与研究方法的应用,但实际上每一个新的研究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新的问题和切入问题的新起点,都拓宽了新的研究资源的来源。南海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南海维权证据链及基础数据库建设,包括监测、提供海域和关键岛礁的动态变化,南海断续线的法理与历史依据专项,南海档案的系统整理与使用专项等跨学科研究;由此推动了交通史、文化交流史以及边疆史的研究,也拓展了海洋史的研究范畴。
结语
在一般理解中,研究模式似乎只关乎研究路径的具体展开与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实现,但实际上,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主题的转变,甚至研究资源的发掘整理同样也是研究范式转变的一种标示。一个世纪以来的北美“中国研究”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研究主题领域几乎涉及了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过程的方方面面;研究方法层面,则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在研究资源的收藏和建设中,不仅重视一手资料的有针对性采集,而且注重采用网络数据库技术,以保证传统研究跟上数字化步伐。
中国的崛起是近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国际现象之一,如何在夯实研究的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建设成就,需要更为客观、科学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式层面调整研究视角,采用全球化思维,拓宽研究领域,把中国问题放置在全球框架下去认识研究,提出新的概念和观点是极为重要的;北美中国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时空范畴和研究视野,也带来了方法论的创新。基于量化数据进行扎实的实证研究,可以让智库研究更为纯粹,也更能为国际所接受,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探究新型智库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将会是智库研究面临的历久弥新的长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