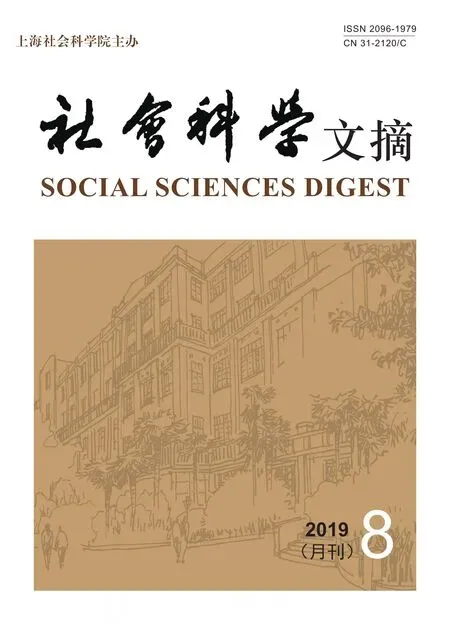莎士比亚的乌托邦
文/张沛
在世人眼中,莎士比亚并不是一个自觉或重要的乌托邦文学作家,虽然他曾与人合作撰写《托马斯·莫尔爵士》,后来还在《亨利八世》(1613)中通过剧中人之口称说莫尔的“博学”和“正直”,但他对后者的《乌托邦》(1516)似乎一无所知,至少是从来没有使用过“乌托邦”这个词。
尽管如此,作为“一切时代的诗人”,莎士比亚并未放弃对人类“乌托邦”理想的关注与探求:从最初的《亨利六世》(1589)到最后的《亨利八世》,“乌托邦”的主题音乐贯穿始终,事实上成为“莎士比亚诗教”(Shakespearean μουσική)——哈罗德·布鲁姆所谓“世俗宗教”和“(现代)人性的发明”——的一处关键。我们将在下文举证分析:这一主题意象或莎士比亚的乌托邦理想具有双重聚焦的两副面相,它们互为对照镜象并最终成为自身的空置反讽。
一
莎士比亚的第一个乌托邦,或者说莎士比亚乌托邦主义的第一副面相,是以完美王者为其人格代表的理想国家——在莎士比亚笔下,它往往就是英格兰。《理查二世》(Richard II, 1595)中国王的叔父冈特的约翰(剧中径直称为“冈特”)曾有一段著名的“英格兰颂”。这段“英格兰颂”向世人描绘了一个超时间-历史的神话国度或理想空间——其美好与虚幻程度,正与《亨利八世》终场时分克兰默大主教为婴儿伊丽莎白施洗祝福而预言的英格兰未来王道盛世交相辉映。然而,这只是一个“应然”的幻觉和假象。事实上,这个乌托邦随时面临着外来入侵(尽管冈特-莎士比亚的言辞成功地掩盖了这一点)和内里腐败的危险,而二者均与统治者的德性(virtus)密切相关。果不其然,我们马上听到冈特话锋一转,痛心疾首地悲叹这个“人间无上国土”被它的主人出卖而堕落了。
在冈特看来(这也是莎士比亚同时代人的观点),即便是国王也要服从法律——这是“国王的法律”,更是上帝的法律或自然法。上帝委托国王管理他的国家和人民,二者均为上帝的造物和产业(property);就此而言,国王并不是他的国家的主人,而只是它的暂时代管者,即上帝的助手或仆人。真正的(proper)王者应当强大而公正,否则即为“无能”或失德。在莎士比亚笔下,我们曾看到一份王者德性清单目录:
马尔康 可是我一点没有君主之德,什么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谦恭、诚敬、宽容、勇敢、刚强,我全没有;各种罪恶却应有尽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
莎士比亚以此向他的观众——其中即包括“今上”詹姆斯一世——婉而多讽地讲述了王者的正当德性(这德性同时构成了他的核心和首要“资产”),堪称西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君主教育文学传统(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与伊拉斯谟的《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即是其中代表)的回光返照。在更多时候,莎士比亚是以戏剧为镜,向我们展示了现实政治中王者德性的缺失和理想王者的反面。
二
例如亨利六世。作为莎士比亚笔下塑造的第一个王者,亨利六世天性善良而懦弱,用权臣约克公爵(即后来著名暴君理查三世的父亲)的话说即是一个“不配统治”而只配被统治的“假国王”。他悲叹人民苦难深重,但一筹莫展,甚至想入非非,在战场上出神羡慕乡村牧人无忧无虑、清闲自在的田园生活。国王的田园理想反证了理想国王和王国的破产,而理想王国的破产又反证了国王的失德。剧中人克利福德勋爵即指责亨利六世不能像国王一样统治。这一批评不仅适用于亨利六世本人,也适用于其他王者,如理查三世、理查二世、约翰、亨利四世乃至亨利五世和亨利八世等。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不够强大而软弱无能,有的人则过于强大而至于暴虐,有的人只是貌似公正,有的人则公然作恶。真正的王者或是已经远去,或是尚未到来,总之非今世之人。就此而言,“(应该/不能)像国王一样统治”这一批评既是通向乌托邦“盗梦空间”的秘密通道,也是解除乌托邦“太虚幻境”的灵验魔咒。在极端情形下,它甚至会变幻出乌托邦理想的他者镜象,或者说反乌托邦——《亨利六世》第二部中暴民领袖杰克·凯德的社会批判和政治理想即是如此。
杰克·凯德是莎士比亚创造的第一个“狂欢节式人物”——就其颠覆性和破坏力而言,也许还是最伟大的一个。不同于后来的理查三世、福斯塔夫、哈姆雷特和埃德蒙,杰克·凯德从不伪装和掩饰自己,而是公然叫嚣并直接运用暴力打倒、摧毁一切既定秩序和文明制度。他以“恢复古代自由”为号召,誓言改制新建一个没有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共享社会或大同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像他许诺宣传的那样美好——他的施政宣言只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或者说下流人性)狂欢想象的暗黑乌托邦。这个以利益-权利垄断——首先是性权利,然后是土地和人身的所有权——和欲望最大化(即个人专制,柏拉图所谓“欲望的僭政”)为标志的“乌托邦”不仅是乌托邦理想本身的异化堕落,更是现实政治的恶性发展。
杰克·凯德的美梦——对由大多数人构成的政治社会来说,它却是不折不扣的噩梦——最终梦断肯特郡乡绅亚历山大·艾顿(Alexander Iden)之手。一如其名(“Alexander”意为“人民的保卫者”即“王者”或“主人”,而“Iden”令人想起伊甸园[Eden]——人类的终极田园理想),亚历山大·艾顿代表了乌托邦理想的另一面相或另一种乌托邦理想,如其登场时在自家园中巡视散步所说:
我对于父亲留给我的这份小小的产业深感满意,我看它赛过一个王国。我并不想利用别人的衰落来使自己兴旺;我也不愿意钩心斗角来增加财富。
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之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亚历山大·艾顿作为它的所有者像神一样自足而自得地生活着。事实上,这也是莎士比亚笔下许多王者的梦想——例如亨利六世。再如哈姆雷特的“果壳”理想或李尔王的“囹圄”幻景。一如“黄金时代”或“伊甸园”,“果壳”和“囹圄”以隐喻的形式主题再现了人类对永恒宁静的原始-自然的本能向往(弗洛伊德所谓“死亡欲望”)。在莎士比亚笔下,这尤其表现为花园(Garden)和森林(Forest)——与宫廷和城市生活相对的自然生活或生命的自然状态——的意象,而正是它们构成了诗人的“第二乌托邦”。
三
西方文学中的第一个“花园”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8卷中“阿基琉斯之盾”上出现的那个葡萄园,其次是《奥德赛》中费埃克斯人国王阿尔基诺奥斯的“果园”。不过说到影响,则当首推基督教《旧约》即希伯来圣经《塔纳赫》(Tanakh)中的“伊甸园”。这里是人类始祖的故土乐园,也是人类童年的天堂记忆——后来成了他们永恒的梦想。冈特的英格兰-乐土、哈姆雷特的果壳-宇宙、亚历山大·艾顿的自家-花园均可作如是观。
不过也有不同。在莎士比亚笔下,“花园”往往也是“政治-国家-人类社会”的原型隐喻。《理查二世》第三幕第四场中约克公爵内府园丁的“花园论道”就是最经典的一例。即如园丁所说,治理国家一如修整园艺,需及时清除杂草并翦灭强梁,否则不免枯萎荒芜。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国花园强调整齐有序、规则对称的空间呈现和视觉效果,诸如按照几何图形栽种和修剪树木、根据编织纹样设计和布置花坛等造园技术皆在当时广为流行而深入人心。技术是思想或精神的体现:就16至17世纪英国园艺而言,这一精神即《理查二世》中园丁助手所说的“道理、规矩和尺度”,而《特洛伊洛斯和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 1602)中的尤利西斯又称之为“秩序”(order)或“等级”(degree)——他的发言极是冗长(当时他在向希腊联军首领阿伽门农进言分析作战失利原因),甚至出离了人物和剧情,但是很能说明问题。对观“园丁”和“尤利西斯”的发言,莎士比亚的花园-政治乌托邦于是不难想见。不同于亚历山大·艾顿的超政治或非政治“花园”理想,这是一个“前政治”的花园:它先于政治而使政治成为可能,并因此是“元政治的”:政治由此奠基并出发,而非被其否定或超越。所谓“超越”只是一种假象:它往往是逃避和退守,而且(除非足够天真或虚伪)难以保持——歌德笔下的人造瓶中小人(Homunculus)和黑格尔笔下执著空明境界的“优美灵魂”即为其传神写照,也预示了它的命运。
小土地所有者亚历山大·艾顿的“花园”正是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假面乌托邦。他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一个看似“万物皆备于我”“帝力于我何有”的世界中,却不知(或者是不愿承认)这一安宁自足其实源于“政治”——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它只能是强大和公正的王权统治——的赐予和庇护。现在,英国的王权统治或“政治”正处于全面崩溃的危险境地,而恶魔杰克·凯德已经潜入他的花园。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亚历山大·艾顿别无选择,不得不以暴抗暴与之生死相争;而当他拿起武器的那一刻,他便从洛克-卢梭的自然状态进入了霍布斯-黑格尔的自然状态。与之相应,他的花园乌托邦也在这一刻转向了自身的反面-真相——强大就是德性、力量裁决正义的现实政治,并从此(即便在他侥幸战胜敌人、因功受赏被封为骑士之后)不复存在。
四
艾顿的“花园”没落了。那么园丁和尤利西斯的“花园”呢?
中世纪人认为王国是国王的身体,而身体隶属于灵魂,故王者的灵魂状态决定了现实政治的品质。园丁-尤利西斯的“花园”是一个整肃有序的政治世界,它的管理者——或者说王国的“园丁”——必须具备强大公正(以及仁慈、慷慨等等)的灵魂资质或王者德性,所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幸的是,这样的灵魂或真正的王者在莎士比亚的世界中难得一见,甚至从未出现: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理查二世、约翰王、亨利四世之类固非其人,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凯撒、安东尼与克里阿佩特拉、屋大维等异族或异教王者也都各有性格缺陷(柏拉图所谓“灵魂的疾病”)。亨利五世看似无限接近这一理想,但他仍不是真正的王者:他治下的英格兰决非理想永恒的王道乐土,而只是建立在腐朽、罪恶和暴力基础上的昙花一现的“阿多尼斯花园”。
莎士比亚晚年与友人合作《亨利八世》,为证成完美王者-国家的乌托邦理想而发起最后一搏。在本剧中,亨利八世好生“修理了他的园地”并“翦除了一切多余的枝条”。的确,这位出色的园丁-国王战胜了一切对手——王后、贵族(白金汉公爵)、大臣和枢机主教(沃尔西),甚至是死亡:他留下了杰出的后裔,未来的伊丽莎白一世。终场时分,克兰默大主教满怀激情地预言了伊丽莎白及其继任者的光荣统治和英格兰的伟大前程。克兰默的预言和想象其实是作家、演员与观众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祈祷。在他们异代同时、咫尺天涯的回顾、想象和祈祷中,“完美王者”“理想国家”和“花园乐土”的意象合而为一,而莎士比亚的乌托邦一瞬间“证得金身”——但也只是一瞬间而已。亨利八世接下来的回答显然代表了莎士比亚本人的真实想法:“你的话很玄妙。”以这种反讽自嘲的方式,诗人否定了他最后残存的乌托邦幻想。他深知这只是一个幻象,而且是一个正在或已经变得过时和可笑的幻象;同时他也深知(并且告诉了我们)现实中的英国更像哈姆雷特眼中的丹麦——在这里人们不得不忍受“强徒的横行和法律的怠惰”,或是李尔所见的不列颠——在这里人们饥寒交迫并流离失所,再或是《约翰王》中庶子理查和《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的渔夫看到的人类世界——一个人欲横流、弱肉强食的市场和丛林世界。
失望之余,莎士比亚将目光转向了森林。这是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世界,也是他最后的乌托邦精神家园。《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1599)中流亡阿登森林的长公爵即为这一生活理想的绝佳代言。与出于愤世嫉俗而隐居山林的泰门不同,他看来是由衷地喜爱山林生活:在阿登森林,他与他的“同伴和弟兄们”组成了一个在野的社会和流动的城邦,共享法外的自由和回归单纯自然-天性的幸福。这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和人类自然王国,但它作为某种“想象的异域”或“异域的想象”却是不自然的甚至是反自然的。
首先,这是个单一性别的世界,确切说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它的基础和动力是兄弟之爱(这也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和法国大革命的核心主张之一)而非一般认为的“爱欲”或男女之情;事实上异性之间的爱欲(以及由此而来的婚姻和家庭)将导致这个男性乌托邦——事实上也是一切男性乌托邦——的解体。莎士比亚的另一部喜剧《爱的徒劳》即写意地证明了这一点:纳瓦尔国王费迪南与三名近臣成立宫廷学园,相约三年之内潜心学术不近女色;不久法兰西公主携三名侍女来访,他们一见钟情而迅速毁约。恋情败露后,当事人之一的俾隆为爱欲申辩并为大家解嘲——这番话似乎也是莎士比亚本人的心声流露。由此看来,正是莎士比亚自己预先反驳了他后来寄情于阿登森林和兄弟之爱的乌托邦幻想。
更有甚者,这个人性得到自由释放的绿林世界或自然乌托邦也是一个人类对自然施加暴力的道德-政治灰色地带。长公爵和他的“同伴和弟兄们”——一群“快乐的男人”——在此过着“昔日英国罗宾汉那样的生活”,但他们的生活就其大端而言无非是抢劫和捕猎,而它们都属于暴力行为:前者是向人类施加暴力,后者是向自然生灵施加暴力。对于前者,剧中虽然没有明言,但是“罗宾汉”已经暗示了答案——后来年轻的奥兰多就曾在阿登森林试行打劫,幸而未成。对于后者,莎士比亚通过剧中人杰奎斯之口提出了激烈的指控。长公爵为自己的杀戮感到愧疚,但也就是说说而已:毕竟,基督教文化中并无“不杀生”的观念(摩西十诫中的“不可杀生”仅指不可杀人),甚至鼓励杀生,例如耶和华不仅随意毁灭自己的造物(在他眼中,人类大概也是一种动物),更为人类规定了诸多杀人的法律;古人(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或者相信“灵魂流转”(因此众生平等)而反对杀生的认识和实践,但这不过是空谷足音,且早已成为绝响。杰奎斯的批判就不同了:在他看来,人类是自然的暴君和杀手,或者说人类文明-社会——包括一切人类乌托邦,如阿登森林这样的世外桃源——本身就是反自然的暴政统治。
在这里,莎士比亚越过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底线,触探到了人类道德-政治-文明——其终端形式为乌托邦主义——的幽暗根基和非正义起源。这是一个洪荒虚无的领域,而莎士比亚也许是第一个来到这里并宣布自己发现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