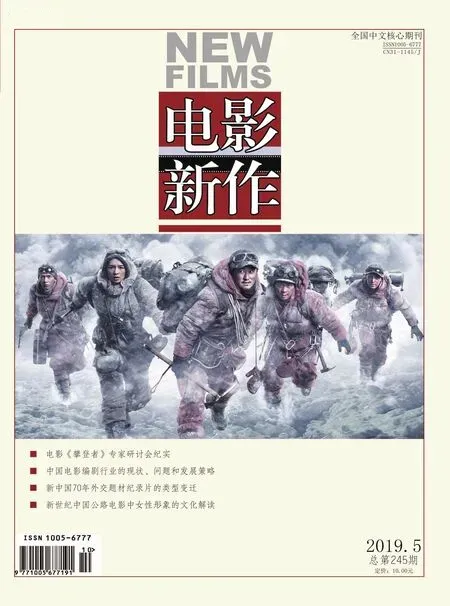新世纪中国公路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
耿小博 常一亮
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公路电影的起点和短暂的辉煌时期。在全球性反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公路电影从初生之始就具有反叛性和批判性。而女性为维护自身权益的女权运动也包含在60年代的反文化浪潮中,相应的,其公路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必然有着强烈的反叛性。
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公路电影也浮出历史的地表。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公路电影在数量上已小有规模,类型化日趋成熟,并带有浓郁的本土特色。其中女性形象在新类型的本土化改写中,并未效仿西方公路电影的批判精神,而从初生之始就夹带着旧有价值的历史包袱。即它所追求的自由和希望为男性的自由和希望,而其中对女性的表达仍是男性中心主义下的新瓶装旧酒。
在本土公路类型中,女性面临种种困境,她们被假想为先天的弱者,处于不利的阶级地位和封闭空间。她们的作用多是辅助男性,她们的话语被弃置,女性些许的对抗行为注定失败且被污名化。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形成,和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公路电影中的女性而言,她们首先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境。
一、女性遭遇的现实困境
1.将女性想象为先天弱者
波伏娃认为:“女性并非天生,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在中国公路电影的表述中,女性分别被男性从身体、能力、道德等三个主要层面假想为先天弱者。
首先,将女性认定为身体上的弱者。电影中出现动作戏份,女性会习惯性地缺席,或者借助其他男性力量来完成与男性的对抗。比如在《心花路放》中由马苏饰演的角色在被主人公羞辱之后,最终是借助另一伙男性力量去完成对抗。《无人区》中最后大段落的动作戏份,完全是发生在男性之间的对决。女性全程处于一种躲闪状态,在男性的庇护之下逃离身体对抗,绝不会像武侠电影中会出现身怀绝技的女侠形象,或如动作片中有女性武打动作的设计等。对于女性先天身体的偏见,夸大了男女之间的身体差距,使得道路上绝少有“女性骑士”形象的显影。
其次,能力上弱者的假定。如果说女性在身体构造上存在某些生物意义上弱者的成分,农业文明中女性劳动力不可避免处于某种力量上的弱势,那么在后工业时代,人类依靠思维能力形成生产力的境况下,对女性的弱者假定更像是一种男权偏见,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下强加于女性的他者、边缘身份标签,其折射出的是男性的完美形象。即便是处于较高阶层的女性精英,都无可避免地面临男性的“傲慢与偏见”。《心花路放》中康小雨在修理淋浴头时的手足无措,所指正是公众想象中此类工作非女性所长。宝马女司机开车时令人哭笑不得的张皇失措,也和男性视阈下对于女司机的偏见联系在了一起。
最后,对女性在道德上的弱者指涉。公路电影中,男性往往来自于北上广等一线中心城市,以文明的、现代的姿态在自己的“伟大征程”中遇到各式女性。女性却多身处于三四线城市、县城和乡镇,成为愚昧、落后、不具备现代文明价值观的所指。于是,男性拯救那些空间上处于边缘地带、道德上处于劣势的女性群体成为中国公路电影最常见的主题。比如《后会无期》中苏米用仙人跳诈骗钱财,而江河却既往不咎,并在功成名就后接纳了苏米。相反,对于男性则绝少使用这样的影像指涉。
2.底层的阶级定位
出于对女性的弱者假想,女性的阶级地位也等而下之。在中国公路电影的影片序列中,它以一种男性意识形态的腹语术,天然地将女性多局限于花样繁多的服务业,诸如空姐(《非诚勿扰》)、高速收费员(《心花路放》)、舞蹈演员(《心花路放》)、理发师(《心花路放》)、大巴乘务员(《人在囧途》)、宾馆前台(《人在囧途》)、杂货店员(《无人区》)、群演(《后会无期》)、护士(《飞越老人院》)。仅有的几个“异类”或者缺席(《泰囧》中高博妻子),或者对其职业一笔带过(《心花路放》中康小雨)。而男性职业则是另一个维度:如音乐人(《心花路放》)、制片人(《心花路放》)、企业家(《人在囧途》)、公司高层(《泰囧》)、高材生(《转山》)、律师(《无人区》),即便是在片头职业较为平常的男性,在片尾都会改换门庭,如《人在囧途》中牛耿从工人变老板,《后会无期》中江河从普通地理教师变成知名作家。单纯以性别修辞粗暴地制造了两性间的阶级鸿沟和权利坐落,处于低阶级的女性面临被既有话语结构的局面,她们又身不由己,被禁锢于一种封闭空间之内。
3.封闭空间下的“娜拉”
巴赞认为:“电影的全部就是关于如何在空间放置人物身躯。”身体空间在电影叙事中承担重要的表意功能,人物所处空间暗蕴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坐标。作为权利话语的博弈结果,中国公路电影中的男性往往处于无限延伸的开放空间中,在浮士德式永远征服的伟大旅程中实现梦想。而女性则多为封闭空间下囚禁的娜拉,封闭空间也规训着她们的主体精神,她们默默承受苦难,等待萎靡、堕落、死亡和男性的拯救。在女性逼仄的空间映衬下,男性开阔的场域才更富有意义。而讽刺的是,当人们选择相信所有苦难的悲剧性在于它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而非自我慰藉时,所谓的“历史进步”只是将女性复位回到核心家庭,女性还是轮回于两个封闭空间禁锢的悖论中。开放空间永远只是男性传奇演绎的舞台。如《后会无期》的男主角所遭遇的几位女性,都处于固定的生活空间中,绝少参与到男性旅途当中,安于“天命”,这里所谓“天”实际上的指征即男性,影片最后,天/男性会选择符合规则的女性将其迎回核心家庭,成为对女性“顺从”男性意志的褒奖。
鲁迅认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②铁屋子成为鲁迅对于前现代文化的空间想象,距今已逾百年。可在中国公路电影中,绝少有苏醒的女性,大多数女性仍安居于铁屋子当中,更无几人合力将铁屋子摧毁的可能。继而失去了和男性在空间上对等的机会,她们的更多的社会形象是担当男性的辅助者。
二、女性的辅助形象
1.物质辅助
中国公路电影叙事的绝对主体是男性,主线是男性追求梦想、赢回自我救赎的传奇寓言,女性悄然失落于自我陈述之外。她们多作为男性追求梦想的辅助者出现于银幕之上。慈爱母亲、贤良妻子、乖巧的女儿等传统的形象成为她们的银幕标签。而当男性以骑士般的洒脱恣意于道路之上时,作为辅助者的女性更多担负起男性的衣食住行之责。如在《落叶归根》中宋丹丹所饰演的卖血女人,其所指正是古老寓言中大地母亲形象,通过卖血、捡破烂的方式供养儿子。她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以奉献和牺牲,成全男性的生命价值。再比如《转山》当中,张书豪数次从女性手中接过食物。对比之下可发现,当男性给予女性食物时,多代表一种权利,如《圣经》中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成为一项神迹。而反之女性的给予被剥夺了象征意义,以日常化的影像呈现,如同一件稀松平常的琐事,不值一提。
当面临男性更大的索取时,女性则要作出更痛切的牺牲。比如《人在囧途》,当男权社会的运行机制出现漏洞时,女画家以神女般的献身精神,苦苦支撑一群孩子的生活。最后,女性的辅助换取了男性的注目礼,也豁免了男权社会运行失灵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电影中的男权漏洞必然是以局部的、可消弭的、无伤大雅的形式出现,最终仍会被卡里斯玛所解决。它绝不同于昔日共工怒触不周山而女娲补天式的天崩地裂,因为这样的男权失责是无法赦免的。相应的,女性的辅助形象所换取的认同也是有限度的。可能仅是获取了女性观众自我感动下掬一把同情之泪,并内化为女性的道德自省和自我期许,成为女性误读自我的常见路径,间接导致女性成为一种“非女性的女性”。
2.男性神迹凝视者
按福柯的说法,凝视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压迫,一个类似于监督的凝视,就会让人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这样的凝视多用于被压迫者。反之,女性对男性的凝视则多是一种服从和赞美。男性达成梦想时,会召唤女性的肯定目光装衬男性的威仪。如《飞越老人院》中,男性选择集体出走,并安排了李老太和女院长两位女性陪同,目睹男性的伟大征程。女院长虽在开场试图阻止男性,但最后选择屈服、跟随、亲历男性奇迹。似乎即便是男性到达生命的衰老期,他们仍然可以完成对于正当盛年的女性的询唤和驯服。而此时,男性虽处于被看的地位,但女性所凝视的是男性传奇,完全迥异于女性的肉体被看或道德沦丧。男性/女性、正确/错误、精神/肉体的二元对立,女性以反对、妥协、认同、凝视等一系列动作的转变再次确证了男性权威的无可辩驳。
同时,通过女性的凝视、服从构建男性的话语网络并将之合法化,从而确立男性中心地位在法理层面的权威。
3.核心家庭成员
20世纪60年代的公路电影中,曾经出现解构传统核心家庭的创作潮流。但在80年代后,世界范围内的公路电影创作放弃了波西米亚式的漂泊,回到了奥德赛式的回家母题。在西方宗教体系中,夏娃是上帝从亚当身上取出的肋骨而成,找到夏娃则意味着亚当的完整。中国公路电影作为舶来品的本土化改写,对应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从初始之起就恪守历经险阻(前现代中国的创伤性体验),终要回家(现代中国核心家庭的美好想象)的寓言式母题和模式。和西方宗教有相通之处,找到肋骨、组建家庭成为男性征途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女性的重要的社会角色就是辅助男性组建家庭,达成她的“肋骨”使命,营造童话故事般“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结局。
之后,一方面女性是漂亮的,她是摆放家中精致的“玩偶”。另一方面女性是勤劳的,是完美的“佣人”。即便男性逾矩之后,如出轨、不承担家庭事务等等,“肋骨”仍会痴情等待,与之达成和解。这样的逻辑理路正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想象下对女性的分工。《人在囧途》的李成功包养小三,久不归家,而妻子却毫无怨言,安心料理家事。而当李成功一时改观后,妻子又既往不咎,以一句“回家就好”宽宥了男性过错,以家庭伦理的宏大理念混淆了实际的道德和法律问题。这样压抑、孱弱甚至畸形的女性形象,不仅是男性想象下的镜中之花,更是历史幽灵的回溯,“绑架”女性为历史的人质。《泰囧》的徐朗在片尾未有任何实际行动的前提下,就获得了妻女的谅解。妻子的妥协、委曲求全反而成为一种女性应有的品德得到褒扬,女性因为主动退让而重新维持住核心家庭,一种弃车保帅的“明智”策略反而使得女性更深陷入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旋涡。
4.心理疗愈者
电影中,女性之于男性的心理疗愈由来已久,影像以女性的春雨润物般的温柔,细腻化解男性创伤。但这种疗愈实质上是在男性占有女性的身体或者精神之后的反躬自省,而并非“孱弱”的女性本身为疗愈者。如果女性有这样神奇的力量,则意味着她们可以和男性在某种情况下对等,这是卡里斯玛无可接受的。换言之,如男性无法占有女性的精神或者肉体,抑或没有男性自己的醒悟,那么女性哪怕为心理学家也无济于事。比如《心花路放》中,宝马女对耿浩好言抚慰,且当其以鸡蛋清帮耿浩缓解淤青时,动作暧昧充满性/身体占有的暗示,使得耿浩几乎要走出阴影重新面对生活,可当耿浩发现宝马女是同性恋时,意味着他无法占据这个女人的身体和精神空间,自然也无法达成疗愈。而片尾又安排了一位女性,暗示观众耿浩会完成对这位女性的占有,象征他彻底疗愈内心,赢得新生。所以,所谓女性的疗愈是一种镜像,实质上还是男性的自我疗愈。
奉献身体,成为女性疗愈男性心理的常见路径。男权社会里的女性是男性欲望的客体,满足男性的性本能成为女性的重要功能。中国公路电影娴熟地将女性身体处于福柯式圆形监狱的窥视之下被观众、男性演员、摄影机无条件观看。本就叙事而言,有的女性甚至可以隐而不见。出于满足男性与“梦中情人”接触的考量,她们才换得出镜机会。如《泰囧》片尾出场的某位女星,以真实身份和假想的小人物王宝亲密互动,换取了将自我与王宝混淆的、真正的“小人物”——观众的与女明星亲密接触的幻想。当下观影中,男性已经被鼓励且毫不掩饰对于女性的窥淫快感。相反,女性始终不直观男性身体,女性的欲望被悬置,不看成为“正经”女性的道德自觉。影像中,很少见到男性身体色情化抑或女性主动凝视男性身体。而当女性主动凝视男性时,往往另有原因。如《转山》中藏族妇女主动凝视男性的画面,与其说流露女性的主体意识,不如说是在汉族视阈下对于少数民族女性的想象。
上述几类女性的辅助形象,并非涵盖全部。女性往往会集齐多种辅助形象于一身。而形象的变化、纠缠多源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身兼多职”且“不堪其重”加剧了女性对自我的茫然困顿。而在其他类型电影中,女性形象更加多元。如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开场台词是“我爱你,但与你无关”。那么形成公路类型的相对单一的女性想象的原因何在?
影像书写离不开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必然代入其所处的社会场域。正如福柯所说,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从历史的纵向坐标出发,2001年起,中国公路电影初露峥嵘。其后影片上映的时间如《落叶归根》(2007)、《非诚勿扰》(2008)、《人在囧途》(2010)、《转山》(2011)、《泰囧》(2012)、《飞越老人院》(2012)、《无人区》(2013)、《心花路放》(2014)、《后会无期》(2014)正对应着新千年后中国社会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和男权秩序重建的时期。公路、汽车等现代媒介“飞入寻常百姓家”,孕育了公路电影的物质基础。现代中国正在由“前现代中国的延续体”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男权历史结构、男性中心主义在由男性主导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辉煌成就下巩固、确立。同时,男性群体在过往集体主义、封闭环境下的压抑的个人情绪需要释放,现实中交通的便利使得他们通过远离现代城市文明、生活秩序,驶向想象的非秩序成为生活常态。因此,借由表征为自由的公路类型实现男性追求新的生命体验的命题自然形成。一言蔽之,公路类型并未像其他类型片经历过男权的动荡时期。它一初始的重要目的就是在稳定的男权背景下,在强大卡里斯玛提供的现实物质支持下,宣泄男性的欲望,并惯性以女性为筹码。正如福柯所担心的,所谓文明的进步带来了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广泛的规训。而这种规训自然是施加于包括女性在内的被压迫群体。
在繁华的社会图景下,潜藏着对于女性的隐秘压迫,它的隐秘并非其所藏甚深而不可察觉,而是一种社会结构下的熟视无睹。这种社会结构既是文明的现代性缺失,更是一场男性历史加之于女性的诡计。
另外,中国社会本身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历史的惰性中的男权意识,持续消融着女性的主体意识,无视、遮蔽女性的生存现实,使之继续演绎客体、他者、辅助者等形象。退而言之,对于年轻的公路类型而言,即便提出在其中重建女性主体形象,也会因为缺乏历史的参照物而一时无从下手,这些社会历史景观,都显影出当下中国公路电影中女性生存状况的底色。
三、新女性的抗争
有学者认为:“女性在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规范与编码过程中充当了合作者和同谋者的角色”。③此类严厉的批评话语促使一部分女性以自省代替“自戕”,重新反思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形成了对抗男性的新女性形象。何谓“新女性”?从字面意义上看来,“新女性”应该具备某种现代性的特征。“现代”的对应词是“过去”,“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分界”④。如何鉴定新女性并无统一标准,但主动对抗男权束缚、追求自我等无疑是重要的标准。世界范围内,对于女性的权利讨论已蔚然间颇有气象。西方电影在西方两次女权运动的现实图景影响下,出现了很多主动抗争的女性形象。但中国公路电影中,女性自我尝试、改变命运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并成为被戏谑的对象。这些新女性的尝试可谓未生先死,成为男权历史壁垒下的一阕绝响,新女性的失败结局进一步确证了女性的“难堪大用”,她们的主动逃脱反而成为一种必然的落网,辅助者进一步成为她们最好的身份标志。
1.失败的突围者
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史并非是前现代史的一种延续,而是一种断裂的历史。在中国公路电影中,反抗的女性成为一种历史的断层,面临无可逃避的失败。如《心花路放》中的康小雨,在经历感情失败之后,她试图以独立女性的姿态重新生活,她主动追求爱情,可拨通的却是一个被丑化的男性的电话。她独自一人上路旅行,经历各种不如意。道路在影片中实际上所指是一种主流外的秩序,它为主人公的反叛行径提供合理想象空间,可在这里它并不属于女性。挫败之后,康小雨重又返回城市所代表的主流秩序中。影片结尾,当一位男性开车来接康小雨后,观众意识到康小雨找到了“幸福”。回归男权比起之前对抗男权而言,更为明智和现实,这也是康小雨在女性旅程的受挫生命经验中得出的“真谛”。对女性种种的主动出击、逾制的银幕书写无非是一场男权威严的“欲擒故纵”,通过对于女性冲击男权的失败案例,映射出男权的正统和坚不可摧。
而同样在《心花路放》中,两位男主人公在和马苏饰演的角色发生冲突后,马苏借由另一伙男性力量来惩戒男主角,可郝义拿出象征菲勒斯的枪支将一众丑类吓走,拥有菲勒斯的男性可以支配女性和缺少菲勒斯的男性的内涵,也即刻昭然若揭。
同时,在男性旅途中遇到女性的对抗时,女性还会被指为非道义,并受到惩戒。比如《无人区》中黑店老板娘的人物设计。在法外之地的无人区,她敢于戏弄男性,男性权威的设定却是无处不在,这也因此导致她招来了杀身大祸。
这三类女性敢于对抗男性的情境前提不同,但结果都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男性电影,中国公路电影中男性女性在数量上的视觉对比也是悬殊的。女性几乎寂然隐形于观众视阈之外,“寡不敌众”也是女性必然失败的缘由之一。女性对于男性的反抗基本处于孤立无援、单打独斗中去对抗男性的集合,一个女性经常要面对多个男性,如《后会无期》中的周沫一人独自应对三个男性童年玩伴。她极力维护自己童年时大姐姐的尊严,却难以掩饰实际生活的落魄和作为“第二性别”的挫败感。而少有的女性集合对抗男性的案例多将女性置于负面形象,例如非道德的形象,女性的集体对抗反而成为一种群体指责。《落叶归根》中,当劫匪代表的男性侠义精神保护了老赵后,转而便对同车的女性发难,充当刁蛮市井之流。当女性背叛了传统中国的侠义精神,她们又如何取代男性,成为中国重新融入现代世界秩序的力量所在呢?
2.对女性的道义指责
女性在对抗失败后,还要面临来自男性的精神指责或道义惩戒。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中,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迷恋于追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成功学,而成功者凤毛麟角,男性则不可避免的遭受追求各种权利所遇到的挫折。一旦男性失去某种权利,比如失去了对于女性的掌控权利,造成男性的焦虑和挫败,女性则需要面临道德审判,被指责背弃了她“应当”的辅助者形象,遭受荡妇羞辱或者拜金指责云云。
这样的故事模式已成套路,如女性在男性将踏上征途时将之抛弃,使得男性在影片初始就跌入更深的人生谷底,和影片最后完成重生形成人物弧光,成为男性人物的光环。影片《转山》中,张书豪刚经历兄长逝世,为男性之间的兄弟情谊而决定上路,女友便提出分手,试图破坏男性间的和谐关系,这样的行为,使得她只能在银幕上彻底缺席,而张则以一次身体和精神的自我历练完成了重生。重生既得到了新的、非血缘的男性兄弟,又得到了女性的注视。又如《落叶归根》中,胡军所饰演的卡车司机,以仗义、阳刚等正面形象示人,而相应的,对他造成伤害的女性则被直接指骂为骚货。通过对女性的道德指责,完成男性的豁免和觉醒。而在《心花路放》中,耿浩妻子选择离婚的原因则被指为拜金而站在非道德的立场上,而耿浩最后选择为前妻出头而大打出手,又使得男性拥有了宽容、重情义的道德褒扬。正如结构主义所认为的,意义只有通过二元对立才能确认。这些影像通过男性/女性、道德/非道德、在场/缺席的多重表述再一次美化男性,相应的贬低女性。面对只有成为男性规训下道德楷模的女性才能立足于男权社会,否则将面临男性社会的抛弃和惩戒的现实景观,使得女性观众形成男性意识形态下的关于道德认知的集体无意识。
结语
中国是世界上女性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公路和现代交通工具本是追求自由的象征物和媒介。遗憾的是,面对历史的“无物之阵”,中国公路电影出现的在路上的女性形象,这些“被困的娜拉们”在男权社会结构下难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以走出玩偶之家、完成女性意识的断剑重铸。女性形象仅仅是一个物理学意义的存在,而在其他意义上视为未完成和不可见。且当我们在讨论女性主义的同时,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仍然难以从历史的深渊中赢回自己的身份。女性如鲁迅所说的“历史的中间物”夹在后现代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裂隙中,进退维谷、左右失据。戴锦华说:“女性的社会与文化地位正经历着悲剧式的坠落过程。中国的历史进步将在女性地位的倒退过程中完成。一种公然的压抑与倒退,或许将伴随着一次更为自觉、深刻的女性反抗而到来。”公路电影中的女性是否会在铁房子里沉睡,而决然叫不醒?还是会醒来,借助群体的力量试图冲破围笼,找回自己的历史主体和文化叙述呢?毫无疑问,女性将面临一个关键的历史选择。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