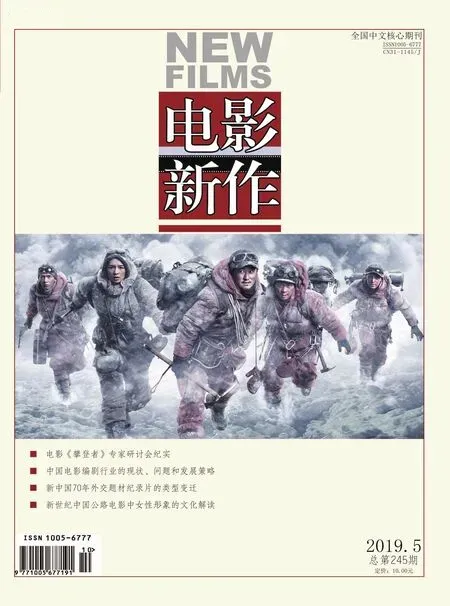《开天辟地》创作谈
汪天云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我参与影片《开天辟地》的创作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年夏天,我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师范大学当老师,受邀去嘉兴,给浙江创作评论协会举办的讲习班做演讲。讲完课后,一群人赴船宴,在船上聊天时,大家就谈起,世界上有很多的政党,但没有一个政党是在船上诞生的。当时程卫东、黄亚洲,还有其他十几个人都说建党这件事写个电影,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行,我就提出可以写一个国民党追捕共产党建党名单的惊险片。结果没多久,那天的创作热情就被落实下来了。黄亚洲到上海来找我,我们两人在上海开始策划,写出了一个详细的提纲,相当于是一个初稿,然后拿着这个初稿去找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文学部的主任是杨时文和孟森辉,他们还没看,首先是让编辑祝洪生看。祝洪生当时说:“这两个年轻人倒是蛮有意思的,要写共产党诞生这个从来没有人敢写的题材。”剧本就留下了。最初,电影的名字叫《开天辟地大事变》,于本正说,“大事变”就不要了,就叫《开天辟地》,气派大。这个片子的诞生,真要感谢他,还有吴贻弓。
党史浩如烟海,人物众多,我们当时写了78个有名有姓的人。上影文学部领导们跟我们商量,到底是以史携人还是以人托史。讨论来讨论去,写过来写过去,我跟黄亚洲两个人就在这个文学部的小楼里一稿一稿地改,改得昏天黑地、胃吐酸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还是要以人来托史。因为写这个过程,可以写很多情节,但是关键还是刻画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三位党的创始人怎么把握主次详略。当时从北大的角度来讲,陈独秀是教授,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毛泽东是书记员。也有人说,把李大钊放第一位,因为李大钊是烈士,毛泽东是领袖,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最后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同志,她拍的板。她用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她说:“我们还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这样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那么按照这个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来统领全片写作就是结合以后的历史的状态,这三个人是有坚定信念的。所以我们就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关系最后定位,主要的笔墨集中在陈独秀,然后是李大钊,之后是毛泽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个旁白就成为这个戏的主心骨。
当然还有其他人,因为这里面有13位党的代表,我们是用例推的办法来写他们早年的性格行为的。这个经验后来也用到了《邓小平1928》,小平同志能力挽狂澜坚持改革开放,来源于他早年的革命理想,也可谓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创作实践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才被共识的方法论。它既是尊重事实,又是要写出历史人物在以后的世纪风云当中的表现倾向。
我们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小细节和大情节的相互关系。大事件是不可以随便去改变的,比如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时代风云,包括从上海的石库门转移到嘉兴南湖的船上。但是小细节我们是可以创造的,最典型的就是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因为这两个孩子后来实际上都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和烈士。但是陈独秀对他们很严酷,晚上让他们勤工俭学拉大锯,但是他又很爱自己的孩子。最后我们就创造了陈独秀捧一锅茶叶蛋去看孩子,这个情节其实来源于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补习英语,晚上放学饿了,就买一点茶叶蛋吃。
还有所谓“大手笔”就是陈独秀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穿着白西装就跑到上海大世界去撒传单,然后被人家抓住,但他很有个性,人家打了他一记耳光,他打还对方一记耳光,以牙还牙。他也很欣赏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在湖南宣传革命的过程中创办的那些传单、海报、宣传品,认为他是个大手笔。这些实际上都是史料上找不到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它是有画面感的,是有感染力的,是有激情的。还有就是第一次让毛泽东下跪,就当时这一点,我跟黄亚洲商量了很长时间,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要这样写。起因是毛泽东去找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当时杨昌济是伦理学的教授,他对毛泽东是有一定保留的,但是他又很纠结女儿的感情,毛泽东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人,所以毛泽东最后在求婚的那一夜是跪下了,希望杨昌济同意把女儿嫁给他。这里面写出了他们两人的情感,毛泽东的那种内心的执著和人生的浪漫。
我们写《开天辟地》那年,市委宣传部搭了四套班子来做这个选题。祝洪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不断地把其他的情况也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做成。当时导演其实已经选定是李歇浦,但李歇浦自己也拿不准到底是用哪个本子更好。要感谢的是张骏祥先生,他是李歇浦的老师,他对李歇浦说:“这几个本子我都知道,你们不用他们大学里出来的用哪个?他们比较严谨地按照党史一件件一桩桩来编写。完全按照浪漫主义随心所欲去写建党恐怕不行。”李歇浦也就此拿定了主意。
我觉得这个本子的诞生真不是我们两个人能够写的,是有很多的前辈、领导、艺术家给了我们帮助,给了我们指点,给了我们力量。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李歇浦是非常有创意的导演,在挑选演员的问题上也很严格,这部电影里面大概有50多个演员,都是对照真实的历史照片去找的。那年冬天,我们在松江中外电影研讨会上看片子,是内部片。制片主任柴益新跑来说,“唉,你们太舒服了,两个人天马行空地写,我们拍得累死累活,你们也来体会体会。”就把我找去了,让我演其中一个角色。他说邵力子这个人物跟你很像,也是大学教授。随后他拿着邵力子的照片,叫了沈东生和殷丽华来给我化妆。邵力子的脑门很大,然后就按照他的照片把我的头发拔掉,眉毛拔掉,拔得像了,他才点头。拔了两天,我第三天就受不了了,幸亏只有两句台词,也就过去了。正是这次表演,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电影表演艺术家。特别是邵宏来,邵宏来是青岛话剧团的演员,他演陈独秀,他对这个人物的研究非常全面,所有陈独秀的文稿、书信、照片,所有的史料细节他都掌握得很清楚。还有孙继堂,他的内在个性跟李大钊很像,比较内敛,演得非常棒。
当时为了找能够演年轻时代毛泽东的演员,几乎找遍了全国。因为1921年的毛泽东很年轻,古月想演,但年龄确实大了。后来摄制组就根据我们写的毛泽东,找了杭州红旗越剧团的一个演员叫王霙。这个人现在已经是演毛泽东的专业户了,因为他和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气质很接近,就是人矮了一点。后来党史办的人说毛泽东是在长征路上长高的。还有一个难题,根据剧本找来找去,找不到能演邓小平的演员。最后是在某一个大学的食堂里看到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过来一问,是广西的。与此同时,也找到了一批能演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共产党优秀骨干的年轻人。佟瑞欣就在那会儿被选上了。
所以这个戏的所有的人物造型,其实功劳是属于导演部门。因为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史料有限,但是我们总觉得那个年代的人,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气质,那种勇敢、坚定、智慧、激情是很可贵的。
当时我觉得这部片子的诞生是非常了不起的,得益于当时国家电影局的领导、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给我们的指示,也感谢老一辈的艺术家,像张骏祥先生,以及当时上影厂的领导,吴贻弓、于本正,还有李歇浦、沈妙荣、杨乃如、朱永德、柴益新、胡立德。现在回过头看看,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他们为我们的主旋律,他们为我们建党的电影,为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这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真是默默地做出了很多贡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后来《开天辟地》就成为这一类主旋律电影的一个标杆,或者说是一个样式,这种样式就被很多电影所吸取。然后我们就有了一种信心,一种信念,或者说有了一种经验,就说敢于这样去写,领袖人物也是真实的人,源于生活可以高于生活,领袖人物可以用他们当年的风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准去写。所以现在,我们描写这一类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越来越感人。
就当时来说,去写建党题材是很难的,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年轻;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得到了老一辈的支持;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这部电影诞生的时候,正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坦途;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上影厂许多艺术家的支持。他们的那种态度是上影厂的传承,上影厂70年留下的,不仅是一批作品,还有上影厂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这部电影我记得当时只花了900多万,拍得是极其的认真,及其的负责。所有的道具、服饰、化妆,所有的烟火、灯光,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上影厂的精华。包括作曲、旁白各方面。所以这部电影后来在各地方放映的时候都受到了高度的赞誉,而且每年7月1日这部电影都会在电视里重播。我觉得做这样一部电影其实对我来说是锻炼,是教育,也是提升,要感谢上影厂,这个已经有70年历史的艺术单位。这个单位给了我们智慧、力量、勇气和收获。在我们以后的日子里,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作品。到上影厂来工作以后,我还和李歇浦一起创作了《邓小平1928》、傅东育导演拍了《西藏天空》,当然还有现在的《攀登者》,所以这种精神一直没有断,这种精神一直在延续,不管我们现在电影更市场化了,或者说更强调它的三性统一了,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的这种严肃认真,还是有这样的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延续。只有这样,我们的电影才能够真正对得起我们的历史,对得起我们的观众,也能对得起我们的后人和未来。
创作《开天辟地》是我一生中不可忘却的艺术历程,也是上影厂70年历程中永远鼓舞我们奋进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