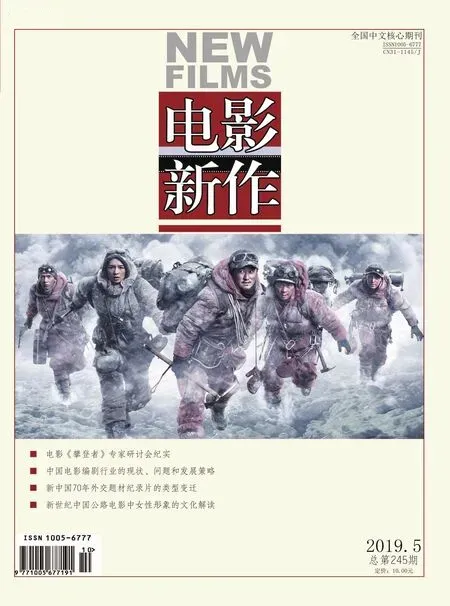早期中美电影关系研究的跨文化概观
王玉良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空前繁荣,逐步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霸主地位。尽管当时好莱坞的影片发行商认为,欧洲才是他们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但他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获取利润的角落,更何况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东方大国。由于1949年之前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上的突出地位,使当时和后来的电影史学家在撰述中国电影史时,从未忽略过有关中美电影的比较论述。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史书写肇始,到当下对中国电影史“重写”的热议,涉及早期中美电影关系方面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总的来看,这些关系研究大致集中在中美电影关系的产业研究、中美电影关系的意识形态研究和中美电影关系的文化研究几个方面。
一、市场性参照:中美电影关系的产业研究
据资料显示,美国影片在一战前后对中国市场的输入出现了快速的递增,“从1913年的189,740英尺(包括已摄制的胶片和没有曝光的原胶片)增加到1919年的1,529,876英尺”,增长了八倍多。这些数字充分说明,美国电影一战后开始大批量地涌入中国。由于当时中国独立的本土电影业还没有形成,虽然有张石川、郑正秋筹组的新民影片公司,黎民伟、黎北海兄弟组建的华美影片公司创作了一些作品,但他们所依托的主要还是美国电影商的资本或技术条件,所出品的影片毕竟势单力薄,远不能满足当时中国电影市场的放映需求。
整个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电影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电影人在欧风美雨中接受了洗礼,开始致力于发展本土电影事业。在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出,表面上看,似乎开始了蓬勃的发展,而事实上这种发展却越来越向着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演进。虽然制片公司为数众多,但能够真正制作影片的公司却相当有限,市场上放映的大多仍旧是美国影片。这一时期美国影片的发行,主要是通过一些外国商人和中国的买办代理,如当时在上海已有“奥迪安娱乐公司”和“潘买(PUMA CO.)公司”两家专门代理发行美片的公司,负责经营派拉蒙、联美、米高梅等公司的影片发行,孔雀影片公司专营雷电华公司的影片。1926年8月,“八大公司”之一的环球影片公司首先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发行公司,此后几年,其他七家公司也相继在上海纷纷设立了各自的“驻中国总公司”。好莱坞电影发行网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不但巩固了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市场地位,也增强了它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发行和放映的联合行动,更为美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强劲动力,影院业的争夺战也愈演愈烈。
在早期的中国电影史述著作中,随处都可以找到一些关于美国电影在华市场影响的相关论述。像程树仁主编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就有关“外人经营之影片公司”“外人所制作之中国影片”“外人所经营之影戏院公司”“国外之各影戏院之调查”“购买国外演映权者”等内容的讨论;谷剑尘的《中国电影发达史》(1934),有关“英美烟草公司托拉斯政策的开端与灭落”的论述;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936),从外商投资国产片和影院事业切入,具体详尽地描述了欧美电影对“土著电影(中国电影)”的影响等。早期的这些研究,大多从制片、放映及影响角度对美国电影在当时中国的市场表现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为早期中美电影关系的建构树立起了市场学的概观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电影史书写,从市场学角度来看,大多还是延续了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观念思路,把美国电影视为一种西方殖民者的全球市场扩张行为。饶曙光教授所著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虽然以介绍中国电影为主,但始终也把美国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坐标系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维度。该书从市场学角度切入,涉及诸多美国电影方面的内容,诸如“外国人垄断下的影院业及外国影片的输入”“大后方的电影放映及其好莱坞景观”“好莱坞电影的输入及其对中国电影的意义”“清除好莱坞电影运动及其影响”等,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电影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影响。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付永春的博士论文《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的产业回应:跨国视阈中的史学建构(1923-1937)》,把关注的重点投向了彼时好莱坞电影产业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方面。本文通过一种跨文化比较的方法,阐述了1923-1937年间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电影产业的互动关系。作者把这一时期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初步形成巧妙嫁接,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当时中国电影产业史的理解,而且对好莱坞具体的影响做出了有力的实证说明。论文首先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好莱坞有声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反思了中美电影在技术领域的跨国交流。其次是说明了中国电影对好莱坞发行体制的“杂化”(Hybridization)模仿,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发行体制从“鹦鹉学舌”(Parrot)到“破茧成蝶”(Butterfly)的转化过程。接下来以联华公司为例,分析了彼时中国电影的制作模式,总结了“中国特色”的资本运作特征。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分析探讨,作者最后得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对好莱坞回应的结论是“在竞争中发展”(Growth though Competition)。充分认识到电影作为一种产业,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制作、发行层面,最能体现一种跨国性(Transnational)的交流。
对早期中国电影史进行书写和研究时,中美电影的产业关系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所以,付永春博士从当时中国电影的发展切入,敏感地注意到了它对好莱坞在产业模式上的效仿和影响关系。由于当时好莱坞电影在声音技术、表演体系、生产预算和商业宣传等方面的较早成熟,无疑会对当时正处于发轫期的中国电影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把中国电影史的研究置于国际框架之中,通过共时性的跨文化比较和分析,这种研究方法体现了电影研究的开放性特征,无疑对当下重写中国电影史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路。
此外,罗卡和澳洲学者法兰宾,通过调查研究和资料证明,为早期中美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新鲜的市场学史料,也为中国电影史的重写开拓了更加宽泛的研究空间。蔡春芳的硕士论文《战后上海电影市场的中外博弈(1945-1949)》、汪朝光的《战后上海美国电影市场研究》等,也都从早期中美电影关系的产业研究诸多角度,对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做出跨文化方面的有益尝试。这些研究的共性之处在于,通过一种市场性参照,把电影的产业研究纳入到了早期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框架中,为早期中美电影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观点。
二、主体性建构:中美电影关系的意识形态研究
对于早期中美电影关系研究,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电影的“主体性”建构。“特别是在当下,中国电影研究已经成为海内外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更是需要检视和反思中国电影、华语电影与跨国电影中的难题与问题,通过跟西方电影文化观念和欧美电影理论所构筑的话语权利进行对话与商讨,在全球化语境里重建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研究,在很大层面上与电影的意识形态有很多的关联性。在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把“卖国的‘中美商约’和美国影片的倾入”放在一起进行批判,就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部“官修电影史”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
当然西方的电影史书写同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有一些外国学者对早期中美电影的交往投向了关注的目光,通过一种异质的视点,分析了某些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早在1963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就出版了由美国学者陶乐赛·琼斯(Dorothy B. Jones)著的《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一书。虽然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主要是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用的,但它无意中为我们梳理了1960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表现中国题材时所体现的典型特征。作者通过由大及小的结构方式,通过个案研究和详实的史料分析,从“美国电影和世界市场”到“美国电影与亚洲市场”,进而论述到“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并详细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本书的编辑虽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客观上为研究早期中美电影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成了较早探讨中美电影交互方面的代表著作。
朱迪·希法(Jordi Xifra)的《公共关系视阈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与纪录片电影的对话》一文,探讨了卡普拉这部重要作品在创作上对战争纪录电影的影响,以及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所涉及的中国内容,并把此片视为当时国际军事关系的重要助推力量。这些研究成果,把政治题材电影纳入到了一种跨文化的视阈之中,从政治与意识形态维度中找到了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历史坐标,也为当下此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找到了一定的样本参照。电影史学家陈力(Jay Layda)的《电影:一份关于中国电影与电影观众的报告》一书记录了1896-1967年间电影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详述了与电影有关的社会生活和人文风貌;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学者里克·屈尔(Rick Jewell),指出好莱坞电影“在叙事上依赖的仅仅是美国公众对外国文化和国民性的狭隘的成见”。并通过分析“派拉蒙”和“米高梅”公司在表现中国人形象时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态度,揭示了电影创作和行政干预间的密切关系。
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早期电影与好莱坞的相互关系”方面探讨的成果,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真正把两者放在特定视阈下进行详细论述的专著,迄今为止,也只有秦喜清的《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1920-1930)》一部。虽然她把“欧美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比照对象,但在实际论述中,涉及的文本却主要还是美国电影,所以其核心内容是在探讨中国早期电影与美国电影的关系。该书把对中国电影的研究划定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一种国际视野的史述方式,提出了“民族认同”的概念,并把它作为贯穿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主体性建构”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主题的统领下,本书突破了以往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孤立考察,用跨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了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的相互关系。在中国电影的萌芽阶段,由于“欧美电影的放映给中国观众带来了民族认同焦虑”,因此“如何从内在层面建构起中国电影的民族身份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的最核心问题”。整体看来,本书在主题定位上迎合了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认同”这一热门话语,但在寻求民族身份的过程中,难免陷入了一种中/西、自我/他者这种二元对立的尴尬境地。本书较早地探讨了早期中国电影与欧美电影的关系问题,但在表述中却显出了一种明显的失衡状态,为了建构中国电影的“主体性”,欧美电影在这里只充当了中国电影话语言说的一种陪衬。对欧美电影的探讨,仅限于相关文本的分析和一些历史事件的综述,而对它们在中国的发行、宣传,乃至与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等方面并没有做出探讨,但这些内容与“民族认同”这一主题却不无关系。仅从几个公司的案例分析来建构“民族认同”这一宏大主题,难免会显得势单力薄。但本书能跳出传统电影史以国别为划分的孤立写作模式,通过一种比较的方法重新认识早期中国电影史,实属难能可贵。
张江彩的博士论文《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视野宽广、立论宏大,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一百多年来好莱坞在中国的文化传播史。虽然这些论述视角特异,但最终又回到了秦喜清所追寻的那种“文化认同”和民族电影“主体性”这些中西文化比较时易于重复的立论观点上。叶宇的博士论文《1930年代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以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状况、美国好莱坞类型片在中国的放映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因为1930年之后,随着新兴电影运动的勃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反帝反侵略的创作倾向,擅长展现歌舞升平和梦幻天堂内容的好莱坞电影,便成了那些左翼文人重点的批判对象。当时“上海各大报的电影专刊,如《申报》《时报》《晨报》《大公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基本上都掌握在左翼手中,以一种有组织、有理论的方式,发起对美国电影的批评”。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成立了电影检查委员会,实行全国统一的电影检查制度,电检会对外国影片的检查尤为严密,不时有美国影片被告知删减或禁演。虽然“从1932到1937年间,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第一次遭遇如此明晰,而又如此大规模的抵抗”。
此外,还有汪朝光的《建国初停映美国影片纪实》、饶曙光与邵奇的《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运动:清除好莱坞电影》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境遇呈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影评者对美国产片的道德和政治批评,一方面是电影人实际上对美国产片的艺术模仿。”传统的中国电影史书写,常常给美国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打上了“文化殖民”的标签,这不仅掩盖了它对中国电影的积极作用,也阻断了两国电影交往方面的正常对话。可以说,没有美国电影,1950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在发展道路上可能要摸索更长的时间。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艺术层面,美国电影的影响意义深远。对早期中美电影关系的研究,既要避免“民族主义”的干扰,也要摆脱“文化帝国主义”的纠缠,用更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建构中国电影的“主体性”。
三、现代性述说:中美电影关系的文化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早期中美电影比较方面的研究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像胡克、李道新、汪朝光、张伟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美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在电影消费、观众接受、在华境遇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详细的探讨,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著述。这些著述大多从文化研究角度切入,以单一民族国家的电影讨论为主。相较国内学者,在早期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群体中,涌现了一批关注中美电影文化交流的华人学者和外国学者,他们因为特殊的“跨文化”身份,往往对中美电影的关系问题比较敏感,并形成了特定的学派风格。像曲春景提出的“感官文化学派”,通过对李欧梵、孙绍谊、张真、张英进、马宁等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学者研究特征的深入分析,发现了他们对上海早期电影的研究体现出了一个显著特征,即“探讨上海早期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关系,考察和寻找好莱坞在全球化进程中对上海早期电影的正负面影响”。这批学者,通过一种现代性述说,从不同角度分析了1950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和历史走向,为早期中美电影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思路。
以早期的上海电影研究为例,上海的城市特征和文化氛围,为美国电影提供了比较合适的传播土壤,也把上海人“摩登时尚”的精神诉求与美国电影“现代性”的影像符码完美地缝合在一起了。正如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所指出的,经典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扩张,最主要是“由于这些电影为美国国内外的大众观众提供了一个现代化及现代性体验的感知反应场(sensory reflexive horizon)”。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的概念,把早期中国默片与日常生活经验联系起来,解释电影作为“集体感官机制”的外在表征。美国电影往往把上海作为它的叙事空间,来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猎奇心理。上海作为当时的国际化都市,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的前沿阵地,这形成了上海观众独特的审美心理,他们对美国电影的热衷促成了当时时尚文化的兴盛,在电影研究方面形成了一种“现代性”论说。
这些中外学者在早期中美电影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要么倾向于在城市研究、文化研究和由“白话现代主义”引领下,对电影及观众在社会文化领域里相互关系的考察;要么就是通过对早期中美电影跨文化交流的概貌分析,来凸显中国电影的“民族认同”和“主体性建构”,而真正对早期中美电影跨文化交互方面的实证研究和具体表现,则显得相对的欠缺。致使我们考察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电影的互动与影响时,许多仍停留在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对美国电影带有鲜明意识形态倾向的价值评判,及其对《上海电影志》中战后中美电影资料和数据的引用层面,少见一些有突破性的论著成果。虽然有个别论文对早期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文化关系做了简单的梳理,但这些成果往往流于景观式的介绍,缺乏对这一问题系统深刻的钻研。涉及早期中美电影文化交互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专著面世,大多散见于个别的专题论文,描摹了这一时期中美电影跨文化交往的简单态势。
事实上,对“早期中美电影关系研究”在实际操作中也是困难重重,这首先因为1949年之前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相互纠缠,导致了这一时期美国电影在输入和市场放映方面时起时落,各方面不稳定的因素加大了这一论题研究的难度。其次是史料方面,有关早期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发行、宣传乃至放映方面完整、系统、连贯的原始资料几乎没有,只能从现存的部分官方档案和大量散见于报刊、杂志中的宣传内容上寻觅踪迹。只有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搜集、甄选和梳理,才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线索。这虽然是一件费时耗力的苦差事,但却是历史研究的必走之路。随着资讯平台的日益丰富和传媒手段的更加便利,它们对早期电影史料的挖掘起到了极大助推作用,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相关成果不断浮出地表,为我们了解早期中美电影关系的跨文化交互提供更加深入的认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