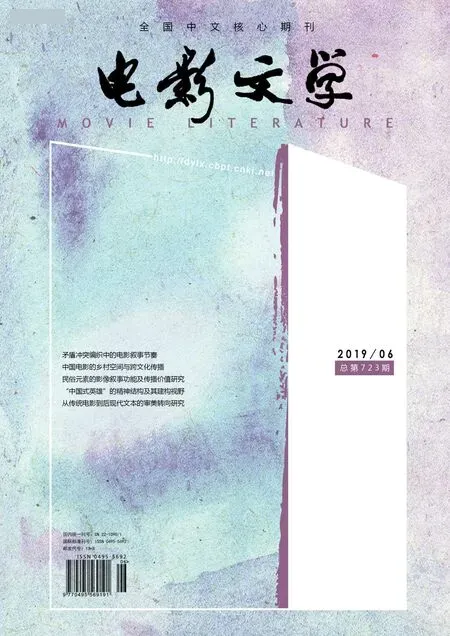父权的式微与放逐
——论是枝裕和家庭母题电影中的父亲形象
崔国琪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笔触从容、细腻,颇具人道主义情怀,他着意描摹日本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记录家庭中成员的琐碎生活,并以此为切口,剖析日本社会潜藏的深层问题,观照根植于大环境下的民众价值观。回望是枝裕和自1995年始,近23年的创作历程,他的成长、创作都浸润在日本进入近代产业社会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多方面变革历史时期。日本社会的主流家庭制度发生着深刻、渐进的变化,封建“家族制”的影响正在历史的进程中日渐式微,而近代家庭制度——核心家庭,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渗透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家庭制度。伴随着家庭制度的改变,家庭中成员功能、伦理关系也在缓慢地解构、嬗变、重建中。而在这当中,家庭中父亲的权责之流变就显得尤为典型。
统观是枝裕和的电影创作历程,他对家庭母题的青睐可见一斑,而其影片中的父亲形象也呈流变之势,具有探讨价值。2004年,是枝裕和首次涉足现代家庭母题剧情长片,拍摄了以真实社会事件为蓝本改编的《无人知晓》。影片中,是枝裕和以一个由单亲母亲和四个孩子组成的“残缺家庭”为载体,反思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衍生的贫穷、弃儿、虐童等社会议题。2008年,是枝裕和再次涉足家庭母题,拍摄了影片《步履不停》,《步履不停》的诞生缘起于是枝裕和母亲的去世,怀着“没能为母亲做些什么”[1]而悔恨不已的是枝裕和,将自身成长阶段对父亲、母亲的情感投射到了《步履不停》的人物塑造中。同时,影片也塑造了极具代表性的日本传统父亲形象——横山恭平。2011年,是枝裕和应日本铁路集团之邀,为纪念九州新干线全线通车,拍摄了继《无人知晓》后第二部以儿童为主角的剧情长片《奇迹》,这篇“命题作文”的母题仍是现代家庭,其中,“没出息的男人”——由小田切让饰演的木南健次这一“废柴父亲”形象——成为是枝裕和电影中众多此类男性形象的典型。2013年到2016年间,是枝裕和接连拍摄了探讨亲子话题的《如父如子》《比海更深》《海街日记》,他在电影中思考和追问:“联系自己和孩子之间的是‘血缘’,还是‘时间’?”至2018年,他的电影《小偷家族》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殊荣,是枝裕和逐渐确立了以家庭母题为主的电影取材风格,在是枝裕和的家庭母题电影中,既有从头至尾缺失于家庭结构中的“消失的父亲”,也有固执古板、试图维护父权权威的传统“严父”,而在《如父如子》《小偷家族》等影片中,是枝裕和塑造了跳脱传统父亲形象窠臼,摘掉“父权”帽子,回归“父爱为上”的父亲形象。笔者将对是枝裕和执导的家庭母题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做以上三类归类,从电影文本出发,结合社会学理论,管窥是枝裕和镜头下父权的式微与放逐,并以此观照日本社会现实。
一、消失的父亲
2004年,是枝裕和以发生在1988年的“西巢鸭弃婴事件”为蓝本,拍摄了儿童题材影片《无人知晓》。这是一部以儿童为主角的电影,成人形象仅作为配角在影片中出现:影片中,除了逃避现实、遗弃子女的母亲惠子这一形象外,家庭中“消失的父亲”也令人难以忽视。出租车司机男A和游戏厅工作人员男B先后在影片中出现,他们仅仅作为孩子生命的制造者——“生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孩子们也不曾希冀这样的“父亲”能成为家庭的抚养者。他们是出生即被父亲遗弃,后又被母亲无视的孩子,在生存的夹缝中艰难地挣扎着。
《无人知晓》的拍摄缘起于是枝裕和少年时代偶然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则社会新闻,彼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1973年石油危机后经济由高速发展转由停滞衰退的特殊历史时期,再加之日本社会自12世纪后,家庭中的男性,即丈夫(同时承担父亲角色),一直处于生产劳动和创造财富的绝对统治地位。一个家庭中,“丈夫作为 ‘前方战士’ 在企业全力拼搏, 妻子作为 ‘后方卫士’ 在家庭倾情持家”。[2]在这样的家庭成员功能划分下,不难想象,一个缺失了父亲的家庭,母亲和子女失去了全部的经济收入来源,几乎毫无保障基本生活物质需求的能力。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忽视造就了《无人知晓》的悲剧,而“消失的父亲”无疑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如此缺位的父亲还存在于电影《海街日记》(2015)中,《海街日记》中的父亲虽出场即去世,但影片剧情的架构、情节的推进、人物的塑造都与其息息相关,因而,作为“幕后人物”(1)“幕后人物”意为被剧作家以暗场方式处理 ,以幕后为其活动空间的那些不出场人物。的父亲在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电影开场,香田家三姐妹在饭桌上谈论着父亲的死讯,仿佛说着毫无干系的他人的故事。父亲十五年前和情人出走,留下了无依无靠的三姐妹,“父亲”二字对于她们来说,代表着背叛、抛弃、痛苦。大姐幸始终无法释怀,起初甚至拒绝参加父亲的葬礼,小妹妹千佳甚至对父亲没有多少记忆,同父异母的妹妹浅野玲的到来,才为她带来了关于父亲的些许回忆。四季流转,“父亲”的缺失给这一家人造成的痛苦回忆不紧不慢地在镜头中缓慢显现,但正如《无人知晓》中野草一般生长的四个孩子一样,香田家的姐妹们也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完成了与父亲的告别,影片结尾,幸和玲站在曾和父亲一起到过的山腰,喊出“爸爸是个笨蛋”,消失的父亲带来的伤痛被消解在如画展开的帧帧生活日记中。
二、式微的父权
除了彻底的缺位与出走,是枝裕和镜头中的父亲形象更多地表现为父权光环的暗淡与失落。“父权制”(patriarchy)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父权制”从广义上讲,是指以父亲权力为中心的一种社会关系体制,从狭义上,它的原则是双重的: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支配及年长男性对年少晚辈的统治支配[3]。父权家长制是东方国家封建社会共有的家族制度,其在日本传统家庭中表现尤为突出[4]。
在影片《奇迹》(2009)、《比海更深》(2015)中,小田切让饰演的父亲木南健次、阿部宽饰演的父亲筱田良多都是父权失语的典型。《奇迹》中,父亲木南健次在有了两个孩子后仍不切实际地一心追求音乐梦想,在家庭中,他更像一个“巨婴”,而不是父亲。不堪忍受的妻子选择了和他离婚,和妻子一同离开的大儿子航一不止一次嘱咐随父亲生活的弟弟龙之介:“以后爸爸就交给你了。”在鹿儿岛开往福冈的新干线“燕”和福冈开往鹿儿岛的“樱”号短暂交会的“奇迹时刻”,弟弟为爸爸许下了一个愿望:“我希望爸爸总是能写出新歌。”这既是孩子对父亲的美好祝愿,也流露出本该“强大”的父亲却如此微小的哀伤与无奈。
《比海更深》(2016)中,筱田良多的父亲形象与父权绝缘也借由儿子真吾的口中说出。电影中,日本老牌影星阿部宽饰演的良多是一名私家侦探,早年他以作家出道,怎奈处女作之后就再无值得称道的作品。他沉迷于赌博,经济窘迫,对他失望透顶的妻子执意离婚。儿子真吾也对他颇为冷淡,奶奶问真吾:“你不想成为爸爸那样的人吗?”真吾点头:“嗯,妈妈就是因为讨厌爸爸才和他分开的。”再反观良多作为儿子的一面,他随意翻看父亲的灵位、打探父亲的遗物中“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拿去典当,已逝的父亲“父权”也荡然无存。
与家庭中男性父权失语所共生的,近20年来,日本家庭的婚姻关系也进入了战后以来最大的动荡期,在婚姻破裂的家庭中,70%的离婚由女性主动提出,这一点在《奇迹》《比海更深》中皆有体现。女性由于家中男性的“无能”,对婚姻关系不满,继而选择离婚。反观此类家庭内部,女性承担了原本社会默认由男性承担的家庭责任,因而权力结构的天平开始向女性倾斜,女性形象也由此表现得更为强势、更具话语权,父权的式微与女性地位的提升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这,无一不是由家庭中男性角色定位变更而产生的连锁反应。
从“消失的父亲”到父权式微的父亲,2008年,是枝裕和在电影《步履不停》中将父亲的形象进一步深化,起用日本老牌影星原田芳雄,塑造了一个为维护父权而挣扎的父亲形象——横山恭平。横山恭平是日本父权家长制中“严父”形象的缩影,他敬业、古板,与不愿意“子承父业”的次子良多矛盾重重。反观儿女对他的态度,良多看着有心而无力的父亲目送邻居被推上救护车,那眼神已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惜,而非对父亲威严的敬畏。电影后半段,母亲让良多在CD机上放起那首《蓝色灯光横滨》的一场戏,父亲在浴缸里听到一门之隔的母亲淡淡地说出“我背着良多一路上去那个女人的公寓,我能听见你的声音,在她的房间里唱歌”,他早年婚内出轨的不齿行为被点破,至此,父亲于妻子、于孩子的父权,都呼啦啦如大厦将倾,溃散之势不可逆转。
《步履不停》为观众塑造了一个极典型的日本传统父亲形象,管中窥豹,其背后蕴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程度急遽升高的个中隐患。现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恰是经历了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代“拼命三郎”,当一代日本男性从职场退休,回归家庭,他们一方面在生活上极度依赖妻子,一方面对子女的教育、关爱匮乏,因而在家中显得累赘、多余,被妻子和孩子称为 “大件垃圾”[2]。是枝裕和导演本人的父亲,便是这样一位不被家人认可,不与家人情感相亲的男性。在2018年上海电影节一条视频与是枝裕和的对谈中,他这样形容电影中男性形象与自己父亲的关系:“我电影中的男人,都没什么出息,因为我父亲就是个这样的人。他经历过战争,还去西伯利亚劳改了好几年,终于才回到日本,但内心苦闷,终日沉迷酒精和赌博。我的母亲从小是被宠大的,她对一无是处的父亲一直都很冷淡,直到死前,还说他们的婚姻是一场错误。”
电影《步履不停》的结尾,阿部宽的旁白响起:“爸爸死了,我没有和他看过一场足球赛。”父权失落的父亲与儿子在生命逝去后达成和解,是枝裕和也借由镜头完成了自己与父亲的告别:“我与父亲之间本来很有距离感,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深入交谈。他的去世让我深刻感到生命的柔弱。清理我们的老房子时,重新发现了许多记忆,我意识到,即使在他死后,我仍能继续发展和生长我们之间的关系。”
三、父权出走 父爱回归
2009年,是枝裕和的女儿出生,“眼看太太一下子转变成了母亲,我作为父亲,却还没完全进入角色”的是枝裕和开始思索“一个父亲到底什么时候才算真正成为父亲”。[5]带着这样的疑惑,是枝裕和先后拍摄了电影《如父如子》(2013)、《小偷家族》(2018)。在这两部家庭母题电影中,是枝裕和探讨了深刻的伦理话题:家的基石到底是什么?是“生”成就了“父”,还是“养”成就了“父”?“家人”也可以自己选择吗?电影《如父如子》《小偷家族》所塑造的生父与“养父”形象,更从深层次描摹了现代家庭形态中父权的出走与放逐。
《如父如子》中,是枝裕和将“父权式父亲”与“父爱式父亲”放置在了对立面。福山雅治饰演的父亲野野宫良多在大公司担任要职,事业心极强,他把对自己的高标准要求投射到了儿子庆多身上;而由中川雅也饰演的斋木雄大则完全是个反例,他“能明天做的事今天绝不做”,但作为父亲,他陪孩子玩、给孩子修玩具、和孩子一起洗澡,与良多截然相反。面对良多的不屑,他说出了那句“父亲也是无人能替代的工作吧”,这宣言许也是为人父的是枝裕和个人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思索。
随着剧情的推进,良多所信奉的父权在亲生儿子琉晴身上呈崩塌之势,面对琉晴的良多遭遇到了父权溃散的危机。他发现他一直引以为傲的“严父”做派琉晴并不“感冒”,相反,他离家出走,试图逃离良多的家,回到“慈父”雄大身边,而抚养了6年的庆多也与他心生罅隙,因他的冷酷而失望无比。影片中良多父亲的形象虽出场不多,却有力地解释了良多的心境:他冷酷又严厉,与儿子的感情十分淡漠,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良多,成年后无意识地将父亲的做法反射到自己的儿子身上。但经历着“换子风波”的良多也在完成自身父权意识的转变,他开始意识到金钱之外,陪伴的重要。影片结尾,被庆多纯洁而温暖的爱意所触动的良多与妻子绿驱车赶往雄大的家,与庆多和解的他也完成了自身父亲观念的蜕变:放逐父权,追逐父爱。
其实,良多与雄大的角色之差异,从根本上讲,是对传统父权意识追逐抑或放逐的区别。《步履不停》中的横山恭平、《如父如子》中的野野宫良多,他们恪守对父权制社会的生存法则,希冀以自身对事业的追求来实现在家庭中的地位巩固,另一方面又因缺席于家人的日常生活,与妻子、儿女萌生罅隙而陷入父权失语的挣扎中。而《奇迹》中的木南健次、《比海更深》中的筱田良多、《如父如子》中的斋木雄大等“没出息的父亲”,从初为人父始,便表现出对父权意识的放逐,他们既无意追逐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也志不在在家庭中树立父亲权威,成为“有权之父”。
在新作《小偷家族》中,中川雅也饰演的柴田治的“父亲”形象与斋木雄大相一致,他一方面将是枝裕和惯用的“没出息的男人”人物设定发挥到了极致(影片中的阿治是一名小偷);另一方面,却在偷东西时偶然带走的孩子祥太身上,流露出为人父的慈爱和羁绊。影片中,面对警察的诘问:“你让孩子偷东西,内心不会感到不安吗?”阿治的那句“我也没有其他什么能教给他们的了”令观众的内心深受震动。是枝裕和借由“小偷家族”提出了一个深刻的伦理问题:家人可以选择吗?柴田治与祥太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合法的收养程序,他们之间从法律上讲并不成立父子关系,但从事实层面,却是不折不扣的父与子。对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柴田治来说,“父”的意义无关“父权”,甚至连“家庭”都是奢侈品,“父”的意义萌生于内心最深处的“父性”,这种“父性”,交由时间来成全,而非血缘。它自然地表现为对家人的物质支持和生活关爱,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小偷爸爸”,却拥有从心而生的至真“父性”,谁又能说这份真情不是父爱呢?
四、结 语
金棕榈、金狮、亚洲电影大奖等多项国际、日本国内的重量级奖项加身,正值壮年的是枝裕和无疑正处在他个人电影创作生涯的高峰期,因其电影往往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索,西方影评界称其为新日本电影新浪潮中“思想最为严肃的导演”。回望他的创作历程,自1995年至今,是枝裕和的电影宇宙浸润于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变中,在这个历史阶段里,日本社会逐步建立了以近代家庭制度而非传统家族制为主体的主流家庭形态,与之相对应的,传统的家庭意识也正缓慢朝个人化倾向发展。是枝裕和的电影镜头如一架显微镜,以管窥蠡测之态,描摹出日本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原生家庭的背离与羁绊,而其电影中的父亲形象,除了客观时代背景的熏陶外,还加入了是枝裕和个人私语化的情感表达,因而倍显真诚、动人。在文集《有如走路的速度》一书中,是枝裕和谈到其个人的创作观:“我不喜欢主人公克服弱点,守护家人并拯救世界这样的情节,更想描述没有英雄,只有平凡人生活的,有点肮脏的世界忽然变得美好的瞬间。”也许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创作原则,是枝裕和才得以以其四两拨千斤的有力笔触,书写出一系列有辨识度、有思辨层次、有探讨价值的父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