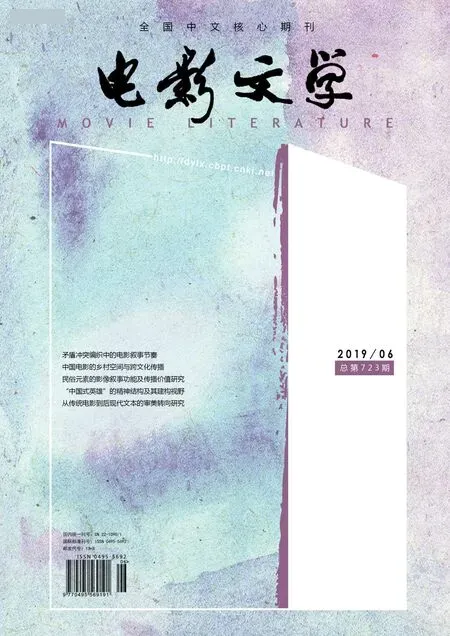再次成为被男权俯视的女权符号
——对电影作品《厕所英雄》的反思
贺思齐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印度电影引进热潮。1月至5月分别上映了《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巴霍巴利王2:终结》四部影片,6月《厕所英雄》又登陆中国院线。《厕所英雄》是由什里·那拉扬·辛执导,阿克谢·库玛尔、布米·佩德卡尔主演的喜剧电影。在印度本土,《厕所英雄》上映两周,票房就超过了百亿卢比(约人民币10亿元),总票房达到200亿卢比(人民币20.59亿元)。[1]由此足见《厕所英雄》受欢迎程度之热烈、观影人数之巨大。引入国内后,根据MtimePro(时光网)票房数据显示《厕所英雄》初战告捷,以60万优势登顶周六冠军宝座,最终内地总票房成绩为9456万元。
该影片主要讲述新娘贾耶嫁给丈夫凯沙夫后,因为家中没有厕所而出现婚姻危机,在丈夫不懈努力和斗争下,最终改变社会陋习、建成厕所并掀起一场女性厕所革命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而言,电影中的“如厕”问题很陌生甚至很荒诞,因为“如厕”在中国不成问题,但在印度却是个关乎个人卫生甚至是女性安全的大问题。在印度传统宗教文化中,厕所被认为是不洁之物,在家修建厕所会遭到神灵的谴责,所以男性毫无廉耻地露天“方便”,将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而女性只能在每日清晨成群结队前往野外,把握一天仅有一次的机会解决生理问题,即使不幸遇到性骚扰甚至是强奸等性暴力也只能忍气吞声。《厕所英雄》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具有特殊“厕所文化”下的印度,由此揭示出“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思想和根深蒂固的传统陋习给女性带来的迫害,导演通过调侃、戏谑的方式将社会问题剧的严肃内核包裹上喜剧化和荒诞化的糖衣。
电影围绕“给妻子建厕所”的情节展开,丈夫心疼妻子绞尽脑汁、奇招频出,最后不惜对抗社会思想观念和宗教文化。在女性难以被尊重的印度,丈夫因为爱而为妻子据理力争,因为爱而为印度女性争取权利,其中的艰辛困苦可想而知。因此,电影被各大主流媒体、甚至是中国片方的宣发冠上了“女性主义”“女权”“平权”等头衔。中国新闻网、北京日报转载报道《厕所英雄:小小的厕所,大大的女权》、腾讯网撰文《厕所英雄:上厕所也是女权问题?》,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以“女权”为题的高频转发也使得该片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但《厕所英雄》真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吗?《厕所英雄》对当代中国电影业又有什么启发性意义?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诚然,在我国进口的印度电影中,女性主义已成为热门元素,从《摔跤吧!爸爸》到《神秘巨星》以及《印度合伙人》都高举女权旗帜。《厕所英雄》的海报上赫然写着“一部改变6亿印度女性命运的影片”,被打上了女性主义的烙印。但实际上,从影片叙事结构的内部构成和女性人物形象两方面分析,这部影片并不能称之为女性主义电影,其展现的是一个披着女权外衣的男性世界。
本文认为,女性主义电影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反映女性特有的需求与愿望、强调女性“主体性”的获得、无性别差异的平权思想。女性主义电影也应当兼具瓦解电影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以及追求真正意义上和女性“灵魂和精神”的对话。
一、“观看”的男性与“被凝视”的女性
由于女性长期处于被男权文化控制与压抑的地位,投射于反映社会成规和社会文化的电影中,男权文化的意识形态隐性影响着电影叙述语言的表达方式。
美国早期女性主义理论家尼克·布朗曾写道:“对于有一类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出发点是下述两个推断:其一,大多数美国影片是由男人和为男人拍摄的,而女人则成了一种景观;其二,从叙事的角度讲,美国影片多将男性表现为主动者,而把女性打发到配角位置上。”[2]简而论之,在男权主导的电影中女性被置于从属和被动地位。虽然该理论是针对美国好莱坞电影体系的批评,但对包括《厕所英雄》在内的多类电影也有其理论批评价值。
从影片内容来看,女性主义要求女性摆脱男性中心文化下的“他者”地位,拒绝父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规定性角色扮演,因此本片应该重点讲述女性从“他者”到“解构”的过程,着力于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但实际上,本片反抗的主体力量并不来源于女性自身,而是来自男性,即愿意为爱情对抗世界的“白马王子”凯沙夫。通过译名得以略知一二,本片的中文译名为《厕所英雄》,纵观全局,厕所英雄应指丈夫凯沙夫,而不是妻子贾耶,因为丈夫凯沙夫占据了修建厕所的主导力量和电影叙事的核心地位,妻子贾耶通常被挤压到影片的边缘叙事地位。因此妻子贾耶没有完全摆脱女性的他者地位,而作为男性主体性的客体存在,反而是丈夫凯沙夫作为男性代言人,他掌握事物发展的控制权。例如,凯沙夫拒绝逃避问题、克服重重阻力,在自己家中修建厕所,电影用了21分钟表现凯沙夫向村委会提议、找当地卫生政府咨询、搜集资料准备诉讼、自己出资在家中修建厕所等情节,但妻子在21分钟的镜头内只出现过五次,且都以数秒的短镜头作为丈夫的支持者身份出现,叙事内容大体为在自己家中通过通信设备了解丈夫的情况。妻子足不出户的停滞行动线和丈夫四处奔走的前进行动线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女性在电影故事的行动中处于辅助性地位,而不同于男性的关键性乃至决策性作用,隐含女性通过无意识依附于男性而实现其目的价值观。即便在男、女主人公相识相恋的爱情叙事中,两人虽在叙事时间比例上平分秋色,但故事叙述的亮点或者说观众的记忆点却集中于哥哥凯沙夫、弟弟纳鲁和贾耶叔公卡卡这几位男性角色。换言之,观众对男性角色的观看有效地隐去了对女性角色的观看。对于观者而言,女性无物可看,无物好看,而男性却则十分“有戏”,间接将女性边缘化、男性中心化。
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曾在《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一书中写道:在一个两性关系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中,看的快感是呈分裂状态的,“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经过父权文化的影响,男性转化为观看的主体,期望通过“色情的观看”满足其观看快感,而女性则作为被动的观看对象,沦为满足男性“视淫”快感的客体。
在电影《厕所英雄》中,女性被编排为具有性暗示和性视觉冲击力的符号编码,成为男性欲望客体的表现对象。倡导男女自由平等的叔公却迷恋当红女星的身体,在家庭的公共空间内不顾及亲人的排斥观看带有性色彩的表演,且数次以性为话题同其他男性交流,以获得男性之间的认同感、满足对他人的性需求窥探欲。观众通过“认同机制”,模拟了以叔公为视点的观看。叔公和观众带有欲望地“看”,将女性的身体物化,进而将女性塑造为“被看”的客体,在这一过程中,电影《厕所英雄》无意识复制了男性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的权利结构。
影片中还存在另一种“观看”,即男主人公通过偷拍、跟踪、未经同意使用其肖像做巨幅海报的方式“观看”,从而在精神层面“占有”女主人公的身体。这种心理下的行为模式是对女性身体的想象与意淫,也是对女性身体特征的强调与肯定。影片中女性身体变相地作为景观而存在,女性的思想却是“缺席”状态。
除了作为男性欲望客体而存在,女性身体特征也物化为女性为了获得男性认同和赞赏所需要利用的手段。正如贝蒂·弗里丹所说:“妇女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传统的呼声和弗洛伊德复杂理论的说教,说她们只该在自身具有的女性特征内荣耀一番,舍此不能别有祈求。”[3]回顾影片男女主人公不打不相识的爱情发展,女性特征被塑造为女性的“制胜法宝”。两人在火车的厕所相遇,女主人公因男主人公未锁紧厕所门的不当行为而愤愤不平,男主人公反驳女主人公进厕所前不敲门也有违礼节,正当两人争执不下、矛盾进一步升级之中,男主人公看到了因气愤而扭头指责的女主人公,女主人公娇美的外貌迅速吸引住男主人公,使得男主人公为了赢得芳心赔礼道歉。两人分别后,男主人公巧舌如簧地拒绝客户对商品不满意的投诉扬长而去,却因为发现商品是由女主人公家所购买,立刻打道回府耐心进行售后服务。影片片段强调了女性特征所带来的便利性,女性通过女性特征而非精神层面“俘获”男性,以便为自己“谋利”。在此视觉符码的影响下,女性观众将会下意识装扮自己,使其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期望以自身的“美”取悦男性,获得男性的好感与认同。
二、男性视域下的女性形象塑造
导演企图将男性意识形态巧妙地缝合于提倡女权运动的《厕所英雄》中,通过女性角色分析,窥见男权意识形态如何塑造影片人物。影片中塑造了两类女性人物:一类是以女主人公贾耶为代表的新时代知识女性,另一类是未受过教育的普通家庭主妇,包括生活优渥的贾耶母亲、年迈的凯沙夫奶奶以及夜壶妇女会众多女成员。
首先,对于第一类精英女性的塑造,其形象过于单一化、低幼化。女主人公贾耶是一位具有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她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商业与管理学士文凭,会说外语,在学校任教,家庭富裕,年轻貌美,男主人公凯沙夫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大龄未婚男,父亲墨守传统陋习、固执而狭隘,第一任妻子是一头母牛,他和父亲、弟弟一同经营自行车行为生。凯沙夫一见钟情后就迅速通过跟踪、窥视、电话骚扰和粗鲁霸道的告白向贾耶表达爱意,而穷追猛打的方式却使贾耶怒火中烧,贾耶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和凯沙夫绝无相恋可能,企图终止这段单相思,凯沙夫却自顾自地向贾耶表示:“我们之间已经产生了火花了,只是你没看到而已。”这种大男子主义式臆想和霸道总裁式的台词,让人感到不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女主人公贾耶从此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凯沙夫,最后终成眷属。幼稚化、扁平化、梦幻化的恋爱描写加之男女主人公在学历、年龄、家庭经济条件上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使得影片更像是草根男性情绪的宣泄与被精英女性强烈压抑后的精神反抗。通过虚幻的电影造梦机制,精英女性莫名其妙地在爱情中处于臣服姿态,从而使草根男性实现了对精英女性的征服,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男权意识形态下对精英女性形象幻想式塑造。
其次,对于未受过教育的普通妇女,则主要塑造为被男权压迫的不自知的麻木形象或是作为男权压迫的帮凶形象。对于贾耶以离婚来解决矛盾的处事方式,贾耶母亲和贾耶的父亲、叔公持迥然不同的立场,母亲反对贾耶的做法,希望她尽快回到夫家,“不要将事情复杂化”,父亲和叔父支持贾耶并批评母亲:“你们女人最大的阻力反而是你们女人。”凯沙夫的奶奶和贾耶的母亲立场一致,她指责贾耶,认为“做女人就得一直妥协,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直到影片结束,这两位女性都没有表示出明确的女权立场,为女性权利奋臂大呼,而是以被动的“沉默”消失。和这两位女性的“沉默”不同,夜壶妇女会的女性成员在贾耶离婚案的启发下,最后实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这份觉醒因为社会的残酷而显示出其理想化的倾向,正如夜壶妇女会的女性成员之一所说,“你想怎么样?想让我们像你一样离开夫家吗?就算回到父母家,我们也没有厕所”,一语击破影片的理想化革命激情的幻想。现实比电影更为残酷,印度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上的不独立,印度女性需要依靠男性实现生活的基本需要。因此,只要印度女性缺乏经济基础,那么她们就无法摆脱男权控制,夺取女性话语权。正如贾耶的回答“我只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贾耶是幸运的个例,但对于绝大多数女性而言,离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解。影片中过于理想化的女性抗争形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能被迫流产。
因此,前一类女性形象难逃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占有与想象,而后一种女性形象则因过于理想化而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存在割裂。
三、影像中的现实思考
当代印度电影并不缺乏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印度新电影之母”米拉·奈尔曾凭借影片《季风婚礼》获得第5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2002年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季风婚礼》讲述在全球语境下,受西化教育和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都市青年人内心的茫然与身份的错乱。她电影的独到之处在于以印度女性的视角拍摄影片,深层探讨印度女性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生存环境、在印度社会中的生存价值和现阶段印度女性在男性心目中的位置。[4]
和《厕所英雄》扁平化、理想化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刻画方式不同,《季风婚礼》表现了多个女性的情感生活,体味女性的心酸与苦恼,深入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细腻地触摸在特定时代下女性的真情实感。有异于《厕所英雄》中女性“相对缺席”的地位,《季风婚礼》中的婚姻世界是一个被女性所建构的世界,女性们敢于大胆地追求自我价值,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而影片中的男性虽然出现,却没法动摇女性的独立性和个人价值判断取向。按照印度传统“父母之命”的婚姻观念,阿迪特被安排和素未谋面的海蒙特成婚,可新娘却钟情于已婚同事,并在新婚前一晚试图与他发生性关系。倡导夫妻间坦诚相待的阿迪特向未婚夫和盘托出这段私情,未婚夫海蒙特虽然火冒三丈,甚至打算取消婚约,但他选择了谅解诚实的未婚妻。斟酌再三后,海蒙特对阿迪特说:“至于我们两个能不能结婚,只有你能回答了。”他将婚姻的选择权交给阿迪特。阿迪特的表姐丽尔年幼时曾被有钱的亲戚泰加性骚扰,却一直未曾揭发。在婚宴筹办期中,她发现贼心不死的泰加再次对家族中的小女孩实施猥亵,沉默许久的丽尔不顾家庭破裂的风险和自己经济窘迫的危机,最终选择了将丑闻公之于众。阿迪特的表妹阿加莎将自己同大学生胡拉之间的调情当作一种男女间的欢愉,而不是神圣的婚姻抉择。影片给予女性对婚姻高度的自由选择权,倡导女性积极探索自我生命意识,不畏男性强权。在这一点上。《季风婚礼》比《厕所英雄》走得更远。
实际上,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批女性题材电影,比如黄蜀芹的《人鬼情》,宁瀛的《无穷动》,彭晓莲的《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和爸爸》,李玉的《苹果》《红颜》,李少红的《恋爱中的宝贝》,侯咏的《茉莉花开》,等等[5]。这些影片对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进行大胆尝试,力图书写多重女性身份,倡导男女平等。但影片也存在无法摆脱男性观看和女性被看的地位,或者脱离实际生活,缺乏对女性感情生活的细腻描绘和深入体验。
中国女性主义电影中的男性虽然处于“缺席状态”,但实际上是“隐形的存在”,男权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女性的天空。在影片中,女性始终期待自己能被男性拯救,但现实却使女性不得不接受被男性抛弃的事实,无奈之下,男性的缺席才迫使女性不得不被动进行“自救”。例如《人鬼情》中的秋芸,她幼年时期遭受霸凌,向信任的二和哥求救,却反遭凌辱;和戏校张老师互生情愫却因张老师主动提出调离工作无疾而终;丈夫不学无术、不能理解和支持秋芸,最后两人不欢而散,以离婚告终。在这类影片中,导演虽然想极力剖析男权世界的虚伪,揭示出男权世界下女性的艰难困境,但对于在男权世界中,女性应如何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经济和身份的合法地位及其话语权的重要问题还是无解。
《厕所英雄》在选题上构思新颖,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今印度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它或是一部喜剧片,或是一部爱情片,但不会是一部以女性主义为主题的代表性电影。它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女性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让女性的身体自主行动,让女性的思想畅所欲言。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