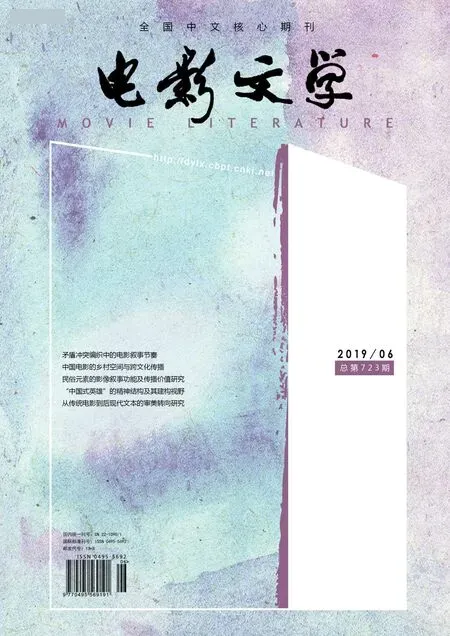从古小说到电影的审美取舍分析
张 瑜 (西安财经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典艺术与现代化文化的完美结合,导致在文学史上出现了各种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这其中古典小说也在不断探索与创新过程中保存了本土意味和优雅形式,同时由于古典小说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上古典小说符合观众的审美需求,使得古典小说成为当代电影重要的取材对象,但是由于古典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古小说运用文字描写给读者一些想象空间的思想感悟,是文学表达的艺术形式;而电影则是通过视觉,听觉等给观众呈现出真实感受,是一种影视表达的艺术形式。电影和小说二者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带给观众或者读者的感受不同,艺术表现方式也不同,因此二者所表现的审美特征也是不同的。但是艺术对于文学与电影的态度是客观而又宽容的,在时代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文学与电影还在此过程中通过在艺术风貌、审美风格等方面不断进步,并对现代化审美进行有意义的借鉴,使之不断进步。本文主要从故事情节、叙事视角、主题主旨的表达等方面探讨了在现代化审美视域下古小说和电影在现代化审美的发展过程中的取舍和发展。
一、艺术化故事情节
无论是古小说还是电影,故事情节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处于整个作品的中心地位,但是由于古小说与电影的载体不同,二者在现代化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展目标也有所区别,因此古小说和电影对于故事情节也有不同的要求。在小说和电影发展日益商业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古典小说改编成电影呈现在观众面前,由于电影是从视觉听觉等多方面呈现出来的影视形式的艺术方式,因此在改编小说的过程中,电影在对整个故事情节的生活化、连贯性、画面感等方面具有更高标准的要求,再加上电影时长的限制,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往往会进行大量的删减来保证故事的连贯性和合理性[1]。例如电影《刺客聂隐娘》就是根据小说改编成的一部电影,但是该电影仅仅采用了原小说的前半部分作为载体,删除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片段,致力于将主角聂隐娘变成一位真实的具有生活化的人物,使得剧情发展更加真实可信。这种小说向电影的转化,只有把握古典小说的精髓和文化意蕴,并尊重电影的艺术特性,尽可能地平衡影片的视听特效与叙事内容的关系,方能取得双赢的结果,丰富和发展古小说的艺术面貌、审美风格。然而影片《刺客聂隐娘》在播出之后出现了评价两极化的现象,是由于大部分的观众并没有接受这种形式的审美,即超出了观众的审美接受能力,使观众对这部影片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不理解不认同。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改编对故事情节的推动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电影《刺客聂隐娘》对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导致小说和电影在故事情节和主题表达方面有很大差异,在电影有限的时间内塑造出主要的人物,凸显出电影主旨,以此来迎合大众的审美口味,至于最后电影《刺客聂隐娘》的票房成绩不佳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大部分观众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了电影的情节表现方面,并没有注意到电影在审美特征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改善,只是过分关注经济利益方面的变化,导演侯孝贤比较注重运用电影手段来表现故事情节,一个好的故事所表现出的审美特征是大众所乐于接受的,因此故事情节的叙述无论是对电影还是对小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霸王别姬》改编自李碧华名作,讲述了在戏院一起长大的师兄弟段小楼和程蝶衣,二人分别饰演生、旦角,以一出《霸王别姬》享誉京城,由于二者对待戏剧与人生的态度不同,在段小楼迎娶名妓菊仙之后,段小楼、程蝶衣、菊仙三人围绕一出《霸王别姬》生出的爱恨情仇战开始随着时代风云的变迁不断升级,终酿成悲剧。在蝶衣发疯似的凄喊“我要跟你唱一辈子戏。少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时,“不疯魔,不成活”六个字是小楼给程蝶衣的评价,也暗示了二人的不同结局。影片开头的“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注定是错的,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程蝶衣“女娇娥”这么多年,京剧深入骨髓,当“女娇娥”再无羞耻,“文革”动荡后,时隔22年未同台的蝶衣、小楼再次着装霸王虞姬回到戏院。此时二人的心境和20年前大不相同,却再也回不到从前那般亲近,这么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情节展现了当时的政治以及京剧艺术上制度的恶劣,以及在那个时代对人心的伤害。
二、多角度叙事视角
虽然古典小说与电影的载体和叙述对象有所不同,但是二者都具有叙事性,可以说叙事性是小说和电影之间的桥梁[2]。例如《芳华》,无论是小说还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版本,无疑都是成功的,但是二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小说与电影的基调不同:小说结局交代了四个女兵各自的结局,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来反思集体主义与个人造成的影响;电影的结构与节奏略显不足,过多的旁白侵袭了观众的感悟,太过直白;剪辑将许多细碎的集体生活穿插与男女主角起伏的命运间,甚至一度让旁观视角的小穗子走入前台,扰乱了主线情感的渲染。后来细想这剪辑应该是冯小刚导演刻意为之: 共度青春的一群人,有人命运突变,有人一直顺畅;下放边疆的人浴血无助时,大院庇护的人欢笑依旧,这样的场景切换更突出了世事无常,导致电影的故事情节没有连贯性,由于情节上的删减,使得电影在叙事方式方面缺乏厚重感,没有完全展示出人物的内心变化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由于人物形象塑造得比较立体,小说中“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珍惜善良”句子,练功房、成分、“解放”等太多感同身受的情节和词汇在电影中体现出来,让观众处于深深的感动之中,在精神病医院,夜晚礼堂外草坪上何小萍的独舞。草坪的尽头,那场即将曲终人散的演出正灯火通明,这个穿病号服的精神病患者放下了当年集体演出中的紧张,完全沉浸在舞蹈中,真是纯美的感伤和荒诞。如果电影在此刻结束,也未尝不可。谁都知道,从此,在中国,时代的车轮隆隆向前,一切都将成为为了忘却的纪念,影片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美好特质。而小说中,严歌苓最擅长营造的,是叙事陷阱。“触摸”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不论是电影里的强抱,还是在原著里写实了刘峰的猥亵,“是刘峰而不是林丁丁吐口了事件中最恶劣的细节:他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经过是这样的:他的手开始是无辜的,为丁丁擦泪,渐渐入了邪,从她衬衫的背后插进去……”坐实他的性侵行为,等于默认在故事结构里,他被流放具有一定合理性,跟她此书的批判主题产生了不协调,甚至是反方向的力,这是严歌苓用笔的主观恶意。《芳华》里有句话,“没有被善待的人,最容易识别善良”。 沧桑经年,“活雷锋”刘峰和“万人嫌”何小萍这两个没被生活善待的人,终于互相体谅,幸而走到了一起。[3]就像《日瓦戈医生》里的日瓦戈和拉拉。《芳华》在萧穗子的独白声中,故事悄然落下了帷幕。“每次大家聚会,别人都是一脸沧桑抱怨着生活,而刘峰和何小萍,却显得平静温和,看起来比别人更幸福。”不管是承载着无限风流的文工团舞榭歌台,还是枪林弹雨中让人绝望透顶的血肉横飞,又或是带来希望的邓丽君的歌声和亲人平反的消息,即使是那没有结果的,不成形的爱情,都带着一种惊心动魄又不堪一击的美。壮丽但不浮夸,残酷却不残忍,克制而细腻,不歌颂不批判,一切贵在真实。《芳华》里面对时代的描绘才是整个作品的中心,故事情节、叙事视角都是围绕整个核心来阐述的。虽然在电影中保留了萧穗子“我”的画外音,但整体上仍然是全能视角的叙述方式,小说和电影都是极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各自具有不同的审美需求,这就表现出了电影的独特的叙事艺术,凸显出了独特的审美特征[4]。
三、现实主题凸显电影主旨
小说是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刻画人物形象,描述故事情节,来表达一定的主题思想。电影则是通过影视手段来刻画表现影片主题,电影《悲伤逆流成河》是一部以校园暴力为切入点切切实实表现出受害人、施害人、亲友、旁观者以及帮凶的各种层面的青春片,主角是长期身处校园暴力的女高中生唐小米,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备受极大折磨,在让人心疼的同时也是全剧中代入感最强的一个人物;其次影片中反复出现了几个角色:“贴口香糖的丑女孩”“被水管浇的男生”“貌似内心不甘但怒不敢言,最后自杀一幕后给了同学一耳光的女生”,有些人是唐小米校园欺凌的“狗腿子”;有些人仅仅是为了找个发泄口出气;有些人不愿意却不敢站出来,当然更多的人只是起哄,墙倒众人推,人云亦云,但不可否认的就是,所有人都是逼迫女主角自杀校园欺凌事件的帮凶。影片所要表达的是面对欺凌,我们拥有了更加强大的成年人水平的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但有一日我们有可能成为父母,或者已经成为父母,我们的下一代仍然会经历青葱岁月,慢慢地从残酷的小孩社会中带着伤痛蜕变成大人。关注校园欺凌事件也许真正和我们相关的,恰好是在片子里找对自己现在应该扮演的角色。比如正确和子女沟通的父母,或者给悲伤少女带一丝阳关和快乐的顾森西。而不是高喊着关注某某某事件的看客。如果当初这部片子里那些“帮凶”们能够全部好像顾森西一样拥有自己独立和正确的判断力并且坚持的话,就不会给唐小米一个欺负他人的空气和养分,让这样的拧巴毒苗肆意滋生了。《悲伤逆流成河》这部影片色彩深沉,故事背景沉重但是并不影响整个电影主旨的表达;相反,沉重的氛围为影片主旨烘托了气氛,是一个凸显主题的辅助手段,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电影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
同样,《教父》也是一部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小说《教父》中的展现的庞大的故事架构,复杂的人物关系,众多的情节起点,为后续的故事发展打下了基础,电影中导演对细节的刻画,让整部影片显得与众不同,咖啡、婚礼蛋糕、油饼、糕点师、护士、小酒馆、酒、车、公路,鲜活地点缀着每一段故事,整个电影的色调庄重而压抑,又为读者呈现出了完美的审美态度。在电影中,也通过一些细节描写展现出教父身上人性化的一面,《教父》告诉了我们,只要你可以体面地面对这个世界,你也就可以体面地活着。《教父》三部曲都有很浓重的基督色彩,再加上较为古典的配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和电影手段在审美表达特征方面的巨大优势。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现代化审美视域下对于文学和电影的要求都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美学则认为艺术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中国电影的美学观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即重视审美中的理知性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伦理的道德力量[9]。在世界电影却日渐呈现出一种在电影文化和审美上的多极均势和文明开化新格局的情况下,电影只有在符合观众审美的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其所想表达的艺术价值,因此研究审美需求无论是对于小说文学还是电影创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