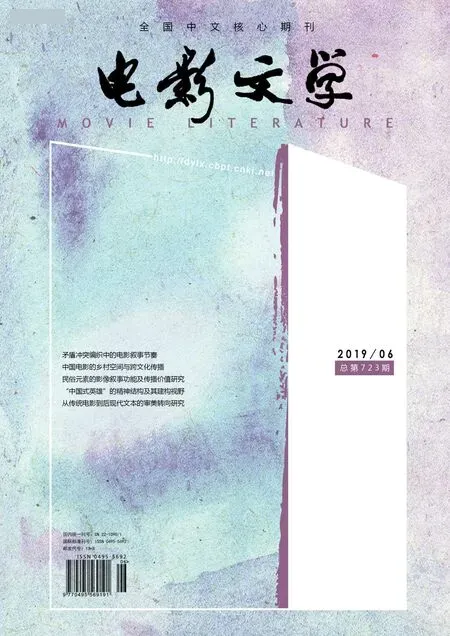中国电影的乡村空间与跨文化传播
段 祎 (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电影是时间与空间的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电影艺术是通过变化不同的空间形象与时间组合来讲述故事,是视与听相结合的叙事艺术,即通过千变万化的视听组合方式和故事样貌来完成电影的创作,因此电影艺术也拥有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独特魅力。电影的声音固然是电影创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电影的空间始终是电影艺术创作的重中之重。电影空间的选取将会决定电影最终呈现出的美学风格,以及能否准确传神地传达导演的创作意图,并最终实现观众的认同与共鸣。近年来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立足于中国广袤而多样的乡村空间的电影作品跻身世界优秀电影的行列,它们给世界电影观众带来了别样出众的视听感受,同样也让世人重新认知了不一样的中国电影和文化。在2014—2016年度,以在贵州凯里为主要叙事空间,讲述了乡村医生故事的《路边野餐》,以张家口顾家沟农村老光棍儿故事为背景的《光棍儿》,以汾阳小城一家三口在时代里更迭的《山河故人》等都成为世界影坛的佳作,在国际上屡获殊荣;在2017年度,《村戏》里20世纪80年代河北农村的土地之争,《暴裂无声》里内蒙古村镇荒废矿区的命案,《米花之味》里云南沧源村寨的母女隔阂与和解,《十八洞村》里湘西苗寨扶贫脱贫的故事……这些电影都在具有独特风味的中国乡村地貌里讲述着农村小人物的故事,并将他们带入了世界电影观众的视野中。2018年,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将山西大同小人物的“江湖”梦带入了世人的视野,承载了巨变的时代下,记录了山西大同的“江湖”中,面目模糊的小人物的悲欢。中国自古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其乡村地貌形态各异,导演们在乡村空间的创作中立足于电影本体的特性,根植于本土人文的空间拓展与深入的再创作,在乡村意象的空间建构中实现了独有的美学气息,为中国电影增加了独特的美感与异域风情,也让中国乡村电影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与跨文化传播的突围之路。
一、乡村空间的陌生化
电影空间首先承载了地理位置和历史时空的特征与信息,是电影叙事展开的首要条件。电影空间的展示是通过导演的立场和视点来决定的,而观众在自我感知中再理解其空间内的故事,这便形成电影艺术独到的观看体验。这种由未知到已知,由疏离到认同的探索,即是电影空间陌生化的建构方式。
首先,2017年上映的中国电影乡村空间中,导演多以一种“闯入者”的视点将其电影的空间打开,如电影《米花之味》中的闯入者是女主角英泽饰演的离家多年的母亲,影片大量表现了诸多女主角中国西南边陲傣家寨子与现代的格格不入:母亲面对充满陌生感的女儿不知所措,女儿用陌生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母亲,大城市归来的女主角在村民口中做了“不干净”的事……导演在镜头里克制准确地表达了这份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疏离感。在人物造型上,女主角开始身着现代服装,和当地民族服饰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空间造型上,为女儿购买的进口食品,用来打游戏的电子设备,以及村里的孩子们围坐在传统的庙前争先恐后用Wi-Fi上网……这些日常感的场景中皆凸显着一种对比与矛盾。在电影《十八洞村》中,故事扎根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和苗族文化,仍是以一群扶贫工作队这群“闯入者”的到来为事件起因,试图帮扶老村民退伍军人杨英俊一家,但是这群城市里的好心人并没有给杨英俊的生活带来欣喜,却激起了他落寞的男人尊严和对自己与土地关系的反思。在面对离开与坚守时,男主角杨英俊一家对于土地的情感渐渐展开,电影在影像中大量呈现出湘西田间耕作的唯美镜头,这些是杨英俊内心对故土的热爱与难舍的外化表现。片中几次的闪回片段里着重表现了杨英俊与妻子在选择外出打工还是坚守在家的场景细节,以及儿子在大城市打工多年未能回家的情节,妻子将小外孙女小南瓜视为珍宝,实则是寄托了一份不离不弃的留恋之情。扶贫队伍里的年轻干事在与杨英俊和其他村民的朝夕相处中,进而了解这个村落的历史、人文、民俗,逐渐理解了这片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和扶贫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影片用大量的画面表现了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深情,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山丘呈现出的世外桃源便是农民心底最不舍的乡愁。
其次,导演们均不吝啬对于中国农村民俗的充分展示。它们仿佛为一个个未知的中国乡村地域的版图赋予了神秘的光芒,不仅为中国观众,也为世界观众做了进一步的影像探索。《米花之味》这部电影在蔡明亮的御用摄影和造型团队的精心呈现下,将西南傣族山野,蔚蓝纯净的蓝天映照着山间色彩明快的农作物,勾勒出一派轻松而唯美的氛围。无论是溶洞、庙宇、米花、山神,还是醉人的传统舞蹈,都让观众充满了对本土文化的无限神往与好奇。片中一个女学生得了重病,按照傣族寨子里的惯例要求助山神,米花是请山神的必备食物。于是母女二人炸米花变成了一场人物情感关系和解的日常却不平常的场景。在一口大锅前,母女面对面拿着长长的筷子,边轻松地聊天边用一种仪式感的方式将米花出锅,一切宁静淡然又和谐温馨;村中的人集体去拜石佛,却发现被开发的景区大门紧锁,门上写着“关”,像是一个黑色幽默式的玩笑。于是大家自发地在门外跳起了舞蹈,村民在天地间忘情起舞,仿佛惆怅也化解在其中了。在《十八洞村》中,影片将悠扬婉转的苗寨山歌、色香味美的湘西美食以及精美的民族服饰巧妙地贯穿进故事中:断交酒、河边洗衣服的穿着苗族服饰的妇女、房顶拴着的椅子嫁妆,像是走进了另一个魔幻而超现实的古老时空,充满了脱离世俗与现代的神秘气息。《村戏》从排演老戏这一情节入手,在故事中融入了大量的传统戏曲元素,让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呈现出了鲜活的光芒。
二、本土乡村空间的象征化
在电影镜头空间中制造出具有象征意味的造型元素才是研究电影空间叙事的一把关键的钥匙,通过其空间造型元素中的色彩、角度、构图、镜头景深、光线、影调等制造一种寓意与巧思,是导演在构建自己的美学空间和表达导演意图惯用的手法之一。
电影《村戏》在影像上极端形式化,全片采用黑白色调,在闪回的段落运用了有些失真、饱和度过强的红绿色块制造了一种强有力的视觉反差。村戏在空间造型的拍摄上使用了很多大胆的构图与角度,如广角变形、极致特写等。在场面调度上,影片设计了一个戏中戏的类似舞台剧的段落,用固定的长镜头来拍摄奎疯子唱《钟馗打鬼》,演员仿佛站在舞台中央,但又被限制在狭窄的屋子里,空间和演员形成了一种戏剧张力,空间压制了疯癫的奎疯子,巧妙地将他内心扭曲而压抑的生存状态外化,同时又与戏曲的舞台感融合。《米花之味》中大量运用的寺庙场景作为主要的叙事空间,也是充满了象征意味。在表现母亲叶楠寻找女儿的情节时选择了夜晚的寺庙。寺庙在夜晚的笼罩下神圣感好像增加了,和尚也说这里禁止女人通过,制止了女主角。但急于找到女儿的母亲并没有被这份威严和神秘吓退,反而绕进了禁区,还在对白中加一些 “佛祖要休息了”戏谑的调侃,把打游戏的孩子赶回家。同样在寺庙里,一对新人穿着现代的婚纱在寺庙的庙堂举行着中西合并式的婚礼,还把百元钞票折叠好去供奉寺庙的神灵,孩子们透过窗户偷看新娘,并调侃新娘新郎的长相,婚礼的肃穆庄严感被杂糅的喜剧感取代。女儿最后还偷了寺庙的钱去上网,又一次让母亲去找女儿回家。母女关系在庙宇的庇护下好像没有多少进展,反而被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打乱了,一次次的冲突与和解成为《米花之味》想探讨的终极命题,镜头无不例外地选择了网吧、庙宇、街头、田间,用充满象征意味的角度与呈现方式来阐释其主题;一个生病的孩子使得全村人去邀请山神,人们一起去祭奠石佛的时候却吃了闭门羹,显得荒诞和无奈;影片结尾,一个具有象征化的溶洞将影片推向高潮,母女二人在古老的大自然创造出的溶洞中,在大佛面前起舞。佛像和溶洞充满了神秘感与禅意,让母女二人仿佛变成了两只蓝孔雀,这个仪式仿佛召回了心灵的回归,人与自然的融合。《十八洞村》片中多次出现椅子,导演试图把每把椅子赋予符号化的意义,即每个人在世界中的一个位置等,都是在竭力地使用空间造型中的道具将空间象征化。《暴裂无声》里多次出现了血淋淋的羊肉、羊头等极致化的特写,选取的大部分空间均以地广人稀的荒野、公路、小酒馆,破败、萧瑟的空间外化出男主角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的绝望心境,在片尾处强化了山洞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空间地点,仿佛在象征着一种无力而循环反复的黑洞,引发观众去思考人性与良知的终极命题。
三、乡村本土空间的多元化
电影空间的发展、演变过程制约于电影技术的发展。在技术条件还不发达的早期电影时代,电影创作者们被现实世界所限制,无法超越对现实空间逼真有效的再创造,因此技术手段的落后导致在空间的逼真性上不尽如人意,在对情节的呈现上增加了许多困难与挑战。纵观电影历史的长河,电影创作大都局限在以现实世界、环境为背景来讲述故事,拍摄手法也多是常规式的。时至今日,电影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如梦如幻的程度,导演可以将故事安放在任何一个想象出的空间之中,无数超现实题材的优秀电影,如《哈利·波特》《星际穿越》《盗梦空间》《雪国列车》《头号玩家》……将观众带入到了电影的魔法时空里。随着VR等先进技术的引入,电影空间可以成为人们从现实世界走向想象世界的桥梁。中国电影的乡村空间除了求取表现手法的创新,更应该与科技手段相结合,创造出更多的具有想象力的电影空间。
其次,2016年出现的以贵州凯里这一乡村空间的电影《路边野餐》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拍摄的可能性。其中40分钟超时空的长镜头带领观众穿越了梦境与现实的时空。无论是水底的绣花鞋,荡麦飘摇的歌声,诗一般的独白都让时空的可能性充满了一种张力,这种打破电影时空限制的尝试是十分出彩的。电影艺术的表现力不应当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真正受到限制的是人类想象力和对电影艺术的积极尝试。
最后,随着网络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和电影技术的革新,电影艺术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由农民自己拍摄、创作,这种由民众参与合作的影像模式的 “参与式影像”也逐步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们使用手机拍摄,不追求规整的灯光与技术要求,为乡村电影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农民的自我观看、自我表达开辟了新的语境。其次,随着城乡一体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乡村电影的受众日渐模糊和宽泛,其传播目标和对象不断在发生转移,从非消费对象到消费对象的身份转变,这些提示我们,电影导演的身份、电影拍摄的要求,以及对于电影空间的尝试都该抛开固有的观念,不断地依据传播者与接受者重新革新认识。
中国电影的乡村空间想要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文化输出类产品,应该不拘泥于单一的创作样式,多挖掘本土空间的优势,传递其独特且共通的人类美学价值的同时,汲取电影技术和传播形式的多样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乡村地貌引领到一个更前沿的创作领地,这一点需要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