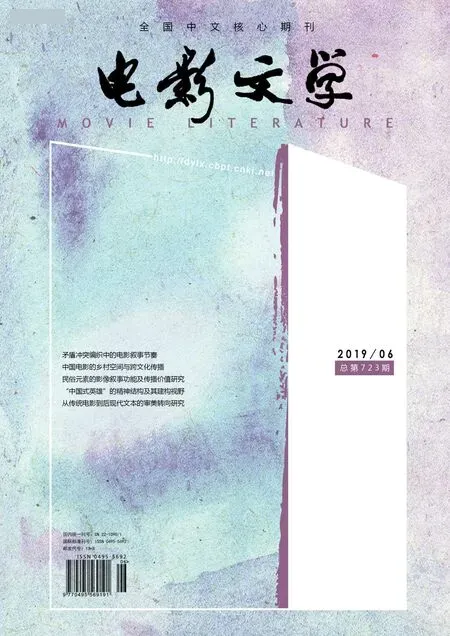中国早期电影国族主义遮蔽下的女性困境
徐雅宁 (西安外国语大学 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要在30年之内完成西方300年的任务,所以将一些社会进程予以提速及整合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地位却是截然不同的。政治革命,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权威,对包括女权、启蒙等在内的社会革命发号施令,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更偏重个体解放的社会革命的诉求和内涵。正如李泽厚所言:“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所有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体权利的注视和尊重。”[1]
与西方女权运动相比,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缺乏性别立场鲜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以被看作是后发现代性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入侵的抗争在性别问题上的一种体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女性解放成为反抗殖民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一个子命题,女性解放在更广阔的层面被纳入到民族解放的轨道中。
由于与民族国家话语的联姻,导致了中国早期电影中性别论说的丰富内涵和复杂纠缠。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民族国家对妇女群体的压制和许诺,也可以窥见妇女群体及女性个体对民族国家的屈从和反抗。
一、去性别化:女性作为苦难民族的隐喻
自鸦片战争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救亡与忧患意识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切身性难题。在这种环境中诞生并成长的中国电影,就不能仅仅当作一种单纯的电影创作来看待,在它的文本中呈现着当时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大多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存在于文本中,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对应着中华民族的现实境遇。
在清末民初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异族王权的腐朽促发了国族主义的剧烈上升,这使得文艺作品中的女性身体成为国族话语策源地。在当时的电影创作者看来,女性形象承载了文化历史所赋予的“可观看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引起注意和同情,所以女性的身体反复承载着苦难、卑贱与被侵占的想象。
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刚刚走出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首先追求的是技术上的成熟和叙事上的完整,以求在外国电影的倾轧之下能够寻得立足之地。但这时的一些电影已经开始在蹒跚学步中关注现实,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曲折的反映。比如《大义灭亲》中的财政总长梅国鲁私借外债导致国家权利丧失,《爱国伞》中的富商傅卜仁置灾民于不顾,卖国借款,《诱婚》中矿物会办席颂坚为一己之力,将中原地区原油开采权卖给“野心国”,《伪君子》中的劣绅史伯仁为了竞选市长,将“全市交通权”贱卖给了“口木公司”等,以及《秋扇怨》《不如归》《扬子江》中涉及了军阀混战、“与邻国开兵端”等背景,呈现了封建阶级、地方军阀与外国势力相互勾结,卖国辱权,伤害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现实。这些影片中的女性角色都有着悲惨的命运,但是造成其悲惨命运的直接原因更多指向了封建腐朽思想所导致的爱情悲剧上,其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控诉和亡国灭种的警醒是比较曲折和间接的。将女性悲惨命运与国家危亡勾连起来的叙事模式进入20世纪30年代才逐渐明朗起来。
进入20世纪30年代,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反帝救亡的呼声空前高涨,这种呼声自然也反映在新生的电影创作中。更重要的是,在左翼进步影人直接参与到电影创作之后,电影的教育和战斗功能更加凸显,批判帝国主义侵略、号召大众民族救亡成为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一大主题,正如左翼影评家王尘无所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从一般娱乐转变为民族解放的武器”。[2]
但是受制于上海被殖民状态的现实困境以及各种电影审查制度,当时的电影不能够直接表现帝国主义、国民政府、各地军阀、封建势力等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只能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在灾难深重的国土与遭受折磨的国民之间建立起一种隐喻的联系,以起到暴露社会黑暗、呼吁奋起反抗的效果。《马路天使》一片中歌女小红演唱《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的两个段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片段,通过声音、画面、剪辑三位一体,隐晦地表达了创作者的爱国思想。小红在茶馆演唱《四季歌》,伴随着第一段“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的歌词,画面中切入的是炮火连天,两军对垒的场景,间接介绍了女主角小红的身世,也借小红的歌唱抒发对日本侵略者的家仇国恨,传达了进步影人号召民众群起抗日的硬性主题。类似的人物设定还发生在《天明》中的菱菱、《船家女》中的阿玲、《火山情血》中的柳花等角色身上。通过女性角色们备受摧残的身躯,中国早期电影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中国被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封建势力等压榨的现实境遇的关注,女性身体被新式知识分子整合进家国叙述中,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符码。
但是这里要指出一点,这些电影在描写这些受难女性形象时存在着很明显的唯美化和情色化倾向。在这种唯美化、情色化描写中,女性的个人痛苦以及抗争和牺牲常常被浪漫化处理了,反派角色对于女性肉体的侵犯,象征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女性的牺牲和反抗也升华为一种国家的使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所遭受的苦难经历和惨痛感情却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正如当时一些男性诗人的诗词中所写的,“最是令人忘不得,桃花血染玉肌红”;[3]“我爱英雄犹爱色,红颜要带血光看”。[4]这些悲惨女性的身体受难经历被避而不谈,女性的受难身体被作为“看客”的男性电影创作者加工成一种可供凝视的极端美学体验。然而,女性本身却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仅仅作为一种投射男性欲望想象的载体呈现在大银幕上,进而提供一种隐藏在宏大主题之下的审美愉悦。
二、姿色救国:男性赋予女性的历史使命
在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急环境中,中国社会尤其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充斥着一种躁动和奢靡的末世情绪。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女体和革命或许是最具刺激性和煽动性的噱头。正如进步影评人柯灵在评价当时的电影广告时说的,“利用宣传文字,信口雌黄,说得天花乱坠,来欺骗一部分浅视的观众,或者专门在广告上运用各种性诱惑的词句,如什么‘香艳肉感’‘酥胸坦雪’‘玉体横陈’‘十六岁以下的童子禁止观看’等,来吸引性欲狂的小市民观客,但近来常常引用‘爱国’‘革命’‘义勇军’等刺激兴奋的名词了”。[5]
在借助女体的损害激发起大众对国土破碎的愤慨之后,如何使女体为革命、救国服务是中国早期电影创作者所着力思考的问题。这种革命进行时中的性别叙述,在消费了女性所遭受的灾难之后,开始征用女性的容颜和身体。
伴随着自清末以来妇女解放思潮的推进,在当时中国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对这些女性形象加以深入分析会发现,在这些形象所彰显的女性自身价值之上,始终笼罩着另一种高高在上的价值——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1928年5月,以筹款支援北伐战争为由,电影界兴起了一股“以腰救国”的风潮,当时一个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阮玲玉以腰许国》的文章:“搂腰救国之议既成,某君登女星阮玲玉之门请求加入。阮曰:以腰求利,舞女也,非我辈灿灿之星所能为,请君勿再罗索,否则面斥莫怪。某君曰:跳舞大会之充当舞女,其价值非寻常舞女可比,盖一则为国,一则为个人生计也。为国而牺牲其人格,爱国也。阮玲玉挺身而起,慨然而言曰:我愿以腰许国矣。”[6]
在当时的古装片创作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强调了片中女性主人公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爱国气节,以起到唤醒民众、号召救亡的作用。这在当时的电影宣传中有着明显的体现,比如《明末遗恨》的广告词写道:“侠妓殉国,嚼舌以死,一代文士,慷慨就义,忠义历史爱国战事古装巨片。”[7]新光大戏院为《赛金花》发布的广告,突出赛金花“以一介弱女挽全城浩劫,凭两片樱唇,救百万生灵。近百年来一页痛史,女性群中一代奇人”。[8]天一公司为《木兰从军》的广告说“花木兰代父从军,千古播为美谈”,称赞花木兰“以一弱女子居然能有这般伟大的怀抱,实可谓千百年来女界的唯一荣光”。[9]
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为分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电影在表现女性的救国行为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中,女性的革命救国行为多与报父仇或报夫仇结合在一起,鼓励女性救国的思想被嫁接到传统“三从”伦理上。在号召女性参加革命的社会动员中,电影创作者一直在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女”“烈女”情愫,不断赋予女性的生命与牺牲以道德/政治意义。在当时的中国,救亡图存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国族权力话语,意味着一种权威话语权力。通过将“孝女”“烈女”的复仇故事与对于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结合起来,电影成为具有教育功能和宣传效果的文化资本。
《大义灭亲》中,梅丽兰得知了抓走爱人郑民威的叔父梅国鲁也是害死其父亲的凶手。梅丽兰拦住总统的汽车“告御状”,将财政总长梅国鲁卖国借债的恶行暴露出来,这一行为同时达到了报父仇、救爱人、救国家三个目的。《诱婚》中,高云英为了青梅竹马的爱人史裴成,偷到了席颂坚将煤油矿产出卖给“野心国”的证据。《孝女复仇》中,胡氏女子的父亲曾经和无良军阀武尚读同为清末革命党,武尚读出卖胡父,导致胡父被杀。胡氏女子为了报父仇,先是嫁给了武的卫队长为妻,以接近武。之后,又在武的纳妾之夜,假扮成新娘,刺杀了武。《和平之神》中,甲乙两省军阀屯兵边界,大战一触即发。凌云飞奉乙省督军之命,前往甲省和谈,却被甲省好战军官扣押。凌的未婚妻林素薇带着妹妹前往甲省营救,利用计策救出了未婚夫,并且向甲省督军表明了和谈意愿,避免了战争。《北京杨贵妃》中,黄正华集家仇国恨于一身,欲刺杀赵大帅,却不幸被捕。被赵大帅霸占了的名伶杨小真一直爱慕黄正华,为了营救黄正华不惜以身犯险。这种叙事手法体现了社会转折时期新旧思想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特殊文化生态,为父/为夫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父爱”/“夫爱”思想的绵延,它的价值和内涵都以从父/从夫为基础的儒家价值理念为根源。由此,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传统无所寄托的时刻,知识分子的革命想象就通过对“为父报仇”的行为以及充满浪漫色彩的“革命情侣”摹写而表现出来。
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中出现了一些新式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开始脱离传统思想中“家庭”的束缚,不再满足于为人女、为人妻,而是为了某种理想或主义,为了民族利益而奋斗。比如《三个摩登女性》中的周淑贞,《女性的呐喊》中的少英,《现代一女性》中的安琳,《新女性》中的阿英,《黄金时代》中的张小妹,等等。虽然这些女性角色在片中大多戏份很少,基本上都是以一种“政治符号”存在,但是体现出对女性的统属权开始从“家庭”向“国族”的移交。
三、男性书写下女性性别主体的缺失
梳理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潮,会发现两个生发点:从帝国主义殖民的框架中追溯,有一个“西方”的源头,即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发生自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追溯,则有一个“男性”的源头,即中国的女性解放直接来自男性知识分子的倡导。
受此影响,中国早期电影的女性形象书写表现出一种向前递进的演进过程:首先是“受难者”形象,以此象征危急时刻的国族;之后是“革命觉醒者”,以起到警醒大众、奋起反抗的效果;再之后是“革命参与者”,协助男性完成革命救亡的历史使命。这一演进过程在《大路》中茉莉这一角色身上体现得十分清晰,导演孙瑜巧妙地将音乐、影像和新闻资料片结合在一起,其艺术构思在今天看来仍属上流。茉莉为筑路工人演唱《新凤阳歌》,伴随着第一段歌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画面上出现的是无数的灾民背井离乡逃难的场景,其中穿插着幼儿哭闹、老人疲惫的特写镜头。第二段歌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年年遭灾殃。堤坝不修河水涨,田园万里变汪洋。”画面上是洪水泛滥的影像,无数房屋被浸泡、倒塌的悲惨景象。第三段歌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百姓苦难当。从前军阀争田地,如今矮鬼(笔者注:即日本侵略者。当时国民政府审查严苛,电影中不准出现日本、东北、侵略等字词)动刀枪。”画面中呈现出的是惨烈的战争画面,其中一个仰拍坦克履带从上而下压下来的特写镜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到这里,将个体女性所遭受的磨难与苦难的民族联结起来,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任务。之后,茉莉运用智慧和身体,从卖国贼家中救出了被关押的金哥等人。片尾,茉莉脱下了旗袍等女性服装,穿着工装加入了男性拉铁磙的队伍,并且加入了男性演唱《大路歌》的大合唱中:“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我们好比上火线,没有退路只向前!大家努力,一起作战!大家努力,一起作战!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
以《大路》为代表,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响应革命的召唤,在男性导师的指引下完成了获救和成长,并获得了一定的革命主体性,但女性自身的性别主体性却逐渐淡化直至被完全遮蔽。女性被解救出来,在走上自我解放和解放同胞的革命之路的同时,自身的性别意识却全部被国族意识所取代。当民族主体和性别主体二者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而是构成了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时,企图超越男性/国族“主体”去寻找中国女性的“性别主体”是不可能实现的。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正是借助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男性/国族话语的不断建构和再构,中国女性才逐渐形成了特定类型的客观形象和主观认知。一旦将男性/国族“主体”所赋予的意义抽离,所谓的“性别主体”也随即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而言,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成为一种去性别化的文化符码。
相对于男性稳定的自我而言,女性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而被赋予不同的身份,并依据不同的身份被赋予不同的价值。从上述影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要么被男性征用成为指向政治、经济或生理目的的工具,要么成为掩饰男性错误的替罪羊,即所谓的“祸水红颜”。而女性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体验者和创造者的身份被抹杀得一干二净,作为历史叙述者的资格也被彻底剥夺,只能无声地等待并接受男性的“书写”。
自清末以来,女性被先后赋予了“新贤妻良母”“国民母”“救国英雌”等多种身份,这在当时的电影中都有所体现。这些身份始终贯穿着男性的民族国家对女性一如既往的期许和询唤,虽然在外延上有着不同的边界,但是其内涵都是一样的。从女性在整个家国叙事中的位置来看,她们始终是协助男性实现救亡图存理想的从属性力量。正如《马路天使》中小红唱的《四季歌》的结尾处,“血肉筑出长城长,奴愿作当年小孟姜”。这些银幕形象所体现的仍然是女性自我意识面对强大的父权时的退守和臣服,所不同的是父权被诸如民族、革命、救亡等置换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由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女性或许连书写客体都算不上,她们只是书写的场域。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男性在女性身上书写着关于国族的“宏大叙事”,在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的名义下,女性自身的性别困境成为无人顾及的盲区。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