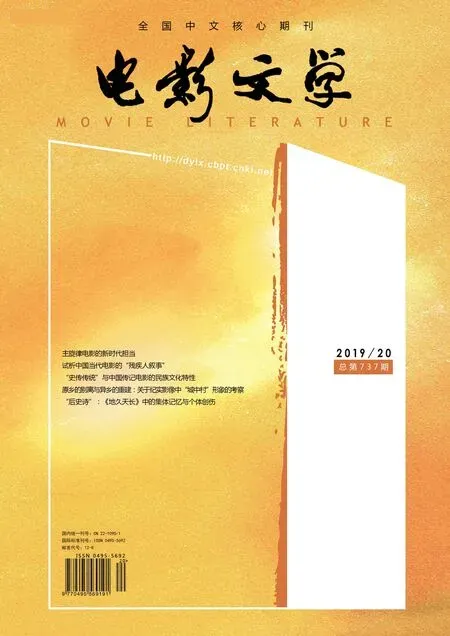《妈阁是座城》的边缘女性建构
李晓娟
(赣南师范大学 科技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虽然各自坚守的艺术领域不同,但李少红与严歌苓都致力于塑造女性,表现女性的情感和生命,这是没有争议的。在李少红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妈阁是座城》(2018)中,众多来历不同,但都被赌博耗尽人性的男性角色,是为烘托出女主人公梅晓鸥而设置的。借由“女叠码仔”这一角色,以及澳门这座纸醉金迷的赌城,一个边缘女性被建构起来。
一、边缘女性建构的发生
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当下的电影人多有对边缘的关注,“边缘人”原本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指在文化混杂的社会中,生活于母体文化和介质文化的缝隙中,难以被归类的群体。而如今在文学以及电影艺术中,诸多生活于社会底层,或有着非主流生活方式的人成为了新的边缘人,而与之相关的叙事则是边缘叙事。有学者指出:“边缘叙事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本原。通俗地表达就是,文学‘活’在人与历史的边缘地带。反过来说,文学,在常态社会里,从来就不应该是‘中心’的产物。”这尽管是对文学创作的阐发,但对于电影艺术而言亦是合乎情理的。当电影注视“边缘”的时候,也就脱离了空泛的“中心”与宏大的捆绑,身处不利境地的个体生命被置于台前,观众无疑是更乐于看到一种更为真实和鲜活的人生际遇的。同时,“边缘”本身又往往意味着某种对观众猎奇心理的满足,人的边缘化处境导致的诸多极端的爱恨情仇,以及复杂、隐秘的心灵世界等,正是电影所需要的戏剧性的来源。
而在边缘人中,女性的地位则又更为边缘。长期以来,女性因为生理性别上的弱势,一直处于一种被政治、历史和文化等遮蔽的状态中,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先天地就面临着某种劣势,女性的发展是被压抑,被忽视的。而似乎互为因果地,女性导演和编剧也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主流的、宏大的叙述,选择边缘叙事,而在边缘中苦苦挣扎的女性则是她们青睐的主人公。李少红在其电影创作中,就总是以一种女性的生命自觉,关怀着边缘女性的生存和命运。例如在《恋爱中的宝贝》(2004)中,宝贝幻想自己会飞,行为古怪的她完全无法被身边人所理解;在《生死劫》(2005)中,胭妮长期寄人篱下。而由于自身的“文革”、战争和移民等经历,严歌苓同样表现出了对边缘女性的强烈兴趣。甚至可以说,边缘女性是其稳定创作水准的支撑。例如在根据其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金陵十三钗》(2011)中,玉墨等女性作为红粉金陵的风尘女子,便是不折不扣的边缘者;在《芳华》(2017)中,何小萍无论是在家庭、在文工团乃至在战地医院,直到最后精神失常,都是一个不能得到足够尊重与关爱的边缘者。而触发严歌苓创作《妈阁是座城》的是一个在澳门大赌场工作的女性,这使她意识到,鉴于男性在对财富的掌握上有着压倒性的优势,赌场固然是属于男性的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但这之中也有女性的身影,并且由于女性更为阴柔隐忍、至情至性,从女性的视角去透视这个战场将更有意义。男性赌徒们成为赌场中的弱者和输家是直观的,而女性在生活中被制约,在精神上成为弱者和输家却往往是看不见又不合理的,这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可以说,女性导演、编剧以及小说作者,往往让女性的过人力量,从残酷的边缘处境中迸发出来,让受众从女性个体的边缘处境中洞见宏大的历史或时代。《妈阁是座城》亦不例外。
二、《妈阁是座城》中女性的边缘性梳理
在《妈阁是座城》中,陈小小、菲姐等女性尽管也有着各自的酸甜苦辣,但受限于时长,电影无法对她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刻画。整部电影中,女性命运的支离破碎、性格的柔中带刚展现得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主人公梅晓鸥,她正是主创选取的一滴折射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的水珠。在《性别政治下的女性发展边缘化》中,杨凤指出,女性的边缘化有三种形式,即显性边缘化、隐性边缘化与反向边缘化,而在《妈阁是座城》中,这三种边缘化恰恰都在不同的时间段或场域中,出现在梅晓鸥的身上。
(一)显性边缘
显性的边缘化,主要体现在女性与男性之间有着明显的控制和依附关系,两性之间是尖锐对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长期承受偏见与压力,导致自我认识产生扭曲,身心不能得到健康发展。如《金陵十三钗》中玉墨等人长期出卖肉体,沾染了丑陋习气后,既无法得到男性的收留,也被自认为冰清玉洁的女学生嫌弃,而她们也自感卑微,她们的仁慈、大度难以为他人认知。在《妈阁是座城》中,生活于21世纪前后的梅晓鸥虽然命运没有这么凄凉,但是在和男性交往,尤其是和前夫卢晋桐在一起时,她是极其卑微的,男女两性的关系是极为畸形的。卢晋桐沉迷于赌博,一旦上了赌桌便不顾一切,在梅晓鸥怀孕数月之后也对她不闻不问,甚至在梅晓鸥前来与其大吵大闹,要求他离开赌场时,输红了眼的卢晋桐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梅晓鸥拳打脚踢。这一段关系也就随着卢晋桐的赌博恶习宣告结束,梅晓鸥决定自己养育儿子。赌场见证了梅晓鸥的第一次被边缘化。与之类似的还有史奇澜的前妻陈小小,陈小小也同样拥有一个嗜好赌博、背负巨债的丈夫,同样需要自己照顾儿子豆豆,这也是阻碍梅晓鸥与史奇澜相爱的原因之一。在这两段关系中,男性都缺乏对女性的重视,有着认为对方是自己附属品的偏见,女性被羞辱,被损害,被置于一种极为坎坷的位置中。
(二)隐性边缘
隐性的边缘化指的是在诸多外部条件的影响下,女性得不到健康、长足的发展。相对于充满了争执、交锋的显性边缘化,这一种对女性的边缘化是较为隐蔽和温和的,甚至别人在伤害她们的同时,她们也有伤害他人的能力。如《归来》(2014)中受特殊政治气候影响,自觉和不自觉伤害家人的冯婉瑜。在《妈阁是座城》中,梅晓鸥的职业是女叠码仔,即博彩中介人员,不仅从拉人赌博中抽取佣金,还与赌场一起与客户进行私下对赌,客户的输赢直接关系着叠码仔的收入,在赌场赌徒造的“孽”中,有叠码仔的一份力。这也就决定了她的生活日常就是陪客、担保、借钱、暗赌和追债,甚至需要帮助客户偷渡。这无疑是一个高度边缘化的、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职业,这一职业也只有在澳门这样赌博合法化的弹丸之地才有生存的空间,一旦客户离开澳门,梅晓鸥要追回数额不菲的赌债,就不得不饱尝艰辛,采取欺骗、威胁等非常手段。
当段凯文负债累累时,梅晓鸥不得不将自己在澳门好不容易买到的别墅抵押出去。在电影中,曾有一只海鸥撞在玻璃窗上惊醒了梅晓鸥,这就是电影对梅晓鸥职业的一种视觉隐喻,海鸥在电影中是一种孤独脏贱,吃烂臭垃圾,还不如老鼠的生物。也正是因为梅晓鸥的职业,段凯文虽然表面上对她彬彬有礼,实际上却瞧不起她,即使是在他落魄之际,都不忘以施舍性的姿态邀请梅晓鸥到他的公司工作。而梅晓鸥之所以选择了这一非主流的职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做单身母亲有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则像她所直言的,她希望能够通过挣赌场和赌徒的钱,以毒攻毒,报复卢晋桐们、史奇澜们、段凯文们。和梅晓鸥类似的还有菲姐。就像华仔对梅晓鸥说的:“洗码的人,只要不赌,就一定会做老板。”菲姐就成为了老板。她们都主动地投身于“毒”中,虽然拥有一定的财富,却依然是边缘者。而在后来,梅晓鸥也为自己的这一边缘职业反噬,她不仅平时极少陪伴照顾自己的儿子,甚至儿子也沾染上了赌博,这对于梅晓鸥来说几乎是五雷轰顶。
(三)反向边缘
女性遭受的反向边缘,即女性的部分特征或功能被过度地神化与歌颂,以至于女性被极大地限定了。如“贤妻良母”等,就是一种对女性看似赞誉,实则为拘禁的反向边缘。在《妈阁是座城》中,梅晓鸥被局限为一种博爱、宽容的“圣母”形象,或如严歌苓所说的,是一个“天使”,默默地承受他人给自己的伤害,总是体贴、理解和支持他人,这是她遭遇的也不自知的反向边缘,导致了她难以从困境中突围。史奇澜作为北京知名的雕塑艺术家,一开始就捕捉到了梅晓鸥身上善良的、对他人有拯救欲的特质,心心念念想为梅晓鸥塑像。史奇澜也确实用双手做出了一个怀抱婴儿哺乳的圣母像。结果他以进一步了解梅晓鸥的理由进入赌场,沦落为一个失去了家庭与前途、毫无体面的人。也正是因为以救赎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梅晓鸥决定要救回史奇澜。又如已经堕落成满口谎言、迷信自私的社会渣滓的地产大鳄段凯文,梅晓鸥依然对其心疼不已,同情他为了挽救自己的商业帝国而孤注一掷地一拖二十,感动于段凯文将本可以还给她的钱,给了曾帮他渡过难关,后来被抓了的大哥,交了他儿子在海外读书的学费。在这种母性光环的限制下,正如梅晓鸥对自己的评价,她也是一个执迷不悟的赌徒。
三、边缘女性艺术形象的建构意义
透过梅晓鸥这一全面被边缘化的女性形象,电影实现了对人性的反思。在阅人无数的梅晓鸥的眼中,男性们无论是有着怎样丰富的知识和人生经验、坚定的意志力和雄厚的财力,都无法从赌博中全身而退。人性在欲望面前是脆弱的,段凯文、卢晋桐等人无不号称要改过自新,但是他们的魂魄早已被赌博所夺走,只能挖东墙补西墙,尔虞我诈,包括史奇澜的远房表弟,也在稍微阔绰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投身赌场。他们也同样是显露了边缘人格,必将为社会主流群体孤立的人。而反之,女性则要善良、克制得多,如史奇澜铤而走险后还给梅晓鸥三千万,梅晓鸥却分文不动;又如在段凯文锒铛入狱的时候,梅晓鸥却依然前去探望他。
同时,电影还借梅晓鸥的经历,展现了女性有着扭转命运,将自己从边缘拯救回来的伟力。在《妈阁是座城》中,梅晓鸥在经历了一次次物质和精神上的危机后,虽然有着“赌感情”的缺陷,但她终究是心底光明、看事透彻,是能完成救人和自救的。对永远高高在上的段凯文,梅晓鸥在酒桌上对其予以揭露;对尚有收手希望的史奇澜,梅晓鸥以讲道理帮助他浪子回头;而最震撼的一幕莫过于梅晓鸥在知道儿子赌博后,将儿子赢来的大把钞票撒到浴缸里点燃,厉声斥责儿子的场景,在目睹众多男性被赌博所吞噬之后,梅晓鸥能够以对金钱毫不吝惜的态度和正理震慑住自己的儿子避免他重蹈父亲的覆辙。可以说,电影让观众看到了女性内心的强大,她们的主体性努力从未缺席。
在《妈阁是座城》中,李少红与严歌苓一起为观众展现了一个纸醉金迷、真情与假意共存的世界。女叠码仔梅晓鸥是电影中最为亮眼的角色,她游走于赌徒之间,与段凯文、史奇澜等人打着金钱上的交道,看尽了众生于赌场之中的嘴脸,而她本人也在经历着另一种意义的赌博,成为情场上的赌徒,在一场豪赌终结之后,她也完成了女性自我的重建。梅晓鸥的职业和生存状态等无疑是边缘化的,但是其内心感受、情感世界又是观众所熟悉的。李、严两位女性以包容、敏感而纤细的心,完成了对这一形象的生动刻画,留给了观众诸多关于人性、女性命运的珍贵思考。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边缘女性这一类型的角色,对于电影人构建某种和主流审美相对疏离的、独特的美学形态,保持旺盛而高质量的创作活力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