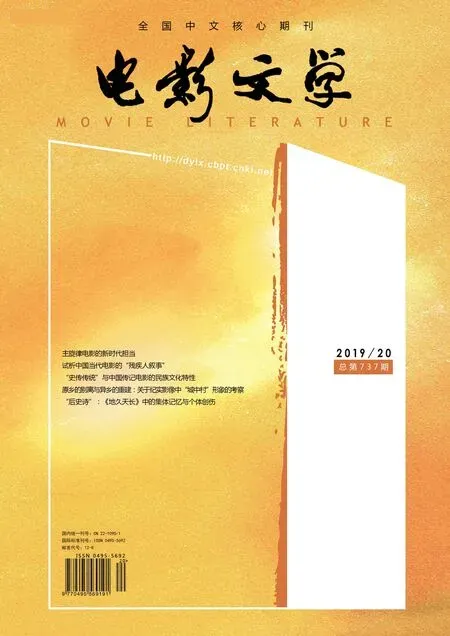《小飞象》与蒂姆·波顿的电影符号学表达
刘 阳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1300)
自克里斯蒂安·麦茨于1964年在《通讯》发表了《电影:语言还是言语》,创立了电影符号学以来,这一理论就为电影文本批评,乃至电影人对作品审美特性的建构提供了支持。无论对于有作者意识,渴望进行个性表达的导演,抑或是对于循规蹈矩完成产业化生产要求,力求实现最高效市场占有的导演而言,电影符号学都与其影片意义机制的建立紧密相关。蒂姆·波顿一贯以特立独行以及“戾气”“暗黑”著称,在他的《僵尸新娘》(2005)、《查理与巧克力工厂》(2005)等电影中,就已经设置了一系列隐喻和象征意味浓厚的符号。在接过迪士尼真人电影《小飞象》(2019)的导筒之后,波顿被认为转变路线,开始尝试走一条更为温情暖心的路线。但抛弃了骇人场景与人设,并不意味着波顿向崇尚“合家欢”的迪士尼妥协,更不代表着《小飞象》是一部低幼童话。波顿电影的内在美学特征依然在《小飞象》中得到了保留,其中就包括了指向性,寓言性极强的符号设置。
一、人物与物象符号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家索绪尔于《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言语活动=语言+言语”的公式后,麦茨深受启发而尝试对电影语言系统进行探索。在明确电影语言与天然语言有着多方面不同的基础上,麦茨认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可以用于对电影的分析的。在电影中,影像是其最小的意义单元,缺失了各种影像符号,电影也就无从谈起。各种人物、道具以及场景等,都是电影的“能指”,也即意符,电影人赋予其“所指”,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松散和偶然的,观众对“所指”的领悟程度,直接关系着其对电影的认同与欣赏。
人物与物象符号是电影中较为常见的能指。“人物影像,是指电影文本对真人的影像呈现,它是构成电影文本的最为常见的影像符号之一。”蒂姆·波顿电影中,人物往往就是文本中居于核心位置的符号,怪异的,超出人们现实经验的人物在波顿电影中屡见不鲜,而波顿对这类符号的生产,往往就有值得剖析的指涉意义。如在《僵尸新娘》中,死去多时,但依然戴着腐烂花冠和面纱的少女艾米丽就代表了依然保有真情的,善良无私的鬼。她所映衬的,正是如维克特等活人们,或失去灵性,或自私自利,一种另类的生命价值观由此得到表达。与之类似的还有如《剪刀手爱德华》(1990)中的爱德华,作为一个半成品机器人,爱德华是“非人”,然而他表现出了最可贵的人性,而相反,不能包容爱德华的人类文明世界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却了人性。
在《小飞象》中,先天性地怪异,长着一对奇大耳朵的小象笨宝,后天性地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的霍特·法瑞尔等人,就是波顿着力刻画的符号。笨宝的母亲是美第奇马戏团的大象珍宝夫人,笨宝也有着和母亲一样,成为表演大象的既定命运,然而笨宝的丑陋吓到了马戏团除了法瑞尔姐弟外的所有人,珍宝夫人作为笨宝的依靠,也因为伤人而被贩卖。霍特则原本是美第奇马戏团的马术高手,在失去一条胳膊后,他只能在马戏团心不甘情不愿地从事饲养大象的工作,再也无法攀上马鞍,成为聚光灯下的明星。人物在身体上的“非正常”导致了他们的孤苦无依和压抑迷茫,成为被社会和他人边缘化的人。同时,笨宝失去母亲,霍特失去妻子,他们的家庭也都是残缺,充满悲剧色彩的。正是在这种境遇中,法瑞尔一家与笨宝建立起了深挚的友情。最终,不同的“非正常者”找到了各自的位置:霍特在改组后的“美第奇家族马戏团”中继续表演自己喜爱的马术,并与美丽的高空女王柯莱特·马钱特组成了家庭,而笨宝则和母亲一起回到了丛林故乡,自由飞翔。人与他人的关系实现了和谐,人对自我也实现了悦纳。尽管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会飞的小象,观众也并非都身有残障,但他们依然能理解这些人物符号的所指,并给予回应。
对于物象的选择和塑造,也是影像符号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各种物的影像在电影中几乎无处不在,……就其意义指涉而言,它们一方面是电影的背景、衬托,一方面也可以是影片发展的线索,甚至也可以是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如在电影中,“羽毛”反复出现。由于笨宝在吸入羽毛后飞了起来,从此笨宝和法瑞尔姐弟都笃信羽毛是笨宝飞翔的关键,他们一次次在紧急关头想方设法地为笨宝提供羽毛。由于羽毛来自鸟类,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羽毛关联着飞翔的力量。如莱维·布津尔在对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神话进行研究时,就表示人们相信口衔或吞下羽毛,就能掌握鸟飞翔的本领。包括人类使用羽毛来制作箭,除了有物理学上的考量以外,也与这种“羽毛指向飞行”的心理暗示有关。基于这种认识,没人怀疑羽毛对于笨宝的重要性。然而《小飞象》最后揭示,笨宝实际上并不需要羽毛来激发飞行的能力,它的初次飞行仅仅是因为羽毛刺激它打了一个喷嚏。至此,羽毛在电影这一文本中,就成了一个独特而复杂的符号,即人们的具有安慰性质的心理依托,它是推力也是阻碍,人只有在摆脱这一依托后,才能真正地、全面地认识自己,羽毛原本的指涉意义被电影所改变。
电影除了在固有文本中能够变更物象符号的原本含义外,还可以进行符号的新创。如《小飞象》中梦幻乐园有一段让人目眩神迷的气泡表演,演员们吹出一个个粉红气泡,气泡逐渐变为无数个能够整齐跳舞的大象,大象再分裂成小象,而最终大象又吞噬了小象,在动画版本的《小飞象》中,吹出气泡大象的是喝醉酒了的笨宝,而在波顿的电影中,这一符号由马戏团的人类带出,气泡的出现和“合体”被解读为某种人类社会的规则,它们指向电影中梦幻乐园对美第奇马戏团弱肉强食式的吞并,人类居高临下对动物的支配等。视觉的美感,和帕索里尼所说的诗性意义在此得到了结合,沉重抽象的社会规则,被波顿以梦幻的、非理性的形象,简而驭繁地表现了出来。
二、动态的组合段表意
除前述可以被拆解为能指与所指的人物符号,物象符号外,电影符号学还借鉴了语言学中的“组合”“聚合”,提出了“组合段”概念。麦茨认为,电影的分镜头与蒙太奇构成了各种组合段,而它们也逐渐拥有了“句法”,如谢尔盖·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中,军队的开火、群众的奔逃与倒下等镜头的组接,就是典型的交替组合段,正与邪、无辜者与残酷者的对立就在这多个场景的交叉拍摄中被凸显出来。艾柯则在麦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层分节”理论,即电影这一代码系统中,存在着图像,图像历时性变化产生的运动,以及一系列运动的组合这三层意义单位,而优秀的电影导演,会妥善地安排这些意义单位。
在《小飞象》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图像的不断运动,在一组镜头中出现的大量元素,为观众传递着某种信息。如在美第奇马戏团被收购以后,麦斯·美第奇带着文件前去找范德维尔理论,范德维尔试图只发给原美第奇的员工一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理由是他们的表演只是对梦幻乐园表演的拙劣模仿。这是违背了范德维尔之前对美第奇的雇用原员工的承诺的。对此,范德维尔狡辩道:“我又没有说要雇用他们多久。”这是一个描述式组合段。此时从画面上来看,范德维尔处于中景镜头的中心,背后巨大的圆窗使得他显得颇为晦暗,范德维尔在谈话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内心的阴暗自私被暗示了出来,而从人物的动作上看,范德维尔在说话时一直在毫不客气地大吃大喝,发出咀嚼声,这不仅意味着他对美第奇的轻视,也暗示了他的家业,实际上正是建立在“吃人”(剥削员工)乃至“吃动物”(迫害动物)的基础上的。
此外,在电影的不同时间点出现,而表意有呼应关系的大语意群,同样可以构成组合段。霍特的几次穿脱假肢、笨宝的两次因火而飞翔等,就是这样的前后呼应的组合段。以笨宝的飞翔为例,笨宝的第一次因火飞翔是扮成小丑象,在美第奇表演小象消防员救火这一节目,恐高的笨宝无法顺利起飞,米莉则冒着火焰爬上梯子去给笨宝送羽毛,最终笨宝飞起来,惊艳了观众,也逃脱了火海;第二次则是笨宝为了救米莉和乔,在范德维尔引发的火灾中奋力飞起,驰骋在夜空中。前一次飞翔是被迫而悲伤的,是笨宝对马戏团制度的妥协,它的飞被人类利用来换取利益;而后一次则是笨宝主动的,是笨宝对马戏团的逃离,在这一次飞翔之后,笨宝将永远只为了自己而飞。主人公历经劫难,走向自由,就是这一组合段要表达的内容。正如艾柯指出的:“各种意义彼此并不沿组合段轴相互连接,而是同时出现,并通过彼此相互作用铺陈出一个宽广的含蓄意指网络。”无论是范德维尔的吃,抑或是笨宝的飞,以及场景中冰冷的办公室、灼人的火等,都是动态共存,共同完成表意的。
三、“镜像论”下的《小飞象》
麦茨在建立第一电影符号学,指出电影中存在符号与符号系统之后,又引用了弗洛伊德、拉康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结合了苏联蒙太奇学派的“画框论”与安德烈·巴赞的“窗户论”后,提出了“镜像论”,第二电影符号学就此产生。在第二电影符号学中,对电影的批评不再仅围绕电影本身,观众的观看行为,电影与观众的心理交流活动也被视为研究对象。
麦茨认为,观众在观影时,逐渐投入电影,如同婴儿在镜子中发现自己,观众也在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在心理上认同电影,“把自己的目光‘投入’事物上,被照亮的事物开始存于我心中”。从行为上来说,在《小飞象》中,观众对笨宝故事的观看,与电影中观众对马戏的观看,有着一种镜像关系。但波顿用摄影机视角,让小飞象的视线多次与观众视线重合,让观众似乎察觉了笨宝在天上高低起伏,不能完全自控的感受,从而使观众与笨宝之间产生了镜像关系。如当笨宝紧张地站在高高的升降台上,注视着下面喧闹起哄的人类时,观众突然能意识到,人类看似喜欢、追捧笨宝,但对笨宝的死活其实并不关心,珍宝夫人的被苛待、笨宝的安全网被撤走就是例子。电影中观众对笨宝稀缺的飞行能力的追逐,导致了笨宝的悲剧,马戏团这一适应于这种供求关系的产物,对动物来说是不应存在的,当笨宝向看马戏的观众喷水,让他们十分狼狈时,电影院中的观众反而会感到心情舒畅。最终观众将自己投射在笨宝,或米莉、霍特等人的身上,认同笨宝的逃走。当笨宝乘坐的船缓缓离开时,观众都松下一口气来,波顿所想表达的“任何一只野生动物都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的理念也由此深入人心。至此,整部《小飞象》成了一个符号,它以虚构的动物经历,在电影院封闭黑暗的“造梦”环境辅助下,引导着观众的意识与情感,让观众倾向于产生关于动物保护,反对马戏的意识。
在蒂姆·波顿的《小飞象》中,人物、物品等成为囊括了丰富信息的符号,参与表意。而在影像的历时运动,在电影连续,不中断的剧情中,还出现了值得玩味的组合段,意义不断地被生成,引发观众的思考。最终,整部《小飞象》成了一个指向爱护动物,拒绝动物表演意义的符号,无论观众是理性地拆分电影各元素,或是只是儿童式地对电影进行印象式体悟,都不难把握到这一意义。可以说,尽管拥有了迪士尼电影“合家欢”“大团圆”的特质,但波顿的《小飞象》绝不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