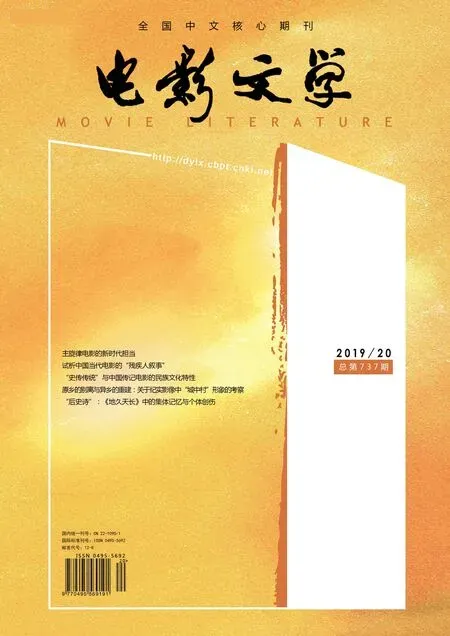“后史诗”:《地久天长》中的集体记忆与个体创伤
陈家洋 宋雪薇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提到“第六代导演”时,人们一般会赋予其较为鲜明的代际特征,诸如对底层人物的关注、纪实性的影像风格,等等。无疑,这些代际特征来自人们对第六代导演诸多作品的概括,彰显出第六代导演作为一个代际群体的整体性创作面貌。
然而,在中国电影发展与衍变、坚守与游移、突破与激荡的进程中,第六代导演也在不断演变和分化,所以,用整体性的代际视角看待多样、复杂的创作群体,以静态的代际审美特征来概括发展与衍变中的电影创作,有可能产生偏颇。事实上,当人们认为“第六代”往往聚焦个体命运、放弃宏大叙事时,一些导演已经将目光转向了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在《二十四城记》中,一直关注底层人物命运的贾樟柯仿照“口述历史”的方式,再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工厂的消失;《江湖儿女》则在开阔的时空背景下呈现出“江湖儿女”的命运起伏。这一次,同样对边缘群体与底层人物充满热情的王小帅,也以一个充满“时间”意味的片名“地久天长”,耐心地展现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
在中国电影快速的商业化浪潮中,人们对第六代导演的关注度正在减弱,而“第六代”作为一个评论范畴,也给人明日黄花之感。然而,兀自前行的第六代导演,似乎正在悄然间转向阔大的世界和深邃的历史,依稀体现出对“史诗性”的潜在诉求。而带着“第六代”独特印记的“史诗性”,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后史诗”的审美特征。
一、集体记忆:《地久天长》的“史诗性”追求
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史诗”一直受到美学家、文艺家的关注。黑格尔认为:“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者‘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1]108在黑格尔看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就是“史诗”的基本内涵。《荷马史诗》即是如此。在此语境下,“史诗”成为特定时期的特定“文体”。“特定时期”,指的是人类的童年阶段;特定“文体”,指的是讲述这一阶段神话传说,或人类重大事件的叙事长诗。进入现代社会后,这一文体随之消失,它成为人类永远不会复现的童年镜像。
作为一种“文体”的“史诗”虽然消失了,但“史诗性”却作为一种美学积淀留存在文艺作品中。“史诗精神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叙事艺术中得以延续,以审美范畴——史诗性的形式存在。”[2]从特定的“文体”,演化为一种跨越时空的“审美范畴”,“史诗性”成为人们对民族历史进行审美观照与美学表达的重要载体。
从字面意思来说,“史诗”包括“史”与“诗”两个层面。“史”首先意味着一定的历史跨度,比如《白鹿原》涵括了渭河平原半个世纪的变迁;其次意味着在长时段的历史跨度上,关注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而这些历史事件勾连出民族的发展进程,《白鹿原》中的内战、抗战可作如是观。“诗”则意味着文学性的表达。也就是说,它不是对历史的直接展示,而是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丰富的细节来讲述历史大背景下的世事变迁与人物命运,最终建构出民族的“精神图景”,诚如《白鹿原》扉页上所引巴尔扎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所谓“秘史”,自然包含着精神层面的内容。
历史变迁、精神图景,这些审美内涵,可以被视为“史诗性”的“质的规定性”。从这个视野来看《地久天长》,就不难发现该片对“史诗性”有着或显或隐的追求。
将《地久天长》放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序列中,可以看出该片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对长时段历史的观照,这可能也是该片给观众留下的突出印象。一个中国工人家庭在三十多年中的命运,被导演娓娓道来。虽然该片使用了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但时间脉络依然清晰可辨。这三十多年之所以被视为“长时段历史”,不仅因其跨度之长,更是因为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因改革开放而获得了长足发展,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地久天长》以具有时代感的影像呈现出三十年来生活空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街道拓宽,高楼拔地而起;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大医院取代了简陋落后的小医院;英明一家从拥挤的筒子楼搬进舒适的大房子;桌上的下酒菜从一盘花生米变成了大鱼大肉;出行工具由老式自行车变成了小汽车,而影片最后,丽云和耀军乘坐飞机返回故乡,更是凸显了出行方式的“现代感”。我们置身在社会变迁的舞台上,或许对这些变化习焉不察。然而,当影片以丰富的画面将这些变化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感知到时代的发展脉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更是人们观念的嬗变。影片中的几个主要角色,最初都在国营工厂工作,他们穿着单调的工装,过着集体化的生活。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大锅饭”开始解体。大家不再执着于统一标准,而是追求各自的道路;也不再故步自封,而是求新求变。社会思想则变得开放和多元。就此而言,影片所表现的时空,分明体现出“史诗性”的特征。
影片内容涉及诸多历史性的事件:计划生育,企业改制,工人下岗,南下打工潮,出国潮,房地产开发等。影片中,几个主要角色都在钢铁厂上班。很快,他们遇上了企业改制。为完成下岗指标,工厂说服“先进工作者”下岗。他们被召集到大礼堂,工厂领导以“我不下岗谁下岗”鼓励大家自谋职业走向社会。安静的礼堂里工人们神色凝重和慌张。最终,丽云不幸下岗,她脸上闪烁的泪光凝缩了改革的阵痛。在经历阵痛后,影片中人物的命运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美玉南下打工,耀军夫妇在承受失独之痛后前往沿海生活。英明投身房地产开发成了大老板。茉莉则走出了国门。
这些历史性的事件不仅是影片中耀军与英明两家人活动的背景,一些事件还成为情节的一部分。其中,计划生育,是对人物命运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影片的叙事内核是“失独”。耀军夫妇的失独之痛是双重因素的叠加:一是耀军爱子星星的意外溺亡;二是海燕态度坚决地带丽云去做人工流产,由此造成丽云不孕,让“失独”成为耀军夫妇终生的伤痛。如果说溺亡是个不可控的突发事件,那么流产导致不孕则是人为的结果。在计划生育的时代语境下,丽云被强行带往医院做手术。耀军虽有反抗,但终归无能为力,只能绝望地用手捶打着墙上“计划生育”的宣传画。耀军夫妇的内心创痛,都与英明一家有关。影片中英明一家三口对耀军夫妇的负疚与救赎让叙事充满张力。可见,计划生育,这一特定的时代话语,深深地嵌入人物的命运。一直以来,反映计划生育的影片并不多。就此而言,《地久天长》通过向观众展现特定时代语境下人物的命运,使自身具有较高的辨识度。
除了耀军与英明两家外,还有一条副线,就是新建与美玉相爱、结合的故事。实际上,没有这条副线,影片的故事依然完整。那么,这条副线承担了什么样的叙事功能呢?影片中新建最先感受到文化的解冻。他拿着录音机,听着邓丽君的歌,后来因为严打被捕入狱。出狱后远走海南,与美玉结合。显然,这条副线所承担的功能更多的是展现文化观念的嬗变。
可见,“时代变迁”不仅是影片的叙事语境,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片隐性的“主角”。对“时代变迁”的言说,让影片具备了“史”的内涵。而“史”的内涵又与“诗”的表达密不可分。影片借助人物命运的叙述,让“时代变迁”转化为民族的“精神图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形态、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都被影片所展现的“长时段历史”重塑。由此,影片所展现的三十多年中的历史事件与文化景观,都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诸如计划生育、企业改制、工人下岗、南下打工,莫不如此。此外,影片还用密集的细节强化了“集体记忆”建构。筒子楼、车间、具有时代特征的宣传画与标语、舞会、喇叭裤、双卡录音机、热水壶、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歌曲,甚至是孩子们玩的游戏机,都能够唤起人们对特定时代的记忆。进一步而言,“集体记忆”并非人们对时代表象的记忆,它意味着无数个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奋斗、悲欢离合等心路历程。事实上,影片所建构的“集体记忆”,正是民族的“精神图景”。凡此种种,都体现出《地久天长》对“史诗性”的追求。
二、解构宏大叙事:第六代导演的“反史诗”趋向
有学者将传统的“史诗性”审美特征概括为“民族性”“整体性”“英雄性”“全景性”四个方面。然而,在后现代语境下,全景性、整体性、英雄性等宏大叙事受到冷遇,而碎片化的“小叙事”,凡人、常人乃至庸人的“日常生活叙事”受到青睐和关注,从而出现“反史诗”趋向[2]。这样的审美趋向,契合了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实践。实际上,第六代导演从一开始便体现出解构宏大叙事的审美特征和“反史诗”的叙事风格。
论者常将第六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进行比较。这一方面是因为二者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另一方面在创作上又显示出质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第六代导演的影像叙事特征正是借助第五代导演的参照才得以呈现。虽然在快速的商业化语境中,人们已经很少使用代际视角观照当代中国电影,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第五代”“第六代”的确成为研究中国电影创作的有效视角。
在笔者看来,“第五代”“第六代”之所以成为有效的观照视角,根本上是因为这一视角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若合符节。都市化、世俗化的进程成为第六代导演创作的时代背景,而随着社会转型,时代的审美趋势也在发生变化,由此,第六代导演在对第五代导演的反思中开启了自己的创作之旅。早在1993年,第六代导演就对第五代导演的标志性作品《黄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部作品把黄土地上人们的生活“风格化”了,由此“导致了一种以浮浅的社会学、文学、文化学甚至精神分析解释自我作品的风格”,而这种混沌的、盲目追求风格化的时代应该结束了[3]。
“风格化”意味着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所展现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对“生活”寓言化的、隐喻化的表达。第五代导演大多在时代的动荡中有着切身的浮沉体验,这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比较自觉的反思意识。有论者认为,“第五代导演是主体意识自觉和强化的一代。追寻和建构历史主体性和大写的人的形象,一直是第五代导演的精神主流”[4]。也正因此,第五代导演偏爱历史表述与文化反思,对“宏大叙事”有着内在的追求。《黄土地》中,陈凯歌导演运用象征化的表达手段,淋漓尽致地呈现了黄土地上人们的坚忍。《霸王别姬》跨越半个多世纪,用宏大的叙事结构,表现出历史的动荡和民族的不幸。《红高粱》以隐喻性的影像语言,对民族的内在力量予以浪漫的表达。《菊豆》则批判了宗法秩序对人性的摧残。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第五代影片大体上是一种宏大的历史叙述,是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想象和叙述,即使叙述个人的事情,其象征隐喻的内涵又使之超越了个体”[4]。
第六代导演恰恰是将宏大叙事、文化反思意识,以及相应的修辞性的影像表达视作“风格化”窠臼。他们普遍缺乏第五代导演在时代中的浮沉体验,但他们成长于经济复苏的开放年代,都市化进程、世俗化进程,让他们更为关注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的生命体验,而不是群体的命运变迁。在第六代导演的创作视野中,“大写的人”转变为平凡之人、底层之人,他们身上毫无光环。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并非始于群体命运与文化反思,而是来自创作者对生活的感受,甚至是对生活的感觉。《北京杂种》《头发乱了》《长大成人》《小武》《十七岁的单车》等影片都可作如是观。当“风格化”消失后,“生活”以赤裸的形态出现在第六代导演的镜头前。当他们不再借助寓言化、隐喻化的手段后,他们便与生活“短兵相接”了,相应地,修辞性的表达转化为原生性的表达,“纪实”遂成为第六代导演的影像风格。
对平凡人物的关注、对生活的原生性表达,以及相应的纪实美学,都意味着第六代导演在创作上有着“反史诗”的趋向。这种趋向让传统的“史诗性”产生了变异。也就是说,当第六代导演希望在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上进行影像呈现时,“史诗性”最终结出了“后史诗”的果实。
三、个体创伤:《地久天长》的“后史诗”叙事
当第六代导演在长时段的历史跨度上展开影像叙事时,他们独特的创作美学使得传统的“史诗性”演化为“后史诗”。这种“后史诗”叙事,呈现出新的形态。“小民性”“日常性”是其主要特征,“小民性”意味着作品所表现的人物不再是英雄,也不再是社会上的精英,而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日常性”意味着作品所表现的乃是世俗生活[2]。“小民性”和“日常性”,都是解构宏大叙事的结果。对《地久天长》来说,“后史诗”叙事还意味着修辞性的影像被纪实性的影像所取代。
《地久天长》围绕个体创伤展开“史诗性”的叙事。影片中耀军、丽云夫妇痛失爱子,这对耀军、英明两个家庭来说,都是创伤性的事件。这一创伤性的事件虽然也与时代有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让耀军夫妇无法再生孩子,这让创伤无法随时间而平复,但总体而言,这一创伤更多地与个体命运有关。它并非历史性的事件,而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而影片也用生活化的影像展现了时代的发展与世事的变迁。
《地久天长》中的人物毫无疑问都属于“小民”,他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有着芸芸众生的期待与快乐,也有着芸芸众生的性格弱点。在影片中,浩浩一直没有勇气坦白自己的过失,多年来选择逃避痛点和隐瞒真相;主角耀军夫妇,没有宏大的理想,只想得到和谐的家庭生活,而从耀军出轨茉莉,也可以看出他们在道德上并不完满。
影片中,耀军夫妇默默地承受了命运所带来的伤痛。对于堕胎、下岗,耀军夫妇显得非常“被动”,他们没有抗争,也没有愤怒的呐喊,在时代的浪潮中他们选择了隐忍,选择了承受。被动性,是“小民”,而非“英雄”的性格特征。然而,小民有小民对待命运的方式,他们远走他乡,在陌生的地方忘记伤痛,在光阴的流逝中抚平伤痕。他们既有小民的沉默,也有小民身上韧性的人格力量。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第六代’导演影片中的人物并不是历史英雄,而时常是一种人格英雄”[3]。事实上,正是人格的力量让影片中的每一个人达成了与现实的和解,也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在影片中,丽云说:“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就是等着慢慢变老。”这是有别于“进步叙事”的时间观。在传统的“史诗性”作品中,主要人物承担着“进步叙事”的功能。也就是说,主要人物的性格、命运、主体精神,都与时代的进步息息相关。然而在《地久天长》中,承受着失独之痛的耀军夫妇,却似乎脱离了火热的时代。他们生活在时代的边缘,那里安静如常,时间的流逝不是以“变化”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不变”的形式悄然发生。当耀军夫妇时隔多年回到旧居时,发现老屋子中的各种摆设一如几十年前,在老屋子里,时间停滞了。只有楼道里微微闪耀的“按摩店”的牌子,显示出时代的巨大变迁,反衬出耀军夫妇与时代的疏离。影片由此显示出与“进步叙事”的差异,而这一点,正体现出“后史诗”的叙事特征。
与解构宏大叙事相适应的,是“去修辞化”“去象征化”的影像呈现方式。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第六代导演纪实的影像风格。大量的家庭生活画面,建构起影片的“日常性”。影片中的一些画面,比如频繁出现的丽云炒菜、耀军就着花生米喝酒的生活场景;耀军夫妇家中因大雨进水,杂乱的物品在水上漂浮等画面,都具有很强的写实性,甚至因此影响到画面的美感。如果说美感是一种修饰,那么影片则为了写实的效果拒绝了这种修饰。生活本身,而非对生活的修辞,成为《地久天长》的影像主体。
总体而言,在商业化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第六代导演的代际特征正在模糊;作为一个评论范畴,“第六代导演”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创作者的艺术探索。在《地久天长》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在长时段的历史跨度上对集体记忆的影像建构、对“史诗性”的追求,但这种追求有别于传统的“史诗性”表达。导演带着“第六代”的印记,将平凡人物的命运放在开阔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表现,“史诗性”的追求最终演绎出“后史诗”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