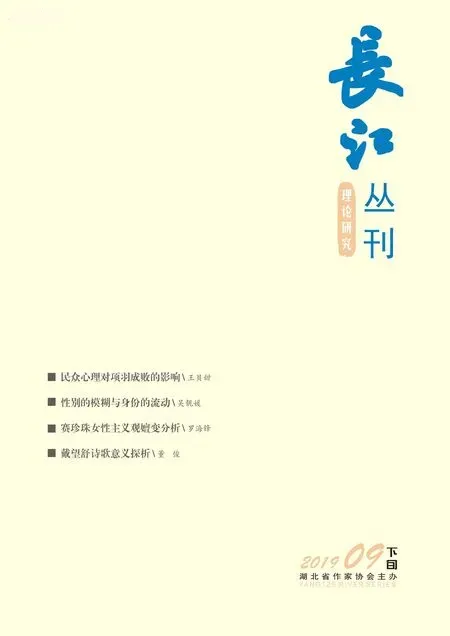性别的模糊与身份的流动
——《蝴蝶君》的酷儿理论解读
■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1904年,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以精致的结构和浓郁的抒情征服了观众,折射出西方对东方、男性对女性的优越想象。1986年,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发表话剧剧本《蝴蝶君》(M.Butterfly),这是作者对《蝴蝶夫人》的反讽之作。剧本根据一名法国外交官被假扮女人的中国男子欺骗多年的新闻报道而创作,但黄哲伦为避免猎奇的色彩,有意不去了解过多细节。他说,“从我的观点看,一个法国外交官被一个乔装为女人的中国男人所哄骗的‘不可能’的故事,似乎总是完全可解释的;考虑到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同样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误识的程度,这种重大的错误会在某一天发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剧本讲述法国驻华外交官伽里玛(Rene Gallimard)迷恋中国京剧旦角宋丽玲(Song LiLing),直至后来真相大白,伽里玛梦幻破灭而死。该剧情节与《蝴蝶夫人》形成强烈对比,值得注意的是,要实现对《蝴蝶夫人》的反讽,也借由一个反传统的东方女性来颠覆柔顺软弱的刻板形象。显然,《蝴蝶君》的性别处理别具深意。以酷儿理论(Queer Theory)来打量《蝴蝶君》,可以发现:宋丽玲和伽里玛都具有性别的模糊性和身份的流动性,这使得《蝴蝶君》把传统二元对立模式转变为一种非固定的关系,一种变化中的张力。
酷儿理论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它“既不是单一的、系统的概念,也不是方法论的框架,而是对于生物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望之间关系的思想研究的总称。……对生物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体系的批判;对生物性别倒错和社会性别倒错的身份确认的研究……”。而《蝴蝶君》的反讽和颠覆之处也突出体现于性别的模糊性处理。当黄哲伦完成《蝴蝶先生》(Monsieur Butterfly)剧本时,妻子认为这个题目太直白,于是就有了“神秘和暧昧得多”的 “M.Butterfly”一名。M代表的到底是Madam,Mademoiselle,还是Monsieur?显然作者对男女性别进行了有意消解,它暗示读者,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会给阅读带来障碍。它“建构”而非“表现”了一个女性主角形象。但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一个表面的真实与一个‘非真实’并连在一起,而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而把次要的那个性别面貌当做不过是幌子、游戏、谎言以及幻觉。”刻意的伪装,以及优越的西方姿态和浪漫的东方想象,共同建构出了伽里玛眼中的宋丽玲形象。
在最后的见面中,两人的对话充斥着对性别确认的渴望和紧张,双方处在一种流动不定的张力之中,展现出“无法用性别与性相话语界定的非男非女、时男时女的身体及其颠覆力量。”同时,作为传统性别关系中强势的男性一方,伽里玛却没有体现出任何优势。他从小就不受女性欢迎,这一点直到身陷囹圄他仍耿耿于怀:“从来没人觉得我聪明。事实上,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就被评为‘最不想邀请来聚会的人’”。在恋爱和婚姻关系中,他也没有发言权和主动权,婚后不育更是让他丧失了自信心,习惯于面对杂志女郎在幻想中满足自己的控制欲。由于《蝴蝶夫人》中的平克尔顿也“长相平庸、不够聪明、懦弱无能”,所以他也幻想着如平克尔顿一般找到他的东方“蝴蝶”。在与宋丽玲的关系中,他在根本上也仍然是用幻想来满足自己。伽里玛坚持“认为”宋丽玲是女人,即使最后真相大白,他仍在回忆往事时说:“曾有一个完美的女人(the Perfect Woman)爱过我”。他在法庭上表露心迹:“我心里有一种感觉,虽然我的幸福是短暂的,我的爱情是个骗局,但我的理性却不让我知道真相,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伽里玛种种不合常理的表现,说明他对于宋丽玲的真实性别是有所觉察的,但他始终不愿放弃男性优势和自我幻象,直到宋丽玲脱下衣服让他亲眼看见“她”的男性身体,他开始真正丧失制造幻象的理由。当宋丽玲追问伽里玛:“那么——你从没有真的爱过我?只有当我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才爱我?”伽里玛则回答道:“我是个男人,可我爱上了一个由男人创造的女人。别的一切的东西——都无所谓了。”最终他承认,“在公开场合我始终否认宋丽玲是个男人。因此我上了头条,也让我那些法国同事无比难堪……但是,当我孤身一人在这件囚室里时,我早已经接受真相。”当伽里玛意识到美丽的幻象无法再继续,巨大的性别和身份危机终于使他难以面对;在生命最后一刻,他甚至把自己称为“蝴蝶夫人”,不妨说,这是一种性别的象征性互换甚至融合,他与自己制造出的幻象难分界限,他也有意抗拒着界限。因此,“爱情没有变化,对象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欲望的结构”,双方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不断流动着的、由规范(性别)、表演(引用)和主体(身体)三者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自我建构的完整过程。
用流动取代对立和僵化,正是《蝴蝶君》的重要主题。性别的模糊性直接导致身份认同的变异,最终造就了身份的流动。《蝴蝶君》首先展示了“传统模式”,即表层所显现的、符合观众认知经验的模式:男性高于女性、西方优于东方。这也是《蝴蝶夫人》所遵循并赞美的刻板想象模式。但《蝴蝶君》在传统模式之下还隐含着“颠覆模式”,也就是表层之下所要揭示的真实关系: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受到嘲弄和挑战。正如学者指出,“如果说宋的变身是对幻象的揭穿,那伽里玛的变身就是在向我们讲述幻象的致死之后果。”显然,伽里玛对于性别、身份及关系的刻板印象或“预设模式”导致了他的悲剧。宋丽玲在法庭上供述的两条原则也反映出这一点:“原则一:男人通常相信他们愿意听到的。因此一个女孩子可以随意撒谎而男人总是会相信。原则二:一旦一个西方男人来到东方——他马上就已经目眩神迷了。”甚至当“蝴蝶夫人”幻象不再,伽里玛仍然不甘心,将自己变成她,制造出短暂幻象并以死亡将其定格。但如果注意到伽里玛此刻的几分悲剧味道,以及他自杀后宋丽玲在烟雾中喃喃自语的“蝴蝶?蝴蝶?”便不能简单地说强弱模式完全被颠覆了,因为此时呈现的是一种流动含混的情绪。
因而,通过男女性别的模糊化处理,《蝴蝶君》还呈现出一种身份与关系的“流动模式”。酷儿理论的身份策略强调性和性别是一种建构,它要解构身份,提倡多重性、变化性及流动性。作者意在消解对立和误读,剧中的性别模糊化是别具深意的。因而,《蝴蝶君》在反讽西方中心主义时,不是单纯地通过关系的倒置来实现文本意图,而是有意模糊性别界限,引导读者探寻身份流动之中的平等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