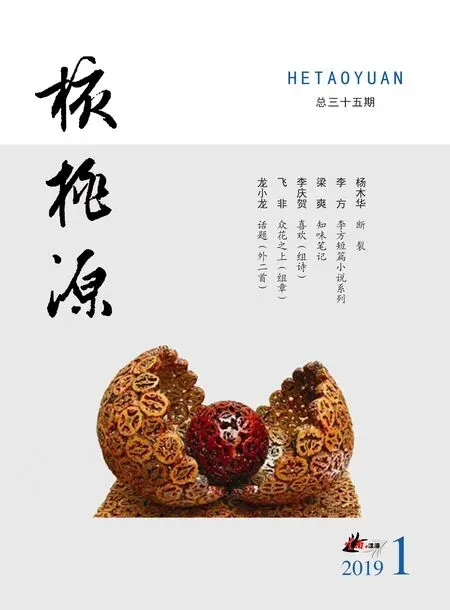众花之上(组章)
飞 非
在三千亩菊园里占园为王
披黄金甲而来。
我已买下这里的花香虫鸣,闲月轻风,并且赎回空中的蔚蓝。
这么多年,我依旧没有学会谦逊。
我想,我还是应该更昂扬些,用我三千亩晴朗的心情照亮三万里河山,
时不时,让我的小资情调泛滥一下。
或者,我顶黄金盔,掼雪白袍,
在菊园里操兵练马,威风凛凛地在三千亩菊园里占园为王,
抱香而死,抱香而生。
这黄昏让我忧伤了三千年。
一掌秋水还没有拍出,月落,乌啼,秋天就到了尾声。
人比黄花,瘦得弱不禁风,一滴金黄的泪顺着秋天的脸颊流下来。
我还要多少次为炉火添柴,甚至将自己突入烈焰之中。
金凤涅槃。仍是一口地地道道的乡音。
这一生的坚持,只是为这一刻的表达。
众花之上,只有我把秋天开成自己的春天。
菊园,戏园
一年四季绵绵不断的乡愁。心上秋。
秋水盈盈处,便是我的戏园了。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蜂一蝶都是我的票友,这里的每一朵花萼都是我的戏骨。
菊花台上,我水袖飞扬,像一枚轻盈闪过的蝶;
兰花指处,我像是你的纤指在触摸屏上点击的临梦伊人。
一举手,一投足,一转身,多么美。
一些台词是溢于表面的流云,风里的清芳。还有一些潜台词,你明白的,
藏在眼神深处。
而此刻,帘卷西风,我只能这样像蜘蛛一样,吐出金丝,
一层层包扎着我的殊荣,内在的伤口也给裹住了。我不是秋水,
秋水的伤口会自己抚平,
只是它的性子越来越冷僻孤傲。这也契合了我的暗伤。
就像一缕炊烟成为一缕青烟。
我能说什么呢,
太多的村庄,都有着相似的命运。
有的谢幕,有的锣鼓紧密。
一杯菊花茶,饮出岁月的滋味
一朵菊,一个秋天还没开够,
还要在一匹波浪里驾雾吞云,慵懒地伸展腰肢;
一片茶,香了一个春天,
又在一泓清冽的水中洇化莹润,扶风一香。
一朵菊,一片茶,相遇于某个日子,像一对初恋的情侣,谈起了恋爱,谈好了,
住进同一只杯子,就是一杯菊花茶了,就像在一个新开发区组建一个新家,
共写一部新“春秋”。
这一春一秋就是炊烟和水煮沸的日子。
我把这一杯水,看成了家。
清贫的,淡淡的,云烟俱净。有浓缩的亲情。
一苦一甘在水中相互沁润,像一次共同的抒情,一次不约而同的互勉,
也像一场坎坷后彼此之间的相互慰藉。
不得不说,痛是对生活的另一种答谢。
这就像一杯菊花茶,饮出岁月的滋味。
我的沉醉,又在另一种艰难中延续。在杯中,我看到了一条河流,
也在艰难地延续。
狗尾巴草
像狗一样活着。乞伶,摇尾。
即使立在墙头,遭遇的也是白眼。
一直是这样,摇摆不定,见风使舵,
只有脚,纹丝不动,像枚钉子,钉在泥土里。
一直是这样,风来时低头,雨来时弓腰。
一直是这样摇摇摆摆地卑微地活着,没有仇恨地活着,没有气节地活着。
一直是这样,被呵斥,刁难,排挤,打压,嘲讽。被顽童玩于股掌。
一直被这样称呼,没有骨头,或软骨头。
当一场狂风暴雨,砍断了路,掀翻了屋顶,拔起了树根,街市成为河流。
曾经道貌岸然的君子们惊慌失措。
只有狗尾巴草坦然,伫立在风雨后的阳光里,慵懒地微笑着伸伸腰肢,耸耸肩,依然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
画地为路或画地为牢
一
此时,我正端坐于城市的层楼之上,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遥望高远的天空,似乎感觉自己也很高大上。
“下来吧,这不是你的,可以走了——”。城市的木然而冰冷的声音敲落目光。
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我只是想停留下,看最后一眼。
而冷冷的声音,像鞭子把我抽到下一站。
下一站,仍是他乡,我听到又一声冷笑,被路上风吹散,
下一站,下一站 ,每一站我都画地为牢,
离开的时候,真的不知,那些酷似牢房的楼里,
囚禁了谁。
二
我画地为牢,也画地为路,画自己的远方,画着越来越长的乡愁,我画下的九万里河山都不是我的。
脉络分明,泾渭分明,一边是越来越炫的街灯丽红,一边是越来越暗的灶膛炉火。
不问来,不问去。
只在年关。
那羊肠小道在村头有隐约的泪光,看一枚叶子踉跄的抵达。
三
我想回家。回家,陪那个总和影子喝着闷酒的人干一杯,
把那些城市码头站牌斟进杯里沉下,再举起,两只杯子互相取暖。
回家,陪那个总和老母鸡唠叨的人一同唠叨,那些鸡鸣狗盗鸡飞蛋打的琐碎和那些城市长长的故事,
一个夜就能掉下来。
回家,多喝一口井水,下一次背井就轻一些。
那条河流的远方
卷水重来,我依旧拽不回那条河流。
那条河流是她带走的。炊烟,是那条河的一部分,流向天空,
伸出过我梦幻的旋梯。灯光,也是那条河的一部分,“月儿明,风儿
静,树叶儿遮窗棂呀。。。”那养鸟人的歌声静静地躺在灯光里打着
瞌睡。
她为我盖着被子,月光为她盖着被子。
星星掉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掉到梦里了。
那灯光仍在照耀着我的行程。在我走过的路上,仍有轻言细语的抚慰。那灯光里藏着我最初远行的干粮。
她收走了那条河,留下了那盏灯。
一个人远去,
一个人夕光深处喊向远方的祝福。
还有什么更为疼痛的东西。
我将如何告诉那个影子,一个人独对苍凉的夜,一只青筋凹凸的
瘦手,是路,也是河流,曾经在地图上千百次重复我走过的路。在大地
的掌纹里,我是否又重复她走过的路呢?
远方有更远的孤独。
步步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