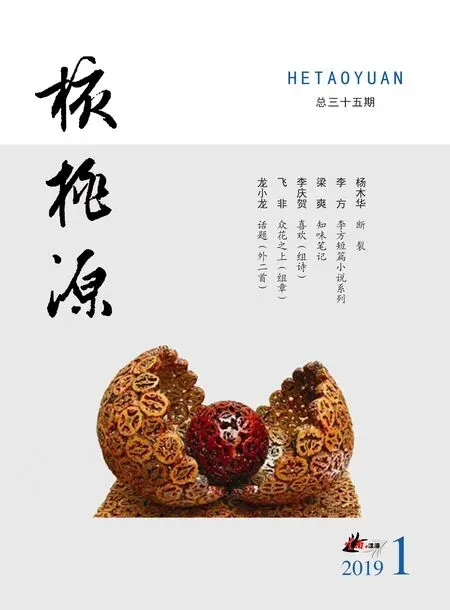断 裂
杨木华
1
时隔两年,我重返那个叫田心的小村庄。这是水瘦山寒的时节,我如约而来,是会会老朋友,遇遇重瓣梅花,再走走金盏河谷。
不来金盏两年,有疏远感觉的不只是河流,更有老朋友阿标。阿标四十多岁,上有年迈的双亲,下有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生活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如今一切都好起来了。阿标是我的初中同学,毕业后回家务农,但我俩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对他的感激要向前推十五年。那时,我妻子得了很复杂的肝病,住院百日未愈,他拿出祖上珍藏多年的野熊胆服用后,病神奇地好了,感恩也就此埋下。
腊月间阿标宰年猪我都会到田心闲一天,这是我与自己的约定。有时候他很忙,我就自己乱逛看风景。我师范毕业时分配到金盏教书,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有感情,加上阿标,这一切都带上了深情。离他家不远的台地中那棵重瓣白梅,也是我一次次抵达的地方。久坐梅树下,一任清风来,很多旧事渐渐释怀。我也一次次走进金盏河,怀念年轻时河谷里发生的故事。在购买了小数码相机后,我到梅树下拍花,走入河谷拍水,换了个视角看风景,很多些微之美定格在时光之外。可连续两年,俗事缠身的我没抵达田心,一种陌生感开始横亘在我们之间。于是,冬月我就主动电阿标,准时出现在他宰年猪的现场。吃过早饭,拍倦梅花后,我带上装备进入金盏河。
今年,我鸟枪换炮重装而来。小数码两年前被我摔坏,好友宏观建议我买了单反,配了脚架等附件,可以快意拍水。那个小数码,我付了三百五十元钱,请一个维修部修理,想着修好后给孩子用。哪料,后来那个修理店的小师傅玩失踪,小相机也就尸骨无踪让人空惆怅。
在金盏河最外边的瀑布前,我支好脚架,取了UV镜装上减光镜,用长曝光拍摄丝绸质感的流水。拍完继续深入河谷,在第二个瀑布前拍摄后,取了减光镜拍摄岩石时,才发现先前取下的UV镜不见了。于是原路返回寻找。可惜,寻遍来时路不见镜片。
断裂。我的相机与第一个UV镜,就这样发生了断裂。
后来宏观安慰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是,断裂已经发生,新的来了,能完全弥补失去的那些裂痕吗?
遗失一个小物件,其实,就是告别一段记忆。
2
喜欢行走山野的我,曾遇到不少断树。有时是一整杈断下,一头在地面呻吟,一头在空中叹息。一棵树断裂了一杈,与母体的断裂,与过往时间的割裂。这样的断裂是一个意外,可更多树木的断裂是人为割裂。一部分树木终将成为木材。一棵树与大地断裂,成为木材。木材之内,木质与木质断裂,成为木板,木板内部再次断裂,于是出现了一个窗:向外联通世界,向内探求隐秘。树木的故事,大多隐秘在年轮之中,外行人读不懂也看不透,我们往往对那些外在的似乎隐藏着故事的断裂更有兴趣。
有时候,看见一个人明显外露的伤疤特别是刀痕,猜想自然生发:断裂皮肤的背后,是否有激烈的故事发生?脸谱化影视时代,那些面部皮肤断裂的形象,往往和反面角色有关联。好在,如今的时代,我们都不再只是看脸吃饭,但脸依然是重点,某些痕迹依旧隐秘着属于断裂的故事。我左手大拇指的手背一侧,有一个五厘米左右的刀疤,那个伤口,承载着小时候的疼痛记忆。
那是没有零食的时代。某天下午,我在木瓜树上摘得一个黄透了的木瓜。左手持木瓜,右手拿家里的杀猪刀,准备削木瓜吃。可一刀下去,木瓜翻滚掉落,刀锋在手上滑过,也许是刀太锋利,血没有及时出现,我看见了白色的皮下组织和牵连的筋络纹路,丢了刀的右手一把压紧伤口,哭天喊地跑回家,母亲用青蒿止血之后用布一包我似乎就忘记了疼。如今早还记得看见刀口不出血时的恐惧,却记不得伤口什么时候愈合,唯有疤一直在眼前。如今,看见那个断裂的皮肤,就想起那些贫瘠的童年生活。这样的故事,只能在纸上说说,如今的孩子怎么也不会相信竟然有这样的故事发生过。
童年时代,我还干过一件寻觅藏宝图之类的事情。那个时代,武侠小说看多了的我,对身边的物事都喜欢用探奇的眼光审视。某天练习毛笔字后,突然发现我的小方形铜墨盒盖上竟然有一个断痕。那痕迹在墨汁浸润下,似乎隐含镶嵌的故事。痕迹的背后,说不定就是藏宝图,说不定就是惊天秘密!
找来小刀,跑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沿着断痕抠,再用刀尖撬。折腾半小时之后,那个断裂痕迹被我清晰剔出来。奇迹就要生发,我大气不敢喘,心都提到嗓子眼,一使劲,一小块铜片撬了下来。可是,惊天秘笈根本没有出现,断裂的下面就是墨盒本身——那仅仅是盒盖的铸造瑕疵被弥补掩盖的故事。
小时候,对这类断裂的探索其实还有很多,只是,结局都是自娱自乐的搞笑。后来的后来,我见到的断裂,残酷却显而易见。
年轻时,某一段时间,我记得整个大理的苍山西坡都在疯狂寻找一种名叫红豆杉的树木。找到之后,最初是砍枝叶出售,不知何时树干本身也遭了殃。红豆杉是一种传说中可以提炼出治癌药的植物,那时的乡村,对癌症并未清晰认知,但恐怖的传说侵蚀了人心,很多人也用上了红豆杉切菜板,更多的红豆杉树木因而被盗伐。记得2003年我带着胶片相机到苍山西坡一个叫三叠水的地方拍摄瀑布,在那个河谷里还见到两人无法合抱的红豆杉,那时我也才第一次认识这传说中的神奇植物,也庆幸苍山西坡的博大与包容。可时隔十年,当我鸟枪换炮带着数码相机再次去到那个河谷拍摄时,红豆杉早已消失无踪,幽谧的河谷中再也没有红豆杉生长过的一点点痕迹。物种的自我传递,就这样断裂。后来,我在几个城市边缘的高海拔处,见到不少人工种植的红豆杉,那些红豆杉长势喜人,可让我无端忧戚:红豆杉在自然中的传宗接代就此断裂了吗?
其实,这样破坏生命传递的事情,我自己也干过。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读初中时假期中的我,生活贫瘠自然向苍山伸出索取的手。我挖卖过三颗针。三颗针是一种小灌木,属于中药材。我们背着锄头砍刀,先用刀砍去其外长的枝条,再挖其根出售。一角钱一斤的根,那个假期我挖了数百斤,消灭了的树,何止几百棵!你以为,这就是我干的坏事的全部,不,如今想来,我干的最缺德的事是剥厚朴树皮。
厚朴,木兰科落叶乔木,叶大花大,花美花香。谈到花,是现在的我的视角。今年春天,我多方打探,终于获知苍山西坡如今还有大片的古玉兰和古厚朴,花开时节,一山靓丽一谷飘香,我和在西坡深处的牟忠老同学说好,花开时节带我去拍摄。当年的我,却从没有注意过花开这类事情。我们关注的是厚朴树的皮。我们几人合作砍倒一棵厚朴树,一米一段用刀环割后,再竖剖一刀,厚厚的树皮就被我们完美剥下来,一人背上一大捆回家,阴干后到街场出售,换得微薄的收入。那时,并不觉得这是杀鸡取卵,反而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如今当然不会再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了,更多的时候我就用镜头诉说热爱,期待唤起更多保护意识的觉醒。
可说不干难道就真的金盆洗手了?其实,剥皮这类缺德事,去年我还干,虽然依旧是不得不干,虽然刻意保护性剥,但依旧是深深的伤害。我患慢性咽炎,久治不愈乱投医。有个老中医建议用橄榄树的内层皮泡水喝,说吃一段时间炎症就会好。那天,我和阿真到一个叫小春箐的水库边钓鱼,喉咙正难受,看见岸边有不少橄榄树,老中医的建议立即浮上心来。阿真媳妇在那里守水库,于是,和她找了一把菜刀,就去剥树皮。那些橄榄树大多小碗粗,砍了剥伤天害理,我就一条枝干选四分之一割一条皮。时值春天,橄榄树本来厚实的外皮,因为正上水很好剥离,可恰巧是这样的容易,让贪婪占了上风,自我欺骗地安慰对树没有影响。割了十来杈树,回头看见那些割除了部分外皮的橄榄树,断口处一滴一滴正往外渗出汁液时,我后悔了,眼泪也差点掉下来。那后,我再也不去割橄榄树皮,管他是不是仙丹妙药,树的泪流入我心,再不做这个让外皮和内心断裂的事。慢性咽炎本来就无法根治,我要做的是按医嘱,戒酒戒辣,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强化自身抵抗力,让疼痛与身体断裂,而想要依赖某一味药物来切断疾病与身体的断裂,这样的期待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
可是,植物界的某些断裂却是人们刻意所为。这个初冬,我在一个苹果园中走过,见到工人对苹果树的修剪,那才叫一个狠。枝条高处自然是不允许长了,可密处竟然也不允许长。大根小根的枝条被剪得零落一地,这个还未抽芽开花的时节,剪成光秃秃的枝干简洁成一副中国画。我知道有修枝一说,可没想到是这样凶狠的修剪。果园主人却说:“就要这样修剪了。留下的枝条,挂果早已足够,剪去多余,省了疏花疏果的繁忙。”这些枝条与母体的断裂,竟然是为了挂果。牺牲了部分,断裂了细枝末节,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效益。可我却还有疑问:这样狠的修剪,剪的人不心疼,可树就真的不疼么?面对果园中一堆又一堆的枝条,我没有那样问,可心却真实地疼了一下。
后来,我见到更多的对核桃树的羞羞答答的修剪。那是过年回故乡见到的。故乡二十年之前大量种植核桃树,精心抚育之下,树自然是疯狂地长,可十多年前看着稀稀拉拉的核桃树到如今早已拥挤不堪。拥堵带来的自然是空枝。于是,故乡人在犹豫多年之后,开始了对核桃树的修剪。有的还不忍心,只对核桃枝条作剪断。有的一狠心,已经整棵整棵地间隔砍除。大量枝条就那样堆积在树下,再也无人过问。枝条与母体这样的断裂,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本无可厚非,可是,并没有征求过树本身的意见,就直接让他们断裂。我担心,某种简单粗暴的种子,是不是会在这样的行动中潜移默化传递给大自然?
这样的断裂,虽然残酷,可物种依旧留存下来,抑或者,精选下来的物种,也许会有更强大的遗传素质。可是,强烈的人类参与,是否会导致物种更快的消失,是否会导致某些变异的不可控?
我见过一棵古核桃树,也许是早年的某个雷雨之夜,主干断裂枯死,可后来断裂处长出新枝,且磕磕碰碰中竟然重新长成大树。我遇见的时候,一窝喜鹊已经在树顶搭窝欢叫。可那些曾经的断裂,依旧很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某些断裂,是缓慢地不知不觉地行进,等我们突然警觉时,溃败早已不可避免。喜欢记录片的我,看到太平洋一个小岛上有一种美丽的挂果乔木,靠种子繁育后代,那树年年开花结果,可近一百年来,岛上再无此种幼树出现。等老树枯死,一切就会结束了吗?生命的传递,难道就此断裂?科学家研究很久之后终于弄清楚,该树的种子自身无法发芽,需要经过某一种鸟的肠胃消化一遍才能发芽,而可悲的是,那种鸟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消失了。很多断裂,难道都这样不可避免?后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才知道有更多物种的遗传密码竟然隐藏在另一相关物种的生命之中,一种生命的延续竟然需要依赖另一物种来承担,物种间的相依为命,竟有如此清晰的存在。
据研究统计,在地球上,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植物界的断裂,更多的是外界的干扰与破坏。我不知道,人类的发展密码,将来究竟依赖谁来传递?
当断裂成为一种常态,人们的神经,似乎渐渐被麻醉,生物链的断裂早已不是秘密,可很多人却依旧视而不见。
我生活工作的小城,被一条叫江而实际是河的水流环绕而过。南丝路穿老城而过,旧时唯一的过江处为云龙桥,古老的铁索吊桥晃荡在清澈的流水之上,桥头的古榕下闲坐几个白须飘飘的老人,这本该是寻常可见的景致。可如今,树依旧茂盛生长,桥依旧古老着自己的古老,流水在日渐瘦弱的同时还发生了颜色革命。清澈已是昨天,如今的水,完全与清澈这个词汇断裂了,浑浊才是正常状态。每年,不正常的状态只出现几天,就是春节前后那几天,流水终于也得过年,回归清澈这个词语——那是沿河而布的挖沙船沙场停工休息的日子。那几天,河流东岸高地上的竹林寺木棉花开,我约了宏观去拍摄。那天,电话中的他有点懈怠,我告诉他:河水清了,来吧!再不来,如此场景一年之后才会有或者永不再出现。他很快前来,我们拍下了以清澈的河流金色的菜花为背景,以怒放的一枝木棉为前景的数张照片,很多人看了惊奇不已——见到水清花放太难得了。这些年来,因为很多不正常,本该正常的景致反而成为奇迹。
河流不再清澈,这只是河流与常态断裂的某一个方面。其实,作为一条河流,更有属于河流的悲哀。在更多的大地上,失去本色的流水,也失去了野性,如今,想要遇见一条野河不知有多难。
除了传统的农灌引水,更多的河流被堤坝拦腰截断。那些自由狂放的属于河流的本质特点,在人类的钢筋水泥前束手无策,乖乖低头臣服。人类在河流上,建了太多约束性的河堤与大坝,更多河流只能委曲求全,顺应人类的安排。可在某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在暴雨的资助之下,在众多溪流怂恿之下,河流也会奋起反击,偶尔暴虐一回,可如今人类的工程机械太厉害了,更多的狂暴也只是暂时的冲动。短暂的雨季一晃而过,更多的时间里河流不得不忍辱负重。
故乡的河流上,有不少引水式的小电站,在旱季不时违背放生态水的规则,弄得一个河谷只见干燥的石头在流动。而某个截流式电站,却是夜晚堵水白天放水,河流的常态完全被经济利益异化。我想,这样的状态持续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新名词,以前叫季节河(流量随季节雨量而变),以后会不会出现昼流河——电站下泄的水量,随着用电量的大小而变,夜晚用电量小自然减少下泄,而利益至上的无良企业,在夜色掩护下,会不会不发电就不放水?
我没有见过截流式电站不放水的情况,但见过旱季傍晚时流量的快速减小。那条河正常下泄时过河需要游过去,可我曾经遇到过提起裤脚就轻松过了河的时候。我想,比我更忧伤的,是河流下游的水生动植物。
苟延残喘。大约只能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河下游的水生动植物。我身边的叫漾濞江的河流,被名字夸大了水量,其实就是一条河流罢了。梯级开发让电站之下的河鱼,早已挣扎在生死边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在河边徒手捉鱼。那种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细鳞鱼,在当时极为常见。哪里料到,如今的细鳞鱼被冠之以“裂腹鱼”的名字且河流中几乎绝迹,本地一个叫姜雨杰的年轻人攻克了养殖难题,开始了大规模人工养殖。野鱼被训化时,野河已经消失。这个被训化的野鱼,大量繁殖之后,各地的电站增值放流都买这样的鱼苗。可是,野河已经消失,这样“训化”了的鱼,能适应那些被异化了的河流吗?除了担忧,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殃及池鱼。其实,这样的变迁,被殃及的何止是池鱼。二零一七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小江河流域绿孔雀保护,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对孔雀这种漂亮的鸟一直喜欢。小城里一年一度的“核桃节”上,总会有一些艺人带着孔雀来凑热闹。被束缚在铁架上的孔雀,安静闲适地供人们拍照。直到读了野性中国微信公众号上的相关文章,才知道孔雀有绿蓝之分。日常所见的都是蓝孔雀,而真正存量极少的绿孔雀云南小江河栖息地,却正遭遇灭顶之灾。
我一直以为,水电站只是殃及池鱼,哪料,这回极度濒危的绿孔雀也在电站的重压之下将丧失最后的家园。发起拯救运动的,是奚志农。
那些年,奚志农发起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惊天动地事我知道一些,可不知道竟然是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和他在云龙天池相遇后,我的某些固定思维开始断裂。听他讲野生动物摄影,讲野生动物保护,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在他平静的叙述下,表面的波澜不惊压不住内心的翻江倒海,滇金丝猴保护,藏羚羊保护,到现在的小江河绿孔雀保护,让我们知道断裂的背后,某种可怕正一步步紧逼贪婪的内心。作为粉丝的我,请他在天池边合影后,我是彻底敬慕他了——比我高一头的他,在合影时特意弯腰降低高度侧身靠拢我,这样照顾陌生的粉丝,这样的人格魅力让我对小江河孔雀的未来,有了更多的信心。
我转发了绿孔雀保护的相关文章,期待用自己的微博之力,唤起更多人的保护意识。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读到了小江河水电站停工的消息,有些欣慰,可更多的担忧无端升起——
河流的自然属性一直在断裂——被截断。经过水电站的江河,常态被打乱,当常态成为异态,非常态成为常态,生活在N次元的世界,一步一步,我们也正在与常态断裂。
3
自然中的生物链断裂了,开展保护性措施某些可以修复如初,表面看不出曾经的断裂。但更多的断裂,是以温水煮蛙的方式悄悄发展。
奔五的我,日常生活只与规律结缘,特别是患上慢性咽炎之后,作息饮食都与喧嚣告别。每天晚饭后,散步成为一种日常状态。我喜欢穿过老城区狭窄悠长的小巷,在一个特定的高台上,用一种侧方位的视角,俯视古道上那座曾经马帮不断的吊桥。可如今的古吊桥上不再有马帮来往,甚至,要等一匹入城的马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在今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集日,我早早起床到桥头蹲守,想要拍摄进城赶年集的马匹。可惜,等了三个小时,没有一匹马走来。在桥上徘徊彷徨的我,大吼一声,桥西边竟然传来清晰的回音。古榕树下的窗口突然探出一个头,很快又缩了回去。那后,再无人关注我的存在。孤零零的我独坐桥上。一个上午,别说马,连过桥的人也很少很少。古老的吊桥,进入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回忆里。古桥与往日的繁盛断裂了。人都到哪儿去了呢?更多的人,更新了入城的方式,以汽车摩托车等工具代替,不再步行往来。也许,某些桥的冷落,成为一种必然。
我去看古吊桥要穿过歪歪仄仄的小巷,那里的侧墙上有不少涂鸦。某些是被不怀好意的人喷涂上的铲了不久又出现的非法广告,有的是被贴上各种正规买卖的小广告,而我关注的是那些用百粉笔写在墙上的发泄语。比如某某喜欢某某,某某恨死某某之类,或给某个人取一个绰号,稚嫩的笔迹以及尽情的发泄话,暴露了刻写者的身份。小孩子们刻写下心情发泄完之后,随着长大离开,因为当事者或刻写的对象再也不从这条小巷经过,这些涂鸦被遗忘在某一个角落,那个情境与发生故事的主角之间,时空出现了断裂。于是,这些性情涂鸦就一直存在下来,被彻底遗忘在故事深处。
我所任教的校园里,有一丛景观竹,粗壮光滑的竹干有大碗粗,正是学生涂鸦表达心情的好地方。那些刻痕,一经刻划就无法消除,我教过的某几个学生的名字,或主动或被动地出现在竹干上。随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离开,涂鸦背后的故事渐渐无人关注更无人读懂,断裂在不知不觉中生发,虽然只被我看见。当然,校园里也有某些显而易见的断裂。
在上个学期,为了美化教室,学校号召各班购买一些花草盆栽摆在教室里。可一放暑假,空荡荡的教室只会促发花草的死亡神经。有些学生把花草带回家养,某些班级把花草搬到走道上,期待夏日风雨交加之时的浇灌生发。可时断时续的浇灌只是间或发生,不可能满足盆栽的需求。在秋季开学时,一层楼的花草却只有一个班的死亡,枯死的四周依旧生机勃发。原来,假期中有校工值班,可某个班班主任魅力与助人的断裂,让他们班的花草也无端遭遇旱情。一走道的碧绿与一小片的枯死,在那里无声胜有声。
这些断裂,无论隐藏还是彰显,其实都无关大雅。可某些断裂,却并非这样简单,更不是我可以指手划脚简单评价。
每年寒假我所在的学校都要组织老师家访。今年的家访中,我遇到一个极其特殊的家庭。那是一位读初一的小姑娘,稚嫩的脸上,根本看不出她所经历的沧桑。故乡远离县城,每次上学她都特别不舍,一走就是几个月的离别。可老家仅仅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在耕耘几亩贫瘠的山地,父亲早已到远方的城市打工,为了节约连续两年春节都没有回来。我问:母亲呢?
没想到,话未落小姑娘竟哭了,手足无措的我慌了,还是她先平静下来且安慰我说:“不怕不怕,老师,没事的,不怪你,是我失态了。”原来,她的故事,超出了寻常。她的母亲在生下她后去世了,后来,她的父亲找了个带着男孩的女子组合成家,那男孩比她大自然成为哥哥。可两年前,这组合的家庭解散,离异后父亲外出打工不回来,继母悄然远走他乡无消息。大男孩几番周折之后找到生父,可生父却不愿收留他——离异时男孩判给了女方,更关键的是,男孩的生父也早已另外组合了家庭,且又有了孩子。“谈判”的结果是他的生父按月支付大男孩的读书费用。正读书的他,钱当然需要,可他需要的却不只是钱啊!天地之大,再没有一个小小的家,漫长假期无处可去的他只得继续留在小女孩家里,崩溃的大男孩如今已上高中了,可叛逆却愈发厉害,每次学校通知家长,都是年迈的爷爷前来。小姑娘一次次哭泣,除为自己去世的母亲悲伤,还为爷爷奶奶悲伤,更为叫哥哥的大男孩悲哀。如今的乡村,不少家庭正发生这样那样的断裂,而每一个断裂故事的背后,都是无尽的辛酸泪,只不过这个小姑娘信任我,她讲了自己的故事,而更多的不信任,一直横亘在那里无法逾越。
我的QQ中有不少学生,某一段时间,我发现一位学生总会在三更半夜转发自己以前的说说。这个现象太奇特了。我想要靠近聆听,可是,又担心拿不准关键之处而适得其反。有些高冷的她,成绩一直非常出色,某天上班路上和她母亲相遇,我忍不住说了她在QQ上半夜转发自己的说说,大约是情感出了问题,请她母亲关注一下。可就在第二天,她的QQ动态和空间都对我关闭了。我知道,某种断裂已经形成,多说已经于事无补。再后来的后来,当她的空间再次对我开放时,木已成舟,故事早已有了另一个结局。唏嘘感叹之余,我总是在想,如果当初不告诉她的家长,或许断裂不会生发,故事,也许还有另一种结局。可是,一切已经成为过去。那后,学生的事我轻易不敢对家长说,三缄其口的瞬间,是顾虑到某种信任一旦断裂,修复再无可能。
前不久和本地一个登山协会一起徒步去看了一次富恒乡石竹村的映山红。那些古老沧桑的花树,留给我们深刻的记忆,可让我记忆更深刻的,是登山回来大家聚餐后发生的事情。我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日常生活中话不多,若遇到志趣相投的朋友,我也会滔滔不绝。登山归途中,我们大队人马在一个农家乐聚餐。我不能喝酒之后,很少在饭桌上逗留,吃完就找个借口一边玩。这天我依旧如此,吃好借接电话转到附近看花拍花。在等待喝酒的最后一桌时,更多的人散开闲聊等待。我一个人转了好久,看见同行的一位男士蹲在一片野菜前看他的妻子采野菜。我就凑过去无话找话想聊天。我说:*老师,你的妻子是本地人吗?那位老师不太熟悉,但一起登山徒步已经多次,我知道他是外省人,于是有这样一问。他回答说:“中国人。”当然聊不下去了,断裂当然有机可趁……
有人拒绝别人的靠近,可某些人,多么期待有人靠近,甚至只说几句话也欣喜半天。我就曾遇见两个孤独的老人,他们的住地曾经与世隔绝,如今外在的交通改善了,但心与心的交流依旧呈现为与世隔绝,他们的心田依旧荒无人烟。也许,过往客人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心灵荒漠中的一片绿洲,可这样的期待,有时也成为奢望。有这种故事生发的土壤吗?有,当然有,且是我眼所见。那是在一个叫“莲花山”的地方。曾经,那样的地方是双足的禁地。是一次文学采风的作品,勾起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勾起一个与这地方相关的一个人——樊斌,这个南下干部这个军旅作家,在那段特殊的年代,被下放到遥远偏僻的云南大理漾濞莲花山,管理治疗一群麻风病人。与文明世界的断裂,斩不断樊斌先生的精神与气质,更斩不断他的文思与才情。后来的后来,拨乱反正之后的樊先生,依旧留在了云南。我是了解到樊先生的特殊经历之后,在途经莲花山时才注意到那个“麻风院”的。我特意停车,一个人从上边的公路上走下去,看看在历史深处恐怖一时的病院如今的样子。两排面对面的瓦顶小平房围成一个小院,两个孤独的老人家,在院子里烤着寂寞的太阳。我进去打声招呼后拍了张照片,说了几句话后在喇叭的催促声中匆匆离开。很多断裂,在这里生发。亲情友情的断裂,自己与世界的断裂。最后可能的是,这两个高龄的老人去世之后,莲花山麻风院也与历史断裂。再后来的人,轻易不懂这里的沧桑……回来后,我把莲花山的图发给了樊斌后人,也算让与他们生活断裂多年的父辈历史有一个重新契合的机会。
莲花山这个地名,一直停留在纸页上,我的遇见纯属偶然。可某些地名,一直在眼前,但某些断裂,让我等后人已经很难知晓它原来的故事。
我一次次与之对望,又两次登临的七星石山,山的原名竟然是多年后在闲聊中才知晓。那山在我岳父家的对面,是我所居住的县域内最高的山峰。基于两度登临我写过一篇文章。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曾详细问询关于这山的故事传说,这山的前世今生。可作为当地人的妻子,竟然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电过岳父,只了解到一个神话传说。时过境迁的两年之后,我竟然意外知晓这山的彝语名字“阿四代”——就是彝语老和尚居住地的意思。而类似地名的背后,该有多少故事生发。我听妻子讲过的另一个彝语地名由“萨密之达”变成了“密达”,原意是“核桃多的地方”,而改成“密达”之后,再无彝语可以解释。将来还会有人知晓这些地名变迁的故事吗?不经意的改变造成历史与现实的断裂。可更多的现实中,基于商业目的改地名或者打着雅化旗号改地名的事件层出不穷,让后来的人,再也难以从地名中,找到这个地域本来的历史与故事,而这类事情的本源,却还与民族语言正在发生的退败有关。
我是正宗彝族,可惜我的民族语言能力已经丧失。现在的年轻一代中,很多都丧失了母语能力。民族母语退守到更高远的山头。失去了语言环境,这类断裂事件的发生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还有一些与此相关的改变,让我们忧心忡忡又无可奈何。
数月前,我接受某杂志社一个采访任务,去采访本地一位省级非遗传承人,发来的资料却只有一个名字与传承类别“木雕石刻”。一番调查下来,原来是一位早年退休的小学老师,已经定居风城,好在打听到了电话。外围了解之后,在寒假中宏观送我抵达他的居所。老人的经历,就是一个传奇的励志故事,聆听、参观、问询之后,面对老人满屋的木雕石刻作品,我问了他的收徒问题。想不到老人家一声长叹:“无人!”轻轻两个字,重重千斤愁!在发扬木雕石刻时,他就在思考传承人的问题,他已经把历史的手艺和现实的需求结合,开创性地做了手工民族器乐,销路不错的现状下却依旧收不到徒弟,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断裂,一直不停地生发……
4
我所在的山区县,水田曾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少量的河谷坝区出产稻米,这是苍天的青眼有加。可近年,某些地方的稻田出现荒芜。每一次遇见都忍不住问怎么了,答案却只有一个:举家外出打工了。那些丰饶的土地,与他们原来的主人告别。也许几年之后那些人回来,还会重新除去莽莽杂草,土地得以重见天日。但更多的可能是主人不回来,抑或者回来了,却再也不愿重拾农桑。土地的收入毕竟有限,很多人不忍田园荒芜也曾试着外包耕地,可惜和村庄一起老去的,就是留守的老人家,耕种权无偿送都无人问津。即使是从城市偶尔的回归,更多归来的人失去了耕种的能力与兴趣。我的故乡是核桃之乡,早已大量种植核桃树。核桃果挂在高高的树上,收打核桃是一件危险的农事。近年已经发生多起打核桃的人坠落的事故,结局之悲让人慨叹。与之相连的事情,是保险意识已经逐步深入——为那些打核桃的人购买意外险。可连带的反应并不止这些。风险加大后,打核桃的工价急剧升高与核桃价格的低迷徘徊牵手,让主人有了更多的矛盾和犹豫,风险加大的同时,利润已经不高了。可更多的担忧一直在背后——如今能上树打核桃的,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随着这一代人的老去,年轻人都进城去了,核桃还会有谁来收获?将来的某一天,在收获核桃的方式上“打”这个字会不会消失不见而转为“捡”——核桃熟透自然掉落,再没有人去打。
其实,与故乡故土发生断裂的,不只是进城务工后农事能力的退化。我与故乡,也发生了某一种层面上的断裂。
在小城工作的我,父母在故乡时我的家也就在故乡,年年春节都回到老家。随着父母的先后去世,那里只是我的故乡而再不是老家了。家乡成为故乡,往事成为故事,那是一种莫名的惆怅。我虽然依旧会不定期回去,可是,那种魂牵梦绕的感觉已经渐行渐远,断裂,早已不可避免地生发……
小城里,我的蜗居靠近一个叫“皇庄坡”的地方,晚饭后散步,有一段时间我老喜欢去那里走。去那的原因很简单,我去捡羊粪——就是山羊拉出来的颗粒状粪便。去到那个坡上,蹲下,扯来两小段枝杈当筷子,一粒一粒,把散落在缓坡上的羊粪疙瘩夹入塑料袋。散步的人不少,最初的几晚不少路人诧异得紧,当看清是捡羊粪而不是宝贝时,又一脸不屑地离开。他们哪里知道,我真把羊粪当宝贝。我捡羊粪的目的是回家发酵后做花肥。小小蜗居中,我种下十几盆美好,化学肥料哪有羊粪好。第一次发现皇庄坡有羊粪后,我也犹豫了几天,但花的需要占据了上风,于是开始了捡拾。后来,个别同道中人见了,告诉我可以在街天去牛马市场扫一点。可我却不想去,我已经把捡羊粪当作每天散步的固定节目。也不知是谁家养的山羊,也不知何时放牧出来,反正我去散步时刚好臭气散尽可以捡。那样的固定节目,在延续了一个多月后,坡上再无羊粪出现,大约是主人出售了羊儿,无粪可捡,某种遗憾缓缓氤氲……
可后来的某种断裂,却让我心痛。
很多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即使说了“感同身受”,其实也只是一种关心,真正感同身受的只有自己。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深化了这样的认识。喜欢拍摄花花草草的我,自然关注苍山的草木荣枯花开花落。当春天杜鹃花的第一张邀请函发出之时,我也就上了苍山。大年初一,在苍山西坡一个叫大花园的杜鹃观赏点,我请同行的两个小侄女做我的模特,在花下拍了数张照片。那时,草坡上的一棵花刚刚开好,侧对一枝繁花微笑的侄女,让陶醉的韵味更为优雅。我用那图发了微信动态:如花与似玉,陪我上苍山。在一个星期之后,在另一个西坡赏花之地,我请妻子入画,作数棵大树杜鹃的背景,拍了也就发上微信,期待更多的人知道苍山西坡又到了盛花之年,可以来赏花了。后来的一件事,却让我为这单纯付出了代价。我的数张图片,先被本地一个微信公众号多次使用却署名他人,我的问询被忽略,我想着都是宣传故乡,用了也就算了。可后来,其中的一张图竟然上了纸媒且刊出的名字也是别人的。一怒之下我和纸媒联系投诉。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这是我一个人的战争。在这个法治日益健全的时代,一个人与一个领域的战争并不意味着失败。很快结果出来,我胜利了,但胜利的滋味却不是喜悦两个字而是五味杂陈。我与某个领域的断裂,自然随之生发。记得以前微信上看见陆兄的图片都加水印,最初不理解觉得多此一举,且妨碍观赏,后来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好在我只是一个老师,管好教书育人的事是主业,其他的事情本来就是身外之物,抛却执念,我依旧是我。
我还是我,就像我日常散步取道老街,不管世事变迁,老街还是老街。我走过时,感慨锋利的时光活生生割断了某一种牵挂。每一次散步,看到老街上老屋门口或闲聊或独坐的老人,我都会放轻脚步慢下来,怕惊醒他们的旧梦。今年冬天,那间老屋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不见了,再看看门上的红对联,我知道,又一个高寿老人到云龙桥那边守山去了(本地的习俗,高寿老人去世门上的对联用红纸)。随着老人的渐渐离去,老街上年轻人更多地选择到新城区。老街一年比一年老了。那些老去的历史,也随着老人的离开而与老街发生断裂,再后来的人,谁会在意一个地方逝去的故事。
在去老街散步的时候,我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那个路口是小城最繁忙的路口,可红绿灯却时好时坏。有时是一边不亮,何时通行得看另一边的灯。有时是一边的灯一直亮,让我们走也不是等也不甘。我所在的小城很小,虽说是县城,可我一直叫它小城,整个小城只有三处红绿灯,可最繁华的这里却老是坏。这灯坏事小,可我们的规则意识,却老是被一次次打破。更多还未建立规则意识的人,潜意识深处,与规则结盟的理念是否会因为红绿灯的坏掉而开始断裂?
这是一种可怕的断裂。因为,某些断裂一旦生发,修复就不是一念之间。
我与好朋友阿端,那是一起玩泥巴的至交,可依旧出现过隔阂。那是某年他的亲人意外去世,因为各种事务我没有亲自抵达。一场变故,疏远了两颗本来很近的心。事后的弥补都不再入心,直到多年后另一场变故的发生,才让我们的心再次靠近。可我知道,某种默契已经断裂,虽然修复了,可痕迹一经出现,就不是说好了就真好了的简单。
5
我原来居住的小区,是一个企业家属区。企业改制之后,这里就无人管理。当然,我也是在企业改制后才购买入住。我住顶层,避免了一些嘈杂。可有一个噪音却是年年月月的存在。对面一楼有一家卖早点的夫妻二人,每天四点多开始磨豆浆。机器启动的声音中,不少人会醒来,别人惊醒后很快入睡,可我一醒来就睡不着,且适逢我睡眠特别差的年月。有时,我也有冲下去吵一架的冲动,但想想大家都不容易,都只是讨生活的人就罢了。那老俩口,女方是本地人,老汉是外省人。早点忙完后,老汉还开三轮拉客挣钱。我坐过他的车,胡子拉渣的他脸上有些沧桑。有时遇到也打声招呼,但一直没有更多交流。我想,整个院子的住户,大多期待他家的破产离开——他家似乎生意不太好,有时候夜晚听见老俩口打架吵闹的声音。他租住的楼上房东有一次来和他大闹一场,房主人要出售房屋,可来看后的人都摇摇头走了——听说楼下的事情谁还愿意买。可也就消停了一天之后,机器依旧准时响起。再后来,房屋终于出售,新来的似乎知晓情况,买了却没搬来入住。后来,老汉家突然搬家,搬走那天,我们一院子的住户都松了口气。
后来,在农贸市场我见到他家依旧在卖早点,我以为他住到城郊不影响别人的地方去了。可知晓真相后的我大吃一惊。他并非租住城郊,而是在城郊公路边建了一栋三层的宽大新房,已经成为房东了。
那些单方面以为断裂了的,其实,早已是新的开始。
我因为患了慢性咽炎,认识了一种中药,才理解了这样的生存智慧其实植物界早就懂了,人类只是学得皮毛。
那是一种叫做“寄母怀胎”的草本植物,只生长在映山红树下。每年二月发芽,三月抽花箭开花,花谢后整株植物死亡,包括地下的椭圆形根块也腐烂。但在根的四周,会有新的小的根块生成。我没有遇到花开,我去看映山红盛开的时候,见到的都是头年枯死的花箭。第一年我不知道花下泥土里的根块腐烂了,刨一棵,烂一个。第二年,在不经意中翻开枯死花箭附近的泥土,才知晓那些枯死的背后,新的生命早已萌发成长。
那后,每年看映山红时,我都撬一些药回家,煮水喝了控制咽炎的变本加厉。有些担心,我会不会灭了这药材。一直生活在苍山西坡的弟弟说:“不可能的。一棵花开后,种子散开一地,大片的新花几年后就出现了,不用担心!”
怎么可能不担心!最近的五六年间,杜鹃花开时节的每个周末,我都在苍山西坡的花间行走,见过很多红遍山野的绚烂场景,也目睹了一些映山红树尸横遍野的惨状。当然,那些映山红都是自然枯死,这些年苍山保护做得很好,无人去破坏更不要说砍伐。那枯死的大树让人触目心惊——当满树繁花与枯死枝干同步出现在视野里,你一定会感慨生命的执着与沧桑,更会担忧映山红的新老交替。是的,新老交替的担忧我一直有,直到去年六月登苍山莲花峰才明白:有些担忧,纯属多余。
在莲花峰的山脊上,我竟然遇到多年未见的映山红幼苗!大约是气候等因素的机缘巧合,让蓄积多年的种子突然爆发,我见到了众多幼苗的勃发。原来,生命断裂发生的同时弥合也不声不响地行进着,生命一直生生不息,只是,更多的更替并非大张旗鼓而是悄无声息地以自己的方式行进。
在一个叫马鹿塘的地方,上一个秋天,我竟然见到了红豆杉,还挂着红色的果子。问过护林员才知道,苍山西坡的红豆杉并未灭绝,在那些险峻的山崖上,依旧有古树生长,而小树自然会出现,生命并不会轻而易举屈服于断裂的安排。
最妙的是前面我写过的那个截流式水电站,竟然是国家“以电代柴”项目,苍山西坡的民众用电,在两百度的范围内,每户每度电竟然只需一角六,西坡人大多由此告别了烟火。苍山西坡人与古老柴火的断裂,是苍山植被得以修生养息的根本。电站影响了鱼类的生存发展,可苍山的植被得以更好保护,一得一失,我终于知道,很多事情的追根究底,不是一个好字或坏字能归结的。可有一些断裂,却是纯粹的美好。
今年三月,我参加本地登山协会的行走,在一个叫石竹的地方,看见了大量古老的映山红,更看到映山后树背后即将完工的石竹水库。那里本来断裂开的山谷,被水泥大坝弥合,新的一年,这里本来的断裂带将被一谷碧水填满,下游干旱少雨的贫困地区,将迎来无忧之水,这里亘古的贫困也将与历史断裂,更美好的生活就等在前面。
去年九月,我曾到石竹水库下游,动员一个学生来读书。那是一个刚刚小学毕业升入初中的小姑娘。开学没来报道,我问了在本地工作的作奇同学,了解到这是一个残疾学生,担心生活不便,所以就留在家中。
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良心。几番动员之后,孩子终于来读书了。她的母亲来学校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可面对一个建档立卡户家庭,这样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支出。多方沟通协调之后,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孩子的母亲到学校食堂打工,学校单独分一间宿舍给她娘俩住。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让那个我写了又写的断裂这个词汇从此和他们彻底告别。后来,我听到一个消息之后,我特意去找了她娘俩。云南民族大学以后要招收白族语专业的学生,而她正好是白族,且是能流利使用白族语的正宗白族,不像我,是一个不会彝语的冒牌货。
6
我一直在看断裂,断裂也在看我。
在我的故乡,有一种叫香橼的水果,成熟之后若不摘,可以连续生长多年。果子黄了又青,青了又黄,历经时间磨砺,三年之后才会成为最美味的果子。
时光在这样的果子身上,不断重复美好。这样的果子,用润物无声的方式不断拓展,让更多非断裂的美好故事温暖着日渐老去的乡村。
原来,更多的温情故事,一直在发生且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