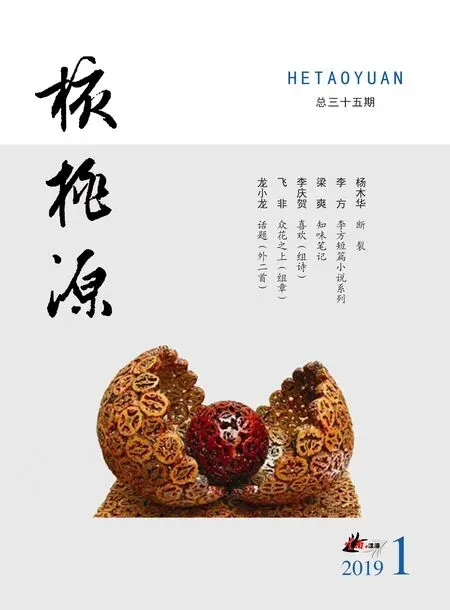三奶奶的心事
陈启忠
1
这是三奶奶上午第三次走出家门了。
三奶奶的家就在村子的最东头,门前有棵古槐,当初三奶奶出嫁的时候就根深叶茂,如今三奶奶已经七十六了,这棵古槐少说也有两百年的历史了,巨大的树冠几乎把半个天遮掩起来,送来了一片阴凉,当初生产队时期,这里就是队上集合派工的地方,如今古槐苍葱依旧,只是人雀冷清,年轻的都出去打工,留下了像三奶奶一样的老弱病残,守着乡村守着古槐。
三奶奶门前有一丛月季,开得粉艳艳的,个头比她还高。三奶奶就站在那里,伸着脖子向村东路口的石桥的尽头张望着。桥头是一条柏油路,向北一扭就不见了。桥下就是著名的马颊河,正逢夏季,河水漫了岸。女儿秀秀在河里洗衣服。她回头瞅了三奶奶一眼,又瞅一眼,说,妈,你等谁呀?没听说今天谁要来咱们家呀?不等,谁也不等,就是在家里闷得慌,三奶奶说。三奶奶的眼底掠过一丝慌乱,好似有什么秘密被女儿秀秀看到了。三奶奶一扭身进了院里,脚步显得有些沉重,好像心没有跟着脚一起进来,她要用力地将心拖进来。
三奶奶踱到窗台前,拿起水壶,给那些海棠、君子兰什么的浇水,以前她看着那绿绿的叶粉嫩的花骨朵,心情也会像花儿一样,可是这次明显心不在焉,水满了溢到了脚下,她才缓过神来,放下水壶,寻到锅台上的一盆芸豆,又拿个矮凳子坐下来,准备剥芸豆。秀秀说了,今中午炖一锅芸豆排骨,外甥盼盼刚从学校回家,最喜欢吃的菜。三奶奶坐下来时,正对着灶台,又觉得不对,她看不到门外的一切了。就又起身,挪了挪凳子。再次坐下时,她的脸上浮现一丝满意的微笑。屋门开着,大门开着,她能看见桥了,桥上有什么车驶过来她也能看见了。三奶奶开始剥芸豆了。刚剥完一枚随手扔出去,才发现自己还没有准备另一个盆装芸豆呢。三奶奶又起身从碗柜里摸出一个铝盆,放在自己腿边。
三奶奶一边剥芸豆,眼睛一边紧盯着门外,盯着桥头。每从桥头露出一辆车,三奶奶就紧张地抬起身子,伸长脖子,眯缝着眼睛,跟随着车来的方向送出去一段路。她心想,要是哪一辆车忽然刹车了,忽然就在她家门外停下来了,她怎么办?三奶奶反反复复问自己,问来问去,她自己并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当秀秀端着一盆湿漉漉的衣服跨进院里,看到母亲手里拿着一根芸豆,却不马上剥掉,只呆呆地看着什么,不免惊诧地问道,妈,你怎么啦?三奶奶一惊,芸豆掉在地上。但三奶奶马上捡起来,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剥芸豆。她对秀秀说,就是感觉眼睛有点疼,没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秀秀说,妈,你去炕上躺一会儿,那点芸豆我来剥。三奶奶没听秀秀的,她手下的动作麻利起来,只听到芸豆一折两段清脆的剥裂声,还有街上来来往往驶过的车辆不间断的喇叭声混合到一处,在三奶奶的耳边交响着。渐渐地,三奶奶已辨别不出哪辆车要停下来,或即将停下来。她不再向门外张望,只一心一意剥芸豆。在秀秀看来,刚才的那一幕和之前的那一幕无非是上了岁数的老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偶尔的失神,不知所以。
是不是我自己老了也会这样?秀秀想到这里,居然噗嗤一声笑了。瞎想什么?离步入老年还早着呢。秀秀这样劝着自己。
2
只有三奶奶自己知道,她心里装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虎婶。
三奶奶辈分大,虎婶辈分小,在乡下,几岁的娃娃能当一个老头子的爷爷,就是萝卜不大长在了背上,其实她们俩同岁,娘家也是一个村的,是同一年嫁到了一个村,只是三奶奶嫁给了老实本分的三爷爷,除了辈分大,一无所有;虎婶呢,当年可是风光无限,她嫁的是当时的土皇帝,村里的生产队长,虎婶也真够厉害的,生产队长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新媳妇虎婶,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可三奶奶不喜欢虎婶,一直不喜欢。在秀秀很小的时候,三奶奶就像讲故事一样跟秀秀讲,“从前人们都要去生产队劳动,虎婶长得一般,但是脾气暴躁,因为是队长夫人,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也许认为我比她好看,女人天生嫉妒吧,那个时候,虎婶常常欺负我,经常吹枕边风,我每天被派干最真脏最累的活,她呢,干着最轻松的活,炫耀讥讽我成了家常便饭,我只有忍气吞声。”
有一次,家里断粮了,可气的是,虎婶拿着黄橙橙的玉米饼子当着我的面喂狗,她知道你们饿得嗷嗷叫,却一点同情心也没有,晚上我实在没办法了,就去了玉米地偷偷掰了几个嫩棒子,准备回家给你们煮着吃,不想被虎婶发现了,喊来了民兵连长,我被抓了个现行,成了反革命破坏分子,戴上大木牌,自己敲着锣游街,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偷盗分子,我破坏大生产……如果不是看在你们还没成年的份上,我寻死的心都有了……
提起过去的创伤,三奶奶记忆尤深喋喋不休。更让虎婶嫉恨我的一件事是因为他丈夫调戏我,我豁出去了,闹到了她的家门口。那是一年的秋后,队长背着虎婶派了我一个很轻松的活,看队上的几头牛,期间队长蹑手蹑脚地走过来,先是语言挑逗,然后要动手动脚,当时我豁出去了,骂着喊着到了他家门口,躺在了他家炕上……后来队长的脸被虎婶挠了好几道深痕,虎婶也越来越仇恨我了,我出了一口恶气,尽管落了一个坏名声,但是值。
以后的日子,我就暗暗下定决心,好好过,活出个人样,让她虎婶瞧瞧,我平常人家也一样挺着脊梁做人。
三奶奶的故事好似告一段落了,可三奶奶激动的神情告诉秀秀,这不是戏的结束,肯定还有更好看的大戏等在后头。果然,三奶奶没等秀秀追问,就自顾自地讲起来。“你不知道虎婶多坏,就像电影里坏人那么坏。她的自留地紧靠着我们家,她就把她地拔的草统统扔到我们地里,还有,我们家地头的庄稼被她肆意践踏,而她家地里的庄稼一棵也不许我们碰,有一年她地头少了几个棒槌,虎婶爬到房顶对着我们家骂了整整一个晚上。
更可气的是,那一年八月十五我们宰了一只自己养的白鹅,偏偏那天她的白鹅找不到了,看到了我们家炖了鹅,就认为我们偷吃了她的白鹅,又是砸门又是砸窗,弄得我们不得安宁,我们报了案,也没有解决好,可是第二天她的白鹅大摇大摆自己回了家,我们气不过,找她伦理,她死猪不怕开水烫,连个道歉的话都没说……再长大一些的时候,秀秀就会讲这个故事了。三奶奶与虎婶的故事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酵,早已在三奶奶三个女儿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母亲说虎婶是坏人,孩子们就认为虎婶是坏人。坏人的标签贴在虎婶的额头上,贴在虎婶的纽扣上,更贴在虎婶走路圈出一个“O”型的罗圈腿上。与虎婶家做邻居这么多年,孩子们就没怎么去虎婶家玩过。哪怕是虎婶家的山楂熟透了,像红通通的玛瑙挂在树枝上,孩子们馋得直流口水,也没有想过去虎婶家要来一捧吃。反倒是虎婶每年摘了山楂,都要送一瓢又大又红的过来。三奶奶手足无措地接过山楂,孩子们围在三奶奶身旁,馋猫样的眼睛早把那一瓢山枣过滤了一遍,瞅准自己要的是哪几枚个头最大的山楂了。
3
三奶奶不是亏人的人,更不愿在虎婶那里落下“一毛不拔”的恶名,于是每年三奶奶家苹果熟了,也总会挑出一些个头大,色泽鲜艳的打发秀秀送一筐过去。据秀秀回来描述,虎婶接过苹果,先是怔怔地楞一会儿,然后向三奶奶家的院落望过来,好像找什么人。秀秀看到虎婶捧苹果的样子,就像得了金元宝一样,双手紧紧搂住竹筐,上身现出一个“O”型,下身现出一个“O”型,模样特别滑稽可笑。
日子在两个人不咸不淡的交往中滑过去几十年。对于从前的事情三奶奶与虎婶从没有坐下来面对面好好谈一谈,而三奶奶也从没有放弃在孩子们面前数落虎婶不是的机会。但孩子们逐渐长大了,年轻人是不大愿意向后看的,后面的那些都是属于母亲时代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在时光机器的搅拌中,长了多少霉斑,兑了多少水分,已经不得而知了。所以三奶奶再一次对虎婶的数落常常是在女儿们借口上班,借口睡觉,借口去河里洗衣服这样的理由的搪塞中被迫中断。三奶奶怔在那里,嘴半张着,那情形就是下一句话马上要冲口而出了,却又不得不紧急刹住了车。落满一脸无奈的三奶奶就在女儿们逃也似离去的那一瞬间猛然间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老了?
这个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问题,被七十六岁的三奶奶就这么揪了出来,像一棵倔强的秋天野地里的茅草横在了三奶奶的心间。同时她还发现虎婶也老了。虎婶的头上白头发比她还多,简直就像深秋里下得最厚的一场霜遮着那张老纹纵横的脸。虎婶的罗圈腿也弯曲的更明显了,仿佛身子一个趔趄,就会软软地烂泥一样地瘫在地上,化成一个再也滚不动的生了锈的铁环。
虎婶也老了,真的老了!三奶奶的心里蓦然间腾起一股喜悦,好似看见虎婶举着她的罗圈腿,真的抬不动步了,软绵绵地倒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而三奶奶紧步上前,不知哪来的勇气把憋在肚里几十年的话噼里啪啦倒了出来。虎婶已经说不出话,只伸出无力的右手抬高了一下,企望三奶奶在这个时候能来拉她一把。而三奶奶本能地后退着,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质问着,她婶,你倒是说说,那一年我掰棒槌是不是你的?你倒是说说,干嘛把一捆湿柴火扔到锅盖上,吓得我家大妞哇哇大哭?你倒是说说,你倒是说说……
最近三奶奶常常生出这种离奇的幻想,心里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感。可是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摸着了一件旧衣服,对着那一个磨破了袖口的地方发呆时,就越发不能理解自己了。
4
吃过了午饭,三奶奶贴着炕边睡了一会儿。
三奶奶白天的睡眠充其量就是打盹。有时候眼睛刚闭上,就被苞米仓下黑狗的一声吠叫惊醒。这一场午觉就算结束了。夏天的中午太热,三奶奶觉得没有走出去的必要。好像哪哪都挂着火辣辣的太阳,哪哪都白花花地耀着人的眼目。三奶奶坐起来,喝了半碗白开水,用粗糙的右手擦了擦嘴巴,就想,自己下午要做什么。
跟秀秀生活在一起,能干的秀秀一手全包了,什么都不用自己做。自己能帮衬上的也就是择点青菜,烧烧火之类的。而这些小活秀秀也常常不用自己插手,秀秀说,妈,你岁数大了,不用你干活,闲不住了去村子里走走,跟老辈人聊聊天,这就是你的活。三奶奶想,她虎婶就没这个福分,女儿出嫁,儿子儿媳都出门打工,家里长活短活都得去干。活该!嗯,活该!谁叫她年轻时太霸道,欺负了这个欺负那个,这是她的报应。
不知怎地,三奶奶时不时地就会想起虎婶,不自觉地就会跟虎婶做起各种比较。三奶奶又添置了一件紫花薄尼外套,三奶奶想,虎婶没有;秀秀去年给三奶奶买了一个金灿灿的黄金镯子,三奶奶乐颠颠地戴到手腕上,又忍不住想,虎婶没有;三奶奶走路腿是直的,能从自己家一直走到三里外的镇子上,三奶奶想,虎婶那罗圈腿可走不了几步路,这一点也不更加不如自己。总之,三奶奶喜欢这样比较,也习惯了这样比较。每一次比较三奶奶都赢了,都像喝了喜酒般的心里盛满了快活与得意。她渐渐发现,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与虎婶比较着,然后一下子压倒了虎婶的气焰,这样的日子不知有多么开心与快乐。从这方面想,还应该感谢虎婶。不对,怎么能感谢她!三奶奶被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吓了一跳,赶紧否定了。
可是三奶奶不快乐,这几天都不快乐。秀秀待她好,没的说;老头子也凡事都依从她,也没得说;虽然颈椎上有点骨刺,腰腿也常常闹些小疼痛,但也都不碍事,也没得说。可是三奶奶真的是不快乐,她快乐不起来。三奶奶心里搁着事。这事若在几年前,几十年前她都会认为不算是事,可现在三奶奶认为这是大事,天大的事。有了这事,三奶奶是不快乐的,它一下子打破了三奶奶的生活节奏,快不起来,慢不下去,皮囊是自己的,而心思又不是自己的。不知在哪里飘着,又怎样才能够落地。
5
三奶奶下午又去了三趟街边。有两次是站在大门口的蜀葵前向不远处的桥头张望,有一次是站在街上,望着桥头的方向,好像觉得哪一辆车上都拉着虎婶。但车到了跟前又不停下来,只卷起一股混合着细微粉粒的尘土,径直掠过她身边开走了。三奶奶站得有些乏累,忽然想起有一件大事还没做呢,就拍拍身上的尘土,绕过在太阳底下沾了一层灰尘的玫瑰花,拐回了自家院子里。
走进灶间的时候,三奶奶居然忘了自己要进屋干什么,就又回到院子里,想了又想。当她终于想起来自己是要去装一些鸡蛋的时候,竟有些眉飞色舞了。鸡蛋篓子放在屋里的烟台上。烟台是宽不过两尺的一条长方形水泥台,连着一铺炕。灶底的烟气通过火炕,再通过烟台,才能从烟囱里冒出去。说白了,烟台就是北方人家在卧室垒砌的一条烟火通道,其他的作用则没有了。三奶奶家的烟台平日放的杂物也不多,除了几床被褥,就是一个鸡蛋篓子了。秀秀的意思是这些鸡蛋都是自家母鸡下的蛋,虽然产量不高,但味道好,营养也高,比养殖的鸡蛋好去了一百倍。她放在烟台上让三奶奶取鸡蛋方便。三奶奶有时候好吃鸡蛋水这一口。烧开了水,打四个鸡蛋,扔锅里煮着。待水开了几开,鸡蛋就像紧实的荷包一样在水里卧着,白嫩的蛋清包裹着鹅黄的蛋黄,俊死个人,这就差不多熟了。三奶奶盛出两个给自己,另两个给三爷爷。各自往碗里加些煮鸡蛋的水,加点白砂糖,喝一口甜滋滋的。
现在,就是此刻,三奶奶要把这些鸡蛋派上另外的用场。她找来一个干净的装过方便面的纸壳箱,把鸡蛋一枚枚小心翼翼地摆放进纸壳箱里。一层层地摆放妥当了,正要封箱子时,三奶奶发现篓子里还剩下不少鸡蛋。于是三奶奶瞬间改变了主意,把装好的鸡蛋又一枚枚取了出来放到篓子里,这就意味着装鸡蛋的工作要重新开始。这一次三奶奶已经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她专捡篓子里个头大的鸡蛋装箱子,那些小的就让它还待在篓子里。这样过了不久,原先装方便面的箱子就铺满了一层又一层鸡蛋,每个都是三奶奶精挑细选出来的,粉嫩嫩的如同刚出生的小娃娃一样,煞是好看。三奶奶对自己的举动颇为满意,竟暗暗地对着一箱子鸡蛋出神了好久。这一出神,就又看到了虎婶的脸。虎婶那张被太阳晒得黧黑的干巴巴的脸在三奶奶面前晃动着,一会儿变得蜡黄,一幅有气无力的样子;一会儿又恢复了血色,但看起来也恹恹的,仿佛那血色很不容易留住,一不留神就会不见的。三奶奶是想把箱子封上口的,但又觉得不对。封上了,鸡蛋露不出来了;鸡蛋露不出来了,谁又知道那里面放的是什么呢。一旦摔了,打了,磕磕碰碰了,那些鸡蛋,自家的喷香喷香的鸡蛋……想到这里,三奶奶已经为不封住鸡蛋箱子的口找到了绝对充足的理由。嗯,就这么做。三奶奶最后这样告诉自己。
6
妈,我虎婶回来了。秀秀的声音从院外传了进来。
回来了?回来了?哦,回来了!三奶奶冷不丁听到秀秀的喊声,浑身一紧张,竟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一低头,看到了鸡蛋箱子。哦,对,自己是要捧上这个箱子的。三奶奶哈了哈腰,两手往箱底一抄,就把箱子搂在了自己怀里。她的手紧紧地用着力,胳膊肘护着箱子两侧,那样子很像是怕谁把箱子抢了去。
三奶奶搂紧箱子走到院子里时,就听到秀秀的声音,虎婶手术怎么样,大成?挺好的,大夫说,我妈这是早期,把胃切除三分之一,注意饮食,控制情绪,能活个几十年的。
把胃切了?三奶奶默默地念着,心里一惊。那都是人身上的器官,咋说切就切呢?那以后还咋吃饭?不能吃饭,还有几天活头?都没活头了,那自己以后再添置新衣服,妞们又给自己买了新鞋,新首饰都戴给谁看?三奶奶心里一急,腿下发软,脚底一个趔趄,一箱子鸡蛋就从怀里飞了出去。鸡蛋纷纷从箱子里长了翅膀一样四散逃逸,在三奶奶急切慌乱眼神的注视下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然后伴随着啪啪的碎裂声砸在地面的碎石上,金黄的蛋汁泼洒一地。
妈,你怎么啦?秀秀惊讶地喊着,朝三奶奶跑过来。
三奶奶,三奶奶……是虎婶大儿子大成子的声音。
三奶奶,当年是我不好,我错了,是我错了。跪卧在地上的三奶奶隐隐约约听到虎婶的声音,那声音那么轻,那么缥缈,听起来那么不真切,好似做梦一样。三奶奶想坐起来,想努力看清虎婶的模样,可是她又感觉到自己飘起来了,像一片树叶一样,从地面飞了起来。她渐渐看谁都模糊了,秀秀的脸,大成子的脸,虎婶的脸,还有老头子的脸,都越来越模糊成一团,她谁也看不清了,谁也不认识了,她离她们越来越远了。
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吧,虎婶从小城的医院被拉回来。大夫嘱咐虎婶回家后不能生气,饮食要注意凉的、硬的、冷的、辣的等等一大堆。虎婶机械地点着头,心思却迫不及待地飞回去了。她急切地想见到一个人。生病住院的这些日子她想明白了一件事:人和人之间较什么劲呢?当年若不是看到她过得比自己好,自己哪会做出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呢。自己要当面跟她讲清楚,要发自内心的道歉,要清清白白地叫她一声,“三奶奶”“三奶奶”……
可是就在虎婶从车上下来的那一瞬间,就看到了一个箱子从三奶奶的怀中飞了出去,黄灿灿的蛋汁在她面前漫天飞舞。她大声叫着三奶奶,也趔趔趄趄地奔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