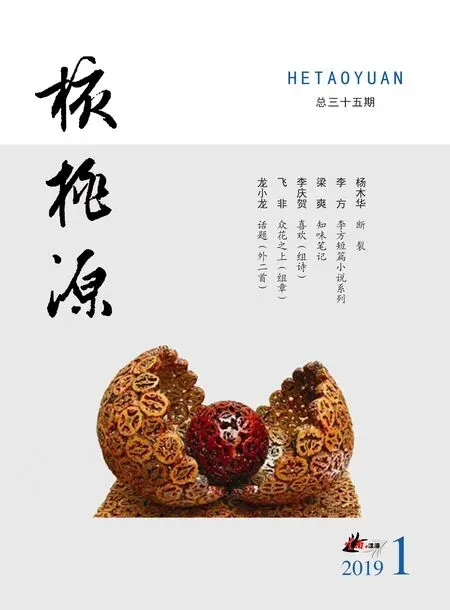李方短篇小说系列
李 方
荞面油圈
进入十月,各级各类培训就多了起来,这可以看作是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新特点吧。倒不是全无必要,但起码有一多半是生拉硬拽、胡乱拼凑的。过去,胡吃海喝的事情太多,进入十月之后,各单位经费吃紧啊。想想,吃喝就像一场接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役,从年头打到年尾,弹药消耗殆尽,都开始哭穷啊,要求计划外拨款,追加经费投入。现在不行了,没人敢明火执仗地吃喝了,年初拨下来的钱,有一些安静地躺在单位的账户上,像养尊处优的女人。看看年底,再不想办法花掉,只能睁着圆眼被财政上收回去,就像那些女人因为生理欲望得不到满足而跟人私奔一样。不但如此,细究起来,还有怠政的罪责不能逃脱。
怎么花钱,当然是个艺术活。唯一正当的理由,是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把大家召集起来,请上几个这一领域挂得上号的主管、领导,按照专家、教授的标准付给讲课费。大家坐在下面,领导坐在上面,但不是讲话而是讲课,领导在满足了平常的权力欲之外,也很高兴有别样的自豪感和满足感,不时学者一样抹抹头发、扶扶眼镜;台下坐着的下属,也不是平常那样地拘谨和腼腆,是受训而不是挨训,自卑感减少了许多。大家的心情是舒畅的,神情是愉悦的,会场气氛也是融洽的。就是吃饭,也很有年夜饭和国外派对的情调,自助餐嘛,端着盘子四处游走,碰上对劲的人,还要站在餐桌边绅士般交谈两分半,真是不亦乐乎,皆大欢喜。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次年末培训会上,见到女人的。
自然,培训也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既不能安排到风景名胜区,也不能食宿在星级宾馆里。这次,主办方将培训班安插到一个四周荒凉、飞鸟绝少的新建培训机构里。这里既不通公交车辆,出租车司机也摸不清方向。因此等我赶到时天上的星星都已出齐,晚饭早已结束。在报到处领取了培训材料和房卡,进入房间后,身心俱疲,也没了食欲。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就翻看培训人员名单。女人的名字非常突然、非常刺眼、非常触心地跳了出来,使我一骨碌从床上翻了起来。
抑制住心的狂跳,仔细地打量安静地泊在表格方框内的那三个汉字,那个很女性化的名字,不能确定就是她。这世上有几十亿人,中国就有十几亿,汉字就那么几个,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就像《中国青年报》的李方,经常为我赢得莫大的荣耀一样。再看工作单位一栏,是一家演艺集团。这倒是极有可能成为她。联系方式一栏内是一串数字,是个手机号码,还有她住宿的房间号。
差不多过去十五年了。
十五年前,我虽然已经结婚,但还不像现在这样老。从事着一种既写本子又兼导演的工作。这个女人(我想当然地认为她已经结婚成家了)还是个女孩子,刚从艺术学校毕业,待在家里找工作。我导演一台话剧,需要大量的、受过艺术训练的演员,她就来了。百灵鸟一样,叽叽喳喳,话多,语速快。但是录用的程序很简单,看简历,面试,录用。确定了她饰演一名雏妓。
你能行吗?
行。绝对行。
对这个角色?
没问题导演,演什么都行。不会我可以学嘛,我喜欢挑战。
让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女孩子演雏妓,这相当残忍,但非常具有挑战性。她不认为是残忍的安排,也愿意接受挑战。
一切游戏,都有规则,包括规则下面的规则,如同静水深流,河床上却遍布深坑大石。事情过后,知道她不是初夜,我心理上的压力轻了许多。
这可真是一个既开朗又开放的姑娘。此后一个多月紧张排练,女孩子的艺术水准无可挑剔,唯一让我感到有点不舒服的是这女孩子的话太多。所有空闲的时间,都能听到她麻雀一样,喳喳喳,喳喳喳。这期间也有过几次,同时了解到她的父亲离婚另娶,母亲改嫁远走,从小她就跟着奶奶生活,奶奶有糖尿病,一直吃荞面。
一个月后演出,无所谓成功不成功,就是做完了一件事情,各方面都有个交代,面子上能说得过去而已。
回到固原,全体作鸟兽散。只剩下女孩和我。
女孩子说:饿了,要吃。
吃什么?
吃荞面油圈子。
这叫什么吃呀?吃个面都不好意思。最差也得吃个火锅、手抓羊肉什么的,吃荞面油圈算什么呀?
就吃荞面油圈,再啥都不吃。竟有些新婚娇妻的恃宠撒娇。
荞面油圈是小吃,只有柳树巷子里有卖。
荞麦不含糖,属小杂粮。用荞面制作的油圈,油而不腻,酥,软,中间空,像淡灰玉环,如黑红手镯。
卖荞面油圈的大妈见怪不惊,或许在心中暗喜,能够遇到这样的顾主,只问价,不讲价,不确定数目,吃多少算多少。女孩不矫揉造作,拿起来就吃,皱着鼻子,两粒雀斑欢快地跳跃。吃过两个,女孩的双唇上就沁出了淡淡的油渍,拿捏油圈的三个手指头也像出了汗一样,她就把手指放到嘴里去吮吸。夏日强烈的阳光穿透柳树巷两旁的树叶,把细碎的光斑投射到她的头发上、脸庞上和手里举着的荞面油圈上,油画一样刻在我的脑海里。
不多不少,共吃了十八个。女孩子八个,我十个。总共花费九元。
以后多联系,有新剧目的话,记得联系我哦。女孩子掏出纸巾擦着手上的油渍蹦蹦跳跳地出了柳树巷。
我知道手机是手雷。我害怕输入女孩特别女性化的名字让老婆发现,想到刚才吃的荞面油圈,就将女孩的手机号码姓名标注为“荞面油圈”。这样,即便她以后打来电话让老婆看见,我就有理由说去医院检查过有糖尿病,医嘱要多吃荞面。并且真地买了一包荞面油圈带回去。话说回来,荞面油圈,也确实好吃。
那天晚上,我强忍着糖尿病带给我的痛苦,没有和她联系。按理说,她也有培训花名册,如果她还有记忆,那么应该知道我也在某个房间里安睡。她没有动静,我这样的年龄,唐突地给她打电话,就有些太不像话了。
课间休息的时候,两人都平淡着各自的表情,像是偶然在大街上相遇的一样,走在四散休息的人群中。除了岁月的风尘和俗世的困顿留在额头上的印记外,她没什么大的变化。
在她的眼中,我大概也是如此吧。
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平声静气地说:那次演出后,奶奶去世了,我就考进了现在的演艺集团,这些年一直都在巡回演出。
她没有谈及家庭和这十余年生活的细节,也没有质问我为什么没再跟她联系。生活就是这样,会深埋一些事情,如果你不愿意将往事的骨骸挖出来暴晒,就不会有绝望的气息散发。你甚至会恍惚,那些事真地发生过,还是仅仅在梦境中出现过。
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确实很长,我觉得就像过去了十五年。如果她还像十五年前那样百灵鸟般或麻雀一样叽叽喳喳,时间可能会过得快一点。但是,她的话很少了。没有人能逃脱生活的追捕和折磨。
上课时间到,重新回到各自的座位上,恰如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当天晚上,我在培训机构的周围走了一大圈,既没有发现有别的宾馆、饭店、商铺,更别提有卖荞面油圈的摊贩了。
因为,我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了。
生汆面
出固原城东门,过菜园子,沿清水河一路北行,可直达三营镇。
清水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河两岸,杂树生花,庄稼掩映,东西两山,苦不甚高,却都蜿蜒曲折,高低起伏地错落着,两山加一川,护卫着河床。到了三营这里,东面的山是麻狼山,西面的山名叫须弥山。麻狼山就是麻狼山,过去,生态环境不像后来那样恶劣,狼是很多的。狼的毛色以灰麻为主,所以三营周边的人对一些明显的、不容置疑的事情,往往口气很硬地说,你还不相信狼是麻的,我要让你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马王爷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从颜色艳俗的老式年画上看,但狼是麻的,这个却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过去狼患严重的时候,专门成立有打狼队,逮住、打死的狼无一不是灰麻的。
西面的须弥山说起来有点小复杂。须弥是梵语妙高的意思,佛教的解释是:须弥山是世界宇宙的中心。一望而知这座山是个香火鼎盛之地,也是佛像雕塑建造集中之地。但当地人一般都不这么叫。说起来都叫寺口子,这是比较有人间烟火气的叫法。山上建寺,两山对峙,寺口子,寺口子山。其实寺口子也不是这么几个字,应该是四口子。孙悟空大闹天宫,与带着哮天犬的二郎神君杨戬斗得天昏地暗,二郎神施魔法,将两座山赶往一起,要把这个处于丝绸之路上的石门关关起来,夹死孙猴子。他赶着两座山快要合拢的时候,正好有个脚户吆着一头怀了驴驹的草驴,驮着他怀孕的妻子通过石门关。妇人看到两山快速移动,惊呼一声:啊呀,我的四口子。女人的这一声喊,破了二郎神的法术,两座山戛然而止,停了,不动了。孙悟空虽然后来被如来佛压在了五指山下,但四口子这个地名还是在民间保留了下来。
三营镇就处在须弥山和麻狼山的中间地带,紧靠着清水河。
清水河现在是没水的,不像过去,水势浩大,载筏扬帆,直下黄河。现在是满河床白花花的石头。
三营这个地名是从明朝叫起来的,民间的说法是宋朝时杨六郎把定三关口,杨三郎在这里驻军和西夏人打仗,所以叫三营。其实是明朝廷重视马政,派杨一清到清水河流域为国家饲养军马,沿河一溜儿摆开,共设八座营,就像是清水河沿岸结的八个葫芦娃。
河里没水,岸上有路。三营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了旱码头。从这里,往西,过寺口子的石门关,就是汉丝绸之路古道,朝凉州去了;往北,也是汉丝绸之路古道,是奔中卫黄河古渡去了。都是丝绸之路,不过一个是北段西道,一个是北段北道而已。因为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因此形成了商贸繁盛、货物集散的大市镇。
有道有市,就得有酒肆饭馆车马店。
俗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干啥的把啥干,犁地的把牛喊,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到了现代,三营镇上就研究发明出了一种面食,叫生汆面。
琢磨出生汆面的这个人,姓马。当初研创生汆面的时候还年轻着。年轻人眼界宽、心思活,他看到南来北往的大车司机要在这里歇脚打尖,赶集贸易的人都要吃饭,就开了一家小饭馆。当然是以各种面食为主。三营这个地方不种水稻,不产大米,没几个人喜欢吃米饭炒菜。新疆拉条子、油泼辣子拌面、臊子面、洋芋面、炒寸节、烩面片……都是些家常饭,可口,饱肚,就是没特色。老马琢磨来琢磨去,就发明了生汆面。
面是纯粹的旱地红芒麦用石头磨子磨出来,这样的面粉做出来的面,即便是用开水煮熟,就有一股麦香味儿。然后用牛肉,加入各种调料剁碎,团成圆疙瘩,桂圆大小。水先烧开,揪面片下锅,把牛肉丸子汆到开水锅里,一起煮熟了,出锅,调盐、醋、油泼辣子、香菜,非得配一小碟咸韭菜,大蒜过口,不然不成体统。色香味俱全的这一大老碗端上桌,蹲在长条板凳上,大汗淋漓地吃。
吃完算账,八毛钱一碗。到今天,已经是十八元一碗了。
任何商品的口碑,都是不长脚而走天下的。因为跑长途的大车司机口口相传,也因为当地食客的赞誉,老马的生汆面很快就创出了牌子,逢到集日,只能排队等候。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生汆面刚好研制出来。我在须弥山脚下的一所乡村小学当教师,精力过剩,业余时间捏着笔胡涂乱抹,谓之文学创作,其实就是瞎胡弄,为周末不回家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有两个和我一样半吊子的文友在三营当孩子王。周末了,骑着自行车,晃到三营去,海阔天空地胡扯一气,说得口干舌燥了,一看, 到吃饭的时候了,走,吃生汆面去。
就是从每碗八毛钱吃起,一直吃,一直涨。吃到每碗十元整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份也吃出来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来了,也轮得上我们兄弟接待陪伴了。
李敬泽清瘦着一张脸,眯缝着一双眼,按部就班地参加完官方组织的活动后,要去须弥山看看从北魏就开凿的石窟造像。就欢天喜地地陪着去啊,专挑保存得好的、精美的雕像看,从大佛楼一直看到相国寺,看得他兴趣盎然。到了中午,饿啊,要吃饭。当然是要吃点好的。山下就有农家乐,想着要表现一下,这是李敬泽啊。但李敬泽平静着脸,说,吃个小吃,吃个特色。
这好,就到了三营,吃生汆面。
给已经胡须花白的老马介绍了,说这是从北京来的客人啊,专门来吃你的生汆面来啦,好好招呼着,精心做着。
老马已经无需亲自动手了,儿子、女儿、儿媳、女婿一大帮在厨间忙活,他陪着我们坐,闲聊。
饭端上来了,吃吧。
吃着,问李敬泽先生,味道如何?
李敬泽是厚道人,礼貌地回答:挺好。
没想到老马叹息一声:不行了,远远不行了!现在,面是别人的,不是我的;肉是别人的,不是我的;调料也是别人的,不是我的。只有手艺是我的。但肉是注了水的,面是机器磨出来的,调料是掺了假的。别人看着我的生意好,也照猫画虎地模仿着做,你看这三营一道街,每家面馆都做生汆面。饭的味道差了,生汆面的牌子也倒了。世道人心坏了,面的味道怎么能好呢?
李敬泽不吃了,停了筷子听着。
回京后,他把这件事写在他的散文《寻常萧关道》里,刊发在《朔方》文学期刊上。
在文章中,李敬泽这样写到:“面其实很香。吃完了,老人把我们送出门口,他的脸上有郁闷的歉意,他又说了一遍:人有钱了,心狠了,假的多了。萧关道上,我记住了这个名叫马登元的老人。”
斯 文
我曾经受邀参加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诗会,至今念念不忘。
诗会的主办者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功成名就、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在主办者看来,那些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了两行半的诗人,都已经成为老朽了,到了该死的年纪而没有死去,是比较惹人厌恶的,枯死的叶子颤颤抖抖,在风中摇摆而不肯凋落,是会影响新芽冒尖的,这可能是主办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受邀参加的人,大都是在正经诗刊上发表作品时被排在末尾而在民刊上被刊登大幅照片、作品打头条的年轻诗人,当然,那些非常年轻但讲究平仄对仗而写古体诗的诗人,也没有被邀请。怎么说呢?那是些已经具备生殖能力但仍吊在母亲乳头上的低能儿,他们试图在古体诗歌的乳头上汲取现代的营养。这可能是主办者内心的另一种想法。
这个诗会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但有几位异常活跃的参加者在不停地用高档相机拍照,后来听说,他们是几家颇有影响的官媒的文化记者,万幸的是,他们在写真实具体的新闻稿件之余,也写一些云遮雾罩的现代诗,因此受邀参加诗会,并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次青春的盛会报道出去。
可见,现代诗并不排斥某种世俗烟火气。
举办诗会的所有经费,由网名“农妇山泉有点田”提供赞助。这个网名翻译成大众能懂的汉语,意思是半老徐娘、山泉写诗、有点闲钱。她经营着一座山庄,会场就安排在她的山庄里。
早上报到的时候,我专意找到徐娘聊天。虽是春天,清晨犹凉,她在衣服外边,加了一条围巾。在尚未离职、经营这座山庄之前,我经常在她主持的报纸副刊上发表发表现代诗。
放着好好的诗歌编辑不干,怎么会想到经营这么一座山庄呢?
她露齿一笑:报纸副刊不比你们官办的纯文学期刊受人尊重且有保障,赚钱生存是第一要务,副刊常常被广告霸占,干着没劲。
期刊也没劲。我挺到她面前,看了看围巾的牌子:巴布瑞。山庄怎么样?我环顾四周问。
起码自由。她指着一片油菜花:开不开花无所谓,有点颜色就行。
有个长发披肩、雌雄难辨的人插进话来:徐总,篝火晚会用的柴火在哪儿?听声音才知道是个男人。
徐娘抖一下围巾,转身一指:就在梅兰厅的后面。然后对我说:你四处走走,看能否泡上个妞,晚上给你开单间。
留下淡淡的香气,拂柳穿花地走了。
就是比当报纸副刊编辑的时候优雅。
上午的研讨会是比较无聊的。北中国几乎一大半的诗歌民刊主编们乌烟瘴气地公开发表着主办者的那些内心想法。春困顽强而执着地攻击着眼皮,我不得不大量地喝水从而不停地上厕所。好在没人理会你是谁,你在干嘛。没有官员参加就有这个好处,用不着正襟危坐。
我每一次上厕所出去或者进来,都会看到坐在门边上的一个容貌清丽的女孩子向坐在她旁边的那个长着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吐舌头。
舌头有什么好看的呢?
实在想不明白。
他们这样年轻,也会是现代诗的写作者吗?我很怀疑。但是:“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据说这是一个七岁孩子写的现代诗,那么,他们应该也是现代诗的作者了。
午餐后,一辆旅游大巴车满载着诗人们,拉到西夏王陵,撒羊粪一样将这些被青春和诗情鼓胀得难受的人放逐到九百多年前的那些东方金字塔之间,他们的情绪才多少得到了稀释和排解。
贺兰衔金乌,余晖照王陵。
回到车上,就有人迫不及待地站在车厢内的过道上声色俱厉地吟哦起了长诗,把西夏的历史和几座著名的陵墓搬上了大巴车。但疯狂地奔跑和臆想了一个下午,大多数人又累又饿,反响不是很热烈。
主办者奉劝:留点力气和精神,朗诵会上再峥嵘。
果然,吃饱喝足,被羊肉和白酒重新唤醒的激情是那样强烈、浓郁和不可阻挡。我都记不清有多少震撼我心的诗句被熊熊燃烧的篝火化为了灰烬。我只记得,那个一直吐舌头的女孩子,穿着透明的胸罩和闪闪发光的三角裤头,捧着一本《诗经》上场了,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端着一盆水跟在她的屁股后面。然后,女孩子坐下来,小伙子跪在她面前,将女孩子的脚捧着放进盆子里,双手揉搓着为她洗脚。女孩子开始千娇百媚地朗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太突兀了。就像早晨突兀地打断我和徐娘的聊天插进来询问篝火晚会用的柴火在哪儿一样,那个披头散发的男人狂奔过去,一脚将小伙子踹倒在地,大喝一声:日你娘!不许你如此侮辱诗歌……端起那盆洗脚水完整地倾倒在女孩子的头上……女孩子尖叫一声:臭流氓!
然后,场面就失控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事先安排好的行为艺术表演,等我头上也挨了不明不白一砖头,血流到脸上脖子里以后,才明白诗会已经变成了群架场。
简直是斯文扫地。
但至少证明我也曾经年轻过。
执 着
从来没有吃过作者饭、喝过作者酒、抽过作者烟的文学期刊编辑是没有的。如果有,那是比较可悲的。说实话,那样的编辑反而不会被作者喜爱和尊重。
因为编辑是人,作者也是人。
既然是人,就免不了俗世的一切。
我就多次被作者请出去吃饭喝酒,人模狗样地坐在餐桌前,接过作者双手敬过来的香烟,啪地唤醒打火机里的丁烷气,很大气很随意地抽着,感觉特别潇洒、帅气,特别像一尊人物。
就这样结交了一大帮古模怪样的作者朋友,天南地北、男女老少都有。尤其是年轻漂亮而又愿意将才情智慧挥霍在创作上的女作者,每次见面小聚都格外亲切、亲近和亲热。但绝不亲密,反而对她们这样执着于文学创作深感惋惜。
要知道,从事文学创作是相当枯燥、相当寂寞、相当孤独的事情啊。
但有一个女作者的宴请,使我对她刮目相看,且记忆犹新。
她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员。
在小地方,像她那样的女人,官能做到市直部门一把手,算是非常成功的了,却偏偏在业余时间喜欢搞创作。
有次周末,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打电话约我吃饭,特别讲明是那个女官员想和我坐坐。我一听浑身打了个激灵,忙说:吃饭免了,她要有什么新作可直接发到我的个人信箱,我会认真拜读的,况且我正在乡下老家陪父母。
挂了电话,慌忙用手机拍了一张父母在老宅前晒太阳的照片,通过微信发给了朋友,这样他也好给人家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我见识过这位女官员的“文学作品”。她当然不可能屈尊亲来编辑部找我,而是委托下属将她自行打印装订的“作品集”交到我手上,名曰:斧正。看是否达到了出版的标准,顺带提提“宝贵意见”。
我抽空大致地翻了翻,十多万字,分为多辑。一是写童年回忆,二是写人生感悟,三是写为官之道,四是写夫妻相处,五是写人间真情……大体如此吧,是一个初学写作者的对月吟怀、感花缅草、咽饭思艰之类。最奇怪的是她认为夫妻二人,就像身体上的左手和右手,所以“左手加右手,托起一个爱”,这个爱才组成了家庭。
多么可爱的文字,可惜不是文学。
因此让人害怕和她坐在一起吃饭。
但一个人如果执着于某件事,总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她约请我们刊物的主编吃饭,他们的级别是对等的。主编顺带叫上我,但并没有说明是谁请客。
到了地方一看,她很官员地坐在主位上等着我们。
这多么让人感慨啊。
饭桌上,她将已经正式出版的“左手加右手”分赠给主编和我。
她左手托腮,面露潮红,微笑着说: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我这个集子,肯定不会入二位的法眼,但总是自己的孩子嘛,自爱是免不了的。
说实话,光是那种恶俗的铜版纸封面的精装,就让人受不了,里面的内容,依然是以前的那几写。只好感叹出版业的不景气,竟然会造成如此不堪的结果。
席间,她不止一次地向主编暗示:集子是自费出版的,里面的文章都未曾正式发表过,看能否选择一两篇,在我们主办的刊物上“登一下”。
主编一直打哈哈。
汽锅三鲜上桌的时候,她操起自己的筷子看了看,上面粘着一片绿菜叶,她将筷子送进嘴里,咂摸掉了菜叶,然后伸进蒸锅里,小心翼翼地夹起了一颗肉丸子,刚夹出锅,肉丸子就逃脱了枷锁,滚到了餐桌上,她神情专注地盯着肉丸子,准确而又稳妥地再次将肉丸子夹起来,然后轻轻地放到了主编的餐碟里。她卸载般快乐地松了一口气,对主编说:吃丸子。吃丸子。主编身子向后缩着,摆动双手说:吃好了吃好了。自己来自己来。她盯着主编的眼睛说:吃个丸子么,能有多大分量呢,我专门为你夹来的……
在她深情专注的盯视下,主编只好拿起筷子夹起丸子送入口中。
宴请结束回来的路上,主编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你选一篇,登上去!如此执着的人,应该让她发表作品的梦想成真,而不是落空!
音乐家
那一年,CCTV-3和CCTV-6在主打节目的间隙里,不断推出全国各地以生态旅游为主题的MTV,直接催生了地方官员以同类形式宣传当地旅游的音乐风光片热潮。
经济发达地区搞这些玩意儿是比较热衷的,也是比较轻松的,大不了花几个钱的事,看着舒心,听着悦耳,宣传地方,促进旅游,名声在外,政绩上也说得过去。
但小地方、穷地方怎么办?只能照着老虎画猫。这些地方的官员是这样想的:你请的是名家、名导、名演、名唱,上的是CCTV;我呢,我请当地的词曲作家,录制成歌曲,转换成手机彩铃,在全县传唱,广播里播放,总不成问题。
音乐家和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请去采风、创作歌曲的。
音乐家的名气比我大一些,年龄也比我大出那么一小截。他是土生土长的音乐人,对当地民歌、谣曲、神调烂熟于心,又在中央音乐学院深造过,他所创作的歌曲,风格上是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调,冷不丁地会加进去那么点空灵缥缈的学院味道,所以大受欢迎。
音乐家打电话给我:你想带谁就带谁,反正吃喝拉撒都由县上管,来去一周时间差不多了。
我那时恰巧单身,就约了一位曾有过肌肤之亲的女朋友。她没有正经职业,是个跑保险的,隔三岔五到银行溜一圈,查查她所签署的那些保险单是否到账,所以乐意跟我到山区小县以著名词作家女朋友的身份散散心。
一见面,音乐家就直了眼睛将我女朋友从头细瞅到脚面。六月天,气温高,女朋友穿得少,也就是在关键部位安置了几片“盾牌”,细高跟,又没穿丝袜,十个脚趾头像十枚红豆,不停地蹦跳。
音乐家说:凉快是凉快,但不适合山野小路。
女朋友天真地问:还要到山野里去啊?
我说:起码,要实地看看吧。
女朋友对音乐家说:到了县城,我买一双旅游鞋。
等女朋友不在跟前时,音乐家摇着满头白发说:你干嘛背着石头上山啊?
我说:你不是说……
音乐家用五指梳理着头发说:我是提醒你,别带着……县里面好女人多的是。走吧。
音乐家的满头白发,并不代表他年纪有多大。他是少白头。但这头浓密的白发,为他的知名度和权威性帮了不少忙。
山里面果然好风景。
首先是凉,自然风;其次是绿,哪儿都是草和树;再就是静,是那种大自然悄然生长的静,让人既感到辽阔寂寞,又在心底里揣着一点疑惧的静。
这个县盛产一种野生果,秋天成熟的时候一嘟噜一嘟噜缀满枝条,像大火燃烧起来那样红,现在全绿着。女朋友就有点生气,说,干嘛不在秋天来采风创作,这野果也不能吃。
音乐家拍拍女朋友翘起来的屁股:现在也能吃。小冯,给女嘉宾拿瓶沙棘汁来。
开车拉我们采风的县委宣传部司机小冯,是个不走路都气喘的大胖子。听到吩咐,像孕妇一样挺着肚子抱着几瓶黄颜色的沙棘汁摇过来,满脸满脖子的汗。
女朋友跑去接沙棘汁。她穿着音乐家在县城给她买的旅游鞋。本来是我买,音乐家说第一次见我女朋友,权当是送个见面礼。我看了一眼女朋友的背影,转过脸瞪着音乐家说:你不该拍她的屁股。
音乐家一脸诧异地说:又不是老婆。
女朋友喝着酸甜爽口的沙棘汁严肃认真地对我说:你真该为沙棘果写首歌。又转过身对音乐家说:你来谱曲吧。
好!音乐家仰头灌了一气沙棘汁,说:就凭你刚才这一笑。
对着我是严肃认真的表情,转过身就成笑脸了?
晚饭的时候,大家都坐在圆桌边等待上菜。音乐家拿过去用来泡八宝盖碗茶的空碗,将饭桌上放着的醋壶里的醋倒在碗里,一仰脖喝了个干净,我女朋友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用不着大惊小怪,这里的醋特别好喝,完全可以当饮料,不信你尝尝。音乐家企图劝我女朋友也来一碗。
我沉着脸用手拦着:别。再闹我真吃醋了。
满桌人都哼哼哈哈地笑起来。
凌晨三点,疲惫不堪的我睡得正香,手机微信铃声叮咚叮咚响个不停,连女朋友都吵醒了,说:啥时候了?是不是半夜鸡叫?
我打开微信一看,是几张音乐家和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躺在被窝里的图片。紧接着又来一条微信:随手捡的石头。
我赶紧关了手机,对女朋友说:你睡你睡,是音乐家有灵感了。
从山区县回来后,我传给音乐家两首歌词让他谱曲。大合唱的歌词,署的是书记和县长的名字,署我名的那一首歌叫《沙棘姑娘》。后来我听说,大合唱只在县上汇演的时候唱过一次,倒是《沙棘姑娘》制作成手机彩铃,到现在还有人用。
我还听说,音乐家和我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婚礼现场播放的也是《沙棘姑娘》,纯音乐,没有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