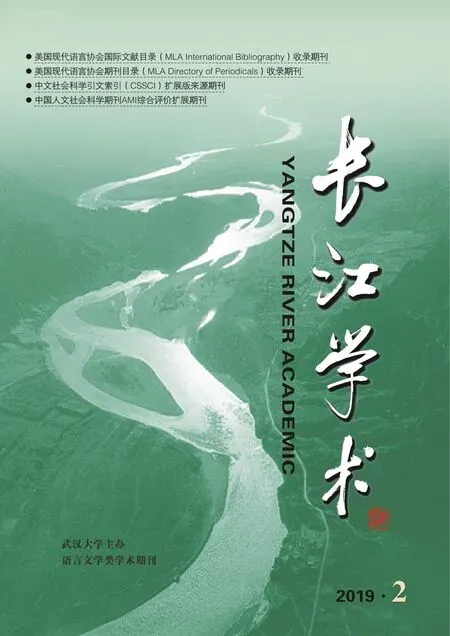况周颐的词籍序跋与其词学思想
孙克强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词籍序跋是词学批评和理论的重要载体。较之词话,词籍序跋甚至可以更为集中、直接、明晰、深入地表达词学思想。在词学史上有许多词籍序跋的名篇,如欧阳炯的《花间集叙》;有不少词学家更是以词籍序跋作为表达词学思想的主要手段,如陈子龙、陈维崧、朱彝尊、厉鹗等。况周颐以词话闻名于世,但他的词籍序跋有同样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无疑是其词学批评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其词学思想的重要表现。
一、词籍序跋的种类及创作背景
况周颐从少年时期开始填词,终生创作不断,并编辑了多种个人词集。同时作为一个深有研究的词学家整理了多部古今人的词籍。况周颐中年之后,在词坛上的地位愈加显赫,不断有词学界的朋友将自己的词集或编选的词选请他作序。况周颐在编辑整理阅读这些词籍时,写下不少序跋文章。或叙述创作编辑经过,或记录词籍中的版本文字校勘,或阐发鉴赏心得,或发表词学见解。特别是况周颐的词籍序跋大多注明了写作时间记录,这是认识写作背景、了解况氏的心路历程最为直接的参考文献。
按照况氏词籍序跋的种类,可分为自序、古今人词集序跋和当代词选序跋三类。况周颐以词名,为晚清大词人。一生自编有多种词集,所有词集均写有自序,记录了各种词集的刊刻经过、词集的背景主题、创作的心路历程等。现存词集自序有:
《养清书屋存悔词序》(己卯1879)
《存悔词序》(壬辰1892)
《蔆景词序》(戊戌1898)
《玉梅后词序》(丁未1907)
《二云词序》(甲寅1914)
《餐樱词自序》(乙卯1915)
况周颐一生钟情于填词,亦终生深研词学,对古代和当代词人的词集十分留意,对不少词集下过很大功夫。况周颐曾在王鹏运的引导下参与四印斋词集的整理校勘工作,为许多古今人词集写过序跋,序跋中叙述了版本源流、文字校勘以及艺术鉴赏心得。
其中唐宋词集序跋有:
《阳春集补遗跋》(冯延巳)
《逍遥词跋》(潘阆)
《梅词跋》(朱雍)
《燕喜词跋》(曹冠)
《养拙堂词跋》(管鉴)
《校补断肠词跋》(朱淑真)
《秋崖词跋》(方岳)
《梦窗甲乙丙丁稿跋》(吴文英)
《章华词跋》(佚名)
《清庵先生词跋》(李道纯)
元人词集有:
《樵庵词跋》(刘因)
《养吾斋诗余跋》(刘将孙)
《蚁术词选跋》(邵亨贞)
清人词集有:
《东海渔歌序》《东海渔歌校记》(顾春)
《和小山词序》(赵尊岳)
《题程颂万美人长寿盦词》(程颂万)
《和珠玉词跋》(张子苾、王半塘、况周颐)
《半樱词序》(林铁尊)
《李慈铭书陆刚甫观察仪顾堂题跋后跋》
《冰红集序》(蒋玉稜)
清末民初词坛繁盛,不少词家或出于展示一代之盛况,或出于宣传词学思想理念,或出于启蒙宣传等目的,编选了大量词选,况周颐曾为一些朋友编选的词选撰写序跋,这些词选有古代词选,如《宋词三百首序》《蓼园词选序》;有当代词选,如《绝妙近词跋》;有地域词选,如《历代两浙词人小传序》《州山吴氏词萃序》《粤西词见叙录》《粤西词见跋》;有女性词选,如《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序》;亦有同人词选,如《薇声词钞例言》。况氏的这类词选序跋,或指明选编主旨,或阐述作品特色,或分析选域背景。
况周颐为自己的词集所写的自序,不仅交待了词集中词作的写作背景、词集编纂缘由,还阐发了自己的创作心路历程和词学思想。
况周颐的一些词籍序跋说明词集的名称由来和创作背景。如《蔆景词序》说明了词集命名的原因:
乙未九月,《秦淮即事》〔金缕曲〕句云:“憔悴菱花年时影,忍向天涯重见。况呜咽、秦淮翠晚。别有西风消魂样,是芙蓉、老去鸳鸯散。盖有所触,绝此所为词,因以为名也。”
所谓“蔆景”即镜中映像,“憔悴菱花年时影”道出了况周颐时光流逝青春不在的喟叹,因以为词集名。况周颐的《蔆景词》大多是怀念王鹏运的作品。赵尊岳《蕙风词史》云:“(况周颐)先生后此去京师,南游由金陵而维扬,《蔆景》一卷,即其时作。亦多感逝伤离之音,而睠睠于半唐者独深。〔齐天乐〕、〔忆旧游〕、〔角招〕、〔寿楼春〕诸阕,均为半唐。”况周颐亦曾说明:“余与半塘五兄,文字订交,情逾手足。乙未一别,忽忽四年。《蔆景》一集,怀兄之作,几于十之八九。”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况周颐离开北京南下,《蔆景词序》写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此时况周颐与王鹏运分离已有四年。“蔆景”的时光之叹亦有与王鹏运的友情之念。
况周颐的《蓼园词选序》记载自己词学启蒙的历史:
曩岁壬申,余年十二,先未知词。偶往省姊氏,得是书(按:指《蓼园词选》)案头,假归雒诵,诧为鸿宝。由是遂学为词,盖余词之导师也。
《蓼园词选》的编著者黄苏,生卒年均不详,原名道溥,号蓼园,临桂(今广西桂林)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人,曾官知县。黄苏是况周颐姐夫的曾大父,曾选编《蓼园词选》。况周颐的词学生涯即从学习这部词选开始。黄苏生活年代与常州词派的领袖张惠言大致相当,由于资料缺乏,无从得知二人之间有无交往。从《蓼园词选》黄苏的批语看,其论词方法却与常州词派的“家法”颇为接近,如黄苏在《蓼园词选》中论词讲求微言大义,常以男女之情比之于君臣家国之意。如云:“士不得志,而悲悯之怀难以显言,托于闺怨,往往如是。”“托意深微”,“托闺情以写意”,“当或亦别有寄托”等等,《蓼园词选》中此类议论比比皆是。可以说,黄苏的词学思想对况周颐走上常州词派词学的道路具有重要影响。
《二云词序》写于民国三年(1914)。所谓“二云”,即指当时生活于上海的两位知名女性傅彩云及朱素云。赵尊岳《蕙风词史》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二云词》以赠傅彩云及朱素云二词为名,盖先生有所寄托,讳以二云也。其自跋云:‘以二云名,非必为二云作。’”指出此词集虽然以两位女子之名命名,其实表达的是别样的情志。况氏《二云词序》云:
岁在癸丑,避地海隅,索居多暇,稍复从事,顽而不艳,穷而不工。姜白石乘肩小女,花月堪悲;张材甫回首长安,星霜易换。此际浔阳商妇,琵琶忽闻,何堪旧人,渭城重唱。有不托兰情之婉娩,缔瑶想之蝉嫣者乎。重以江关萧条,知爱断绝,言愁欲愁,则春水方滋;斯世何世,则秋云非薄。似曾相识,唯吾二云,二云而外,吾词何属,以二云名,非必为二云作也。
清朝亡覆之后,况周颐以遗老身份寓居上海。改朝换代的变化使况周颐充满了悲凉的感慨。《二云词序》中用到宋代词人姜夔、张伦(抡)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典故。此三人虽然不在同一时代,但其作品中皆有星移斗转、物是人非的感慨。如序中所说“张材甫回首长安,星霜易换”,张伦(抡)字材(才)甫,自号莲社居士,开封人。为南渡词人,后人辑其词为《莲社词》。况周颐言及之词为〔烛影摇红〕《上元有怀》,全词云:“双阙中天,凤楼十二春寒浅。去年元夜奉宸游,曾侍瑶池宴。玉殿珠帘尽卷。拥群仙、蓬壶阆苑。五云深处,万烛光中,揭天丝管。 驰隙流年,恍如一瞬星霜换。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可是尘缘未断。谩惆怅、华胥梦短。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此词写上元夜的感触,通过南渡前后两次上元夜的对比,抒发了故国之痛、家国之悲,正如况周颐所评:“此词情真调楚,悃款缠绵,故国故君之思溢于楮墨之表。”
况周颐的《二云词》主题亦是如此。赵尊岳《蕙风词史》曾予以说明:“从可知之,傅彩云尝偕洪文卿使英。庚子之变,又在京师与德帅瓦德西游,饱更世变。迄辛亥后,又张帜海上。时如皋某君与之稔,介先生识之,遂投之以〔莺啼序〕。朱素云都下名优,工小生,传王愣仙、徐小香之学。方其在都,多与贵人游,先生夙习之。辛亥后,又来海上,谒先生寓庐,因为赋〔绮寮怨〕。”傅彩云,即沪上名妓赛金花,早年沦于青楼,同治朝状元洪钧娶作外室。洪钧受朝廷之命作为外交官出使俄、德、荷兰、奥地利四国。但洪钧的正房夫人王氏不愿同往,傅彩云遂以公使夫人身份随同洪钧出使欧洲五年,其间见过德国皇帝、英国女王还有铁血宰相俾斯麦,受到了王公大臣的待遇,俨然上流贵夫人。洪钧任满回国后不久病死,傅彩云为生计所迫,只得重操青楼旧业,并改名赛金花。朱素云是京剧著名小生,在北京梨园行知名度颇高,曾为清“内廷供奉”,多与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配戏。清亡后,寓居上海。“二云”皆有人生跌宕起伏的巨大变化。与“二云”的人生经历有某种相似之处,况周颐由清入民国,社会动荡同样给他以巨大的触动,况周颐是从傅彩云及朱素云的人生经历和变化引起了自身的联想和感慨。
二、词学思想的变化
况周颐的第一部词集为《存悔词》,为这部词集况周颐前后写有两篇自序,前一篇《养清书屋存悔词序》写于光绪己卯年(1879),后一篇《存悔词序》写于十三年后的壬辰年(1892),前后相距13年。这两篇序记录了况周颐关于“艳词”的认识及其变化。前序云:
吾生二十以外,便非妙龄。明镜笑人,黯然今昔。况复养花天气,薄暖清寒;殢酒情怀,才醒又睡。一春鱼鸟,不信浮沉;两字鸳鸯,也拌惆怅,寻芳倦矣,和影谁怜?不得已以恨遣情,以悔分恨,悔而存之,仍无不悔之一时也。央花比瘦,忏甚红愁;著柳伤离,依然绿苑。至若铜琶铁拨,尤多当哭之音;玉引砖抛,强索无憀之作。既无庸悔,更不足存。冬郎风格,不能例以香奁;秋士萧疏,不过好为妮语云尔。
写《养清书屋存悔词序》时况周颐20岁。况周颐在晚年曾说:“蕙风词有二病,少年不能不秀,晚年不能艳。”意为少年多写艳词,晚年不再染指艳词。况周颐少年词多写艳情,王鹏运曾批评其“淫艳”。《存悔词》词集名曰“存悔”,表面来看像是“悔其少作”,其实况周颐别有寓意。况氏云:“不得已以恨遣情,以悔分恨,悔而存之,仍无不悔之一时也。”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自己少年时期性灵情感的自矜自怜。“冬郎风格,不能例以香奁;秋士萧疏,不过好为妮语”,是说自己的艳词重情与香奁诗的浮艳不同,试图为自己的香艳词风加以辩解。从词学思想的角度论之,况周颐此时认同的是“词为艳科”的观念,认为情和艳是不可分离的。
13年后的壬辰年(1892)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重刻《存悔词》再次作序时已经与前《序》有了很大的差异:
余性嗜倚声,是词为己卯以前作,固陋。无师友切磋,不自揣度,谬祸梨枣,戊子入都后,获睹古今名作,复就正子畴、鹤巢、幼遐三前辈,寝馈其间者五年始决,知前刻不足存,以少年微尚所寄,未忍概从弃置,择其稍能入格者十数阕,录附卷末,功候浅深,不可彊如是,后之视今,犹今视昔,庶有进焉。
这篇序对《存悔词》所载的20岁之前的词作进行了反思,承认其“陋”,甚至贬斥为“谬祸梨枣”,与13年前相比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变化的原因是在戊子年(1888)来到京师,认识并得到端木埰(子畴)、许玉瑑(鹤巢)、王半塘(幼遐)的指教,从与三人相识到写此序时正好五年。此时况周颐的词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变化,“前刻不足存”,说明他已经否定少作的淫艳风格,此时所说之“悔”的涵义已经与13年前为艳辩解全然不同了。
正如《存悔词序》所言,况周颐写词由偏爱艳词到摒弃艳词的转变,端木埰和王鹏运的教导起到了重要作用。端木埰(1816-1892)字子畴,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是晚清词坛十分有影响的词学家,其词学思想为常州词派的体系。端木埰是晚清四大家的师长辈,对况周颐有直接的教诲。况周颐曾说:“端木子畴前辈,曩同直薇省,奉为词师。有感气类之雅,辄学邯郸之步。”况周颐奉端木埰为“词师”,可见对其影响之大。况周颐曾记载了端木埰对他作词的一次教导:
曩作《七夕词》,涉寻常儿女语,畴丈尤切诫之,余自此不作《七夕词》,承丈教也。《碧瀣词》〔齐天乐〕序云:“前人有言:牵牛象农事,织女象妇功。七月田功粗毕,女工正殷,天象亦寓民事也。六朝以来,多写作儿女情态,慢神甚矣。丁亥七夕,偶与瑟轩论此事,倚此纠之。”“一从豳雅陈民事,天工也垂星彩。稼始牵牛,衣成织女,光照银河两界。秋新候改。正嘉谷初登,授衣将届。春耜秋梭,岁功于此隐交代。 神灵焉有配偶,藉唐宫夜话,诬蔑真宰。附会星期,描模月夕,此作人间欢爱。机窗泪洒。又十万天钱,要偿婚债。绮语文人,忏除休更待。”即诫余之旨也。
这里提到的“七夕词”即况氏《存悔词》中的〔鹧鸪天〕《七夕》,全词如下:
眉样月儿分外幽。晚凉又是一天秋。好将韵事酬佳节,都把前欢当梦游。 何限限,几多愁。也无情绪问牵牛。谁家三五轻盈女,和月新妆上小楼。
此词通过写七夕故事,表现对爱情的向往,风格轻盈婉艳。应该说这是七夕故事带给年轻人的一般情愫。但是在端木埰看来此词没有沉挚之思,凝重之笔,正是端木埰“切诫”之“寻常儿女语”。端木埰的告诫是要引导况周颐走重、拙、大之路。端木埰亦曾写七夕词,与况周颐的《七夕》词形成对比的是,端木埰的词中将七夕写成农作事功的记录,断然否认七夕的男女爱情内容,不免有诗教的迂腐色彩,然而亦可看出端木埰反对词为“艳科”的观念,提倡词的认识和教化功能的思想所在。况周颐的《七夕》词是其早年“纤艳”风格的体现,也是端木埰批评的焦点。在端木埰的影响之下,况周颐的词风和词学思想开始转向,走上了“重、拙、大”的道路。
写于光绪丁未年(1907)的《玉梅后词序》记载了王鹏运对自己的教诲,以及关于“淫词”这一概念,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理解:
《玉梅后词》者,甲龙仲如玉梅词人后游苏州作也。是岁四月,自常州之扬州,晤半唐于东关街仪董学堂,半唐谓余,是词淫艳不可刻也。夫艳何责焉?淫,古意也。《三百篇》杂贞淫,孔子奚取焉?虽然,半唐之言甚爱我也,唯是甚不似吾半唐之言,宁吾半唐而顾出此?
“甲龙仲如”乃甲辰年(1904)二月。序中主要记载了王鹏运与况周颐对于“淫艳”的不同认识。王鹏运告诫况周颐“词淫艳不可刻”,况周颐却认为,淫艳是不能苛责的,《诗经》就有所谓“淫”诗,孔子仍然推崇。况周颐虽然不同意王鹏运的批评,但仍然认为王鹏运的批评是爱护自己的。在此之后,王鹏运、况周颐的交往日益密切,在王鹏运的教导下,况周颐终于“体格为之一变”,放弃了艳词的写作,转变了艳词的观念。
《餐樱词自序》作于1915年,这是一篇回顾自己一生习词、治词经历的文章,特别是谈到王鹏运、朱祖谋对他的影响:
余自壬申、癸酉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有今日万不能道者,而尖艳之讥,在所不免。己丑薄遊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而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塘亟奖藉之,而其它无责焉。夫声律与体格并重也,余词仅能平侧无误,或某调某句有一定之四声。昔人名作皆然,则亦谨守弗失而已,未能一声一字剖析无遗,如方千里之和清真也。如是者二十余年,壬子已还,辟地沪上,与沤尹以词相切磨。沤尹守律綦严,余亦恍然,向者之失,龂龂不敢自放。《餐樱》一集,除寻常三数熟调外,悉根据宋元旧谱,四声相依,一字不易,其得力于沤尹与得力于半塘同。人不可无良师友,不信然欤?大雅不作,同调甚稀,如吾半塘,如吾沤尹,宁可多得?半塘长已矣,于吾沤尹,虽小别亦依黯,吾沤尹有同情焉,岂过情哉!岂过情哉!乙卯风雪中,沤尹为锲《餐樱词》竣,因略述得力所由,与夫知爱之雅,为之序,与沤尹共证之。
这篇序是况周颐表现自己学词经历和词学思想的最系统的表述。举其要者有以下三点:第一,况周颐开始学词的时间是“壬申、癸酉间”,即同治十一年(1872),此年况周颐12岁。此可与况氏《蓼园词选序》所说“曩岁壬申,余年十二,先未尝知词。偶往省姊氏,得是书案头,假归雒诵,诧为鸿宝。由是遂学为词,盖余词之导师也”相互印证。第二,己丑年(光绪十五年,1889),况氏29岁,认识了王鹏运,赵尊岳《蕙风词史》说:“先生初为词,以颖悟好为侧艳之语,遂把臂南宋竹山、梅溪之林。自佑遐进以重、大之说。乃渐就为白石,为美成,以抵于大成。《新莺》词格之变,草线可寻。”序中所言“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是况周颐所受王鹏运教导最主要的内容。受其影响,词风由“尖艳”转向重、拙、大。第三,壬子年(1912)况氏52岁时以朱祖谋为师,走上“声律与体格并重”之路。朱祖谋(1857—1931),字古微,后改名孝臧,号沤尹,又号彊村,归安人(今浙江湖州)。光绪八年(1882)中举,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广东学政,后辞官寓居苏州,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朱祖谋以精通词律、严于词律著称,有“律博士”之誉。朱祖谋不仅自己填词词律谨严,而且对包括况周颐在内的弟子也严加要求,况周颐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思想深受其影响。序中况氏习词的三个阶段概括得十分清楚,对王半塘、朱祖谋的指教以及两人的友谊十分感念。
三、况、郑交恶的缘由
民国词坛上有一段公案颇引人注目,即同为晚清四大家的况周颐与郑文焯二人的交恶。况周颐的《玉梅后词序》和《二云词序》记录了这段词史公案。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瘦碧、冷红词客、鹤道人、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今辽宁)人。郑文焯在当时词名甚盛。同为“晚清四大家”,郑文焯与况周颐曾经关系密切,后来又产生隔阂,乃至交恶。两人关系的破裂除了性格原因,与词学思想的分歧亦有直接关系。
况周颐与郑文焯结识于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夏秋之际,此时况周颐离开北京,经苏州、上海、广州、杭州来到苏州。此时郑文焯正卜居苏州。两个才子词人相识,相得甚欢。赵尊岳《蕙风词史》云:“先生(按:况周颐)于苏识易实甫、文小坡,因有〔寿楼春〕及〔喜迁莺〕联句之作。”况氏《香东漫笔》亦记述:“辛卯、壬辰间,余客吴门,与子芾、叔问素心晨夕,冷咏闲醉,不知有人世升沉也。”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况周颐在苏州编成《玉梅词》,其〔喜迁莺〕小序云:“壬辰正月二十日,与子芾、小坡柳宜桥酒楼联句和梦窗韵”。二人的友谊在郑文焯的词中也多有记录,如《冷红词》卷一〔寿楼春〕《和梅赠夔笙同年》、〔绛都春〕《夔笙新纳吴姬,用梦窗为李篑房量珠和韵赋此》等。况周颐与郑文焯曾经晨夕相伴,联句唱和,关系很是亲密。
二人交恶之事缘于况周颐刻词集《玉梅后词》。《玉梅后词》是况周颐光绪庚子(1900)之后游历苏、常所作,此集共收词二十阕,多写男女相思艳情,下语用字颇艳丽。如〔临江仙〕:“记得云鬓香覆额,新兴梳裹便宜。绣兜初卸海棠时。银蟾刚一寸,光艳越娇痴。 翦绿匀红无限好,泥人缕缕丝丝。天涯对影愧须眉。兰成青鬓减,生怕小菱知。”又如〔琵琶仙〕:“何况离别时候,更兰桡催发,花路远骢嘶不度,隔麴尘竚想罗袜,记否,一曏旬留绛纱嘑闸。”另外词中多写如“香眉”“鬓云”“红楼”“香鬟”“春衫”“罗袜”等香艳之物,词境亦呈现缠绵秾艳色彩。赵尊岳在《蕙风词史》中说:“《玉梅后词》十余阕,则艳词之成于苏、杭、常者也。维时先生虽流离江海,而朋友文字之乐,不减畴昔。故词境又趋于侧艳一流。”夏承焘亦云:“阅况夔笙《玉梅后词》皆怀妓作。好处可解甚少,不知由予学力未到耶,抑况翁此编非其至耶。”该词集所收确为况氏年少艳冶之词。正是这些艳词引发了况氏与郑文焯的矛盾与交恶。
况周颐作于1907年的《玉梅后词序》云:“半塘旋之镇江而杭州、苏州,略举余词似某名士老于苏州者,某益大诃之,其言浸不可闻。”序中所云“某名士老于苏州者”即指郑文焯,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的记述可为一证:“序中且极诋郑叔问,所谓某名士老于苏州者也。”况周颐作于1914年的《二云词序》又记述了此事云:“《蓤景词》刻于戊戌夏秋间,距今十六年,中间刻《玉梅后词》十数阕,附笔记别行。谓涉淫艳,为伧父所诃,自是断手。”此处所云“伧父”亦是指郑文焯。况周颐的学生赵尊岳对此事也有记载:“《玉梅后词》成,文叔问(按:即郑文焯)常窃议之。先生(况周颐)大不悦,其于词跋有云‘为伧父所诃’,盖指叔问。”
况周颐刻《玉梅后词》受到王鹏运批评,以及郑、况相恶之事在当时词坛流传开来,夏承焘曾专门致函张尔田,询问“大鹤、蕙风交恶情状”(1936年3月12日),张尔田回函云:“蕙风生平最不满意者,厥为大鹤。仆尝比之两贤相扼。其于彊老恐亦未必引为同调。尝谓古微但知词耳,叔问则并词而不知。又曰:作词不可做样,叔问太做样……(况)在沪时,与彊老合刻《鹜音集》,欲以半塘压倒大鹤……大鹤为人,不似蕙风少许可,独生平绝口不及蕙风。”况周颐与郑文焯均为才华横溢且个性奇崛乃至于偏执的人,两个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的人 相处难免失和。
况、郑交恶的起因是二人对所谓“艳词”的态度。况周颐《玉梅后词序》云:“夫艳何责焉?淫,古意也。三百篇杂贞淫,孔子奚取焉?”他认为“艳”的本质是深挚的感情,正如赵尊岳在《蕙风词史》中又对《玉梅后词》的推释,他认为“侧艳”之词“有绝重、绝拙、绝大处,则非作艳词者所可望其肩背矣。”也就是说同样是艳词,有了深挚之情就可以归入重、拙、大。
况周颐与郑文焯对艳词的不同诠释和理解是二人交恶的根本原因。郑文焯一贯反对作艳词,这一点与况周颐非常不同。赵尊岳曾对二人的差异有分析:“叔问学白石、学清真,雅尚面目,而天分或不及先生。先生充其所至,‘胡帝’‘胡天’,外蕃丽而内幽怨,不为叔问所知,故有所议也。”意思是说:况氏的这些艳词不同于一般人作的艳词,“艳”只是外壳,内里却有极深的情感蕴涵,而这一点又是郑文焯所没有认识到的,因此他认为郑氏不能理解况词。赵尊岳又说:“其艳词姚丽入骨,而灵心慧笔,足以济其胜,为词林所罕见。”在郑文焯看来,况周颐作艳词是少年轻佻;而在况周颐看来,自己的艳词是深情的记载,未可一概否定,尤其是像郑文焯那样如“伧父”般轻慢地加以否定,更是不可接受。郑、况两人互不相让,交恶终老。
况周颐词籍序跋不仅篇目丰富,意涵思想亦十分深厚,本文集中探讨了况氏词籍序跋与其创作心路历程以及词学思想的关系。况氏的词籍序跋更为丰富的内容,如关于词人词作鉴赏评析、词学理论阐发、词史论述等等,则有待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