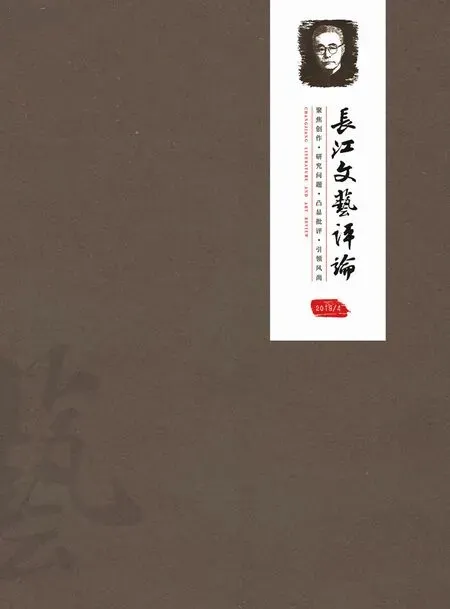回归心灵与存在的写作
——论朱朝敏的散文创作
◆刘月新
任何好的文学都是对生命经验的唤醒与激活,其中散文似乎又与生命经验的关联尤其密切。诗歌能够以生命经验为触发点大胆想象和幻想,小说可以通过虚构将生命经验扩展和放大,而散文则必须紧紧贴近于生命经验本身来做文章。作者从生命经验出发,经过心灵的反刍和体验,最终又回归这种经验。这三个阶段类似“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三种境界。从这一角度看,散文是一种最为本真的文学,是一种直面生命经验与人生存在状态的文学,也是在平凡中见智性和诗性的文学。每次读到朱朝敏的散文,都加深了我对这一观点的认识和体会。
十多年前,我曾就朱朝敏的散文写过一篇评论,题目是《在回溯中寻找本真的自我——论朱朝敏散文的“记忆”》,发表在2007年的《当代文坛》。当时我对她散文的一个感觉和印象是善于开掘个人记忆,在对过去经验的追溯中弥合心灵的创伤,实现心灵的救赎和自我的超越。时至今日,朱朝敏的散文无论是量还是质都有一个大的飞跃。虽然她的散文题材仍然来自于挥之不去的个人经验,但和前期散文相比,其境界已经变得深远阔大。她不再单纯沉溺于个体经验的咀嚼与回味,而是以更为沉稳平静的心境去书写自己的内心状态和所熟悉的生活,将自我消融在人、事、景、物之中,为读者袒露了一个幽深曲折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一个日常而神奇的生活世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更为丰盈充实的自我。
朱朝敏的每一篇散文都凸显了自我的存在,有的是直接表现自己真实的心理状态和内心体验,有的是表现与自我相关、浸透了自我心灵体验的人、事、景、物。在直接表现自己心理状态与内心体验的散文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仍然是那些直面自己生存困境和内心隐秘的作品。这些作品都与作者的成长经历和创伤体验密切相关,展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心灵轨迹,大都运用了回溯—寻找—反省的叙事方式。随着生命和岁月的流逝,作者常常在回溯中寻找自我的存在,但这个自我常常又被创伤经验所困扰。为了摆脱创伤经验对自己的影响,修复自己心理的残缺,作者就像一个冷静客观的外科医生,用手术刀细致地解剖自己的心理结构,从意识深入到潜意识,将隐藏其中的魔鬼释放出来,将心理的阴面袒露在阳光之下,使之得到净化和清洗。这些作品大都采用了心理对话的结构,即现在之我与过去之我的对话,具有很强的复调性。过去之我是一个遭受创伤的自我,现在之我是一个被创伤所困扰、力图摆脱创伤的自我,两个自我之间既融合又分裂,充分表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纠葛。《好看的霜》《轻伤的道路重伤的梦境》《黑夜游戏》《谁的切梦刀》《亲爱的身体》《麻醉师》等作品都携带了十分明显的创伤经验,有些细节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呈现。这无疑是作者对自我一次又一次的修复,是作者对自我内心反复的审视。于是乎,作者的文字表达就变成了一个清淤的过程,目的是还原出一个澄明而洁净的自我。
《好看的霜》中有这样的文字:“我说出,意味我对自己孤僻症结的梳理。语言显然没有文字叙述的优势,是我轻微自闭而为。”《轻伤的道路重伤的梦境》也有类似的表述:“当我以文字的形式一层层拨开这些黑洞时,无异于在清扫记忆通道里的腐殖。那么,请让我详尽这些心灵黑洞中的细枝末节。……请你理解它,怜悯它爱它,你才能正视它,它为你呈现,你的童年,你将伴随它再次生长。你的心灵你的世界。”这不仅是在与自我对话,也是在与读者对话。《黑夜游戏》中也有这种叙述:“多少年来,我常常不由得回忆起那个夜晚,它从下半夜开始,摇晃、颠簸,它种下一个季节的黑夜记忆——总在某个时刻跌入回溯中,夜被揉亮了本质的色彩:黑暗,悲伤,深邃。我一遍遍地回味,一遍遍与那个夜晚相遇。”这些叙述片段都说明了此类散文就是作者内心对话的体现,是作者为了寻找自我而产生的内心挣扎。
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是时间的存在,都存在于过去—现在—未来之中,现在既包含着对过去的回忆,又包含着对未来的预期,而对未来的预期常常又依赖于过去的经验。从这一角度看,朱朝敏的写作绝不仅仅是为了抚慰过去的创伤经验,而是拷问自我与追寻自我存在的写作。因为过去的一切都是自我存在的证明,都是生命经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看,每个人的人格都具有阴面和阳面,两个层面有着深度的对话和冲突。如果文学创作能够直面这种对话和冲突,就会揭示人灵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作品具有耐心寻味的张力结构和深层意味。文学批评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总结出了复调式的对话结构,其中一种对话就是人物自我的内心对话,人物的两个自我之间力求在对话中寻求平衡,但结果却是徒劳无益,甚至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朱朝敏的散文无疑也具有这种对话的张力结构,她时而沉溺于创伤经验的冥想,穿越于恐怖经验的黑洞,详细叙述各种伤痛经验和细节,时而又力图挣脱这种经验的缠绕,两个自我逐渐从分裂走向融合,赋予作品丰富复杂的心理内涵,呈现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自我。
朱朝敏是敏感而细腻的,当她向内心世界开掘时,她显得矛盾而焦虑,难以祛除内心的阴影,填补内心的黑洞。于是她将视线投向大千世界,试图在宗教境界、生活场景和自然物象中获得心灵的寄托,找到生存的根基。在这类散文中,有《般若甘州》《在高原》《船歌》《婺源梦境》《我家襄水上》《回到乐平里》等作品较为典型。这些作品都与她的旅行经历有关,是她走出自我与获得自我的方式。《般若甘州》记述了作者远赴甘肃张掖(古甘州城)的见闻和参拜大佛寺的心灵激荡。文中有这样的词句:“大地呈现极尽奢华的颜色,那是生命达到极致之后才焕发的光辉。这种辉煌灿烂的色彩,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今,它们匍匐在地上,以黄金甲的贵重启示我,我却一时无法领会这贵重的启示。”随着对大佛寺了解的加深,作者受到触动和震撼,心胸逐渐变得开阔,认识到“从肉身剥离出来的佛,曾为血水浸染又最终脱离了血水,就像一个人在时光层递下无数次转身,完成最优美的定格。……彻悟了,佛也就脱离了血水包裹的肉身,光芒四现”。作者从对佛性的认识过渡到对自我的反省,她将佛作为映照自我的镜子,以佛的大境界衬托自己的小格局,期盼以佛光驱散内心的阴影,为心灵找到一条出路。
如果说《般若甘州》书写了作者在宗教中反思自我和寻找自我的心灵轨迹,那么《回到乐平里》则体现了作者对圆满自足、凡俗而诗性的生活的皈依。佛的大境界毕竟太渺茫,而此岸的凡俗生活则触手可及,如果能够在这种生活中获得精神的满足与心灵的超越,则更能体会到自我存在的踏实感和幸福感。乐平里是伟大诗人屈原的故里,屈原的美德和事迹在这里广为流传,这里的人们将屈原奉为自己的精神偶像,每年端午和中秋都要举办祭祀屈原的诗会,让屈原的英灵回返故乡。这里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这里的人们过得自在而幸福。尤其可贵的是,这里的人将日常生活与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天生的诗人。他们的诗生长于大地之上,融贯在稻束和柑橘之中,既质朴又浪漫。作者在乐平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她被这里的一切所感动,因成为一个农人而幸福,从中得到心灵的启悟:“诗歌的本质是浪漫,但拒绝轻飘与虚妄。它的浪漫是皈依泥土后的抽芽与成熟,犹如一粒谷子的破土,必然被泥土裂变成一束束稻穗。——从泥土里生长的诗歌,谙熟土地的秘密,它更能诠释浪漫和高贵……当它从书斋里走到原野走向日常时,它完成了心灵的试炼。”人生也是如此,人只有栖居在大地之上,破除执念,以开阔的心胸去拥抱泥土和自然,才能获得存在的稳定感与踏实感,才不会成为一个精神的孤独者和流浪者。《回到乐平里》在作者散文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作者走出封闭的自我,在日常而诗意的生活中找到了精神的圆满与自足。
作者对自己心灵和存在的回归最集中的体现在描写自己家乡生活的作品中。作者的家乡——百里洲是长江的第一大岛,是作者精神的出发之地与回归之地,她的大部分散文都是对这里的书写。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水有关,水成为一个凝聚人多重经验的原型意象,既给人带来了生命和繁衍,又带给人死亡和毁灭。作者以水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故事,表现了百里洲人对水的复杂感情。《1954:母亲的孤洲》《出岛记》《你的岛》《水漫漶》《梦潭》《行无嗔》《大水天上来》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追述了先辈的生活经历,有的书写了作者自己独特的童年经验。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2016年问世的散文集《循环之水》。在这部作品集中,作者对百里洲进行了系统的、多角度的描写,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百里洲的形象画卷。作者首先追索了百里洲那个神奇而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本身就具有生命和死亡的双重寓意。然后从不同的侧面书写了这里的人、事、景、物。“日常的温度”描写了春台、雕花木床等木器,“石头奔跑记”描写了石磨、石碾等石器,“无上清凉说竹”描写了竹床、竹扫帚等竹器,“嘉木青葱岁月录”描写了岛上有名的树木。此外,作者还描写了岛上的风俗以及几个神秘怪异的人物,构筑了一个以百里洲为底座、天地神人一体的世界。
作品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与百里洲人密切相关的器物与植物。这些器物与植物本是平常之物,也并非百里洲所独有,但在作者笔下都别有深意,饶有趣味。因为这些器物与植物都是百里洲人存在的证明,灌注了作者和先辈的生命气息。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这些器物与植物,而是表现了祖父、祖母、母亲以及其他亲人和这些器物与植物的关系,讲述了一个个人与物之间的故事,既把握了这些器物与植物的特性,又表现了人的生存方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共在”,人不仅要与天、地、神、人共在,而且与自己所使用的器物共在。人与器物的关系首先不是理论探讨的关系,而是更具本源性的使用关系,只有在人与器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才能显现器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他说:“打交道一向是和用具相结合的,而唯有在打交道之际用具才能按本来面目在它的存在中显现出来。”人一旦将物作为凝视和打量的对象,孤立地研究和描写物,人就会丧失与物的本源关系,造成人与物的分裂和异化。从这一角度看,《循环之水》对器物植物的描写,所呈现的是先辈们与器物植物之间的本源关系,再现了一个人与物融合的真实的人性世界。
里尔克说:“在我们的先辈的眼中,一幢‘房屋’,一口‘井’,一座熟悉的塔尖,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衣服和长袍都带着无穷的意味,都与他们亲密贴心——他们所发现的一切几乎都是固有人性的容器,一切都丰盛着他们人性的蕴含。”作者事无巨细地描绘百里洲的器物与植物,既是为了还原先辈们有灵性的生活,那些或古朴、或精致、或笨拙的器物都凝聚了先辈的情感、经验和信仰,是他们生活的象征。又是对自己存在之根的追问,追问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唤回一个已然消逝的精神故乡,追寻自己的生命足迹。当作者怀着肃穆而虔敬的心情描绘这些物件、表现人与物的关系时,就是在举行一场生命的回乡仪式。回到生命的出发地,回到生命的本源,以对抗当下生活的乏味与无聊。正如作者所说:“念旧,就是面对心灵,追根溯源的一刻。带着对现时自己的不满和修正,回到生命最初的地方,以期获得重新生长的契机。”
作者对存在的追问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经历和经验,而且还上升到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作者面对天地自然时有这样的反省:“你信奉,在当下属于你的时代,自然的真理尚在。但你的信奉却夹杂疑虑焦躁,真理总是残余,是废墟,它遍体鳞伤。欲望旗帜到处招摇的背景舞台,真理岌岌可危。你看见的听见的触摸到的,均在后退,后退,退步于钢筋水泥夹缝,演绎尚古修饰。而高歌猛进的现代化浪潮终将洗礼它们并革面。”这一反省既是作者个人经验的表达,又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有感于现代化的科技浪潮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破坏了人与自然的本源关系,自然的真理被遮蔽,导致了人与自然的无家可归。他呼吁要限制人的欲望,重建人和自然的关系,让自然以其本来的方式存在。作者对自然充满了崇拜之心,因为自然既能让她获得灵魂的寄托,又能显现世界的丰富与神奇。她以空明虔敬的体道之心,表现了对自然的倾听、体察和理解,还原了自然本身所具有的状态。在《山野黑暗录》中,作者忠实记录了黑暗笼罩天地时的状态,以精细的语言将黑暗来临的过程、黑暗的质感、黑暗的轮廓、黑暗的纯粹描绘出来,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混沌不分的世界。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黑暗是一种文化原型,与恐怖和阴谋相关。但在朱朝敏笔下,黑暗则呈现出全新的维度,它褪去一切喧嚣、浮躁和虚假,显得原始、深邃、寥廓、神秘;宁静,是催生一切的母体,就像母亲黑暗的子宫是孕育新生命的摇篮。回到黑暗就是回归世界的根部,就是回归生命的本源。
作者对自然的崇拜还表现在对植物和山水的显现。以植物为例,她作品中有对各种植物的生命形态的描写。《循环之水》就对百里洲标志性的植物有详细的介绍,所到之处,她都对当地的植物有浓厚的兴趣,且在作品中有或粗略或精细的刻绘。如《般若甘州》对大佛寺树木的描写:“这样那样的树木,没有一棵是相同的树种,它们或高大粗壮,或低矮瘦弱,或古老葳蕤,或幼小稚嫩。它们不同又相同,不同科目的树木笔挺挺地直着腰板,而开花的树木一律是细碎的白色花朵,芬芳的气息若有若无。它们似乎少了袅娜,却站出了刚劲和硬朗。”这段描摹虽然不够精细,但足以凸显西北区域树木的特性和格调。《薇时代》中对草本植物薇的描写:“万物复苏,草木萌发的季节,松树林里,一种蕨类植物,顶着毛茸茸的皮肤冒出来。白色的绒毛蓬松紧致,严严实实地裹住里面的枝丫,顶头又极其秘密地打个卷,勾下脑袋,藏匿它的神情,藏匿它的水嫩光滑和隐秘心事。”朱朝敏对植物的观察是细腻的,只有对植物做过一番认真研究,才能描摹得这么具有质感。她写植物,不是将植物作为感情的载体,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风景描写,而是显现植物独特的生命形态,让植物自己站出来说话。她所要做的就是倾听,在植物中倾听自然的声音,显现自然的存在,回到人与自然最本源的关系。
朱朝敏对散文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她说自己的散文是回到根部的写作。所谓回到根部,就是回到心灵和存在,祛除遮蔽心灵和存在的迷障,让心灵和存在以其本来的面目显现,洞彻人性和世界的真相。她在呈现自我创伤时,不回避内心的阴郁体验和身体的破败体验,而是以精细之笔,将其还原在读者面前。她知道,这些都是真实自我的组成部分,是人心与人性的另外一个侧面。只有将其真实的呈现出来,人心和人性才有拯救的可能。她在表达内心圆满幸福的体验时,凸显了这种体验的踏实感与真实感,破除了浮泛的抒情与虚假的自足。她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没有将山水植物降格为抒情的媒介,而是以虔敬之心显现了自然本身的存在。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当人类文明给人心和自然蒙上了厚厚的尘垢,导致存在的异化时,写作要有回过头来思考的勇气,要直面真相和真实。诚如作者所说:“小说开放叙述,是拿一颗炙热心撞击时代生活的大石,而散文以回撤的姿态娓娓阐述,祛表相袒心胸露灵魂。一个向外一个朝内,却经由多种技艺打开了缺口,最大程度地呈现背后的东西……”这就是回到根部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回到根部的写作是一种陌生化的写作,它拒绝以自我为中心的抒情主义,反对流连于事物的表面感觉和印象,而是致力于显现和反思,返回到人与自我、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关系,在语言上追求感性、智性与诗性的统一。感性就是显现,就是感性直观,让事物的物性自己涌现出来。智性就是本质直观,在感性直观中直击事物的本质。感性与智性的统一就是诗性的生成,它灵动跳跃,反转腾挪,具有质感和弹性,一会让你瞩目于事物的感性特征,一会又将你引入智性的思维空间,让你的思绪在虚实之间流动跳跃。《船歌》中有一段描写视觉和听觉的文字:
溪流里有月亮的影子,弹珠一般地弹跳,在水流中若隐若现。潮汐起伏中,它们破碎、圆满、再破碎、圆满。你陷入了恍惚。耳际边有一个细微的声音发出,类似种子炸裂的声响。细小又宏大。是什么声音呢?你努力集中自己的思维去捕捉分辨。嘣,咚,嘣。细碎,断续,不绝。它既不是泉水的声响,也不是夜晚虫鸟的鸣叫。
三个月后,你在迷糊的睡梦中回忆这个细节,才恍悟——那是一粒种子掉在地上的声音。
它使你的回忆充满神圣和感激。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具有极强的感性直观能力,对色彩、声音的变化极为敏锐,三言两语就将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但作者绝不会流连于事物的感性层面,而是上升到智性的思考与体验,将感性、智性、想象、回忆融会贯通。阅读这样的文字,需要你调动全部的感觉和思维,将整个生命投入其中,才能与作者展开感觉和心灵的对话,与作者创造的文学世界对话。
朱朝敏不仅致力于语言的探索,而且致力于文体的跨界创新,她是一个游走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跨界写作者。她的散文和小说之间具有很强的互文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题材的互文性。她的不少散文和小说具有相同或类似的题材,都是对家乡百里洲的书写,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第二是视角的互文性。她的散文和小说都具有鲜明的个人视角,都是从我的视角来叙事的。一般来说,散文写作适合体现作者个人的存在,而小说应该尽量淡化作者的个人色彩,但朱朝敏的小说却凸显了个人的存在,这说明散文写作风格对她小说的影响;第三是文体的互文性。朱朝敏的不少散文与小说在语言风格、叙述方式和结构安排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她尝试打破两种文体之间的界限,其明显表征是淡化叙述的故事性,以散点透视的方式来叙述真实的人物、事件和场景,如《水之央》《1998年的水上书》《行无嗔》《大水天上来》都具有比较明显的跨界性,很难界定它们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也许用非虚构作品来命名更为恰当。在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的评选中,《大水天上来》获得非虚构作品提名奖。这说明朱朝敏的跨界写作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这种跨界写作的好处是有利于个人性、纪实性、自由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作者不必过于受到文体规范的局限,能够更自由地书写心灵和存在。
注释:
[1][2][3][4][5][6][10][11][12][13]朱朝敏:《山野虚构》,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238-240页,249页,76-77页,81页,205页,124页,79页,165页,280页。
[7]【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映嘉、王节庆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5页。
[8]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9]朱朝敏:《循环之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