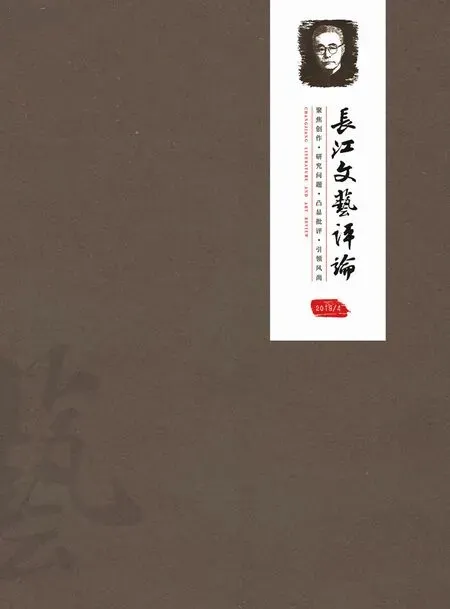温和讲述世界的早熟一代
——对“90后”创作者的印象
◆艾 翔
如果没有记错,“80后”一词的诞生与1999年《萌芽》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密切相关。现在无论认可或非议,这个词都被视为某种“理所应当”“自然而然”,但当时却同“朦胧诗”等文学史概念一样经历了从污名化到中性化的过程。还记得当时有一档节目——今天回想明显带有满满的恶意——召集了数名“教育专家”与韩寒进行对话,“教育专家”问韩寒平日聊天是用“ICQ”还是“OICQ”,韩寒温柔而羞涩地说是“聊天室”,“教育专家”立即表示在聊天室聊天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80后”最初指代的正是无经验、幼稚、叛逆、莽撞甚至胡作非为,整体形象是“问题少年”。当“新概念”的特征从第一届以思想性优先到后来逐渐以艺术性尤其是语言和意境优先,从韩寒过渡到郭敬明,并且随着保送制度的取消、大众的习以为常以及高考作文命题模式对“新概念”的借鉴,这一群体的异质性被逐渐淡化。由“80后”衍生出的“90后”这样的指称,虽不带有原先的恶意,已经变为单纯标记时间的范畴,但由于同属青年亚文化群体而引起主流社会的警惕,经常附带着“非主流”“杀马特”等贬称。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80后”和“90后”有一阵在网上骂战不可开交,现在再没人提起,其实是个有趣的事件。有趣的是,在“80后”和“90后”的网络大战中,“80后”也操起这套语言进行攻击,化身为当年自己的对立面。也可见当时对新一代年轻人的认知,还未脱已成型的认知模式的窠臼。
在“80后”概念诞生二十周年之际,早有许多针对以代际划分文学创作的抗议。但我想无论抗议还是赞同,大概都不如将其视为一个文学史概念进行梳理与辨析更有意义。这里简单地说一点,即新世纪初被称为“80后”的小群体,可否视为以表现校园生活、残酷青春、叛逆言行、基于青年亚文化的认知等内容为主要特征的作家群或流派。也就是说,当时的“80后”和当下的“80后”指涉范围有所区别,甚至完全不同——前者通过一系列精英文学运作已被宣判为一种“不成熟”的文学形式。从两个“80后”指称的变迁可见,这个年龄段的写作主体经历了整个美学体系的调整变革。
这些梳理并非离题,通过“80后”反观“90后”,虽然命名方式类似,但历程完全不同。因为期刊市场化、《萌芽》被迫改版、策划“新概念大赛”并引发“80后”的突然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让主流文学界甚至主流社会被动应对,经历“野蛮生长”后,文学体制才逐渐形成标准模式的“培养机制”。不可否认,后来这批“80后”以及“90后”能够引起关注,与最初的“80后”有内在微妙联系。尤其是“90后”,由于代际命名的惯性,在“90后”尚未或刚刚浮出水面的时候,我们早已知道会有“90后”“00后”的次第出现。因此面对这一代创作者,主流社会和文学界的心态就显得十分平和、主动了,各种期刊开设专栏、丛书出版、批评应对、研讨会召开、媒体宣传等一系列活动顺畅开展,“90后”某种程度上比前几代作家更早、更顺畅地进入文学场和体制运转,这也是其创作丰富多彩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毋庸讳言,这种略显粗暴的命名方式之于两代写作者都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就要认同这种命名方式,很明显,当下很多“80后”和“90后”并不具备当初“80后”那种流派意味,内部更为繁杂。然而这种繁杂也并非绝对,过分强调内在差异或许一样不足取,既然是一代人,总有共性,那么读读便知。
王苏辛的《白夜照相馆》有一种超乎年龄的冷静。故事一眼可知其虚构色彩,帮助人重塑记忆甚至改造历史的照相馆,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但自始至终有一种逼人的现实感,也是一件怪事。地点命名为“驿城”,正是为了凸显移民的身份。城市不是市民视角的“家”所在地,而是被广泛忽视却数量庞大的非本地居民甚至流动人口开拓了的书写空间,或许正是这种视角的新颖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感。其中出现了高大男人这个人物,要说不说地透露出了自己同李挪即更名后的李琅琅的关系,并且向余声捅刀,后又与李挪、刘一鹤在街头纠缠中尽皆殒命。不过这两段暴力事件都是侧面概述,不见任何刀光剑影,这同80后的“残酷青春”迥然不同。主人公赵铭和余声历经波折后都分别默然离开了这座城市,始终没有情绪波动,自然而然,波澜不惊。在他们的故事里,现实变得格外“真实”,没有幻想憧憬,也没有抱怨愤懑,叙述者充满了自信却并无任何显露,只从自己的眼里看世界。并不是拒绝世界,而是冷静观看;并不是零度叙述,内含情感,却也十分克制。
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如同一册民俗风情速写,每篇故事都不长,相对独立,又在细微处彼此关联,很显巧思。很难想象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愿意做家乡往事的记录者,一丝不苟陈述每一细微点滴,语言平实舒缓,儿童叙事方式,却明显加入了后置式的视角,带有洞悉一切的沉稳,讲述并不平静的历史。《八摊》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困难时期”迫于生计的村民的拾粪浪潮,颇有国外历史学研究文本的感觉,从非常小的细节入手描摹整个时代状况。其中有意思的是两处。其一是在一个推进“合作化”热潮的时代每个人关心的是自家的粪池,而且关心到了对粪便吝惜的程度;其二是作者在一个短小说的篇幅中运用了张清华教授所谓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的历史性纬度,将主人公“八摊”五六十年代生存技能(拾粪)的纯熟延续到了当下,虽然并非一个顽固的滑稽形象,也随时代大流外出打工,但仍然清贫一生。叙述者在进行历史叙述时,扮演口述史采访者形象,面对回忆往事的爷爷,叙述者的主体意识是隐藏的,但到了当下,其自我意识鲜明显现,即使对爷爷辈的八摊热情,对其依然满不在乎甚至不无鄙夷。这种微妙俯视姿态不是源于历史断裂或历史虚无这两种认识论模型,恰恰是基于对历史连贯性的体认:当时媒人说亲也需要“有房有地”“门当户对”“要人有人,要个有个”,人性永远是复杂的,而非被要求的那样积极上进和单纯。同时,作者和叙述者明显拉开了距离,叙述者对“八摊”的微妙俯视受到作者冷眼观看,整体上维持了小说的冷静风格,并没有因为当下叙述者介入历史而改变。
王占黑的《空响炮》大多关注老社区里的父辈们:鞭炮店老板、打工者、物业、公交司机、环卫工、保安、收银员、联防队员等等,感兴趣的都是生活中的常事:过年放炮、打麻将、催婚、打牌、江湖义气等等。语言也是老练而平实,情绪也并不激动,巧合也毫不突兀,叙述者带些少女的调皮,安静地讲每个平凡人的平淡生活,却从贴切和传神的描述中透露着浓浓的真情,好像这些人物就在眼前走过。这一系列小说很少涉及历史,都是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却常常隐藏着丰厚的历史,因为她的用力点正是时代变迁下的个人处境。这些人有各自的小心思,有各自的喜怒哀乐、俗世生活,但总体上因为社会身份和年龄等因素,弥漫着一种哀凉的氛围。传统在当下显得若有若无,在同题小说《空响炮》中,环卫工老棉袄清楚地意识到乡情并不像以往那样可靠,但还是怀念故乡,怀乡也是在矛盾的情绪中升腾起来的:城里禁止放炮,工作量减轻令其欢喜,但“年味”的贫乏令其若有所失,反而怀念放炮的日子和放炮的家乡。《麻将,胡了》中的电机厂下岗工人葛四平,“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还明白无误地延续着,一想到城里到处遍布着当年工友、今日的值班亭保安,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但另一方面,这种自豪是用“埋伏着我们的同志”这样不无戏谑的词语带出,同时作者还写出了“工人阶级”在历史层面上的多义性,即并非全部吃苦耐劳,而是也有偷懒、今天称之为“安逸”的秉性。即使叙述充满了历史感,王占黑还是调侃了一把,让历史上最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爱上了用茶杯喝资本主义商业帝国的垄断产品可乐。王占黑虽然有少女的调皮,但还是极为认真地书写长辈们的日常,以及他们之间用自己独特方式表达的彼此间情感,也对他们抱有浓浓的温情,也对他们如《怪脚刀》中体现出的小人物抗争时代的骨气表达敬意,在表达代际冲突的《美芬的小世界》中,贴着父辈写,感受父辈体温与脉搏,深切理解子辈和父辈彼此相悖的历史必然性。像《演说家吴赌》这样的作品充分体现王占黑懂技巧,但精于克制,点到为止。读她的小说,令人惊异她的早慧,轻描淡写就八面玲珑,实在是很机灵的女孩。
庞羽呈现出来的也是令人惊讶的冷峻。《佛罗伦萨的狗》中的主人公是个早熟的小女孩,面对廉租房区域实施性侵的中年男性,“我”一点也不慌张,致使性侵者反倒做贼心虚。同样面对授课老师和心理医生,以及有较长期联系的“大叔”,女孩都显得镇定自若,没有情绪的激昂、迷茫或困顿。整篇作品几乎没有同龄人出现,只有年龄比自己大的“哥哥”和被自己婉拒的乐队男生。陆医生感叹“如果青春的时候,你善于表达一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苦闷”。女孩却“受不了”地“转过头去”。两人的交流基本顺畅,但仍然有细节令女孩不悦,那就是陆医生居高临下的态度,无论是“有自虐倾向”的判断,或“我会治好你”的自信。女孩期待的是倾听,而不是“治愈”,因此她说“只有继续讲下去我才能振奋起来”。但青春表达的对象只能是同龄人,年长者不会倾听,只有双方用同一套语汇进行平等交流,才是女孩真心盼望的,所以她的青春势必不善于表达,与陆医生的会面也属于历史必然性范畴。这是一个早熟的女孩,不然为什么向往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是什么样的地方?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聚集着当时大量的财富、艺术和智慧,正在形成现代意识。如果将人类历史视为人的成长,作为现代史开端的文艺复兴意味着阅历增长到足以堪称步入成熟的年龄。这与小说中女孩的思想状态吻合,当她与成熟的“大叔”在一起时才“不再频繁地想起‘佛罗伦萨’”。庞羽小说中有明显的代际感,不过并不呈现激烈冲突的状态,既没有主观意图,也没有客观需求。除了《佛罗伦萨的狗》,《操场》也是如此,肥阿哥、钮约和“我”在曹老头的带领下收集骨骸,聆听陈焕甲讲述不同的抗战故事,三个孩子出人意料地回顾历史、直面生死,这是庞羽讲述的另一个儿童视角的《活着》。《福禄寿》和《一只胳膊的拳击》就不止是叙事者的早熟了,而是直接进入了中年甚至老年状态,知名教授华玉卿和市井小民祁茂成,人生经历和社会地位迥异,但在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是毫无例外展现出了光鲜之下的窘态。尤其是《一只胳膊的拳击》熟练的烹饪描写中,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作者面对作为描写对象的中年人的艰辛、困厄和压抑,显得自信自如,反而是面对近乎同龄人的祁露露(小说结尾提到阿里逝世,表明故事时间在2018年,则祁露露生于1997或1998年,比作者庞羽小四五岁)表现出冷眼旁观其幼稚的姿态。
宋阿曼也是一位十分冷峻的叙述者,但这并不妨碍她愿意贴近人物内心。争吵、家暴、出轨、不婚、酗酒、凶杀,宋阿曼笔下多是人间的冷酷无情、惊心动魄,但竭力维持稳定的叙述语调,并不流露出情绪化的痕迹,虽然她确实有自己的情感立场。《午餐后航行》也是一个出轨的故事,但有一种复杂的缠绕,即出轨故事是作为痴情故事的伴生物呈现的,并且所谓的“外面有人”的那个人何溪是一个由性而爱的人,这就甩脱了一般性的道德审判,带领读者进入人性深处。如果换一角度,何溪可以视为一个很“现代”的女性,有自主自觉的身体意识,独立理性,却在情感交流方面存在障碍。但正是这样一个人,遇到合租邻居王灿灿的男友徐魏后,不由自主退回到审美化的古典时代,情感依赖,身体意识退化,幻想未来,担心现在,“母性”被召唤,反而患得患失甚至趋于敏感。前半段很有“80后”写作的感觉,但宋阿曼明确地传递出自己另起炉灶的决心,让小说发生折转。身体还是情感,独立还是依附,租客还是家庭成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主题,或者说一个未出场人物——时代。时代的力量或者说惯性是个体难以抗拒的,即使是出轨,也还是要回归;即使是现代女性,也还是会成小女人;即使格格不入,也要完成个体的社会化,就算是伤痕累累。“父亲”关于倒流河终将“百川东到海”的言辞反复出现,个体无论是拒绝或无能,终将被时代涡流吸入。所以在开放性的结尾,我倾向于何溪没有跳楼,无论是“父亲”在天空回荡的人生格言,或是与徐魏有直接关联的飞机意象,表明女主角一方面被时代说服,另一方面仍有情感羁绊而不至于决绝。也就是说,“和解”而非“决裂”是个体与时代关系的解决方式,就像《普通乘客》中男主角在购买性服务后还是回到了“随着世界再次更新”的女友身边。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很有限,我所能接触到的除了作为上一代人的亲属,就是年龄相差不大的同学、朋友、同事,作为相邻时代出生的“90后”反而成了灯下黑的区域。通过作品了解这一代人,可能并不全面,但也并非愚蠢。如果非要说什么代际共性,“90后”似乎普遍有一种令“80后”感到惊异的早熟,成熟老练地生活,成熟老练地写作,成熟老练地看穿一切。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是生活中的王者、写作中的高标、世间万物的洞察天机者,但他们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在他们的作品中,能够看见矛盾的事物、复杂的人性、纠结的情感和困顿的人生,但所有的不利点和消极面并不造成自我与世界严格的对立,事情也远没有到达不可解决、无法挽回的地步。
他们早熟,同时是个乖孩子,现实又和谐,冷静地观察,努力地成长,笑看世界。在很多“90后”创作者那里,都能看到诙谐、机智的笑意,这意味着他们心态的宽和,与世界的和解。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参透了宇宙玄机,至少表现出来的样子十分超脱。即使是修新羽的科幻作品《死于荣耀之夜》,即使是对人类文明史和科学主义的冷静反思,即使这种反思关涉到作者自己的运动员身份,也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克制,结尾于对家庭的依恋。这一短篇令人联想到科幻小说的鼻祖《弗兰肯斯坦》,但有趣的是,修新羽没有令其带有丝毫恐怖怪诞的青年亚文化色彩,也没有犀利的针对性,毕竟主角及其训练师还葆有真善美的人性。这些就是我所看到的“90后”创作。
相比之下,“80后”反倒显得更为天真、理想化、情绪和思维容易呈现不稳定状态或者固执己见。为了一个信念甚至只是简单的理念,就能奋不顾身顽抗到底决不罢休,多少显得鲁莽而悲壮。在杨庆祥《80后,怎么办?》的小型讨论会上,阎连科毫不掩饰地指出:“相对50后、60后,80后这一代人是相当懦弱的一代,懦弱到我们今天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一种80后的声音来了。”当然,面对追求“以头撞墙”艺术的文学前辈,“80后”一代人确实显得勇气不足,在上一代作家“70后”悍然崛起的时候被衬托得更为明显,甚至更晚的“90后”一代也在用更多的心思接触时代与历史,无怪乎文学前辈们对“90后”纷纷表示欢迎和赞赏。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不看处理的对象,只看态度,又不难发现“80后”残余的“叛逆”和批判性,以及“90后”的“圆润”与和谈意识,这从婚姻态度、工作态度、生活态度以及创作态度都可见一斑。这就出现了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情,即“80后”和“90后”的丰富创作本身并不能令两个以年代为划分标准的文学概念成立,但是“90后”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使“80后”实现了历史性地闭合,反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清晰的“80后”面貌。所以在面对这些代际概念时,接受和拒绝总是相对容易,看到其背后的深意或许会更有价值。比如,两代人呈现出的创作姿态及其背后的思维模式,是否与各自的“童年记忆”相关,即1980年代的“个人主义”和1990年代的“保守主义”?如此看来,严肃地讨论代际问题,也是认识历史的一种方式。
注释:
[1]罗皓菱:《阎连科: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没我们以为的那么反叛》,https://culture.ifeng.com/a/20150728/44285776_0.shtml,2015年 7月 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