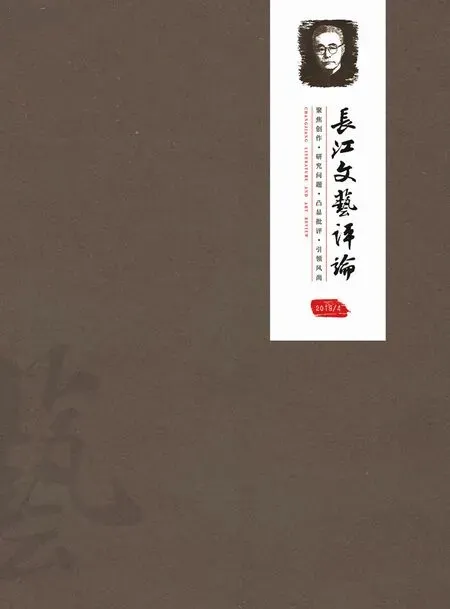在纪实与虚构之外
——从“非虚构”的概念悖论说起
◆赵 牧
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兴起,我当然知道这是因为对文学远离现实不满,而希望在虚构的文学之外寻求参与现实的力量,但是我却一度对它的这种命名方式抱有抵触的情绪。
因为这个缘故,当我第一眼看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和虚构》时,便不由分说地喜欢上了。“纪实”与“虚构”就那么明目张胆地对峙着,似乎用不着再费心找它们各自的反义词了。然而细读小说,却发现“纪实”与“虚构”,跟互为反义词的意义大相径庭,而是相互包含,难分难解的。比如说一方面是个人的成长,一方面是家族的追溯,小说给个人的成长经历赋予了“纪实”的价值,而漫长的母系家族的历史,则也隐含在各种口传和文本的叙述中而具备了“虚构”的特质。也就是任何叙述,都是不可靠的,这实际上构成了王安忆的信仰,但她给自己的使命,就是在不可靠的叙述中寻找某些真实的生命体悟。按这样一种辩证的认识,“纪实”也是一种“虚构”,而“虚构”也是“纪实”,所谓的“虚实相生”,在王安忆的写作中找到了新的范例。然而她的向历史借镜,虽关联着历史意识的建构与反省,却让人们在文本化的沉溺中感到一种现实参与的乏力。我们当然不能否定王安忆重构母系历史的现实诉求,但面对纷乱无序的现实,一方面是盛世狂欢,一方面是无根漂泊,狄更斯所谓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就被借用过来了,让人们觉得文学躲进“历史”或者“虚构”的小楼,似乎有些跑偏了,而所谓的“纪实”,也被当作了“虚构”的方式,人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在“纪实与虚构”的形式对立中找到有关现实的体验,尤其是不能从中发现自己在这个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的位置,分享其间的梦想、成功、失落、忧伤、尴尬以及彷徨。于是就有一种声音,期待文学不仅给予我们这个时代以真实的记录,而且对现实施加某种影响。
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的概念被从国外借用过来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了。“非虚构”在原词前面加一个表示否定的前缀,一眼就知道它是一个舶来品,但在追溯其缘起时,大家几乎都会提及《人民文学》杂志相关栏目的设置,并因此,韩石山的自传《既贱且辱此一生》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这原因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也不可否认,的确就是《人民文学》及其时任主编李敬泽的大力推动,“非虚构”不但成了近几年文坛上热议的话题,而且在其内涵和边界久辩不明的情况下就已成为了主流叙事。
希望“非虚构”能站在纪实与虚构之外,获得一种向现实发力的位置,或许正是《人民文学》将之作为常设栏目并积极推动的原因。这想法若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肯定会被认为匪夷所思,因为那时,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各种西方的现代观念和方法蜂拥而至,文学似乎再也不愿意充当时代政治的吹鼓手,“回到文学本身”成为最为响亮的口号。那么什么才是“文学本身”呢?陈晓明的说法直截了当:“虚构是文学的生命所在,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想象力,也就没有文学。文学虚构就是文学性本身。”这当然不无道理,文学从来都应是思接千载、浮游万物的,没有无中生有的能力,怎好意思自称文学家呢?但放在八十年代末倡导“纯文学”的语境中,陈晓明对“虚构”的强调,其实是从现代主义的观念出发,对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成规提出了挑战。很大程度上,他认为现实主义中的“现实”掺杂了太多陈词滥调,反倒不如现代主义的“虚构”更接近存在本身。专注于“内心的真实”的“精神分析叙事”,或者面向生活的鸡零狗碎的“零度情感叙事”,似乎能够提供给我们比真实更为真实的东西。然而这样一种带着浓重的西方现代哲学观念的论述,却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语境中,让文学从广阔的社会现实和公共事务中脱身而出,转而专注一己的悲欢和私密的体验了。接踵而至的,更是装饰性的橱窗文学、缺骨少血的牙签文学、哼哼唧唧的自慰文学、宣泄欲望的宝贝文学,在世纪末的文坛轮番亮相,虽各有斩获,但昙花一现,终归沉寂,而殚精竭虑和苦心经营的“纯文学”作家们,虽仍占据文学的半壁江山,但一呼百应的境况再也没有出现了。
求仁得仁,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虚构和自我中沉溺的作家们却又不甘寂寞,一度为文学“回归”所谓的“常态”而自鸣得意的理论家也坐不住了,他们集体反思的结果,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学”病了,而“非虚构”,则是因应这一病症的诊断,认为“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对‘虚构’文学所存在的问题的一种反思或反拨,试图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使我们重新认识文学,也重新认识当下世界”。照此理解,“非虚构”就不再是一个信手拈来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文学观念变革的内涵,其所谓的“非”,也带有了某种否定的意味,矛头所向,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倡导的“纯文学”概念(具体则落实于马原、余华、格非、苏童、洪峰、孙甘露等人的先锋文学实践)及其在“回到文学本身”的观念指引下确立的写作成规。所谓的“回到文学本身”,一方面解构宏大叙事,一方面热衷形式试验,其实都是以“虚构”的方式,向传统的现实主义抢夺“失去的真实感”。这充满悖论的诉求,原本极具解放能量的,但如今却演变成了脱离现实的负资产。而正是反感于缺乏现实关怀、缺席公共事务的“虚构文学”,“非虚构”论者才“试图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于是乎,一度势如破竹的先锋文学及其遗产似乎遭遇滑铁卢,而节节败退,以至于被人误以为现实主义似乎正有意争夺道义的制高点。
仿佛一切被颠倒过来的东西又被颠倒过去了,然而,现实主义却不是“非虚构”的对应物。“非虚构”是对虚构的反拨,但现实主义所能提供的却还是虚构类型的作品。据谢俊考证,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与十八世纪长篇小说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小说一度竭力想跟“虚构”“编造”划清界限,但这样一种“非虚构”的倾向,却在后来的文学实践中逐渐演变成了“现实主义无法实现的对知识论的承诺”。谢俊指出,这个“无法实现”的问题在自然主义那里已很明显了,而后左翼叙事传统中的现实主义,更是将“现实”变成了某种僵化教条的东西,这才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深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先锋文学提供了可乘之机,得以通过强调“虚构”来实现文学的自律性和作家的创造与想象权力,并以一番诡辩式的说辞,强调这才是通往“真实”的终南捷径。结果,经历此劫的现实主义陷入低谷,人们似乎很难再相信模仿、再现等文学观念可以提供“真实”的保障。所以,尽管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先锋文学的遗产不无非议,但借着底层写作之名强势回归的现实主义仍让人心存疑虑,以为它们所呈现的“现实”,总还是“别有用心”的“剪裁”,而此中的“用心”,或被定性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或被指认为学院派的话语方式,真正的生活或真实的底层,却在叙述中隐匿了。
然而没有主体介入的“真实”存在吗?李敬泽说:“‘非虚构’的‘非’是一种叫板,它不是不要‘虚构’,但却是要向标榜‘虚构’的文学强调自己是‘真实’的。”这实在是一个难题,不过好在李敬泽对“虚构文学”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所指,那就是渐趋没落的“纯文学”的写作成规,他对此提出的反拨,也因应了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等现实主义的回潮,强调作家真诚地介入社会现实和参与公共话题。但在文体上,“非虚构”写作却与我们所熟知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有着极大的不同而具有鲜明的跨界特征,既类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仿佛新闻记者的深度报道,并且因为它们的参与者,大多具有学者的身份,则又跟学术随笔不无瓜葛。如此一来,“非虚构”所在文本的世界中给我们描绘、展示、分析、评判的社会现实问题,与“底层写作”一样隐含了作者的主体性,其间的“剪裁”和“用心”,也少不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但却很少遭遇用道德的判断取代了文学判断之类的指责。个中原因,或在于“非虚构”不像“底层写作”一样担负了现实主义文学之名,而背叛了自己的知识论承诺,那也就无怪乎人们热衷于讨论“底层经验”如何被文学表达的“学术问题”了。相较于此,“非虚构”凭借一个“非”字就摈除了一切负担,像黄德海所说的:“人们似乎天然地明白它与新闻、戏剧、散文、随笔的不同,甚至报告文学,也不在它的范畴之内。”“非虚构”几乎“非”掉了一切,它自由地游走于不同的文体之间,而不需要承担这些文体的历史负担。但问题是,“真实”呢?我们既不敢说“非虚构”与“虚构”的对决中有多少胜算,而比之“底层写作”,如声名远播的《出梁庄记》与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相比,却也很难看出究竟哪一个更真切地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的乡土现实。
因为涉及“真实感”,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毕竟如李敬泽所言,“真实”并不是一块石头,它永远涉及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而这个认识、这个判断,本身就存在纷繁的矛盾和分歧,这使“真实”变成了一个极具难度的目标。但问题是,原本在“虚构”基础上建立起“真实”权威的小说,已难以支撑起我们的信任了,而“非虚构”通过给读者预设了一个看作品的特定角度,标榜自己不是“向壁虚构”竟在某种意义上确立了它对小说的优势。这种自我的标榜,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获得广泛认可和热烈追捧,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虚构”小说的信誉危机为前提的。有一句被大家经常提及的话,生活比小说精彩,这一方面是感叹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有时远超以虚构见长的小说,而另一方面,却也是说明沉迷于私密经验的小说已经让我们觉得贫乏,不足以触碰我们的神经,丰富我们的体验,带给我们真切的感动了。要知道,今天很多人的生活已在很大程度上为高精密的摄像头和屏幕所俘获,而数字化网络媒介的普遍应用,更是让影像化的日常生活便捷地传播和分享,在其中,不仅能够轻易窥探到别人的生活,而且有充分的途径释放剩余的力比多。这时候,人们似乎不必仰赖“虚构”小说获取现实生活的戏剧感和传奇性了,相反,倒是奇异幻想背后有关“现实”的深度分析,才成了满足人们审美期待的重要维度。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虚构”才敢向“虚构”叫板,允许主体深度介入的“真实”,才又绕过现实主义的坎,成为文学正面肯定的价值。
随着这样的“非虚构”理念的深入人心,昔日的先锋作家余华,一度将“虚构”奉为圭臬的,却也玩起“新闻串串烧”,出版了《第七天》。这让我们像李松睿一般恍然意识到,原来“作家也像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仅仅通过屏幕和摄像头观察这个世界”,“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其实也是被媒介所限制的”。李松睿却对像余华这样“非常优秀的作家的作品开始表现出某种新闻化的倾向”大为不满。对于李松睿的批评,余华或者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串联新闻事件,是对于现实的正面表现,而为之辩护的木叶,更是将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拿来做了类比,以为相比卡波特瞄准一个新闻事件,写下去,穷尽它,“余华是把源自社会的一系列事件集束性地回敬给了这个社会”。且不管木叶的类比是否恰当,却别忘了在众多为“非虚构”寻找国际支援的论述中,卡波特的《冷血》一向是被当作“非虚构”典范。他以新闻记者的姿态主动出击,历时一年多,几乎穷尽了新闻背后的各种关联,而余华,却不过将新闻事件作为想象和虚构的前提。所以,我们虽然对“非虚构”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还不清楚,但就余华和卡波特而言,他们一个坐在家里依据新闻创作小说,一个以新闻调查的方式写小说,这姿态上的差别,或应算作“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写作的基本分野吧?
注释:
[1]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2]李云雷:《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
[3]谢俊:《在文本细碎处描写真实》,《今天》,2018年第115期。
[4][6]李敬泽:《关于非虚构答陈竞》,《杉乡文学》,2011年第6期。
[5]黄德海:《作为竞争的虚构与非虚构》,《东吴学术》,2017年第2期。
[7]李松睿:《以反思的姿态理解生活》,《文艺报》,2018年6月22日。
[8]木叶:《先锋之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