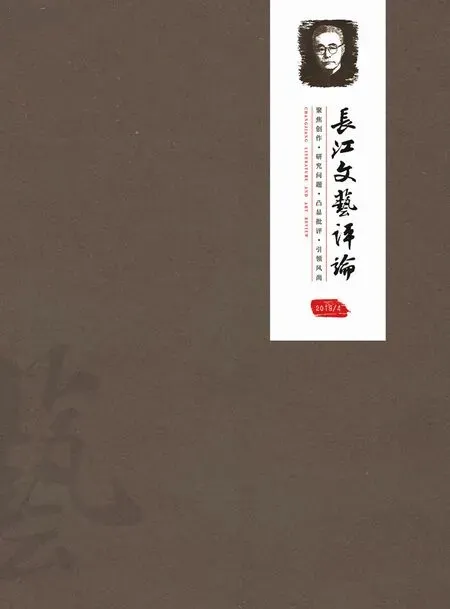“非虚构”写作的勃兴与趋向
◆阎海军
一、“非虚构”写作勃兴的内部机制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一直是高悬在理想人类社会追求者头顶的三把利剑。这三大差别在人类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中都有最直接“最彻底”最充分的反映,文艺创作概莫能外。回顾各个历史时期,文艺在反映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方面,总是偏重于前者,偏心于前者。整个文艺史,普通人想“我手写我心”很难实现,“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打破了文艺为特权者所独占的局面。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一语言革命,不仅使“引车卖浆者流”的话语进入文学世界,而且于无意识中赋予劳动者以写作工具与权利,开启了劳动者书写的大门,书写底层和底层书写成为可能。这一潜能在革命文艺中得到释放,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写作主潮,大量文艺家进入民间,进入底层,不仅丰富、升华了自己的情感世界与艺术世界,而且也普及了文艺,在民间播下了文艺的种子。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产生了握锄头者也能握笔的新局面,涌现出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形成了“西李马胡孙”(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梯队。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笔下的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工农兵中产生了一批作家、诗人,真正实现了写作主体的革命。比如陈登科就是典型的农民作家,而胡万春则是典型的工人诗人,这样的作家、诗人还有不少。
当然,这样的文学作品,不是高居庙堂或者学院的作者创作不了,而是他们不想这么写,有的甚至不屑这么写,因为在他们眼中,文学是典雅的、高贵的、阳春白雪的。更进一步说,在有些人眼中,文学是权力,文人的权力,怎么甘心将其让渡给底层、民间,让渡给普通的劳动者呢!实际上,新时期后,此前好不容易向广大劳动者打开的文学创作的大门又渐渐关闭了,文学再次成为了文人的特权或专利。加之在物质快速增长的进程中,物欲和消费渐成风潮,文艺上的三大差别再度深化。文学艺术领域涉及底层的创作,尤其是“涉农产品”全线萎缩,即便出现农民形象,也是以喜剧、调侃、消费、搞笑元素点缀其中。“告别革命”“告别崇高”之后,就连英雄主义都淡出了文艺作品,反映底层民众奋斗精神和内心焦灼的文艺作品自然更是凤毛麟角。娱乐、低俗、媚俗、消沉成了各类文艺作品博取噱头的卖点。
1980年代是文学红火的时代,纯文学、商业文学、主旋律文学三足鼎立。纯文学基本上跟现实不发生具体的关系,不描写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只描写个人抽象的苦闷、绝望等情绪,好似无病呻吟;商业文学是资本占领精神文化领域,文学成为商品;主旋律文学侧重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很少触及真正的社会问题。这三类文学都与大众的真实感官、意志情趣存在距离。
到了1990年代,情况更加恶化,文学界普遍发出了“文学边缘化”的哀叹。大众逐渐厌倦了端着架子、拿着腔调说话的文学写作。即便将文字拿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码出来的无非是一堆技巧。没有对现实的观照、没有真情实感的流淌、没有人格思想的升华、没有崇高人性的宣扬,不论多么华丽的辞章也只能落入空洞。
这种局面的出现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一点是“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起了坏作用。面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裂变,文学生产传播的土壤并没有特殊的免疫功能。
针对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的一系列病灶,文学界革故鼎新的力量奋力突围。其中,尤以“底层文学”的形成最为显著。曹征路、陈应松等面向底层创作的一大批作品,形成了“底层文学”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崛起之势。“底层文学”在内容上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主要继承了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青年文学评论家李云雷认为“底层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先锋性的一种文学形态。
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作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它的文化意义在于揭示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叩问人的生存意义,沟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憧憬人类的未来。这个关于文学的文化意义,应当是文学创作者极力去追求、努力去实现的创作目标。底层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者,但他们的主体性在文艺作品中基本被忽视了。“底层文学”在新世纪初期的集中呈现,是文学文化意义回归的标志,也是对文艺创作缺乏底层主体性问题的直接回应。
转瞬间,又是十年。正当“底层文学”追求写作应当关注底层民众理念之际,一种全新的——从形式到内容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创作理念——“非虚构”写作,经由西方记者的作品开路,迅速在中国流播。“非虚构”写作倡导写作成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常态,并认为,没有天生的写作大师,不论你是高高在上的学界泰斗,还是终日忙碌在田间地头的农民,在写作的权力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非虚构”写作鼓励所有人不只做现实的参与者,还可以成为现实的记录者。
普通读者、大众读者被阻拦在门外,久而久之,文学变成了小圈子、小阵营把玩的小天地。对“纯文学”固步自封状态的批判,如果说“底层文学”是一个文学流派的话,那么,“非虚构”显然是以一种全新的文体出现的。“非虚构”倡议“人人可为”的草根心态,更能激起大众的共鸣。与“纯文学”或者传统文学追求技巧、追求辞章不同,“非虚构”写作更注重真相和感情的呈现,这是切合大众心理的关键。“非虚构”在形式上,与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19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相近。在观照现实的追求上与“底层文学”理念有一脉相承的逻辑。
以上脉络,是文学内部生产机制催生“非虚构”写作的原因。
二、“非虚构”写作已经开创了新局面
“非虚构”写作发端于美国,起初称“新新闻主义”,是一种新闻报道形式。“新新闻主义”报道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英美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记者型作家,但凡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大都是“非虚构”写作大师。这种非虚构写作方式主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风行,但由于记者为了报道的戏剧性效果,会对事实进行篡改加工,从而歪曲事实,遭到了学界的激烈批评。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于1995年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开设“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研究生课程,标志着“新新闻主义”作为一种二十世纪重要的新闻学流派被学术界正式接纳。
二十一世纪,“非虚构”写作理念进入中国。《寻路中国》《打工女孩》《两个故宫的离合》《落脚城市》等外国记者撰写的“非虚构”作品被出版,好评不断。中国一些媒体也致力于“非虚构”新闻写作的实践,形成了“特稿”写作风潮,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稿件。专著方面,中国本土写作者也推出了一些代表性作品,比如《中国在梁庄》《崖边报告》《大地上的亲人》等。但总体而言,中国“非虚构”写作尚处在起始阶段。
当下,不论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新媒体,都存在如何更好地扩大传播效果的问题。“新新闻主义”是为了让新闻更好看而动用了文学创作的可读性优势。中国传媒业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在趋同世界水准的节点上,追求“非虚构”文体理所当然。
但由于“非虚构”边界广阔,国内还没有清晰的共识。目前,国内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基本是两路人马:一路是纯文学作家,一路是媒体记者。两路人马由于体制性的障碍,各自有各自坚持的理由。概念是关于写作观念和套路的,无论贴合哪一种概念的写作,真诚表达至关重要。从“非虚构”写作的发展历史看,如果用美国成功的“非虚构”评价体系检验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很多标识为“非虚构”作品的纯文学,是难以获得认可的。这也是李敬泽认为“真正好的非虚构写作会在记者中产生”的原因。
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生命。美国“非虚构”作家的作品,把文学的修辞非常限制地糅合进了新闻写作,而新闻写作在追求真实性的同时,注重文学化地表达,增加了“非虚构”的吸引力。
“非虚构”写作借助互联网传播,在国内已经形成气候。“腾讯谷雨”“网易人间”“正午故事”“真实故事”等非虚构写作平台,聚合了数以万计的读者群。有的平台大力扶持民间语文,真正做到了不薄新人,以质论稿。还有一些公号,写得好了,打赏多多。这完全是脱离于传统体制的新市场,充满了活力,也是大众书写、大众传播局面真正形成的重大标志,无疑给发行量捉襟见肘的纯文学刊物敲响了警钟。不过,也有一些“非虚构”自媒体平台为了收割流量,出现了猎奇、编造、洗稿等不良现象,这也是亟需加强监管并警惕的问题。
鲁迅先生曾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非虚构”写作无疑给中国文学开辟了新路。眼看各家互联网“非虚构”写作平台不惟名家、以质论稿传播的故事动辄收获数百万阅读量,眼看各个自媒体平台真正实现了“我手写我心”、人人能发声的局面,仰仗体制存活的纯文学写作者和刊物,如果依然沉睡在小圈子小阵营相互赏玩,只能走向边缘化。
最近几年,矿工陈年喜、保姆范雨素、女工李若、农民余秀华的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被万千网民热捧,就是因为他们的书写浸透着生命历程和人世沧桑,是坦诚、感人并催人奋进的;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等关注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发展图景的专著之所以引发媒体、学界、读者广泛关注,核心原因就在于他们扎根人民,有着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
尽管目前中国作协和中国记协都没有在评价体系里确认“非虚构”写作,但这个新兴潮流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已经开创了不可小觑的领地,未来必然是不得不正视的力量。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非虚构”写作
笔者作为媒体记者,同时热衷文学创作,过去十多年一直从事“非虚构”写作。结合创作实践,笔者认为,“非虚构”从调查采访到写作,必须注重共在、共鸣、共识。
1.共在:带着真情采访
“非虚构”作品的本质是真实。为了追求真实,“非虚构”创作不论敏感于时效抓取当下,还是潜入到历史挖掘故去,都必须要有扎实的采访。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非虚构”的采访也决不能抱着置身事外的心态品头论足,以机械化、程式化的操作去完成。如果机械地为了完成采访而采访,写作者不可能挖掘到典型的材料,也不可能让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具备震撼人心的力量。去除程式化、形式化的采访,只有让采访回归到“人类共在”基础上。也只有从“共在”这个基础出发,才能真正客观真实地反映人的社会存在,才能更好地参照制度、规则、宗教、信仰、公序良俗等社会因素,发现人性的力量和价值。
“非虚构”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深度。“非虚构”写作作为针对专门领域、特定对象展开的深度观察,必须要放下身段,进行扎实的田野考察,谋求与人建立共在关系。这就要求“非虚构”故事必须深入挖掘,进行实地的采访。林强写《生命的力量》,和麻风病人交朋友,连续15年走进四川凉山无数个麻风村;亚妮写《没眼人》,十多年投身山西太行山,与盲艺人同吃同住同走艺……每一部感人的“非虚构”作品,采访都建立在与被采访对象的共在之上。
“非虚构”写作者可以是每个行业的从业者,但在调查采访中,必须成为“记者”,成为懂得与被采访人在时空关系中建立共在意识和行动的人。对被采访对象,不能割裂成他者。记者是为如何抵近真相而寻找路径的职业,仔细检索,古今中外,拿出大文章,关注大世相的作家,都是像记者一样去采访的。所以,“非虚构”写作,必须要像记者那样扎扎实实去采访。
2.共鸣:写出感同身受
写作就是为了表达,但凡表达,终极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话有人听。表达要获得认知,就得从说话技巧上布局,这是传播学的范畴。通俗讲就是要找到共鸣点。什么最能引起共鸣,肯定是“关注大家关心的”。这是搞新闻的人天天要念的经。新闻有地缘性、时效性、贴近性,但还要讲究“关注大家关心的”。那么,不属于新闻范畴的“冷”题材,主题确立更应该注重大家是否关注的问题。
共鸣,必须从大多数人的立场出发去寻找,要从大多数人的心底间去寻找。关注当下,关注大多数人的喜怒哀乐,就是最大的共鸣。伟大的“非虚构”作品,必然是改写时代进程,参与历史运动的。
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深度调查,推动国家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无缘社会》揭示日本老龄化、少子化、人与人互相切断联络等问题,中国也将迎来老龄化,所以该书在中国出版,同样引发了中国读者的共鸣。《落脚城市》检视世界各地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困苦,中国正在急速城市化,所以“农二代”感到了深刻的共鸣。
为什么太过专业的论文式著作大众不喜欢看?为什么徒有形式、文辞华丽的纯文学不被大众阅读?因为不接地气。“非虚构”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综合了新闻性、文学性两种文本的优势,总是在人与社会关联性最紧密的节点处聚焦。
“非虚构”创作,求得与读者的共鸣,要做到主题确立关注当下而不猎奇,叙述语言生动而不浮华、为文姿态冷静而不冷血、组织结构纵横自如而不杂乱。“非虚构”要接地气,就不能打精英腔、文艺腔、学术腔、官僚腔,不能讲空话、套话、假话。要反映占人口数量最庞大的那一部分人的喜怒哀乐,他们才是社会的主流。
3.共识:寻求社会认知最大公约数
思想的争辩、观点的争鸣,最终的落脚点应该归在共识。只有寻求共识,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的发展进步。
建构共识,首先得有崇高的使命,要把写作当成严肃的精神活动。伟大的文艺作品,必须是震撼人心的,必然是具备观点立场的。寻求共识必须要有坚定的立场:确定自己的屁股坐在谁的一面。以人民为中心书写,不是口号,而是真经。背离大众志趣、背离大众喜怒哀乐的作品,不可能赢得大众的掌声。
当下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讲道理容易陷入枯燥乏味,寻求共识得考虑方式方法。生活远比想象更震撼,节制抒情、多讲故事、少来道理,是一个上好的办法。人生来热爱故事,所有的艺术都是用故事来升华主题的。好莱坞用故事构建了文化软实力,将他们的价值观无孔不入地进行着传播。“非虚构”的标志是真实和故事,寓情理于故事之中,是“非虚构”求共识的有效手段。比如《我从新疆来》讲述了100个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新疆人的故事,展现了多民族团结奋斗才能进步发展的共识。
共在、共鸣、共识,是相辅相成的三角关系,只有让它们既是方法也是目标,既是过程也是结局,才能促成一部好作品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