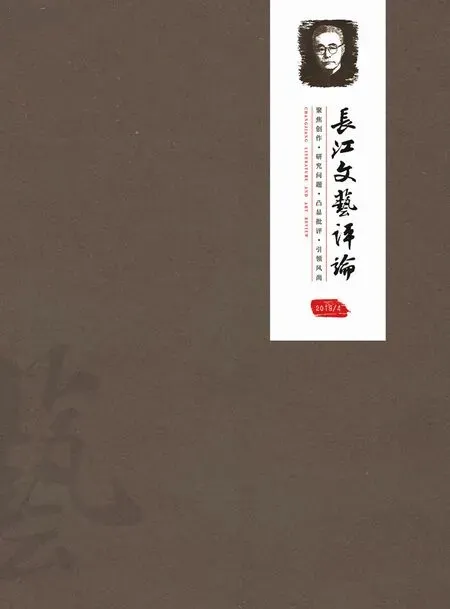微小的精致与宏大的缺失
——论“9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
◆张琳琳 房 伟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呈现出丰富化、多样化的形态,作为文坛新生力量的“90后”作家则愈发闪耀。他们凭借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表达着他们对于社会人生的理解。代际划分源于现代中国飞速发展的现实,于他国他族而言,代际区分也许并不鲜明。同时,作家代际划分也不乏媒体、商业资本的幕后推动。代际尚不足以概括一时一代的作家创作,文学的意义恰在于作家的个性,于作品间见出个体心灵的光芒。尽管如此,面对纷繁多变的文学发展现状,凭借代际视角,用以分析文学面貌、文学发展实际,又是有效的。“90后”作家出生、成长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跨越式变革的时代,当以代际眼光观察处于巨大历史变局中的“90后”创作,更要关注他们能否从同代人的经验出发,写出“同时代人”的生活、情感和心灵状态,写出他们独有的时代感知,呈现出独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命景观。
一、隔代继承:“90后”的先锋叙事
总的来说,“90后”作家是相当会讲故事的一代,这首先就指向了技术的问题,直接关乎于“怎么写”,但又不止于此。“90后”作家大多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不少人还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在大学里的中文系读书。同时,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使他们比前辈作家拥有更多的中外文学经典和理论资源的储备。他们深谙现代小说写作之道,同时又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他们的创作里,充满着无处不在的先锋精神,“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这在“90后”作家的创作里随处可见。这种讲故事的能力,不只在于叙述语言的连贯流畅,小说结构的精妙清奇,更在于对于先锋精神的承续与发展。
李唐的小说《降落》堪称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砂原不堪忍受冷漠无爱的父母和家庭,厌倦了平庸乏味又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琐碎生活,甚至一度被周围人当成是贼。于是走上了漫无目的的流浪之旅。他去桥洞找温暖,为谋生做推销员,甚至一度加入猎猫小组,通过残忍捕猫以维持生活。尽管小说里现实与虚幻的界限并不清晰,但砂原对于自己想成为什么样人的追问从未停止,毫不动摇地遵从内心的声音,这些从未变过。甚至不惜去流浪,以至最后冲上跳伞塔,在生与死的极端状态里看清自己的内心,完成自我成长。而在小说《挽歌》里,李唐则进行了一次人生历程的预演。“我”担任护工照顾年迈老人,单调无聊又充满死亡气息的生活日常,让我深感厌烦。当我眼见老人的衰老,生命气息的逐渐消亡,竟突然醒悟:我和老人是彼此依存的。老人看似衰老的身体,是使我不至偏离太远的最后防线。于是我和老人有了临时起意的海边探险,这是老人生命中最后一抹希望之光,却以失败告终。在小说结尾,我成了那位老人,曾发生在老人身上的事,在我身上重演,题目“挽歌”既是唱给老人的生命挽歌,也是给我的,更是给所有人的,这是人类的宿命。生命的历程就是我到老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不只有作为常态的琐碎日常,也有探险大海的果敢尝试。李唐的笔下多是漂泊无助的孤独个体,世界是不可知的,更是难以把握的。日常生活在不知不觉间完成对人的塑造,但一切又是留有希望的。然而,这一切感知与思考的起点,却是个人化的、从日常现实出发的体验。王苏辛在小说《马灵芝》里,通过“多声部”的文本组织方式,在孙女“李挪”和“外人”的双重叙述里,讲述了祖母马灵芝的晚年生活,是个令人啼笑皆非又不乏辛酸的故事,同时也是关于孙女李挪的成长记忆,在祖孙两代人双重镜像的相互对照里,足见“90后”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理解:当生命被简化为活着、老着、死着,故事的讲述更是在处理“我”与世界的关系,而这个世界就是“我”所处的生活本身,就是此时此地。
在小说《所有动画片的结局》中,王苏辛通过点播台的动画片——这个属于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在时空交替的叙述里,讲述对于人情人世的理解:人与人之间总是渐行渐远的,他们始终不同,却在对他人的投视里,我们看清了自己,才得以真正维系彼此情感的勾连。我们和朋友间是如此,父母们亦然。然而,生命本身却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就如点播台的动画片一般,永远没有结局,永远存在无尽希望。智啊威的小说《世世无穷》是通过亡灵叙事讲述有关妹妹的故事。当年“我”为救落水的妹妹而溺亡。伤心的妹妹带着和哥哥一同照料的小羊,对着树叶、荒草、风声、雨声、鸟鸣、暮色喊哥哥。小羊是兄妹亲情的见证,更是对哥哥情感的延续。可就是这样的小羊,竟被母亲狠心卖掉以换取姐姐的医药费,绝望无助的妹妹吞下大瓶农药。乡村的破败、贫穷和生存之难,难于割舍的兄妹之情,共同构成了“90后”笔下独特的乡村景观,它关乎亲情、死亡和永生。
像李唐、王苏辛、智啊威、索耳、国生等专注于先锋写作的“90后”作家,他们的创作中充满现代、后现代意味的叙事腔调,先锋气质总是毫不意外地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写作,由于对于形式探索的过度强调,造成了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相对封闭,缺少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文学的现实指涉能力明显减弱。“90后”的先锋写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规避了前代先锋书写现实指涉性不足的缺憾。他们从现实生活出发,自己的亲身体验、身边人的经历成为他们先锋叙事的起点。文学本位的先锋立场,旗帜鲜明的现实关怀,这些使得“90后”作家的先锋写作颇有光彩。
但是,“90后”作家的先锋书写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如果说,“90后”作家的先锋写作根源于现实土壤,讲述的是个人化的体验,是关乎个体心灵的历程,但过于先锋的笔法,无疑加大了阅读的难度,就使得这种难能可贵的个人化思考,降格为自我话语的缠绕与梦呓,个体心灵的声音成为了难以窥探的迷梦。经由先锋书写抒发的个体感知,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人所领悟?
更大的问题在于,“90后”作家的先锋书写,似乎跳过了“80后”的文学经验,特别是尖锐的代际冲突,在回归先锋的同时,也通过“隔代继承”回到了文学体制。他们的作品,可视为对文学传统的延续与继承;另一方面,“90后”作家却又难以真正走出前辈作家的窠臼。如果说,所谓的“叙事圈套”“叙述空缺”和“结构性叙事”是属于马原、格非、孙甘露这些前辈作家的探索与创造,那么属于“90后”这一代的先锋创举又是什么?什么能代表他们这一代的先锋探索?而这正是“90后”作家尚未完成的答卷。“90后”作家更多还是在延续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文学发展脉络,他们的创作是当下文坛的自然延伸。如何写出“90后”这代人独有的先锋体验,既拥有现实生活的根基,又葆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于不乏真诚的个体声音中创造出独属于这代人的先锋探索?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90后”的先锋写作者抱以期待,而这也正是“90后”作家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二、理解自我:“90后”笔下的情爱叙事
抛却“怎么写”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写什么”——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同样不容忽视。和前辈作家相比,“90后”作家的创作心态相对放松,“影响的焦虑”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试图给人们营造出开放自由的景象,“主流意识形态退到后台。它允许‘中国故事’悬置它的存在,却不允许任何文学冒犯设定的意识形态禁忌。只要在游戏规则内,任何欲望表述都不会成为禁忌”。于是,在世纪之交出现以卫慧、绵绵、木子美为代表的女性“身体书写”的热潮,大胆直露女性欲望,直面情爱叙事,在新消费时代的背景下,营造关于女性与民族国家叙事的另类合流。同时,韩寒、张悦然、郭敬明等“80后”作家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正式亮相,他们主打青春叙事,抒写成长焦虑,情爱叙事更是必不可少。从九十年代初以朱文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的欲望化叙事,到新世纪之交以卫慧《上海宝贝》为代表的身体书写,情爱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逻辑里,一度扮演重要角色,成为难以忽视的文学风尚。“90后”作家也写青春记忆,自然也少不了情爱叙事,但处理这类相近题材时,却和前辈作家有着明显的差异。
宋阿曼的小说《领灯》,看似写的是顺子胡同里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往事。小说在多重叙事空间展开叙述,女主人公云珍与同为租客的马马强相恋。马马强是个村里娃,肩负父亲的期望,一心要考北京的公务员,两人在平日的相处里越走越近。尽管这是小说重要的情节线索,但却并非唯一,这更是一个关乎父爱、成长和人情人性的故事。云珍的父亲在矿难里丧生,母亲拉扯云珍长大,要她出人头地走出矿区。云珍争气考上大学,独自在外打拼。最终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走向末路,马马强第三次考公务员失败,竟不告而别离京返乡,留下云珍一人,连同他们栖居的顺子胡同也即将拆迁,心如止水的云珍重回满载童年回忆也是父亲所葬身的矿上。种种表象的背后是作者对于世态人心的洞悉。在小说《午餐后航行》里,宋阿曼讲述了主人公何溪独特的爱情过往,她在与异性一次次“试错性”的交往里,收获的不仅仅是失败,似乎更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实现关于自我主体的辨识与认知,以期找到自己人生之流的正确流向。当何溪意识到自己与徐魏情感的错位,她在楼顶上的疯狂、无助、失态以至昏厥,既是她过往人生的终点,更是新的起点。
庞羽的小说《没人拒绝得了董小姐》,透过一次好友间的婚前旅行,我们看到了两种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婚恋观念。小说以董雪君的视角看董小宛的寻爱之路。在“爱情顽主”董小宛一次次啼笑皆非的爱情交往里,在她“没人能拒绝得了我”的宣言中,见出的是青年女性对爱对情的向往执着,是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矛盾里,对于真情真意的渴望与期待。
周朝军的小说《西安今夜有雪》,是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古老母题,却以“忏悔录”式的形式展开叙事。“我”与木青校园结情,毕业后同到西安打拼。木青温柔体贴又吃苦肯干,可我却背叛了她另结新欢。如今回首往事,一切物是人非,我已为人夫、为人父,木青也有了新的开始,新的生活,追忆这段无疾而终的情感,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对于自我的体察与认知,是以情爱为表,写成长之实。
换言之,不同于“80后”作家的情爱叙事,受到太多类型文学的影响,将情感问题视为情节发展的唯一逻辑,将之确定为思考的起点与终点,也不同于“新生代作家”将一切情感因素都简单归结为欲望问题,在“90后”作家这里,情爱叙事一度成为理解自我,实现自我主体确认的重要方式,并以此实现个体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完型。
通过情爱叙事实现关于自我主体的确认,这并非“90后作家”的独特创造,早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在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中就可见端倪,再后来丁玲的创作里,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得就更加明晰。这种书写不失为“90后”作家理解自我与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在实际的创作里又产生了新的问题:“90后”的情爱叙事呈现出相似的面貌,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多是讲述现代女性的成长故事,女性们或是粉面如钢,或百转柔肠,却都逃不过各式的爱情牵绊与纠缠,最终经历“由凡入圣”的终极考验,由此完成关于女性的自我成长。“90后”的情爱书写大体不出这个路数,作家或者自我重复,或者彼此重复。更严峻的问题是:经由情爱书写能否真正实现“我”与世界关系的确认?并由此实现关于自我主体的确立?这个自我是不是独立完备的现代性自我?即使通过情爱叙述走向完备的个体自我,情爱本身又近乎成为唯一的叙事动力,这是否又走向了另一种欲望化叙事的陷阱?这些都是“90后”情爱书写无可逃避的问题。
三、“轻”与“重”的失衡:精致却微小的现实笔触
尽管“90后”作家正努力在各个题材领域开疆拓土,创造出丰富繁多的文学盛景。但谈及“90后”一代的创作,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90后”创作里鲜明的个人化倾向。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国文坛深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在文学创作里出现了一股反叛传统的先锋潮流,关注的焦点从作为类的文化建构转向个体自我的确立。这种倾向在刘索拉、徐星等人的现代派小说和“第三代”诗歌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文学甚至人文学科的边缘化,作家们无需再像以往那般,从时代的和鸣共声出发进行创作,相反要发出个性化的独特声音,表达个体自我对于社会人生的感知,这种趋势一路延续至今,成为今天“90后”创作的主体面貌。
当中国当代文学逐渐摆脱革命话语和宏大叙事的裹挟,转为关注小人物、普通人凡俗的日常生活以后,这类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里并不罕见。不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潮流,还是后来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或九十年代盛行的以迟子建、范小青、何玉茹为代表的抒情性日常现实写作,作家们对于小人物、普通人平凡日常生活的书写从不缺乏。那么“90后”作家们对于小人物平凡人生的关注,其书写的独特性又是什么?
于是,王占黑的小说《空响炮》里,禁放爆竹这一小小政策的施行,给鞭炮业主、香烛店老板、清洁工、公交车司机、居委会大妈等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如此巨大的震动。王占黑从禁放爆竹这样微小的细节切入,写出小人物面对生活里任何微小变化的惊慌无措,表现他们无力应对生活里的任何变动。在《美芬的小世界》里,母亲美芬早年丧夫,她含辛茹苦拉扯女儿长大成人,她人生唯一的期待,就是在女儿婚礼上风风光光打扮一次。她为女儿婚礼而给自己置办的三套行头见证了这一切。但女儿这一代人对于婚姻爱情的选择,使她的期望彻底落空。《演说家吴赌》则是一个当代孔乙己的故事。主人公吴赌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他人生里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便是站在公交车的投币处做个“演说家”,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丰功伟绩”。但实际上,他的故事对他人而言不过是谈资而已,没人真正在意。但这滔滔不绝的“演说”,却成为他实现自我确认的唯一途径。王占黑通过一个个精妙的细节,讲述了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各式经历、各样灵魂。这些不仅关乎生活,更关乎生存。
郑在欢的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则把关注的目光对准了他的家乡河南驻马店,关注那里人们的苦辣辛酸、人生百态,整部小说集被整合为两个序列,分别是“病人列传”和“Cult家族”。笔尖所至都是我们身边人,有“疯狂原始人”——“我”的奶奶,继母“暴烈之花”,还有誓死捍卫贞操和枣树的“圣女菊花”,也有百年难遇的拾粪高手八摊。小说里明显有着对鲁迅式国民性批判传统的承续。在那里,人们贫困而愚昧,落后而不自知,但却对生活有着难以想象的执着与坚强。“生活意味着承担一项活下去就必须承担的功能,而这开启了竞争、成功和失败的领域。”当小人物的主体性受到压抑,他们无以改变自身的处境,无以表达自我,“底层人不能说话”时,“90后”作家的底层叙事和小人物书写就显出了可贵。
但是,这种现实书写又存在问题。“90后”作家的现实书写根柢在于个人化叙事,即私人叙事,不论是书写自己的故事,还是“为他人写作”,都是从个人化的视角出发,生发出对于时代人生的理解。这就导致了“90后”作家的现实书写,尽管细致精巧,能从细微处入手,见出个性化的见解,乃至于对时代社会的认知,但最终还是局限于个人这一方小小天地,个体之外的广阔天地被悬置。当个人化立场占据过多叙事空间,就造成“自我”无限放大,世界只局限于“我”眼中一隅,“他者”只能冷眼旁观,至多驻足叫好,却永远不能感同身受。最终走向自我情绪的泛滥,却找不到真正坚实的存在内核。过于微小的现实描写使得“90后”作家走向了“微观现实主义”,是放松的、微小的、精致的,却丧失了探索宏大问题的能量,失去把握总体性、宏观性问题的能力,这成为“90后”写作的通病。
换言之,“90后”作家个人化的现实叙事,带来的是一种失衡,是“轻”与“重”的失衡。“90后”的创作太过于“轻”了,过于微小,过于精致,这个问题不只局限于个人化的日常现实书写,在“90后”的先锋叙事和情爱书写中同样存在。“90后”作家过于关注个体自我的小情小绪,却对重大历史问题、历史判断持回避的态度,而这恰恰是文学书写震撼人心之所在。这种缺失既是由于“90后”自身经验的匮乏,同时也是源于时代社会的塑造。不像父辈们亲历时代发展的进程,与社会一同激荡蜕变,“90后”与时代的关系忽远忽近,他们真正触及到的只有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但是历史与现实是同构的,无法正视历史,如何能看得清现实?没有对过往历史的认知,又如何能真正理解今天?缺少对宏大问题和重大历史的思索、判断的“90后”创作,如何能真正走得更远?正如捷尔吉·卢卡奇所言:“小说则试图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建构隐蔽的生活总体。”显然,小说着力展现的是一个总体性的世界,更是“轻”与“重”双向平衡的世界。如果生活总体是被塑造的结果,同时也就表明了对塑造的态度:“历史情况自身所承载的一切破裂和险境,都得包括进塑造中去,而不能也不应该用编排的手段加以掩饰。”“90后”作家正是由于过于关注个人微小化的体验感受,而缺少对于重大历史判断与宏大问题的呈现,导致了他们在总体性世界的建构里出现了“轻”与“重”的失衡,这也使得“90后”作家的创作始终难以突破原有文学体制的框架。如果说“80后”作家在消费时代的大背景下,以类型化的文学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文学体制,那么“90后”的文学创作则还是处于“纯文学”的范畴内。如何处理“轻”与“重”的关系,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如何有所创建,这是摆在“90后”作家面前的最大考验。
实际上,对日常现实的关注没错,进行个人化叙事更没有问题,这甚至成为当今世界文学主流。不论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还是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无一不是从个体出发,扩大到整个家庭家族,再到一座城市,甚至于整个民族国家。真正的问题在于:“90后”作家如何处理自我与宏大问题的关系?个人化叙事决不可只局限于自我的一隅之地,私人叙事应当承担起更宏阔的现实所指。
这样一个急剧变动、飞速发展的时代给予了文学创作无限的可能,今天更应是一个出现大作品的时代,我们期待作为“同时代人”的“90后”作家,既置身于时代变革的大潮里,又能保持相对独立自省的声音,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的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90后”作家在个体自我与宏大历史之间找寻到一种平衡,既能放宽视野,又能立足于时代,写出这一代人所独有的时代经验和中国故事。
注释:
[1]【法】欧仁·尤奈斯库:《论先锋派》,《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79页。
[2]房伟:《“城市中国”:文化空间的幻像之舞——另一种有关上海的“都市想象”》,《文艺评论》,2018年第6期。
[3]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6页。
[4]【匈】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第88页。
[5]【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6][7]【匈】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3页,53页。
[8]【意】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载《裸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9]【意】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