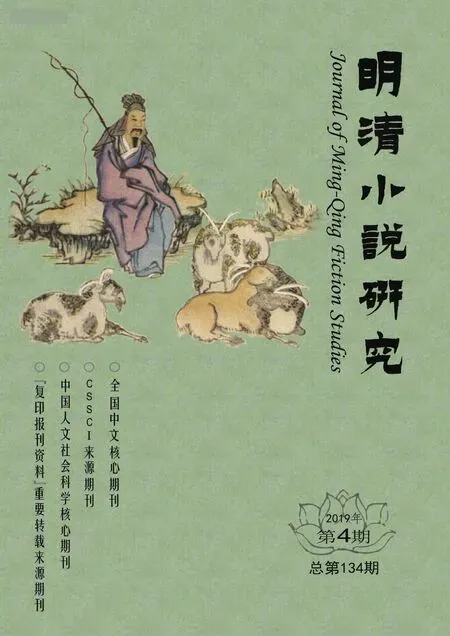意图力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个性化关系研究
——以明清小说文本为例∗
·公维军 阳玉平·
内容提要 意图叙事理论是对西方叙事理论的一次突破与创新,其研究视角从纯粹的行为转向人物及其心理动态,符合中国叙事作品的客观实际。基于此,文章拟围绕作品叙事者的叙事意图与接受者的接受意图之间的关系展开,从反简单化、乐喜厌悲、顺乎天命“三原则说”新视角对意图力进行深入阐释;同时,借鉴西方文学分析中的“陌生化”等理论,从内、外叙述者两个宏观视域剖析意图力能够得以顺利实现的个性化问题,通过意图力与叙事个性化关系的分析,凸显意图叙事理论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中的优势所在。
叙事学深受法国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故而西方叙事学理论建构在表音文字基础之上,是一种立足于语言学共时态分析的行为(故事)叙事理论。然而,当我们满怀着“普适性”期待,套用西方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作品时,却明显体认到削足适履的不适之感。因此,在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合理性内核的前提下,如何建构一套符合中国文学研究实际的叙事学理论,就成为当前中国文学界学人共同关心、思考并探索的问题。
“意图叙事理论”的提出,为中国文学研究适时开启一扇希望之窗,在以许建平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潜心研究阐释下,取得日渐丰硕的成果。许先生指出,这套中国式叙事理论“借鉴西方行为叙述理论,意在追寻行为背后生成行为的根源,对其做出心理和哲学的阐释”,其与行为叙事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一是重视人物,二是强调意图。行为叙事重行为而轻人物,认为人物完全从属于行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甚至否认人物在叙述上有任何重要性;而意图叙事却能够深度契合人本主义理念,在修正行为叙事封闭性和褊狭性的同时,强化着心理意识和意欲动机,并不断扩大自身学术研究视域。可见,意图叙事理论是西方叙事理论“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尤其适用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能够不断凸显从小说人物行为意图的全新视角研究“人”的行为及其结构。
一、“意图”与“意图力”析疑
意图,是人们希冀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打算或设想,是心中所怀揣的欲望与动机,简言之,即内心萌发生成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愿景。然而,意图叙事理论所强调的“意图”,则“指行为者活动前萌生的想要达到的某种目的性的图景,是具体化的生活欲望”。法国文学家克洛德·布雷蒙认为:“叙述者可以把一个行动或一个事件化为现实,也有自由或者让变化过程发展到底或者在中路把它截断:行动可能达到目的,也可能达不到目的。”在此,布雷蒙所言的“达到目的”,与本文所要探讨的“意图”,二者所示涵义是一致的。
意图叙事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意象、意味与意图,因此,以古代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是一种高文化浓度的文学,这种文化浓度不仅存在于它的结构、时间意识和视角形态之中,而且更具体而真切地容纳在它的意象之中,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运用意图叙事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作品,可以发现这些作品中通常包含三种不同类型的意图,即文本创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意图)、叙述者的意图(外叙述者的意图)和主要人物的意图(内叙述者的意图)。总体而言,“人物的意图体现着或小于叙述者的意图,而叙述者的意图又体现着或小于作者的意图,即作者的意图是借助于叙述者意图、人物意图而得以实现的”。
那“意图力”又当如何理解呢?“意图力”完全承接“意图”而来,简言之,即实现意图的能力。它是小说叙事的内驱动力和助推力,意图叙事理论正是通过意图力关系得以冲破小说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艰难壁垒。许建平先生参照力学原理,将意图力分为以下三类:其一为主意图力——主要人物人生意图与实践意图的形势、能力以及与主要人物人生意图相同的意图力;其二为反意图力——与主要人物人生意图相反的人物意图力(包括与主要人物意图相对抗的反意图力、与主要人物意图不一致的侧面撞击力);其三为调节力——具有调节人物意图力与非人物意图力关系的力量。但是,这种受物理学启发的分类法虽然能够清晰彰显意图力的实现态势,却并不足以完全阐释清楚“意图力”所包含的准确内容。
其实,意图力是一个内容极其复杂的学理概念,依其结构状态,我们拟从纵向、横向两个视角予以划分。纵向上包括心智力、行为力以及知识技能。毋庸置疑,对于叙事小说中渴望成功实现意图力的主要人物而言,心智力居于最高层次,他应当具备强大的意志力、开阔的胸襟、过人的胆识、优良的思想品德、天才的智慧以及过硬的心理素质;行为力也显得尤为关键,这体现在良好的性格、娴熟的人际交往能力与缜密的精细度三个方面;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技能当然亦是其意图力得以实现的有益补充。横向上,则是针对上述十一种因素中的有无与多寡而论,我们并非苛求小说主要人物具备全部因素方能实现其意图力,毕竟,缺失是常态,力求全面型难度甚大,几无可能。正因如此,当叙事小说作品中主要人物意图力不足时,叙述者的意图就适时表现出来了,施展空间也变得明显开阔起来。
二、意图叙事三原则
对于所有的叙事作品而言,既然有叙事者,自然就有接受者,而接受者正是外叙述者意图比内叙述者意图多出来的思考对象,因而,如何考虑接受力影响下的意图力变形问题,如何关注并满足接受者的需求,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围绕叙事者的叙事意图与接受者的接受意图之间的关系展开。虽然许建平先生也曾在《意图叙事论》一书中简要提及意图叙事的原则问题,但接下来我们仍将重点从意图叙事三原则着手,进而具体展开分析与阐释。
(一)反简单化原则
通常而言,实现意图的能力愈强,过程实现起来就变得愈顺利,这样接受者便于理解,印象就会更加清晰。由于读者内心不希望小说中人物繁杂、线索充斥,若依此,那么小说就应该简洁而明了,这就遵循了一般的简单化原则。但是现实中的叙事小说作品完全不能按照这样的简单化原则处理,否则,就会失去小说本身蕴含的无穷艺术魅力。叙述者期待吊足读者的胃口,为满足原始的本能欲求,采用“陌生化”等手法将小说写得跌宕起伏,给人强烈的惊险刺激之感,如此一来,叙述者即需要将小说描述得曲折神秘、纷繁复杂、模糊迷离,这种做法就是所谓的“反简单化原则”。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因与“忠厚志诚”的李甲情投意合,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摆脱老鸨的有意刁难,赎身成功,并在柳遇春、谢月朗及众姐妹的帮助下得以成行,看似杜十娘离开教坊司院后,终于可以“鲤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读者自是期待二人能够爱情美满,走向婚姻,从而结为长久夫妻。然而,叙述者不愿意这么简单乏味、平铺直叙地完结小说,不希望被读者的一厢情愿左右,偏要出现一个风流的孙富,偏要设置一个作为“调节力”的场景,“忽闻江风大作,及晓,彤云密布,狂雪飞舞……因这风雪阻渡,舟不得开”,让孙富与杜十娘、李甲相遇,进而使得李甲偏信孙富的挑唆之词,加之自己内心的惧父情结,毅然决定变卦断情。终致杜十娘为证清白,沉江而去,为情落得个“三魂渺渺归水府,七魄悠悠入冥途”的凄惨境地。这样的故事生变,自然是读者所始料不及的,但是读毕唏嘘之余,那种酣畅淋漓的阅读感,着实享受于心。叙述者的良苦用心,促使小说得以盛传不衰,读者绵绵不绝,成就不朽经典。
观其他诸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无不体现着“反简单化”原则。诚如清代学者毛宗岗对于《三国演义》的评论一般,“《三国》一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杜少陵诗曰:‘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此言世事之不可测也,《三国》之文亦犹是尔。本是何进谋诛宦官,却弄出宦官杀何进,则一变。本是吕布助丁原,却弄出吕布杀丁原,则一变。本是董卓结吕布,却弄出吕布杀董卓,则一变。本是陈宫释曹操,却弄出陈宫欲杀曹操,则一变。陈宫未杀曹操,反弄出曹操杀陈宫,则一变。……论其呼应有法,则读前卷定知其有后卷;论其变化无方,则读前文更不料其有后文。于其可知,见《三国》之文之精于其不可料,更见《三国》之文之幻矣”。
可以说,叙述者遵循“表达自己简单明了,感染读者曲折多变”的写作法则,根据自己的叙述经验,通过小说中激烈复杂的冲突去展示所要表达的意图,从而积极获取读者的关注、信任与支持,换言之,“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而小说核心人物却总是希望自己的意欲和计划实现过程愈顺利愈好,时间愈短愈好,殊不知这样的意图必然造成小说故事情节的单调与乏味,故而无法成就伟大的作品,这也正是叙述者所极力避免的,同时凸显了反简单化原则的重要性。
(二)乐喜厌悲原则
叙事作品中意图力的实现,也深受读者喜好的制约。传统上,中国读者喜欢吉利、热闹、团圆,不喜悲苦;而西方读者却恰好相反,因为深受史诗、哲学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更偏爱悲剧。对于大部分小说作品而言,就不可避免地贯彻了“乐喜厌悲”的叙事原则,而这一原则对意图力能否得以顺利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方社会是一个易于产生悲剧的社会。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悲剧,而后者又源于酒神祭祀,题材取自神话。亚里士多德第一个为“悲剧”下了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该定义涵盖了悲剧的摹仿对象、摹仿媒介、摹仿方式及摹仿目的。自古希腊始,西方出现了诸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为代表的伟大悲剧作家、诗人,产生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希波吕托斯》以及《哈姆雷特》等大批悲剧作品,西方悲剧理论与哲学紧密结合,逐渐构成了一个庞大成熟的理论体系。
我们通过梳理西方悲剧理论发展史不难发现,西方社会的悲剧叙事作品,从古希腊时期的戏剧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的小说,虽然反映悲剧主题任务的承担载体发生着变化,但这一过程中,受宗教因素和哲学思想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却自始至终被坚持。可以说,西方叙事作品实现的目的都在于,希望能够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引导我们对产生悲剧的自身原因进行否定、反思和批判。
反观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作品,很明显可以发现东西方存在的迥异取向维度。因为历来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追求以和为贵,主仁政,厌战乱,在很大程度上使百姓思想变得驯顺化,甚至诸多叙事作品的结局走向成为百姓聊以自慰的精神寄托。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国古代小说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中,哲学养分不断流失,这当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因为东西方的理论家生活在不同的文学土壤之上,所以致使他们对于悲喜剧的态度大相径庭。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和戏剧要高于史诗和讽刺诗,但是悲剧又要高于喜剧,也就是悲剧地位独尊。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所谓“情节中心说”忽视了人物性格对于受众的积极影响,而且通过对“悲剧”所下定义不难看出,他的立足点仍然是人物的行动(行为),而非人物本身,所以秉承的依旧是西方行为叙事理论的基本套路,不可能脱离开来。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列出《谐隐》篇,其中透过谐词隐语可知,刘氏最为推崇的是主旨正大的讽刺作品;清人姚华在《绿漪室曲话》中将喜剧视作“滑稽文学”,直言“文学之至,喻于上天,滑稽文学,且在天上,滑稽者,文学之绝谊也”,“绝谊”一词足见其对于喜剧的推崇备至。我们并非要争出个悲剧、喜剧孰优孰劣的所以然来,而是要强调中国人是有乐喜传统的,即使是一部过程曲折、内容伤感甚至凄惨的小说,叙述者(包括内、外叙述者)都会有意倾向团圆、欢喜结局,突出忠孝、仁义、善有善报等乐喜主题,这也是中国读者心理上最容易接受的,为了最大限度吸引读者眼球,无非将叙事过程进行反简单化处理而已。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王美娘被骗沦落为风尘花魁,因卖油郎秦钟对其惜爱有加,遂心生从良之愿;秦钟为美娘存攒银两,却不料美娘遭太守公子羞辱,以致陷入欲自尽之境地,幸得秦钟相救,千辛万苦之后,终成就美满婚姻,此乃爱情之喜。《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王员外将张廷秀过继做了儿子,并允其与二女儿定亲,但王员外大女婿赵昂却对张父诬陷迫害,张廷秀兄弟二人为救父外出伸冤,却再遭巡捕杨洪加害;后幸得恩人相助,兄弟二人登科高中,返乡之后拆穿赵昂阴谋,救父出狱,最终兄弟二人家业兴旺,家庭美满,此乃亲情之喜。《老门生三世报恩》中,老门生鲜于通三次成功考取功名,蒯遇时也是由最初的“爱少贱老”到最终发出“真命进士”的慨叹,成就师生之谊;鲜于通为报蒯公“三番知遇之恩”,先是在蒯公被大学士刘吉迫害时及时周旋相救,继而为其公子蒯敬共积极伸冤,最后供其孙蒯悟读书,此乃知恩图报之喜。这样的叙事小说作品不胜枚举,严格而言,它们不同于“滑稽”意义的喜剧,但从意图叙事理论视角分析,当归入喜剧。亚里士多德这样谈及悲剧和喜剧的区别,“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这样的总结留足了供我们质疑和探讨的空间。
(三)顺乎天命原则
天命,简言之,即上天的意志,是上天主宰下的一种自然力。人们的命运受其操控,因而此时的意图力也必须服从于天命原则。
天命观念由来已久,顺天意在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人们不敢轻易亵渎,深知不可违忤逆从,否则会招致各种祸端与不详。《书·盘庚上》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载:“且人之生也,贫富贵贱,夭寿贤愚,禀性赋分,各自有定,谓之天命,不可改也。”清代王夫之《张蒙注·诚明》载:“是以天之命,物之性,本非志意所与;而能尽其性,则物性尽,天命至,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无不通。”叙事作品中人物意图力的实现,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服从或听命于自然天命法则,给人一种“只可远观”的无奈之感。
《三国演义》第一百三回《上方谷司马受困五丈原诸葛禳星》中,诸葛亮精心设计,密令马岱在葫芦谷内外造木栅,掘深堑,积干柴,搭草房,伏地雷;命令魏延佯装讨战,诱使司马懿出战,进而引入葫芦谷;吩咐高翔运用木牛流马装米备粮,故意让魏兵抢去,意在迷惑魏军。一切准备就绪,生性多疑的司马懿也果然如诸葛亮预判,中计被困于葫芦谷中难以逃脱,司马氏三父子抱头痛哭。就在诸葛亮得意,要将司马懿连同魏军活活烧死之时,却万万未料及,“正哭之间,忽然狂风大作,黑气漫空,一声霹雳响处,骤雨倾盆。满谷之火,尽皆浇灭;地雷不震,火器无功”。司马氏父子因此得以成功脱逃。也怪不得作者假借后人口吻,如此百般感叹:“谷口风狂烈焰飘,何期骤雨降青霄。武侯妙计如能就,安得山河属晋朝!”
对于主人公诸葛亮而言,他的意图自然是认定司马懿“此番必死”,但置司马氏于死地的意图受到了属于非意图的意外事件阻遏,最终以失败告终。应该说,诸葛亮的意图力在此处是完全失败的,天降大雨根本不是其本来意图,他输给了不可预料也无法战胜的天命,也不得不接受自己意图力失败的现实,自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仔细分析,我们亦可得知,导致诸葛亮意图力注定失败的还有一个“人为的天命”——叙述者的意图,作者罗贯中为了自己的意图需要,不得不牺牲小说主要人物的意图,他要为后面的十七回做铺垫,因此,即便在过程叙述中,凭借诸葛亮的计谋,读者认为司马懿必定丧命葫芦谷,但是读者同主人公一样,都未能料及司马懿因天命救赎而大难不死,这要归功于叙述者及其掌控的“天命大权”。所以,诸葛亮葫芦谷火烧司马懿的意图是注定失败的,叙述者罗贯中意在表达诸葛亮的智慧与天命不可违的愿望,即司马氏父子不死于诸葛亮之手。
然而,这种自然的天命观,假借叙述者人为操控,属于作者叙事意图未能体现主要人物人生意图的情况,这种天命原则所产生的小说叙事个性化特点是非常突出的。诚如清代文康在《儿女英雄传》第一回《隐西山闭门课骥子捷南宫垂老占龙头》中对天命原则发自内心的顺势表述:“宦海无定,食路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里了,倒不如听命由天的闯着作去,或者就这条路上立起一番事业,上不负国恩,下不负所学,也不见得。”
三、叙事作品的个性化问题
意图叙事理论研究在国内虽然暂未完全普及开来,但是其蓬勃的生命力已经开始显现,研究者对该理论的学理个性研究逐渐开始倾注心力,意图力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个性化的关系问题也是始终绕不开的着眼点。



但叙事作品的个性化问题才是我们研究意图力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时所关注的重点,我们仍旧以中国古代小说为例,拟从以下两个视角展开论述:小说内叙述者(主要人物)完成意图的个性化;作者和外叙述者(叙述者)意图实现的个性化。
(一)小说内叙述者完成意图的个性化

许建平先生经常列举《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例子来阐释意图叙事理论,我们也不妨移花接木一番。孙悟空成为花果山之王后,突然心生众猴生命无法长久的忧患意识,于是听从老猴子的意见,决心“务必访此三者(佛、仙、神圣),学一个不老长生”,在这最初意图实现过程中,孙悟空展现出了超强的意图力,包括坚定成功的意志力、超常的智慧和悟性、坚韧的性格等,这些确保了“猴王长生不老”意图的顺利实现。第二个意图“花果山众猴长生不老”实现起来,阻力也不大,通过斩妖除魔、练兵自卫、找阎王勾去生死簿上所有猴子的名字等过程如愿达成。而借助作者“大闹天宫”情节的设计,孙悟空开始了第三个意图——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普度东土大唐众生。这也成为孙悟空的人生意图,但是该意图的实现过程难度非同小可,中间需要遭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正是凭借孙悟空持久的韧性、迎难而上的胆识、豁达的胸襟、超人的心理素质、机敏的智慧、强大的技能等意图力的综合作用,才实现了他将佛经传入东土使大唐众人长生的最终意图。八十一难,难难惊心,但是正是这些磨难才将孙悟空意图实现的个性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无可挑剔。
但小说中并非个个人物都完美,当然也并非只有人物的特长才能促使意图实现的个性化,小说人物的缺陷(失)同样也能表现个性化。《水浒传》中,武松正是由于多疑、爱面子、易冲动的性格短板,才使他不愿意接受别人善意的劝告,甚至一度怀疑别人谋财害命,拿大虫吓唬他。当看到“榜文”,确认景阳冈上有老虎存在时,担心折返回去遭人耻笑他不是好汉,只得硬着头皮上山。可见,形单影只上景阳冈是出于无奈,此时并不存在打虎意图。当真正遭遇老虎时,武松的性命受到威胁,故而才借助条件反射,瞬间不自觉地将打虎变成自己不得不去面对的意图,当然这个意图最终得以成功实现,也才有了后面我们所熟知的故事延续。通过分析得知,武松本身性格上的缺陷,非但没有使小说叙事限于死寂沉闷和平铺直叙,反倒从另外一个视角开辟了故事向前发展的新路径,使得武松完成打虎意图的个性化得到完美呈现。除此之外,《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好色、潘金莲的淫乱,《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奸诈、司马懿的多疑,《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多愁善感,《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金玉奴的忍让妥协等,无不是借助人物性格的缺陷(失)来实现各自意图的个性化。
可以说,内叙述者诸如豁达的胸襟、过人的胆识、良好的交际能力、渊博的知识等都可以实现意图的个性化;同样,狭隘的胸襟、粗心的性格、拙劣的技能、弱化的意志力等,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人物意图的个性化。特长与缺陷(失),二者皆是表达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作品中人物完成意图个性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小说作者、外叙述者意图实现的个性化


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主人公文若虚仗着自己有些才华,不肯用心经营家业,致使家道衰败,虽有心做生意,却也不走运,卖个扇子却难得遭遇持续阴雨天,扇子俱因受潮而废,人送外号“倒运汉”。后来,跟随张大等人走海贩货,却开始出现撞运之兆,船上没人理睬的“洞庭红”橘子反倒阴错阳差卖了好价钱。如果此时,货船顺利返回大陆,肯定就会陷入平铺直叙。于是,叙述者让他们遭遇狂风巨浪,逼货船驶向荒岛,而此时就会引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迫切想知道在荒岛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文若虚因为好奇,继而伤感,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大鼍龙壳,如获至宝拉到船上,遭到众人的嘲笑和讥讽。后来到了波斯胡,一个叫玛宝哈的主人愿意高价收购这件鼍龙壳。这又让读者进一步产生疑问,这东西有什么价值和奥秘,能够让富有的玛宝哈这么看中?随着他本人的一番解释,众人方知壳内藏有24颗珍贵夜明珠,疑团方才最终得以解开。叙述者的这一番叙述,渐渐使得文若需的人生意图得以最终实现,靠着五万两白银,最终成家立业,一个“倒运汉”终究变成“转运汉”!
由此我们方能明确叙述者的主要意图,即感染读者的同时,能够表达自己。当然,这两个意图实现起来却是极易产生冲突的,因为感染读者遵循隐曲、激烈、陌生的复杂原则,而表达自己却是遵循直白、明了、清晰的简单原则,也即构成前面提及的矛盾逻辑构成问题,而这也直接催生出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使得故事曲折多变,情节引人入胜。外叙述者的意图个性化最终促使人物意图实现的个性化,这样的情节设计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作品中可谓俯拾即是,无需一一赘言。
结 语
意图力与小说叙事个性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需要在意图叙事理论架构之内仔细探讨的复杂问题。小说内叙述者的人生意图渗透着作者和叙事者的叙述意图,各种悬念、冲突、矛盾的设定以及作为调节力的特定场景的设置,无不是作者和叙述者意图的着力体现。小说作品中人物的意图力实现过程顺利与否、个性化体现充分与否,都深受作者与叙述者意图力的共同操控,最终取决于作者的主观叙述意图。

注释:
① 许建平、在元《意图叙事说》,《兰州学刊》2014年第11期。
② 许建平《叙事的意图说与意图叙事的类型——西方叙事理论中国化的新思考》,《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③ [法]克洛德·布雷蒙《叙述可能之逻辑》,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
④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⑦ [清]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303页。

⑨⑩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