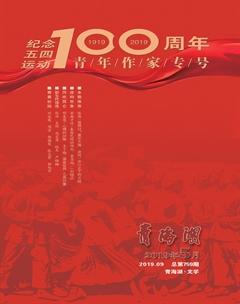土房子及其他(散文)
刘永霞
土房子
1997年我出生在靠近河滩的一间土房子里,而后的数十年里,和庄廓院里的芍药牡丹一同长大。牡丹在时间的催化下日渐丰满,用一棵树的姿态占据了庄廓的一角,在干涸的土地里日复一日地延续着生命。芍药也每年春天发芽,夏天开花,冬天就成了一墩枯枝,被爷爷点一把火烧了。
土房子在我们一家人居住的时候,凡是不种菜不堆放杂物的地方,都被我们过来过去地踏成了平滑而坚硬的地势,虽然屋子的角落里有几个老鼠洞,台沿底下有几个蚂蚁窝,漏瓦槽下面有一个被雨水冲刷的浅坑,但是吹风或者人走过的时候,几乎扬不起一丝尘土。
我们身上的尘土来自于庄廓以外的田地、小路,还有烧柴、麦捆和一天也离不开的农具。
都说庄廓是养人的,其实是人在养着庄廓。后来,我们离开了,庄廓在几年不住人的情况下扬起了一星半点的土。
那些扬起的土里有我奔跑的脚丫,也有机械辗过的痕迹。它们在没有人的空隙里毫不客气地落在土房子的角角落落里,包括曾经视若珍宝的面柜上,和散发着霉味的粮食上。它们才不会管土房子孕育了几代人,才不会理土房子经年久月的存在,没有了人,一切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土房子里出生和逝去的人就好像是院子里一季一季长出的植物,总会有新的一部分去替代。
庄廓院里几乎没有树,家里的老人认为院子里兴土是不吉利的。芍药牡丹是母亲嫁过来时从娘家带过来的,起初种在院子里的时候也还是幼小的苗,用一两间土房子构成的庄廓显得有一些空旷、寂寥,即便是栽种一些作物也觉得院子缺少了灵性,于是牡丹栽种也没费多少功夫。只是不曾想牡丹的根一扎便是二十几年,人也没想过会在牡丹之前离开这个院子。
庄廓院在不住人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老化,椽子间存在的不再是灰尘,是一些密密麻麻的虫眼,它们用不同的姿态表示着土房子被丢弃之后的面目。有时候梦里出现的土房子与眼前是截然不同的。墙围子、面柜、陪嫁箱子,好像这些东西比土房子存在的时间更要久远。
芍药牡丹在没有人照料的时间里开得比人在院子里时还要繁盛,好像花取悦的从来都不是人,是日复一日无法回得去的土房子。土房子门槛前打的地坪,在日照和风雪的作用下,显示出了岁月该有的痕迹,那一条条裂缝里长出的杂草好像是在责备人的忘却。牡丹树上凋敝的花朵不断地增加,新的枝丫要等到来年暖和的日子才会成长,庄廓墙的豁口由小变大,直至里面的人能看到外面的事物。芍药的根好像伸进了院子的角角落落,包括那个我出生的土炕。地坪四分五裂,土炕中间的缝隙里可以看得见一层一层的炕灰。
从远处看土房子,破败和不堪即刻充盈着大脑。一排排新式建筑物中突兀的并不仅仅是建筑的落后,好像折射着某种人的存在和思想。土房子最先失去的是土,是多年以前整个村庄里的人一锨一锨撂上去的土,而后是院子里的一些作物,一些人离开之后像解脱了一样疯长的作物,那些作物终究没有明白欲速则不达。牡丹胜似往年地开放着,枯枝更胜,如地壳运动时的裂痕。
终究,还是失去了土房子。也许跟一场雨有关,也许是久不打理的缘故,也许土房子的灵气被芍药牡丹占据了,谁又能说得上呢。
学 校
我知道终究有一天我会离开熟悉的地方,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在陌生的环境中营造熟悉的氛围。这世上的许多存在无法用永恒来定义。
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想着自己终究有一天会再次来到这个地方,那个经常背书的南墙角我看都没看一眼就离开了。不曾想多年以后一个下雨的黄昏,南墙和学校被庞大的机器推翻了,村庄的孩子们奔向了亮堂的大教室,留守学校的孤寡老头也被遣送回了自己的村子。只有校门口的那一渠水源源不断地穿过学校流向庄稼地里。
推翻的学校仍旧是学校,成了幼儿园,只是去上学的幼儿寥寥无几,许多孩子随着父母走进了城市的房子里。曾经那所庄严、古老、破旧的学校,一瞬间成了村庄最不起眼的地方。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孩子在校门口的荒地上玩,他们手中的玩具不再是玻璃球、弹弓,而是清一色的智能手机,手机里有什么内容谁也说不上,孩子们为了拥有一部高端的手机也会和家里的人争吵,甚至不去读书。孩子不断地成长,残破的土墙好像越来越低,童趣和天真也离孩子们更远了。
镇上的小学放假时,是村庄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背着大包小包等着父母接回家,父母在学校外面铁栏杆缝隙里寻找自己的孩子,有一两个相似的背影闪过的时候,他们也会误以为那是自己十几天没有见到的孩子。来接孩子的父母从来不会在这一天有事情,他们把孩子和东西带回家,做上热腾腾的饭菜,他们问孩子们学校里的生活状况以及学习情况。
在放假的日子里孩子们像风一样回到自己的家里,偶尔的某一天也会陪父母拾掇一下地里的庄稼。庄稼从来不会等农人的时间,学习也不会等懒惰的孩子,有时候孩子的成绩与镇上的孩子相比,也会有一些出入。
后来,村庄里几乎没有了独立小学的存在,孩子的脚步也随之消失。走在村庄的时候,孩子少了,欢笑也缺失了。
无 题
村庄具体是什么时候被命名为村庄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村庄里的人是几辈子住在这里的,村庄里的一副副庄廓和园子就是最好的佐证。
那些庄廓土墙上的纹路经年被风雨洗刷,墙面上留下的沟沟壑壑足以证明时间之长。园子里一季一季生长的冰草和灰条似乎是多年以前先人们播撒在田间的种子,在时间的累积下走过田间地头,奔向院子,在院子之后是庄廓,庄廓之后就从庄稼人的眼际消逝。园子里的树才能真正证明这个村庄的久远,比如梨树、苹果树等,尽管这些树上已经很难再结出像样的果子,它们的存在足以证明黄土地上曾存在过一些物种。
走过村庄的时候,倚靠着河流出现了一些小楼房,如果真的想走进去看一看,房内的世界早被一层一层的红砖青瓦包裹起来了。我开始不知道这个村庄里居住的人到底有多少,凭借着我所听见的大部分人已经搬进了城里的楼房里,凭借着我所看到的大片的庄稼地被流转出去,凭借着如今政策占地占房的好处,一些不肯改变居所的传统的农人开始转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在村庄里行走的时候很少能看到村民,连吃草的畜牲都看不到。
村莊的建筑好像有一些改变,有时候对农人来说,田园风光与高楼大厦相比,后者更加接近于生活。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对村庄而言都是可疑的,甚至是可恨的。最初的时候,人们以能否成为庄稼好手来评判一个农人的价值,后来以从外面带回来多少钱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干。只不过,有时候,恰恰是这些无用的东西,帮助人们度过了艰难时光。
该去的一定会去,想留的也由不得人。